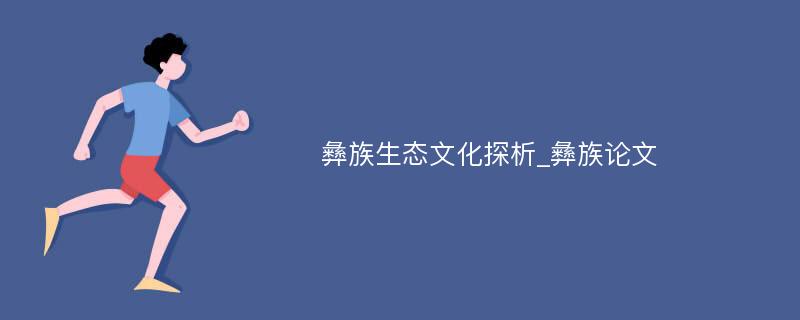
彝族生态文化探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彝族论文,探析论文,生态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110(2002)05-0119-04
生态文化指人类社会所形成的尊重自然、保护环境的物质技术手段、制度措施、生产生活方式、思想观念和价值体系的总和。包含着物质文明、精神文化、制度文化三个层面。彝族分布在山区,从事粗放的农耕生产。他们所处的地域、自然条件,以及生产力发展水平,决定了他们在实践过程中对人与自然界相互关系的认识水平,从而形成自己的生态文化。
一、对树木分类管理的文化传统
彝族大多分布在山区,对山水林木有特殊的亲切感,自古以来,形成了一套管理林木的办法,是其生态文化中最为闪亮的部分。
公有林 清朝咸丰元年(1851年),大理市吊草村彝族,就村寨公有林立了一块《永远扩山碑记》,其碑文云,“君依山林则所重者,林木也。上有国家钱粮出其中,下而民生衣食出其中,所关诚大也。讵得不为之经心哉!今有远近之人,不时盗砍,若不严守保护,恐砍伐一空,不惟国课民生无所赖,即军需炭觔从何出乎?故捐资生息以为守山之用,则其利公而溥其风正而醇也。故垂之贞珉,以图永久是为记。”[1]其文言简意赅,阐明了林木对人的重要性——“国家钱粮出其中”、“民生衣食出其中”。因为有人“不时盗砍”,将会导致“国课民生无所赖”。必须加强保护林木,其办法是“捐盗生息以为守山之用”。采取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捐资方式,委派人员守山。
武定大洗衣村彝族习惯法规定:任何人在公有山林盗砍一棵树,被罚一头牛,全村人同食这头牛的肉;村寨里各家各户轮流当“山头”(即护林、守山的人),守护公有林、家族占有林,其职责是护林、防火、防盗。对于违反公有山林管理使用习惯法的人要给予惩罚。道光年间,景东彝区习惯法规定,“凡村界内,无论公山、私山,不得擅行砍伐,违者照乡规罚银:一禁纵火焚山,犯者罚银33两;二禁砍伐树木,采枝者罚银3两3钱,伐木身者罚银3两3钱;三禁毁树种地,违者罚银33两;若有在公山砍柞把者,每把罚银33两。”[2]
龙树 如滇南彝区村寨内或附近都有一片树林,其中以枝繁叶茂的一棵为主,用石块打制象征龙宫的器物放在这棵树下。每年在此祭龙,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禁止人攀爬或砍伐龙树。龙树在今后屏县龙朋、哨冲、龙武等乡的彝族村寨还多有保存,至今依然古树苍天。滇东北镇雄塘房区一带彝族也敬奉龙树,适时举行祭祀活动。
护寨树 巍山的龙潭村,在村子东边近村口的大路傍边,有棵高大的多纡树,有2人合围粗,是该村的护寨树。自古及今,每逢二月八、火把节、七月半等节日,村民都要来祭祀树神。武定县大洗衣村,寨内坛上的树也是护寨树。石屏的竜黑村,也有一棵护寨树,树干粗大,须2-3人合围。树荫下,人们聚会,交流信息。护寨树一律禁砍。
山神树 巍山的龙街彝族不准砍、爬象征山神、土地及祖宗的各种神树。这些神树即使在十年动乱中,也没人敢碰一下。彝族大部分居住在山区,其社会活动多受自然力的支配,他们对各种自然界的力量都存在着敬畏心理,并由此产生对自然力的崇拜。他们认为山神主管风雨雷电以及各种灾害。人们要消除自然灾害,求得清洁平安,六畜兴旺,获得丰收,就要祭祀山神。彝族群众认为山神住在气势雄伟、长满乔木和灌木的山上。因此,祭祀山神的树或树林不准砍。如有犯禁者,要送交官府论罪。如道光十一年(公元1831年)正月十七日,武定那氏土司辖区内姚正清、林炳芳等二十余人来以德抢砍古树三十二棵。“押解赴辕,严究追价给领,以安神树而救性命”。[3]
风水树 从清代武定那氏土司遗留下来的档案材料看,当地习惯法十分重视保护风水树。如茂连乡井衣基边夷地界内所蓄养的风水树,“自祖及今已历一百余年之久,非数载所能培养。凡相地无一轻为砍伐。”[3]武定大洗衣村正前方的山形象“虎”,村民把这座山上的树木视为“虎”的皮毛,当地习惯法规定,严禁砍伐该山上的林木,甚至不准拣松毛。违者合村老幼公议重治其罪。滇东南石屏的黑村正前方于建寨时即栽种了一片柏树,村民视之为风水树,严禁采伐,至今依然一片苍翠。
水源林 巍山地区小潭子村后山有小黑龙潭,清代光绪年间立有对水源林的保护碑,“禁砍树木,禁放牲畜,倘敢故违,罚银壹佰”。[4]因而这里至民国年间依然“苍木擎参天,茂枝蔽覆地,绿茵遍处生,藤葛攀树枝;青生显苍翠,怪洞起涌泉。”[4]祥云县东山彝族乡思多摩村有关水源林的习惯法规定:“有龙潭一路树木,沟上留二丈之地,沟下留一丈之地,勿得妄自砍伐。若有私自偷砍者公凭重罪。”[5]武定县大洗衣村禁砍水源林,如有违犯给予重罚。滇东南石屏县哨冲彝族村,有一地名“老可拉”,该处龙潭昼夜喷涌,当地习惯法禁砍水源林,至今依然树木丛生,灌木、乔木青翠可爱。
彝族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受“实用理性”原则的支配,反复实践、交流后形成了对客观世界发展变化及生态环境保护的粗浅认识。意识到林木作为整个自然界陆地生态系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保护自然界生态平衡过程中占有重要地位,起着核心作用,森林有很强的涵养水源保持水土的作用。对此,彝族在社会实践中有过亲身体验并不断总结,使这方面的知识得到积累,认识逐步加深。《彝汉教育经典》上说:“山上长的树,菁中成的林,亦不可滥伐。有树才有水,无树水源枯。”[6]表明彝族先民对生态系统的平衡及相互间的关系的认识不断加深,对林木有一种朦胧的保护意识。
二、精神文化中的生态文化
彝族先民的“图腾”崇拜习俗,蕴含着珍爱动植物的思想情感。崇尚其旺盛的生命力和刚强勇猛的性格。如武定一带彝族自称“罗罗”(虎族),男人自称“罗罗颇”(公虎),女人自称“罗罗摩”(母虎)。在彝族社会生活中的人名、地名、物品等以虎命名的比比皆是,崇虎而将自己打扮成虎的模样(将虎符号搬到自己的饰上或穿虎皮等),这在彝族中较为普遍。楚雄、武定彝族幼儿穿虎头鞋、戴虎头帽,其虎头帽两耳耸,额上绣一王字,眼鼻分明,尤以嘴最为形象,缀以两银雪白的獠牙、突出了虎的勇猛和威严。该地彝族妇女的围腰上部是一张白布底的虎口,两边露出两个虎爪,中间绣上马樱花或马兽花簇拥着的虎头。牟定、南华等县彝族老人至今仍有穿虎头鞋,孩子戴虎兜肚的习俗。武定风氏土司后裔那氏土司的“虎袍”堪称彝族虎服饰之精华,它集刺绣、挑绣、堆花、打子花、扣花、切针、贴布多种刺绣手法于一体,该袍前后均绣有一只猛虎图,穿上虎威赫赫。虎出现在服饰上,蕴含着驱镇邪魔的文化含义。[7]透过这些文化事象,蕴含的文化含义就是人与动物的和谐相处,人与动物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
像其它农耕民族一样,彝族有一套农耕祭祀礼仪,宣扬祭农务总神之灵验:“农务之总神,献酒及他阿,过了些日子,到耕耘之日,垭耕不遇风。原耕不失露。土边蛇不屈,田外鼠不窜。护神好来护,禾秀蝗不害。守神好来守,见守雀不临。田大秧不费,工人腰不疼。禾长就出穗,出穗就结谷,结谷就成实,收割就逢晴,簸净遇风力,大仓满,小仓盈。”[8]人在整个生态系统中,虽然可以发挥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但人力有时尽。转而仰农务总神之力,能获五谷丰。
人类“灵魂”观念产生之后,从而推想到世界上万物都有灵魂,诸如日、月、星、山、川、巨石、怪树等都有所谓神灵。把自然界的一切人格化,幻想任何自然物都有一种超自然力量在主宰,自然界中无处没有神灵的存在。比如,凉山彝族对自然界的众神中最崇敬的是山神,认为风雨雷电都与山神有关。这是由于他们的生产与生活都和山区息息相关,所以把山视为神圣的所在。毕摩的《请神经》中所列举的几乎全是山神,而各地各家支的山神也不相同。对于强有力的天神、地神、山神等,则要举行祭祀,祈求降福庇佑。有名目繁多的祭神仪式,比如,“芝固”是为了祈求丰年,逢耕种、收获时举行,届时延请毕摩作法念经,请诸山神和五谷丰登神降临。“则士”是防雹灾,毕摩之巫术。由一村或几村联合举行,群众需出鸡、酒等物,送五至十五人和毕摩一道上山,打鸡烧熟供敬神人,然后毕摩将鸡翅膀、鸡头、鸡脚拿在手中念防雹经,祈求免遭雹灾,获得谷物丰收。祭祀山神和五谷丰登神,是对自然崇拜的表现。[9]参与整个生态系统的,有自然界的日月星辰、山川河流,还有人格化了的神,从而彝族的生态文化中包含了浓郁的宗教迷信色彩,拨开宗教迷信的面纱,透露出人们企盼生态良性循环的美好愿望。
三、生产生活及社会活动中生态文化
彝族村寨多建在当阳的一面,万物生长靠太阳,人也不能违背自然法则。滇南彝族住房多为土掌房,房顶用泥土覆盖并夯实,可遮挡风雨,可凉晒谷物,简易实用。房前屋后栽种果树,春华秋实。农田、农地就在村子附近,田间沟渠交错纵横,随节令变化栽种不同的农作物,山地则主要用于种植旱地作物。
滇南一带彝族有使用农家肥的传统,用猪鸡牲口的粪便肥地,他们还知道采集一些植物的嫩叶放到毛厕中过一段时间就成为肥料。村民把干枯的树枝和枯草堆在一起外面用土覆盖经过燃烧成为上好的肥料。用于种荞、麦、蔬果,苗长得肥果实饱满。土地越栽越疏松肥力也不会减弱。有的人家还把猪、牛等牲口的骨头收集起来,放火焚烧碾碎,用来栽蔬菜。在调查中村民还告诉我们,科技含量高的化肥,其反作用也越来越大。长期使用化肥的田地,粮食产量虽然有所增加,但土质变硬,土地的肥力反而下降,前景令人堪忧。农家肥这种原始的肥料,一直受到村民重视。再则,彝族村寨地势较高,水田分布在村子的不远处,冲刷村子的雨水汇集的肥水顺势注入田地里,增加土地的肥力。彝族还有一种田称为“雷响田”,人们在田地周围开挖沟渠,一旦下雨,雨水顺沟流入田里,便可栽种稻谷。因此,他们利用自然,但没有破坏自然。
古代史书、方志上多有彝族在山区从事刀耕火种的记载。其实刀耕火种有一定的规矩,并非毫无节制地砍树烧山。选择合适的地点,坡度不宜太大;地面上多为杂树丛;在放火烧地时,要把枯草树枝集中在地中央,选择风小的日子焚烧,尽量避免野火四处漫延。另外,刀耕火种地一般采用轮歇休耕的办法,有的地耕种一年后轮歇,有的地耕种2-3年,轮种不同的作物后让该片土地轮歇。因此,刀耕火种包含着人们对自然资源合理利用的冷静思考。时至今日,滇南一带的彝族仍是如此做法,尹绍亭在《刀耕火种志》中深入论述,称刀耕火种蕴育的农耕文明,确乎有一定道理。当然这种生产方式现已不宜提倡,但它的出现,毕竟是彝族及其他民族的先民在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一种选择。
功利思想,政策导向,促使彝族地区的生态环境急剧变化。比如,石屏县哨冲、水官冲一带的彝族,直到解放前村子周围还有茂密的森林,建国后,大炼钢铁的时期,人们毫不情愿地砍倒了一棵棵松树做燃料。后来修通了公路,又大量采伐林木。至今村寨周围大多只是一些低矮的小树丛,村民盖房子的木材,要到很远的地方去砍。划分为责任山以后,有的人家在自己的责任山上种杉树,这种杉树经济价值高。虽然出于功利思想,但这种自觉行为,对改善生态环境有积极的作用。村民用来做饭、烤火用的主要还是木柴,习惯上他们主要砍低矮的杂木,一般不砍松树,每户人家的用量也是不可小算的。尤其是近年来大规模种植烤烟,以木材作为烤烟的燃料,消耗掉的木材数量惊人。有的村民说,再烤几年烟树根都要挖完了。种植烤烟虽可暂时解决经济困难的问题,从长远看,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其负作用也是不言而喻的。如何处理目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的相互关系,村民与当地政府还没有清醒的认识。
总之,彝族生态文化中的有关制度和习俗,是在生产力水平和科技水平都较低的情况下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朴素认识的反映,具有一定程度的科学性和科学内容。但只能算直观的、朴素的的观念。按现代科学实证性和精确性要求看,彝族传统的自然生态观尚不能对人与自然的复杂关系作出全面、精确的科学解释。从彝族传统生态文化的制度层面看,多数是以乡规民约和风俗习惯的形式体现出来的,离现代文明所要求的规范性、系统性和确定性还有较大的距离。现代彝族地区的人们所面临的生态问题的越来越艰巨、严重、特殊、复杂,其传统文化远远不能满足彝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必须在继承传统生态文化合理内容的基础上,从总体上实现对传统制度文化内容的发展和超越。必须按照现代制度文明的要求,进一步提高制度文化的水平和层次,才能适应当地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我们认为在新的历史时期,彝族地区的物质生产方式要实现由传统粗放型向现代集约型转变,发展生态经济和生态产业。建成山水林田路综合开发的生态系统,继续发挥使用农家肥的传统,培肥地力,用养结合。有组织、有计划地开展人工植树造林,采取“谁投资,谁管理,谁受益”的办法。还可适当推广种植经济林果,增加收入。只有经济收入增加,人们才可能投入更多的资金用于保护生态环境。最后,彝族传统的保护山林的做法,由村民捐资聘请专人看护山林,做到保护与适度开发相结合建成良性循环的农业生态系统。只有这样,才能促使彝族地区人与自然相互关系的协调发展,推动彝族地区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收稿日期]2001-11-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