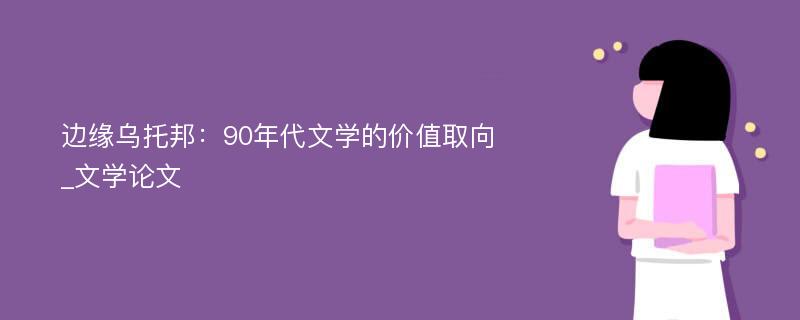
边缘乌托邦——90年代文学的一种价值定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乌托邦论文,边缘论文,年代论文,价值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1993年,文学界发生了两起极具启示意义和象征意义的“经典性”事件,一是《废都》的出版,一是顾城之死。尽管这两起“文学事件”经过了精心的包装后的“商业性轰动”模糊了它们的本真意义,然而透过华彩的商业迷雾,我们仍可发现其重要的“文学意义”。这相继发生的两起事件,明确地宣布了一个“文学现实”:文学已经彻底告别了“中心”,走到了边缘。
当然,告别“中心”并不都是主动的、自觉的,走向边缘也不完全是轻松与愉快的。饶有趣味的是,80年代曾是那样差异明显的两类作家到了90年代竟在边缘处汇合,这使得1993年所发生的这两件事更为耐人寻味。或许可以说,在90年代走向边缘已是文学必然的定位,区别仅在于,不同的“文学人”对这次文学位置的变迁所持的态度及界定的差异:是“回家”、“回到常态”,还是被遗弃。
因而,一个问题被严峻地提了出来,即,文学走向边缘之后,是否意味着既往被认定并被认真地实践过的价值已经彻底失落?文学是否具有建立新价值的可能与必要?更重要的是,处于边缘地带的文学,该如何进行自己的价值定位?
问题是迫切的。一方面文学已经明白无误地走到了边缘,文学只能在边缘处生成和运作,至少在当下,任何将文学“拉”回到“中心”的企图都是徒劳的。另一方面,文学又不能在“无价值”状态中取得生存的合理性,而价值的“空虚感”已经弥漫在文坛,阻滞着人们的价值探求。无疑,《废都》和顾城之死会加剧人们的悲观情绪,因为它们从两个方向对边缘状态的文学的价值提出了似是有力的否定。顾城和贾平凹,一个是主动地撤离“中心”,一个是为“中心”所遗弃,然而,结果是同样的悲哀:前者在边缘处不住地“寻找”,无尽地流浪,终于未能获得心灵的妥贴与超越,绝望而自杀;而后者则是在被“遗弃”后,价值体系归于崩溃,落入自暴自弃式的“价值难民”的行列。《废都》中的庄之蝶,这个被视为“市宝”的“著名作家”,几乎已全盘放弃了属于他那样年龄的作家的一切价值理想,只得在与四个女人的做爱中显示自己最后一点价值(显然,这并不是惟有作家才能具有的独特价值)。我们当然不能简单地在庄之蝶和贾平凹之间划等号,但庄之蝶与贾平凹在价值追求中“部分”重叠,似乎是有依据的。昔日的“辉煌”失却之后的“价值真空”无疑是令人痛苦的。
显然,这两个令人悲哀的“边缘成果”会打击在边缘处重建文学价值的努力,甚至会“复活”某些人的“中心化”梦幻,但我们应冷静思考的是,这两个极端的事件是否足以否定文学在边缘处进行价值重建的努力?
对此,我们不必过于悲观,尽管重建是艰难的,但并不是说80年代文学处于“中心”时所建立的价值才是文学的唯一价值,舍此便意味着文学价值的失落,并以此为标准进而否定其他一切价值。这在价值多元化的90年代显然是行不通的。
二
90年代文学的边缘状态,并不是在一夜之间被强加的,也不是时代/社会对文学的“惩罚性放逐”。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始于70年代末的一系列文化/话语裂变的必然产物。
整体意义上的话语是一个系统,它由权力话语、精英(知识分子)话语及大众话语构成。但在80年代以前,这三套话语被人为地挤压在一个平面上,真正存在的是权力话语,而精英话语和大众话语是虚拟的,它们不过是提供了一个能指,而所指则由权力话语规定。精英话语与大众话语的能指/所指是断裂的,所指不是立足于本文、生成于本文的所指。而且,所指的“权威性”,又反过来阻塞能指的多样性。这种现象不仅在“十七年文学”、“文革文学”中存在,即使在“伤痕文学”中也大量存在。卢新华的《伤痕》将一个巨大的能指可能具有的丰富所指全部湮灭,只剩下一个“权威”所指——揭批“四人帮”。这与80年代中期史铁生的《我那遥远的清平湾》、梁晓声的《今夜有暴风雪》、孔捷生的《大林莽》构成了有趣的对比。后者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个能指中生成了远比《伤痕》丰富而沉甸甸的所指。这些作品以一种深层次的反思取代了“哭诉式”的政治、道德判决。
当代话语的第一次裂变大约发生在80年代初。精英/大众话语从权威话语中裂变出来,话语的平面状态被打破,精英/大众话语开始获得话语权并逐渐形成相对独立的话语系统。当然,它们远未斩断与权威话语的联系,也没有完全摆脱权威话语的操纵与干预。但是,经历此次话语裂变之后,精英话语/大众话语的缝合状态依然存在,这表明真正获得话语权的只是精英话语,大众话语只是话语的承受者。精英话语的操纵者——知识分子(作家)以一个拯救者、先觉者、精神导师的身份出现在大众面前,试图给世界一个永恒的、终极的解释,给困扰大众的一切问题以一个终极的解决,把自己想象为大众的“合法”的、别无选择的“代言人”。显然,“代言人”不过是其制造自己身份的“合法性”的一种表述策略,一个更合乎实际的指称,应是“精神布道者”。而大众是沉默的、失语的,只有一颗“迷途羔羊”般期待拯救与指点的心。因而,精英(知识分子)在取得话语权之后,却剥夺了大众的话语权。如果说在权威话语中,精英(知识分子)只是一个“雇工”,那么在这次话语裂变之后,却从权威话语手中“接管”了大众话语,并使大众成为忠实的“听众”,接受其“启蒙”,接受那些无法兑现的承诺。诚然,精英话语的这种“仿权威”地位,在一定意义上可以看成是“历史选择”的结果。但是,不应忽略的是,其对历史/民族/人民的“代言”,不过是他们的知识/意识形态表达,而这种表达,与其所自命的地位是不相称的。说到底,这只是“个人的”声音,而不是“历史之音”、“民族之音”、“大众之音”。他们的解释远不是“终极的”,他们开出的“药方”也不是“万应的”。大众所接受的,只是一套经过精心编码的话语策略,柯云路的《新星》就是一个饶有兴味的例子。在这部曾引起“洛阳纸贵”般轰动的作品中,作者将一个改变民族命运的浩大而艰巨的工程“改写”为“黑猫警长式”的卡通故事,“戏剧化”地渲染了大众对李向南这个当代“包公式清官”的迷信。更为有趣的是,小说将李向南塑造为解决问题的能手,一切问题能否解决,只取决于他是否“在场”。但李向南的问题谁来解决?这是当代文学中“英雄们”常常遇到的问题。通常的解决办法是“萧长春式”的,即找“上级”并获得上级的“指示”、“肯定”和授权。这也是李向南“解决”问题的一种方式。但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李向南,又有了新的方法。小说制造了一个富有象征意义的视觉/听觉组合,一台象征“现代化”的收录机,播放着西方经典音乐大师贝多芬的《命运》。这表明,柯云路不仅使李向南获得了“传统式的”权力授予,而且还为他请来了象征“现代”的西方的“精神导师”。于是,李向南重新成为“时代英雄”。这实在不过是“街头卦师”式的承诺。
当代话语在80年代中期进行了第二次裂变,精英话语与大众话语的缝合状态被打破,代之而起的是“精英话语圈”与“大众话语圈”的各自独立。
80年代中期以后,以“解构”为主要特征和主要话语策略的“实验文学”逐渐取得了文学的主导地位。“实验文学”是以“先锋性”为表征的。一旦打出“先锋性”的旗号,便意味着它与大众话语的脱离。而且,“实验文学”的“解构”策略,必然导致其不仅解构了文学的习俗和陈规,也会同时解构了精英话语与大众话语的即有关系。因而,它便丧失了对大众话语的“发布权”和“操纵权”。即使某些先锋作家依然存有“启蒙”和“代言”的冲动,但大众话语已拒绝其“代言”的授权,不再甘当“启蒙”的对象。这并不是说,大众话语拥有了话语权,而是它已转向适时而起的“消费文化”寻求话语。
精英话语与大众话语的“断裂”造成文学的清冷,同时,文学也失去了其既有的地位。文学(精英文学)不仅走到了权力话语的边缘,更走到了大众话语的边缘。
三
进入90年代后,文学的“边缘感”之所以如此强烈,是因为在80年代的话语格局中,文学并不热衷于建立自己的话语中心,而是“占有”其他话语的中心地位。因而,当话语格局经过两次裂变后文学不再拥有这份“占有”时,才有一种被弃的感觉,心态随之失衡,价值也无从定位。因此,将文学的边缘状态理解为价值无从定位是没有依据的。如果以权力话语和大众话语为参照的“中心”,那么,文学处于它们的“边缘”似乎更为正常而合理。边缘才是文学的常态。文学可以适度地“进入”中心甚至影响中心,但不应是以往的方式。而对90年代的文化/历史现实,文学不再可能是权力话语的简单延伸,也不再能“操纵”大众话语—一新兴的“文化工业”使“消费文化”牢牢地占据了大众的话语空间。因此,过去那种正面的干预、居高临下的“启蒙”已经消弭,代之而起的更为可能的方式将是“呈现”—一一种价值呈现,一种“供选择的”价值的呈示。同样,价值的实现与否也不能简单地理解为是否为大众/社会“直接接受”,产生“直接”影响。存在本身即是一种价值。
文学“进入”边缘后,具有了价值定位的多种可能性,因为边缘是不确定的、自由的。单一化价值将随之被改变。事实上,崛起于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新诗潮”,恰恰是得益于其所处的边缘状态,才可以自由地、不受干预地发展,从而一举改变了较为单一、沉闷的诗歌格局。
进入90年代,在一部分作家为话语格局的改变而发生“角色困惑”的同时,也有相当一部分作家从既往价值定位中解脱出来,逐渐找到了立足于90年代语境的价值定位。80年代后期一批“激进的”先锋作家,相对缓和了其“激进性”,进入一种相对“平和”的状态。苏童率先“转向”,热衷于“历史”的华丽叙述;余华的《活着》也一定程度地放弃了对暴力、恐怖的“迷狂”。只有格非似乎还在“坚守”,他近期发表的《雨季的感觉》似乎还能略见《迷舟》的影迹。“新写实”则早已从对市民生活的批判,转向认同乃至玩味。总之,“激进”在减弱,“张力”在缓解。这与文学的边缘状态是相适应的。
文学的边缘状态不仅标志着80年代及其以前关于文学的神话的破灭,更标志着作为五四以来文学的价值中心的“现代性”神话的破灭。换言之,进入90年代以后,文学已不再是一个关于“现代性”的寓言,文学的价值也不再体现为对这个寓言的书写。中心化价值破碎之后,代之而起的不再是以民族/国家为主体而是以个人的生存处境与生存状态为主体的价值选择。
然而,价值选择的改变,并不意味着文学的基本特性也随之改变。立足于边缘的文学的价值确立,仍然没有也不能背离文学自身属性的规范。我以为,文学的最本质的特征在于它对现实世界的“理想化改造”和“虚构性重构”,舍此,便不再是文学。文学注定永远不能放弃对“神话”(广义的)追求和书写而沦为对现实的复制。另一方面,文学从来也无力承当世界的终极阐释者的角色。人们也从来没有以真正“历史的”、“科学的”标准要求文学,衡量文学的成败得失并依此确定其价值。文学对世界的解释,从来都是主观的、片面的、个人化的。因而,文学始终是人类“乌托邦情结”的理想的寓所。
进入90年代以后,文学依然不能放弃它的这一由其本质特性规定的价值形态。但随着文学由“中心”走向边缘,文学的价值定位也从“中心乌托邦”走向“边缘乌托邦”。
当然,我们将90年代以前的文学价值定位为“中心乌托邦”,而把90年代之后的文学价值定位为“边缘乌托邦”,并不完全是一种简单的比附。90年代之前的文学,不仅位居话语系统的中心,而且其价值也如我们在前面指出的,它是以民族/国家为主体的“现代性寓言”。它所热衷的,是对这个贯穿近一个世纪的民族/国家的中心价值的不间断的追求。90年代以后的文学,也不仅因为文学已经从中心撤离,而且其价值追求也偏离了90年代之前的那个“中心”。或许可以说,正因为90年代文学的边缘化状态和边缘化价值取向,才使其更有可能充分地体现其乌托邦特色。
“边缘乌托邦”作为一种价值定位,与“中心乌托邦”相比,第一,它不再有一个全面覆盖文学的价值中心,尽管这个价值中心因社会/历史因素的变化常呈现为不同的形态,但这个中心却始终存在并发挥巨大的影响力;第二,它不再以民族/国家为价值主体;第三,它不再是民族/历史/大众的代言和对民众的“强制性启蒙”,它不再具有拯救历史的权威性;第四,它不再与社会/政治/历史进程完全同步,不再为了其现实“使命”牺牲个体的自由。
因此,“边缘乌托邦”不是政治乌托邦,而是一种纯粹精神性的理想和归宿。它立足于边缘,享受着边缘的自由,也承受着边缘的局限。“边缘乌托邦”是一种无中心的“众声喧哗”,任何一种价值形态都具有存在的天然合理性,而且它们也没有价值上的高低之分、优劣之别;“边缘乌托邦”是一种以个体为价值主体的价值选择,它是纯粹个体化、个性化的精神梦园,而且绝没有君临一切和普济众生的优越;“边缘乌托邦”是一种价值呈示,它不强求更不强制人们接受,因为它只是立足于个体的生存状态和人生经验基础上的价值选择。
因而,“边缘乌托邦”是一次文学价值“非中心化”的集体尝试,它是对主流中心化价值的逃避和撤离。它是一种立足于个体的自我抚慰和温情寄托,是逃避现实生活激烈矛盾和冲突的梦幻世界和诗意情怀,也是对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轻盈的消解。或许,这也是一种间接的、“审美的”抗争。
需要指出的是,90年代文学价值的总体特征是多元化。因此,本文并不认为90年代文学的价值定位皆可用“边缘乌托邦”来界定,以“中心化”、“主流化”为特征和旨归的“主旋律”文艺的存在就是一个例证。而且“边缘乌托邦”作为价值追求的总称,其中亦存在具有明显差异甚至对立的诸种形态,依然具有多元化特色。
四
作为一种价值定位,“边缘乌托邦”在90年代文学中有下列主要的表现形态。
1.走向“历史”。以苏童、叶兆言、余华、刘震云等年轻作家为代表的作家群,近年普遍表现出对“历史”的强烈兴趣。然而,细读他们笔下的“历史”,不难发现它与我们所习惯的“历史小说”的巨大差异。尽管他们的小说大都是以颓败的“历史”和衰落的家庭为故事的,但却流淌着不尽的温情,全无通常的“历史小说”中那种理性的严酷和悲剧的庄严。
因而,90年代文学的走向“历史”,并不是一种简单的回返与对传统观念和方法的重新发现。我们只要稍加比较,就可轻易发现它们与《李自成》、《皖南事变》等“时代的代表作”的巨大差异。走向“历史”,恰恰不是回返“中心”的征兆,而是走到“边缘”的表征。因为,在上述作家群的创作中,“历史”已被赋予新的表述方式,“历史”的内涵也被进行了重新改写。
这类被称为“新历史小说”或“后历史主义小说”的文学创作的边缘化意义体现为两点。一、历史的主体由民族/国家改变为个人。“历史”被定位在个人/家族史上,回避对其进行民族/国家意义上的挖掘和阐发。或者说,他们关心的是以个人为中心的“历史”的过程,而不去进行诸如“启迪”“参悟”“唤起”“弘扬”之类的“深层次”努力。他们更感兴趣的是个人的命运转捩、家族的兴衰沉浮。“宏大”的历史被改写为“家史”,而且是“偶然的家史”。这里没有“史诗”,甚至没有“悲剧”。二、历史的表述完全是“个人化”的。所谓“个人化”,具有两层内涵:首先,历史本身的时空区域不再具有其应具的约束力和规范作用,它常常只是为“历史叙述”提供了一个场所和氛围,作者并不去刻意寻求与历史时空的吻合。因而,在这些作品中,“历史常识”的错误是普遍的,而且,作者对此似乎并不在意。因为他们书写的,并不是曾经发生过的那段“历史”,而是他们认为在那个历史时空中应该进行的“历史”。历史是为个人的需要而存在的,书写历史,也只是为了自己书写的欲望。或者说,历史只是当代作家借助历史时空进行的当代的、个人的表达。其次,叙述人“在场”。尽管在这些作家的作品中所表述的“历史”显然是远离当代的,他们不可能亲历,但是他们却常常将当代的叙述人植入“历史”之中,使“历史”在这个叙述人的注视之下流动。因而,他们常常喜欢使用第一人称。需要指出的是,作家们在建立了叙事人与故事主人公的血缘关系,使之“目睹”了“历史”的流变之后,并不让“他”参与“历史”,而只在一旁静观。“在场”而不参与,这就是叙事人的位置。这样,“历史”就成了个人的、温情的“家史”,小说也就成了“家史”的叙述。“历史”上曾发生的“前辈们”的恩恩怨怨、刀光剑影,经过“时间”的过滤之后,在当代的“后辈”眼中,通通变成了“传奇”,披上了一层温情的面纱。苏童甚至在《紫檀木球》这部关于武则天的故事的新作中,也植入了一个当代的注视者,足见他们对这种方式的偏爱。由此,这类作家成了历史的温情的抚弄者。历史对他们意味着什么,似乎也无须多说了。
2.走向“原始”。留恋过去,可能是人类的天性。尤其是进入工业文明之后,面对工业文明对人的挤压,人的这种回返的心态就更为强烈。这是中外文明史上一再复现的人文景观。尽管人类现代的生存方式和生活质量在总体上无疑是大大地向前发展了,但这种发展绝不是均衡的。人类在进步的同时,也失去了许多。而失去的这一部分不仅因为它也是人类的需要,而且因为它已失去而显得十分珍贵。因而,原始的生存环境、生活方式成为现代人的理想的审美梦园和心灵寓所,而它恰恰也是外在于现代社会的主流和中心的。
顾城,无疑是走向“原始”的重要代表。笔者已指出,顾城一直是位在边缘处寻找的诗人。他的文学活动从未被纳入中心。如果说,80年代中期以前的顾城只是热衷于语言的边缘化的话,那么,80年代中期以后的顾城追求的已经是更广泛意义上的生活世界的边缘化。从中国到西方,再到毛利人居住的新西兰小岛——激流岛,这条“撤离”中心的路线清晰地表明了顾城心中的向往。激流岛是与顾城的追求最为吻合的一片世外的充满原始气息的“静土”:而在岛上近乎原始的生活才能填补他在“文明世界”形成的内心的焦虑与空虚。
当然,顾城的人生经历并不具有多少文学意义,但是,这些“不常有”的人生经历,却使他创作出了“绝笔之作”——《英儿》。《英儿》无疑是走向“原始”的代表作。小说营造了一个与现代社会规范完全背离的生存场所,展示了三个同样悖离于现代人的生存方式、价值标准和情感方式的主人公的恩恩爱爱。我们不应从通常的意义上来理解“一夫二妻”的人物格局,顾城迷恋的,是这种具有原始气息的生存格局中人的那种近乎“无知”的爱。他爱两个女人,并希望两个女人真诚相爱,而这两个女人,确实也具有了一种超越“常态”的感情。恐怕我们不能用“道德堕落”来评判顾城的艺术创造,这更多地表现为一种原始情结。
我以为,我们在考察《英儿》,对《英儿》进行价值评判时,应将它与生活中的顾城及顾城之路拉开一段距离,更不应因顾城的残暴的悲剧性的终结而否定《英儿》的意义。顾城之死并不能消弭原始情境在心灵上、尤其是审美上的意义。如果说顾城的悲剧与此有关的话,那也只是因为顾城错误地将一种心理的、审美的存在“现实化”,模糊了理想世界与实践世界的界限。它是乌托邦的,而不是现实的。
走向“原始”的意义在于它向人们提供一种在现实世界亦已消失的“过去的世界”,满足人类的原始情结,同时,它也使现代人疲惫的心灵有一个暂时的、“审美式的”栖息之地。它不是为了阻断现代文明的进程,它也无力如此。因而,它与现实生活中的“保守”力量并不是一回事。心灵的需求是多方面的,文学有义务满足人的多样性需求,因为它是虚构的。
3.走向“顺从”。在以“顺从”作为“边缘乌托邦”的一种表现形态时,首先必须指出,它并不等于弱者的消极选择。“顺从”是80年代汪曾祺、阿城的淡泊、隐逸等渗透着道家精神的价值选择的延伸。它们的共同之处,在于它们都肯定现实世界的确定性和坚固性,人所能做的,或者说人生的智慧就体现为在一个几乎已被确定的命运格局中找到一个自得其乐、自我满足的支点。汪曾祺、阿城所做的,是对现实世界的审美式的审视,即放弃对它们作现实层次的评判,而只注重其所蕴含的审美意蕴,从而使其艺术成果总与现实世界保持一段距离。
池莉的《热也好冷也好活着就好》是一篇颇有意味的作品。一方面它体现了新写实小说在90年代的转轨(这与转向“历史”的另一支具有同样的意义),另一方面它也构成了走向“顺从”的经典范本。这部以炎热夏日“火炉”武汉为背景、以在热浪中“煎熬”的武汉人为故事主体的小说中,作者一扫其以往作品中烦恼、无奈、无聊等基本情态,而把热浪中武汉人的生活写得有滋有味。“热”不仅没有给小说中人的生活带来困难,反而给他们的生活平添了许多的乐趣。生活本来就是这样,顺从它,也许是最好的选择。与汪曾祺、阿城的小说相比,池莉等的小说,少了“空灵”,多了现实的生存之道。但他们的基本走向,都是避免直接的冲突和愤世嫉俗。既然我们无力改变,既然人注定为环境所支配,我们又何必作无谓的抗争与无用的叹息,何不从中找到人生之乐呢?
如果说走向“历史”、走向“原始”是一次相对实在的时空撤离、意在寻找一个外在于现实中心世界的“边缘世界”的话,那么,走向“顺从”则是在现实时空中的心理上的撤离。如果说前者是以重构的个人化的“另一世界”为自己的心灵寓所,那么,后者则是对现实世界心理的个体化的重新定位,以支撑其在此岸世界的生存。但是,所有这一切,都是“乌托邦”的、艺术的、审美的。它们对于我们的意义也是如此。
除了上述几种形态之外,张承志、史铁生的走向宗教,任洪渊等人的诗作的走向语言,林白、陈染等人小说的走向“状态”,都具有一定的“边缘乌托邦”特色。当然,笔者无意造成一种印象,即“边缘乌托邦”已成为90年代文学的一种普遍的价值定位。笔者所关注的同时也是写作本文的动机是探讨90年代文学的新的价值定位,而“边缘乌托邦”也只是一种尝试性概括。
标签:文学论文; 价值定位论文; 英儿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精英主义论文; 乌托邦论文; 文化论文; 艺术论文; 废都论文; 顾城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