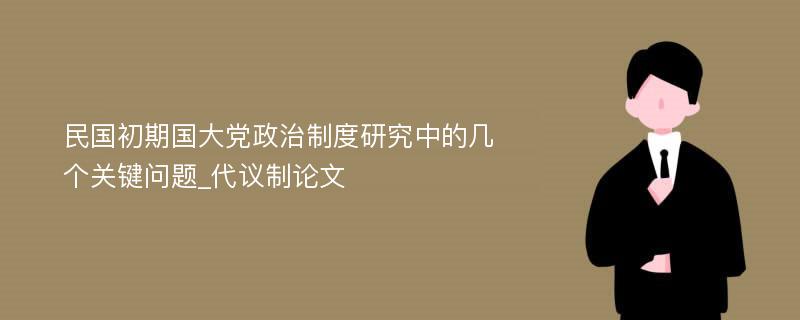
民初国会政制研究中几个关键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政制论文,几个论文,民初论文,国会论文,关键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5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6-0766(2016)03-0005-09 清人陈澹然说:“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隅。”①对于历史研究而言,或许可以认为,由于政制史在近代中国历史研究中举足轻重,而国会乃兑现“民主”的制度建构,为理解近代民主政治的关键,研究者应首先着力把握,因而是理解任何“一隅”事物时必先把握的“全局”性问题。伍德罗·威尔逊在《国会政体:美国政治研究》一书中,强调国会乃是美国“联邦制的中枢和支配力量”,②亦可见国会政制研究对于认识现代民主政制具有何等重要的地位。然而在中国大陆,由于非学术因素的影响,很长一段时间内学界对源于西方的民初政制研究都保持着基于“政治正确”的戒心,相关研究殊难令人满意。最近十余年,风气稍变,经学界共同努力,民初国会问题研究已奠定良好的基础,但仍有一些重要问题,如“直接民主”政制主张及其对代议制国会的影响,被视为旨在体现“主权在民”理念的国会的权力是否应当在分权体制下受到限制,国会与“政党内阁”建设的关联性,以及究竟是何种因素构成了国会政治的根本威胁,凡此种种,均为研究民初国会政制所不可忽略,却并未引起足够重视。这就导致民初国会政制史研究难以在更高的学术维度上展开,堵塞了近代中国政治史研究的纵深进路。本文拟就这些问题提出宏观的有类“谋全局”的研究构想,希望对“一隅”性质的具体问题研究贡献有价值的参考。 一、直接民主与代议政制的选择 “直接民主”(direct democracy)观念源自西方,③为国人所知则始于清末。所谓直接民主是指由国民直接行使主权。楼桐孙在1920年代曾说,中国近十余年来,“主权”二字无日无时不与国人有密繁之接触,从《临时约法》到“双十贿宪”,皆有“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之明文,可见“主权”概念已近家喻户晓。④杜威在华讲学时则明确向国人传达了基于这种思想的“直接民主”观念。⑤后来吴贯因在《再生》杂志撰文指出:“易‘代议制度’而为‘自议制度’,此实现代民权之新潮流。”⑥吴氏所说的“自议制度”,就是实施“直接民主”的制度。⑦ 或许有些“背运”,中国代议制国会的酝酿筹建几乎与构成其否定因素的“直接民主”观念为国人同步认知。早在清政府颁布预备立宪上谕宣布将于9年后召开国会之时,章太炎便对代议制国会进行了抨击。与此同时,由以“国民会议”决定国是的主张开始为国人知晓。⑧1907年12月,杨度等呈递请愿书,主张“全体人民民选议院”,已包含直接民主理念。⑨武昌起义发生后,南北交战,杨度于1911年11月17日致函资政院呼吁停火,提出组织“临时国民会议”以决定国体的主张。⑩民国肇建,仍不断有人倡导此议,认为是矫治代议制缺陷的良方。 章太炎等人批评代议制的逻辑是,中国广土众民,非比小国寡民之邦,民意无法代表,且中国没有阶级,职业不发达,议员没有特定的阶级可代表因而只能成为纯粹政客。然而在反对者看来,章太炎等很明显将逻辑颠倒了,按照国会政治理论,恰恰是因为广土众民,信息交通不灵便,没有直接民主的实施条件,不得已才采用代表制。诚如李三元所言:“时至今日,人人知代议制之为害,而竟无一人敢于断然谓代议制之宜废除。法、意诸国革命的工团主义者固尝有‘直接行动’之主张,无治主义者且进而根本反对政府之存在。然而陈义愈高,其去事实也愈远。凡有广土众民之国,民意表现之方法,究不能出代议制范围,是以虽创巨痛深,终不肯决然舍去。”(11)李氏的反驳有力且中肯。就是在今天,代表制在西方国家也是政制主流,直接民主只在少数国家和地区为特定问题表决而实施,并非政治常态,遑论百年前的民国。在不具备实施“直接民主”的时代条件下,代议制尽管存在弊端,却是无可奈何的选择。 反对代议制国会者认为,国会与“阶级”的存在呈正相关性(positive correlation),中国没有“阶级”,议员缺乏特定代表对象,故无存在依据。其实这是个伪命题。中国自创设科举制度实现不同阶级的上下流动后,确实已无英、法等西方国家那样固化的“阶级”。但民初的中国,因经济及社会发展,社会分层仍十分明显,议员可以成为不同阶层和不同社会集团的利益代表,何必一定要代表“阶级”?英、法等代议制“祖国”在经历破除“阶级”的革命之后,已淡化了议员只能是不同“阶级”代表的观念,中国有何理由固守西方中世纪的“阶级”窠臼?就事实而言,民初议员的代表性并非毫无体现。在众议院,进步党倾向走上层路线,代表社会中上阶层的利益;国民党“民粹”色彩浓重,多少反映了下层民众的诉求。而在代表性上看似与众议院没有多大代表性区别的参议院,至少在制度设计者心中,也有趋重不同区域及不同民族利益的考虑。(12)中国区域经济、文化及社会发展不平衡,主要为汉族地区的沿海与内地发展有差距,少数族群地区经济、文化明显不同于汉族地区,而同为少数族群地区的满、蒙、回、藏,文化与利益诉求也各异,设立参议院,有利于反映不同区域的利益。美国没有欧洲式的贵族,其以众议院反映民众的诉求,而以参议院反映各州的不同利益,亦运作顺畅。中国略仿美国设立两院,不能说全无代表性。至于职业是否发达是一个相对概念,我很怀疑民初中国各项职业的发达程度尚不及议会政治实施初期的英、法、美、日等国。因而要说民初议员不代表任何阶级,也没有职业基础,只能成为政客而扰乱国政,未必客观。 不幸的是,以“代议”为存在形式的国会在中国实施不过10年,就因“直接民主”主张的提出,加上其自身运作出现问题,被国人弃若敝屣。然而“直接民主”果真是中国政制的不二选择吗?民初国人救国心切,主张实施“直接民主”,却忽略了以“直接民主”作为政治号召,否定以“代议”为运作方式的既有国会政制,未必能实现民主自由的政治愿景。 从实践层面观察,在揭示代议制弊端过程中产生的国民会议、国民大会,以及标榜实施“最广泛民主”的苏维埃制度,均因缺乏凭借,陷入“代议”与“自议”的制度选择两难,结果国会政制被严重扭曲,要么混淆了制宪会议与国会的区别,要么畸变成在“多数人统治”名义下实施的集团专制。以南京国民政府筹议召开的“国民大会”为例,国民政府建政南京后,“五五宪草”出笼,拟议中体现“直接民主”的政治制度被表述为“国民大会”,但国民大会的性质界定却存在极大问题。孙科说,国民大会颇似美国建国之初的大陆会议(Constituent Assemble),大陆会议只开一次会,旨在制宪,中国将其弄成常设的“国家政权行使的最高机关”,标榜要让“人民行使四权”,这样的“国民大会”当然与立法机关国会有别。(13)事实上,南京国民政府另有立法院的政制设计。让人费解的是,在其设计的政体结构中,国民大会被赋予部分立法机关职能,而本应代表民意立法的立法院却并不具备民意机关性质,两者关系如何协调,也存在诸多问题。(14)钱端升说南京国民政府立法院“非代表民意机关,系议决法律机关,只少数专家已足”,将立法院的性质一语道破,也间接说明了当时政制的畸形。(15)由于政制设计存在问题,直接民主难以实施,国民大会也就“僭代”民意,由理想中的“民意机关”变成了“民意制造机关”,在追求现代民主政制过程中将其实并未过气的代议制国会轻率抛弃,换来的却未必是真民主,值得标榜追求现代民主政治的国人认真反省。 二、分权制衡体制下国会的权限 国会研究涉及行政与立法的关系问题。民初国人拘泥“主权在民”理论,以为既然国会是民意机关,就应加大立法方面的权力。这种主张看似有所理据,却破坏了权力之间基于力量平衡形成的相互制约,使行政机关难以正常运行。最突出的表现是,民初临时参议院通过《临时约法》赋予立法机关对行政首脑发布命令的“同意权”,却无对应的行政机关对于立法机关的“解散权”,致使立法机关强大到足以使行政无法正常运作的程度,两者冲突因此不断。梁启超很早就意识到民初政制的这一缺陷,曾撰写《同意权与解散权》一文,主张在国会拥有对于总统任免重要官员之同意权的同时,赋予政府首脑对于国会的解散权,以求平衡。(16)所论击中了《临时约法》的要害。 由于遭到质疑,临时参议院在炮制《天坛宪草》时虽对《临时约法》作了修正,规定行政首脑有权解散国会,却又横生枝节,设置须参议院三分之二多数同意的限制,在参、众两院均为国民党人操控的情况下,该条文形同虚设。临时参议院秘书长林长民就认为,有此限制,解散权“不免为有名无实之权”。(17)制宪国会议员王印川对《天坛宪草》规范的权力关系更是不屑削一顾,称之为“极端议会政治”。(18)由于对此规定不满,时人甚至对袁世凯解散国会的政治作为予以肯定。钱基博说:“综其行事,所最为中外佩服者,即其解散国会一事,谓其有利刃斩乱麻之能,而抵制日本要求不与焉。”(19)然而直到代议制国会在中国衰亡,作为制衡立法机关手段的“解散权”始终没有完全确立,这不能不说是中国国会政治运作的一大败笔。(20) 问题的复杂性在于,袁世凯取代孙中山担任临时大总统后,北洋掌控军政大权,国民党占多数席位的国会仍掌握着立法权并处处掣肘行政,袁因北洋系统并未成立自己的政党,不能以国会内合法党争的方式与国民党抗衡,只得依靠以军权作为凭借的行政机关压制国会中的反对派,这就使本属正常的权力制衡,参入了诸多“负面”因素。 本来,在政务纷繁复杂的现代政治中,国家权力会自然偏向行政方面。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及战后一段时间西方各国的情况看,为应付非常时期的非常之需,加强行政权力已成普遍趋势。中国在民国肇建、百废待举的情况下,适当加强行政权力,避免过度政争,亦属必要,这也是“国权主义”在袁世凯时代一度兴起的重要原因。罗文干对袁世凯奉行“国权主义”的实际效果就颇为称许,认为与后来的执政者相较,袁氏已不可及:“袁氏之世,法令能行也,国库裕如也,各省肯解饷不敢截留也,官制官规非毫无定制也,中央之政不必请命于军阀也,对外尚能统一也,吏治也考绩也,仕途不冗滥也,百官不能躐等也,官方尚能整肃也,登庸有考试也。故以袁方诸华、拿则不可,而此十余年来国稍以安者,亦袁氏在位之日已耳。其所以雄视一世,自以为可以称帝者或亦以此。是故袁氏为帝则不足,为‘的得多’则有余。”(21)然而袁世凯在缺乏“政府党”作为政治支撑的情况下直接以行政力量压制国民党占据多数席位的国会,以超越国会体制的方式解决所面临的政治窘境,其未能得到国人认同和研究者首肯,亦属自然。 袁世凯不被认同并不能反证《临时约法》政制设计正确。从实践立场观察,该约法在设计包括国会制度在内的民国政制时,片面强调加大立法权,压制行政权,将立法与行政的关系弄成畸形,致使两方冲突不断。谢彬说:“南京参议院制定之《临时约法》,伸张国会权,制限政府行动,胥有过当之处。”(22)鲍明钤认为,《临时约法》的这一缺陷“使中国付出了内战的沉痛代价”。(23)“光一”后来总结民初政治,也认为以《临时约法》为依据产生的国会难辞其咎:“中国近年政治,闹得乌烟瘴气,不见天日,国会军阀,负同样的责任。”(24)今日学者研究民初国会多偏重政治解析,忽略了在政治技术上,《临时约法》的政制设计就包含了国会最终被否定或发生畸变的内在因素。(25) 然而民初政治的偏颇尚远不止此。民国肇建之初,南方既已宣布虚位待袁世凯反正,却又着手选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议决若袁宣布拥护共和,孙须让位于袁,这本身就是一个制造矛盾及利益冲突的蹩脚的政治决策。黎元洪在获此信息之后,曾通电表示反对,有谓:“各省代表在宁议举临时大总统,此时关系全局,窃以为和议未决,不宜先选总统,致日后兵连祸结,涂碳生灵,追悔莫及。公等系鄂全权代表,责任綦重,兹事体大,亟宜注意。”黎电到后,适浙江代表陈毅由鄂到会,也指出:“袁内阁代表唐绍仪到汉时,曾表示袁世凯亦赞成共和。”(26)鉴此,南方曾一度议决缓选大总统,但最终仍在南北谈判期间就率先选举孙为临时大总统。这就在民国建立之初,人为地设立了两个政治地位等同的国家元首,为后来孙、袁不和埋下伏笔,并殃及国会。 袁世凯乃一代枭雄,政治上奉行实用主义,本无“成执”,其政治立场在一定程度上是由政治对手的作为所决定。孙中山曾告诫身边人:“袁氏可为善,勿逼他为恶。”(27)但孙似乎忘了这应为与人共勉之语,他利用立法机关处处掣肘行政,已无异“逼袁为恶”。若跳离善与恶的价值判断,仅就袁世凯的政体主张论,鉴于其政治幕僚大多主张君主立宪,或可大致判断出他的政体倾向。研究北洋历史的人都习惯把袁世凯称帝说成是做“皇帝梦”,其实袁最初未必会做甚至未必敢做这样的梦,民初政制设计导致的政治乱象让国人对“民主共和”深感失望,“君主立宪”政体主张复活,才有了他“做梦”的条件。当是之时,政体问题讨论,即中国在推翻清朝统治之后所作民主共和的政制选择是否明智的问题,已引起不少国人关注,这构成了袁做“皇帝梦”的重要背景。然而袁的政治作为果真是为圆“皇帝梦”吗?“二次革命”之后,袁世凯已打倒国会内的反对派,大权在握,深谙政治之道的他应该不会太在乎头上戴的是总统帽还是皇冠,他曾对冯国璋坦言其所居总统位置与皇帝并无多大区别。(28)就其对国会的态度而言,他虽曾宣布解散现有国会,却并未否定国会制度,在其颁布的命令中,多有民国不可无国会的强调。(29)因而民初关于“国体”问题的讨论究竟是袁为圆“皇帝梦”而做的“学术”安排,还是源于北洋集团改造政体的内外期许,兴许还有讨论的余地。 在袁世凯“称帝”问题上,需要稍作辨析的是,相对民主共和,君主立宪也是现代民主政制的一种形式。说它是一种“民主”政制,是因为“君”是虚的,骨子里搞的是宪政,所以形式上虽有“君”存在,仍属民主政治范畴,两者的区别颇类今天英国和法国政制的区别,并无高下优劣之分。但很长一段时间内,国人似乎都认为君主立宪政制很糟糕,恢复这个制度就是复辟,就是反动。其实袁世凯如果真的要搞货真价实的君主立宪,在当时未必没有实施条件,也未必“反动”,因为民主共和已被公认为搞得很糟糕了。不过袁的“君主立宪”并不地道,他最初可能是希望建立英国式的君主立宪政制,鉴于日益严重的共和乱象,他又不愿自己的权力被过度“虚化”,于是半推半就地朝着集权皇帝的政治方向走了一步,其政治形象也就自我模糊化了。在这个问题上,很可能他自己就分不清立宪制度下的“君”与专制时代的“君”究竟有何区别。在一定程度上,他是被人蒙蔽了,因而他身边的人,包括外国顾问,要对此负很大的责任。袁世凯至死都主张以宪法治国,据说他的临终遗言只有两个字,就是“约法”。(30)显然,袁世凯是一个悲剧性人物。他曾说他的家族里没有一个男人活过60岁,几个儿子又没有一个可以成器,何必称帝?(31)果然,天不假年,他57岁就死了。很难说如果他不死,后来的民国历史会怎样书写。 不过无论袁世凯的真实意图如何,张大行政权都应以梁启超所说的不谈国体为政治底线。(32)强调这一点十分必要,研究者不能给人造成赞成离开民主轨道、回头走专制路线的印象,给试图这样做的人留下口实。梁启超最初“挺袁”及最终反袁的原因均在于此,其去就取舍的考量,值得认真研究。 三、政党发育对国会政治的制约 作为立法机关,国会要正常运作须协调与行政机关的关系,达此目的的理想方式是建构“议会政府”(Congress Government),由国会多数党领袖组阁施政,实现立法与行政的统一。20世纪初英、法等国的情况即大率如此。(33) 议会政府由在国会内居于多数席位的政党领袖组阁,立法与行政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阁会合一,在政制设计上确能化解立法与行政的冲突。问题在于,当政府以“政党内阁”形式组成时,政党在政府中作用突出,故政党发育状况也就成为能否建立成熟稳固的国会及内阁的前提。反观民初中国,政党内阁的实施条件并不具备,其中最关键的是政党发育状况不佳,西方国家成功运作责任内阁政制的政党条件即两大主流政党对峙的政治格局在民初并未真正形成。民初因党禁放开,国会召开在即,陡然冒出数百个“政党”或政团,经分化组合,第一届国会召开前夕,虽逐渐形成国民党与进步党两大系统,却发育幼稚,基本为临时的利益组合,没有共同的政治信仰,没有维系内部关系的纽带,缺乏广泛的社会基础。(34)政党发育不成熟,政党内阁自然没有凭借。在民初内阁政制运作过程中,宋教仁遇刺是一重要转折点。有人设想,若无“宋案”发生,宋教仁或可顺利组阁,实践政党内阁理想。其实即便宋教仁没有罹难,处于当时的政治格局,在政党发育极不成熟的情况下,也不可能建成真正意义的政党内阁。 在民初政党格局中,在野党身份相对明确,孙中山下野之后的国民党在回归“革命党”路线之前,就居于在野党地位,但民初始终没有形成由国会多数席位产生的“执政党”,阁会不统一,致使政治呈现出不稳定的性状。由表象看,执政的北洋集团似乎也有“政党”,进步党就被认为是北洋系统的政党,一度被视为“政府党”。但进步党与北洋集团的关系极为复杂,很可能其党魁梁启超具有改造北洋政治家使之走上现代政治轨道的政治初衷,但将进步党与北洋集团混为一谈并不恰当。事实上,以北洋集团为代表的军政势力与国会的斗争也包含与国会内的进步党议员之争,只是争论的问题与国民党不尽一致罢了。国民党被袁世凯从国会中清除后,梁启超产生物伤其类的悲伤,也可以证明这一点。(35)从人数上看,“宋案”发生前,进步党在国会中的席位远不及同盟会或其改组而成的国民党,故袁世凯上台后行政方面与立法的对立,实际上是行政与国会内占多数席位的国民党的对立,而非袁世凯操纵的一党与另一党的二元对立。“二次革命”发生后,国会形势丕变,立法与行政关系亦随之变化。此时国会与行政的冲突,很大程度上是袁世凯不满《临时约法》,希望另立根本,改变既有“法统”所致。因为要另立“法统”,袁世凯便通过约法会议及政治会议等机关制定正式约法,这必然与原有立法机关发生冲突,第一届国会最终被袁世凯解散。除了前面提到的权力不平衡的因素之外,此亦重要原因,而与北洋是否成立自己的政党无关。 民初政治不甚成功的实践证明了政党内阁的价值和意义,并提示“宽容”乃国会运作必不可少的政治生态。成功的政党内阁多以两大主流政党的形成为依托凭借,谁受选民拥护,占居国会多数席位,谁就组阁执政。不同政党共同推进国会政治,相处之道只能是政治上彼此宽容。宋教仁案就是政治家容不得异己存在的典型案例。通常认为,现代西方最重要的价值是自由,其实很多情况下,“容忍比自由更重要”。(36)在政党内阁建设中,容忍异己力量的合法存在是最基本的条件。梁启超曾用下棋来比喻政党政治,认为善弈者必求高手过招,棋势方才可观。(37)凡主张政党政治者,都不认同政治上的排他性,因为没有他者存在,失却外部制约,内部就会出问题。陈炯明与孙中山闹分歧,原因之一就是不赞成国民党“一党专政”的主张。针对国民党对异党的排斥,陈炯明指出,国民党“必欲高唱党外无党,其结果适得党内有党。观于左右派之分裂,层出不穷,何莫非食此报而来耶”?(38)陈炯明认为国民党主张“党外无党”的结果必然导致“党内有党”,可谓将国民党内部你死我活斗争的原因一语道尽,可惜这一极具洞察力的思想,知道的人实在太少。 在缺乏宽容的政治生态中,无论在朝与在野,政党都很容易趋走极端。从政治实践角度观察,民初国会政治崩盘很大程度上系因同盟会及其衍生的国民党与进步党两派政治力量都不愿同台演出国会政治这场戏所致。后袁世凯时代,活跃政坛的政党基本是从该两党衍生出来。被指责偏向政府的进步党党魁缺乏现代民主意识姑不具论,就革命党来说,可以批评指责之处亦不在少。如果国会分裂表现为两党关系破裂,“宋案”发生后孙中山及其领导的国民党不愿继续遵守议会政治的游戏规则应是很重要的原因。“二次革命”是孙中山及其领导的国民党回归革命路线的标志,是导致袁世凯去世后国会重建仍未能弥合与进步党系各政团矛盾的重要原因,也是直奉战争之后“法统重光”语境下“大孙”派政治家与“旧国会”议员没有共同语言的症结所在,仅从北洋之政治作为的角度解析国会分裂,难得要领。 我们今天都认同“将权力关进笼子里”的思想,这一思想的精髓在于强调权力不能漫无限制。针对民初现实,应进一步强调的是,由于责任内阁制是由国会多数党领袖组阁执政,因而执政党的权力尤其应受到制约。在国会体制下,制约的职能须由他党来执行,不能由执政党自己来执行。中共创始人陈独秀很早就意识到国会政治是普遍参与的政治,不能一家独揽。1918年7月,在张勋拥溥仪复辟失败后的国会重建过程中,段祺瑞试图以安福俱乐部操纵国会,具有民主意识的陈独秀立即发现了问题所在,提出三点意见。其中第二点是“当抛弃以一党势力统一国家的思想”。为此,他不仅表示“始终主张北洋、国民、进步三党平分政权的办法”,而且表达了在多党竞争体制下由国会居多数席位的大党领袖组织内阁的“梦想”。他强调指出:“中国无论何党何派,自己甘心在野,容忍反对党执政的雅量,实在缺乏。这种状况不改变,国家政治绝无前途和希望。老实说一句,一碗饭要大家吃,若想一人独吃,势必大家争夺,将饭碗打破,一个人也吃不成。”(39)可是,陈独秀如此重要的思想,却因发表在1918年的《新青年》上,产出时间偏早,针对性过于具体,未能对后来倾向一党独裁的国民党发生任何影响。 四、威胁国会政制生存的政治因素 对民初国会构成严重威胁的另一因素是国家政治裂变。国会在北京开会,属于南方阵营的人可以拉出一帮议员南下上海或广州开会,人数不足就号称“非常”,国会因此分裂,国家亦因缺乏政治“公约数”,导致政制“碎片化”。 这种局面与“地方自治”思潮兴起有关。清末兴起的地方自治思潮,已包含自治与联邦的诉求。民国创建,走的不是武力扫平敌对势力建立统一民族国家的路线,而是走一省起义、各省相继宣布“独立”,再谋求建立新的政治共同体的路线,揆之改朝换代传统模式,已是异数,民初甚至还出现趋向于分而非趋向于合的政治局面。当时曾有人主张效仿美国搞联邦制或邦联制,前提是实施地方自治而非中央集权,是“民主”而非“君主”。(40)1920年代,章太炎耸人听闻地提出“分立数国”的自治办法,(41)得到包括青年毛泽东在内的不少人的响应,毛泽东进而提出将中国27省区建为27国的主张,公开喊出“湖南共和国”的口号。(42)这与志在“武力统一”的北京政府发生了利益冲突。北伐开始后,本身就在“割据”称雄的南方转而对“军阀割据”持批评态度,国民党亦凭借对“军阀割据”的批判,彰显自己的“政治正确”,对地方自治的认知陡变。 其实北洋时期“割据”包含的地方自治理念对于中国这样广土众民、文化多元的国家来说,并不一定是绝对的坏事,对国会政治也未必是负面因素。国家统一固好,但分也有分的好处。政治“公约数”的要义在于“公约”,而“公约数”是可以变化的。天下大势,本来就是“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中国在延续了两千余年的集权统治之后,要解构“大一统”,就要寻找新的“公约数”。我们过去习惯于沿袭国民党集权政治的思维模式认识北洋时期的“分裂格局”,不知国民党在一党专制集权、排斥其他政治力量参与政治的前提下实现的“统一”,才是后来中国爆发大规模内战,进而导致国会制度遭到根本破坏以至国家出现更加严重灾难的根源。中共在反对国民党的过程中正是抓住国民党一党专制进行批判,其取而代之的“合道性”与“合法性”才得到认定,可见这个问题是何等重要。总之,我们不必对政治的“碎片化”过于恐惧,在一定历史时期内,对“大一统”的“碎片化”,正是建设新的政治共同体的必要前提。问题的关键是如何建立新的政治共同体以及用何种价值和制度作为中国人的政治“公约数”。从国共两党斗争一胜一负的历史经验中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这个“公约数”应该是基于自由价值的现代民主观念与政治制度,它与地方自治理念并不一定构成矛盾。 当然,北洋时期的自治有时不免趋向极端,即便如此,地方自治也并不一定构成国会政治的否定因素。史扶林(H.Z.Schiffrin)说,19世纪末中国的“地方主义”是一种“分”是为了“合”的“中央方向上的地方主义”(center-oriented regionalism)。(43)很少有学者意识到史扶林的意见用于说明民初中央与地方关系也大体适合。在某种意义上,当时地方自治对于国会正是有着向心作用的“中央方向上的地方主义”而不是相反。力主地方自治的章太炎的政治作为最能说明这一点。虽然章氏很早就对源于西方的代议政制提出质疑,但他并不根本否定国会的价值,恰恰相反,在其政治实践中,他都极力宣扬这一政制。1925年章应赵恒惕之邀主持实施地方自治的湖南县知事考试,担任考试委员长。章所拟初试题目是:“联治实行,制定国宪,对于国会制度,应采两院制乎?抑采一院制乎?试说明之。”(44)题中既有地方自治,又有国宪国会,体现出以国会政制来统摄全局的明显意图。 真正对国会政治具有“杀伤力”、导致后来国会政制畸变的莫过于苏俄政制及其影响。代议制国会在中国可谓生不逢时,一方面,中国遭遇外国列强侵略,国家民族面临严重的生存危机;另一方面西方世界发生空前大战,使人对起源于西方的现代政制产生怀疑,议会批判思潮勃然兴起,新的政治思想层出不穷。在政治上陷入迷茫不知所从的国人以为要根本解决问题,就要移植“最新最好”的制度,否则无济于事。在巴黎和会中国外交失败而俄国因外交所需向中国示好的背景下,在批判西方代议制过程中产生的苏维埃制度遂被认为是现代政制发展的极致,国、共两党都不同程度加以采纳。苏维埃制度的产生有其历史合理性,至少在西方政制因第一次世界大战暴露出严重问题一时又未找到解决方案的情况下是如此。但国人对“新思潮”的追求不免有些因急于救亡而忽略民主思想启蒙的倾向(胡适就说彰显民族主义的五四运动是对新文化运动“不幸的政治干扰”(45)),对政制的选择亦受此影响。从世界政治思想的演变来看,当时西方虽已兴起议会批判思潮,但西方这一政治思潮的主流多具改良主义性质,中国激进政治家、思想家在接触这一思潮时将并非主流的“非议会主义”(anti-parliamentarism)批判思潮加以采纳,以为西方已是如此,遂有转变方向学习俄国政制之举。 不过尽管部分国人倾慕苏俄政制,民初多数国人在政制上的翻新追求基本是沿着技术路线进行,非尽关乎“价值”层面的取舍。在有关代议制度的讨论中,国人大多否定的是现存国会,主张根本取消国会制度者只占少数。响应章太炎参与“代议然否”讨论的学者及政治家,无论是走传统路线的章士钊、瞿宣颖,走自由主义路线的胡适、高一涵,还是走折中路线的梁启超、潘力山、楼桐孙,基本都是在“间接民主”与“直接民主”即民主的形式上进行选择,并未站在民主制度的对立面。就连在政治上否定现存国会的段祺瑞政府也不敢轻易否定国会制度,碍于“革命”与“法统”选择的两难,段祺瑞临时执政府的举措只在废除既存国会,尚不具有根本消灭国会制度的“革命”含义。从其所拟宪法草案可知,在未来的正式国家机关中,国会制度将会保留,“仍采两院制,然参议院颇近似与普通上院性质迥异之德国新宪法之联邦参议院”。(46)因而代议政制在民初的失败,似不能简单归纳为民主政制在中国的失败,而只是“代议”这一间接民主形式的挫顿。(47) 需要强调的是,尽管民初国会批判思潮高涨导致国会生存危机频现,主张代议制民主者也并未因议会批判之声大作而完全失语(be voiceless)。毛以亨堪称捍卫国会政制正面价值的典型。一方面他因应潮流对代议制弊端展开批判,认为代议制日久弊生,无可讳言;另一方面他又告诉国人,“代议”只是政体形式,是表面现象,民主政治才是这一制度的内容实质,认为代议制不能废除,只宜改造,改造代议制须洞悉中国传统政俗,合乎世界思潮,主张根据国情,“以智识界为代议士”,并提出限制议员资格以实现精英政治的具体主张。(48)毛以亨的思想主张具有多大程度的代表性和可行性,当然值得研究民初政治者认真分析,但“改造代议制”思想的提出,至少证明并非所有国人都头脑膨胀发热,选择了一味趋新甚至激进化的政治路线。 要之,民初国会政治运作不成功,南橘北枳,形质畸变,原因极为复杂。除了上文所论之外,今日学者讨论的许多问题(如国家权势重心的失却致使国会运作缺乏稳固的政治支撑、军队非国家所有导致军人可以随意推翻国会等)均不可忽略。鉴于国会是由议员运作的,选举这一环节也不能漠视,要使议员真正成为人民利益的代表,避免舞弊,选举的公正性须有切实的制度保障。选民的素质也至关重要,国会政治是普遍参与的政治,没有制度保障选举公正,没有高素质的国民共同参与推进国会政治,任何好的制度在实践中都可能走样。 ①陈澹然:《迁都建藩议》,《寤言》卷2,附于氏著《江表忠略》后,收入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正编第197册,台北:文海出版社,1968年,第577页。 ②威尔逊:《国会政体:美国政治研究》,熊希龄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年,“前言”,第1页。 ③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年,第84、99-122页。 ④楼桐孙:《我之萨威稜帖观》,《东方杂志》第23卷第2号,1926年1月25日,第5、16-18页。 ⑤《杜威讲演会中之趣闻》,《民国日报》1920年11月20日,收入袁刚等编:《民治主义与现代社会:杜威在华讲演集》附录2,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756页。 ⑥吴贯因:《民国成立廿三年尚在讨论中之宪法》,《再生》第1卷第11期,1933年3月20日,第5页。 ⑦《东方杂志》载文指出:“此新倾向之最显著者,即劳动运动中工团主义一类运动,对于议会政治表示莫大之不信,嘲笑咒诅靡所不至,主张舍弃议会主义而依直接行动以达其目的,并企图其主张之实行。此新倾向之表现为日虽已甚久,然自大战以来,其势益强。且从前唯英国以外之法意等国稍有此种倾向,近则议会政治产生地之英国亦甚显著。其余诸国则势力更大增矣。……近来主张直接行动之非议会主义大得势力,政治之倾向,遂带激进的革命色彩。所谓革命的民主主义,今已展其羽翼于世界诸国。”昔尘:《议会政治之失望》,《东方杂志》第17卷第17号,1920年9月10日,第20-21页。 ⑧详见杨天宏:《国会存废之争与民国政制走向》,《近代史研究》2015年第5期。 ⑨《湖南全体人民民选议院请愿书》,刘晴波编:《杨度集》,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489页。 ⑩《致资政院陈情书》(1911年11月17日),刘晴波编:《杨度集》,第542页。南北谈判期间,民、清双方为政权鼎革后“国体”究竟应为民主共和还是君主立宪发生争执。不久南方宣布建立民国。鉴于局势严峻,清廷采纳杨度等人建议,在谈判中提出召开“国民会议”以决定国是。对此,南方断然拒绝。但这只是出于南北政争的考虑,不愿刚刚建立的共和民主“国体”面临可能被颠覆的命运,并非从政治理念上不认同体现了“主权在民”观念的“国民会议”,因而民国建立后仍不断有人重提以“国民会议”决定国是这一主张。 (11)李三元:《代议制之改造与消极投票》,《东方杂志》第21卷第6号,1924年3月25日,第15-16页。 (12)楼桐孙:《改造代议制之具体方案:两会一院制之建议》,《东方杂志》第23卷第16号,1926年8月25日,第19-21页;梁启超:《中国国会制度私议》,《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十四,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1-41页。 (13)孙科:《中国宪法的几个问题》,《东方杂志》第31卷第21号,1934年11月1日,第47-52页。 (14)张君劢指出:“今天国大要求立法院将某项法案交复决,明天又提出立法原则,要求立法院制定法案,此种作风,徒然引起人民心中立法院能力不足的感觉。再次立法院初创之际,偏偏有人批评他,说他不对。试问立法院的地位,如何能有巩固之一日?所以立法院之上,再加一个如国民大会的太上国会,我人期期以为不可。……‘五五宪草’将国民监督政府的权力分属国民大会和立法院两个机关,立法院为中央政府之一部,不像它国国会那样居于监督机关的地位。国民会议则不同,被赋予创制、复决诸权,对于立法院所订法律可提出修正案,并可向立法院提出法律,权力甚大,有类‘太上国会’。立法院是立法机关却非民选,国民会议行使主权却要参与普通立法,叠床架屋,权能交叉。鉴此,张主张削弱国民大会权力,加强立法院的作用,规定立法院由选举产生,行使国会职能。即便仍要保留国大,也应‘化有形之国大为无形之国大’。”张君劢:《中华民国民主宪法十讲》,台北:宇宙杂志社,1984年,第28-29、40页。 (15)钱端升等:《民国政制史》上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35页。 (16)梁启超:《同意权与解散权》,《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第1-5页。 (17)《宪法波澜中之面面观》,《申报》1913年8月29日。 (18)王印川:《致汤议长论宪法》,胡春惠编:《民国宪法运动》,台北:正中书局,1978年,第194-195页。 (19)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下编,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386页。 (20)汉密尔顿曾“一再提到立法机关常有干预、侵犯其他部门权力的倾向”,并据此认为,“总统拥有对立法机关两院法案的否决权或部分否决权是适当的。……我们应更为担心他在必要时不肯运用此项权力,不必过于担心他会过于经常或过多第予以运用,其理甚明”。汉密尔顿等:《联邦党人文集》第73篇,程逢如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372-374页。 (21)罗文干进一步指出:“民国既元,以言官制,则起草者手执日本法规大全选译之,以成吾国各部官制,以言官规官箴,则昔日之弹官制度科举制度举叙制度考绩制度等等,视为满清故物,不合共和,制度既废,人心愈嚣。民国三年,袁氏专政,京外乃有划一之官制,铨叙乃有一定之成规,登庸乃有一定之考试方法,整肃官方,弹官乃设,官俸官规于是乃定,谋官吏保障之法,乃设惩戒法规,免地方干托之风,遂恢复回避本籍之例。虽云复古,然行之两年,吏治稍以整顿。乃袁氏一死,国人则又谓此乃帝制之遗物,有径废弃之者,有虽存之而形同虚设者。故自民国五年以至于今,则又是元年乱后景象,且愈趋愈下矣。”罗文干:《狱中人语》,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正编第16册,台北:文海出版社,1966年,第74-75、119页。 (22)谢彬:《民国政党史》,荣孟源等编:《近代稗海》第6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3页。 (23)Mingchien Joshua Bau,Modern Democracy in China,Shanghai:The Commercial Press,Limited,1927,p.98. (24)光一:《时事短评·国会当然消灭》,《现代评论》第1卷第2期,1924年12月20日,第2页。 (25)详见杨天宏:《论临时约法对民国政体的设计规划》,《近代史研究》1998年第2期。 (26)张国淦:《北洋从政实录》,杜春和编:《张国淦文集》,北京:燕山出版社,2000年,第321页。 (27)于右任:《答某君书》(1912年9月13-17日),傅德华编:《于右任辛亥文集》,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6年,第238页。 (28)张国淦:《北洋从政实录·洪宪遗闻》,杜春和编:《张国淦文集》,第151页。 (29)白蕉:《袁世凯与中华民国》,荣孟源等编:《近代稗海》第3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79-83页。 (30)张国淦:《北洋从政实录·近代史片断的记录》,杜春和编:《张国淦文集》,第356页。 (31)张国淦:《北洋从政实录·洪宪遗闻》,杜春和编:《张国淦文集》,第151页。 (32)梁启超:《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三,第85-98页。 (33)以英国为例,按照威尔逊的说法,英国政府无论实施何种政策和行动都对议会负责,政府官员同时也是立法机构的执行委员会成员,他们的任期由这个立法机构来决定。由于妥善处理了立法与行政的关系,英国是内阁制度最成功的国家,在保持国会立法及监督权力的同时,政府也并不软弱。他引用詹宁斯(Ivor Jennings)的话说:英国政府如果不是世界上唯一最强有力的政府,也是最强有力的政府之一。在法国,由于实施责任内阁制,议会领袖同时也是政府行政官员,是共和国总统从议会多数派中挑选出来的,这与英国的内阁由英国国王挑选的情况颇为相似。威尔逊:《国会政体:美国政治研究》,第68-69页。 (34)参阅张玉法:《民初政党的调查与分析》,《中国现代史论集》第4辑,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0年,第33-45页。 (35)宋教仁被刺身亡,作为同样主张议会民主制的政治家,梁启超不免有物伤其类之感。然而,梁氏所伤感的远不止于此。在追究凶犯及主谋时,梁启超作为国民党的对立党的领袖,自然被义愤填膺的国民党人当做怀疑的对象。为了表明自己与此案无关,梁启超发表了《暗杀之罪恶》一文,极力称赞宋氏为在中国推进议会民主制所作的努力,视之为一流的政治家,认为宋氏之死,是中国民主政治“不可规复之损失”,明确表示,“暗杀者如驯狐如鬼蜮,乘人不备而逞其凶,壮夫耻之”。梁启超:《暗杀之罪恶》,《庸言》第1卷第9号,1913年4月。 (36)胡适:《容忍与自由》,北京:京华出版社,2005年,第251页。 (37)梁启超:《莅民主党欢迎会演说辞》,《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十九,第21页。 (38)陈炯明:《中国统一刍议》(1927年冬),段云章等编:《陈炯明集》,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046页。 (39)陈独秀:《今日中国之政治问题》,《新青年》第5卷第1号,1918年7月,第2-3页。黄远庸对此亦有预感,他说民初国人“尚有一大噩梦,则将来政党之变迁是也,或大势忽变,遂不许他党发生,只许一党存在,亦未可知。若其不然,则将来政党之变迁,殆如读奇门遁甲之书,非常人可解”。黄远庸:《闷葫芦之政局》其二,《远生遗著》下册卷3,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102-104页。 (40)在这样一种政治格局之下,北京所具有的俯视天下的崇高地位迅速下降,国内政治家对它的重视程度亦远不如前。唐绍仪在一次谈话中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北京所发生之事实,于全国无重大影响,北京乃一隅,而非全国,且不能统治全国。当今急务,在乎联合各省成就一种结合,庶日后渐能遵从合宜之当轴。历来北京政府从未为此,且亦未尝图及,不过推翻某某军阀,迎入某某军阀,以暴易暴,徒事激起内争而已。”《唐绍仪与外报记者谈话》,《申报》1924年1月27日。 (41)章太炎:《改革意见书》,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选集》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798页。 (42)毛泽东:《湖南建设问题的根本问题——湖南共和国》,湖南《大公报》“湖南建设问题”专栏,1920年9月3日,第2版。 (43)Harold Z.Schiffrin,"Military and Politics in China:Is the Warlord Model Pertinent?" Asia Quarterly:A Journal from Europe,Vol.3,1975,pp.196-197. (44)章太炎主张分立数国的具体办法是:“或分为二,或分为三,或分为四五,悉由形势利便、军民愿望而成。譬如兄弟分财,反少内讧。此实今日观时立制之要点也。”《湖南考试县长之初复试》,《申报》1925年10月5日。章太炎当然不是国家分裂论者,他所提出的是地方充分自治的主张,深通古文的太炎笔下的“国”可能更偏重“邦”的含义,他主张效法美国实施联邦制,希望在自治的基础上整合国家以实现新的国家统一。这与分裂有本质区别。 (45)胡适:《“五四运动”——一场不幸的政治干扰》,唐德刚译:《胡适口述自传》,北京:华文出版社,1992年,第206-227页。 (46)《林长民之宪法起草谈话》,《顺天时报》1925年11月15日。 (47)详见杨天宏:《民初国会存废之争与民国政制走向》,《近代史研究》2015年第5期。笔者对该文有关国、共两党批判代议制国会走的也是技术性路线的提法有所修正。 (48)毛以亨:《代议革新议》,《东方杂志》第21卷第23号,1924年12月10日,第17-22页。标签:代议制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美国政党论文; 日本政党论文; 日本内阁论文; 英国政党论文; 民主制度论文; 袁世凯论文; 进步党论文; 北洋集团论文; 内阁制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