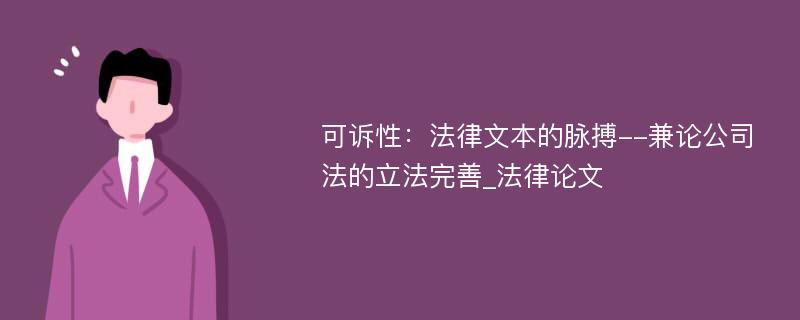
可诉性:法律文本的脉搏——兼论公司法的立法完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脉搏论文,公司法论文,文本论文,法律论文,可诉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可诉性是现代法律的基本特性之一。形象地讲,可诉性是将“纸面上的法”置换为“运行中的法”、尤其是“诉讼中的法”的枢纽,也是沟通立法与司法的纽带。可诉性堪称标识法律文本生命的脉搏,缺乏可诉性的法律往往可能蜕变为形同虚设的“一纸空文”甚至毫无活力的“法律木乃伊”。遗憾的是,忽视对法律可诉性的关照一直是中国立法,尤其是经济立法的通病,缺乏可诉性成为不少法律的表征和症结,难怪某些“看上去挺美”的法律往往在进入司法操作时出现捉襟见肘式的尴尬。下面不妨以公司法为例,对立法尤其是经济立法的可诉性技术缺陷作一番法理剖析。
某些条文明显缺乏可诉性就是公司法的立法缺憾之一,尽管1999年12月25日九届人大常委会第13次会议已对公司法作了重大的修改,但依然忽视了从立法角度解决有关条款的可诉性问题。例如,公司法第54条和第126 条均规定监事会或监事的职权包括“当董事和经理的行为损害公司的利益时,要求董事和经理予以纠正”,却没有规定纠正和制止上述行为的请求方式,尤其是没有规定可能最终“对簿公堂”的诉讼方式,没有明确赋予监事会或监事相应的起诉权。因而,上述未顾及可诉性的条款明显有失之疏漏之嫌。又如,第63条的规定也同样颇为含糊暧昧,既没有界定追究责任的主体,也没有规定追究董事、监事、经理责任的程序,尤其是没有明确规定在上述人员拒不承担赔偿责任时可以以提起诉讼的方式请求法院责令其履行赔偿责任。这种对可诉性的立法疏忽势必会使相关条款的执行或适用陷入无所适从的困境。尽管修改后的公司法对不同利益主体的权利、义务或职权、职责乃至法律责任等都作了比较详尽的规定,但可诉性司法救济条款的“缺席”或“暧昧”依然能使利益主体的权益得不到及时有效的司法救济,可能使利益冲突得不到及时有效的司法解决。如何强化公司法的可诉性的确是进一步修改现行公司法时必须认真对待的现实问题。
可诉性差在其他经济立法中表现得也颇为突出,这或许也是导致不少经济纠纷当事人投诉无门而起诉又于法无据以至迟迟得不到及时有效解决的缘故之一。从一定意义上讲,经济立法的主旨是要使经济行为服从规则治理尤其是法律规制,进而使经济纠纷的解决纳入司法程序,使诉讼成为解决经济纠纷最后也是最权威的一种途径。在现代法治社会,经济纠纷的主流解决模式已由传统的行政干预型转变为现代的司法裁决型,经济立法也应有意识地通过强化法律的可诉性来适应并推进这一有意义的制度变迁。
在我看来,可诉性缺席现象貌似立法技术问题,实质上与立法者立法理念的相对匮乏有关。立法者往往局限于从法律创制的层面,关注法律规范自身在逻辑结构上的完整性,而忽视从将来法律付诸实施的前瞻性视角关注法律的可诉性问题。立法者不是如雕塑家般塑造“看上去挺美”的凝固的“法律木乃伊”,而是应当有意识地为制定法嵌入诸如可诉性之类可激发法律自身潜在活力的“脉搏”或“枢纽”,使“纸面上的法”真正成为嵌入了现实社会秩序,具有鲜活生命力的“活法”,使“文本上的法”具备向“运行中的法”尤其是“诉讼中的法”变迁的潜在可能。依我之见,中国式成文宪法之所以缺乏应有的权威,就在于宪法文本在形式上被宣言性的治国安邦“总章程”所遮蔽,且在立法理念上没有真正将宪法作为一种“法律”(尽管是具有最高效力的“根本大法”)看待,以至宪法的程序性尤其是可诉性规定近乎空白,可以说,正是缺乏诸如程序性、可诉性等活性要素,宪法始终难以摆脱对诸多违宪现象无能为力的尴尬困境。从这个角度讲,强化宪法文本的程序性尤其是可诉性,并通过设立宪法法院或宪法监督委员会建构宪法诉讼制度,才能真正激活宪法条文的内在活力进而彰显宪法至上的权威。
霍姆斯说过一句耳熟能详的名言:“法律的生命不是在于逻辑,而是在于经验。”诚哉斯言,诉讼可以激活法律条文的生命,可以为法律自身的形成和发展积累经验,因而我想进一步对霍氏名言作一番司法维度的“加工”,亦即:法律条文的生命在于它的可诉性。一言以蔽之,可诉性堪称法律文本的脉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