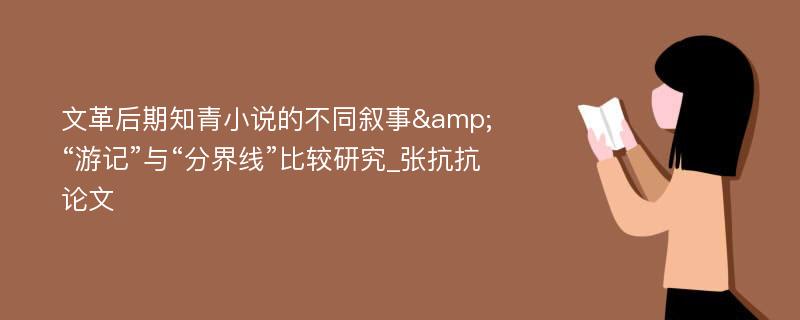
“文革”后期知青小说的不同叙述——《征途》与《分界线》的比较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分界线论文,知青论文,文革论文,征途论文,后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50年代开始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到了“文革”时期达到高潮。最初的轰轰烈烈之后,1970年代,全国性的知青运动已经从最初的高歌猛进陷入困境,同时,大规模的“招工、招生、提干、参军”,知识青年纷纷想尽办法回城,所谓的“扎根农村干革命”的号召已经显得空洞无力。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这一时期却出现了一批歌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长篇知青小说,最有代表性的是上海人民出版社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有计划地出版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丛书”,这套丛书有着较为明确的目的:“为了及时地用文学形式反映这个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新生事物,艺术地再现我国青年一代在广阔天地里经风雨、见世面的斗争生活和锻炼成长的历程,鼓舞他们更好地前进,我们于一九七○年秋着手组织创作这一题材的长篇小说。”①
“文革”后期,上海已经成为激进革命的重镇,上海人民出版社也善于紧跟政治形势,抓富于意义的重要选题。这批知青小说给我们留下了研究“文革”后期知青运动和文学创作的重要资料。郭先红的《征途》、张抗抗的《分界线》即是这套丛书较有代表性的作品。《征途》是较早以长篇小说的形式反映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作品②,《分界线》是由知青作家创作的知青题材长篇小说,这两部小说均以上海知青在黑龙江边疆这片广阔天地中经风雨、见世面,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扎根落户干革命的事迹,塑造了以知识青年的英雄形象。受到写作语境的制约,这些作品有着“文革文学”的诸多共同特征,尽管如此,我们仍然能够从这种叙述的缝隙中找出这些小说各自的特征和意义点来,进而找出这些作品思想的出发地和落脚点,这是我们对“文革”时期“公开的文学界”进行“个案研究”的一个开始。
一、“再教育”与“塑造知青英雄形象”
“文革”时期的小说(尤其是长篇小说)从情节构思、人物设置到叙述方式,都有着非常模式化的特征,洪子诚将这种模式化概括为“作品人物符码化和情节结构规格化”③倾向。这种“人物符码化”首先是“高大完美的主要英雄人物”,第二是“围绕主要英雄的若干非主要的英雄或正面人物”,第三是“作为英雄人物的对立面,通常是阶级敌对力量”,即反面人物。在此之外,还有“在正面力量与其对立面之间,设置了各种问题人物(落后人物)”。“情节结构规格化”体现为:围绕主要事件(革命事业、生产建设等)展开阶级冲突。常见的结局是:“主要英雄人物在群众的支持下,教育、争取问题人物,战胜、孤立敌对势力。”④这种叙述模式显然是遵循“三突出”创作原则的结果。
作为“文革”小说重要题材之一的知青小说当然也无法出离这样的创作规则,只是人物设置和情节安排在突出阶级斗争的前提下更具有知青生活的符号特征。在人物设置上:主要英雄人物具有知青身份(出身一般根正苗红,革命烈士家庭或工人劳动阶级);与此同时还有和知青英雄并肩作战的老领导(老领导一般具有战争经验,并且担任书记或指导员职务);对知青进行再教育的“贫下中农”角色也必不可少(“贫下中农”一般苦大仇深,具有革命血泪史);相应地,作为反面典型的阶级敌人大多具有和国民党有关的身份和历史,对现在处境不满,拉拢、腐蚀知识青年,试图破坏社会主义革命;受到阶级敌人影响的人物就是落后干部和落后知青,落后干部(一般担任生产队长、工作组长职务)实行“利益挂帅”,不自觉地走上资产阶级错误路线,落后知青多数出身知识分子家庭或家境较好的城市家庭,追求个人名利和生活安逸,所以容易受到阶级敌人的诱骗。⑤
一般说来,塑造知青英雄人物形象、反映两条路线斗争、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斗私批修、扎根农村干革命等也是1970年代知青小说都会涉及的主要问题。但是,一部小说的创作在触及多个问题的同时,总会有自己的侧重和选择,而这恰恰就是小说的意义点所在。
郭先红的《征途》是“文革”时期知青题材小说中较有分量的一部,并早于张抗抗的《分界线》列入上海人民出版社的第一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丛书”。上海知识青年奔赴黑龙江边疆插队落户干革命、经历阶级斗争的考验,成长为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的故事,是两部小说的共同主题。除了“上海知青”和“北大荒”这两个关键词之外,《征途》和《分界线》在情节构思、人物设置、叙述方式上都在符合“文革”小说规范的前提下,有着诸多相似性。但是,细读起来,在“知青英雄形象”的塑造和如何呈现“阶级斗争”这一宏大主题方面,这两部小说的着眼点还是有很大不同。
塑造知青典型形象,是知青题材小说的首要任务。“文革”中知青小说的情节也多是围绕着知青英雄在进行革命事业中和反面人物的斗争而展开,当然,知识英雄的斗争不是孤立进行的,整个小说情节的展开不能缺少其他英雄人物或正面人物的支持、关心和有力帮助,从而造就知青英雄成长的土壤环境。这也是和当时伟大领袖的“再教育”指示不可分割的。1968年12月毛泽东作出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这一观点,在当年被反复宣传、引申、论证,成为“文革”中上山下乡运动的基本理论,又称“再教育理论”。⑥“三突出”的创作原则要求“在英雄人物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主旨则是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强调与工农大众的结合。如何把“塑造知青英雄形象”和“接受再教育”成功地结合起来,是知青小说面对的一个很难的平衡问题。
《征途》中的钟卫华和《分界线》中的耿常炯都是作者着力塑造的主要英雄人物。《征途》构造了知识青年如何在老领导和贫下中农的关怀指导下进行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成长小说模式。《征途》的“内容简介”也将作者这一努力展示得非常明确:“在贫下中农的热情关怀教育下,他们刻苦改造世界观,茁壮成长。小说以生动有力的笔触,描绘了大队党支部书记李德江、知识青年钟卫华和老贫农关东海等高大的英雄形象,展现了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锻炼的我国青年一代在继续革命的征途上焕发昂扬的精神风貌。”⑦在核心人物钟卫华的周围,有着一系列英雄的群像。
也正因为如此,有研究者敏锐指出《征途》中“描写知青英雄接受再教育的场景中,英雄人物(知青英雄)‘高、大、全’的展示受到一定限制,而施与再教育者(一般是老领导)得到重点突出”⑧。这一点,我们在小说中也看得非常清楚,老支书李德江、老贫农关爷爷,在指导帮助钟卫华成长的同时,显然也抢去了英雄不少的“风头”。《征途》中,革命建设事业的对立面主要有阶级敌人张山和落后的生产队长于春保,对付这两个人,老支书李德江显然比年轻的钟卫华更有经验和威力,他既能够坚持正确的方针路线,又能够凭着丰富的经验识别敌人的阴谋诡计,最重要的是能够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力挽狂澜。在第六章“较量”中,面对敌人信号弹的挑衅,大队根据县民兵工作会议精神,决定组建武装基干民兵和动员群众挖土坑、架电线,“备战、备荒”,可是大队长于春保却担心耽误生产,一心想多干点庄稼活,搞副业,好年底分红。局面僵持不下:
(钟卫华)口气平和地问:
“于队长,你这话啥意思?”
“啥意思?”于春保以教训的口气对钟卫华说:“这还不是‘和尚头上的虱子——明摆着的玩意儿?’副业抓不上,春耕备不好,脑门上长瘤子——净搞些额外负担,到年底算总账分红的时候,让大伙喝西北风去呀?……”
于春保话音刚落,钟卫华尽量克制住自己说话的声音,用极大的耐心进行说理辩论:
“于队长,你对组建武装基干民兵和架设电柱的重要意义还没有搞清楚。党要我们所做的一切都必须从广大社员的根本利益考虑,从革命的长远利益着眼。这和群众的眼前利益也不矛盾。我们搞的是劳武结合,是‘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是‘农民以农为主’,‘也要兼学军事’。这是毛主席为我们全国广大农民指出的方向。挖土坑埋电线杆子是战备任务。可是你想的是……”
……钟卫华站起来,义愤地说:“面对野心勃勃的社会帝国主义,我们要提高警惕。毛主席教导我们要有准备,‘有了准备,就能恰当地应付各种复杂的局面’。我们埋电柱、搞武装民兵、登岛巡逻就是这个意思。一旦敌人打过来……”
“打过来也不要紧”,于春保重新抬起头来,打断钟卫华的话,满有把握地说,“有解放军顶着,枪对枪、炮对炮地跟兔崽子们干。……”
……“反正我是‘灶王爷上天——有一句说一句’。我看差不离该散会了吧!”说罢,抓起貉壳帽子往头上一扣,站起来准备走。⑨
这段描写可以看出几个问题,一是队长于春保自以为经验丰富,劳苦功高,并不把知青钟卫华当回事;二是钟卫华在说服的过程中,运用的多是一些大道理。小说不厌其烦地写到他经常深夜学习马克思、列宁、毛泽东的书籍到天亮,口袋里时时装着红色的宝书,遇到解决不了的问题首先想到的是求助于《毛泽东选集》。但是我们看到,很多时候,这种至高无上的理论固然能够在气势上压倒人,并不能真正使人心服口服,这使得钟卫华的革命工作面对于春保这样的“老领导”时也遇到了不小的阻力。与其相比,李德江不仅有政策上的远见,更有过人的经验和胆识,也正是他晓之以理,工作有理论、有方法,在关键时候能够挺身而出,解决了不少困扰着钟卫华的难题。
所以,在《征途》中,李德江才是真正的“卡利斯马”式人物,这一点,显然与“三突出”的文学理论有一定不符之处。当然,作者这样的安排,并不是有意违背“三突出”原则,而是有意凸显“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这一伟大号召。小说结尾处,作者通过“入党”(在“50-70年代”小说中,加入中国共产党意味着英雄形象的最后完成)后的钟卫华的思考点明了“征途”的寓意和小说的主旨:“革命征途道远任重啊!下乡上山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才只有不到一年的时间,这只是万里长征的起点啊!⑩
《征途》将小说的重心放置在知识青年如何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层面上,因此老领导和贫下中农的叙事自然占据了相当的分量。与此相比,《分界线》中,老领导和贫下中农所占的分量相对减少了许多。在塑造知识青年耿常炯这一英雄形象时,“三突出”理论把握得更为到位。耿常炯刚出场时,就是个较为成熟的英雄形象,相比于钟卫华经常要接受老领导李德江的支持帮助,耿常炯的“老领导”周朴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并不在战斗现场,小说更多的是显示出这位知青英雄独立的思考能力和行动能力。小说中,对尤发的斗争、挽救杨兰娣、和落后干部霍逦之间针锋相对的斗争,都显示出英雄的超人的魄力和胆识。他带领知识青年涝时开渠、洪灾筑堤,确保了遭受涝灾的东大洼,坚持毛泽东的革命路线,把农场办成粮食生产的基底,以事实教育了“利益挂帅”的工作组长霍逦;他以自己扎根农场的坚定信念,给一心上大学的薛川上了生动的一课;他大胆地“将计就计,引蛇出洞”,使利欲熏心、破坏农场建设的尤发露出本来面目,同时也拯救了迷途知青杨兰娣。
从张抗抗提供的资料来看,《分界线》的创作和修改中,上海人民出版社的编辑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写出初稿之后,出版社曾专门邀请张抗抗去上海“改稿”。“文革”后期的上海正是激进文化的摇篮,“三突出”理论和“两结合”的创作方法成为进入主流文学界必须遵循的宗旨,张抗抗正是在这里努力学习运用,将作品写得符合出版社的要求。她非常自觉地将塑造知识青年英雄作为写作的重中之重,耿常炯这个人物“倾注了全部的心血和热情”:
修改中遇到比较多的问题,是关于人物的塑造。在当时,尤其是上海,“三突出”理论占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任何人都不可能违反它、超越它,我也绝不例外。我正在学习如何掌握“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我必须用全新的思维,来把握我的小说人物。
那并非完全是违心的,而是半信半疑又亦步亦趋的。
我在小说里鞭挞那种口头的革命派,鞭挞了挖社会主义墙角的新生暴发户,我批判了一个故步自封、因循守旧的领导干部;我倾注了全部心血和热情所刻画的主人公耿常炯,是个有思想、谋取个人利益的优秀知青典型——这实际上是我心目中所推崇所景仰的知青形象,是我头脑中“理想主义”的产物。(11)
二、“阶级斗争”如何呈现
除了知青英雄形象之外,阶级斗争展开具体内容的差异也能够显示两部小说的区别。“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是“文革文学”的主旋律,阶级斗争在宏观上往往表现为走资本主义路线和社会主义革命路线之争。按照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逻辑,阶级斗争不仅体现在波澜壮阔的革命斗争中,还往往体现在日常生活的具体场景中,而文学创作就是要把这宏大叙事落实在每一个具体的情节展开和每一个活生生的人物上面。
《征途》和《分界线》都是知识青年在具体的阶级斗争中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事业、成长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的。但是具体考察,两部小说对阶级斗争主题的具体展示仍是有所不同的。具体说来,《征途》中的阶级斗争不仅仅体现为两条路线的斗争,更多体现为新旧社会的对立。小说花了不少篇幅来追溯钟家和关家在旧社会遭受的压迫,并让钟妈妈——钟卫华的母亲、关东海老人来向知识青年“痛说革命家史”,对知识青年进行再教育。小说中主要的阶级敌人——张山,一直对农村的革命事业进行破坏,个中原因最后才揭示清楚,原来他是潜伏在人民群众中的国民党特务分子,解放后一直以“老贫农”的身份在我们内部隐藏二十多年。这个国民党特务,解放前就欠下了人民群众累累血债,“文革”期间又试图“立功”投奔主子。而知识青年内部的冲突,除了有些被“漫画化”的娇气的万莉莉,并没有很明显的矛盾和冲突。
《分界线》中,对知识青年问题的反映显然占据了相当大的篇幅,小说沿着两条平行的线索,除了“路线斗争”之外,小说重点写了知识青年内部的矛盾和动摇:一心想上大学的薛川和受到“返城风”影响的杨兰娣。尽管作者采取和“文革”主流话语一致的口径解决了这些问题,但是,作为知识青年一分子的张抗抗,对知识青年内部中的思想分化问题的深切感受还是体现在作品的字里行间。所以,《分界线》一方面非常严格地遵循了“文革”“样板戏”所确立起来的基本原则,包括“两条路线、两个阶级的斗争”、“三突出”、“两结合”;另一方面,它比较真实地展现了“文革”时期知识青年思想上就“扎根”与“返城”之间的争论、农场生产建设中存在的难以解决的困难等。(12)
由此看来,《分界线》较之《征途》来说,更带有“知青小说”的特征,它更多地触及到了贯穿上山下乡运动始终的一个基本主题——“扎根”和“拔根”问题。《分界线》的内容在写作前后经历了很大变化,但小说一开始确立的“扎根”这一基本主题在修改前后并没有变化,而且在题目还没有的情况下已经非常明确:
题目暂时没有,先空着吧。重要的是故事,一定要标新立异,出奇制胜。
我很快决定,要写三个杭州知青,分别去了北大荒、海南岛和浙江农村;先分头写出他(她)们在各个地方的生活,然后在他(她)们回杭州探亲时候,为将来的前途,为扎根还是返城,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当然,经过痛苦的思想斗争,最后,他们统一了志向,又各奔四方……
——张抗抗:《谁敢问问自己:我的人生笔记》(13)
在“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号召下,“大有作为”的理论与知识青年所面对的现实问题在很大程度上的脱节,是贯穿上山下乡运动始终的一个问题。也就是说“扎根”与“拔根”始终是困扰着知识青年的根本冲突。尤其是1970年代知青运动陷入困境,各地知识青年的返城风愈演愈烈,国家基于多种因素考虑,将上山下乡运动重新正名为“党的一项具有战略意义的正确方针”。1967年5月4日和7月9日,《人民日报》连续发表社论,系统阐释上山下乡的政治意义,突出强调它在三大革命、培养和造就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缩小三大差别、巩固专政、防止复辟等方面的重大作用,这种阐释奠定了上山下乡运动的基本理论框架。与此同时,各种报道将支边青年返城称为“一场尖锐的阶级斗争”。(14)在《分界线》中,政治眼光敏锐的耿常炯正是将“薛川考大学”、“杨兰娣返城”作为阶级斗争的对象来挽救教育的。在这一点上,张抗抗的《分界线》显然触到了一个敏感的时代神经。
《分界线》中坚定的“扎根”立场和对阶级斗争主题的呈现,后来在作者对自己“文革”时期创作的反省中被认为“本质上是不真实的”,原因在于她“根本看不到当时日益尖锐的社会矛盾,也没有能力去认识和表现”。(15)但是,在我看来,《分界线》作为一部知青写作的知青题材小说,显然是触及了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文革”后期知青生活的许多矛盾和困境,而且,这也是这部小说的意义和价值所在。
三、“时代精神”与“生活气息”
体现鲜明的“时代精神”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对文学的要求,而“时代精神”更多地体现为契合主流意识形态的要求。“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应该是“文革小说”最为鲜明的时代精神之一,作为主要阶级斗争工具的文学,就是要用自己鲜明形象的艺术感染力去呈现这种时代精神。正因为如此,“体验生活”才是必须的,只有这样,文学即便是以“为政治服务”为目的,但也不是干巴巴的说教,而是富于“生活气息”。
《分界线》在这一方面可以说是个成功的典范,作品出版的时候,它的“内容简介”给予小说这样的高度评价:“这部小说时代精神较强,语言生动,并富有北大荒的生活气息。”(16)而同样写知青生活的《征途》就被认为是“热情可贵而可信程度不高”(17)。
这两部作品的具体创作情况也许可以部分地揭示这种差别。《征途》属于“受命之作”。1970年秋天连续的暴雨,逊克县山洪爆发,河水冲跑了摆在地头的战备电线杆。正在双河大队插队的上海知青金训华,奋不顾身跳进河水里捞电线杆,被洪水冲走牺牲。金训华的事迹传到中南海,周恩来总理指示要把金训华的事迹写成小说,向全国推广。上海文艺出版社到黑龙江省组稿,组织上把采访金训华事迹、创作小说的任务派给了当时哈尔滨市文联的驻会作家郭先红。工人出身的作家郭先红有着苦难的童年,家境贫寒的他没读完高小就辍学,14岁就进厂当学徒。解放后,身为工厂主人的郭先红在《北方文学》上发表短篇小说《站起来的人们》,这篇反映工人自力更生的短篇小说受到老作家茅盾的赞扬并将其推荐到《人民日报》副刊发表。后郭先红受长春电影制片厂之邀将小说改编成电影在全国上映。郭先红自此获得了巨大荣誉,作为优秀工人作家代表参加1960年全国第三届文代会,受到国家领导人的接见,同时被调到市文联当专业作家。接受这个任务后,经过一年半的深入采访和体验生活,郭先红终于完成了48万字的小说《征途》。从创作方法上,《征途》更多继承了十七年文学的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特征,因为缺乏与知识青年对社会生活的复杂联系,在很多地方是用阶级斗争的理论来图解现实。而受命创作奠定的歌颂基调,也使作者毫无保留地肯定知识青年的上山下乡运动,以一种藐视困难、征服自然的心态书写知识青年在北大荒艰苦自然环境中所面临的困难,相当程度上忽视了知识青年的真实生活和心理状态。
与此相比《分界线》的创作显然更多是作者的个人生活体验。1969年,怀揣文学梦想的张抗抗离开杭州老家到遥远的北大荒,残酷的现实使作者曾陷入“深深的失望和迷惘”,写作成为她“拯救”自己、努力寻找“光明”的途径,她开始尝试写作发表作品。《分界线》发表于1975年,准备于1973年,写作于1974年。参考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有关文献资料,《分界线》准备写作前后,正是大规模的知青“返城风”盛行的时候。上山下乡工作已经陷入困境、步履维艰,知青问题已经成为一个社会性的问题,许多地方知青前途无望,集体自杀。就连作者本人也是时刻准备着考大学,在大学梦破灭之后开始写作。
所以,《分界线》虽然是按照文革文学的规范来塑造英雄人物、展现阶级斗争,但同时它也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了自觉的文学意识,是作者“苦闷的象征”,它部分真实地展现了知识青年当时的真实生活、愿望要求。正如有些研究者指出的,这些知识青年英雄的斗争,“虽然表现为对追求实际利益、重视生产、经济的上级干部的抗拒和批判,但是他们的批判始终和知青地位、权益的保障有关;要求改善电影院的环境,对知青大学的构想,对培养青年专业人才的建议等,都是知青的‘真正确立知识青年是农场主人的观念’的要求”(18)。相比于《征途》中那些高呼口号来展现革命激情的场景,《分界线》的确显示出较多的文学色彩和“生活气息”。
这两部题材相似、主题相近的“文革”主流小说,在塑造人物、呈现主题方面却又有如此大的差异和不同。当然,仅仅指出这种差别并不能呈现出深刻的文学史意义来,但是,这却是我们研究50-70年代“公开的文学界”的另一个起点。以这些作品的细读为出发点,有助于我们祛除对“文革文学”乃至“50-70年代文学”“整体化”和“本质化”的理解,打破“文革”时期“公开的文学界”“千人一面、千部一腔”的文学史结论。同时,“文革”后期发表过重要作品的作者,到了新时期之后,有的基本上销声匿迹,有的却实现了创作的成功“转型”,成为参与“新时期构建”的重要作家,前者如《征途》作者郭先红,后者如《分界线》作者张抗抗。这些作家在新时期的“转轨”与他们之前的创作有着什么关系?这种关系能否帮助我们进一步清理“文革文学”和“新时期文学”的关系?对于文学史研究来说,这都是需要进一步深入思考的地方,本文的比较仅仅是一个微小的起步。
注释:
①《征途·编后》,上海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
②有研究文章说《征途》是国内第一部反映知青上山下乡的长篇小说,见《文革主流小说的话语形态及其延伸》,肖敏,首都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另外,加拿大学者王仁强在《模范和动摇者——剖析70年代三部知青小说》中也这样提及过,见《当代青年》1992年第6期,《分界线》是第一部由知青作家写出的知青题材的长篇小说。笔者认为这种说法不太准确,因为在《边疆晓歌》、《军队的女儿》等知青题材小说均于1960年代出版,而由知青作家汪雷创作的《剑河浪》(1974)也早于张抗抗的《分界线》(1975)的出版。但是《征途》和《分界线》确实是“文革”时期较有分量的两部知青小说代表作。
③④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10页,第209-210页。
⑤⑧(18)对知青小说模式的分析参照了韩国研究者曹惠英的论文《考察过去,映射现在——文革时期知青题材与红卫兵写作研究》,《二十一世纪》网络版,2003年11月号,总第20期。
⑥(14)刘小萌:《中国知青史·大潮》,当代中国出版社,2009年版,第136页。
⑦郭先红:《征途·内容简介》,上海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
⑨⑩郭先红:《征途》,上海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319-320页,第733页。
(11)张抗抗:《大荒冰河》,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66页。
(12)张红秋:《努力跨过“分界线”——论张抗抗从“文革”到“新时期”的创作转折》,《当代文坛》2006年第6期。
(13)(15)张抗抗:《谁敢问问自己:我的人生笔记》,时代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第179-180页,第186页。
(16)张抗抗:《分界线·内容提要》,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17)[加拿大]王仁强:《模范和动摇者——剖析70年代三部知青小说》,徐有威、沈波摘译,《当代青年》1992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