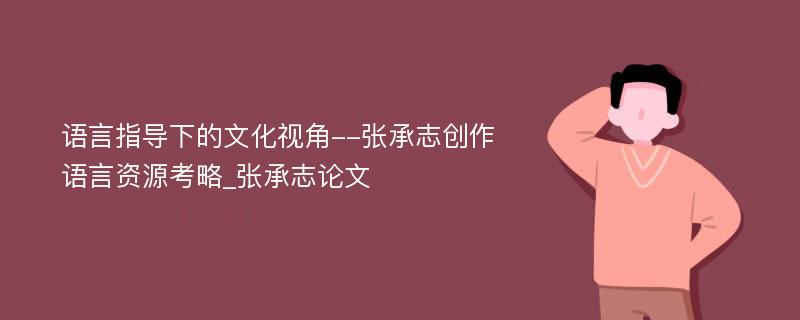
语言引领下的文化透视——张承志创作中的语言资源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语言论文,透视论文,文化论文,资源论文,张承志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让自己写出的中文冲出方块字!”
——张承志
在我们深入张承志的创作视域时,“汉语写作中的回族作家张承志”便是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也是读解他创作文本的一个“结”。亦即,张承志摆脱不了汉语的写作方式以及这种方式背后的文化抑制。我们也在剥析此“结”之中发现了:他的创作历程简直就是他一步步试图找寻真正属于自己的语言形式的艺术跋涉之途。这找寻,本身又是异质文化间相融互揉的一种努力!
一、语流的成因
一般来讲,语言的内容和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语言的词汇多多少少忠实地反映出它所服务的文化。亦即,语言是高一层次的文化现象。这又主要显现在以下四方面:“第一,语言的习得是无意识,对所有的人都是平等的”;“第二,语言是人类文化成长的关键”;“第三,语言是文化现象流传广远和长久的工具”;“第四,语言是文化的代码。每一种语言都有它的文化背景。”(注:游汝杰:《中国文化语言学引论》,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年4月版,第16—17页。 )而“文化背景包括各个时期的历史进程、社会状况及其变化、民族特点与习俗、民族语言、特殊的地理环境等,涉及的方面很多,可归纳为物质的、制度的、心理的三个层面。”(注:宋永培、端木黎明编著:《中国文化语言学辞典》,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版,第27页。)联系张承志的人生阅历,就会发现:他在汉文化(当然也包含他与同代人所受过的那点西方文化的影响)这一大背景下,又明显受过三个亚文化背景的制约,而这,便相应地形成了三股语言资源的支流。我们“走进”他的语言疆界的前提,便是探讨这三支语流的成因。
(一)京都权威语流(庙堂语流):
出生于北京的张承志,自小在汉文化的中心腹地——皇城根长大。皇城根文化主要以悠闲自得、自负自傲而显示其权威专断性。尤其在五、六十年代,这种亚文化又被红色激情膨胀了原本的优越感。发源于京都的那场“文化大革命”,在带来民族浩劫的同时,也制就了一批“红色词汇”,例如“文革”、“红司”、“牛鬼蛇神”等等。在语言学家看来,某一时期的词汇有多少并不重要,只要有需要,可以随时用来制造新词。因为所有的语言都有足够的资源。也正是这些极富时代质素的红色词汇又在一定意义上塑造着他们这一代人特有的人格心理、制约着他们的行为准则和价值取向:试想,假如“革命”、“理想”、“共产主义”等这些词语不在张承志们的心里作响,他们会为了“革命理想”而激情振奋,又满怀革命理想”去“广阔天地”里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吗?特别是“红卫兵”这一特定的人格身份,使张承志们一时成了那个特定时代的激情载体。他们欲运用这些词汇来统摄舆论导向、影响人们的言行、营造时代的氛围。于是,这些红色词汇便以权威、中心话语的面目在那个“共名时代”里被集体与个人同声部地运用着,并对人们(尤其是红卫兵们)以潜移默化的方式渗透着特定时代的文化因子。浪退潮息后,自然会遗下深远的文化影响。张承志等“知青作家”在进入创作之初,都会自觉不自觉地动用自己语库中的这部分资源来表达自我的。他们不约而同地严守“文以载道”的创作圭臬,恐怕又有在此找到充分的语言理由。
(二)北方民间语流(民间语流):
张承志曾插队内蒙草原、游历新疆天山南北且专攻过北方民族史。他声称“有幸在自己最年轻好学的时候深入到这个文化以及创造这个文化的勤劳牧民的底层,长见识,添学问,逐渐地懂得了和接受了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相知:谈谈小说〈雪路〉》)并因此而认识了蒙古族、哈萨克族、维吾尔族等其他北方少数民族。而他从感性和理性上均接受了北方游牧文化的浸染,最初却是凭借掌握少数民族语言而闯入这一亚文化圈的。因为,不同的语言代表着不同的文化。当他在世界观未完全定型时,闯入了异族文化天地接受贫下中牧再教育。于是,掌握民族语言便成了他在陌生语境中安身立命的前提。在某种意义上,民族语言不仅成了他与另一个语言集团交流思想、联络情感的主要工具,也成了他闯入另一个文化圈的通行证。随着各种语词的逐步领悟,他也步入了一个藏污纳垢的底层民间世界。那些极富地方性与民族性特征的词汇却正反映出被压抑的民间如何以自己的方式拒绝来自权力的庙堂文化:如骏马之于牧民的美意识、沙漠之于草原的参照、莫台烟之于底层交往……他的成名作——《黑骏马》也是借助了北方游牧文化的质泽而成功的。
(三)母族宗教语流(宗教语流):
张承志的那“一腔异血”里已储就了伊斯兰文化的精神基因,命定般地闯入母族文化圈后,才真正意识到母语的存在:
“母语的含义是神秘的……一支异乡人在中国内地、在汉文明的大海中离聚浮沉,居然为自己重新选择了母语——这个历史使我感到惊奇。”
——《美文的沙漠》
事实上,回族丧乡失语的背后却是被迫趋同的无奈心理与语言的借用、杂交、双语直至同化的漫长过程。回族祖先曾操用的阿拉伯语、波斯语等主要残留在信仰、民俗未被同化的底层回民的日常口语及教内文献里。这些残留的成分通常被称作语言化石。而回族为自己重新选择的母语则是他们对这些语言化石的利用与再造以及对汉语固有的包容性的创造性发掘与利用:
(1)音译词:
乃玛子(波语)——礼拜;埋体(阿语)——尸体。
(2)音译加意译借词:
洗阿布代子(波语)——小净;做乃玛子——做礼拜。
(3)音译语素加汉语语素组成新词:
要乜贴——要饭的;望理体——吊唁;和遗体告别。
除了在日常生活和宗教礼仪中大量活用阿、波语外,还在他们的姓氏上顽强地保留着祖先遗留下的姓氏音节:马、海、哈、麻、穆、纳、忽、萨等。
除利用阿、波语词残留外,还有纯以汉字组意的词汇,一般可以望文生义,但作为一个具有特殊含意的语汇,仅在回族中流行。如:“归真”——逝世之意;“完(无常)了”——死之意;“口唤”——同意或认可之意。回族除了避讳说“死”之外,更避讳说“肥”,常用“壮”代之,恐怕是避说“猪肥马壮”中的“猪”字。而回民又是禁食猪肉的……这些微妙的用词心理是不易被族外人所察觉的。值得强调的是,回族能为自己又重新选择了一种特殊的语言表达式,伊斯兰教所起的媒介作用是不容否认的。可以说,《古兰经》不仅是他们日常生活中言行规范的准则,也是祖先留给他们可以代代相传的语言文化的教科书。就在他们每日五次诵念阿语的《古兰经》的同时,也在本能地持守着祖先的语言、文字与文化。这实为民族情感上的语言忠诚问题。
然而,满族的汉化则为另一种情形:满人曾以统治者的身份大举入了北京城,以胜者心态推行汉化政策,在化汉为满的掠夺中,逐渐遗失了满人自己。同样都是汉化,满人就比回族来得主动、迅速,也就更彻底。回族原本就“大分散”于民间底层,又被清政府的多次“剿回”而逼向穷山僻壤。这种迥异于满族的生存处境与民族心态,便使他们对统治者推行的汉文化怀有本能的拒斥,他们宁肯后代无文化也不能让他们失去伊玛尼(信仰),显示了一种对孔孟文化的最坚决的对抗。
显然,同样被汉化,满族与回族的结果不同;同样操汉语,回族与汉族的用词心境又迥异。这事实本身不也正说明回族拥有实质意义上的“母语”吗?
总之,勘察了张承志的语言资源后,我们发现:庙堂语流的主要特征是:语意直白、外露、庙堂色彩浓厚;语速急、节奏快且有激情;共名性词汇居多,缺少个性特征;民间语流的主要特征是:语意丰富、内涵深远、极富民族特色;语速平缓、节奏悠长、情感奔放、粗犷;拒斥权威语词,共鸣性较弱;宗教语流的主要特征是:双语混用、寓意深邃;伊教色彩浓,本能抗拒异质文化的渗入;语意多歧义,隐晦难解,共鸣性差。同时,我们也感到:张承志这位多种语言的操用者,实为地道的文化混血儿。因为,在闯入不同的亚文化圈的同时,既掌握了异族的语言,又汲取了异族的文化,并巧妙地战胜了由此而生的内心冲突与困惑。当他动用不同语流进入创作时,逐渐找到了真正属于自己的语言形式。探寻的艰辛与曲折,又在语流运用中得以印证。
二、语流的运用
在前《心灵史》阶段:语言是表达工具,存在是被表达者,作家利用语言来描写客观的人与事,又在人、事上涂染作家主观的情与理。于是,“圈外人”的情与理便和“圈内人”的生活间产生了无法弥合的“夹缝”。起步文学不久的张承志就已隐约感到此“隔”所带给自己的“痛苦”:因感古歌《黑骏马》“是理解蒙古游牧世界的心理、生活、矛盾、理想,以及这一文化特点的钥匙”(注:《张承志文学作品选集·散文卷》,海南出版社,1995年8月版,第31页。 )而创作了同名小说,决定“用民歌来结构它”,但却终未达到“朦胧感到的飞跃”。原因恐怕在于作家在当时并未真正领悟到:“黑骏马”和牧民特有的生命观及古歌终句中“不是”所蕴藏的深刻的人生启悟。用一个不太恰当的比喻:小说以古歌来结构全文,如同一件西装上镶了民族手工织的花边,和衣服本身不协调。这也许才是作家真正之“痛苦”吧?
同样反映游牧生活的《春天》、《顶峰》和《绿夜》等,均因皮毛般地转述了几个异族生活片断而发抒了较空泛的激情,有些甚至有些矫情之嫌。
展示母族生活的《黄泥小屋》,其创作初衷是为了思索“人的处境到底是什么?”的哲学命题,因而在小说中“把人划分成五种符号——食、色、劳动、宗教、人本身——用五个人物来代表。”(注:张承志:《我所理解的民族意识》,《民族文学研究》1987年第5期。 )这便有了主人公为远方闪隐的“黄泥小屋”而盲目奔赴的结局。同样,《九座宫殿》和《残月》的主人公们也都是靠“念想”存活的人。但是,作家在当时,并未真正领悟到:这种支撑生命的“念想”与母族血泪历史间的内在关联和因果关系。
反映同代人生活的《北方的河》与《金牧场》等较集中地体现了他的“红卫兵情结”。人物多为作家情、理的寄存物,因被过浓的探问激情和过硬的理辩思省而淹没了血肉个性。更因作家与人物几乎完全的叠合而带来的局限又影响了作品应有的共鸣度。尤其是《金牧场》,简直就是作家从60年代到80年代个人经历的重大事件及其思考。当他突破自我狭小天地而感悟人生、体验生命真谛时,他便弃“牧场”而选了“草地”!
在后《心灵史》阶段:作家逐渐地摆脱了语言工具论的局限,还原了语言自身特有的独立审美表现力。语言与世界的同维性,便让我们领略了语言的生命底蕴。此时的作家,已将语言当作文本所展示的对象,文本世界被包含在语言本身的展示中。不同的语流浸透着不同的文化因子,动用不同的语言资源也便动用了不同的文化资源。至此,语言已成了文化的代码。而且,词汇是语言的基本构素,是语言大系统赖以存在的支柱,因此文化差异在词汇层次上体现得最为突出,涉及的面亦最广泛。作家也正是借一个个关键词的领悟性展示而和我们一同步入了异族人民深广神秘的文化天地。
在《金草地》、《胡涂乱抹》及《黑山羊谣》等中,较集中显示了作家对北方游牧文化的特有体认,而这又是凭对“骏马”和“nutak ”(努特格)等关键词的纵深描写来达到的:在马背民族心目中,“骏马”还有更为特殊的词义:(1 )马是“一种实在但又比生活好些的希望”:在终无止境的“逐水草”的人畜跋涉中,马不仅是人强有力的脚,更鼓舞着人的意志和欲望,使其成为人本身的一部分,完成着人已经不敢想象的事业;(2 )马是“牧人心中的美神”:他们认为骏马集中了一切生物(包括人也在内)的优点,“骏马的形象和对骏马的憧憬,构成了游牧民族特殊的美意识”(注:《张承志文学作品选集·散文卷》,海南出版社,1995年8月版,第284页。);(3 )女孩是“马倌”:在天山深处的哈族老人眼里,马是“骏的”,马又是“真主造化的一种清洁的动物”,其“性情难以捉摸,就象姑娘一样”。(注:《张承志文学作品选·中短篇小说卷》(同“散文卷”),第394页。 )若缺乏对上述游牧民心情的理解,特别是缺乏对他们承受的生产和生活样式的理解,就很难明白古歌《黑骏马》为何把爱情和一匹不相干的骏马扯在一起。作家在创作同名小说的当初,也许未能明确意识到此,但在《美丽瞬间》尤其在《金草地》中,对“骏马”的感悟可谓地道在行了:白马亚干成了母子大迁徒中最强有力的成功保障;红马星、忽伦成了“我”心目中青春之美的象征;黄马希腊“完全象个美丽的黄袍姑娘”而被“我”一见钟情……于是,“白马、红马和黄马“便与“额吉、我和小遐”之间构成了颇具意味的精神写照与文化暗示,而包裹着文化因子的“意味”很难被外人所“译全”的……;“nutak ”一词的基本意思是“营盘或家乡”。但在真正的牧人心中,它还是远方“一块圆形的墨绿色的草”、是毡房迁后留下的“一块痕印”、是“一缕亲切、伤感和朦胧的记忆”、它连结着“出牧的方向”、保存着“体验过的经验”、含藏着人畜酣睡潜入土地的“体温”、它甚至“还有着青色和黑色之分”,“也许十个努特格就可以构成一个牧人的青春,一百个努特格就意味着一部草原史。”于是,在《金草地》中,额吉一生牵念的是“阿勒坦·努特格”——金色的家乡/金色的草原/金营盘。可以说,额吉迁徒的人生是被此驱策的;她虽久经磨难却仍不失游牧民族之本质,而额吉这一人物所负载的文化底蕴也便由此显出……无论如何,“骏马”的强壮与绝美已浸透牧民身心,这便形成了一种既勇敢骠悍又自由散漫的民族性格;“nutak”所深藏的生命底蕴又使他们所逐的“水草”不仅是人、畜生命之源的征象,更成了他们一生所渴念的安居之所。实际上,因四季更迭与水草之枯荣,注定他们永无实际意义上的“家”,“具象的家”在他们不断游动的马背上。
在《心灵史》、《西省暗杀考》和《海骚》等中,又集中体现了作家对母族历史的特有体验,他也是在关键词的引领下实施自我体验的:一部《心灵史》简直就是对“哲合忍耶”一词的血泪诠释。(1 )此词是“阿拉伯语,意思是——高声赞颂”;(2 )在本书里特指中国回民中“以死证明信仰的教派”;(3)“是一大群衣衫褴褛的刚强回民, 手拉手站成一圈,死死地护住围在中心的一座坟”,而圣徒的坟墓才配称作“拱北”。对游牧民而言,“水草”是他们实质上的家,而对回民来说,“拱北”便是他们的无根之根了,他们“藉这些拱北看守着自己的一切——信仰、情感、财富、历史。”在哲合忍耶中,拱北又完成了象征和抽象意义:七代宗师舍命流血就是为争一块圣洁的“拱北”且“冤屈和鲜血是拱北的根源”,拱北的命运也就成了哲合耶的命运折射;(4 )圣征们在争取拱北的同时也迈上了“束海达依”(殉教)之途:“束海达依”的“基本的涵义就是为了伊斯兰圣教牺牲”,他们视“手提血衣撒手进天堂”为生命的最高境界;(5 )尊奉“束海达依”实为追求一种清洁的人生。真正的穆斯林应日诵古兰五次,每次诵前沐浴、怀净意行净礼以达“净心”之目的。于是,“水,是伊斯兰教净身进入圣域时的精神中介。水又是净身时洗在肉体上不可或缺的物质。”哲合忍耶的“带血下葬”又将这“水”换成了“血”,在“水净、土净”之外又添加了“血净”……可见,整部《心灵史》的中心词就是“哲合忍耶”,每章节专为清楚地剥析此词而布设,每一宗师又从不同的侧面完善了此词的条目。作家正是经由此词的不断掘进而为我们展示了一个鲜为人知的心灵世界,伊斯兰文化的刚勇与清洁也便在此得以凸现。《西省暗杀考》的主要价值也在于对“束海达依”的一次成功的艺术演泽。
总之,作家对诸多关键词的体悟之义很难在词典上查到现成的词条,他只是在闯入异质文化圈后,用心读解着底层民众心中拥有的博大精深的文化词典,自己也正是在这种文化读解中,逐渐地蜕变成了“骑手兼旅人”的复合型的人:他既要怀揣“心火”,心存“念想”地坚守自我“在路上”,又要严奉“避祸异命”的生命法则、心胸宽广地去奔赴人生的“金草地”。为此,他深有体会:
“能够了解并最后理解一个民族是很难的,但我做了。我因理解这份感情而使自己丰富了”。(注:《张承志文学作品选集·散文卷》,海南出版社,1995年8月版,第211页。)
实际上,他也因此而为自己和自己的艺术争得了一个新生:
“我不敢自称有双语能力,但即使是几个单词,也能启发你思考许许多多问题,让你摆脱一个习惯了的思维方式,让自己从一种濒于死亡的惰性中获得一个焕发,一个启示,甚至一个新生。”
——《我所理解的民族意识》
显而易见,他在运用三支语流的实践中,逐渐探索出了真正属于自己的语言形式,即:借汉字躯壳,蕴民族文化之魂,在开放的文化态势中使用兼蓄多种文化因子的语词。其相应的用语方式为“体悟富有文化底蕴的语词以展示其背后的隐形世界,在美好感受中净化与重塑自我。尊奉“正确的方法存在于研究对象拥有的方式中”的方法论,向显形世界传达深刻、独特的生命启示。
三、语流的意义
当我们梳理了张承志的语言资源后,发现:他在运用三支语流进行艺术实践时,三支语流又启发且指导了他的艺术探索。主要表现如下:
第一,语流启发下的独特语言观:
张承志在坚守“艺术即规避”的艺术观的同时,又坚持“美文不可译”的语言观。这一观念就是他在动用语言资源进入创作时所获取的领悟:
“无论是书面语(包括文学语言)或是口语,一旦在它们表达着使用者和使用民族的心境、情绪、特定意识、弦外之音、独有的生活、基于传统和文化的只可意会的心理素质的时候,它们就是很难甚至是不可翻译的。能够翻译的只是表面只是大意、对应或比喻。翻译过程中的精益求精或刻意求真只能导致一个泥潭,站在两片文化之间束手无策的泥潭。”
——《美文的沙漠》
张承志的创作实践已证明:改变语言就是变换思维。张承志虽都操用了汉语入创作,但他笔下的每一个方块字下却蕴藏着不同民族之魂。这又不同于韩少功的《马桥词曲》:前者是“语言与文化”的问题,后者则是“语言与方言”的问题。亦即:马桥人虽没有经文明修饰了的“语言”,但却拥有自己独特的认识世界、表情达意的“言语”,它具有时空的凝滞性,是对方言的一种捍卫。
第二,语流启发下的叙述转向:
一般而言,叙述分表层叙述(行为叙述)和深层叙述(心理叙述)两种。在张承志创作的前期,属转述他人行为的转述文本,后期创作属陈述心同此境的陈述文本。亦即:他由表层叙述向深层叙述转向、由“表现”向“感受”转向:前期感到表现主义对自己的胃口,甚至在《北方的河·后记》中宣称:“这就是我的表现主义。”后期则投进关键词背后的隐形世界里感受美好。他不是为写作而写作,他宁愿“在丰富的感受中活着”人们便发现:他的作品越来越深晦难懂,他的三支语流也由可读性强(语意浅白)走向可读性较弱(语意深刻),再走向可读性弱(寓意深邃),最后索性由可读的文字走向沉默的色彩,完全隐去了一切“表现”的主观因素,剩下的全是感受,让他人在感受中与作画人神会地交流。
第三,语流启发下的艺术辩证法:
虽然张承志极重视自己的“一腔异血”,但对中文却怀有深厚的情感与独到的认识:他“热爱使用中文的独自写作”,在他眼里的中文“有无限的可能性,它变幻而沉隐”,他也在此中获得了“无拘无束地用中文汉语指点江山、发掘和丰富这美好文学的喜悦”。(注:《张承志文学作品选集·散文卷》,海南出版社,1995年8月版,第343页。)能够如此洞察汉语,主要得益于张承志这个文化混血儿的高超悟词能力。亦即:当张承志个人的文化优势、语言优势与汉语本身所固有的包容变幻的优势遇合时,他便真正地“冲出了方块字”了!个性与共性的矛盾却在此实现了统一,达到了艺术的辩证高度。
第四,语流启发下的语言理想:
张承志曾坦言:“美文即理想;无共同理想则无理解可言,也无交流必要。我热烈盼望自己能够找到属于我的十全十美的语言形式,但我并不打算让人人叫好。”(注:张承志:《荷戟独彷徨》,《上海文学》1987年第11期。)尽管他历经千辛万苦找到了真正属于自己的语言形式,但要达到“十全十美”尚需漫长的跋涉。在他的心目中,“传神的或有灵气的语言”入作品后,“如诗如画,优美动听”,这才是美文。为此,他经文字语言又向色彩语言进军,以期寻找那“十全十美的语言形式”!
我们在验证张承志这一文化混血儿的结论时,之所以过问语言,主要是由于语言的证据,比其他任何证据都更重要:作为文化代码的语言,既是一种文化化石,更是一种文化的境象折射。对张承志而言,尊重民族文化的独立品性,坚持母族文化的思维方式,用民族化的思想感情去酿就艺术精品,这是张承志及其作品走向世界的基本品格。我们热切期待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