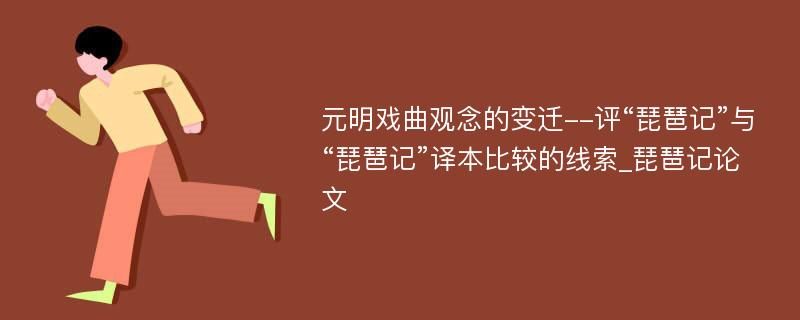
元明戏曲观念之变迁——以《琵琶记》的评论与版本比较为线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戏曲论文,琵琶论文,线索论文,观念论文,版本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戏曲的校勘与一般诗文的校勘有着较大的差异。诗文就其文本而言,因为经由作者的写定,就获得一种凝固特性,各个文本之间不会有很大的歧异。而戏曲无定本。作为一种舞台的艺术,它通过演员的表演而与观众相沟通,演员的表演成为戏曲活动的主体。戏曲文本虽是表演的依据,而演员却也可以根据自己的理解而对文本作出改动,根据观众的反映与要求予以变化。所以中国传统戏曲中,作者的权利常常被抹煞,只有艺人们为所欲为。这在早期南戏的传演中尤为突出。其结果便是一批“世代累积型”作品的出现。同一剧名而有不同的传本。说它们是一剧,则常常相互间出入甚大,已近于新的改编本;说它非同一剧,则其情节和曲文每多因袭,显出一源。若要为读者提供一个可靠的读本,则取何者为底本,便是一个难题。当我们编集一代总集之时,以哪一个刊本作为定本,校勘中如何取舍,更是令人难以抉择。在以古为尚的观念下,人们总试图寻找一个“最早”或“最好”的本子,而贬低别本。在这《琵琶记》也不例外。如钱南扬先生在认定陆贻典抄本的底本为“元本”之后,即将另一系统的传本视作“被明人改得面目全非”的本子。笔者最初撰写有关论文时多少也是认同了这一点,以为论定了其“最好”本子以后就可以使理解与评价归于同一。但事实并非如此。无论如何,毕竟流传最广、明清时期影响最大的便是这种“面目全非”的本子。它承担了《琵琶记》接受史的最长的时段。而当我们转换一下视角,便可以发现这一戏曲校勘上的难题,却同时也是一份珍贵的礼物。因为象《琵琶记》这样具有重大影响的作品,它不仅影响着戏曲文学史、戏曲批评史,而且也贯穿了戏曲表演史;它不仅把各个时期的改造展示在各种刊本和选本之中,同时在无意之中也把各个时期的观念凝结于其间,给了我们认识戏曲发展史的最好材料;它甚至比批评家们直接的表述更接近于真实,因为它免去了主观的混杂,直接把无意识呈现出来了。
同样,戏曲批评史也不能只看作好坏对错观点的叠加。其价值或正在于各种观点背后所支撑的审美观念和价值观念、欣赏习惯,正是这些要素影响着戏曲创作和戏曲活动的展开。
一、音律
产生于元末的《琵琶记》,要原封不动地搬演于明代,显然是不可能的。事实上,明中叶前后,随着各种戏曲声腔的兴起,艺人们就已经对曲韵音律作了改造,以适应新的观众和舞台的需要,这种改造也必然包括文字的修订。但另一方面,虽然戏曲声腔的勃兴本身表明了南戏地位的提高,但它并不意味着人们对于南戏的认识有了同步的提高;更无论对于戏曲发展规律的把握了。虽然其间的论争有何者更接近真谛之别,但更多的情况下,则是自以为智珠在握,其实离题甚远。
观点之一,是认为南曲出于北曲,于是以北曲的音律来要求南戏。
王世贞论曲,篇首即说:“三百篇亡而后有骚赋,骚赋难入乐而后有古乐府,古乐府不入俗而后以唐绝句为乐府,绝句少宛转而后有词,词不快北耳而后有北曲,北曲不谐南耳而后有南曲。”“稍稍复变新体,号为南曲”(《曲藻》)南曲出于北曲,这也是明代最为流行的看法。从何良俊到沈德符,都有相近的表述。作为北曲“不谐南耳”之后的产物,《琵琶记》遂被视作“南曲之祖”。虽然徐渭在《南词叙录》中对南戏源流作过正确描述,但事实上这种正确的意见反倒没有引起注意。《南词叙录》之获得关注和重视更是晚近的事。因而南戏出于东南沿海,受南方地域的语音所制约这样一个显著的事实被明人所忽视。于是便有以北曲音律来要求南戏的情况。《琵琶记》更是首当其冲。
令人哭笑不得的是对于《琵琶记》的颂扬亦不例外。如河间长君在嘉靖戊午(1548)所作《重校琵琶记序》中说:“爰迨宋元以来,尤尚声歌,更为戏曲,……然皆北音,可以比之丝管,而不可以南音歌之。独高则诚此记,虽云专用南音,而移之北音,亦罕称乖调。”并据北曲而论记中字之阴阳,韵之高下,音之短长;其后更附《音律指南》,所取实为周德清《中原音韵》所引之《唱论》。其按语又说:“调虽有南北,而若此之类,大略相去不远。特金元时专尚北调,故周公偏详之,非谓南调又自有一机局也。”王骥德《重校题红记例目》也说:“周德清《中原音韵》,元人用之甚严。亦自二传(《琵琶》《拜月》)始决其藩。”
北曲无入声,入声派于平上去三声,所用之韵出于中州韵;而南曲实据南方音,承自诗词,不仅有入声,而且多借韵混押,所谓用韵不纯。以中州韵衡量,《琵琶记》在用韵与声律方面便颇多瑕疵。这是明代戏曲批评家最乐于品头论足的一事。徐复祚说:“今以东嘉【瑞鹤仙】一阕言之:首句‘火’字,又下‘和’字,歌麻韵也;中间‘马’、‘化’、‘下’三字,家麻韵也;‘日’字,齐微韵也;‘旨’字,支思韵也;‘也’字,车遮韵也:一阕通只八句,而用五韵。假如今人作一律诗而用此五韵,成何格律乎?吟咀在口,堪听乎?不堪听乎?”(《三家村老委谈》)其曲为则诚辩护者则云:“凡歌曲入弦索,难于更端。每以一调自为终始。记中杂曲,间有出调,于于韵脚及间句结煞,字亦多不拘平仄,与拘拘者不同。故首说破‘也不寻宫数调’一句。不以辞害意,此记得之。”(此条并见于继志斋本、玩虎轩本等多种昆本裔本)而另一些批评家也只是因为高则诚已经如此“说破”而不能直责,但仍以为不无遗憾,如王骥德即说“不寻宫数调”之一语:“开千古厉端,不无遗恨”。(《曲律》论宫调第四)徐复祚则毫不留情地说:“寻宫数调,东嘉已自拈出,无庸再议。但诗有诗韵,曲有曲韵。诗韵则沈隐侯之四声,自唐至今,学人韵士兢兢如守三尺;曲韵则周德清之《中原音韵》,元人无不宗之。曲不可用诗韵,亦犹诗之不敢用曲韵也。”(《三家村老委谈》)徐氏执着于用北曲标准,不明白同是“曲”而南北曲用韵本不相同,南曲与唐诗宋词的用韵传统从未割断,只是南曲出于北曲的观念,使其不仅误以为南北曲的用韵也是同一,并且强求别人达到这种同一。而关于汤显祖《牡丹亭》的曲律之争,这一戏曲史上的重大事件的发生,究其原由,其实在于沈伯英等人以周德清《中原音韵》为式用于昆腔;而汤氏原不为昆腔而设,是为源出于海盐腔的宜黄戏班而作。所以明代人关于戏曲曲律曲韵的论争与批评,其实是在不同的标准下展开的。如果不明其间的实质差异,单就字面而论,是不能得出一个公允的结论的。
观点之二,以古为尚,借古律今。
曲律本身也是处于变化之中的。一些元代及明初尚时行的曲牌,在明中叶以后逐渐退出舞台或不为人们所知,遂不得不加改订。例如《琵琶记》“代尝汤药”出【歌儿】一曲,明中叶已不明其板式,故昆山本《琵琶记》从《中原音韵》“句字可以增损”的例证中觅得【青歌儿】曲牌以当之,受到沈伯英的批评;而沈氏另觅得【望歌儿】曲牌以当之,其实也欠妥当。(见《南九宫曲谱》卷十五)又如“勉食姑嫜”出【玉井莲后】曲仅二句,沈氏引录,注云:“不知全调几句耳。然此二句,又不协调,不可晓也。”亦以此之故,《风月锦囊》本及昆本裔本均将其改作【夜行船】一曲八句,以便于歌者演唱。
又,沈谱于“羽调总论”说:“一个曲牌,做二曲,或四曲、六曲、八曲,及二个牌名,各止一、二曲者,俱不用尾声。观《琵琶记》之【祝英台】、【高阳台】、【驻马听】、【惜奴娇】与【黑麻序】、【四边静】与【福马郎】等曲,则可以类推。”但这虽是曲律惯例,而民间艺人却不理会。故所见的则是通行本《琵琶记》较之“古本系统”,即使在上述情况范围内仍增入了尾声,所以昆本裔本及锦本、《蔡中郎忠孝传》本等,较陆抄本多五曲尾声,分别见于“南浦嘱别”、“临汝感叹”、“官媒议婚”、“强就鸾凰”、“官邸忧思”等出。玩虎轩本还于“官媒议婚”出批云:“一本删此【余文】,即如秦钧天而金无玉,乌乎可?”
中国传统向来以古为尚,故多有借复古而创新者,如韩愈的古文运动。而文学的复古思潮,尤以明代为烈。前后七子的复古运动,文必秦汉,诗必盛唐,以模袭为能事。这种思潮实际上成为明中叶以降的文学主流。它也影响到了戏曲的批评和创作。只是这一点当代研究者向未引起特别关注而已。
戏曲批评的“复古“倾向,则是以元剧为尚,一概抹杀明代的创作,而忽略了一代有一代之文学,一代有一代之特色,忘记了戏曲本身从曲律到语词都在变化之中,这种变迁是合理的。所谓的“俗本”和“坊本”对原作的改造,就其合于变化了的舞台及观众构成而言,是十分正当的。所以沈氏谱主要为昆山腔而设,尽管沈氏在谱中挥斥方遒,但即如《琵琶记》而言,昆腔所演,仍不从沈氏所用之“古本《琵琶记》”,而用经过改造的时本。只是这种改造后的“时本”,当其问世之时,也是“托古改制”,假托于所谓之“元本”“古本”。结果,明代各家刻本各各标称有独得之秘,或谓囊出“元本”,或云别得“古本”,每每自诩其所改之处为佳,而斥责别家本子为“俗本”“坊本”,“不通如此”。令人莫辨真伪。正如凌初成于其所刻本之“凡例”所说,则诚原本为“妄庸人”改窜,“大约起于昆本,上方所称依‘古本改定’者,正其伪笔;所称‘时本云云者非’,则强半古本。……而世人遂不复睹元本矣。”王骥德也说:“坊本一出,动称古本云云,实不知古本为何物。”(《新校注古本西厢记》附评)
二、虚实
中国向有历史的传统,史传文学尤为发达。故戏曲小说大抵取材于前代的历史故事。当宋元小说戏曲兴起之时,艺人作家别无依傍,自铸伟词,意之所至,不妨驱遣历史,为我所用。其所注意者乃系“意境”之完整和“真实”,乃在于所要表述的“意象”之传神,固不在是否纯合于史事。史事不过是叙述的触发点,一个必须的框架而已。“神”和“意”,当是创作者的关注之点。正如宋元以后文人写意画的勃兴,而以“写意性”、象征性表演为特征的戏曲,无疑吸收了此种精髓。而观客听众,也习见此种形式,并不特别深究,观听止于耳目,感泣止于言语,既不知本来如何,亦不必知其原本何如。戏者,戏之耳。是为共识。
宋人论说话,谓最畏“小说”人,一段故事,离合悲欢,顷刻提破。而讲史者,亦是将此种小说的手法用于史事,展开想象的翅膀,幻化出种种情状。戏曲则是在讲唱文学的叙事艺术高度成熟的基础上,构建自己的大厦的。戏曲的生命在于戏剧冲突。这虽是西哲首先拈出的,但它也确实是合于戏曲发展的事实的。为了使冲突集中突出,书会才人们往往任意驱遣人物,编织故事,使偶然的历史,变得风情万种、曲折离奇、箭拔弩张。其最甚者,如无名氏之《黄鹤楼》,将姜维与刘备归于一处,戏非佳品,作者亦非名人,但如此驱遣而人不以为非,不能不考虑“接受者”的欣赏习惯。顺此习惯,则汉代伯喈,不妨中唐宋始有之状元,一代名儒,不妨赘入相门。观客听众所关注在事,在戏中之意,而不在于戏外之人。得意忘形,得鱼忘筌。惟其质朴至极,感之痛之,反以之为真。作者编者,以斯为游戏三昧,本为小道,固非高头讲章,何须拘拘然泥古不化。“大家胡说可也”(徐渭语)。所以要在宋元戏曲中找今人所谓的“历史剧”,难免南辕北辙。
对戏曲小说的纪实性情况的关注,是从明代开始的。如胡应麟谓《三国》“七实三虚”。罗贯中写定《三国志演义》,其实已经尽量往历史史实靠拢,删去“草莽三国”的内容,体现了文人化的特点。故其虚实观得到了认可。而“三虚七实”之类,亦成为历史题材创作的基本标准。如果说宋元戏曲小说尚是向民间大众倾斜,无所谓真实与否的话,明人则开始要求其向正统的史传文学回归,并以合于史传为尚。如对梁辰鱼的《浣纱记》的一个重要评价便是“不用春秋以后事”。这种变化可以看作是文人化倾向对于戏曲小说的侵蚀。所以元代戏曲尽管有“名公才人”题咏,却仍较多保有其民间性特色,而明代中叶以后的传奇化浪潮,却使戏曲整个地典雅化了。其间的差别正如元代杂剧之“文采派”之于明代传奇的“文词派”的不同。
这种对于史事的要求也出现在《琵琶记》的评论中。如“春宴杏园”出关于马的对白,继志斋本批云:“马色自布汗至苏卢皆元人胡语;马名大半是汉以后诸代畜产;马厩皆是唐宋题额。考诸桓灵以前,此类甚多,岂东嘉未之深思也?”又,“间询衷情”出,玩虎轩本引《七步余谈》云:“解缙学士与客云:怎做得扬子云阁上灾,不若陶渊明归去来,尤工切。客曰:惜为桓灵以后事耳。缙曰:钟乳三千辆,金钗十二行,若非牛僧孺事乎?客曰:虽然,亦东嘉千里之一曲也,何以再为?”徐复祚论《琵琶记》,谓“若其使事,大有谬处。【叨叨令】末句云‘好一似小秦王三跳涧’,【鲍老催】句‘画堂中富贵如金谷’,不应伯喈时已有唐文皇、石季伦也。”(《三家村老委谈》)
但明代文人的批评与艺人的搬演也仍有着很大的差别。前者责怪高则诚用桓灵以后事,后者却为了使观众能够明白该典故,加入解释,结果把高则诚原本暗用的典故变成明典,便真的不妥当了。例如前引“金钗十二行”下,本用暗典,青昆演出本有直接补叙谓“这是牛僧孺之事”云云。诚如继志斋本所批:“坊本‘画堂’下说出孟尝君,犹是汉以前人;至‘绣屏下’说出牛僧孺,却失体。”这说明高则诚用典亦有其标准,即用暗典,取其意,且字面本身亦可说通;但不用明典,以免突兀。故据陆抄本,则全剧除“春宴杏园”出有丑角诨语道“我好似小秦王三跳涧”之外,并不直接犯出汉以后人名。这种方式,也是为宋元戏曲作家所共同遵守的。而明人所谓不用汉以后事,未免过迂。
明人对《琵琶记》的史实的批评,还集中在本事问题上。对其本事之说颇多,一类是考前代小说,如从唐人小说,得故事相近的《玉泉子·邓敞》和《说郛》所载唐人小说“蔡生”条。王世贞责问道:“其姓氏相同,一至于此,则为何不直举其人,而厚诬贤者如此耶?”(《曲藻》)一类是附会于“刺王四”说,其说传之甚广,至清毛声山评本,犹以此说为中心而曲为之解说。对此,徐复祚有较通达的观点:“要之,传奇皆是寓言,未有无所为者,正不必求其人与事以实之也。”(《三家村老委谈》)再一类是从旧牒和陆放翁诗(一作刘克庄诗)而知出宋代的戏文或说唱,故近于史实,但不及前二说之富于传奇性,反而不彰。清周亮工也说:“高则诚传奇,即云有所讽刺,假借托讽,何不杜撰姓名,行其胸臆;乃一无影响,遂诬古名贤若此,诚所不解。”(《书影》)这方面的一个共同的倾向,是认为《琵琶记》除了名姓与蔡邕相同外,与历史人物毫无关系。这种观点也影响当代的一些研究者。
其实,高则诚在创作中,把有关蔡邕的史实,尽可能地用到了剧中,以增加其“真实”感,而蔡伯喈的形象及其悲剧性遭际,与历史人物的人生悲剧,有着相通之处,即所求在某种条件下的“神合”,而不在外部的形似:它体现了元剧作家的一个共同准则:大处不妨出自“假定”,而细处却是历历可按,所得为特定的艺术“境界”中的真实,而非史的逼真。正如王维雪里的芭蕉图,两种绝不可能同生之物却不妨绘于同一画面。王国维论元剧之“文章”,一曰“自然而已”;申言之,则曰:“有意境而已”。(《宋元戏曲考》)可谓切中肯綮。因为元剧本质上近于“诗”,作者着眼点不在于事,而是借事为机缘而构筑其“意境”,故往往取其一端,而意之所至,不妨任意驱遣。说其非史,则人事无不出之于史;说其是史,是处处可见捏合之迹。唯其至者,虚者实之,实者虚之,虚实相生,计白当黑,化泯无迹,奇思巧意,反令人忘其为“假”,臻于“自然”“化工”之境。明人重实,遂失却“诗”之境。晚明及清初重密针线,填满虚空,结果滞涩而无生发之余地,似真反假,唯见扭捏。此点下节论“针线”亦可为证。
元人重意之一端,还可以从细处得之。如陆抄本所叙五娘事,道是“罗裙包土”。“罗裙”,一词,出现于“副末开场”、“筑坟”、“书馆相逢”等出;其传承,乃来自早期说唱与戏曲,故元杂剧叙赵贞女事而有“罗裙包土筑坟台”之语。说“罗”,意指其质地之薄脆,暗寓女性独身筑坟之不易。但明人坐实了“罗”字,以为饥荒之后,不当仍着“丝罗”之衣,而应是披麻戴孝,故改作“麻裙包土”。玩虎轩本并批云:“‘麻’今尽作‘罗’,大谬。”继志本则谓“奈何说‘罗’?”泥于实的结果,则是当“两贤相遘”出“血痕尚在衣罗”一句改作“衣麻”后,王骥德反责高则诚落韵不稳,批评道:“‘衣麻’,是何话说?”(《曲律》)
三、针线
李笠翁说:“若以针线论,元曲之最疏者,莫过于《琵琶记》。无论大关节目,背谬甚多。如子中状元三载而家人不知;身赘相府,享尽荣华,不能自遣一仆,而附家报于路人;赵五娘千里寻夫,只身无伴,未审果能全节与否,其谁证之:诸如此类,皆背理妨伦之甚者。……此等词曲,幸而出自元人;若出我辈,则群口讪之,不识置身何地矣。予非敢于讎古。既为词曲,立言必使人知取法;若扭于世俗之见,谓事事当法元人,吾恐未得其瑜,先有其瑕。”(《闲情偶记·结构第一·密针线》)
以元剧与明清传奇相比较,针线之密实与否,确为其间显著的差别之一。这种差别的产生,却源出于元人重意而明人重事。重意者不计细处,高处着眼,以白当黑,偏得空灵生动之致;重事者针线细密,虽一一可按,却多有重枝节而忽主干之弊,反觉呆板无神。明人传奇创作本身也有一个演进的过程。前期作者多属文词派,曲文典雅,而情节取材多泥于原始素材,显见其凑合拼接和模仿之迹,粗糙而稚拙,尚不能自运匠心。中经汤显祖而达顶峰,但其曲律若依昆腔要求,犹有不足,故时人颇以为逞才情而乖曲律。明末清初作者,则渐以临川之笔以合吴江之律,辞气流畅,笔调华美,而编剧技巧日进,情节益见细密。观其弊端,则重情节与文采而昧于汤氏所说的“意”。因偏于情节,故类同于今日侦探小说之曲折离奇;其错中有错,巧中见巧,翻奇出新,而愈翻愈奇,遂走火入魔,偏离正道。如阮大铖、李笠翁诸剧,多有此弊。演来甚是“新巧”,而不耐咀嚼回味。合于小市民情趣,却无大家气象。针线之密,可谓环环紧扣,固前所未有:但毫无想象之余地,一切填满,不知虚实相生之法。一笑之外,别无余意。求其深思,固不可而得。
凌初成说:“戏曲拾架,亦是要事,不妥则全传可憎矣。旧戏无扭捏巧造之弊,稍有牵强,略附神鬼作用而已,故都大雅可观;今世愈造愈幻,假托寓言,明明看破无论,即真实一事,翻弄作乌有子虚。总之,人情所不近,人理所必无,世法既自不通,鬼谋亦所不料,兼以照管不来,动犯驳议,演者手忙脚乱,观者眼暗头昏,大可笑也。”(《谭曲杂札》)凌氏以旧戏与今剧相比较,亦近于元明创作之别也。
以此观之,元剧之空灵疏朗,有非明清作家可及之处。笠翁所谓元曲针线之疏,乃是元剧长处所在。盖趣尚有别。明人如王骥德谓汤显祖独得元人三昧,但其着眼仍不外汤剧之语言,以《南柯》《邯郸》二记,削尽蘩芜,入于元人堂奥。正如赞《牡丹亭》而仍以为佳处尽在文采,不知汤氏不可及处乃在其“意趣”。如今看来,汤氏真正所得的“元人三昧”,乃在其得元人作剧之意和所传之神。临川四梦,正在意象高妙,既有别于此前作者之多模袭而生吞活剥,又别于此后作者密针线而沉溺于情节之离奇曲折。
笠翁论《琵琶记》针线不密,又谓“赵五娘于归二月,即别蔡邕,是一桃夭新妇。算公婆已死,别墓寻夫之日,不及数年,是犹然一冶容诲淫之少妇也。身背琵琶,独行千里,即能自保无他,能免当时物议乎?”(《变调第二》)故为之改作“寻夫”一出,补出张公遣小二同行云云,自以为可补“缺略”,却不知男女同行,更为相悖。且此种“全节”云云,乃是注重节孝的明清人才想得出来的事。其实,剧中多处提到脸儿黄瘦骨如柴,三载饥荒,咽糠度日,又那得还有“冶容诲淫”可言。则元人之疏略亦未必真是疏略,乃在于关注之点不同。
对《琵琶记》“缺略”的责疑与补苴,实不始于笠翁。因为明人已做了大量的工作。如李卓吾评本即对于新婚而父母年已八十,不能遣一仆回去,见拐儿假书而不辨父亲的笔迹等提出异议。藏晋叔《玉茗堂传奇引》谓“陈留、洛阳,相距不三舍,而动称万里关山;中郎寄书高堂,直为拐儿给误:何缪戾之甚也。”所以明人曲选所录青昆演出本,于“丹陛陈情”出作了这样的补充:“(末)状元,既亲老妻娇,何不寄一封音信回去?(生)大人,争奈朝中董卓弄权,吕布把守虎牢三关,纵有音信难寄了。”(据《乐府菁华》、《乐府玉树英》等)潮州出土本于此出补出伯喈陈情时明说家有妻室之事。《乐府玉树英》录“伯喈书馆思亲”一段,还有“今吕布把守虎牢,纵有音书难寄”之语。北京图书馆藏本《蔡中郎忠孝传》,补出伯喈盘问拐儿的情节。通行本依惯例补出“考试”一出;凌初成刻本独有伯喈夫妇归守庐墓途路一出。这些都可以说是从情节上的补充。
上引各例尚属明显之例。一些看似不起眼的改动,其实更能体现元明观念的不同。如“题真”出,通行本于五娘题诗后增入数语云:“奴家题诗已了,不免说与夫人知道,待伯喈来看。”继志斋本有批语云:“诸本无结尾白。若非先与说知,则牛氏安知真容源委,而后折遂有‘丹青入眼’之句也。”其实五娘自说是牛氏叫她到书馆“题几句言语打动伯喈”的,则五娘回头告知牛氏,乃必有之义;且后出牛氏亦自说“教他题诗句暗中指挑”,故则诚以为可以省略,而明人以为不可省略。高则诚原是留有空白供想象,故并不全部说完:而明人却将这“空白”当“缺略”了。
以故,诸家所说《琵琶记》的“罅漏”,亦未必即是疏漏,而是观念的差异和理解的角度不同之故。高则诚以意为主,故强调新婚二月而父母年过八十,是为逼试张本,因为唯有如此高年,才使在家孝养成为不可缺之事。又如虽未直接描写牛相如何禁着伯喈,但其写法却正是从牛之可畏和不敢遣一仆回去的事实来反衬伯喈的处境,来显示“战钦钦拿着个怕犯法的愁酒杯”的功名“孰知为忧患之始”的情状。所以从科举社会的一般情况看,《琵琶记》的写法有其缺陷;从高则诚所强调的特定条件而论,则仍可自圆其说。于此可见,元剧的“读法”与明剧的“读法”亦当有所不同。正如今人以阶级对立角度出发,以为唯有负心弃妻方才合符生活的必然逻辑,并以此挑剔《琵琶记》的缺失,与其说是作品的问题,不如说是“接受者”自身的原故。这不仅是重意抑重事的问题,而且更是不同时代关注重点有别的问题。明清人看到了孝,今人看到了负心,并从这一角度作出审视,遂居高临下地看出了“缺漏”。但高则诚要求“知音君子这般另做眼儿看”的内容或许并不在此,则所有的指责也就并不都是有效和合理的。
再举通行本所作的“密针线”的例子。“庆寿”出,陆抄本只是由称寿而及一家之欢乐,目的是反衬后文之灾难日子,并不涉及其他。通行本则让蔡公在祝酒时即说:“人生须要忠孝两全,方是个丈夫。我才想起来,今年是大比之年,昨日郡中有吏来辟召,你可上京取应,倘得脱白挂绿,济世安民,这才是忠孝两全。”玩虎轩本说:“元本有此外白,与‘卑陋’句何等照应。”而据陆抄本,原无此白,况且蔡公原本只是要改换门闾而已,这是一位乡村老人对于功名富贵的虚荣心,并无“济世安民”的境界。“逼试”出,通行本生唱“天须鉴蔡邕不孝的情罪”句前,有“〔生跪天科〕”及一白,玩虎轩本批云:“‘蔡邕’,今尽作‘孩儿’,自不似矢天语。”按陆抄本中,此虽是指天为誓,但并不是跪天发誓,此一“跪天科”,乃明人所增,虽一小小的动作的差别,其实也包涵着对于一种争论场景表述的不同。据陆本,则是平常父子之争,正如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所见的一样;据通行本则是依照孝子程式的所为,故既是跪天,则亦自不能作“孩儿”称了。又如“糟糠自厌”出【山坡羊】曲,“几番拼死了奴身己”句,陆抄本作“几番要卖了奴身己”,玩虎轩本说:“‘拼死’,今尽作‘要卖’,则‘有贞有烈’胡为乎言哉!”意思是卖了身己,亦即失身失节,而有贞有烈的孝妇是不当说出这样的话头的。此类例证尚多,皆是理解的基点不同之故。“疏漏”者有疏漏的原因;补苴者亦自有补苴道理,他们说的并非同一事。
另外还一些例证,虽不及上引者之关涉颇大,而也可知理解的出发点有别。如“庆寿”出之“一朵桂花难茂”,“迎亲”出之“女儿话难听”,通行本二“难”字均改作“堪”。后一条玩虎轩本有批云:“‘堪’今作‘难’,这是乱道。”盖前一条是以为伯喈好才学与好人品,足以“堪茂”;后一条则因牛氏的谏语“堪听”而使牛相有改过之意。凌刻本对前一条驳云:“‘难茂’,即合下一子不忍遣求功名之意。时本作‘堪茂”,无解。”今按:后一条正因“难听”,才使牛相惕然深思,遂想出“一个团圆策”,若是“堪听”,何来前文之触怒?而玩虎轩本之所以觉得难以接受,乃其意中牛氏谏父时所说的完全合于礼教的话头,是不能作说成“难听”的,否则便是“乱道”了。这可谓是“诛心之论”。又如“筑坟”出,“教人道赵五娘亲行孝”句,通行本改“亲”为“真”,玩虎轩本批云:“‘真’,今尽作‘亲’,是行孝岂可倩人为?”亦是这种放大镜观照下的苛论。还有“书馆相逢”出决定归守庐墓时,贴唱“与地下亡灵添荣耀”句,通行本改作“使地下亡灵安宅兆”,玩虎轩本、继志斋本均有批评责难作“添荣耀”者“岂贤媛口吻”,亦属同一理由。
四、人物:个性化与类型化
在《琵琶记》被看作违反“生活的必然逻辑”“强扭团圆”的时候,其人物塑造是不可能被视作“个性化”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因为人们总是从自身所处的角度来看待古代社会的。当代人先天的优越感,使我们常常居高临下,以为可以随心所欲地信口雌黄。不要说《琵琶记》,即使其他当世很“红”的古代作品,也很难获得“个性化”评价。因为中国戏曲小说中,类型化的“扁平人物”确实更为普遍。但如果对元明作品作一比较的话,则可以发现,元人较之明代一般作品,或许是更加接近于“圆型人物”的要义的。
以《琵琶记》张公这一人物为例。据“古本系统”传本,细玩作者之意,高则诚对张公,肯定之中,仍有所批评。即写出了其复杂性。张公的“施仁施义”,这是人所共知的。但高则诚同时又着意叙写了张公可悲可叹的一面。这就是世俗功名的观念。逼试成功的关键便是张公力劝,并主动承担看顾蔡家的责任,使伯喈无可推托。这还算“高义”。可悲的是这一人物只知功名之荣耀而不明功名之忧患。故伯喈痛别时他却说“所志在功名,离别何足叹”;蔡家灾难已成,他一度归咎于伯喈;但当李旺说知强官强婚不得已之情,他马上原谅了伯喈,却又道:“这是他爹娘福薄运乖,人生里都是命安排。”守墓时,伯喈痛不欲生,他却以为人“人生如朝露,论生死荣枯有定数。……况腰金背紫,不枉了光荣门户”。将灾难归于命运。所以最后他稍作谦让即接受了牛相的赠金,便是十分自然的。蔡伯喈从其自身的遭际而知“为功名误了父母”,一切实由为官之后“战钦钦拿着个怕犯法的愁酒杯”之故;而张公意中圣明的君王仍是不可怀疑的,所以将灾难归于命运了。
但明人意中,张公便是“高义”的化身,继志斋本云:“一云张大公即高东嘉托名。”所以通行本系统中,一是让张公担当了旁评者的角色,二是将上述“缺点”作了修正;更突出“施仁施义”的形象。所以一面增加了许多张公旁赞五娘贤孝和责伯喈不孝的话头,一面删去伯喈守墓出张公所唱“人生如朝露”等曲,改由张公冷语刺讥伯喈作结;并将张公在场面上的所有活动,都直指照顾蔡家这一题旨(陆抄本如“请粮”、“祝发”等出是路途中偶遇五娘),以显示其“义”;末了则改为张公不受牛相之金。继志斋本、玩虎轩本、唐晟刻本都有这样一段批语:“张大公终不受谢礼,赵五娘终不易衣装,见得孝妇义士之心,一无所为而为,坊本失东嘉之意多矣。”
有些情况下,牵一发亦足以动全身。由于张公被改成完美的“义”的人物,进一步论,则原作中另一些不这般看待张公的描写,便成有问题了。如李笠翁说剪发一折,“并无一字照管大公,且若有心讽刺者。”例子一是五娘自思是“只为上山打虎易,开口告人难。”笠翁说:“此二语虽属恒言,人人可道,独不宜出五娘之口。彼不肯告人,何言其难也?观此二语,不似怼怨大公这词乎?”其二是对张公说:“只恐奴身死也没人埋,谁还你恩债?”笠翁说:“试问:公死而埋者何人?姑死而埋者何人?对埋殓公姑之人而自言暴露,将置大公于何地?且大公之相资,尚义也,非图利也,‘谁还你恩债’一语,不几抹倒大公,将一片热肠付之冷水乎?”(《结构第一·密针线》)这是心中先有这么一个高义的概念,所以凡对此种高义而有抵牾的语词,均觉不妥。细味之,则诚笔下,张公固属高义,却仍是从普通人中显出其高义来的;而明清人的理解和改动却是让一个高义人物来展示其高义的。五娘虽感谢张公救助,但她也只是感激,却并不是把张公作高义人物看的,所以她仍说出“人人可道”的“恒言”。观众的体悟不能代替剧中人的思想,人物仍需从自身的性格和心理出发,这是直奔主题与自然流露、扁型与圆型的成因。
所以元明两代戏曲传演中对人物处理的不同,主要在于元剧作家尚无明确的“范本”意识,只是从对于具体的人的体悟出发来叙写人物,或任由人物依其性格思想而展开;而明代改本则先有一个“高义”“孝妇”之类的框式,依照这一理想的标准作改造或创作。前者无意识之中切近了个性化;后者则有意识地按照类型化的要求作了改造。高则诚尽管着意肯定孝子贤妇,却仍达到某种程度的“个性化”,而明人如《五伦全备记》《香囊记》等的“关风化”,却变成了概念的图解。差别便在于是从人物出发抑是从概念出发。元剧作家多是从抒发个体的性灵着眼,以为“我家风月”;两明人则多从代圣贤立言入手,“备他时世曲,寓我圣贤言”,从邱浚到沈璟都对此有所强调,而汤显祖的卓尔不群,正在超越了这一关。换言,明人有一种“宣传”的意识,树“榜样”的要求——这同时也是来自社会的需求。正如五十年代论《红楼梦》的价值而有人提出能向贾宝玉学什么一样,可见写人物而必须有可学之处,非好即坏,不容“中间人物”,原出于传统;——而元人并无此种意识,即如马致远等人称道神仙道化剧,也是对于现实无可奈何之余的一种逃遁,却并未树立一种可供直接仿效的典型;因为它只是着力揭示一种人生,是对无奈的人生的一种感叹,而无意提供一种范本。此其对于戏曲功用理解与处理的不同。
此种情况在四大南戏中也可以见到。其早期传本和晚明通行本,在人物处理上有显著的不同。如《拜月亭》,原有“误接丝鞭”一出,造成人物的一种尴尬,富于喜剧性;而明人以为于不负心坚贞形象有损,遂改为坚辞不接。又如《杀狗记》,《风月锦囊》摘汇本中,其妻有直接的劝谏争执,而经过“三改”之后的汲古阁本则以贤妇相要求,变作不争。故其形象的差别便是一为符合正常人性的妻子,性格鲜明,冲突构设清新可喜;一为合于礼教的贤妻,概念化的同时又试图回避冲突,便无足观。从前者可知其列于四大南戏并非无由,从后者则唯觉远逊之。但据说参与改订的有冯梦龙等文人作家,却偏愈改愈拙,唯一的原因,只能是观念的错误所致。(参见拙文《杀狗记版本考略》,《文献》1992.3)
五、主旨
高则诚于卷首即称:“不关风化体,纵好也徒然。”又说“只看子孝共妻贤”,似乎一剧题旨十分明确。但由于高则诚着力处仍在于人物的创造,从人物本身出发而并不是完全依据概念来安排人物行动,因此在某种程度上达到了“倾向的自然流露”,惟其如此,才使人物和主题有着多种生发的可能,给予种种分歧的见解以支持。但明人对《琵琶记》的理解却也十分简单明了,即是“《琵琶》教孝”。王骥德说:“不关风化,纵好徒然,此《琵琶》持大头脑处,《拜月》只是宣淫,端士所不与也。”(《曲律·杂论下》)所以昆本系统和其他改删本的一个重要特色,即是加强了对于孝子贤妇行为的直接或间接的评述,并使人物言行更合于“贤孝”范式;常常是惟恐观众不知而特别“点明”,故渐失“自然流露”之义。这是依照明代社会具有共同性的“接受视野”,而作适合于此时此地的改造。正与今人以“古为今用”原则而改编旧剧相同。这使原本有着一定丰富性的主旨,向明人所需的单一性转化。人物的言行,遂更多地带有“直奔主题”的特点。这是上节所说的明人从概念出发安排人物和情节的方式的必然结果。故一般而言,元明戏曲的重要区别之一,也就是“自然流露”与“直奔主题”以点明之别:而汤显祖之得元人三昧,傲视侪辈,其突破此一窠臼,亦为一端。
试举一例:“剪发”出末尾,张公许诺资送后,昆本裔本作:“〔旦〕如此多谢公公。请收这头发。〔末〕咳,难得难得,这是孝妇的头发,剪来断送公婆的。我留在家中,不惟传留作个话名,后日伯喈回来,将与他看,也使他惶愧。”继志斋本、唐晟刻本有批语云:“末白又重在头发上,甚有意味。坊本作‘我要这头发作甚么?’非复人言。”玩虎轩本作:“岂是张公盛德语。”这也是明改本为高则诚“密针线”之一例。从场面看,这一改动似乎更为细致入微;一般而论,应属“改好”之例而予肯定。但细味之,被责为“坊本”的“古本系统”传本的处理,亦有其不可更易之处。原因在于改者心中有“孝妇”一念,并由人物直接表露:而原作只是人物自身所思。大约元代人并不如明人这般时时有孝之一念,故则诚笔下之张公,面对饥荒现实,只虑如何过关,初未想到扬孝一事,所以见头发而略为一怔,道是“我要头发做甚么?”——如果不是为了宣传五娘的孝心,确无用处,故并非不近人情。从此点生发开去,可知虽细处亦不得轻忽。如则诚笔下之张公,虽有照顾蔡家之承诺,但张公是照应自家之余而及于蔡家的,故“古本系统”中,张公出场并不是“直奔”照顾蔡家这一主题的。而当公公去世之时,赵五娘也因屡屡烦劳张公,不好意思再求,故有剪发之举,并说“上山擒虎易,开口告人难。”这应当说是符合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一般情况的。但通行本却以为不妥,改作凡张公出场,即是为蔡家,仿佛不如此便不足以显其高义;另一面,正因张公已成高义的化身,再无私事与私虑,故见了五娘的头发,也就必须有上引议论方合情理;所以李笠翁责难说“告人难”之语,置张公于何地?——正是此种细微处,可见两个系统的传本中,已自形成各别的人物面貌。从一个具有善良品质的好人,变成一个毫无私利的完人,这种高大全式的改造,自然也对主题表述不无影响。
高则诚标称“关风化”,只看子孝共妻贤,颇受今人讥议。因为其目标似乎即是“宣扬封建礼教”。但剧中的描写固然有人物之合于礼教的一面,却也有违反礼教的一面。如蔡公临终前,自责误了五娘,担心“你身衣口食,怎生区处?”所以写下遗嘱,“我死后,教他休守孝,早嫁个人。”这与“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的程朱理学,便不相同。而五娘的回答是:“公公严命,非奴敢违。只怕再如伯喈,却不误了我一世?公公,我一马一鞍,誓无他志。”不改嫁,是因为对婚姻失去了信心,而不是因为守节!这是正常人的想法,却不合于“孝妇”声口。所以通行本赶紧将“只怕”句改作“那些个不更二夫”;唐晟刻本有批语说:“古本‘不更二夫’句,诸本作‘只怕再如伯喈’,甚非。假使稍胜,真肯改嫁乎?”玩虎轩本则说:“‘不更’句,坊本作‘只怕再如伯喈’,岂是贤媛口气?”前举“几乎要卖”句,也属同例。
高则诚虽标称关风化,但元代社会毕竟是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至少程朱理学尚未渗透到社会的底里,故《琵琶记》仍不妨以人情物理着眼,不必事事紧扣伦常;而明代社会程朱理学已是一统天下,再容不得逸出规范了。
但高则诚的关风化之说却是得到明清剧作家和批评家的普遍的赞赏。因为厚人伦,敦风俗,风以化之,原本是《诗大序》以来的传统。文以载道的观念亦已深入人心,为文人士大夫所奉行不悖。在邱浚、邵粲、沈璟、王骥德以及晚明大多数作家看来,戏曲的内容和主旨是既定的,只需将圣贤之言图解演绎出来即可;因而戏曲创作的问题,便只是一个文采与曲律的问题。汤显祖的“凡文以意、识、神、趣为主”,便被视作逞才情而傲曲律;四梦的成就也只归于文采而已。汤沈之争之所以不分高下,最终归于调和,亦在于内容和形式之矛盾中,内容既是永恒不变的“道”,则其间的争执,自然也就只能归之于形式,而且是形式的最表层:曲律。殊不知汤氏所载之道,并非图解的之伦理,而是真实之情性。以情抗理,却也依然是道;是左派王学之道。然而无论如何,元剧作家却并没有这样完整的载道意识。即如高则诚也依然强调“知音君子这般另做眼儿看”,而并不完全局拘于伦常纲纪。所以元剧创作在整体上与明代剧作有着区别。因为元剧更多地带有市民阶层的气息,只属于才人们自身的独特的人生体验,是礼崩乐坏之后书生们绝望的呼喊,而儒家的伦常似乎离他们更远了一些。除杨梓等少数作家外,可以说总体上是有才人气而无道学气。正因没有明代那种儒教伦常的强制或自觉的要求,却又在以杂剧为我家生活之中精通曲律,下笔成章,元剧作家才得以自由驰骋,星斗焕耀;固非拘拘然之明代曲家所可比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