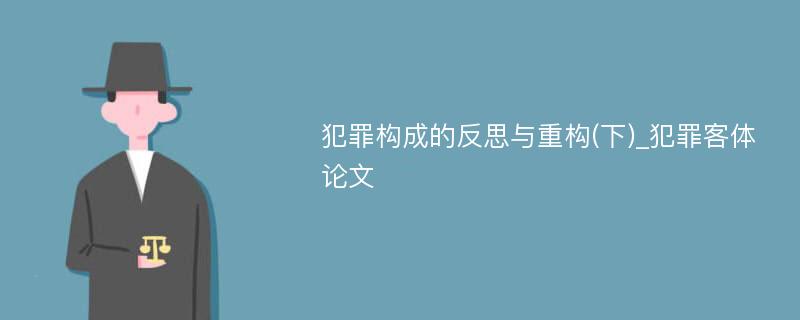
犯罪构成的反思与重构(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重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二)对传统犯罪客体理论的质疑
几乎所有的现行刑法学教科书和传统的刑法学理论对何谓犯罪客体作了如下的表述:犯罪客体是指为我国刑法所保护而为犯罪行为所侵犯的社会主义社会关系。并认为一切犯罪都必然侵犯一定的客体,不侵犯任何客体的行为,就不会危害社会,也不能认定是犯罪。犯罪客体帮助我们正确地确定犯罪性质,因此,犯罪客体是犯罪构成的基本要件之一。(注:《刑法学》, 法律出版社1982年5月版,第106页、第108页。)然而,这样一个概念,能否揭示犯罪客体的应有本质和固有属性,给犯罪客体在犯罪构成中如此定位能否说明犯罪的性质?所有这些问题在我们看来大有可质疑之处。第一,传统的犯罪客体理论首先把犯罪客体视为是一定的社会关系,并认为是被刑法所保护的而为犯罪行为所侵犯的社会关系。然而何谓社会关系?马克思,恩格斯曾经指出:“生活的生产——无论是自己生活的生产(通过劳动)或是他人生活的生产(通过生育)——立即表现为双重关系:一方面是自然关系,另一方面是社会关系;社会关系的含义是指许多个人的合作。”(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3页。)列宁也指出:“人与人的关系即社会关系。”(注:《列宁选集》第10卷,第88页。)马克思主义的这些原理表明了社会关系是人们在生产和共同生活活动过程中所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而自然关系不过是人们在生产和共同生活活动中所形成的人与物之间的相互关系。社会关系,包括自然关系不论以何种形式出现,它总是存在着一个显著的特点,即不可能脱离一定的人或物而产生、而存在,脱离了一定的人或物的社会关系从来没有,也永远不会有。所以恩格斯指出:“经济学所研究的不是物,而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归根到底是阶级与阶级之间的关系;可是这些关系总是同物结合着,并且作为物出现。”(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8页。 )由于社会关系具有的这一显著特点,使得要认识社会关系必须从人或物着手,要产生、变更或消灭社会关系,也必须使人的行为与一定人或物发生接触或者联系。犯罪虽然是一种反社会的行为,但它同样是一种社会行为,这种行为要产生一种新的社会关系——即犯罪的个人与被侵害的利益人之间的一种关系,其首要的前提必须是犯罪行为与一定的人或物发生接触或联系才有可能,进而进入到刑法的评价领域。把犯罪客体说成是犯罪行为侵犯的社会关系,必然是把犯罪行为看成可以跳跃一定的人或物直接与他人之间已存的社会关系发生接触或者联系。然而他人之间已存的社会关系又无不是以一定的人或物为基础的,跳跃一定的人或物,犯罪行为何以与社会发生接触或联系,简直成了真空世界的行为,这样的社会关系又怎么能成为犯罪客体?由此,传统的犯罪客体概念一开始就给人一种无边无沿、无法把握的感觉。
主体与客体共存的哲学原理已经揭示,客体与主体是通过一定的人的行为联接在一起的,一定的行为总是具体的,因此一定的行为主体总是确定的,与此相对应,一定的行为客体也总是具体的、确定的。把犯罪客体说成是一定的社会关系,实际上抽掉了社会关系中人与物的内容进行无限拔高的所谓抽象,但这种已失去人与物内容的社会关系,又何以能成为犯罪的指向呢?例如犯罪行为对人的侵犯,马克思说过:人“在其现实性,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8页。)在社会生活中, 人身可以体现或者代表不同的社会关系,因此犯罪行为究竟侵犯什么社会关系,就可以任意概括。正因为把犯罪客体说成是社会关系存在无法自圆其说的矛盾和混乱,以致于现有的刑法学理论在总则理论体系中,对犯罪客体进行具体内容的抽象后大谈特谈,而在分则理论中又无法加以具体确定,出现了要么闭口不谈,要么又重新用犯罪对象加以替代,在有的对人的犯罪中,干脆用一个“人身权利”搪塞过去。然而脱离了人的现实存在,人身权利又何以依附。
违反哲学原理和法学原理的这种传统的犯罪客体概念本身包含的逻辑矛盾和性质错误,使得人们无法了解犯罪行为究竟指向什么,通过什么对象加以实施的,以致于有人开始对这一概念试图作出修正,把犯罪客体说成是为刑法所保护的而为犯罪行为所侵害的社会主义社会利益(注:参见周荣生:《应当重新认识犯罪客体理论》,载《政法论坛》1989年第6期。)或者是社会主义生产力。 (注:参见何秉松:《关于犯罪客体的再认识》,载《政法论坛》1988年第3期。 )然而这种“换汤不换药”的注释,仍然不能说明犯罪行为到底指向了什么。而试图用“社会关系”、“社会利益”或者“生产力”来说明犯罪行为的社会性质和社会危害性,在我们看来,犯罪概念的确定已经完成了这一性质揭示任务,又何需犯罪客体代劳。而在具体的犯罪中,例如杀人罪,非要再次说明行为人非法剥夺的是一个我们社会主义社会中的,为我国刑法所保护的人的生命权利不可侵犯的观点,在理论上显得苍白无力。因此,我们有必要还犯罪客体一个本来的含义:犯罪客体就是指被犯罪行为所指向或受犯罪行为影响的人或物。
第二,传统的犯罪客体理论把犯罪客体视为可以帮助我们确定犯罪性质的依据。传统的犯罪客体理论把犯罪客体解释为一定的社会关系,不但混淆了犯罪的本质特征与作为犯罪构成内容的犯罪客体之间的区别,而且也无助于我们确定犯罪的具体性质。持传统观点的人为了说明犯罪客体与犯罪对象相区别时,常常以犯罪行为侵害一定人身的时候,是杀人罪还是伤害罪,关键就看两者侵犯的客体是人的生命权利还是健康权利为例。然而一定的犯罪行为指向被害人人身的时候,行为本身并不能作出直接的回答,而一定的人身背后隐藏的各种社会关系作为客观属性,本身也不能作出直接的回答,面对这种尴尬情形,传统观点又只好回过头来说,行为指向何种客体,是由行为人的主观目的内容所决定。这样主观罪过的目的内容决定了客观行为的指向,决定行为侵犯的客体性质。然而就在这种观点的逻辑结构中,我们丝毫看不出为什么犯罪的主观罪过内容不能直接决定犯罪的性质?在我们看来,主观罪过的内容决定了行为指向,行为作用于犯罪客体,其犯罪过程是:(主观罪过的)目的——行为——客体。这里决定犯罪性质的依据是犯罪的主观罪过目的,行为性质既然已由主观罪过性质决定了,又何需由犯罪客体来再决定犯罪主观罪过的性质。持传统观点的人也有的试图以盗窃正在使用的通讯电料与盗窃库存的通讯电料为例,来说明犯罪客体与犯罪对象的区别,前者属于破坏公共安全罪,后者属于侵犯财产罪,两者之所以发生区别,正是由于两者的客体性质不同。然而当行为人无法认识到所盗窃的通讯电料属于正在使用的通讯电料,此时当如何定性,结论恐怕不言而喻。而正是想通过犯罪客体与犯罪对象的区别来说明具体犯罪的性质,以致于出现了诸如挪用公款罪到底属于破坏经济秩序罪还是属于侵犯财产罪的疑惑不定的现象。(注:单长宗:《试论挪用公款罪的司法适用问题》,载《刑法发展与司法完善》,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89年9月版,第300页。)这正说明把犯罪客体说成是社会关系根本无法区别犯罪的具体性质。脱离了犯罪主观罪过,把社会关系作为犯罪客体内容,只能给人一种“画人最难,画鬼最易”的只图省事的感觉。
第三,传统的犯罪客体理论把犯罪客体解释为社会关系后,把它作为犯罪构成的一个必要要件,提出没有犯罪行为就没有犯罪客体,反之,没有犯罪客体,也就没有犯罪行为。然而在这一观点的逻辑结构中,到底是先有犯罪行为,还是先有犯罪客体?到底是犯罪行为的认定决定犯罪客体的存在,还是犯罪客体的存在决定犯罪行为的认定?说没有犯罪行为就没有犯罪客体,显然是犯罪行为决定犯罪客体的存在。犯罪行为已被认定,又何需犯罪客体作为犯罪构成的一个必要要件来说明犯罪的成立与否?说犯罪客体决定了犯罪行为的成立,那么犯罪客体本身怎么认定的?正如有的刑法学者所指出的,以社会关系为内容的犯罪客体,要么它在犯罪构成之外,要么犯罪已在客体之外,两者根本互为前提。(注:杨家贵:《关于犯罪构成的客体与对象之浅见》,载《政法论坛》1988年第5期。)斯言诚哉。我们认为犯罪行为与传统的客体之间的关系,决不像主体与客体的相互关系,是由行为作为中介而将两者联系起来,而犯罪行为直接作用于犯罪客体,这里缺乏中介环节,无法互为前提,以犯罪行为决定传统意义上的犯罪客体,本身已表明犯罪客体不可能是犯罪构成的一个必要要件。
(三)对传统犯罪客体理论的反思
传统的犯罪客体理论将犯罪客体视为刑法所保护的而为犯罪行为所侵犯的社会主义社会关系,它的形成并在我国刑法学理论中至今仍然占主导地位,这既有历史的原因,又有现实的原因;既有对犯罪理论根据的选择错误,又有对犯罪构成功能的理解错误。
1.对传统犯罪客体理论形成过程和理论根据选择错误的反思。
众所周知,犯罪客体理论是随着资产阶级在刑法理论上提出犯罪构成的概念而出现的。早期的资产阶级刑法学理论虽然对犯罪构成的内容及其意义存在着理解上的不同,但对客体就是犯罪行为所指向的对象的理解却趋于一致。例如沙俄时期的刑法学者在1875年的《普通刑法初级读本》中提出了犯罪构成的四要素,即:“一、犯罪的主体或犯罪实施人;二、客体或犯罪加于其上的对象;三、主体的意志对犯罪行为所持的态度或是它所表现的活动;四、行为本身及其结果或是主体的外部活动及其结果。”(注:参见[苏]A·H·特拉伊宁:《论犯罪构成的一般学说》,北京,中国人民大学版出版社1958年版,第99页;第15页;第50页注。)
应当指出,早期的刑事古典学派的资产阶级犯罪构成理论是以行为为中心而建立的,这种犯罪构成与他们提出的形式的犯罪概念一样,不指出行为的社会属性,只是在犯罪范围之内兜圈子,从而使隶属于形式犯罪概念的犯罪构成,与形式犯罪概念一起抹杀了犯罪的社会性质,这样为它遭到历史的必然否定埋下了伏笔。随着资产阶级刑事人类学派和刑事社会学派的兴起,对犯罪的研究开始从“行为”转向“行为人”。这一研究方法的转变,导致了资产阶级司法活动的传统原则的中断。刑事社会学派的代表李斯特在1882年就曾提出:“应当惩罚的不是行为,而是‘行为人’”。(注:参见[苏]A·H·特拉伊宁:《论犯罪构成的一般学说》,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58版年,第28页。)资产阶级的刑事实证学派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完全破坏了犯罪构成的法律意义。
十月革命胜利后,年轻的苏维埃刑法学者以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和阶级斗争的理论为指导,开始批判地继承资产阶级的犯罪构成理论,并加以彻底改造。他们一方面公开揭示了犯罪的社会性质,提出了具有实质意义的犯罪概念,指出犯罪是一种威胁苏维埃制度基础及工农政权在向共产主义过渡时期所建立的法权秩序的一切危害社会的作为或不作为的行为,(注:参见1922年《苏俄刑法典》第6条。 )另一方面又试图给犯罪构成赋予崭新的内容,这集中体现在将犯罪客体视为社会关系,并以此将新的犯罪客体概念与传统的犯罪客体概念被犯罪行为所指向的对象——人或物分离开来。苏联刑法学者特拉伊宁指出:“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任何一种侵害行为的客体,都是为了统治阶级的利益所建立起来的社会关系。社会主义的社会关系是社会主义刑法体系中的犯罪的客体。”(注:[苏]A·H·特拉伊宁:《论犯罪构成的一般学说》,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102页。)自此以后,这一论断在肯定苏联以前学者的有关观点后一直成为社会主义国家刑法理论关于犯罪客体的传统观点。
透过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的尘封,我们不难发现,现行的传统犯罪客体理论的形成其理论根据在于马克思在1842年《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一文中的一段著名论断:“犯罪行为的实质并不在于侵害了作为某种物质的林木,而在于侵害了林木的国家神经——所有权本身。”(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68页。)马克思的这一论断在社会主义国家刑法理论支持现有的传统犯罪客体理论时被无数次地引用作为注解。这里有一个我们如何理解马克思的这一著名论断实质意义的问题。我们认为马克思的这一论断即使是早期的马克思在系统研究了刑法学以后得出的终结性结论,但我们在理解马克思所说的犯罪行为的实质在于侵犯所有权本身的时候,仍不能从中自然得出马克思已说过犯罪行为指向的客体就是所有权本身这样的结论。因为这里马克思是从犯罪行为的实质在于侵犯所有权本身的现象中揭示犯罪概念的本质属性,这与马克思后来所说的“犯罪——孤立的个人反对统治关系的斗争”(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29页。)含义是一致的。即使马克思在上述文中曾也使用过“客体”一词,但这一概念的使用与对象含义是同一的。所以我们认为现行的传统犯罪客体理论从它产生的第一天起,就有着一个理论根据的选择错误。尽管年轻的苏维埃刑法学者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公开揭示了犯罪概念的本质属性以后,又试图对犯罪构成进行彻底改造的初衷是无可非议的,但是脱离了刑法学本身的内在规律性,随意创造别出心裁的新形式,是无法体现相应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的。
2.对传统犯罪客体理论现实存在和构成功能理解错误的反思。
我国的犯罪构成理论是新中国建立后从苏联引进移植的,其中犯罪客体理论几乎就是苏联刑法理论一套内容的翻版。这一传统的犯罪客体理论之所以至今仍然在我国的刑法理论中占有主导地位,其主要的原因不但在于我们长期囿于某种僵化的思维定势,认为承认犯罪客体等于犯罪对象,势必会陷入资产阶级刑法理论设下的陷阱,像资产阶级刑法学一样,掩盖了犯罪的阶级本质。这种观点,混淆了犯罪构成具有的定罪功能与犯罪概念揭示的本质属性应有的区别,把犯罪构成看成是犯罪概念的附属品,是犯罪概念具体化的产物,以致于把犯罪构成固有的定罪功能转移到对犯罪社会危害性的揭示上,使得犯罪构成成为衡量犯罪社会危害性的尺度。而在这一点上,将犯罪客体视为社会关系,正好可以借此说明犯罪构成反映犯罪的本质,决定犯罪的本质。(注:苏惠渔主编:《刑法学》,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8月版,第95页。)
把犯罪构成等同于犯罪概念,犯罪构成不过是犯罪概念的具体化,首起于刑事古典学派的德国刑法学者费尔巴哈。1813年在其草拟的《巴伐利亚法典》第27条专门规定:“当违法行为包含依法属于某罪概念的全部要件时,就认为它是犯罪”。在费氏看来,这一违法行为就等于犯罪构成,而犯罪构成不过是包含了犯罪概念的行为,以致后来费氏根据这一观点专门给犯罪构成下了如下定义:“犯罪构成乃是违法的(从法律上看)行为中所包含的各个行为的或事实的诸要件的总和”。(注:参见[苏]A·H·特拉伊宁:《论犯罪构成的一般学说》,北京,中国人民大学版出版社1958年版,第99页;第15页;第50页注。)费尔巴哈的犯罪概念是以行为为中心的,虽然这种犯罪概念没有指出犯罪的社会本质,但将这种犯罪概念溶合于犯罪构成之中,使犯罪构成担负起定罪的功能倒是恰如其份的。后来苏联的刑法学者认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刑法应当旗帜鲜明地揭示犯罪的社会属性,不应当只在法律范围内兜圈子,于是明确确立了犯罪的实质概念,这无疑是刑法史上的一个突破。但是在处理犯罪构成与犯罪概念的关系上,依然把犯罪构成看成是犯罪概念的附属品,提出了在确定两者关系时,“首先必须抛弃那种割裂犯罪概念和犯罪构成概念的政治意义和法权意义而来探寻它们之间的区别界线的做法”。(注:参见[苏]A·H·特拉伊宁:《论犯罪构成的一般学说》,北京,中国人民大学版出版社1958年版,第99页;第15页;第50页注。)主张犯罪构成不能脱离犯罪的实质意义。同时对当时个别学者提出的“犯罪概念是对犯罪的政治评价,犯罪构成是对犯罪的法权评价”(注:参见[苏]A·H·特拉伊宁:《论犯罪构成的一般学说》,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50页。)的观点进行了无情的批判后予以摒弃,提出了“犯罪构成不只是法权评价,它永远也包含着政治评价”。(注:参见[苏]A·H·特拉伊宁:《论犯罪构成的一般学说》,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50页。)这样,犯罪概念要揭示犯罪的社会属性,犯罪构成也要揭示犯罪的社会属性,按照犯罪构成四要件的划分法,其任务自然地落在了改造过的犯罪客体上,事实也正是如此。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在引进移植苏联犯罪构成理论时,几乎照搬不变。
将犯罪构成具有的定罪功能转移到犯罪概念的揭示犯罪本质属性的功能上,从表面上看似乎抬高了犯罪构成的作用,但实际上是降低了犯罪构成的地位。犯罪概念说犯罪是危害社会的行为,犯罪客体紧接着说犯罪是侵害社会关系的行为;犯罪概念说一切犯罪必然是危害社会的,犯罪客体就会进一步说明杀人罪之所以构成杀人罪,就在于杀人行为侵犯了社会主义刑法保护的社会关系——生命权利。事若如此,事果如此,不能不给人以一种重复的感觉。正是这种传统的犯罪客体理论自己为自己注定了在犯罪构成中必遭淘汰的结局。因此我们的结论是:传统的犯罪客体理论除了重复犯罪概念的内容外,不可能具有犯罪构成要件应有的定罪功能,它不可能在犯罪构成中找到应有的位置,只有当犯罪客体恢复了它的本来面目时,才能成为犯罪构成的应有内容。
(四)犯罪客体(对象)的内容及性质的确定
我们通过上面的论证,恢复了犯罪客体的本来面目,使犯罪客体同一于犯罪对象。为了使犯罪客体(对象)更好地在犯罪构成中找到应有的位置,也为了使犯罪客体(对象)更好地起到印证犯罪行为的作用,我们在这里有必要就犯罪客体(对象)的三个存有疑惑的问题加以澄清。
1.犯罪客体(对象)的内容除了人与物,还可包括其他内容吗?
刑法学界有人提出,犯罪客体(对象)的内容除了人与物以外,还应当包括人的行为,(注:参见周荣生:《应当重新认识犯罪客体理论》,载《政法论坛》1989年第6期。)也有人提出还应当包括事,(注:杨家贵:《关于犯罪构成的客体与对象之浅见》,载《政法论坛》1988年第5期。)但这种观点指出,所谓事即人的活动,人的行为,它是人存在和行使权益的表现。我们认为,在承认犯罪对象已经包括了人以后,再把人的行为引为犯罪对象的内容,实属多余之举。其理由是:
(1)人的行为与人相辅相存,密不可分,脱离了一定的人身, 人的行为无所依从。犯罪行为欲指向他人的行为,实际上是以他人的存在为前提的。我们不可能设想犯罪行为欲影响他人行为的时候,可以脱离行为主体而能够实施。例如妨害公务罪,行为人实施该罪,其目的无疑是妨害国家工作人员依法履行职责的行为,但该罪的实施必定以行为指向或影响到国家工作人员的这一人身为前提才有可能。因此,这里的犯罪对象还是人。
(2)人的行为,无非是一定的人在一定空间中的活动形式。 从物理的角度来看,人的行为是抽象的、无形的、不可见的。我们所见到的、感觉到的人的行为,实际上是见到的、感觉到的一个个在一定空间活动、运动的人。脱离了一个个活动的人,实际上是不存在人的行为的。主体的活动总是指向一定事物的对象化活动。犯罪,虽然作为一种与人类一般活动有别的扭曲的表现形式,但同样也是一种指向一定事物的对象化活动。无论在行为人的认识活动开始时,还是在行为活动进行时,它都不可能没有具体的活动对象,在人与人的行为关系上,犯罪人不可能不见到人,不感觉到人而先见到、感觉到人的行为。正是从这一意义上说,犯罪对象中的人已经包括了人的行为,我们没有必要再把人的行为作为犯罪对象的一个内容。
(3)我们承认,很多犯罪的实施,犯罪人的目的是以引起、 变更或消灭他人的行为为内容的,但他人的行为与他人的人身紧密相连。他人的行为受到影响是以他人的人身受到影响为前提的。而犯罪行为也只有作用于他人的人身,才能使他人的行为发生变化。因此,犯罪行为指向的对象只能是他人的人身即人,而不可能是他人的行为。
2.是否存在着没有犯罪对象的犯罪?
在刑法理论上,不但传统持犯罪客体与犯罪对象相分离的观点认为某些犯罪并不存在犯罪对象,而且有的持犯罪客体等同于犯罪对象的观点也认为:“对于某些行为来说,就是不存在其作用的对象。根本没有必要硬给按上一个对象”。(注:陈兴良:《刑法哲学》,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1月出版,第20页。 )这些所谓没有犯罪对象的犯罪,通常是指我国现行刑法中的组织、积极参加黑社会犯罪集团罪,脱逃罪,偷越国(边)境罪,重婚罪等罪名。这些观点实际上只看到行为本身,却没有看到行为是基于什么而得以实施的。按照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在社会活动中任何行为主体的实践活动都必然是基于一定客观事物的活动,都必然是具有一定对象性的活动。我们很难想象,缺乏一定的客观对象,人们的认识活动从何而起,人们的行为活动从何而为。犯罪行为虽是一种反社会行为,但其行为原理是一样的。有犯罪行为,就必定有犯罪对象,而且必定先有客观对象,然后再有犯罪行为。没有犯罪对象,犯罪行为就无所指向,也就没有犯罪行为的发生与存在。在上述被认为没有犯罪对象的犯罪中,并不是真的没有犯罪对象。而不过是没有被持上述观点者所认识、承认。在我们看来,在组织、积极参加黑社会犯罪集团罪中,被组织的人就是犯罪对象,在积极参加黑社会犯罪集团罪中,向已在集团内的成员靠拢、提出加入要求时,这一已是集团成员的人就是积极参加黑社会集团罪的犯罪对象。至于集团成立后又进行其他犯罪,那么所侵犯的一定的人或物就是新的犯罪的对象。在脱逃罪中,一定的监管场所就是脱逃行为的对象。没有这些监管场所的可以剥夺、限制在押人犯人身自由的牢门、警戒线,就无所谓有什么脱逃行为。在偷越国(边)境罪中,一定的界桩、界碑以及介于界桩、界碑之间的国(边)境线,就是偷越行为的对象,没有这些对象,就没有偷越行为。在重婚罪中,双方都以对方为犯罪对象。因此,一切犯罪都必定有犯罪对象,没有犯罪对象的犯罪是不存在的。
在如何认识一切犯罪都必定有犯罪对象这一原理时,传统的认为只有被犯罪行为所侵害的对象才能属于犯罪对象的观点必须加以纠正。其实,在犯罪行为与犯罪对象的相互关系中,犯罪行为对犯罪对象的侵犯加害仅仅是这一相互关系中的一部分,如对人的杀害、伤害,对物的毁损、破坏,但不是两者相互关系的全部。例如在窝藏、包庇罪中,就不可能发生对人这一犯罪对象的侵犯加害,在窝赃、销赃罪中,就不可能发生对物这一犯罪对象的毁损、破坏。从这一意义上说,应当把犯罪对象理解为是受犯罪行为指向、侵害、作用或影响的人或物才是全面的,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正确揭示犯罪行为与犯罪对象的全部关系。
3.犯罪对象是否需要并能否为刑法保护?
刑法理论上有的学者认为犯罪对象只有被犯罪行为所侵害而为刑法所保护时才能构成。(注:参见周荣生:《应当重新认识犯罪客体理论》,载《政法论坛》1989年第6期。)将犯罪对象视为需要并且能够为刑法所保护,实际上是把犯罪对象简单地等同于传统的犯罪客体,进而把犯罪对象提高到一个不恰当的高度,把它看成是决定行为是否构成犯罪的一个重要因素。我们认为,犯罪对象作为一种客观事物,作为一种客观存在,其本身具有好坏之分,但这一好坏之分并不是作为是否为刑法保护的依据。刑法规定某些行为为犯罪并加以惩罚,其目的在于禁止这种行为的实施,而不是在于对受犯罪行为指向、侵害、作用或影响的犯罪对象的保护。因为在犯罪中,有的犯罪对象,刑法根本不可能加以保护,反而是需要加以消灭的。例如所有伪造的东西,都不可能在刑法保护之列。也许有人认为,伪造性的犯罪其犯罪对象不应该是伪造品,如伪造贷币罪,其真正的对象是真币。对此我们认为,这里与犯罪行为发生关系的只能是伪币。在有关毒品犯罪当中,我们说犯罪对象只能是毒品本身,但毒品本身决不可能为刑法所保护。因此我们认为,犯罪对象本身的好坏并不在刑法的评价之中。行为是否构成犯罪,是由该行为是否为刑法所禁止所决定的。某种行为之所以为刑法所禁止,是由犯罪概念所揭示的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所决定的。而犯罪对象属于犯罪构成的内容,它主要解决行为构成什么罪,解决犯罪的法律性质问题。因此,盗窃合法财产是犯罪,窝藏非法赃物也是犯罪;变造合法的真币是犯罪,伪造非法的假币也是犯罪。尽管刑法禁止某些行为的实施,本身意味是对某些犯罪对象的保护,但犯罪对象的认定却不能以是否受刑法保护为标准。
四、犯罪构成的重构
我国现行传统的犯罪构成理论是从苏联移植引进的,是苏联模式的翻版,尤其是1958年我国翻译出版了苏联著名刑法学家A·H特拉伊宁的《犯罪构成的一般学说》一书,更是对我国的犯罪构成理论的建立和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我国的犯罪构成理论至今仍然打上特氏理论的烙印。这个犯罪构成理论摒弃了以前资产阶级以行为或行为人为中心的主客观相脱离的犯罪构成体系的弊端,把犯罪构成视为主客观的统一体,因而具有一定的进步性。尽管这一犯罪构成理论在解决定罪问题方面已经包含诸多实质内容,在某种意义上已开始起到定罪的规格和定罪的模式作用。但是,这一犯罪构成理论是以犯罪概念为基础,以论证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为己任,从而使犯罪构成成为从属于犯罪概念的附属品,不过是揭示犯罪本质特征的犯罪概念的具体化。同时,由于这个犯罪构成体系存在着机械、僵化等缺陷,在许多问题上并没有明确具体划清罪与非罪的界限,以致呼吁对现行传统的犯罪构成理论进行重构被提到了刑法学研究的议事日程上来。
(一)犯罪构成重构的理论依据和指导原则
提出重构犯罪构成的理论依据主要在于现行传统的犯罪构成过分强调以犯罪概念为基础,以犯罪概念为内容,以致使自己仅仅成为犯罪概念的具体化表现,这样混淆了犯罪构成与犯罪概念的应有区别,严重影响了犯罪构成自身的定罪功能,这样犯罪构成的重构就势在必然。在我们看来,犯罪概念的基本意义在于揭示犯罪的本质属性和基本特征,以表明在我国刑法中所规定的所有犯罪,其本质都是对我国现有社会制度、社会秩序和社会利益的侵害。犯罪概念解决的是犯罪行为的政治内容问题,所以犯罪概念一经高度抽象,任何犯罪都不可能跳出这一范畴。而犯罪构成的基本功能在于明确犯罪的成立条件和表现特征,以解决犯罪行为的法律评价问题。犯罪构成实际上是刑事立法规定的犯罪的“规格”,是刑事司法进行法律评价的定罪模式。因此,犯罪构成的内容(要件)都应该为这一基本功能服务,同样,任何事实特征也只有符合这一基本功能需要才能成为犯罪构成的内容(要件)。
犯罪构成的基本功能既然是犯罪的规格、定罪的模式,那么犯罪构成在重构时必须受定罪的原则所制约,也就是说,我们对犯罪构成的重构,必须以犯罪构成应有的基本功能为出发点,以主客观相一致的定罪原则为指导,以能够在司法实践中解决危害行为能否构成、是否构成犯罪为归宿。主客观相一致的定罪原则作为我国刑法的一个基本原则,其本身表明一个人的行为要构成犯罪并欲追究其刑事责任,必须认定行为人不但在客观上实施了危害社会的行为,而且在主观上存在犯罪的罪过,同时其罪过的内容与行为的形式具有一致性。这两个方面的内容缺一不可,否则就不能认定行为构成犯罪,也不能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犯罪构成不但应当受主客观相一致的定罪原则的制约,而且其内容(要件)也应当体现这一原则的应有内容。即能够反映行为人主观罪过和客观行为的内容才是犯罪构成的要件。
(二)两种犯罪构成的比较对重构的影响
现行传统的犯罪构成所存在的明显缺陷,使得很多刑法学者对犯罪构成的重构跃跃欲试。提出了种种新方案。有的提出犯罪构成三要件,此说认为犯罪主观方面和犯罪客观方面二者本来就是密不可分的有机整体,并且如果抛开危害行为中包含、渗透着行为人的主观罪过这一特殊性,就难以正确解决刑法的因果关系,所以此说主张把主观方面与客观方面合并为“危害社会的行为”这样一个要件。这样,犯罪构成的要件就是三个:主体、危害社会的行为、客体。也有的提出犯罪构成五要件说,此说认为没有提到犯罪行为就先提到犯罪条件,在逻辑上是不通的。因此,犯罪构成的要件应当是:犯罪的行为;犯罪的客体;犯罪的客观方面,即犯罪的危害结果及其与犯罪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犯罪的主体;犯罪的主观方面。(注:高铭暄主编:《新中国刑法学研究综述》,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11月版,第117~118页。)应当承认,这些探索是可贵的,但这种探索的成功可能性是值得怀疑的,正像有的刑法学者一针见血地指出的:“在一些人那里,所谓犯罪构成新体系只不过是像玩弄并积木游戏那样,对旧的内容(要件)作新的排列组合”。(注:陈兴良:《刑法哲学》,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1月版,第549页,第673页。)正因为如此, 这几种对现行传统犯罪构成提出修正重构的观点,并没有对它产生伤筋动骨的影响,犯罪构成四要件说至今仍然在刑法学上占据着统治地位。
我们认为,犯罪构成重构过程中要件的组合与取舍,不但应当以犯罪构成应有的基本功能为出发点,以主客观相一致的定罪原则为指导,以能够在司法实践中帮助解决危害行为能否构成、是否构成犯罪为归宿,同时对当今世界刑法学上两种主要的犯罪构成体系进行必要的比较也会给我们应有的启迪。
当今世界刑法学上两种主要的犯罪构成体系,一种是指前苏联和我国现行传统的犯罪构成模式,它由犯罪客体、犯罪的客观方面、犯罪主体、犯罪的主观方面等四个要件组成。另一种是指德国、日本等大陆法系国家的犯罪构成模式,它是由构成要件的符合性(该当性)、违法性和有责性三个要件组成。在大陆法系国家的犯罪构成体系中,构成要件的符合性(该当性)是指行为人的行为已经符合法律对某一具体犯罪规定的客观外部的要素要求,违法性是指行为违反刑法要求禁止实施的规定,有责性是指行为人在具有责任能力的前提下在主观上具有故意或过失的罪过时应当承担的责任。这两种犯罪构成的功能都是要为刑事司法实践提供一个正确定罪的模式。但是在具体定罪的方法上或构成适用的方式上,两者是有显著区别的。有的刑法学者将前苏联和我国现行传统的犯罪构成四要件模式称之为是一种耦合式的逻辑结构,将大陆法系国家的犯罪构成之要件模式称之为是一种递进式的逻辑结构。(注:陈兴良:《刑法哲学》,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1月版,第549页,第673页。)
两种犯罪构成在逻辑结构上和构成运用于定罪时的方法上的不同,使得支持、主张其中之一的学者都津津乐道地认为只有其中的一种才是最好的,而对另一种则嗤之以鼻。然而,两种犯罪构成模式的基本功能的同一性,表明了两者之间存在着可比性,特别是当我们对某种具体的杀人、放火、抢劫等犯罪行为,放在这两种不同的犯罪构成模式中去衡量认定,其结果却是惊人的相似,都不会出现有罪变为无罪,无罪变为有罪的令人担心的结果。这种殊途同归的结果,使我们能够清醒地认识到,不经过深入的研究、仔细的比较,武断地认为谁是谁非,以致盲目地赞颂一个、排斥一个的做法是多么的肤浅。
两种几乎不同的犯罪构成模式对同一种行为的认定为什么会得出如此惊人相似的结果?原因何在?实际上这种殊途同归,异曲同工的现象表明这两种犯罪构成模式结构中必定存在共通共有的内容。比较的方法常常能使人获得崭新的启示。只要我们对这两种构成模式进行比较时将两者重叠起来加以考察,就会发现在这两种模式中,四要件说中的犯罪的客观方面与三要件说中的符合性(该当性)完全是同出一辙,而四要件说中的犯罪的主观方面与三要件说中的有责性别无二致。这就告诉我们,任何一种犯罪构成的建立,都必须以犯罪的主观罪过与犯罪的客观行为作为各自模式的核心内容,它们对任何犯罪的认定都是绝不可缺少的,缺少其中任一要件,犯罪构成就不成为犯罪构成,在解决如何定罪的问题面前将变得一事无成。这种比较的结果同时还告诉我们,两者完全重叠之外的所有其他要件,对于任何一种构成模式来说,都是可有可无的。本无变有,反而变得累赘拖沓,影响犯罪构成本身的科学性。
由此我们认为,在我国现行传统的犯罪构成模式中,犯罪主体不能作为犯罪构成的必要要件,作为犯罪主体的资格是犯罪构成得以成立的基础,作为犯罪主体的身份是犯罪构成得以确认后的结果。这是因为犯罪构成是犯罪实事的特征表现,犯罪主体不属于犯罪事实的组成部分,因此它不作为犯罪构成的应有内容。同样,传统犯罪客体所指的社会关系、社会利益也不能作为犯罪构成的必要要件。任何犯罪都是对社会主义社会关系、社会利益的侵犯,这是犯罪概念所要揭示的内容,也已被我国刑法的犯罪概念所揭示,是社会危害性的集中体现,并且是刑事立法对犯罪进行宏观规定和分类时的必要依据。犯罪概念既然已经解决了社会关系、社会利益在刑法保护中的地位,没有必要再成为犯罪构成的累赘。
而在大陆法系国家的犯罪构成模式中,从构成要件的符合性(该当性)着手,以有责性为印证确定行为是否构成犯罪时,再引入违法性要件也是多余的。在我们看来,行为的刑事违法性与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一样,也是犯罪概念揭示的内容,是犯罪的基本特征、属性特征,而不是犯罪行为本身的事实特征。因此,将违法性作为犯罪构成的一个具体要件,实际上降低了违法性在刑法中的地位和意义。同时,违法性作为犯罪的一个基本特征,又是司法活动评价的结果,而不是评价的对象,也就是说不是犯罪行为本身的事实内容。对这一点,大陆法系的刑法学者也已看到,例如台湾刑法学者韩忠谟指出:“行为之违法性与行为之侵害性同属犯罪构成三要件而其性质有异,侵害性乃行为所具侵害法益之情状,而违法性则系侵害法益之行为所示之消极的价值”。(注:韩忠谟:《刑法原理》,台湾雨利美出版公司1981年5月增订14版,第137页。)尽管韩氏仍把违法作为犯罪构成的三要件加以论述,但他已经指出违法性实际上是规范评价的结果。这样,违法性就不应该成为犯罪构成的一个要件。
(三)犯罪构成的重构设想
通过以上我们对犯罪构成基本功能的认识,对犯罪构成重构的理论依据和指导原则的确定,对现今两大犯罪构成模式的比较,我们认为犯罪构成归根到底是要解决行为是否构成犯罪,构成什么罪的问题,所以犯罪构成的重构自始至终都要为这一目的服务。同时我们认为对犯罪构成的重构论证应当是深入的,但重构后的犯罪构成应当是简洁浅显的。我们不赞成把犯罪构成塑造成一个庞大的体系,把它看成是一个无所不包的体系,又是一个对所有问题都有灵验的妙药。
据此我们认为,犯罪构成是指在主观罪过支配下的客观行为构成某一犯罪时所应当具备的主客观要件的有机整体。这种犯罪构成既是刑事立法规定某一犯罪时设立的具体的规格标准,又是刑事司法认定某一行为是否构成犯罪的定罪模式。在这个犯罪构成中只有两个必要的构成要件。即作为主观要件的主观罪过和作为客观要件的客观行为。主观要件是定罪的内在依据,客观要件是定罪的外在依据。
在这个犯罪构成中,有一个问题我们需要提出来加以特别指出,即以人或物为内容的犯罪客体(对象)能否作为一个独立的构成要件而存在?对此刑法理论界有人持肯定意见。我们认为,以人或物为内容的犯罪客体(对象)作为一种客观存在,在被犯罪的认识活动和犯罪的行为活动指向、作用之前,是不具有任何刑法上的意义的。而当它一旦被犯罪的认识活动和犯罪的行为活动指向、作用时,犯罪客体(对象)就同时与主观罪过与客观行为发生联系。作为犯罪的主观罪过其形成过程和形成特征应当是:意识——客体(对象)——意志;作为犯罪的客观行为其实施过程和实施特征应当是:行为——客体(对象)——结果。因此,我们认为犯罪客体(对象)不应是犯罪构成的一个独立的构成要件。
五、犯罪构成在刑法学中的地位
犯罪构成理论在我国社会主义刑法学理论体系中据有十分重要地位,但这一地位重要到什么程度,在刑法学理论体系中如何给它正确定位。随着我国刑法理论的深入探讨和我国刑法学理论体系面临更新的时候,有必要重新审视。
(一)犯罪构成在刑法中地位的现状及其思考
新中国的刑法学是在充分借鉴、吸收前苏联刑法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而犯罪构成的理论几乎是苏联刑法学中犯罪构成理论的翻版,审视犯罪构成在我国刑法中的现有地位,我们不得不回顾一下犯罪构成在苏联刑法学中的地位。苏联刑法学者A·H·特拉伊宁在《论犯罪构成的一般学说》一书中写道:“犯罪构成的一般学院,在社会主义刑法理论中占着核心的地位。犯罪学院中的一切问题——关于犯罪行为及其结果的问题,关于应受惩罚的行为的范围及其组成因素的问题——都是同犯罪构成这个总的问题的解决密不可分地联系着的。其次,对刑法中的许多重要制度——罪过、共同犯罪、预备行为和未遂——的研究,也必须预先对犯罪构成及因素有明确的了解;这里特别会发生这样的一些问题,如关于社会危害性和违法性的意义问题、关于故意的范围的问题、关于未遂与预备行为二者之间的界限问题等等”。(注:[苏]A·H·特拉伊宁:《论犯罪构成的一般学说》,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2页。)特拉伊宁的这一论断, 在整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刑法理论上产生过十分深远的影响,我国的刑法学理论在过去很长的一段历史期内,更是对此深信不疑,打开现有的众多教科书,几乎是千部一腔,众口一词。然而当我们对这一论断细细探究之时,就会感到这里大有可质疑之处:
第一,犯罪构成处于“核心地位”,那么刑法上的一切规定和一切问题自然都应以此为中心而展开。但是犯罪构成的基本功能主要在于规定犯罪的规格,以此作为认定犯罪的标准。这样犯罪构成的这一功能必然受制于犯罪概念,离开了犯罪概念,犯罪构成就无能为力,无所依存,而犯罪概念本身揭示了危害社会的行为,只有具有刑事可惩性,才有可能在刑法上作为犯罪而被规定在刑法之中。刑法本身就是关于规定犯罪与刑罚的法律规范,犯罪与刑罚彼此不可分离,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和刑事可罚性通过刑法的规定被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然而在犯罪构成这一封闭性的结构中,刑罚的内容在现存的犯罪构成中没有任何位置,刑罚的内容不过是作为犯罪构成的法律后果而存在于刑法理论上。于是在犯罪论体系之外又自然地产生了一个刑罚论体系,出现了以刑罚论体系与犯罪论体系相并列并以此作为两大板块基本格局的刑法学体系。在这样一个刑法学体系中,将犯罪构成作为刑法理论体系的“核心地位”本身就不摇自动。
第二,将犯罪构成视为刑法理论体系的“核心地位”,就必然得出只要解决了犯罪构成问题,量刑问题就自然得到解决的结论。然而犯罪构成的基本功能主要在于规定犯罪的规格、解决犯罪标准的特点,决定了犯罪构成是承担刑事责任的基础。从犯罪构成的宏观角度,固然解决了认为行为符合犯罪构成而构成犯罪,就必然要承担刑事责任,但是从犯罪构成的微观角度,行为构成某一具体犯罪,怎样量刑以体现罪刑相适应的等衡关系,犯罪构成都无法作出正确的回答。例如同是贪污罪,数额较大的贪污与数额巨大的贪污,情节较轻的故意杀人与情节严重的故意杀人同存于一个犯罪构成中,此时量刑的轻重与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大小相适应的,然而社会危害性大小的程度在犯罪构成中找不到应有的位置。由此看来,认为解决了犯罪构成、解决了犯罪的性质、解决了承担刑事责任的基础,就等于解决了量刑问题,显然是无法自圆其说的。
第三,现有的犯罪构成是以既定的犯罪规格为全部内容,这就决定了对适用刑罚轻重的人身危险性依据无法予以包容,例如累犯制度,自首制度等等,但正是这样一些涉及人身危险性大小的因素都是我们量刑时必须加以考虑的。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犯罪构成至多能够解决已然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性质,它只是解决了量刑基础的一部分,而以此认为犯罪构成是刑法的核心问题,显然不够全面。
由于犯罪构成“核心地位说”存在着上述致命的缺陷,其“核心地位”发生了根本的动摇,于是摒弃这一“核心地位”的观点就应运而生。(注:张智辉、赵长青:《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刑法学体系》,载《政法论坛》1993年第6期。 )更有刑法学者提出了建立以罪刑关系为中心的刑法学体系。(注:陈兴良:《刑法哲学》,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1月版,第549页,第673页。 )这些观点的提出无疑是对犯罪构成“核心地位说”的有力否定,具有较大的合理性。我们认为,刑法理论不等于刑法规范,正像刑法规范不等于刑法理论一样,应当允许多元化的争鸣。
(二)犯罪构成在刑法学体系中的重新定位
否认犯罪构成的“核心地位说”,并不是否定犯罪构成在刑法学体系中的应有地位,这里有一个怎样给其合理定位的问题。给犯罪构成合理定位,必须以犯罪构成应有的功能为基础。
犯罪构成理论的刑法理论上的提出,一开始就肩负着实现罪刑法定原则如何确定犯罪规格的使命,在现有的刑法理论中,离开了犯罪构成,就无法正确地体现犯罪概念的应有内容,无法正确地确定行为是否构成犯罪的问题,犯罪构成在确定犯罪方面的作用,直至今天仍然是其他理论和其他标准所无法替代的。但是有一点我们始终不能忽视,即犯罪的理论体系的内容在刑事法律规范上、犯罪行为的事实结构上、刑事司法的规范评价上有着不同的体现。在罪刑法定原则的前提下,先有法律对犯罪行为的规定(这不是以犯罪与法律产生的历史发展过程加以考察的,而是从刑事立法对犯罪的规定和刑事司法对犯罪的认定角度加以考察的),后有行为人的行为是否具有违法的事实,再有司法实践依据法律进行司法评价,判断违法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尽管有的刑法学者提出:“应当把刑法上规定的犯罪构成称之为法定的犯罪构成,把社会现实中客观存在的犯罪构成称之为现实的犯罪构成或犯罪构成事实”,(注:何秉松:《〈犯罪构成系统论〉导论》,载《政法论坛》1993年第3期。)但是,作为犯罪规格的犯罪构成只能是指刑法规范。即使在学者们提出的各种充分说理和自恃具有理论根据的刑法学新体系中,(注:储槐植:《刑法例外规律及其他》,载《中外法学》1990年第1期。 曲新久:《试论刑法学的基本范畴》,载《法学研究》1991年第1期。 )犯罪构成也都只是各种刑法学新体系中“罪”的组成部分,它起着法律对犯罪规定的界限作用,它是刑事立法者对某种行为确定为犯罪的意志体现,但它不可能是“罪”的全部内容。它只是规定犯罪的法律规格,是犯罪的行为事实,是犯罪的司法认定的“犯罪系统理论”中的起点。认识到犯罪构成在刑法学理论体系中的合理位置,我们就决不应该再过分夸大它在整个刑法学理论中的作用。这一合理位置也应当是犯罪构成理论的合理回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