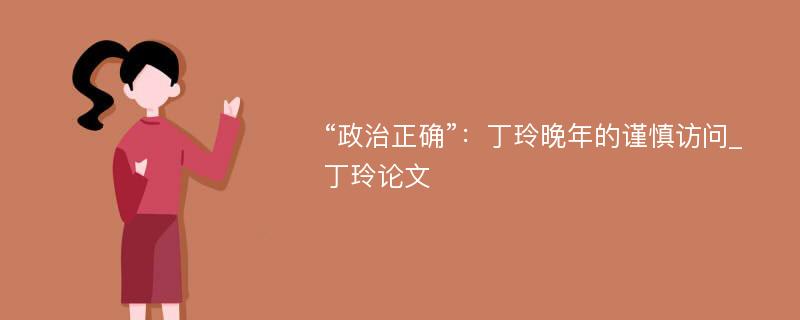
“政治正确”:丁玲晚年谨言慎行的出访,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谨言慎行论文,晚年论文,正确论文,政治论文,丁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丁玲年轻时就有出国的愿望和可能,但都没有实现。1920年代中期,丁玲在北京“漂”着时,曾经有人表示愿意出资带她去欧洲留学,她有些心动,但因亲友的阻拦而未果。1927年,丁玲的《梦珂》发表,得了二百元稿费,她想用这笔钱去日本留学,因此经人介绍跟冯雪峰学日文,但是,二人未能成为师生关系,却成了恋爱关系,学日文和去日本的事不了了之。1936年,丁玲从南京逃出来,在去往苏区的途中,潘汉年建议她去法国为革命募集资金,她虽然对法国无限神往,但在不明不白地被国民党软禁三年之后,她更急于向党证明自己革命的忠心,所以,还是选择了去苏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丁玲有过几次出国的机会,但去的都是苏联、东欧这些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
丁玲对于英语的态度,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她对以英语为中心的西方世界的兴趣。艾芜回忆左联时期自己在丁玲领导下工作时写道:记得有一次谈到个人的将来,她感慨地说:“我要抽点时间,把英文继续学下去,将来老了,不能创作了,就翻译外国文学书。”①1948年,丁玲参加在匈牙利举行的世界民主妇联第二次代表大会,她在日记中写道:“……我了解了我工作的渺小,我了解了许多人为什么改行。只要会说两句英文就比一个作家有用得多,被看得起得多。”②
丁玲的文学影响,主要是在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以《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获得斯大林文学奖为顶点。美国人在1980年代初期感兴趣的是沈从文这样的自由主义作家,丁玲在“清污”中接受记者访问时说:“还有种怪事,30年代某些作家的一些远离人民生活的作品,只要国外有人捧,我们就也有人跟着叫好。”这“某些作家”,至少是包含她所不服的沈从文在内。所以,从扩大文学影响力的角度讲,她对美国乃至西方文学界是不抱多大奢望的。她访美访欧的主要动机,是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
历史到了“新时期”,国门打开,丁玲也获得了政治解放,终于有了去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看看的机会。此时,“冷战”结束不久,“冷战”思维尚未褪尽,丁玲这样一个来自于社会主义国家且受尽政治迫害的女作家的出访,当然会引起政治上的敏感,这敏感来自国内,也来自国外。
国内,她的政治对手们在等待着听她在国外说什么,或者直接说,在等待着她在政治上出现什么言语闪失,那将成为他们打击她的重要把柄。甚至在她访美之前,中国作协就已经有人放出风来,说邀请她的“国际写作中心”是拿美国联邦调查局的钱的。
国外,那些“敌视中国人民的外国文人”③、“别有用心的外国记者”④,期望从丁玲口中听到某种叛逆的语言,来作为攻击社会主义中国和中国共产党的口实。
出去看看的愿望是简单的,但如此“内外交困”的阵势,却使丁玲不能不面临巨大的政治压力。这不仅是一次观光旅行和文学交流活动,而且是一种具有微妙的政治含量的外交行为。丁玲是谨慎的,正如有人所说:“丁玲在参加重要的国际活动前,总要认真了解党和国家的有关政策原则,研究有关情况。”⑤
她甚至是紧张的,她知道兹事体大,任何一点微小的闪失都将使她万分被动。此时,她的历史问题的结论还是:在敌人面前犯过政治上的错误。她必须把政治上的安全放在第一位,宁可不讨喜、不可爱,宁可被骂、尴尬,也不能在政治上陷入被动,她是输不起的。
这种态势决定了丁玲在国外的发言几乎别无选择。
1981年11月,哥伦比亚大学,丁玲向在座的三百位中美文化界的朋友说:“有个美国记者问我:在那些遭受折磨的漫长岁月里,什么力量使你能够活到现在?我告诉他:一是相信党,二是相信人民,带着党历来对我的教导,我深入人民之中,是人民给了我勇气和力量。人民群众对我的了解和信任,是医治我心灵上隐痛的良药。”⑥
丁玲在依阿华、芝加哥、普林斯顿、华盛顿、哈佛、耶鲁等大学的讲演,以一个中国共产党党员、一个中国作家的骄傲,充满激情地回答说:“以‘自我中心主义’为最高生活准则的美国人,是不能理解我经历了那么多的不幸,为什么还如此朝气蓬勃?你们大概不理解,我首先是共产党员,其次才是作家。在我遭受不幸的时候,我们党和人民,也都在同样遭受到蹂躏。许多功劳比我大的革命元勋、建国功臣,他们所受的折磨比我更深,我个人的一点损失算得了什么呢?”“一个革命者,一个革命作家,在革命的长途上,怎能希求自己一帆风顺,不受到一点挫折呢?现在我们的国家,正处在大乱之后,疮痍满目,百废待兴,举步维艰。此情此景,很容易使人联想到古代的多少爱国诗人,他们长歌当哭,抑郁终生。但我决不能沉湎于昨天的痛苦而呻吟叹息,也不能为抒发过去的忧怨而对现今多有挑剔,我更不能随和少数人那种虽出自好奇心,但忽视全局、轻易做出的片面的论断。我们需要的是同心同德,埋头实干,勤奋学习,奋发图强的精神。现在,我搜索自己的感情,实在想不出更多的抱怨!”⑦
有的人问:“共产党把你已经整成这个样子了,你怎么还是——或是,就是要整得你只能这么说了?”丁玲的回答是:“不!整我的不是共产党,只是党里作了错事的人!这才是整得我更明白的道理!”⑧
据丁玲说,当时就有人善意地提醒过她:“在爱荷华大学教中国民族民间舞的、北京去的中国舞蹈学校的教师许淑英打电话对我说:‘阿姨!你的讲话被认为太官气了,好像官方代表讲话,这里人不喜欢听,他们希望你能讲讲自己。’”⑨
丁玲的讲话,有官方考虑,也有她自己的真诚,当一个人把自己的命运与国家、时代结合起来的时候,她确实会有这样的感受。
境外反共势力试图利用丁玲。联想到张光年在她的历史问题平反时,抛出从香港来的徐恩曾的回忆录,可以推知,一旦她被境外所利用,国内就会有人把境外对她的利用拿来进行再利用。但是,境外一旦利用不成,就会对她冷嘲热讽,而这也会成为国内奚落她的话柄。但这比政治话柄的杀伤力轻多了,她还是宁肯被冷嘲热讽,也不要被利用。只要得到上头的肯定,她的对立派再怎么奚落冷嘲热讽,她都可以笑傲以对。
根据“敌人拥护的,我就反对”这一原则,丁玲甚至希望被境外反共势力所骂。她在哥伦比亚大学的演讲中提到:我在爱荷华时,有位台湾来的年轻人来找我。我跟他说,如果有人写文章骂我我也不在乎。如果有人要在台湾写文章骂我,那就更好,那增加了我革命的政治资本。我还问他,你知不知道我是共产党员,你是在跟一位共产党员说话。⑩
因为历史问题的诉求,丁玲确实比一般人更提防被利用。美国出了一本书,有一章专门讲她,称她为“持不同政见者”。然而,丁玲说:“我不是什么持不同政见者,我是拥护党,拥护毛主席的!我是‘歌德派’!”(11)她不能不发表这样的“严正声明”。为她带来“左”的口碑的许多言词,其实就是这样被逼出来的。类似这样的话,她还说了很多。(12)
她在回答一位别有用心的外国记者时说:“我宁愿在国内当‘右派’,也不会去国外当‘左派’。”(13)
她对李黎说:“我自己就感觉宁可在底下当右派劳动,尽管苦,其中还有乐。要我跑到外国去,也许人家会当宝贝,拿我做具体反共产主义的标本,但我才不去!”(14)
陈明接受李辉访谈时说:丁玲在晚年还是注意维持和周扬的关系的。在国外访问时,丁玲从来没有讲是周扬整的她,只是讲是党的一些失误。(15)陈明不同意把周扬列入丁玲治丧委员会名单时说:我们在国外时,外国人总问丁玲:周扬怎么打的你呀?丁玲说:不是周扬的责任,是我们自己愿意下放锻炼。丁玲对我说:在外国人面前不能不护短。(16)
既然对“宿敌”周扬都如此护短,那的确说明丁玲是内外有别的。但是,又有人对这一情节给出相反的说法:
1981年秋天,我同丁玲一起去美国参加爱荷华大学国际写作计划中心的活动,住在五月花公寓,有一个多月。有一天,一位保加利亚作家和夫人来访问她,由我充当翻译。那位保加利亚作家问丁玲:“当年定你为丁陈反党集团,把你流放到北大荒,据我们所知,主要是周扬对你不好,那么现在你饶恕不饶恕周扬呢?”丁玲就讲:“我不饶恕,我永远都不饶恕,直到我死去那一天。”说得那么坚决的。
我只替她翻了“我不饶恕”那句话,而“我永远不饶恕,直到我死去那一天”这一句,我没有替她翻成英语。我觉得她这样说不好。周扬当然有不对之处,但都已经过去了嘛,何必到死都不饶恕呢,特别是对外国人这么说,我认为不好。(17)
对此说法,陈明坚决予以否认。
一篇研究丁玲传记的文章指出:由于丁玲特殊的经历和历史环境,有些材料如果不加辨析和使用难免会以讹传讹。比如关于解放初期丁玲和沈从文在北京的相见情形、关于丁玲50年代被打成反党集团的真实原因、关于丁玲在北大荒的情形、丁玲和当代中青年作家的关系问题、丁玲在美国演讲遭冷遇的问题等等,不少版本的传记都有不同的表述甚至互相矛盾。到底哪些材料经过证明被认定为真实可靠的,可以引用;哪些被证明是“伪证”的必须被抛弃,这些恐怕是丁玲传记的作者甚至是研究者要特别谨慎对待的。而这些材料如果本着对历史负责的态度下一番大力气是不难搞清真伪的,遗憾的是我们看到有的传主在使用材料的时候不够严谨,这难免使自己的研究成果大打折扣。(18)
但证实与证伪,都谈何容易!历史某种程度上就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历史永远不会只留下唯一正确的版本,研究者在没有足够的依据做出取舍判断之前,只能把各种版本都呈现出来,连同迷惑一起交给读者。
丁玲对自己在国外的表现是满意并如释重负的,她对自己的讲话体现出来的政治高度和外交水准感到自豪。她有充当大使的自觉,同时也让周扬看到了:讲官话不是他的专利。
她坦诚地说,我这次访美,有人是有戒心的,好在我在美国说的话都是对得起人民的,对得起国家的,对得起党的。我不是好好的回来了吗?(19)
谈到美国某些人对她的“失望”,过去有人对她的出国是有戒心的,还设障碍。这次令人担心的美国之行,她说,也算是不辱使命吧。(20)
显然,对于自己的出访,丁玲是很有使命意识的,所以,当她义正词严地捍卫党和国家的利益时,胸中是充溢着政治使者的光荣感的。
丁玲的访美表现招致驳杂甚至截然对立的评价。西方对其表现除了不以为然甚至无法忍受,也有表示首肯的。
丁玲在美国访问期间,许多美国报刊发表了评论、访问记。纽约一家报纸在评论中写道:“我们在她身上看到了作为一个革命和文学殉道者的美丽灵魂。”(21)
“我在美国爱荷华听一位朋友说,你们的丁玲是位‘女强人’,她的政治气质令人难以置信。”(22)——其实这位朋友的话可以做中性的理解。
也有美国的丁玲研究者表示理解和体谅。丁淑芳说:“1981年访问美国时,她好像继续在说服自己。……她避免在任何场合批评党……我相信她的自我牺牲和热情的爱国主义符合传统的中国历史悠久的孝道典范。从那个观点来看,她只是不愿向外人暴露对党可能有的任何不满或者批评。”(23)“或许她必须通过进一步使党变得人性化为其所受的伤害作合理解释。”(24)
国内不以为然者有之,大加赞赏者也有之。但总体上看,前者多于后者。
对于前者来说,丁玲访美期间的表现,是她被封为“左”王的重要“罪证”。陈明说过:丁玲由“右”派变成“左”派,因为丁玲在清除精神污染中讲了真心话,丁玲在国外没有骂党,不说共产党的坏话,丁玲就是“左”王。(25)
丁玲访美期间的表现,也是前者做出“丁玲晚年已深深陷入一个走不出的怪圈,其突出表现在失落感、失语症、恐惧情结等方面”(26)这一论断的重要依据。对此,有人反驳说:“奇怪得很,是丁玲晚年陷入了政治怪圈,还是某些研究丁玲的人陷入了思维怪圈,先给了丁玲一种预设的选择?难道丁玲复出后牢骚满腹,访美期间大肆抨击共产党员就符合逻辑了?就不是陷入怪圈了?就是正常的丁玲了?”(27)诸如“异邦人士大失所望”(28)这样的措辞,确实带有点鲁迅先生所批的“友邦惊诧论”的意味。
前者相对年轻,多是文学创作和研究者。后者多是与丁玲同时代的人,与她一样走过早年参加革命、晚年犹九死未悔的人生道路,他们对于丁玲晚年的肯定,某种程度上就是对自己人生选择的肯定。二者相左的背后,其实贯穿着整个中国20世纪更深层的思想观念和道路选择的冲突。
后者往往也会被前者视为“老左”。从后者在丁玲访美问题上的发言,可以知道何以如此:
她是清醒的,自觉的,是会相机工作,而又守纪律的。这点,几年来,我是比较清楚的。这与某些单纯强调作家的个性,自由,开放等等,而不顾其他,甚至连国格、人格也无所谓的人相比,丁玲的风格是高的,形象是好的。不回避,也不迎合。她不愧是一位经过考验的社会主义中国的老战士、老作家。(29)
出访美国之前,她先赶回北大荒去看望父老乡亲,此举真正震动了我的灵魂,我觉得这不仅是丁玲对祖国母亲的深情,也是一个共产党员鲜明的政治立场。在美国,她没有抱怨、没有诉苦,在演讲时,第一句话就是“我是一个中国共产党员”。(30)
极为难得的是丁玲对这长期冤屈的遭遇,毫无怨言。有的别有用心的国外资产阶级的所谓学者,总想从我们被伤害过的同志中,打开一个缺口,但这种企图,在丁玲那里却受到了严正的回击。(31)
同样一段话,前者与后者的反应是如此不同。
前者的反应是:
1981年,丁玲在美国访问期间与美国朋友进行了交谈,她认为:“我个人是遭受了一点损失,但是党和人民、国家受到的损失更大。……一个革命者,一个革命作家,在革命的长途上,怎能希求自己一帆风顺,不受一点挫折呢?”(周良沛:《丁玲传》第782页)这种对待历史的态度表面看来是非常豁达的,其实质是回避历史,没有正视历史,因为1949年以后,经历苦难的并不是她丁玲一个人或者少数几个人,而是“党和人民、国家”。因此,就算她不为自己的不幸遭遇鸣不平,放弃个人的某些权利,她也应该像巴金、邵燕祥、张贤亮、王蒙等人那样为整个中华民族的空前浩劫,整个国家的历史悲剧去思考,作出深刻的反思,这是一个知识分子不可推卸的责任!作为一个作家,丁玲没有任何理由不面对历史,反思历史。因而,她的晚年这样的人生态度多少令人失望。她的这种局限决定了她不能从自己几十年的从座上客到阶下囚的过程中得出这样的认识:她的所有不幸只是为了维护自己的作家身份,而不是充当别人喉舌的宣传员,只是为了维护知识分子的一点有限的独立和自尊,也是为了保持一点尚未消磨殆尽的个性而付出的沉重的代价。她所付出这些代价仍然没有催醒她对这个问题有一个清醒的认识。(32)
后者的反应是:
在这近四分之一世纪的漫长的时日里,她遭受到的磨难不可谓不重,时间不可谓不长,而她对党不仅没有丝毫抱怨,且革命的立场更坚定了,对党更热爱了,对马列主义的信仰更笃诚了,这一点确实震撼了我的灵魂。她不止一次地说……她在访问美国对公众讲话时,也是这样说的……(33)
以丁玲去北大荒以及养鸡这件事的发言为例,来放大一下她访美的尴尬语境:
丁玲在美国作过几次演讲。有一次她在一次集会上演讲,有人问她:丁玲女士,你为什么要到北大荒呢?她说:“我是为了去体验生活。”其实,怎么会是去体验生活呢?应该讲,那是因为划了右派嘛。所以,当时美国人听了,就在会上大声喊:“She is telling lie!”“她在撒谎!”人家知道的,怎么能隐瞒得过去呢,大概她这不是说给美国人听的,是说给国内的领导人听的吧。(34)
有些人热衷于了解她所经受的苦难,甚至有的出于特定的政治目的,希望她用自己的遭遇为他们提供攻击中国共产党的子弹。遇到这种情况,她就变得更为小心谨慎,甚至常常说些言不由衷的话。比如在访美期间,一些别有用心的人问起她在北大荒养鸡的事,她回答说“养鸡也很有趣味”。(35)
去北大荒“体验生活”和“养鸡也很有趣味”,当然是自欺欺人的回答。
丁玲在哥伦比亚大学的演讲中提到养鸡:
我在北大荒养鸡,不了解我的人很奇怪,认为我是作家怎能干这种活。他们不知道我那时想的是有一天摘帽后能当个好的养鸡队长,我不是为了工资或地位,而是一心想如何能把业务搞好。文化大革命后期,我在狱中,有的时候就拿旧报纸在床上摆图型,设想何处应是养鸡场、运动场、饲料场等。(36)
当我同一位作家谈话,说到在农场养鸡的事时,那位作家哭起来,说你是位作家,怎可让你干那种事。我说我是个共产党员,任何工作都可以干。他说你虽是共产党,但首先是作家嘛!我说不!我首先是共产党员。共产党员任何事都能做:能上,也能下。(37)
在接受日本学者的访问时,她还说,在北大荒,我们自己有家,住的地方干净利落。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人们都以为我们当时的生活苦得不得了,实际上并不是那样的。(38)
这是代表丁玲真实思想的说法吗?显然不是。正像有的学者指出的那样:“在另外的一些情况下,她也曾写到上述这些内容,但态度和观点则完全不同。同样是写北大荒养鸡生活,她愤慨‘为什么杜厂长、姜支书不另外给我们一栋房子,硬要我们把家安在养鸡的院子里。这里到底是我的家,还是鸡的家呢?’”(39)
丁玲在北大荒养鸡时间并不长。1958年7月12日,丁玲从汤原农场向作协党组发出第一封信,介绍自己住在养鸡场,在孵化室工作。(40)在王震的关心下,丁玲喂过一年鸡后,便当起了扫盲教员。也是在王震的关心下,丁玲和陈明后来住进了招待所,干净利落倒是有可能的,但那并不是他们的家。
养鸡也并未真正改变丁玲。张僖在正式报告中汇总当地对丁玲的看法:这个人表面上看来是叫干啥干啥,在劳动中也能挑土,挑鸡粪,切鸡菜等,干比较重的活,但此人并不简单。她原来的那一套还是原封不动,指望她的思想、立场有根本改造是比较困难的。(41)
在“文革”的困厄之中,养鸡的设想确曾给丁玲内心带来一丝光亮,如果说养鸡的“趣味”略可成立的话,依据可能就在这里。“我只想将来问题能解决,我希望陈明的政治处境能比我好一点,我能当一个养鸡队队长就满意了。坐在监牢里的时候,我把牙粉袋撕成碎方块,在铺板上摆着。摆什么?摆想象中的养鸡队的规划:那个地方是鸡舍,那个地点是运动场;要用多少人;饲料队,打鱼队等。我没有再当作家的希望或计划。”(42)
丁玲接受於梨华访问时说:“我爱我的文学事业,但我首先是共产党员,共产党员可以在任何处境下去做任何事情。我在延安参加过大生产劳动,劳动对我不是负担,我要求自己不把这看做耻辱,我是作家,在基层生活更亲近了人民,从另一个角度看,倒是难得的收益。”(43)
劳动对她也并非“不是负担”,她的脚腕都肿了,一按一个坑。她曾打算雇一个人洗衣服做饭,想必也是为了减轻劳动负荷。对于在北大荒劳动,她的说法有些自相矛盾。对於梨华,她说,“我是作家,在基层生活更亲近了人民,从另一个角度看,倒是难得的收益”;在丁玲创作讨论会闭幕式上的讲话中,她也说,20多年来,我在底下劳动工作,做家属工作,做群众工作,觉得也有好处。(44)但在1979年四次文代会上的发言中,她却说,“虽说在底下劳动了,但从我这个人来讲,到底不能算成绩”(45)。对于在北大荒劳动,她不会真心认为是好事,但她又不能说不是好事,因为,深入工农兵生活一直是她所宣扬的,所以,她只能一分为二:劳动是没有成绩的,但接近人民群众是有收获的。
“我要求自己不把这看做耻辱”,这句话实际上透露出:她并不是真的“不把这看做耻辱”。越是确认其包含耻辱,越是要竭力涂抹和掩盖。毕竟那是含有“改造”成分的劳动。
丁玲有意识地淡化和省略了苦难的一面,强化和突出了甜蜜的一面。在晚年的一次会议发言中,丁玲说:“二十多年的辛酸苦辣就这么过去了,很多事情我是不会讲的,跟我的女儿也不讲,讲这个做什么,但是好的哪,我要讲,我讲了许多好的东西,许多使我有收获的东西。”(46)
报喜不报忧,以喜掩饰忧,这是一个老年人的面子问题。在国外不报忧,并不仅仅是家丑不可外扬,在国内她也一直不愿提那些难堪的岁月,因为不堪回首,因为丢不起面子,在内部整肃中败北,被自己忠诚的党所“发配”,在她无论如何不是一件值得夸耀的事情。如周扬晚年并不把“异化”问题当作自己的骄傲,丁玲也并不把“发配”北大荒当作自己的光荣。
1975年丁玲从秦城监狱释放,来到山西长治,给侄女蒋祖静的信中说:“我们一九七○年来北京,住在郊区。环境极好,绿树参天,十分幽静。生活待遇,亦极丰厚。书籍很多,尽我浏览与攻读。……尽管我们来北京,系接受严格审查,但我们都很乐观,真正做到无私、无惧、无虑。”(47)在给儿子、儿媳的信中则说“在北京那样极为优越的条件下”。凭这种描述,谁能想象得到,所谓北京郊区的优越生活,其实是在秦城监狱坐牢呢?给亲人的信,她不必为党遮掩了吧?但她还是这样含蓄地美化,可见,是她自己要面子。一个给亲人的信中都会把自己的坐牢描述得如此幽雅的人,在外人尤其是外国人面前,怎么可能不维护自己的面子呢?
西方人士愤怒于丁玲的“撒谎”,但是,那样的发问,大致决定了它会得到怎样的回答。“怎么会是去体验生活呢?应该讲,那是因为划了右派嘛。”难道西方人士不明白这一点吗?为什么还要逼迫丁玲用自己的嘴说出来呢?如果她老实地做出“因为划了右派”的回答,必然又会面临下一个“为什么”,一直到她说出“受了共产党的迫害”为止,而这正是西方人士想要的答案。如同文本中会有“隐含的读者”,带有诱导性的发问也隐含着预期的答案。如果丁玲给出了西方人士想要的回答,回到国内,等待她的是什么?她的历史问题还有望平反吗?
既然她不控诉,大家也心知肚明;既然她美化,大家也不会相信,还何必要她控诉呢?如果她选择说出来,对别人的意义在哪里?对她,却是真实的麻烦。她的遭遇本身,就是最好的控诉,何必再给她增添新的遭遇?
问题不在于她的回答不诚实,而在于那些询问别有用心。应对别有用心,需要用诚实吗?也许是她带有政治宣传色彩的演讲令西方人不快,所以,才有了这样逼迫性的发问?丁玲的此种演讲,窃以为的确不做为好,至少她可以换一个话题,比如换一个文学话题。
因为这种半官方色彩的访问中所蕴含的政治压力,丁玲的“立功”愿望可能急迫了一点。“大概她这不是说给美国人听的,是说给国内的领导人听的吧。”——既然知道她需要“说给国内的领导人听”,还何必如此不以为然呢?丁玲可能有这层用意,毕竟,这对她历史问题的解决不无裨益。历史问题的平反结论,是西方国家给不了她的,也是指责她不说真话的人给不了她的。一个没有额外政治压力的作家,可以选择不回答,而带着历史问题紧箍咒的丁玲,就连沉默都不合适,所以,她选择了如此言说。另外,她也是不想给国内那些等着喝她倒彩的人一个机会。国内国外的眼睛都在看着,国家的对手、个人的对手都在看着,这注定是一个捉襟见肘的丁玲。是不是心里话?这个问题是天真的。大多数时候,人在社会中并非天真地活着。丁玲晚年的许多话,就像“反右”“文革”中的一些话,根本不能当真,更不必深究。
丁玲的回答既是出于自身的政治安全需要,也是对于别有用心的反驳。既然那些问话本身就带有政治预设,那么,拆解这种预设,不就等于避开一个陷阱吗?毕竟,谁也不愿意对一个话语圈套就范,反抗被动是人的本能。而西方人士的反应,则是落空之后的恼怒。
不管丁玲对中国怎么看,都不意味着她会跟美国跟西方站在一起。丁玲自己也反复表示:“我要批评自己的祖国,也不会到外国来批评。”(48)
操持外交语言是免不了的,不必较真,也不必深究。深究意味着世界上每个人每时每刻都在说真话,而事实上,言不由衷几乎在每个人身上都经常发生着。世道人心是经不起这种深究的,对于普遍“世故”的深究意味着苛责。在一种规约模式之中,人可以说什么,几乎是没有选择的。所谓察人论世,就是指在对问题作出评判时要充分体察个体的处境,如果前提是有限制条件的,结论却不顾条件限制,那么,再怎么义正词严的结论,都是没有信服力的不察之论。
想当年,在王实味被捕几个月之后,外界对王的情况十分关注且传闻颇多。一些到延安访问的中外记者便纷纷要求会见王实味。为了宣传的目的,组织上决定由丁玲出面将王实味带到记者们的面前,让王在已经备受折磨而又仍在政治高压的情况下,认罪悔过并感激毛泽东的宽宏大量和仁慈。一位在场的记者后来写道:“一个脸呈死灰色的青年,让丁玲带着,出来背书似地向记者们痛骂自己。”(49)
丁玲现在见海外人士尤其是海外媒体,如当年作为“陪绑”带王实味见那些“到延安访问的中外记者”,简直有异曲同工之妙,她能说什么呢?
丁玲在给宋谋瑒的信中写道:“自然,也很难不见外国人,这种时候,我大半很谨慎,怕授人、授自己人以柄,为再来挨一顿棍棒做口实。但愿这只是我的‘余悸’。”(50)她知道其中利害,但她见记者和外国人的次数还是不少,那就意味着她说“官话”的机会不会少。“官话”自然是官方爱听的,却导致了她在文坛的形象减分。
在文坛,丁玲旅美期间对个人苦难的讳莫如深,是被频繁指责的一个问题:“有的青年读者看了她的访美印象文章后给她写信,说她是‘配合宣传’,‘不能不使人失望’。”(51)
有学者说道:“在出国访问期间,津津乐道她被打成‘右派’时在北大荒‘体验生活’的快乐经历,且强调‘养鸡也很有趣味’时,她对自己遭受的非人道迫害丝毫没有反思,使异邦人士大失所望,当场有人指她在‘说谎’。”(52)这样的质疑还有很多。(53)
然而,她在国外的表现,也获得了肯定性的评价。1984年《关于为丁玲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中提到:(丁玲)几次出国活动,都有良好影响。(54)
丁玲的后事中,邓力群指示:最重要的是把悼词写好。(55)所以,丁玲的悼词是印发下去广泛集中意见后定稿的。作家支部的书记曾克送来的悼词修改稿和附信中说:丁玲同志在十一届三中全会恢复工作后,多次从事外事活动,影响突出,应有所表述。(56)
负责处理丁玲后事的中组部副部长郑伯克说:“中央领导同志了解丁玲,对丁玲的评价很高。”(57)“……这几年出国,中央反映很好。”(58)“丁玲在国外讲话时,不但没有怨气,而且拥护党的方针政策。”(59)
《人民日报》1986年3月16日《丁玲同志生平》中提到:她不顾年老体弱,多次出访,参加国际性文学交流活动。
看来,丁玲晚年的出访,对她个人来说是一件毁誉参半的事情,“誉”来自上层、官方以及她的“同道”,“毁”来自文坛民众层和西方。而正是这种“毁”与这种“誉”相加,共同打造了“晚年丁玲”的形象。
①艾芜:《有关丁玲的回忆》,中国丁玲研究会编《丁玲纪念集》,湖南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21页。
②丁玲:《从哈尔滨到匈牙利》,1948年12月3日日记,《丁玲全集》第11卷,第364页。
③(25)《拨乱反正的历史结论必须坚持——中国丁玲研究会针对〈百年潮〉杂志发表〈丁玲历史问题结论的一波三折〉一文召开的专题座谈会纪要》,《常德师范学院学报》(社科版)2001年第3期。
④杜烽:《缅怀丁玲》,中国丁玲研究会编《丁玲纪念集》,湖南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622页。
⑤朱子奇:《永不消失的春天——悼丁玲》,中国丁玲研究会编《丁玲纪念集》,湖南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81页。
⑥⑦郑笑枫:《丁玲在北大荒》,湖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67页,第67-68页。
⑧周良沛:《丁玲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783页。
⑨丁玲:《中国周末》,《丁玲全集》第6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92页。
⑩(36)(37)丁玲:《我怎样跟文学结下了“缘分”》,《丁玲全集》第8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41页,第240页,第241页。
(11)陈漱渝:《一个真实人的真实片段——悼丁玲》,中国丁玲研究会编《丁玲纪念集》,湖南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345页。
(12)比如,丁玲还说:“去年我被邀访问美国,有美国人希望我讲些铁幕里的话。我不知有什么铁幕。我热爱我的祖国和人民,我接受真理,坚信共产党,坚信马克思主义,做个螺丝钉,我的心就会发热、发光……”(林焕平:《她的心在发热、发光——记丁玲在桂林》,中国丁玲研究会编《丁玲纪念集》,湖南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107页);“我们是中国人,又不能重新投一次胎变做外国人,我们只能希望中国好起来,只能努力使中国好起来。”(朱正:《第一次去看望丁玲同志》,中国丁玲研究会编《丁玲纪念集》,湖南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241页);“我这个人很好理解。就算共产党里面有坏人,那也是我们自己的事,不能在外面说坏话。”(陈明仙:《让我们共同回忆》,中国丁玲研究会编《丁玲纪念集》,湖南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388页)
(13)杜烽:《缅怀丁玲》,中国丁玲研究会编《丁玲纪念集》,湖南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622页。
(14)[美]李黎:《“今生辙”——访丁玲》,《左右说丁玲》,汪洪编,中国工人出版社2002年版,第289页。
(15)李辉:《与陈明谈周扬》,《往事苍老》,花城出版社1998年版,第265页。
(16)王增如:《无奈的涅槃》,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版,第75页。
(17)(34)《黄秋耘访谈录:悲哀的中国作家群》,http://www.wangjiwang.com/memorial/shc13036.html
(18)文学武:《中国左翼文人传记写作研究——以丁玲传记为中心》,《南方文坛》2010年4期。
(19)胡真:《一个无私无畏的人——怀念丁玲同志》,中国丁玲研究会编《丁玲纪念集》,湖南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540页。
(20)李锐:《怀丁玲》,中国丁玲研究会编《丁玲纪念集》,湖南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62页。
(21)郑笑枫:《丁玲在北大荒》,湖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69页。
(22)(29)朱子奇:《永不消失的春天——悼丁玲》,中国丁玲研究会编《丁玲纪念集》,湖南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81页,第81页。
(23)(24)[美]丁淑芳:《丁玲和她的母亲:人文心理学研究》,范宝慈译,厦门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91页,第194-195页。
(26)许传宏:《析丁玲晚年的文学价值取向》,《当代作家评论》2001年第4期。
(27)赵焕亭:《从〈牛棚小品〉论丁玲晚年创作的个性〉,中国丁玲研究会编《二十世纪中国社会变革的多彩画卷——丁玲百周年诞辰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湖南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658页。
(28)(52)陈建华:《“五四的女儿”:爱情、传记与经典》,《随笔》2009年第6期。
(30)刘白羽:《丁玲在继续前进》,中国丁玲研究会编《丁玲纪念集》,湖南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98页。
(31)杜宣:《杏花红——悼丁玲同志》,中国丁玲研究会编《丁玲纪念集》,湖南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103页。
(32)孙德喜:《从丁玲的人生道路看中国20世纪知识分子的命运》,《新气象新开拓——第十次丁玲国际学术研讨会文集》,同济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90-391页。
(33)魏巍:《醒来吧,丁玲!》,中国丁玲研究会编《丁玲纪念集》,湖南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70页。
(35)(39)(51)张永泉:《走不出的怪圈——丁玲晚年心态探析》,《华北水利水电学院学报(社科版)》,1999年3月,第15卷第1期。
(38)[日]田畑佐和子:《丁玲会见记》(节译),《丁玲研究在国外》,王中忱,孙瑞珍编,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14-415页。
(40)(41)陈徒手:《人有病天知否——一九四九后中国文坛纪实》,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25页,第130页。
(42)(44)丁玲:《在丁玲创作讨论会闭幕式上的讲话》,《丁玲创作独特性面面观》,湖南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4页,第4页。
(43)张凤珠:《信仰的归宿——记丁玲》,《丁玲研究》2009年第1期。
(45)(46)周良沛:《无法漏抄的一则发言记录》,汪洪编《左右说丁玲》,中国工人出版社2002年1月版,第125页,第125页。
(47)《丁玲全集》第11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43页。
(48)[加拿大]刘敦仁:《哀丁玲》,中国丁玲研究会编《丁玲纪念集》,湖南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537页。
(49)尹骐:《丁玲在延安的“洗礼”》,《炎黄春秋》2004年12月。
(50)《致宋谋瑒》,《丁玲全集》第12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76页。
(53)比如以下说法:丁玲访美之行,作为一个“被看者”,她打造出了“政治化”的丁玲形象;作为一个看者,她有意拆解美国文明,以政治成见描绘出了她心目中的美国形象。(秦林芳:《政治视镜与国粹心态——从访美之行看晚年丁玲文化心理》,《江苏教育学院学报》第23卷第6期)丁玲到美国大讲她的北大荒经验是如何美好快乐,以致一些并无偏见的听众觉得矫情。(王蒙:《我心目中的丁玲》,《读书》1997年第2期)晚年的丁玲警惕着她的那些同样从苦难中走出来的宿怨们,她不断地写文章,表白自己对那个让她受尽磨难的时代的忠贞不渝,尤其是在她出国期间她非常谨慎地控制着自己的言行,始终给人一种与国家权力者保持一致的形象。(丁言昭:《丁玲传》,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65页)
(54)《一九八四年七月十四日中央组织部〈关于为丁玲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丁玲全集》第10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03页。
(55)(56)(57)(58)(59)王增如:《无奈的涅槃》,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版,第53页,第73页,第77页,第94-95页,第77页。
标签:丁玲论文; 北大荒论文; 周扬论文; 政治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国外工作论文; 作家论文; 体验生活论文; 右派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