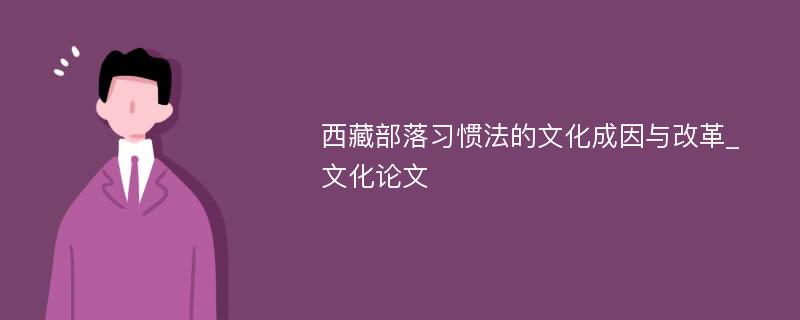
试论藏区部落习惯法的文化成因及其改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习惯法论文,成因论文,试论论文,藏区论文,部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文化,是与人类共生的现象,“是一种最富有弹性的社会要素系统”[①],就宏观而论,它可以大到与人类文明等量齐观;就微观而言,它可以小到一条规范、一种礼仪。我们所要讨论的藏区部落习惯法,其实也是一种文化,只不过它是大文化中的一个子系统。藏区部落习惯法的形成和发展,是与藏区部落整个社会大文化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它是在这种大文化圈内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具有鲜明特质,对人格转型产生无形影响的潜性文化的一种。因此,我们研究藏区部落习惯法,就应该把它放在整个藏区社会大文化圈内进行剖析和审视。
一、藏区部落社会的基本特征及其习惯法
藏族是我国世代繁衍于青藏高原的一个古老的民族,其先民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在这里谱写自己的历史。据史料所记,从远古时候起,藏族的先民就以血缘为纽带,组成大大小小的部落,散居于青藏高原,从事游牧和狩猎。并进行着改造自然,争取生存与发展的艰苦卓绝的斗争。那时,由于生产力水平极端低下,劳动产品的数量极为有限,从而社会的财富愈受限制,社会制度就愈是在较大程度上受血族关系的支配。”[②]而“亲属部落间的联盟,常因暂时的紧急需要而结成,随着这一需要的消失又随告解散。但在个别地方,最初本是亲属部落的一些部落从分散状态中又重新团结为永久的联盟,这样就跨出了形成民族(Nation)的第一步。”[③]旧时藏区部落的形成及其发展的历史,正是对这一马克思主义观点的注脚。在原始社会中晚期,藏族的先民们在创造自己的物质文明的同时,也创造了自己的精神文明。据藏文史书记载,赞普拉托托日年赞“以前凡27代,均以仲、德、苯三者司政。”[④]这就是说,藏族先民们在进入文明社会之前的文化,是以神话、传说、苯教为核心的“司政”文化。由此可以看出代表寓言、神话、故事的“仲”和代表谜语的“德”以及原始宗教苯教的“苯”三者,在当时的社会、政治活动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那么,这三者是怎样“司政”的呢?在松赞干布建立吐蕃王朝之前,藏族还没有文字,要把一些重大活动和事件记录下来,作为历史世世代代传播下去,唯一的方法就是凭籍人的大脑记忆,以经常给人讲述的方式传播开来,代代相袭,其中也包括人们改造自然、顺应自然的经验教训及其对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的直观解释,对“美好”未来的憧憬与向往等,这就是“仲”的主要内容;所谓以“仲”司政,就是以故事、寓言、神话的形式向人们讲述历史,从而达到借鉴和教育的目的,保障社会的稳定和正常的社会生产、生活的活动。“德”,就是谜语。即以谜语的形式对当时社会政治生活和自然现象中的一些问题,作出被当时的人们可以接受的解释和预测,如占卜等,以安定民心、稳定社会秩序。“苯”,就是苯教,是一种原名笃苯的原始宗教,其司政功能主要是“下方作镇压鬼怪,上方作供祀天神,中方作兴旺人家的法事而已。”[⑤]可见“仲”、“德”、“苯”三者司政是藏族原始部落社会的基本特征之一。这种司政的历史一直延续到了松赞干布建立吐蕃王朝,创制文字、制定法律的公元7世纪。
公元7世纪初,在西藏的山南雅隆河谷地区,悉补野家族崛起,以雅隆部落为基础,直向今拉萨河流域扩展。松赞干布逐步统一青藏高原,建立了吐蕃王朝,定都于今拉萨(罗娑),并开始确定行政区划,建立军事、政治管理机构,制定法律制度,并创制了文字。也就在这个时期,佛教才从印度大规模地传入吐蕃,并得到王室信奉,从而使佛教在与苯教的斗争中取得了胜利,于公元779年建成了吐蕃第一座正规的佛教寺院——桑耶寺。佛教在与苯教的斗争中,也从苯教中吸收了不少对自己有用的东西,这就形成了“仲”、“德”和吸收了苯教成分的佛教共同参与政事的社会格局,呈现出异彩缤纷的民族文化的独特内涵和社会特征。加之,在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下,山隔水阻,交通极为不便,信息十分闭塞,地方割据日烈,藏传佛教内部分化,教派纷争。这都是由于部落之间战争所分化组合的结果,成为部落习惯法形成和发展的社会基础和文化土壤。
从以上的叙述中,我们可以看出藏族社会的原始组织,也跟其他原始社会的氏族组织一样,都是以血缘为基础的人类社会的最初组织形式。这种组织形式虽然十分简陋和原始,但它毕竟是代表了一种社会权力的,这种社会权力代表着整个氏族社会的利益。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下,人们的行为在很大的程度上就受到自然的必然性支配,很少有人的自行选择的自由,必须无条件地遵守“仲”、“德”、“苯”所记述的解释和预测,无条件地遵守各种习惯和禁忌。这些习惯和禁忌是在“仲”、“德”、“苯”的长期传播和制约形成的传统的力量来维持的,还没有也不需要特殊的强制机关的执行和保障。但是,到了松赞干布建立吐蕃王朝,确定行政区划、推崇佛教、创立文字,生产力有了较大发展,社会分工和交换也陆续出现,导致了私有财产的迅速发展和阶级的剧烈分化。奴隶主和奴隶的阶级对立,加速了原始社会的氏族组织的解体,原始社会的那些习惯和禁忌也随之发生了变化,其中有的在现实生活中失去了存在意义,有的则还继续存在,甚至有了加强,但性质变了,带上了阶级的烙印。这就是说,它们已不再代表整个社会的意志和利益,而只是代表在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意志和利益。由此可知,藏区部落习惯法是由原始氏族社会的习惯和禁忌等衍生而来的,它们之间存在着历史的继承性。原始社会的习惯、禁忌等,为习惯法的产生提供了经验材料。正如恩格斯在《论住宅问题》一文中指出的:“在社会发展某个很早的阶段,产生了这样一种需要:把每天重复着的生产、分配和交换产品的行为用一个共同规则概括起来,设法使个人服从生产和交换的一般条件。这个规则概括起来,后来便成了法律。”[⑥]藏区部落习惯法尽管带有不可避免的原始性和落后性,已经远远不能适应现代藏区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甚至已经成为藏区社会发展的桎梏,但从藏区社会发展的历史全过程来看,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是起到了一定的积极的作用的。简而言之。就是起到了调整人们的社会生活和社会关系的作用,保证了社会关系中的统一的不可割裂的社会秩序,使个人行为服从于被经济决定的一切社会生活的一般条件,成为人们必须遵守的规范,保证了社会机制的运行,表明了藏区社会调整的质的飞跃。
二、社会大文化是产生部落习惯法的重要“土壤”
纵观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举凡法的产生不仅与阶级、阶级斗争有直接的联系,而且是一定的生产方式本身的需要,也是人类社会进入文明时代社会生活的复杂变化,特别是社会经济生活本身的客观要求。藏区部落习惯法就是在特定的藏区社会中社会经济生活本身的需要,并在这种特定的大文化土壤中孕育而产生的。法,作为一种文化,是在同其他文化结合在一起形成“大文化”而共同作用于社会的。这种大文化,“是人类行为的主要决定因素之一,文化同自然环境一起代表着塑造人类行为模式的两种主要的‘外部’来源进行交互作用,从而构成人类行为的基本决定因素。文化有内外两种表现,在外部,通过不同的社会机构和人工制品来表现;在内部,通过不同的价值观念、信仰系统、世界观和认识论来表现。所有这些力量同时进行交互作用,而个人在任何时候都是这些影响力的承受者和保留者。另一方面,由于它们可以通过生理和心理调整而内化,个人又成为它们特性的反射。”[⑦]而藏族社会及其民族心理特征就是在文化的内、外两种表现形式的交互作用下形成的,习惯法也是在这个特定的社会文化环境中孕育出来的。
如前所述,公元七世纪前后,青藏高原上处于各部落割据而治的状态,部落之间的战争此起彼伏,频繁不已,互不统属。后来,崛起于雅隆河谷地区的雅隆部落集团攻伐各部,松赞干布统一了青藏高原诸部,建立了吐蕃王朝,嗣后,又陆续建立了官职、行政、军事、法律等方面的一系列制度,应该说基本具备了与其社会形态相适应的国家形态。但它毕竟是脱胎于部落组织形式的,还保留着一定的原有社会形态的痕迹,当吐蕃王朝崩溃之后,在前后藏地区出现了地方割据势力的纷争局面,家族统治与农奴制领主庄园迅速发展而部落制度基本解体。但在藏北、青海、甘肃、四川等藏族地区,仍然保留着部落的组织形式,即使是到了元代及其以后的历代中央政权,在甘肃、青海、四川等藏族地区还都采取了封赐藏族部落首领官职,允许其代代世袭的制度,使部落组织形式得以保存,一直延续到建国初期和民主改革以前。
在社会结构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依然如故的情况下,藏传佛教又日益深入人心,特别是政教合一体制建立之后,佛教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发挥着更大的作用,“德”为适应新的社会需要也作了某些改变,而“仲”虽然走出了宫廷进入了民间,但由于部落组织依然存在,其作用也是不可低估的。部落习惯法正是在这种大文化圈内依然深深地潜入于社会心理之中,即使是进入到今天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仍然在某些方面无形有形地支配着人们的社会行为,产生着对群众生活模式的一定的规范作用。所以,我们在研究部落习惯法的时候,就应把它放在藏区大文化系统之中进行考察,分析它依附于大文化而又反作用于大文化的基本规律和特征。正如张友渔在为《青海藏区部落习惯法资料集》一书写的序中所说:“从文化结构上看,习惯法规范属于表层结构,民族心理素质则属深层结构。……这种心理,特别是其中的法律心理、法律观念,制约着部落习惯规范的形成,而部落习惯法规范反过来又影响着民族素质的提高与发展。”这种大文化系统对习惯法的形成和发展的制约推动作用,简而言之,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游牧业生产方式的文化模式是产生部落习惯法的主要社会基础。游牧业生产方式的主要特点就是逐水草而牧,牧民虽然都应在自己部落划定地界的范围内放牧,但部落之间夺地而牧的矛盾几乎代代相传,至今亦未得到彻底的解决,草山矛盾时有发生。同时,在游牧迁徙的过程中也易出现一些意想不到的困难和人为的骚扰,因此,就必须有一定的规约统一大家的行动,依靠群体力量保障迁徙途中的人畜安全。正如恩格斯说的:“在没有明确的和平条约的地方,部落与部落之间便存在着战争。”[⑧]为了对内实行有效的统治,对外进行兼并扩张,各个部落不但都有自己的武装,而且制定“军事法”,其中就有对付“外敌”的“降伏外敌法”等,明确规定凡为本部落的利益杀死了外部落的人,命价由本部落公众负担。以部落法的形式确定下来,旨在鼓励和培养着人们的尚武精神,增强部落意识。
2、家族和部落神权观念是习惯法的形成及其功能得到充分发挥的思想基础。部落一开始就是以血统关系为基础而形成的社会组织,并有一定的地域界限,不但家族观念有调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作用,而且都有自己的“地方保护神”。这从藏语地名中可以得到印证。地方保护神崇拜,反映了部落神权观念在人们的部落意识中的主导地位,所谓“地方保护神”,往往是将某个历史人物、某个先逝的部落首领和为捍卫部落利益而牺牲的“英雄”,或者是与部落的起源、祖先的宏基伟业的传说相联系的某个地方或雪山、峻岭的地貌特征、色彩特征等当作他们的亡灵显现的化身或神光而尊为“神灵”,世代崇拜、祭祀。这就是恩格斯说的“由于自然力被人格化,最初的神产生了。”这些神便拥有超自然的伟力,主宰着部落的一切。例如雄踞果洛北部的阿尼玛卿大雪山,藏族人民称之为“博卡瓦间贡”,认为是开天辟地九大造化神之一,专门掌管安多地区山河浮沉和沦桑之变,是藏族地区的救护神,所以当地藏族群众称之为“神山”;又如果洛东南部的年保叶什则山,亦被当地藏族人民称为“神山,相传是果洛藏族的发祥地。保护神的意志,其实质也就是部落统治者的意志,由统治者制定、颁行的习惯法,必然是部落统治者意志的集中体现。
3、藏传佛教的传播为习惯法的颁行创造了浓郁的文化、思想氛围。宗教是一种意识形态,它是一定的社会条件下的产物,没有一定的现实社会基础,就不会有这一种社会意识形态的存在。但是,宗教对客观世界的反映不是真实的,而是虚幻的、荒诞的。在阶级社会里,它被统治阶级用来麻痹劳动人民的斗志,向劳动人民灌输“前生注定今世”的思想,让劳动人民去追求一个什么虚无缥缈的“极乐世界”,使劳动人民成为精神上的被奴役者,而甘愿忍受、顺从他们的剥削、统治,放弃改革现实困苦环境的斗争;使劳动人民迷信“神”的力量而轻视自己的力量,加之,部落与寺院在“政教合一”的作用之下,相互利用、统为一体,部落为寺院提供物质需要,寺院是部落的精神依靠。这样,部落习惯法的产生和功能的发挥既有物质基础,又有精神支柱。“各种化学元素虽然是独立存在的,但它们一经化合,同一的元素会表现不同的作用。”[⑨]社会现象也同样如此。在藏区,部落、寺院、地方保护神、部落习惯法等相互依托,互为条件,形成合力,共生共振,发挥出维护藏区部落社会秩序和森严的等级制度的作用,严重地阻碍了藏区社会的发展与进步。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藏区部落习惯法的产生和实施,不但有其特定的社会制度和社会基础,而且与这种特定的社会文化结构、思想观念、社会心理也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在对待习惯法的问题上不能不看到这些方面的因素,绝不能用孤立的、静止的、简单的认识论的方法去对待这个问题,而应该历史地、辩证地去认识它产生的社会根源及其负面效应。只有这样,才能剔除其糟粕、吸收其对藏区社会发展有益的东西,并加以改造和消化,使之融于社会主义法制的科学体系之中,成为藏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积极因素。
三、改革习惯法必须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相协调
藏区社会制度随着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都先后跨入到社会主义社会的新时代,至今已有40多年的历史了。当我们回过头来回顾这40多年的历史,就会深切地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的“存在决定意识”,意识的发展又具有相对独立性或超前或滞后于社会存在的这一思想的深刻含义。美国学者奥格本曾经说过:“现代许多变迁都起源于物质文化,物质文化变迁又引起文化其他部分的变迁。……由于某些独特的力量和原因,非物质文化比物质文化变迁扩散得慢。因此在很多情况下都是物质文化变迁在先,所引起的其他变迁在后。有时,这种滞后引起的失调时间很长,成为重大的社会问题。”[⑩]这说明非物质文化尤其是人性、人格的变迁进步要相对滞后,新中国建立以后,党和政府对包括藏族地区在内的各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发展,经济、文化、教育、卫生等各项事业的建设都十分关心,给予了人力、物力、财力等各方面的始终一贯的大力支持,藏族地区跟其他民族地区一样,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和内地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藏族地区的落后,不言而喻,首先是经济的落后。藏区社会发展水平低于内地,主要是通过文化形式表现出来的。因此,我们说藏区社会文化的状况是藏区社会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也是衡量藏区社会进步水平的基本尺度之一。更值得注意的是“青海藏区部落习惯法的积淀和形成,是与青海藏区民族心理素质的形成相互影响、互为作用的。……统治阶级的法律心理在全民族心理中一直居于主导地位。”(11)这种表现为深层次的民族文化心理特质,正是部落习惯法及其某些旧制度、旧观念在现实生活中悄然复现的无形土壤。特别是在藏区几乎是全民信奉藏传佛教,藏传佛教在人们的心灵深处已根深蒂固,其影响是广泛而深远的,由此而形成藏区特殊的文化经济圈。这个文化经济圈内的一切领域都无不烙有藏传佛教的印记,给这里的政治、经济、文化以极大的影响和制约。“一个社会或民族的传统是由历史和心理文化的发展积淀而成的。这一积淀与社会发展似乎存在一种力学关系:积淀越沉厚,传统所形成的惯性就越大,改变它就越不容易。”(12)这些都说明了藏区习惯法存在有其深厚的文化土壤,要废除它或者改革它,都必须会受到这个由种种因素构成的合力的传统势力的抵抗和干扰。所以,在处理习惯法的问题上应该着眼于藏区社会的整体改革和经济发展、文化建设等的全局,不能孤立地、静止地看待习惯法问题。具体地讲,笔者认为应该抓住以下几点:
1、要历史地、辩证地看待习惯法。习惯法,也是一种法,它是建立在藏区封建部落制经济基础上的法律制度。今天的藏区已经是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人民当家做主的新社会,必须废除包括习惯法在内的一切旧制度,建立社会主义的法律体制和一切适应藏区社会发展的新制度,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是,从广泛的民族学意义上讲,习惯法也属于文化范畴。西汉刘向在《说苑指武》中说“圣人之治天下也,先文德而后武力。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致,然后加殊。”他说的“文化”,就是文治教化的意思。从这个意义上讲,习惯法尽管是“历代部落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是维护封建部落制度的法规,应该彻底改革和改造,但在当时维护封建部落社会秩序、保障社会安宁、处理民事纠纷等方面起到了一定积极作用,加之,这种习惯法与宗教观念、家族观念、部落意识、神权思想等掺杂在一起,深深地潜入于人的社会意识之中,如果企图以利爷砍木的简单方法去废除它是办不到的。就习惯法本身来说,我们应该用马列主义的法学观点对其“解剖”、审视,废除那些封建落后的、愚昧的、非社学的原始性东西,涤除那些带有宗教、神权色彩的成分,结合藏区的社会实际,根据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总要求,对其进行科学的鉴别和扬弃,把那些在今天的社会主义条件下有利于民族的进步、社会的发展的成分吸收到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中来,其法律效力才能得到充分的发挥,社会主义的行为规范、伦理道德也才能逐步建立和完善起来。所以,我们在民族地区的法制建设中,必须注意到民族地区的社会特点和民族特点。
2、习惯法的改革,必须与藏区的社会改革紧密地结合起来。如果把藏区社会比作一架机器,那么,习惯法就是这架机器上的一个部件,它和其他部件组合在一起,才造成了一架可运转的机器。当其他部件已经进行了革新和改造,唯独它还依然如故,甚至陈旧破损,这架机器的运转就会失灵,甚至发生故障;同样,其他部件原封不动,只对它进行了改革和改造,也同样会运转失灵,因为它们是一个有机整体,相互之间存在着彼此依存的互动关系。作为社会整体结构中的一部分的习惯法,产生于那个时代封建部落制的经济基础之上,就适应那个社会制度而发挥出应有的法律效力。到了社会主义的今天,藏区社会制度、经济基础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它不可能成为依附于这个社会制度及其经济基础的法律、法规,更不可能为新的社会制度和经济基础服务,因此,必须进行改革。但是,作为藏区社会的成员所获得的知识、信仰、艺术、法律、道德、习俗及其他能力与习惯的综合体的文化来说,它又产生和发展于这个特定的自然的、历史的和社会的环境之中,其传统功能不可能一下子适应新的社会制度和经济基础,也有一个“大文化”的推陈出新、改革、发展的问题。这种改革和发展,又必须是由藏区的历史的、社会、自然的等多种因素决定的,不可能超越这一文化产生和发展的条件。今天,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藏族地区也同全国各地一样,在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的指引下,改革开放,逐步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是,藏族地区的历史包袱依然十分沉重,传统文化中的那些陈旧过时,滞阻发展的陈规陋习、思想观念、传统意识还没有彻底消失,甚至有的还有所复活。在这样的社会环境和文化氛围中,改革习惯法,只有与藏区社会的整体改革相协调,才是唯一有效的途径。
3、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发展社会主义的文化教育事业,全方位地推进藏区的社会进步发展,是改革习惯法,建立社会主义民族法制的重要条件。我们所说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不是割断历史而凭空产生的,它应该是千百年来整个人类文明优秀成果的继承和发展。就藏区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来说,应该是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总方针指引下,与社会主义一定阶段的政治条件和经济生产条件相联系,以民族传统为基础,尊重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自身规律以及藏区社会的实际和民族特点,千万不可忽视藏族地区长期形成的社会物质条件和社会心理基础。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要从对民族文化的扬弃与继承开始,努力发展具有民族文化特点的现代民族教育。“一个时代的文化离不开它的思想,或者如现在人人常称的价值观念,它借以表现的社会生活方式和维护这一切政治体制。其中、政治体制往往是最集中、且显而易见的部分,其次是人们的生活方式,最抽象的是价值观念。”(13)在藏区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改变人们原有价值观念中的某些落后的,不协调的因素,而树立崭新的、具有民族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价值观念,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必须花大气力,因势利导,创造良好的社会文化氛围和健康的社会心理取向。这个任务就不言而喻地落到了发展社会主义的文化、教育事业上来了。
在发展民族教育事业上,我们要防止和克服那种把民族教育仅仅看成是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脱贫致富的手段,必须看到民族教育还具有培养民族认同感、民族自尊心、责任感和传承民族文化的功能。民族教育在承担培养“四有”人才的同时,还必须体现民族独特的文化,而民族文化又是个体社会化的基础,是“培养个体成为一个充满活力,具有健全人格的社会成员的基本条件。”(14)因此,在发展民族文化和民族教育事业上,必须着眼于现代化,使民族传统文化和民族教育朝着现代化的方向发展,以推动藏区社会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变革,从游牧经济走向现代化的畜牧业经济,实现社会的全面进步和发展,人的价值观念也就会在这种环境的潜移默化中发生质的飞跃。那时,习惯法也会随着它们存在的“土壤”的彻底消失而必然消亡,崭新的、完整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及其法律意识和观念,必将深深地扎根于广大藏族人民的心中,成为广大藏族人民唯一的法律准绳和履行公民权利和义务的法律保障。
4、努力发展藏区社会主义经济,是消除习惯法的影响,建立和完善具有民族地区的社会特点和民族特点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重要物质基础。民族地区的落后,首先是经济的落后。经济的落后导致了人的思想素质、文化素质及各项事业发展的滞后,而这一切都往往从包括法律、法规在内的文化方面表现出来。“一个有高度文化水平的民族,它必然是富裕兴旺的民族”(15)。从一个民族文化发展状况,就可以看出一个民族经济发展的水平和社会进步的程度。发展民族经济是改变文化落后状况的基础,没有经济的发展,就没有文化、科学的进步,两者互为因果,相辅相成;在注意经济发展的同时,不能忽视非经济因素的作用,特别是包括科学、教育、文学、艺术、医疗卫生、宗教信仰、风俗习惯、道德规范等因素的作用。这就是说,抓经济建设,也要抓精神文明建设。两手抓,两手都要硬。这样,藏区的经济发展才会有扎实的基础和保障。不能一抓经济,就忘记了抓精神文明建设,如果没有健康的社会氛围,旧思想,旧观念以及那些陈规陋习还依然十份浓厚,即使是经济发展上去了,也只能是一个畸形的、不健康的社会,其经济发展是不会有强大而持久的后劲的。正如邓小平同志说的“风气如果坏下去,经济搞成功了有什么意义?会在另一方面变质,反过来影响整个经济变质,……”(16)他的这段话虽然是指全国而言的,但对藏区的经济建设同样具有重大的现实指导意义。发展藏区经济,必须同文化建设、教育发展等各项事业相协调,决不能顾此失彼。只有在这种社会整体发展的总框架上去认识、鉴别、改造习惯法,吸收其中的某些有用成分,才会成为可能。
作为一种文化类型,藏区习惯法是藏区传统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由于它产生于封建部落制社会,并为其社会经济基础服务,它不可能适应今天的藏区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所以,必须依照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要求,进行改造和扬弃。作为一种文化,与其产生的社会制度及其社会结构有着密切的关系,社会结构决定文化,文化又作用于社会结构。要使藏区社会康健发展,必须使两者之间相互适应。但是,我们必须看到,包括习惯法在内的藏族传统文化中的一些成分已不适应藏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诸如宿命论、特权思想等价值观念、法律心理以及男尊女卑、官贵民贱等门阀等级观念和其他旧思想等,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要求是不协调的。尽管这些陈旧观念,落后意识已不占有社会意识的主导地位,是潜移在人们意识中的残留,但“观念变革则要受巨大的阻力和冲突的考验。”(17)对社会的负面效应是不可忽视的。一言以蔽之,习惯法的产生有其特定的社会基础和大文化土壤,改革与扬弃习惯法,必须同藏区文化变革相协调,要从藏区社会发展的整体构架上去分析,研究这个地区法律文化的历史发展过程。“对于那些维护封建部落制度的法规,必须屏弃;对于那些有利于促进民族团结进步,有利于繁荣民族地区经济文化事业的或无害的法规,予以吸收和保留,以便为加强这个地区的民族法制建设提供依据。”[①⑧]这才是唯一正确的态度和做法。
注释:
[①]叶南客《论现代人格的转型动力与转型机制》(载《社会学研究》1995第2期)
[②][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30、108页。
[④]《智者喜宴》(藏文)上册,民族出版社1986年版,第166页。
[⑤]刘立千《土观宗派源流》西藏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94页。
[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538—539页。
[⑦]〔美〕A·马赛拉等《文化与自我》江苏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第291—292页。
[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94页。
[⑨]〔日〕中村元《比较思想论》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39页。
[⑩]〔美〕W·E.奥格本《社会变迁——关于文化和先天的本质》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44页。
(11)(18)张友渔《青海藏区部落习惯法资料集·序》青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12)于敬尧等《走向富裕的探索——青海经济四人谈》第107页。
(13)赵复三《对现代西方文化某些方面的一些思考》(载《人民日报》1987年3月23日第5版)
(14)万明钢《民族教育研究中的文化问题》(载《教育研究》1993年第5期)
(15)陈定秀《民族文化进步与经济发展》(载《贵州民族研究》1992年第2期)
(16)《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54页。
(17)于胜利《“韩国病”的文化因素》(载《当代韩国》1994年秋季号,总第4期)
标签:文化论文; 藏族论文; 藏族的风俗习惯论文; 习惯法论文; 社会主义社会论文; 社会改革论文; 社会观念论文; 法律论文; 经济论文; 社会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