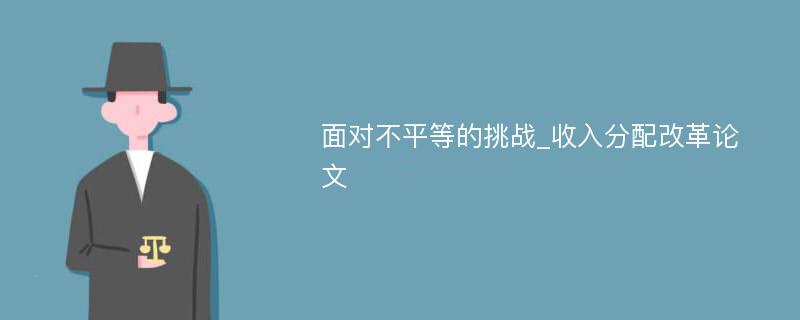
正视不平等的挑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不平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改革后的第一个10年,每个人都从飞速发展的经济中得到了实惠,不平等程度相对较低,公平问题没有提到日程上来。然而,从80年代后期起,改革所产生的经济政治社会后果开始引起人们的担忧。到了90年代中期,不公平现象越来越严重,其可能造成的社会和经济不稳定已经成为制定政策的重要问题,也成为学者们研究的对象。
一、日益扩大的不平等已形成严重挑战
最近,中国科学院国情研究室的胡鞍钢博士和我刚完成一本题为《不平衡发展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国个案》(The Political Economyof Uneven Development:The Case of China)的英文书。 该书集中研究了一种形式的不平等,即地区间的不平等。它讨论了中国各省之间存在的巨大差距,探讨了这些差距产生和变化的原因。对大量数据的分析,我们得出三个结论。
第一,省际之间的不平等正在扩大。在改革初的很短一个时期里,各地区经济发展一度曾比较平衡,出现人均GDP相对差距缩小情形。 但是,这种趋势很快就逆转了。沿海与内地的人均GDP从1983 年开始扩大,更严重的是,1990年以来这种差距扩大的趋势急剧加快(注:TheWorld Bank arrives in an essentially similar conclusion in its,Sharing Rising Incomes:Disparities in China (Washington DC,World Bank,1997).)。
第二,地区发展差距非常大。从我们所掌握的17个国家的资料看,中国的地区间不平等是最严重。
第三,地区不平等表现在方方面面。不管是看经济指标还是看社会指标, 地区差距都十分明显。 贫富省份之间的差距不仅仅表现在人均GDP上,也表现在社会经济发展的各个方面。 用联合国开发署的人文发展指标衡量,中国最富和最穷省分之间的差距几乎相当于西方发达国家与最贫穷国家之间的差距(注:UNDP,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1995,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5,pp.231.)。
新古典派经济学家预言,市场本身的运行,加上经济增长,能自然而然地导致地区间收入趋同。我们不同意这种观点。如果这一观点成立的话,中国自90年代以来的迅速市场化应已大大缩小了地区发展差距。然而,过去20多年的经验说明,寄希望于市场魔力只是一种幻想。生产要素的流动方向实际上往往与新古典经济学的预测恰恰相反。市场的力量不是使稀缺的资本和人才流向落后地区,而是将这些经济增长的必需的要素引向发达地区,因为这些地区是内外经济的集聚点。落后的地区仅有的优势(廉价劳动力)难以抵消这种集聚力的优势。结果,经济增长的大潮并没能使小船浮起来。尽管过去20年中国经济总量增长很快,但地区差距却在不断扩大。我们并不认为缩小地区差距是不可能的事。不过有一点是清楚的,即地区差距并不会自动缩小,市场并没有新古典经济学赋予它的那种神奇力量。
地区差距只是不平等在中国表现的一个方面。在地区差距扩大的同时,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注:世界银行发现中国的城乡差别非常大。其他国家城乡收入比一般在1.5以下,很少超过2.0。在中国,城市收入是农村收入的4倍。见World Bank,Sharing Rising Incoms,pp.7~8.),城市或乡村内部贫富家庭之间的收入差距(注:世界银行使用没有经过调整的数字得出以下结论:中国农村的吉尼系数从 1983年的 0.242提高到1995年的0.333,城市的吉尼系数从0.176提高到 0.275 。World Bank,Sharing Rising Incomes,p.17.Khan and Riskin对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字做了调整, 得出类似的结论。 根据他们研究的成果,1988到1995年城乡不平等急剧扩大。农村收入的吉尼系数从0.338 提高到0.416,在城市,该系数从0.23上升到0.33。 见 Azi zur Rahman Khan and Carl Riskin,Income and Inequality in Chin a :Composition,Distribution and Growth of Household Income,1988 to 1995,China Quarterly,No.154(June 1998),pp.236 and 241.)以及男女两性之间的收入差距(注: World Bank,Sharing rising Incomes,pp.38 — 41.其他有关中国不平等状况的最新研究包括,Keith Griffin and Zhao Renwei,eds.The Distribution of Income in China,New York:St.Martin's Press,1993; Terry Mckingley,The Distribution of Wealth in rural China,New
York, M. E .Sharpe,1996.)也在扩大。这些不平等是相互重叠又相互关联的。 地区间、人际间、城乡间的差距使当今的中国成为建国以来整体收入分配最不平等的时期(注:World Bank,Sharing Rising Incomes,p.7.;Khan and Riskin,Income and Inequality in China,p.246~247.)。80年代初,中国是个收入分配相当平均的社会,不平等水平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注:World Bank,China 2020:Development Challenges in the New Century,Washington,DC:World Bank,1997,p.8.)。到90年中期,中国的不平等程度虽然仍比大多数拉美国家和次撒哈拉非洲国家还低,但中国已没有任何骄傲的理由了(注: World Bank,Sharing Rising Incomes,p.2.)。因为哪怕是依据保守的估计,中国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已超过了多数过渡经济国家(前苏联和东欧国家)和西方发达国家。更让人担忧的是,中国的不平等程度已超过了不少亚洲发展中人口大国,如印度、巴基斯坦和印度尼西亚。这些国家以往都是发展经济学研究里认为收入分配非常不平等的国家,而中国的情况比它们还糟(注:World Bank,Sharing Rising Incomes,pp.1~2,7~8.)。
在80年代和90年代,世界上很多国家都在进行市场取向的改革。不平等的扩大似乎是个世界性的趋势。然而,在其他进行市场改革的国家,分配不公平的情况并没有像在中国那样恶化得如此之快。世界银行的研究表明,中国的整体不平等“是所有有资料国家中恶化最快的”(注:World Bank,Sharing Rising Incomes,pp.7~8.)。从历史的角度或比较角度来说,在这样短的时间内,一个十分平等的社会变成了一个相当不平等的社会, 这无论如何都是极不正常的(注: WorldBank ,Sharing Rising Incomes,p.8.)。展望未来,如果对这种两极分化的趋势不加以制止,中国社会很快就会像拉丁美洲和次撒哈拉非洲国家那样成为世界上最不平等的国家之一。
这是不是一种应引起中国的决策者高度重视的不祥之兆呢?答案是不言而喻的。如果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仍是中国政府追求的目标,如果稳定和发展仍是一切工作的中心,中国政府就应该谨慎地处理分配不公平的问题。任何社会都会有差别存在,一定程度的不平等是难以避免的。但是,如果不公平超过了一定限度,就会对社会经济发展造成政治上的威胁。尤其对中国而言更是如此,因为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其政府的合法性是建筑在平等原则基础之上的。它没有理由容忍不平等无休无止地发展下去。大多数中国人都认为不平等在道义上是说不过去的。政府也许可以说服他们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以求最后达到共同富裕。但是,如果伴随着改革与发展的是不断扩大的不平等,人们无法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贫富差距就会变得让人难以接受,政府的道义基础就会削弱,它的合法性就会遭到怀疑。
在中国,不少人相信不平等有利于经济增长。然而对其他国家的历史研究和比较研究表明,这种想法毫无事实根据。实际上,很多最新的研究都表明,分配不公往往导致经济增长速度的停滞不前(注:World Bank,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1991,Washington,DC:World Bank,1991;A.Alesina and D.Rodrik,Distribution,Political Conflict and Economic Growth,in A.Cukierman,Z. Hercowitz and L.Leiderman,eds.Political Economy,Growth and Business Cycles ,Cambridge:MIT Press,1992,pp.23~50;T.Persson and G.Tabellini,Is Inequality Harmful for Growth,American Econmic Review,Vol.84,pp.600~621;Roberto Pertotti,Growth,Income Distribution,and Democracy:What the Data Say,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Vol.1(June 1996),pp.149~187;United Nations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Income Distribution,Capital Accumulation,and Growth,Challenge,Vol.41,No.2(March/April 1998),pp.61~80.)。更为严重的是,如果只有少数地区、 少数人口和少数阶层能从市场转型和经济增长中获利的话,人们对不平等的忍耐力就会降低,不满情绪迟早要爆发。其他国家的经验表明,没有任何政府能在经济极端不平等的条件下维持政治稳定。中国自身的历史也充满由经济不平等所引发的起义、造反和革命。社会紧张局势和不稳定显然不利于经济增长。中国越来越严重的不平等有可能使经由20年市场改革和经济增长形成的大好局面毁之一旦。
这里,让我们特别谈一下地区差距可能带来的政治后果。地区间收入上的不平等说到底是个资源分配问题,而任何资源分配问题说到底都是个政治问题。地区差距常常引发地区冲突,并由此破坏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这是因为,一方面,日益扩大的地区差距容易使生活在低收入地区的人民产生失落感。他们往往认为,本地区状况得不到改善的原因是中央政府对他们缺乏必要的同情。另一方面,发达地区则认为,中央政府采取的任何再分配政策都意味着削减它们对本地区资源的控制。在它们看来,向落后地区倾斜的政策对自己是不公正的。每个地区都希望政策的改变有利于本地区的利益。由于发达地区在经济发展中占据主导地位,在与中央政府或其他地区打交道时,它们往往在政治上具有更大的发言权。这样,中央政府很可能沦为富裕地区的俘虏,变成维护它们利益的工具,使区域不平等永久化。如果出现这样的局面,就会激怒贫困地区,使它们产生追求独立发展的想法,以便更好地维护自己的利益。而那些位于边界,与世界经济打交道多于与本国经济打交道的富裕地区也可能产生分离倾向。尤其是当这些地区在民族、宗教或语言等方面与国内其他地区存在着文化差异的情况下,分裂局面更容易产生。这种先例很多,诸如印度的旁遮普邦,前南斯拉夫的斯洛文尼亚,前苏联的立陶宛、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布干维尔,意大利的伦巴第,扎伊尔的加丹加,以及尼日利亚的比亚佛拉。这些地区都是本国收入水平最高的。它们都认为从母国分离出来是摆脱穷亲戚的一个好办法(注:Milica Zarkovic Bookman,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Discontinuous Development:Regional Disparities andInter-Regional Conflict,New York,Praeger,1991,pp.2 and 27~33.)。
在这里谈别国的教训并不是说中国也已经到了民族瓦解的边缘。中国目前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这种局面会在中国重演。但俗话说得好,不怕一万,就怕万一。我们认为,哪怕地区冲突的可能性只有千分之一,中国领导人也不应掉以轻心。相反,他们须竭尽全力避免最坏的情况发生, 以百分之百的努力去防止这种可能性转变为现实(注: Yasheng
Huang,Why China Will Not Collapse,Foreign Policy,No.99(Summer,1995),54~68.)。
综上所述,日益扩大的不平等不仅在道义上说不过去,还可能蕴含着经济停滞,政治动荡,国家分裂的危险。对如此重大的问题,凡是关心中国前途的人都应予以充分的重视。目前中国的不平等程度已相当严重,采取措施缩小不平等的时机已经成熟,它应当成为今后中国发展任务的重中之重。
二、不平等不是不可避免的
现在很少人否认中国存在不平等(注:有一项研究发现了地区间的趋同与市场化和开放程度有很强的相关性,而中国正处在趋同过程之中。见See Tiannlun Jian,Jeffrey D.Sachs,and Andrew M.Warner,Trends in Regional Inequality in China,China Economic Review,Vol.7,No.1(1996).)。争论的焦点在于是否应当解决和如何解决地区差距问题。有些人认为在中国改革和发展过程中出现不平等是不可避免的。在他们看来,由于自然资源分布很不均匀,由于市场经济强调能者多得,由于现代经济的发展不平衡,某些个人、社会集团和地区比其他人、社会团体和地区先富裕起来是很自然的。这是“自然力”或“经济内部规律”所造成的。政府出面干预,人为地缩小差距是错误的,因为它会破坏改革和发展的自然进程(注:胡大源:《转轨经济中的地区差距——对“地区差距扩大论”的质疑》,《战略与管理》,1998年,第1期,第35~41页。)。
我们不能同意这种观点。这种观点不仅在道义上站不住脚,而且没有实证基础。从国内外近几年的研究成果中,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1.不平等也许是难以避免的,但是,坐视不平等任意扩大是不正常的
以地区差距为例,地区发展水平的确与自然环境有很大关系。在中国,各地区间的差别非常大。那些落后的省份,地形复杂,可耕地少,气候干燥、寒冷,远离城市和国际市场,基础设施差,人口教育水平低,缺少技术和管理人才。这一切都加大了落后地区的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使他们在与其他地区竞争中处于极为不利地位。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地区间收入差距是自然条件造成的,是不可避免的。
然而,这些因素却无法说明地区差距的变化。自然条件在短期内不会发生很大变化的,但是,地区间的不平等程度却可能在短期内发生巨大的变化。我们的研究发现,改革初期,地区差距有所缩小;但从80年代中期起,差距开始扩大;到了90年代,地区差距开始急剧扩大。很明显,这些变化仅用自然条件是难以说明的。应该说,这种不平等程度的变化与政府行为(即采取某些政策或不采取某些政策)有直接关系。
不管怎么说,不平等的加剧决不是命中注定的。如果说不平等的程度在过去可以朝某一个方向变化的话,它也应能在将来朝另一个方向转变。这将取决于政府采取什么样的公共政策。
2.不平等的扩大在市场转型中不是不可避免的
在中国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收入分配的不平等扩大了。但是,这并不意味不平等的扩大是不可避免的。至少不平等扩大的程度并非一定要像在中国那样大。80年代和90年代,许多国家都在尝试改革自己的经济体制。然而,没有一个国家在转型期内出现像中国那样急剧扩大的不平等。有的国家甚至还缩小了不平等(注: World Bank,Sharing Rising Incomes,p.8.)。这说明市场转型不一定非以不平等为代价不可。
在世界上,没有两种市场经济是完全相同的。并不存在某种可以被称之为“自然的”市场经济的市场经济。所有现存的市场经济都有其特定的社会基础,与特定政治体制相搭配(注: Claude,S. Fischer,Michael Hout,Martin Sanchez Jankowski,Samual R.Lucas,Ann Swidler,Kim Voss,Inequality by Design:Cracking the Bell Curve Myth,Princeton:Princetaon University Press,1996,pp.129~157.)。也就是说,市场经济实际上可以与不同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制度相结合(注:Amartya Sen,Social Commitment and Democracy:The Demands of Equity and Financial Conservatism,in Paul Barker,ed.Living as Equal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p.19.)。市场与其他体制的不同搭配, 会对不同社会集团的利益产生巨大影响:一种制度安排下的赢者在另一种制度安排下很可能变成输者,而这两种制度都可称为市场经济。放眼世界,我们可以发现,有些市场经济国家的收入分配比较平等,那儿的人们或多或少都是市场经济的受益者。而另一些市场经济国家的收入分配却极度不平等,在造就一批市场英雄的同时,
也造成了更大一批市场的受害者(注:Victor Nee,Raymond V.Liedka,Markets and Inequality in the Transition from State Socialism,in Manus I.Midlarsky,ed.Inequality,Democracy,and Economic Development,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7,pp.202~224.)。从比较的角度看问题,我们就能清楚地了解到,中国不平等的扩大并不是市场转型的必然产物。要解释不平等的恶化,我们必须从制度安排上和公共政策上寻找原因。认识到这一点,人们就会了解,我们呼吁正视不平等问题并不是为了否认市场导向的改革。恰恰相反,我们希望找到一条能够避免过大差距出现的市场改革之路。
3.不平等的扩大不是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
有些人认为,不平等的扩大是中国为经济快速增长所必须付出的代价。他们认为,在效率和平等之间存在一种损益关系(trade-off), 要想提高效率,就要在一定程度上牺牲平等。如果为了争取更大程度的平等而调整资源配置和分配方式,有可能会损害中国经济的增长潜力,从而降低整体经济的收入水平。他们相信,这样做对谁都不利,包括低收入阶层。
然而,最近有多项研究发现,效率和平等之间的冲突并不是不可避免的。只有当将两者推向极端时,这两个概念才是相互对立的。否则,追求平等并不一定与提高生产力相矛盾。这两个概念到底是相容还是相斥取决于具体的制度安排。通过制度变革和政策调整,有可能形成这样一种局面:即在缩小不平等的同时,还可能提高经济的总体效率(注:Gary S.Field,Poverty,Inequality,and Development,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0;Samuel Bowles and HerbertGintis,Efficient Redistribution:New Rules for Markets,States and Communities,Politics and Society,Vol.24,No.4(December 1996),pp.3070342;Joseph Stiglitze,Distribution,Effoiciency and Voince:Designing the Second Generation of Reforms,manuscript,World Bank,1998.)。
如果说平等不一定妨碍经济增长,不平等则很可能妨碍经济增长。许多实证性研究发现,不平等与经济增长呈负相关。不平等程度高的国家往往经济增长比不平等程度低的国家要来得慢(注: Torsten Persson and Guido Tabellini,Is Inequality Harmful for Growth,American Economic Review,Vol.84(1994),pp.600~21;Roberto Chang,Income Inequality and Economic Growth;Evidence and Recent Theories,Economic Review(Federal Reserve Bank of Atlanta),Vol.79(July/August 1994),pp.1~10;Alberto Alesina and Dani Rodrik,Distributive Politics and Economic Growth,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Vol.109(1994),pp.465~490; George R.G.Clarke,More Evidence on Income Distribution and Growth,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Vol.47,1995,pp.403~427.)。
中国有必要为争取经济高增长而牺牲平等吗?答案是否定的。如果平等并不一定拖经济发展的后腿,如果不平等有可能阻碍经济增长,那么,中国就没有必要在增长和平等之间作痛快的选择。可以兼而有之,何乐而不为呢?
4.政府政策偏好的重要性
如果自然条件、市场过渡和经济增长都不是造成不平等的扩大根本原因的话,那么到底什么才是根本原因呢?我们认为,中国近20年来出现的不平等在很大程度上可能是有意造成的,这就涉及到政府的政策偏好。
20年前开始的改革,标志着中国发展的指导思想发生了根本的变化。邓小平的名言“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便是这种变化的反映。这显然背离了毛泽东的平均主义思想。由于指导思想的转变,中国领导人不太愿意以牺牲经济增长为代价去追求收入分配的平等。恰恰相反,为了追求尽可能快的经济增长,他们宁可容忍收入差距的扩大。社会主义的平等思想被抛到九霄云外,至少在短期内是如此。中国领导人似乎相信,随着经济的增长,全体人民或大多数人都会在中长期内“自动地”富裕起来。
从80年代初到90年代初,中国政府和知识界很少注意收入分配的公正性。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们甚至抱怨中国的收入分配太平均了,并为此刻意扩大分配的差距,希望藉此调动方方面面的积极性。例如,在区域发展问题上,中国采取了优先发展沿海地区的战略,把投资重点从内地转移到沿海。此外,还为沿海地区提供了其他地区无法分享的种种优惠政策。这些作法对自然条件本来就有利的沿海地区是锦上添花。与此同时,对落后地区的雪中送炭却被忽视了。沿海地区经济快速发展加深了它们与内地之间业已存在的鸿沟。从这一点看,地区差距的不断扩大从一开始就是人为造成的。
承认造成的80年代不平等扩大的人为原因比用自然条件解释不平等的扩大更有说服力。另外,认识到这一点也为我们争取缩小不平等增强了信心,因为这说明,只要我们调整政府的偏好,采取更加开明的政策,就可以避免两极分化,同时又不牺牲经济增长(注:Khan and Riskin,Income and Inequality in China,p.253.)。
5.国家能力的重要性
政府承诺保持分配公正是缩小收入差距的必要条件,但是,光靠承诺是不够的。要想达到这个目标,政府必须有能力动员必要的社会资源。没有足够的财政资源作后盾,政府连基本运作都谈不上,遑论达到其政策目标(注: Margaret Levi,Of Rule and Revenue,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8.)。一般而言, 财政汲取能力强的政府比财政汲取能力弱的政府更能实现其政策目标。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在收入分配方面,政府财政汲取能力至关重要。
我们在自己的研究中探讨了中国中央政府财政汲取能力变化的趋势,并检验了它对地区差距的影响。改革前,中央政府在资源分配方面起着关键作用。那时,它可以从发达省份大量汲取财政资源向落后省份转移。然而,1978年以后,随着财政权力的下放,中央政府的财政汲取能力大大下降。从1980年到1993年,在财政包干体制下,各省的财政收入主要看自己动员,各省的财政支出主要由自己支配。结果,中央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迅速下降。到90年代初, 这一比重已低于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在财政极度紧张的情况下,中央政府已经不能在全国范围内重新分配资源(注: Shaoguang Wang,The Institutional
Roots
of Central—Local Rivalry:China,1980~1996,a paper presetned at Internation al Conference on"PRC Tomorrow",National Sun Yat-sen University,Kaohsiung,Taiwan,June 8~9,1996.)。 中央政府进行再分配能力大大削弱的一个后果便是日益扩大的地区差距。显然,即使中央政府有缩小差距的意愿,如果它的财政汲取能力太弱的话,是难以实现自己政策意图的。只有当政府既有意愿又有能力时,均衡增长的目标才有可能实现。
三、政策目标选择
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对越来越不平等的事实不能熟视无睹。社会主义制度是一个追求平等的制度。前苏联和东欧共产主义制度崩溃之后,许多人再一次宣布社会主义已经死亡。然而,在当今世界上,社会主义者所谴责的种种不平等依然存在,人的基本生存权利被剥夺的现象依然存在。这样,消除不平等仍是人类社会面临的严重挑战,追求社会公正仍是大多数人的美好愿望。阿玛蒂亚·孙说得好,“虽然现实的社会主义制度存在着种种经济和政治弊端,但是社会主义所追求的目标仍然像半个世纪以前一样吸引着人们。
”(注:
Sen, Social Commitment and Democracy,p.17.)对中国来说,尤其是如此, 因为中国政府仍然宣称自己坚持的是社会主义原则。如果中国政府不把追求平等当作自己的优先目标,社会主义制度又怎么能体现出其优越性呢?
我们追求平等,首先就要知道怎么才算平等?平等可以有四种不同的标准(注: Douglas Rae,Equalities,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9,pp.110~112.):(1 )极小极大化标准(the minimax criterion),即减少最富群体的收入, 使之与一般人一样。(2)极大极小化标准(the maximin criterion),即尽量提高最穷群体的收入。(3)比例标准(the ratio criterion),即缩小贫富之间的相对差距。 (4 )最小差距标准(the
least
differencecriterion),即缩小贫富之间的绝对差距。
哪一个标准最适合中国呢?让我们以地区差距为例来讨论一下。首先,我们不主张极小极大化标准。在追求平等时,不要忘记平等不是社会关心的唯一价值。效率也是人类社会追求的目标之一。平等和效率并不是不相容的。但是走极端的话,两者的确会产生互相冲突。正如道格拉斯·瑞所指出的,极小极大标准是“平均主义的利剑”(注:Douglas Rae,Equalities,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9,pp.112.)。将富裕地区的生活水平拉到贫困地区的水平,可能会牺牲整体福利,同时也导致落后地区的利益受损。更重要的是,即使我们采取了刻意降低发达地区生活水平的政策,只能取得平均的效果,却无助于减少贫困地区的苦难。
极大极小标准要求将注意力集中于改善贫困地区的状况。遵循这个原则,就必须改变资源分配方式,向最贫困地区倾斜。在制定区域政策时,政府当然应当考虑最贫困地区的利益,并尽量设法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极大极小标准则是非常虚弱的平等。一个国家可以满足这一标准,而让贫富之间的差距任意扩大。因此严肃对待不平等,政府都应当把极大极小原则当作自己的最低目标,而继续努力缩小相对不平等和绝对不平等。
比例标准也不尽如人意。因为在贫富之间相对差距下降的同时,绝对差距可以继续扩大。如从6∶2变为10∶5,用相对标准衡量, 后者的差距小于前者的差距(2倍而不是3倍);但用绝对标准看,后者的差距比前者要大(5而不是4)。相对差距只是在作统计的人看来有意义。在人们日常生活中,最重要的还是绝对差距。因此,追求平等最理想的目标是在缩小相对差距(比例标准)的同时,消除绝对不平等(最小差距标准)。仅仅缩小相对差距只是次优选择。然而,政策建议不应只考虑什么是最理想的,还必须考虑什么是可行的。既然不平等是长期以来形成的现象,我们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将它彻底消除。采取激进的政策也许可以强迫达到绝对平等,但其代价却可能是大多数人不愿承担的。因此,中国的政策目标应定为:在短时期内,首先阻止不平等的继续扩大;在中长期,努力缩小相对差距。消除绝对不平等只能作为我们的最终目标。对这个最终目标,我们只能不断地逼近,却永远无法达到。
用上述观点来分析地区发展问题,我们认为中国的地区发展政策不应当限制富裕省份的发展,而应设法帮助贫困地区发展经济,提高增长速度。只有这样,才能防止地区差距进一步扩大,使贫困地区有机会赶超上富裕地区。对富裕地区而言,政府所需要做的就是取消沿海地区的优惠政策。这些地区具有自然资源,地理位置,基础设施和人力资本等诸多方面的优势。即使无优惠政策,它们也能快速发展。以往中国地区发展战略向沿海倾斜实际上是极大极大原则(maximizing the maximum)。这是最不公平的原则,违反了所有关于平等的标准。这种倾斜使贫富地区差距人为地更扩大了。取消这种倾斜政策有利于缩小地区不平等,但并不会损害富裕地区自身的增长潜力。
四、正确处理三大关系
要创造一个能保证实现以上政策目标的制度环境,中国政府必须正确处理以下三大关系:
1.市场机制和政府干预的关系
近十几年来,在新古典经济学的影响下,政府干预好象成了一种罪恶。即使是用政府干预来促进平等也变得好像名不正言不顺,似乎只有市场才是解决一切问题(不会不平等问题)的正常途径。在中国,有许多人相信,尽管地区差距现在扩大了,只要允许市场自由运作,资本会从发达地区自动流向落后地区,廉价劳动力会从落后地区自动流向先进地区,其结果是发达地区增长速度放缓,而落后地区增长速度加快。因此,缩小地区差距只是个时间问题,市场机制足以应付,不必由政府代劳。那么,为什么近来地区差距呈扩大趋势呢?据说这是因为现在市场化还不够充分,生产要素还不能完全自由流动。这些人相信,如果中国进一步减弱政府的作用,财富就自然而然地由富裕地区向贫困地区流动。
这种对市场的迷信对一个急需解决地区不平等问题的国家来说是非常有害的。市场可能会带来很多非常美好的东西,但是按照社会公正的原则分配资源却根本不是市场的功能(注:王绍光:《市场经济转型中国家的作用》,《战略与管理》,1994年,第2期。)。 无数研究成果表明,市场本身如不加以限制只能扩大地区的不平等,而不会自动的缩小不平等。即使我们退一万步,接受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假设,相信市场的力量最终将缩小地区差别,这种结果也不会在短期内出现,恐怕需要等几十年,甚至几百年。这使人不由自主想到凯恩斯那句名言:“从长远观点看,我们都是要死的。”如果不平等的扩大还要持续几十年或上百年,在此期间,各地区之间的巨大鸿沟将会导致严重的社会和政治冲突。在不稳定环境下,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包括革命和国家分裂。正是出于这种考虑,没有任何国家会放手让市场来决定地区的发展。
自从民族国家出现以来,政府就竭力制止地区不平等的扩大。在北美和西欧国家,政府往往制定种种政策来抵消市场所造成的“倒流效应”(backwash effects),支持市场产生的扩散效应(spread effects)。如果说在现代发达国家中地区发展是比较平衡的话,这并不是由市场的自然力造成的,
而是由政府干预市场所创造出的一种平衡(注:Gunnar Myrdal,Economic Theory and Under- Developed Regions,London:Gerald Buckworth,1957.)。在第三世界国家,政府在区域发展中进行干预也是司空见惯的(注: AlbertoHirschman, The Strateg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58,pp.183~195.)。
这里最重要的一点是,政府在促进地区均衡发展时进行必要干预是不可避免的。为了缩小地区差距,中国政府应当积极地执行均衡发展战略,不要被某些经济理论所迷惑,不要期待市场创造奇迹。
2.中央和地方的关系
过去十几年,世界上除了流行对市场的迷信外,还流行对分权的迷信。人们往往怀疑中央政府的运作效率,却相信向地方政府放权是解决各类问题的灵丹妙药。现在,几乎没有一个国家不谈论权力下放,既包括美国这种联邦制国家,也包括法国那样的传统单一制国家。在这股世界潮流中,中国也许走在了最前列。它的放权的水平比任何其他国家都高。的确,有不少政府职能最好是由地方政府来承担。但是,在人们对分权的好处津津乐道的同时,却往往忘了有些政府职能必须由中央政府来执行(注:王绍光:分权的底线》,计划出版社,1997年。)。区域发展就是一个例子。区域发展政策涉及到各地区的切身利益。如果允许每个省制定自己的地区发展计划,又没有中央政府协调的话,唯一可能的结果是,这些分散的计划互不衔接,互相矛盾,甚至以邻为壑。在这种情况下,地区发展不可能是平衡的。只有中央政府才有意愿和能力为实现平衡发展而在全国范围内进行资源再分配。
我们并不是说省政府在地区发展中完全不能起作用。在各省范围内,省政府就是那里的“中央政府”,它们应承担起缩小本省内部地区差距的任务来。另外,中央政府的区域政策也要求省一级政府配合执行。在有些情况下,中央政府只须负责资金的再分配,至于各省具体任何达到预定的目标,可让它们灵活执行。中央应允许和鼓励各省在执行中央决策过程中发挥自主性和创新精神。
3.政策变化和制度变化的关系
面对不断扩大的地区差距,中国政府当然应当改变被扭曲了的地区发展政策。若说过去的优先发展沿海战略造成了今天这样巨大的不平等,很明显我们需要制定另一套政策来改变这种状况。下面我们将提出一些具体政策建议。然而,光在政策上纠偏是不够的。仅仅将不平衡发展战略改变为平衡发展战略,并不能保证被扭转的政策不会被再扭转回去,也难以保证新政策能够得到贯彻实施。因此,缩小地区差距,不仅要着眼于对政策进行必要调整,而且要创造一种制度环境,使区域平衡发展的政策不会再遭逆转,使新政策的实施有坚实的制度保障。这就需要对涉及政策制定和实施的现有制度安排加以检讨并进行改革。
解决地区差距问题的前提是有一个能对经济进行有效干预的中央政府。如果中央政府财政非常紧张,无法运用诸如财政转移支付之类的政策工具,区域政策就不可能得到有效的执行。在中国,中央政府财政汲取能力下降就是地区差距急剧扩大的重要原因(注:胡鞍钢、王绍光、康晓光:《中国地区差距报告》,辽宁人民出版社, 1995 年; Mark Selden,China's Rural Welfare
Systems: Crisis
and Transformation,a paper presented at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PRC Political Economy:Prospects Under the Ninth Five-Year Plan,",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Taiwanm June 7~10,1997;Loraine A.West and Christine P.W,.Wong,Fiscal Decentralization and Growing Regional Disparities in RuralChina:Some Evidence in the Provision of Social Services,Oxford Review of Eocnomic Policy,Vol.11.No.4(1995).)。因此, 如果中国中央政府希望在全国范围内实现均衡发展,它就必须改变目前过度分权的财政制度, 以增加自身财政汲取的能力(注:王绍光,China's 1994 Fiscal Reform:An Initial Assessment
AsianSurvey,(September ,1997).)。
一个干预能力很强的政府可以有效地执行各种政策,包括那些加大地区差距的政策。因此,有必要创造一个制度环境,使中央决策不再向发达地区倾斜。这就需要各省,不管其发展程度如何,在中央决策过程中都享有同样的参与权和发言权。正如前文讲的,80年代,在中央的决策过程中,富裕省份的要求通常比贫困省份的要求更有分量。这是因为,当时中央决策采取了一种十分特殊的方式,即中央政府与各省一对一的单独谈判。这种形式容易使经济发达省份凭借自己在国民经济的地位与中央大胆讨价还价。而贫困省却没有本钱做到这一点。因此,在这个时期, 发达省份的利益在中央决策中得到了特别的关照(注:王绍光, The Institutional Sources of Central-Local Rivalry:1980~1993,"manuscript,Yale University,1996.)。
很显然,各省都有自己的特殊利益。为了实现地区均衡发展,中央政府应当平衡它们之间相互冲突的要求,而不是偏袒那一方。这就要求在中央决策过程中,代表各种不同利益的呼声都要能被听见(注:Sen,Social Commitment and Democracy,pp.21~22.)。 只有当所有省份都有参与决策的平等机会时,中央政府才能有效地抵制来自经济实力强大省份的压力。此外,倾听各种不同的声音,将决策过程透明化,还能促使中央政府在制定公共政策时采取更加负责的态度,避免政策的失误或政策的大起大伏(注:Joseph Stiglitz,Distribution,Efficiency and Voince.)。
五、采取六种必要的行动
如果地区差距(或其他形式的不平等)扩大不是必然的,而是倾斜政策和政府能力下降的结果,那么,均衡发展就不仅仅是一个理想的目标,而且是可以达到的目标。怎么才能防止地区差距进一步扩大并进而逐步缩小地区差距呢?我们提出六项政策建议。
1.取消向沿海地区倾斜的优惠政策
向沿海地区倾斜政策是建筑在所谓“梯度发展理论”基础之上的。这种理论在道义上比臭名昭著的“下渗理论”(trickle-down theory)更糟糕。下渗理论只是反对中央政府为了落后地区的利益进行干预,而梯度理论则主张中央政府应站在发达地区的立场进行干预。据梯度理论的鼓吹者说,为了争取经济总量的尽快增长,政府应当有意识地将各种资源集中在发达地区,使它们成为经济增长的火车头。
如果不改变这种向沿海富裕省份的倾斜政策,内陆省份就永远没有机会赶上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优越得多的沿海地区。
2.重建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制度
前面讲到,中央政府没有调动资源的能力是贫困省份落后于富裕省份的重要原因。因此,要缩小省际之间在收入和增长方面的差距,就必须努力缩小省际之间在资源上的差距。财政转移支付是各国用来缩小地区差距的主要形式。从建国到改革前,中国也曾采取过这种办法,并取得一定的成功(注:Nicholas R.Lardy,Regional Growth and Income Distribution in China,in Robert F.Dernberger,eds,China's Development Experience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0.)。改革以来, 这种办法几乎弃置不用了。由于过度放权,各省在财政上变得高度自治。随着发达省份对中央财政的贡献越来越小,中央政府能掌握和调配的资源也越来越少。中央的那点财政收入应付自身的开支尚嫌不足,哪有多少资源可供用于财政转移支付?地区差距于是变得越来越大。
为了缩小各省在收入水平和增长潜力方面的差距,中央政府必须下决心重建中国的财政分配体制,提高自己财政汲取能力,以便在重新分配资源方面发挥更大作用。只有中央政府才能够从富裕地区汲取资源向贫困地区转移;只有中央财政的调整,才能实现均衡发展的目标。
3.消除贫困
每个社会成员都有权享受健康、长寿和体面的生活。然而,贫困却剥夺了一些人的这些基本权利。贫困不仅使他们得不到最低生活保障,还剥夺了他们作为人应有的尊严(注: UNDP,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1997,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7,pp.15~23.)。因此,每个政府都应承担起最大限度地消除贫困的责任(注:UNDP,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1997,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7,pp.6~7.)。
解放以来,中国政府在消除贫困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在过去20年里,大约有两亿人口摆脱了绝对贫困。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有这么多人脱贫,这在人类历史上是一个空前绝后的奇迹。然而,中国还没有资格自满,因为到1998年,仍有5000万人挣扎在贫困线之下。这里的贫困标准是中国自己的标准。如果采取国际上通用的贫困标准(即按1985年购买力平价美元计算,人均生活费不足1美元),中国则仍有近1.5亿贫困人口,占人口的12.5%(注:World Bank,Sharing Rising Incomes,p.4.)。中国政府必须把消除贫困作为国家的优先政策目标。
贫困在中国并不只是地区现象。即使在沿海地区,如广东、河北、江苏和海南,也有不少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不过,贫困现象在西部和中部的内陆省比沿海省份要普遍得多(注:UNDP,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1997,p.23.)。因此,在制定扶贫政策时,中国政府应当特别注意贫困地区里的最贫困人口。在财政转移支付时,应当拨专款救济那些因不平等增长所造成的最贫困人口(注:中国有 592 的贫困县 (以1992年人均收入水平)。这些贫困县是中央政府协调的扶贫计划的主要对象。)。
4.保证最低水平的基本公共服务
在中国,落后地区不仅仅人均收入低,而且各项公共服务也最差。中央政府有义务保证向每个公民提供最低水平的基本公共服务。这就要求通过转移支付使所有地区都具备提供最低基本公共服务的财政能力。
基础教育和卫生保健是最重要的公共服务。这类服务可以从两个方面帮助贫困地区。首先,它可以提高这些地区人民的生活品质。更最重要的是,它可以提高那里劳动力的素质。研究证明,人力资本的投资是现代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只有当落后地区的劳动力身体健康且普遍受过基础教育时,这些地区才有希望进入经济增长的主流。从这个角度看,用转移支付的方式为所有人提供受教育和医疗保健服务的均等机会,不应被看作一种慈善行为,而应被看作是一种投资。这种投资不仅有利于贫困地区而且也有利于整个国家。
5.改善落后地区的基础设施
基础设施是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在中国,落后地区之所以落后就是因为这些地区缺乏交通运输设施、供电供水设施等等现代增长的先决条件。基础设施不足在许多方面限制这些地区增长潜力的发挥。例如它们缺少与沿海和海外的市场的联系;它们的生产和运输成本太高;外面的资本、技术和人力不愿流向这些地区;它们的劳动力不了解其他地区的就业机会等。总之,由于缺乏必要的基础设施,在与发达地区竞争中,落后地区只能处于下风。
为了实现均衡发展的目标,中国政府至少应当为落后地区创造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利用转移支付改善贫困地区的基础设施是实现对所有地区提供均等发展机会的第一步。
6.促进生产要素流动
任何一种区域发展战略都不能满足于对落后地区的补血,而应着眼于培养它们自身的造血机能。如果一项发展战略不能使落后地区获得自己发展经济的能力,那么它就是一个失败的战略。
要帮助落后地区发展经济,就必须设法将各种经济活动吸引到这些地区去。当然,改善基础设施是吸引外来投资的一个条件,但是,仅仅如此还不够。外部投资不会因为落后地区基础设施有所改善就自动流到这些地区去,因为发达地区的基础设施条件要好得多。因此,除了加大对落后地区基础设施的投入以外,政府还必须千方百计促使生产要素(资本、技术、劳动力和人才)向有利于落后地区的方向流动。
政府怎样才能促使企业到落后地区投资办厂呢?如果没有政府干预,落后地区当然不是企业投资的首选目标。其他国家的经验表明,以下这些政策工具往往是行之有效的(注:Stuart Holland,Capital Versus the Region,London:Macmillan,1976;A.J.Brown and E.M.Burrows,Regional Economic Problems:Comparative Experiences of Some Market Economies,London:George Allen & Urwin,1997; R.L Matchews,ed.Regional Disparitie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Camberra:Center for Research on Federal Financial Relations,1981;Harvey Armstrong and Jim Taylor,Regional Economics and Policy,Oxford:Phikip Allan,1985;Douglas,E.Booth,Regional Long Waves,Uneven Growth,and the Cooperative Alternative,New York:Praeger,1987;Hal Hill,ed.Unity and Diversity: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Indonesia Since 1970,Singapore,Oxford Unversity Press,1989;David Smith,North and South:Britain's Economic,Social and Political Devide,London:Penguin Books,1989;Alex Bowen and Ken Mayhew,eds,Reducing Regional Inequalities,London:Kogran Page,1991;Huib Ernste And Verens Meier,eds,Regional Development and Contemporary Industiral Response:Extending Flexible Specialization,London:Belhaven Press,1992;Donald J.Savoie,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Canada's Search for Solutions,2nd edition,Torontao:Unversity of toronto Press,1992.):为厂商提供有关在落后地区投资机会的信息,以降低不确定因素;向在落后地区投资建厂者提供补贴,以降低投资风险;为开发落后地区提供种种服务,如建立工业园区等,以降低投资成本;为开发落后地区的资源提供补贴;在落后地区兴建中央项目,作为经济增长的起动机(注:在美国,这种政策往往是以在各州分配国防产品订货的形式实现的。);对落后地区提供财政转移支付,扩大当地需求,刺激经济增长。
此外,政府还应促进劳动力跨地区流动,减少地区间就业与收入的不平等。政府特别应该鼓励而不是限制落后地区的剩余劳动力向发达地区有计划地流动。
这一条政策建议符合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观点,即应努力清除不利生产要素流动的种种障碍。如果资本向落后地区流动,劳动力向发达地区流动,长此以往,地区差距就会缩小。我们与新古典经济学不同的地方是,我们不相信仅靠市场的自发力量,资本和劳动力就会自动朝我们所希望的方向流动。促进生产要素流动仍需要政府政策作为“润滑剂”。
六、小结
中国正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在此过程中,尽管需要在很多方面对现有体制进行改革,我们却不应当放弃社会主义所追求的公平分配的目标。在前面,我们提出了一些缩小地区差距的政策建议。这些建议是符合市场经济原则的, 其精髓可以用一个英文词来概括:empowerment(增强能力)。首先,要增强中央政府干预经济的能力。 其次,中央政府要增强落后地区发展经济的能力。那么,中国政府应当怎样增强落后地区发展潜力呢?补贴是必要的,不过补贴应主要用于扶助绝对贫困人口。但光靠补贴不行。中央政策的重点应当放在如何使落后地区获取依靠自身发展经济的能力上。这样就需要帮助它们在人力资源方面进行投资,改善它们的基础设施条件,并为它们吸引外来投资提供有利的政策环境。采取empowerment的作法, 是为了将生产要素推到或拉到它们能得以充分利用的地方。这种作法不仅有利于缩小地区差距,还为加快整体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创造了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