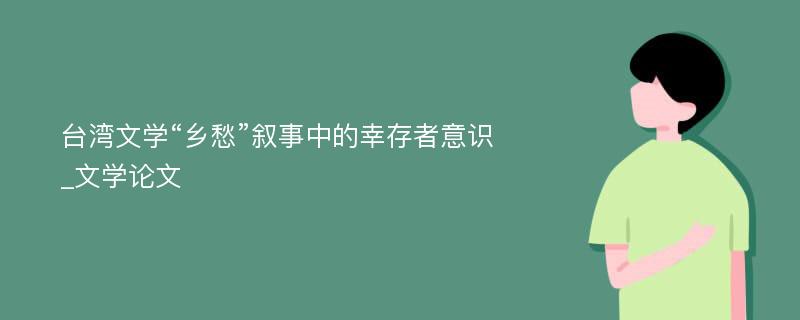
台湾文学“乡愁”叙事的遗民意识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遗民论文,乡愁论文,台湾论文,意识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2560(2015)02-0046-05 台湾的乡愁文学,与遗民文学是相互关联的。[1]100台湾三百年的文学历史,无论是明末清初以沈光文所代表的抗清文人志士所留存的怀乡诗文,还是日据时期抗日反日的文学作品,甚至20世纪50-70年代乃至80年代后台湾文学中时隐时现的浓重、感伤的文学“乡愁”,都弥漫着一种“强烈的流亡意识‘和思旧情怀”、形成了“台湾文学特殊‘移民性格’和‘遗民性格’”,构成了“台湾文学繁衍不息的重要文学母题”。[1]11明末以降,台湾社会文化中积淀了数代汉“遗民”知识分子的思想遗存,遗民意识构成了台湾社会文化心理结构中最底层的集体无意识。“遗民”群体,是汉民族知识分子在改朝换代的剧烈政治动荡的历史时期,以坚持原有政治价值取向与文化信念所构成的独特政治文化群体。遗民的潜意识,构筑出台湾文学的魂魄,而“文学乡愁”意象,寄予了汉族知识分子的爱国主义以及“民族主义”的精神本质,其文学原型则是“遗民文化”。台湾社会的遗民文化特性,决定了孤岛上汉族知识分子藉文学的“乡愁”抒发悲愤压抑的遗民政治意识、表达叛逆抗争的遗民历史意识、反映遗民群体灵魂无所依存的“孤儿”社会意识。 一、“乡愁”隐含了“不可为而为之”遗民政治意识 政治意识,是遗民文学“乡愁”的“剪不断理还乱”的心结。 台湾是典型的汉族移民社会,其社会文化思潮所隐含的潜意识是汉族遗民文化历史意识。生活在台湾的汉族族群特殊的历史记忆,不同于中原主流汉族社会文化的历史意识,台湾三百年来的悲痛孤岛历史,导致台湾汉族族群的政治价值取向,徘徊在“民族”与“非民族”、“家国”与“非家国”的矛盾之中。文学作为意识形态的特殊组成部分,以其虚拟的形象与环境,表现作者的社会理想与政治诉求。台湾的乡愁文学,投射了汉族知识分子强烈的政治意识。因此,台湾文学的“文学乡愁”,蕴含了诸多政治意识与政治意愿,包括政治认同、民族认同,以及与此相关联的政治文化、民族价值取向等,从反清的明郑时期到日据反日时期,再到“二蒋”时期,文学“乡愁”的政治意识顽强地存在着,其中还包含了“不可为而为之”的“复国”的政治意念与逆历史而行的叛逆性历史意识。 明末清初,清兵节节南下,南明抗清志士撤往台湾,他们带去了中华文化的种子,台湾文学创作出现第一个高潮。赴台明遗民的这些早期诗文,也就是遗民文学,反映了遗民的社会生活与情绪情感,表达了他们的政治志向,而文学乡愁与此结伴而生。被誉为台湾文学第一人的沈光文(1612-1688)①是浙江宁波抗清志士,他在台湾传播中华文化功不可没。在沈光文的诗文中遗民政治意识较为鲜明,其一是传播遗民的爱国主义思想。在其《感怀》一诗中所表达的:“采薇思往事,千古仰高踪。放弃成吾逸,奉迎有昔庸。”②就以宁愿饿死首阳山而不食周粟的商朝遗民伯夷、叔齐的典故明志,诗中“伯夷、叔齐”意象,既表达了作者对民族母体文化精神的追寻,又显示坚守政治忠诚的操守。其二是表达抗清复明的“复国”政治信念,如《见博者》:“好将孤注作机关,名士清谈未是闲。驿骑但能传捷报,出游何必不东山。”诗用谢安之典表达作者东山再起抗清复明之志。其三抒发对大陆故土的无限依恋。沈光文开拓了台湾文学“乡愁”的母题。他笔下乡愁,是生离死别之愁,是亡国亡家之愁,如《怀乡》:“万里程何远,萦徊思不穷。安平江上水,汹涌海潮通。”诗以诗人永远回不了故乡的悲情,而寄乡思于海水,联想台湾的安平江由海潮通往宁波甬江。另外,《赠友人归武林》中,同样表达了类似的乡愁意境:“去去程何远,悠悠思不穷。钱塘江上水,直与海潮通。”以上三类诗中,文学“乡愁”忽明忽暗隐现其间,所表达的是遗民政治观念。遗民中,具有代表性的文人还有卢若腾、徐孚远等。复国诗中,郑经的五绝《满酉使来,有不登岸不易服之说,愤而赋之》:“王气中原尽,衣冠海外留。雄图终未已,日夕整戈矛。”仍有铿锵豪气,而同为遗民的明太祖后裔朱术桂,却道出了复国无望的绝望的“乡愁”《绝命词》:“艰辛避海外,总为数茎发;于今事毕矣,祖宗应容纳。” 日据时期文学“乡愁”主要表现在守护和传播中华文化方面。 1915年的“余清芳事件”③后,台湾抗日武装斗争结束。日本殖民者以“皇民化”文化高压,迫使台湾人成为新“日本人”,而1937年汉文被废止。维护、延续中华文化道统,不与日本殖民者合流成为台湾遗民艰难的重任。此时,遗民的原乡情结和坚守中华文化意识,始终盘踞在这一时期的台湾主要文学观念中:充满着孤独的抗争、渺茫的期待与悲壮的感伤。而这时期的赖和、张我军、吴浊流、龙瑛宗、吕赫若等代表作家的作品中弥漫着遗民的悲苦情调,而遗民固守“故国”政治操守的潜意识投射在文学“乡愁”意象之中。日据时期台湾民众反日爱国与中国大陆人民抗日救国环境存在巨大差异,大陆人民抗日,有抗日根据地和抗日政府的有效依托,而台湾民众的抗日爱国,隔着台湾海峡,在日本殖民者的高压统治下,处于秘密和自发状态中,爱国知识分子出于遗民的一片“汉魂终不灭”的“孤忠”之心,这种爱国主义更为艰难。吴浊流的《亚细亚的孤儿》中,胡太明在壁上所提诗句“同心来复旧山河”,就反映了遗民潜意识中对故国的呼唤与对民族存亡的焦虑。 20世纪50年代后,台湾文学“乡愁”的政治意识表现得十分复杂,其遗民性显得隐晦而多变。 从台湾20世纪50至70年代的文学流变中,可以看到文学“乡愁”嬗变的路径:在“战斗文学”、“女性文学”中滋生,其后蔓延至“现代派”文学与“失根文学”,为台湾“乡土文学”思潮的渊薮,并影响台湾“本土文学”的成长。此阶段文学“乡愁”思潮的出现,源于两岸的隔绝与岛内政治文化高压生态,以及台湾所谓“中华民国”在70年代被国际社会的边缘化。此“乡愁”文学叙事,一方面反映了追随国民党政权败退台湾知识分子的大陆“原乡”心结;另一方面则是与台湾知识分子对60、70年代台湾岛内社会政治状况不满与岛外国际地位式微的反省有关。文学“乡愁”是这种社会心理的辐射。 而20世纪50年代的“战斗文学”几乎就是政治文学,以反共复国为宗旨。此类文学中最具艺术性的,要数文学“乡愁”所再现的原乡意境,而这种原乡追忆,却是一种复国的暗示。 台湾文学作品所反映出来的“文学乡愁”,无论其政治价值取向如何,其本质都含有屈原“哀郢”式的“悲情”,也有屈氏“复国”而“上下求索”的政治意识,一种汉遗民“不可为而为之”的执着,藉文学“乡愁”而投射其信念理想与意志操守,将其抗争的叛逆精神传布给读者。当强大的冷酷的现实浇灭理想的激情火焰之后,文学“乡愁”则反映遗民精神家园失落的“无根”悲情,白先勇笔下湖南老兵王雄“赶尸”投河,难免让人联想到屈原绝望中自沉湖南汨罗江。而台湾乡愁文学从作者个体“怀乡”经验的投射,到追求政治理想、政治诉求,再到历史意识的觉醒,进而上升到哲学境界追寻精神家园,是遗民文学精神从现实境遇到精神追寻的升华之路,是台湾文学“乡愁”演绎发展的一条隐形路径,折射了文学“乡愁”的遗民文化属性。 二、“乡愁”的遗民“心灵创伤”与叛逆不屈的历史意识 遗民的“复国”政治企图与遗民的“抗争”意志是同时存在的,“复国”是遗民的政治目标、“抗争”是遗民“复国”的一种手段,由此阐述遗民的历史意识与历史哲学。当“复国”了无希望后,遗民“失国怀乡”的悲情升腾而起,寄托“遗民心灵创伤”的“乡愁”的诗文也就出现了,文学“乡愁”以“怀旧”等意象来传播叛逆的遗民抗争精神,因而,文学“乡愁”是一种遗民文化与思想的载体,文学“乡愁”再现和表现了遗民的政治意识、历史意识与文化精神,是“以诗证史”的借文学记录历史的遗民历史叙事。 因此,“历史意识”是遗民情结的核心,这种历史意识源于对原有政治意识形态或民族文化价值理念的坚持,是维护旧“道统”的必然反映,是面对强大的异己力量乃至敌对势力的反抗。遗民现象的出现,往往在武装反抗遭遇惨痛失败后,遗民史观的最佳表达渠道是文学,文学可以假借文学形象、文学语言等多种文学手段,隐晦、曲折地反映遗民的政治意识与价值取向,表达遗民不同于主流史观的历史意识。遗民叛逆抗争的历史意识,是与文学“乡愁”结伴而生的。清初遗民沈光文所代表的“台湾文学播种”④期是如此,日据时期更是如此。 日据时期,这种历史意识与历史哲学尤其凸显:“台湾自郑成功就具有的‘遗民’精神,对日人的同化政策具有天然的解毒功能。”[2]86此阶段,反映对日本殖民统治的文学“史观”,是台湾作家以对原乡的思念与对中华文化的依恋展开的乡愁文学,是遗民精神的反映,用宋泽莱的话说,有着“弥天盖地的悲剧文风”,[3]199这种悲剧风格,充满了崇高的美学境界,他们一方面在“乡愁”的字里行间埋下“抗暴”的意识,渲染、引导台湾民众对日本殖民统治者的反抗,揭露殖民统治者对台湾人民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的反动性,以此埋下反对日本殖民统治的种子。另一方面,阐述播种中华民族意识,传递“中华史观”,表明台湾的殖民地现实。日据时期台湾文学家吴浊流在《亚细亚的孤儿》中,借主人公胡太明,表达了遗民抗争的精神与历史意识:他在墙壁上写下“志为天下士,岂甘作贱民?击暴椎何在?英雄入梦频。汉魂终不灭,断然舍此身!”诗句,而“汉魂终不灭”反映出台湾人民的“乡愁”与汉族主体性觉醒,也象征台湾人民在日本殖民统治时期遗民身份认同的觉醒与历史意识的存在。 台湾著名作家、现代文学评论家宋泽莱在评论吴浊流的《亚细亚的孤儿》所反映的日据时期台湾人的社会地位时曾悲愤地指出:“日治时代,台湾人的家园已经不再专属台湾人所有,而是日本人所有。台湾人表面上还有家园;但是背地里,日本人才是真正的主人,台湾人事实上是丧失家园的民族!”[3]262这个民族,就是指汉民族,就是台湾被殖民的历史。 日本殖民统治时期的台湾,是典型的“警察社会”,日本殖民政府是通过系统警察制度的建立,来统治台湾。“日据时期,台湾殖民体制中最严重的问题,可以说绝大部分均出自其所施行的专横的警政制度。殖民地的各项行政都是通过这一警政制度而得以实现的。”[4]台湾的“遗民创伤”来自于殖民地警察暴行。“殖民地伤痕”[5]是台湾文学“乡愁”的历史记忆,遗民抗争是通过对日本殖民警政制度的黑暗揭露与殖民当局对台湾民众的掠夺的文学叙事得以反映,这一时期的作家赖和、杨逵、陈虚谷、吕赫若、杨守愚等的作品具有代表性。 赖和的《惹事》就是以弱者的觉醒、维护道义与反映抗争思想,来藐视、否定殖民司法制度的一篇力作。作品以一名被殖民警察欺压的寡妇故事,来反映正直知识青年“丰”的反抗精神,“丰”面对殖民警察诬赖贫苦寡妇偷鸡滥施刑罚而勇敢站出来伸张正义,揭露警察的罪行。“丰”的形象象征着台湾人民时代意识的觉醒与不畏警察暴政的气概。同样,陈虚谷的《无处申冤》在揭露日本殖民警察制度的非正义性方面最具代表性。作品描述了好色的殖民警察冈平,在一个深夜强奸了地保的弟媳妇。此后,被害妇人的丈夫持证据到郡衙控诉。然而郡衙却将受害妇人抓来并强迫其否认冈平的强奸,但是她不肯屈服终被折磨而死。结果,地保被免职,地保的弟弟,也就是受害妇人的丈夫则被判“诬告及侮辱”官吏罪被判刑。《无处申冤》明确指出日本殖民统治下的台湾社会,是一个“无处申冤”的罪恶、黑暗的社会,并以此暗示:只有推翻日本殖民统治,台湾民众才有出头之日。在此,赖和与陈虚谷等遗民文学家是从历史的高度,去看待日本殖民统治的非正义性与非法性。 三、文学“乡愁”是遗民社会“疏离”与“孤儿”意识的心理投射 “疏离”、“孤独”、“孤儿”、“无根”等社会意识是台湾文学三百年来挥之不去的阴影。“乡愁是人类家园文化与离散现实的矛盾冲突并人生羁旅心灵诉求所触发的带有悲剧意味的普遍情思与深刻感想”,[6]黎湘萍先生对台湾遗民文学“乡愁”的社会意识与寻找失落的精神家园,有一段精辟的描述: 从明末开始,台湾逐渐滋生着一种挥之不去的“废墟”心态:悲情。它一再重演着中国历史上的南北对立(明末遗民与清朝的分庭抗礼,1949年以后两岸的对峙),以及南宋时代国土分裂(甲午战败被清朝割让给日本)的悲剧。这种分裂状态只有清一代(1683-1894)和1945年到1949年的短短几年间曾一度结束。这一点使得台湾文学始终难以摆脱与民族和政治的双重认同相关的移民或遗民色彩。它一方面背负历史遗留下来的苦难,另一方面为这种苦难进行着充满悲情救赎。这种救赎是以对异族统治的反抗和对祖国的认同为归依的。[2]44 黎先生所指的“废墟”心态,实质是一种遗民的社会意识与遗民精神家园失落的“无根”社会心态。而遗民的精神归依,就是祖国认同意识,遗民对精神家园的理解,首先是“故国”社会民族的文化价值,其次是“故国”的“疆土”。 荣格曾认为“不是歌德创造了浮士德,而是浮士德创造了歌德”,[7]精神家园的失落与无着的社会心结,是台湾文学“乡愁”的遗民社会意识的核心。“疏离”、“孤独”社会意象与承接不断的“孤儿”情感方式,催生了遗民的文学“乡愁”,而台湾这种特殊的政治历史背景下的文学“乡愁”,则是遗民社会群体主体意识的不甘寂寞的呼唤。有台湾文学研究者钟文榛对台湾文学作品中的“孤独与疏离”进行梳理,发现从日据时期作家到当代作家的作品中,都可以挖掘出这种社会“疏离”与社会“孤独”的思想源,作者统计和分析了包括“黄春明《儿子的大玩偶》、王祯和《嫁妆一牛车》、白先勇《寂寞的十七岁》、王文兴《家变》、七等生《我爱黑眼珠》、陈若曦《城里城外》”和“骆以军《远方》、朱天心《古都》、朱少麟《伤心咖啡店之歌》、邱妙津《蒙马特遗书》、林文义《流旅》”[8]等在内的诸多小说中社会“疏离”与“孤独”心灵的变迁。以此说明20世纪50年代后台湾第一代、第二代甚至第三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孤独”与社会的“疏离”。台湾20世纪70年代前后,无论是外强中干的“战斗文学”,还是思乡怀乡的“女性文学”,抑或是“现代派文学”以及“留学生文学”,遗民“乡愁”意识都以“疏离”、“孤独”意象出现在台湾文学中。这种文学“乡愁”的“疏离”与“孤独”,是遗民社会背离主流社会意识所出现的心理特征,在明郑时期如此,日据时期如此,即使“二蒋”时期,身居孤岛的大批追随二蒋败退台湾的大陆移民,也摆脱不了失去大陆的阴影,摆脱不了对大陆故乡的思念。文学“乡愁”承载和表达了这种“疏离”与“孤独”的社会意识。吴浊流的“孤儿”社会意识,就是典型的遗民社会心理,是遗民精神家园失落的潜意识反映。因此,社会“疏离”与“孤独”意识,是遗民精神家园失落的反映,同时,这种社会“疏离”与“孤独”意识,造就了台湾文学叙事与文学文本的无数遗民“乡愁”意象。 吴浊流的长篇小说《亚细亚的孤儿》深刻而典型地表达了日据时期台湾人民身份认同的矛盾与精神家园失落的社会悲情意识:一则台湾民众排斥异族殖民统治,不甘做“二等日本”子民;其次,台湾日本殖民地的事实,使得台湾民众既不能得到祖国(中国)的认同,又非中国人(法律意义上日本殖民地客观上的不认同)的矛盾与尴尬境地。小说中胡太明的遭遇,典型反映了台湾遗民社会群体那种灵魂无所依附的“疏离”与“孤儿”悲情。“孤儿”社会意识是台湾民众深层心理结构中挥之不去的遗民集体无意识,是遗民情结在乡愁文学中最悲苦、最无助的社会心理投射。在龙瑛宗的小说《植有木瓜树的小镇》中,林杏南一家的悲剧:大儿子自杀,女儿翠娥如同出卖,被迫嫁富户,林杏南自己发疯等遭遇,说明日据时期台湾青年理想的破灭,反映了台湾知识分子群体与日本殖民统治的主流社会巨大的社会鸿沟与社会隔膜,反映了遗民绝望的“孤儿”社会心理。 在台湾留学生文学中,将遗民“疏离”与“孤独”的社会意识上升到哲学高度来认识,提出灵魂失去“精神家园”的“无根”社会意识。 首先提出“无根一代”的是於梨华,她被称为“无根的一代的代言人”,[9]在她的小说《又见棕榈,又见棕榈》中,反映留学生牟天磊在中西文化冲突背景下,“精神家园”缺失、灵魂无所依存,一种“失根”的孤独心绪使之演化成为无处不在的乡愁与悲情。“无根”文学的代表作家还有白先勇,他的小说《纽约客》反映了留学生吴汉魂在东西方文化的矛盾中选择沉湖底自杀,同样反映了精神家园无着、远离美国主流社会所形成的“疏离”与“孤独”的社会意识。此外,白先勇的《台北人》、聂华苓的《台湾轶事》则反映了台湾岛内的“台湾人失根”的“疏离”与“孤独”的社会意识。而白先勇的短篇小说《那片血一般红的杜鹃花》中老兵王雄的形象,则较为深刻地反映了赴台大陆客与社会的“疏离”以及心中的“孤独”和对大陆故乡铭心刻骨的“乡愁”悲情。 收稿日期:2015-03-18 注释: ①引自叶石涛《台湾文学史纲·序》,春晖出版社2003年出版。叶石涛认为“明末,沈文光来到台湾开始播种文学,经历二百多年的培育,到了清末,台湾的旧文学才真正开花结果,作品的水准达到大陆旧文学并驾齐驱的程度”。 ②范咸《台湾府志》卷二十三,艺文四。转引自黎湘萍《文学台湾:台湾知识者的文学叙事与理论想象》,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版。 ③又称“西来庵事件”,日本占领台湾时期台湾武装抗日中规模最大的一次。1915年余清芳在台南的“西来庵”王爷庙宣传抗日,宣称日本气数已尽,中国将派大军前来支援。事发被镇压,近2000人被捕,其中866人被判死刑。 ④此处,借用叶石涛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