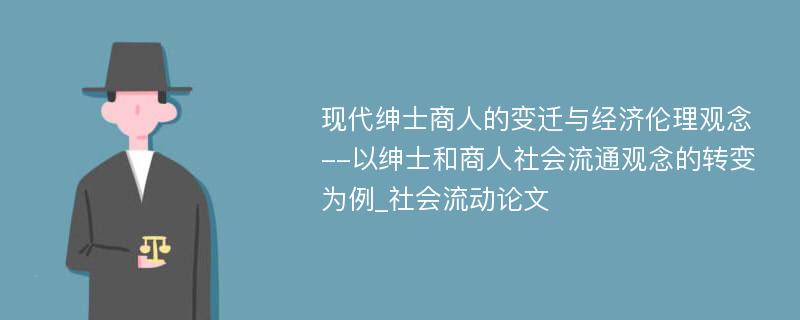
近代绅商与经济伦理观念的变迁——以绅商社会流转观念的变迁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观念论文,商社论文,为例论文,近代论文,伦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近代绅商互渗的社会学检视
社会流动是一个社会学概念,“流动”既指社会主体流向的地理区域层面,也专指流向的职业、身份、角色的变动性问题。本文使用其后一种涵义。
中国历史上的社会流动是一个持续不断的历史过程,规模较大的结构性流动也多次出现,但大多属于战争、瘟疫等社会和自然变故。清季晚期是中国社会新旧嬗替的转型期,人口流动的起因则较多地归结于商品经济发展和西学东渐所促成的观念意识的转轨继替,其中,绅商互渗以至于绅商合流作为社会结构性流动中最为显著的景观,其流转变迁的观念性动因,也莫不是种种传统观念意识转化调适的结果。
绅商对流作为晚清的一种社会突现,实际上是绅士、商人两个阶层的人沿着不同的流动渠道各自向对方阶层“渗透”,甚至达到“合流”的程度。这一过程预示着绅士阶层和商人阶层各自寻求自己的最佳社会地位,以更多地摄取有价值的声誉资源和经济资源。关于这一问题,张仲礼先生有深入的研究。他考察19世纪中国绅士阶层时发现有两点明显的变化:首先是新绅士人数不断增长,在19世纪的100年中, 新绅士占绅士总人数的比例,由前50年的32%上升到后50年的37%;其次是绅士阶层的收入结构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商业性收入稳步上升。(注:张仲礼:“Thelncomt of the Chinese Gentry ”,in The Chinese Gentry (Washington University PreSS,1955),P.215、217。)绅士收入结构中商业性数字的增长表明绅士阶层有向商人阶层流动的趋势。
实际上作为一种社会流动,绅商互渗不仅出现在近代,早在宋元时期已渐露端倪,但是直到晚清时代才迅速地产生了规模较大的结构性流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称之为社会突现。既然是“对流”,那么也就蕴含着两个不同的流转形式,即包括了“由绅趋商”和“由商趋绅”两种不同的对流过程。
其一,“由绅趋商”流转问题。随着唐代以来重商意识时起时伏以及各地商品经济发展的推动。“由绅趋商”的流转机制早已启动,但因传统经济、政治、文化、伦理观念的规约,这一进程是相当缓慢的,到清季末期,随着中国近代新式商业的涌现和近代社会生活的变迁,传统的功名身份固然重要,但已不再是唯一的价值资源。实业价值的提升浸润了传统的士绅阶层,以至“同光以来,人心好利益甚,有在官而兼营商业者,有罢官而改营商业者”,士绅阶层对商贾群体的改容相向,促使实业价值陡然攀升。连一向抑商困商的清政府也作出转轨性表态:“向来官场出资经商者颇不乏人,惟狃于积习,往往耻言贸易,或改换姓名,或寄托他人经理,以至官商终多隔阂。现在朝廷重视商政,亟宜破除成见,使官商不分畛域”(注:《商务官报》,第2册,第19期。 )。实业价值的提升与科举制的废止也不无关联。科举制本是传统中国社会一项使政教相连的政治传统和耕读仕进的社会变动落在实处的关键性建制。科举制废止后,耕读之路走不通,终于使最后一代居于四民之首的绅士被动地走下了等级社会的首席。四民社会结构的解析也就趋于显性化了。故此,原来“由绅趋商”流转的早期形态已跃进至近代意义上的社会流动形态,突出的表现是绅士投资观念中愈益器重新式企业和近代公司。按张之洞的说法,“湖南诸绅现已设立宝善公司,集有多股,筹设各种机器制造土货之法,规模颇盛”(注:《张文襄公全集》,卷四五,奏议四五,十八页。)。在近代新兴的纺织企业中,由绅士创设的工厂数目占到68.42%。资本数额则占到73.27%;金属采冶行业中,由绅士投资创办者可占20%左右。(注:据《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下册,870~877、924页各表测算。)王先明先生对绅士阶层的社会流动趋向颇有研究。他曾就由绅趋商的社会流动提供了一个典型材料,按其说法,甲午战后中国商界规模的扩大,较大型工厂企业和农牧垦殖公司人多是由绅士们创办的,在近代11个资本企业集团中,除祝大椿、曾铸等人外,大多数是由绅趋商的典型。这些典型的资本集团其资本总额已占到1895年~1913年商办企业投资额的10.7%。(注:据《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下册,1069、1091~1096 页;又见王先明《中国近代绅士阶层的社会流动》,载《历史研究》。1993(2)。 )时至1907年,清廷颁行《改订奖励公司章程》规定:“集股二千万元者,拟准作为本部头等顾问官,加头品顶戴,并请仿宝星式样特赐双龙金牌,准其子孙世袭臣部四等顾问官,至三代为止。”(注:《改订奖励公司章程》,见《大清光绪新法令》,第16册。)巨大的声誉和利益资源使得实业更呈“显业”,“反映出实业活动实际上已成为仕途之外另一条可以为人们所接受的出路”(注:【美】陈锦江:《晚清官、商与近代企业》,39页。)。以研究近代中国资产阶级早期形态著称的马敏先生曾称这种近代的“由绅趋商”流转已不单纯是偶发的逐利或赶时髦,而已经汇成一股潮流,蕴含了某种新的社会意义。(注:马敏:《过渡形态:中国早期资产阶级构成之谜》, 142 页,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此为确然之论,至于其“新的社会意义”究竟何在,笔者俟后将稍作经济伦理观念的关注和考证。
其二,“由商趋绅”的社会流转问题。自古以来,“重农抑商”的传统治术和观念一直制约着商人社会地位的擢升。但即便如此,商人入仕为官仍有不绝之势,只是限于禁令规模一直不大,并且常遭物论。(注:《隋书》,卷五六《卢恺传》;《旧唐书》,卷七二《颜籀传》。)9世纪以后,商人入仕途径渐趋开阔:科举途径、经济谋职、 军功谋职等,这的确为商贾阶层流向士绅阶层提供了机会,此后商贾人仕为绅的实例才多见于史乘。
传统的中国社会是一个主要以功名、官位和文采取定威望与地位高下的社会,这种价值取向常常使得那些因经商而囊丰筐盈的商人被诗书举子所藐视。因而,以财富来弥补社会地位和个人声望的心理冲动便构成了“由商趋绅”社会流转的潜在动因。这种社会流转的主体渠道便是始于汉代的捐纳制度。时至清代,尤其是甲午以后,清政府亟需敛财以弥补财政亏空,因而卖官之事愈盛。由此,清季末年绅士群体的相当部分是来源于资力雄厚的商贾群体。据张仲礼先生研究,19世纪一大批盐商、广东行商及山西票号商人都是经过捐纳或捐输而混进绅士阶层的。当时的面粉业资本家荣宗敬、汉口巨商宋炜臣、上海商人曾铸以及地域商帮中的诸多人士基本上都通过捐纳等途径,取得大量官衔、封荫及官职。据对苏州商会“组织沿革”档案的分析,在73名绅士中,经由捐纳途径而入此群体者占到84.93%,捐纳花费之巨非一般人所能承受, 绝大部分非商人莫属。商人加入绅士群体,造成绅士阶层已不纯粹是原来意义上的绅士阶层,这在人们观念上反映出来的变化就是“绅商”这样一种并列称谓,有时甚至将“绅商”视为一个独立成型的群体,例如“该绅商”之类的称谓。(注:参见《商务官报》中有关对呈报创办公司、企业的官方批复。)
相对于“由绅趋商”的流动,“由商趋绅”这一社会流动历时久远,而且规模巨大,两条对流路线和对流方向相比较,各自反映出不同的观念趋向,尽管两个社会阶层都属于晚清社会流动中的显要部分,但支配其参与流动的人文观念和价值取向则有着异质的差别。这种异向流动和支配流动的观念差异一直是有关学者关注的问题,笔者拟从经济伦理的转承调适这一视角来观照其脉络背后的观念底蕴。
二、绅商互渗:经济伦理观念的制约与促动
对一种社会历史现象作出“经济伦理”的关怀和揭示始于德国著名学者马克斯·韦伯,他在本世纪初将“宗教经济伦理”与“西方独有的资本主义精神”作了某种关联性研究,并尝试着对“宗教经济伦理”作了一个并不完整的界说:是“在宗教的心理和实用的脉络之下促成行动的实际动机”(注:张鸿翼:《儒家经济伦理》,3页, 湖南教育出版社,1989。)。这一界说是模糊的,后来国内外学者在沿用这一概念时也格外小心、犹豫。时至今日,国内外学者对其完整涵义、评判规约的范围、学科构架和作用力度等都未能作出一个完整科学合理的界论。即便如此,它作为一种研究历史现象的参考观照体系,能够充当考察社会历史运作规律的中介工具,理应不可漠视。
绅商对流首先是一种社会行为,这种社会行为的产生按列温的“动力场”理论来说,不外乎是参与社会流动的绅士、商人两种社会主体本身的文化心理因素和社会环境冲击制约的作用。实际上,主体文化心理和社会环境是紧密相联的。主体文化心理既具有一定的稳定性,但也随着社会环境的嬗变而发生结构性改变。就绅商对流的宏观环境而言,中国传统的“伦理—政治”型文化深刻地影响到绅、商社会行为的方方面面。这种文化模式的主要特征是以伦理取向来看待历史,并规范现实和未来。中国文化传统中的泛道德主义源远流长,其滥觞则为注重德性心灵修养的内圣之学,至宋明时期,理学诸子将“内圣”推为一切文化、行为的出发点和立足点,诚所谓“学莫大于知本末始终。致知格物,所谓本也,始也;治天下国家,所谓末也,终也。治天下国家,必本诸身。其身不正。而能治天下国家者,无之”。这无疑是泛道德主义的典型语言。这种文化根性深刻地影响着历代绅士、商人和士大夫阶层,使他们在看待社会生活、政治和经济等诸类事物时莫不以“本末”、“始终”、“体用”等思想来权衡酌量,诸如“末修则民淫。本修则民悫”,“舍本逐末,贤者所非”。这既是传统伦理观念的主体内容,也是调节社会性行为(如社会流动)和经济行为(如务农、经商)的经济伦理的重要范畴,“重本抑末”、“存天理,灭人欲”这种典型的经济伦理即作为传统的经济行为调节器构成了影响人的一切行为倾向的重要环境因素。历代反对与民争利,反对抑商轻商,主张“农末俱利”的观点,也都没有突破“农本工商末”这样的经济伦理划分。绅商对流的初始过程极为缓慢,尤其是由绅趋商的流程至为迟缓,直到晚清时期才演成一个流转高峰,这种传统的经济伦理观念恐怕是绅士主体行为的基本制约因素。
宋明理学将“伦理—政治”型文化模式及礼仪至上的传统经济伦理观念发展到极端,使伦理纲常与社会经济进步的趋向割裂并相互对立,从而偏离了儒学伦理道德中与现实人生相协调的实用精神,致使传统经济伦理走上物极而敝、隙漏毕现的境地。因而,就在理学经济伦理盛行之时,反传统的近代经济伦理思想也就逐步出现。特别是明季中叶以后,社会承平日久,城镇商业经济发展,市民阶层扩大,世俗生活繁荣,市井流行着崇财逞欲的生活方式(这在当时大量的小说笔记中有充分的反映),与此相对应,谈心性者更加脱离实际,并走向空疏和虚伪。当时的一些有识之士基于现实生活的感触,起而抨击理学伦理思想,公然张扬“人欲”、“日用”、“私”、“利”,与传统的“存天理,灭人欲”的经济伦理形成对峙。如王艮主张“圣人之道无异于百姓日用”,“人欲即是天理”;(注:《王心斋先生遗集》。)李贽提出“吃饭穿衣即是人伦物理”,直至明清之际的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颜元等提出“私欲之中,大理所寓”。(注:李贽:《藏书·世纪列传总目前论》;王夫之:《四书训义》。)主张“工商皆本”。这些惊人之语实际上揭开了经济伦理近代化的序幕。
时至洋务新政时期,弘扬和实践“尚富强”的经济伦理成为洋务运动的灵魂,这是一种以西方经济伦理为参照系的开放性思维的产物,也是一种基于现实利害的理性趋向的选择。它指向的是俗世的功利性的价值目标,在很大程度上是对西方世界工业化经济伦理观念的认同,标志着以近代理性为取向的经济伦理观念开始蕴育发展。尽管如此,它在整体上尚未达到马克斯·韦伯理论视野中的清教伦理的程度,其俗世化的路程将相当漫长,洋务运动以后的经济伦理在总体上尚处于一种过渡形态。经济伦理的过渡形态首先表明其演化嬗变的不彻底性,传统经济伦理与理性化取向的近代经济伦理杂揉相处,这就导致它调节伦理主体行为的功能是不完善的。诸如绅、商主体行为在其他环境因素的综合作用下显现出逆向且不同步对流的特征。按桑巴特(W.Sombort)的观点, 中世纪时期,人们是由社会权力获取财富,而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们则是由财富获得权力。这是对两种社会形态中典型的社会对流的集中概括。一旦用这种参照理论来分析中国近代社会中的绅商对流的观念动因,我们却会感到十分困惑:在近代社会中,人们理应将工商社会作为社会流动的主要趋向,譬如由绅趋商的社会流转,但根据上述分析,近代社会恰恰存在着由商趋绅这样一个不容忽视的社会现象,直至民国初年,这一势头仍不算弱。如此便涉及到一个经济伦理中主体价值认可的问题。
过渡型经济伦理不纯粹性的主要表现是主体价值取向中,传统的功名、翎枝成分与尚富求利、张扬私欲成分混杂渗透。众所周知,近代商人仍未放弃对传统绅士社会价值的认同,“绅为一邑之望”的巨大声誉、徭役豁免权以及“家有举贡士,敢把钱粮蚀;孝肃与忠介,所以疾巨室”(注:《潜皖偶录》,卷九,一五八页。)的境界,仍在吸纳富商大贾流向绅士阶层。经济伦理观念中的这种价值取向恐怕可以作为我们解释由商趋绅流转现象的主要依据。当然,这并不是说,支配商人社会性行为的经济伦理观念仅此而已,事实上,对商人来说,过渡型经济伦理中也不乏近代理性的成分,崇尚务实,以及对商人价值的自我认可仍然支配着其经济行为。余英时先生在其《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中较多地谈到这种情况,他将此谓为商人的“超越性动机”(注:余英时:《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见《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是“良贾何负于闳儒”心理的一种表现。
将桑巴特的社会流动理论用来解释绅士阶层的社会流动特征,我们依然遇到不可思议的理论难点。因为绅士阶层的社会流动在近代社会中仍旧是处于一种“多维向流动”的过渡形态,且大多数绅士仍局限于本等级范围内的流动。现代心理学研究表明,人的行为是由动机支配的,动机则是由需要引起的,人们的行为都是在某种动机的规约下以便达到某个目标。因此,需要、动机、行为、目标就构成了心理与行为的一般互动结构。实际上,在这一互动结构中,就绅商对流这一社会现象来说,“动机”基本上相当于调节人们社会经济行为的经济伦理,经济伦理的过渡性、复杂性也就预示着“动机”形态的复杂性,近代经济伦理中关于价值取向“传统与近代并立”的格局在很大程度上使得“动机”所反映的“需要”充满了不同类质的功利成分,既要功名、地位,又追求物欲享受,这就是绅士阶层的“需要”结构系统,在这个系统中,“功名”、“身份”成为主导系统。“物欲享受”和“崇富求强”仅为从属系统。近代绅士阶层经济伦理观念的转承调适也就是这一结构系统在经济变迁和时局变幻中的矛盾运作。但是,近代中国社会是一个变动剧烈的社会,西方经济方式和思想观念的冲击,社会经济生活的多元化趋向,都使得绅士的价值认同结构系统发生新的变化,这种变化的基本趋向就是对物欲私利的刻意追求。民国初年有人对此作过描述:“自西洋物质文化输入以后,吾社会全体,对于物质界之欲望顿增。故衣食居住之模仿欧风,日用品物之流行洋货,其势若决江河,沛然莫御。生活程度之高,乃倍蓰于曩日”(注:伧父:《论社会变动之趋势与吾人处世之方针》,载《东方杂志》,第9卷第10号,1913年4月1日。)。 此描述固然是泛指社会各个阶层,但绅士作为当时社会的“望族”绝不可能置身其外,况且这种世风变化也促使以“本”、“末”等标准划分的“四民”社会格局发生局部性改观,“通都大邑,贸易繁盛,商人渐有势力……商与官近至以‘官商’并称,通常言保护商民,殆渐已打破从来之习惯,而以商居四民之首”(注:《孙中山与辛亥革命史料专辑》,112页。), “士农工商,四大营业者,皆平等也,无轻重贵贱之殊”(注:《贵业贱业说》,载1902年11月20日《大公报》。),社会价值指标的变化也就从容地推动着绅士阶层的经济伦理观念孕育滋生着近代化成分,他们即在这种近代理性取向的经济伦理观念的支配下参与到晚清以至民国初年的“多维向流动”中去,厕身于实业、教育、法政、文化等各个领域,变成各种自由职业者了。(注:据王先明先生研究,经过科举制的废除和辛亥革命,在结构性社会流动中,传统的绅士阶层趋于消亡。在民国时期,虽然还有“绅”的称谓,诸如缙绅、豪绅、开明士绅之类,但它与传统的绅士阶层不同,不再是以“功名”身份获取社会地位,而且它是否能构成一个社会阶层也是一个需要研究的问题。)
三、近代经济伦理观念的演进:绅与商的价值估价
下面我们将考察近代经济伦理演化的推进机制中绅士群体和商人群体的价值地位问题。
很久以来,史学界在探讨近代思想观念转型时无不推重享有巨大声誉的趋新社会群体中的杰出人士,诸如王韬、马建忠、薛福成、郑观应、陈虬、何启、胡礼垣等。不用说,这些近代趋新社群的娇娇者确实给窒息的中国思想界注入了新鲜的血液。就本文所论及的经济伦理观念的变更来说,这些趋新人士的灼见也曾给中国传统的经济伦理以深刻的冲击。但是,经济伦理的嬗变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过程。不但专指思想理论上进行建设性转换,更重要的是新型伦理观念在较大规模上的认同和轰轰烈烈的实践,这自然是基于经济伦理的调节功能而言。这种调节功能的实现需要以思想认同为前提,然后才是实践层次的问题。故此,笔者在此关注的是思想认同、扩散以及实践层次的问题。
近代新型的过渡形态的伦理观念必须经过思想较为敏感的社会群体的接收,产生思想共振,然后付诸实践。就近代中国的社会结构系统而论,这样的社会群体主要便是绅士和商人两大群体,尽管他们所起的作用不能等量齐观,但也是各具千秋。
其一,绅士阶层在传播倡导新型伦理观念上的主导性价值。在传统的封建社会中,社会结构系统由官、绅、民三个子系统构成,绅居“中等社会”,它基本上由三种成分构成:(1 )具有举贡生员以上功名者,这是绅士阶层的主体成员;(2)乡居退职官员或具有官衔身份者; (3)具有武科功名出身者。由此看来,这是一个知识阶层。 选定这样一个阶层作为考察对象,除了基于中国近代社会的结构特征的考虑而外,主要看其在社会实际生活中发挥的独特作用。首先,近代社会风气的进化,新式思想的传播和扩散必须途经的一个阶层就是绅士阶层。“下等社会之视听,全恃上中等社会为之提倡”(注:《吉林全省地方自治筹办处第一次报告书》,中卷。),绅士阶层作为“四民之首”理所当然地在倡导新观念方面极具优越性,即绅士阶层基本具备了接受、传播新的伦理观念的条件。从绅士阶层的实际活动来看,他们大约也是发挥了倡导、传播、实践新观念的作用。一方面,甲午战后,绅士们积极地介入到新式教育和传播事业活动中,“各省地方绅士热心教育开会研究者,不乏其人”(注:《清学部奏酌拟教育会章程》,载《东方杂志》,第3卷第9号。),主持地方旧式学务的绅士受到新潮流的推动,成为新学创建、投资的承担者,他们不断接纳着来自各种途径的新思想新观念,经过认同、梳理,然后传播给角色不一的听众和读者,起到了思想输导的中介作用。在介入新式教育和传播事业的过程中,绅士阶层无论是作为信息的发出者,还是信息的接受者,无一例外地感受到新学说新观念的浸染。据吉林省和浙江省的地方自治机构的史料披露,当时绅士们已大致了解到近代西方社会科学中基本的学科知识,诸如经济通论、法学通论、财政学、政治学、国家原理等等,这些新的知识体系已深刻地影响了近代绅士阶层,(注:据《吉林全省地方自治筹办处第一次报告书》和《浙江省地方自治筹办处文报》。)而他们又作为信源将各种新的价值观念(包括近代经济伦理观念)依凭各种途径传播扩散开来。另一方面,绅士也是实业创办的倡导者。中国“实业不振,首在提倡”,1903年商部设立后,即在其有关文书中对绅士的实业倡导作用寄予希望。(注:1905年6月30日《大公报》。 )绅士阶层张謇当之无愧成为实业倡导的先锋人物,他“半生精力耗于实业”,至民国元年他所创办的有影响的企业已有29个,而且行业门类极为广泛,这在当时传统经济领域“本末”之争依旧存在的环境下,确实起到了开创风气,张扬“求富求强”等近代经济伦理的重要作用。
其二,商人阶层在突破传统经济伦理观念的束缚、实践新型经济伦理原则方面的独有价值。实际上商人阶层对传统经济伦理观念在近代的转承调适所起的作用是一个极为复杂的问题,在论及这一问题时采用历史考察角度和结构分析角度都是必要的。就历史考察角度看,商人社会群体的价值地位评判应与其实际社会地位结合起来。从理论上讲,商人恰好处于上层文化与通俗文化的接榫之处,似乎理所当然地对经济伦理的转承调适会产生主要的影响。但是实际上,商人由于其在社会中居于末位,他们在伦理观念变更中所起的历史作用便不能夸大。时至晚清民国之交,尽管专制政治仍旧控制着中国社会的各种资源,但是西学东渐引发的改革潮流,新的生产方式导致的观念冲击,加上晚清政权的两次新政(同光、清末),越来越催生出一个独立于官僚阶层而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紧密相连的工商社群,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已能够独立地发表自己的见解,包括大胆地鼓吹利润、私欲,以及工商立国这类经济伦理信条。更重要的是他们通过组织商会,较有成效地积聚着自身的能量,并依凭自治性机构和各种传媒不断向社会张扬着自己的价值理念,担当起社会公众论坛的角色。也只有在这个时候,商人阶层的独有价值才得以充分地展示。
从结构分析的视角来看,商人阶层对经济伦理的建设性转换的主体贡献是对伦理规范系统的实践以及在实践中的发展。韦伯在论及新教伦理时特别推重“德”、“勤”两大要目,其实,这也是中国传统经济伦理中具有重要调节作用的规范,它在明清时期商人身上体现得更充分。勤俭应是明清商人基本的伦理规范,而占据中心地位的伦理规范当算是“诚信不欺”,即言行一致,表里相应,遇事坦然有余地的道德信条。诚信规范,既具有屏卫儒教仁、义、礼之道的现实功能,又对人们的商品观念及其商品经济行为具有规范和制约的功能。明清商人的诚信事例史乘多有记载,如果将商人群体看成只知“孳孳为利”的俗物,这与历史事实是大相径庭的。除此而外,研究明清商业集团的学者还举出一些行之有效的伦理规范,如以义为利、仁心为质、薄利多销、精恩创物,灵活应变、顾客至上等等。对这一伦理规范的实践价值的评估似乎有两点需要注意:一是商贾凭此拓殖自己的事业并尽快积累起雄厚的财富,这更加促成了他们实践这些伦理规范的自觉性,并有可能发展和充实它的内涵结构;二是凭此赢得的产业振兴也以巨大的典范效应辐射到其他的社会阶层,进而弘扬自己的价值观念,以推动全社会各阶层实践这种伦理规范。与绅士阶层相比较,这两点评价正好体现了商人阶层在经济伦理演化发展中的独有价值。自然,时至晚清,商人群体的独有价值不限于这两点,具体到伦理观念转型,伦理规范的近代化方面,随着商人集团的日益独立和强大,他们更以今非昔比的影响力推动着经济伦理向近代理性迈进。
标签:社会流动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社会结构论文; 经济论文; 群体行为论文; 传统观念论文; 社会观念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 经济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