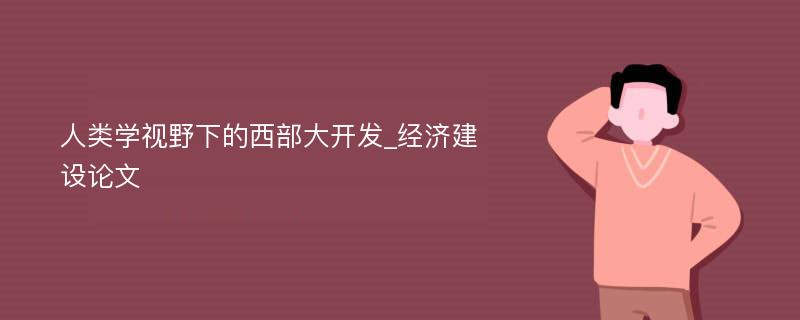
从人类学观点看中国西部的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人类学论文,观点论文,西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关于现代化的概念、定义,说法颇多。〔1〕人类学家通常把现代化视为文化变迁的一种形式,西方人类学界关于文化变迁的著作大多是研究不发达社会如何向现代化迈进的。在人类学家看来,现代化过程一般由四个亚过程组成:一是技术科学化,二是农业商品化,三是工业化,〔2〕四是都市化。另一些人类学家认为,世界各国现代化进程所共有的特征主要有:工业化、法制化、民主化、都市化、均富化、福利化、社会阶层流动化、宗教世俗化、教育普及化、知识科学化、信息传播化、人口控制化,等等。〔3〕
随着现代化的进展,人们一方面要不断创新变革,改变自己固有的传统,另一方面要不断适应变迁的处境,因此,文化变迁问题便成为现代化过程中最重要的问题。一些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比较注重文化变迁过程中社会解体及其相关现象的研究;另一些人类学家则较注重变迁的过程中社会的某一部分产生病态或不适应的研究。美国人类学家奥斯卡·刘易斯(Oscar Lewis)在1965年便提出文化变迁中的“贫困文化”(culture of poverty)问题。他认为,在现代化过程中,或者说文化变迁过程中,最常见的现象是只有部分人的现代化,换而言之,社会中的部分成员己改变其传统的生活,而接受了现代生活方式。但是,另一部分或小部分人却因种种原因未能现代化,仍处在贫困之中。这些未能享受现代化生活的人,就形成特殊的社会群体,表现出既不能进又不能退的状况,而自成为一种文化模式。刘易斯称这种次文化(sbculture)为“贫困文化”。“贫困文化”可以出现在大城市的区域内,就是一般所说的“贫民窟”或“陋巷”;也可以出现在乡村地区,即穷乡僻壤或特殊职业或种族的地区。〔4〕
中国地域辽阔,经济文化发展水平不平衡,各地的现代化进程差距很大,贫富差别悬殊,两极分化较严重。刘易斯所说的“贫困文化”,无疑在全国各地都存在。特别是在西部地区,现代化进程远远落后于东部和沿海发达地区,“贫困文化”现象也就更为普遍。如果东西部差距越拉越大,两极分化愈来愈严重,“贫困文化”所产生的副作用也就越来越大。一些经济学家曾提出“梯度推移”理论,即先发展东部,然后再发展西部。但是,如果不尽快消除西部的“贫困文化”现象,人们的心理就会很不平衡,西部的社会稳定也就没有保障,进而将影响东部的发展,甚至可能会影响国家的统一。因此,决不能在东部完全发展起来之后,再考虑西部的发展。
按传统的说法,中国西部一般是指新疆、甘肃、宁夏、青海、陕西五省区。本文所指的西部,主要是指新疆、西藏、内蒙古、青海、甘肃和宁夏六省区。这些地区都是民族地区,在许多方面具有特殊性。
如何发展西部,逐步缩小东西部的差距?这是当前民族学、人类学研究的重要问题。本文试从人类学的角度,结合自己的调查材料,对如何发展西部地区,提出一些个人的粗浅的看法。
二、内源性变迁和外源性性变迁相结合
(一)社会变迁基本模式
加速西部地区的发展,缩小东西部地区的差距,首先要明了东西部差距越拉越大的原因。下面我们从社会变迁模式分析两者的不同。
1.创新性变迁,专导性变迁
从社会变迁的强弱程度来看,社会变迁大致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微型变迁,即微型的社会变迁。它又可分为两种形式:渐进性微变和突发性微变。这类变迁是发生在同一社会经济形态或同一生产方式之内的社会、经济、文化的积累性的渐变和突变,它是传统的变迁模式。另一类是巨型变迁,即巨型的社会变迁,这是指突破社会经济形态和生产方式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大变化。这类变迁都具有革命性、突破性的质的变化,它是现代的变迁模式。
从变迁的性质来看,巨型变迁也可分为两种类型:其一是创新性的巨变,它是通过自身的积累、创新、发现、发明,突破原有社会经济形态的革新性社会变迁;其二是传导性的巨变,它是突破原有社会经济形态的外因诱导性巨变,这主要是受外因诱导发生的生产方式和社会形态的变化。〔5〕
创新性变迁与传导性变迁并不是界限分明的,在大多数地区,两者往往相结合,相辅相成,只不过是主次不同而已。
2.内源性变迁和外源性变迁
从社会变迁的形式来看,由于创新性变迁与传导性变迁两种方式不同,从而形成两种不同类型的社会变迁过程。一类是内源性变迁(endogenous change),它源于创新性变革,即由社会自身力量产生的内部创新而发生的社会变革的道路,其外来影响居于次要地位。学术界又称这种变迁为内源的现代化(modernzation from within)。另一类是外源性变迁或外诱变迁(ex-ogenouschangge)。它源于传导性变革,即在国际环境影响下,民族社会受外部冲击而引起的内部社会变革的道路,即通过文化传播的方式,采借、引进其他国家、其他地方、其他民族的文化而求得发展的道路,其内部创新居于次要地位。学术界又称这种变迁为外源或外诱的现代化(modernization from without)。由于历史条件不同,各个时期的社会变革的方式均不相同。在古代社会,社会较封闭,彼此之间交流不多,内源性变迁即自身的发展是社会文化变迁的主要形式,外源性变迁是次要形式。在现代社会,社会开放,交通发达,信息灵通,外源性变迁即传播或借用是社会文化变迁的主要形式,内源性变迁是次要形式。一切成功的变迁过程,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内源性变迁和外源性变迁相结合,只不过是主次不同而己。在较适合外源性变迁的地区,往往以外源性变迁为主,以内源性变迁为辅;在较适合内源性变迁的地区,以内源性变迁为主,以外源性变迁为辅。
3.东西部社会变迁模式的差异
中国东西部情况不同,现代化模式和发展的道路也就不可能完全相同。改革开放十多年来,东部和沿海发达地区得地利之便,开放较早,开放程度也较大,大量引进外国资金、技术和人才,各种类型的三资企业如雨后春笋。在外部因素的冲击下,人们思想解放,观念更新快,竞争意识强,经济体制得到较快、较好的转换。同时也由于东部和沿海地区科技水平较高,市场经济条件较好,文化素质较高,基础设施、交通、信息等条件较好,因而其社会变迁是急速的、大幅度的。从变迁的性质来看,它是传导性变迁为主、创新性变迁为辅的变迁模式;从变迁的形式来看,它是属于外源性变迁为主、内源性变迁为辅的发展道路。外来因素的冲击和压力形成为主要的推动力,外部因素的作用超过内部因素。而西部地区的发展模式和发展道路则与东部的有所不同。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一是对外开放较晚,许多地区至今仍处在半封闭状态;其二是西部地区大多属内陆地区,周边都是欠发达国家,因而发达国家的先进的技术难以对这些地区发生直接的、较大的影响;其三是西部地区没有东部地区的优越的自然条件,要引进外国和港台资金、技术、人才来开发很困难;其四是面积辽阔,外来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在这些地方传导很慢。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西部地区的发展主要通过内部的改革、调整而形成推动力,其变迁是自上而下的、渐进变革的过程。因而其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不是快速的,变革引起的社会矛盾也是逐渐展开的。这种变迁能保持社会的相对稳定和较大的连续性。从变迁的性质来看,它是以创新性为主、传导性为辅的变迁模式;从变迁的形式来看,它属内源性变迁为主、外源性的变迁为辅的发展道路。内部因素的作用超过外部因素。
(二)增强外源性变迁:加速西部发展的关键
在现代世界,高速发展社会的经济、文化因素对低速发展社会具有强烈的传导性,而国际竞争机制又使这种传导性变得越来越强,从而产生一种不同于一般文化传播的特殊传播效应——“现代化效应”(modernizing effect),引起强化的适应性的社会变迁,这就是典型的传导性或外源性变迁模式。这利变迁模式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取得较快的发展,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以这种变迁模式为主。改革开放以来,东部地区采用外源性变迁为主的发展模式,在短短的十几年内便取得巨大的发展。
加速西部发展,缩小东西部差距,刻不容缓。国家应该有一个明确的目标,制订长远的规划,完善开发西部的各项制度。外源性变迁是当代世界快速发展的主要模式,因此必须通过各种方式,增强外源性变迁的广度和深度,大力引进先进技术、人才和资金,增进交流。
1.扩大引进
中国西部六省区的特点是:其一是民族性,它表现在民族成分多,民族人口比例较大。其二是自然环境独特,它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面积辽阔,地大物博;二是自然条件差,基础设施落后,交通不便,信息不灵。其三是文化独特,它也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伊斯兰文化在新疆、甘肃、宁夏等省区占有重要地位,二是藏传佛教文化在西藏、青海和内蒙古地区占有重要地位,而这两种文化都与中国东、中部地区的文化差异较大。其四是国际性,它也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边境线长,二是跨界民族多。其五是经济文化发展滞后,社会尚处在半封闭状态。贫困面大,思想保守,观念落后。
外源性变迁的方式又可分两种,一种是主要靠引进、移植国外的现代化模式。事实证明,东中和沿海发达地区大量引进海外先进技术、资金和人才的外源性变迁模式是成功的,是要引进海外资金、技术、人才来开发西部很困难。前几年,西部地区一些省区举办了多次经贸洽谈会,当地政府花了很多钱,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外商来了很多,签订的协议、合同虽然不算少,但真正能履约的为数极少。大多数外商都是抱着看一看的目的来的。我们于1993年到新疆富蕴县调查时,据称他们曾努力寻求外资,多次邀请外商前来洽谈共同开发矿产资源,花了不少钱,但都因为基础设施太差而告吹。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应该为西部地区排忧解难,制定较东部沿海发达地区更有利于引进海外资金、技术、人才的各种优惠政策;通过各种渠道,鼓励海外企业家(尤其是港台等地的企业家)到西部地区投资。
另一种外源性变迁模式是在一个国家内,落后地区引进国内发达地区的资金、人才和技术以求得发展。在目前情况下,在难以引进国外资金的西部地区,则应走第二条外源性发展的道路,即大量引进国内发达地区和科研单位的资金、技术和人才的道路。
西部地区矿产资源丰富,近十多年来,西部地区和东部地区联营,或引进发达地区和科研单位的资金、技术和人才而获得成功的事例屡见不鲜。下面以1993年和1995年我们在新疆调查的材料,说明西部地区引进国内技术、人才和资金的重要性。
富蕴县地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北部,全县居住着哈萨克、汉、维吾尔等民族8万余人(1990)。它以矿产资源蕴藏丰富而有其名。1990年,富蕴县之所以在短短的几年内取得如此之大的发展,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引进国内的科学技术、人才、资金,并与丰富的矿产资源相结合。富蕴县1986年全县的黄金产量仅1000余两。自1988年开始由个体开彩向集体、国营开采转变,由手工开采向机械化开采转变。1989年,富蕴县政府为充分开发矿产资源,与地矿部低品位堆浸中心和新疆地质矿产局第四地质大队合作,在一个名为萨尔布拉克的地方进行堆浸提金科技试验,进行机械化开采,采用先进的采金技术——堆浸,当年堆浸矿石2.4万吨,产出黄金2000余两。在此基础上,1990年建成全国最大的低品位金矿石堆浸工程,堆浸矿石10.7万吨,浸出率为90.06%,总回收率达87.75%,生产黄金1.1万余两,成为新疆第一个黄金万两县,同时也成为全国第一个堆浸黄金万两县。在短短的几年内,黄金产量猛增10倍。此后黄金产量年年增长,直至1994年,黄金年产量都在万两以上。
引进技术、人才、资金与资源优势相结合的另一成功事例是富蕴县珠宝公司。该公司于1987年3月组建,与地矿部技术开发公司合资生产经营,引进日本先进的珠宝加工技术和设备,于9月开始投产。当年产值10余万元,利润1万多元。此后,产值和利润成倍增加。1988年产值30多万元,利润5万多元;1989年产值50多万元,利润12万元;1990年产值80多万元,利润17万元;1991年产值121万元,利润21万元;1992年产值280万元,利润41万元;1993年产值500万元,利润50万元;1994年产值514.28万元,利润27万元。1992年初在福建莆田市成立分公司,在上海、大连、南京、云南等地设立了经销点,产品远销日本等国,经济效益十分明显。
与上述两个成功范例相反,有的企业由于未引进科学技术,未与科研单位和先进企业联营,结果造成亏损。如县黄金公司“龙江”一号溜槽,虽然引进了先进的机械化设备,但因缺乏人才和技术,在无可靠地质资料的情况下,盲目上马。尽管实行科学的管理制度,调动了职工的积极性,提高了机械运转率,也无济于事,导致企业连年亏损。1990年处理矿石近4万立方米,只产金4.8公斤,亏损3万余元。
在国家目前难以向西部投入大量资金的情况下,最富前景的是东西部互助互利的经济合作。国家和政府应通过各种方式,进一步鼓励东部发达地区及国内各科研单位与西部地区对口支援,促成西部的资源优势与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的科技、资金、物资、人才等优势相结合,互通有无,联合开发。这样,既能使西部地区的经济、文化、科技得到迅速发展,并培养和造就当地一大批技术和管理人才,又能使东部地区经济发展具有强大的资源基地,从而增强综合国力,同时也可以促进文化交流,增进相互了解,加强民族团结。
以上事例表明,实现西部地区现代化重要途径之一,就是努力与国内科研单位和先进企业联营,引进发达地区的资金、人才和先进技术。
然而,西部地区地广人稀,气候恶劣,尤其是边疆民族地区,远离大中城市和铁路线,市场狭小,运距远,运费高,经济效益差,致使许多内地和沿海发达地区的企业不愿与西部民族地区联营,有的企业或单位即使与民族地区联营,但并不是真正出于支持和帮助少数民族地区目的出发,一旦联营企业效益不佳,便终止合作。据郝时远等人调查,内蒙古新巴尔虎右旗从1988年起,与北京矿冶研究院合作,兴建贵金属冶炼厂,1991年建成正式投产,冶炼粗铅、精铅及白银等。当年冶炼精铅2000余吨,企业赢利30多万元。由于多种原因,从1992年起,贵金属冶炼厂出现亏损并且亏损额逐年增加,于是双方终止了合作关系。〔6〕国家应采取各种措施,鼓励科研单位和大中型企业积极与西部边疆民族地区联营,共同开发资源。科研单位和各企业也应本着共同富裕、扶持民旅地区经济发展、维护祖国统一的精神,要像五六十年代支边干部不斤斤计较个人得失那样大力支持边疆建设,共同开发边疆。
2.增进交流
缩小东西部差距、增强外源性变迁的深度和广度的另一重要方式是增进交流。人类学家认为,文化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之一是文化交流,因为文化交流能够使各种文化形态增生出许多不被自己地理环境所羁绊的、从更高层次上超越这种地理环境的文化因素。各种文化相互交流,可以相互学习,取长补短,较高的文化必然会影响较落后的文化,从而使两者的文化逐步接近。如果文化交流面较大,较频繁,则不同文化的接近和整合也就越快。世界上各种文化,都是多种文化的混合物,其中有自身固有的,也有相当部分甚至大部分是外来的。市场经济是开放、交流的经济,它必然会打破各地区、各民族间封闭的壁垒。市场经济越发达,社会便越开放,地区之间、民族之间的交流也就越频繁。社会的开放,族际之间的频繁交流,必然会使各族之间相互理解、认同和接近,并导致文化的传播和相互采借,吸收各自的文化精华,逐步缩小经济和文化上的差距。东西部通过广泛的交流,才会了解相互之间的差距和不足,从而才有可能逐步缩小差距。
文化交流的形式有多种。其一是科学技术交流,有计划组织东西部科技人员进行交流,共同探讨西部在科技上存在的问题。其二是信息交流,组织信息、采购、销售人员等进行多层次的交流,互通信息,以便使西部地区更好地了解国内外市场情况。其三是商品交流,组织东西部商品交流会,可使双方了解各自的优势商品,同时也可使双方明了自己与他人的商品在质量上的差异。其四是人才交流,它可分为两种形式,一种是人才培训,东部发达地区应负起培训西部地区科技和管理人员的责任;另一种是人才调动,东西部互调,可以是长期的,也可以是短期的。
人口流动也是文化交流的重要形式之一。应当保护合法的人口流动,保护西部地区的少数民族到内地和沿海发达地区从事正当的商业、饮食业等。西部民族地区到内地和沿海发达地区从事各种行业的少数民族,对西部地区的经济繁荣和发展,起到了有益的补充和推动作用。其一,使他们开阔了眼界,解放了思想,更新了观念,学到了新的技术和知识,成为有胆识、会经营、懂管理、技术的市场经济人才;其二,他们通过在发达地区进行合法的劳动,积累资金之后,回到自己家乡兴办各种企业,把自己学到的各种技术和知识带回家乡,推动家乡经济的发展;其三是扩大了就业门路,增加了收入,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贫困问题。当然,人口流动虽然对当前社会稳定造成一定的影响,但这是暂时的,并不会影响大局。从长远来看是有利的,它有利于各地、各民族间文化的整合,有利于中华民族意识的巩固和发展。人口流动有一个适应、冲突、整合过程,对于流动人口,不能因为他们与社会发生一些冲突便加以限制,尤其是少数民族到内地和沿海地区从事正当行业的人员,不仅不能限制,而且要加以鼓励和保护。
多层次、多渠道扩大东西部的交流,无疑将会逐步提高西部地区的科技水平、信息水平,丰富经营管理经验,增强竞争意识,对西部地区的发展将起到较大的推动作用。
(三)强化内源性变迁:西部发展的基础
现代化发展的两种形式——外源性变迁和内源性变迁,对于不同国家和不同地区的发展进程具有重要意义。但不论是哪种情况,发展只有在社会内部的发展潜力被广泛有效地动员起来之后才有现实可行性。这两种发展进程并不是完全对立的、纯粹的,而是相互关联、相互制约的。即使是内源的现代化也是处在国际性因素交互影响之下,不是封闭性的自我转变,任何国家、任何地区都不可能单独实现向现代社会的转变。
西部地区由于种种条件的制约,主要通过外源性变迁而实现现代化是不现实的,也是不可能的。西部地区应在扩大引进和交流,增强外源性变迁的深度和广度的情况下,脚踏实地进行内部改革和调整,注入新的文化元素,使自身的文化和社会充满活力,不断地向前发展。
内部变革表现在多方面,一是硬件的现代化,如基础设施、生产机器等的现代化。二是软件的现代化,如人的各种观念、意识的现代化,各种社会制度的改革和完善等。
对于西部地区来说,硬件现代化的重要一环是基础设施现代化,这也是自身发展的最重要的物质基础。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实施了各种改革措施,充分调动了农牧民的积极性和责任心,西部地区的农牧业生产发展很快。例如我们在1993年调查的新疆富蕴县,从1978年到1990年,农牧民人均纯收入由147元增至628元,年平均增长27%。但是,进入90年代以来,发展速度明显减慢,甚至出现负增长。如1993年牲畜最高饲养量达79.02万头(只),由于冬天大雪牲畜损失4万多头,1994年最高饲养量只有74.53万头(只)。90年代以来农牧业发展速度之所以减慢,其主要原因是基础设施太差,经济发展后劲不足。十多年来各级政府的投资、贷款主要集中在建工厂、办企业、盖楼房和城市建设等方面,即把钱主要用在短时间内能见到效益、能看到政绩的那些方面,对基础设施的投资不仅很少,而且有逐年减少的趋势。特别是近几年,各级政府的财政十分困难,无力搞大规模的基本建设。由于基础设施投入少,水利、电力、交通、能源、草原和农田基本建设仍相当落后,成为制约经济进一步发展的主要因素。
内蒙古是我国最大的牧区之一,但长期以来,对畜牧业生产基础设施和草原建设不够重视,靠天养畜意识仍然较严重。由于缺乏草原建设资金,80年代末以来草原退化严重。呼伦贝尔草原是全国最好的草场之一,据中国科学院1962年调查,全盟退化草场面积占总面积的12.4%,到1988年则增至21%。其中新巴尔虎右旗退化草场面积最广,1988年已达873.59万亩,占该旗草场可利用面积的28.9%。由于草原基本建设差,草场退化,超载严重,致使牧业生产难以抵御自然灾害的侵袭,导致牧业生产出现多次大起大落的现象。蒙古族古谚云“十万白音(意为拥有10万头牲畜的富翁),一场暴风雪成为穷人。”〔7〕这正是天然畜牧业脆弱性的真实写照。
西藏和平解放以来,国家对农牧业生产基本建设的投资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效果显著1952年至1985年的34年间,全区用于农牧业的总支出为8.81亿元,平均每年投资2600万元。据1986年不完全统计,仅水利建设一项,全区共建各类水库(塘)5000余座(不含报废数),总库容3898万立方米(不计复蓄指数);机电提灌站102处,总装机容量3970千瓦;万亩灌溉区13处,配套机井106眼,灌溉水渠1万余条,保灌农田127万亩。在畜牧业建设方面,灌溉草场20多万亩,建网围栏面积280万亩; 改良退化草场100万亩,人工种草60万亩。此一期间的农牧业基本建设对提高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促进农牧业生产的发展所发挥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但是,自80年代后期以来,虽然农牧业生产基础设施投资绝对额达历史最高水平,而占财政支出比例则明显下降,有一半以上的经费被事业费吃掉。生产建设资金不足,水利设施年久失修,草场沙化严重,造成农牧业生产长期徘徊不前。在90年代初,基层已发出“再不增加投资,农牧业三年后就会萎缩”的呼声。〔8〕
甘肃肃南裕固族自治县从1987年和1989年开始,存栏牲畜总数和牧业产值相继出现连续负增长的现象。存栏牲畜总数1987年增长-1.5%,1988年增长为-1.92%,1989年变为-1.15%,1990年为-2.31%,1991年为-12.13%,1992年为-3.99%;牧业产值1989年增长-2.35%,1990年为-3.85%,1991年为-1.68%,1992年为-6.1%。出栏牲畜的平均肉产量自1983年至1988年一直呈上升趋势,但从1988年至90年代初,则呈下降趋势。1983年出栏牛平均产肉60公斤,每只出栏羊产肉12.5公斤;至1988年,每头出栏牛平均产肉增至108公斤,每只出栏羊平均产肉增至17公斤。1988年后开始出栏牛羊的肉产量逐年下降,1992年每头出栏牛平均肉产量比1988年减少48公斤,每只出栏羊肉产量比1988年减少5公斤。其主要原因是牧业生产基本建设投资不足,无力进行草场建设,草场退化,牲畜超载,从而造成牲畜抗病能力差,产肉量减少。〔9〕甘肃甘南藏族自治州牧区由于地方财力有限,入不敷出,缺乏草场建设基金,国家投资又逐年减少。“八五”期间,国家对甘南牧区草原建设投资平均每亩只有2分钱,造成草场质量下降,草畜矛盾突出。据90年代调查和测定,牧区草场平均每亩产鲜草量由50年代的426公斤下降到336公斤,下降21%。退化草场达数百万亩,重度退化草场比一般草场的产草量下降50-60%。现在人工和半人工草场仅有70万亩,每个羊单位不足0.1亩。据测算,平均建设每百亩围栏草场的费用为2000多元,按每户建设500亩围栏草场计算,每户负担在万元至数万元以上,加上建设住房、棚圈、人工种草等费用,数额更大。〔10〕
西部地区是十分缺水的地区,水利建设最为重要。新疆、内蒙古、西藏、青海和甘肃等省区的牧区辽阔,牧业人员占有较大的比例,但由于水利建设没有搞上去,无法在适于定居的牧场大面积种草和打贮饲草,因而也就无法定居或半定居,大多数牧民仍然过着原始的逐水草而徙的游牧生活,如不大力发展水利建设,就难以彻底改变落后的游牧生产方式。新疆富蕴县是新疆的牧业大县,但80%以上的牧民仍过着逐水草迁徙、居无定所的游牧生活,一年搬家上百次,一年四季的迁徙路程为七八百公里。而要改变这一生产方式,就必须搞好草原水利建设。如果牧民实现定居或半定居,牧民的生活方式就会发生一系列的变化,科学技术和文化教育将会得到迅速发展,从而也能改变游牧民族的文化模式。
搞好水利、交通、通讯、能源等基础设施建设,是西部开发和起飞的前提,也是西部现代化的准备阶段。它不仅能为自身的发展打下基础,同时也为更好地吸引国内外资金、人才和技术创造了条件。然而,西部各省区地域辽阔,自然环境复杂,搞好基础设施建设需要大量资金。而西部地区财政入不敷出,无力进行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在这种情况下,应动员全国的力量,尤其应动员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给予支持。从历史上看,历代王朝管理新疆、西藏和蒙古地区,俱投入了一定数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在汉代初期,国泰民安,“都鄙廪庚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11〕此说明当时从京师到地方钱粮积累之巨,生活之富。而至汉武帝时,有大批匈奴人来降,为资助他们的生活和生产,“县官费众,仓府空。”〔12〕汉武帝还把大量钱财赏赐与匈奴,把匈奴视为骄子。《史记·汲黯传》:匈奴“浑邪(王)率数万之众来降,虚府库赏赐,发良民侍养,譬若奉骄子。”在生产和生活上竭力资助,毫不吝惜,《史记·平准书》:“胡降者皆农食县官,县官不给,天子乃损膳,解乘舆驷,出御府禁藏以赡之。”此外,汉朝中央政府还帮助西北地区大搞水利建设,挖渠引水。《史记·河渠书》:“……用事者争言水利。朔方、西河、河西、酒泉皆引河及川谷以溉田;……佗小渠披山通道者,不可胜言。”清人王国维在《观堂集林·西域井渠考》中认为,今新疆的坎儿井,源于《史记·河渠书》所记载的陕西的“井渠”,是汉代的关中一带的“秦人”教给他们的,他引《史记·大宛列传》所记的一个传说为证。《新疆图志》载林则徐被贬戍新疆时,帮助新疆各族开凿和推广坎儿井。该书卷114《林则徐传》:“尤以创凿吐鲁番坎儿井为最,吐鲁番为古火州,其地亘古无雨泽,周礼用水作田之制,无从施设,则徐思得一法,命于高原掘井,而为沟导井以灌田,民间名之曰:坎遂,变赤地而为活壤焉。”同书卷2《建置》又载:“初吐鲁番有灌田久芜,云贵总督林则徐谪戍伊犁,始浚托克逊及伊拉里克等渠,复增穿井渠通水,民用温给。”下有夹注:“谨案:井渠者俗名坎儿,……此法盖始于汉,而林则徐复兴之。”清政府统一西北地区之后,采取一系列错施,支持边疆发展经济。如对蒙古地区只取“九白之贡”,不收赋税。此外,采取救济灾荒、建立仓贮、派人传授生产技术、发放农具和种籽等促进生产发展的措施。康熙三十七年(1698),康熙派原内阁学上黄茂等前往内蒙古巡视,并谕令其“查明无生计者赈给之”,并“教之引河水灌田”。〔13〕对西藏也一样,采取免税、减轻劳役、赈济等政策,扶助其发展经济。清政府规定,西藏两年进贡一次土特产,表示对清王朝的臣属,但免其所有赋税。同时,还以赏赐的名义,给予西藏地方大量财政补助,每年照例将打箭炉等地方税收5000两白银和大批茶叶等赏赐给达赖、班禅。乾隆六十年(1795),清政府还拨银4万两赈济灾民。〔14〕
清政府平定准噶尔之后,即决定对新疆地区“薄取其赋,除去准噶尔一切苛政”,维吾尔族等族“大悦”;〔15〕并支持新疆发展工矿企业,采铜、炼铁、采煤等。1772年清政府批准陕甘总督文绶提出的新疆“屯田五事”,即屯垦、发展商业,修路和修渠等:“一、招新疆商贾、佣工之人,就近认垦,以省资送;一、指明新疆地名、道里情形,晓谕民户,以期乐从;一、乌鲁木齐大路数丈,请修治宽阔,以利行旅;一、安西沟渠应疏浚畅流,以益灌溉。”〔16〕此外,各省和海关每年均需上交“协饷”,以支持新疆地区。新疆财政,在清代全赖外省“协饷”维持。新疆第一任巡抚刘锦棠称:“祖宗朝平定准、回两部以来,关外用款向赖内地协济。”〔17〕清代新疆建省之前,各省“协饷”,均先解送陕甘总督处,然后每年按旨意调拨新疆各处。《清实录》对此有大量的记载。如道光二十三年1841),清廷于9月12日、9月14日、9月16日、9月21日、10月18日、10月27日、10月28日、11月17日多次谕令陕甘总督拨银解往新疆各地。〔18〕其他年份也一样,年年如此调拨,《清实录》记述甚详。
新疆收复之后,各省和海关亦照常给予“协饷”。只是由于内乱纷起,各省和海关未能正常将“协饷”解赴新疆。据《新疆图志》载:“新疆每年原分协饷二百四十余万,均系计口授食之需。自二十六年拳匪肇衅,各省关只解到银一百七十八万余。二十七年只解到银一百六十五万余,二十八年亦只解到银二百五万余。”〔19〕《清德宗实录》载有大量的关于新疆催解各省关“协饷”的奏折。在新疆第一任巡抚刘锦棠的奏折中,有不少是奏催各省关尽快解赴“协饷”的。如光绪九年(1883)九月初八日《饬各省关赶解协饷折》中称:“各省关欠解西饷极多,……自正月至六月,湖南已及五成,河南及闽海、江汉两关已及四成,江苏、江西、安徽、四川已及三成有奇。其余浙江、山东、山西、广东、湖北、福建等省成甫及一、二成,又或一成未及,并全未起解不等。综计共报解银二百四万九千余两。……新疆经算年需实银四百万余两,系属必不可少。……恳天恩饬下各省关督抚、将军严饬藩司、监督,将九年(即光绪九年)分的饷,并户部限提积欠之五十万,如数提前起解。”〔20〕
新疆每年财政由内地各省关支持外,建城和衙署亦赖内地支持。如光绪十四年(1888)南疆修城和衙署共28起,共需银37万余两,均由清廷指派各省关解银。刘锦棠于光绪十四年十月二十三日奏称:“于光绪九年奏修南路城工十三起,衙署十五起。……估银三十七万四千余两。蒙恩饬部指拨各省关银三十六万六千七百余两。……尚欠解一十九万余两。现在挪用军饷,急须划还借款。……请饬下各省关,赶将下欠银两悉数提解,俾得清还欠款。〔21〕
此外,清政府还筹款赈济灾民。如乾隆三十六年(1771),蒙古士尔扈特台吉渥巴锡率部众数万,跋涉数万里东归,清政府即“指地安插”,“赐以封爵”;〔22〕并“赏给土尔扈特归顺人众羊只皮衣等”。〔23〕同时,为保障他们的生活,自东归后便供给口粮,直至乾隆三十七年(1772)六月。〔24〕
光绪初年,阿尔泰地区的蒙古人“连年瘟及牲畜,不可胜数,以致穷苦万状,生计全无。”〔25〕光绪九年(1883)二月,伊犁将军金顺等奏报需要抚恤、救助的人数及办法,并预算救助款项约需7万余两白银。奏折称:“复查蒙民向以牧养为生计,该处……所遗牲畜迭年瘟死倒毙殆遍。其东界蒙古牲畜,现时所存无几,困苦不堪言状。……奴才等悉心筹虑,抚恤蒙民惟有筹款购牛羊,散给以资牧养。然既为蒙民计,能不为国家计乎。总之,处此时艰,库款未充,自应力求撙节,必使恤所当恤,减所当减,详加分别,酌量抚恤。庶帑项不致虚糜也。前据乌梁海散秩大臣等奏报,西界蒙民男妇老幼约计七千余名,内除稍有牲畜,聊可自给者一千数百名,又除大小婴孩约七百余口。以上二项应无庸抚恤外,其余极苦无牲畜者五千余名。奴才等拟将此项极苦蒙民,量力抚恤,按二名赏给乳牛一只,每一名赏给乳羊五只,以备牧养滋生,取乳度日。且砖茶乃蒙民一日必不可少之物,按每名酌给砖茶二块,以资食用,如此抚恤,则蒙民均沾实惠,感戴皇恩无涯矣。再,查西界哈夷,约计二万余人,及东界蒙、哈,其中贫苦者,尚未计其多寡,虽不能与前项蒙民之比,亦当随时查察,择其极苦者,量加抚恤,用彰朝延一视同仁之至意。窃思抚恤蒙、哈,采买牲畜砖茶……等项,通盘合计约需银七万两。……亟应请旨饬部,无论如何,款先行筹,拨银七万两。”〔26〕清廷接折后即饬户部拨给所需银两。〔27〕
由上可见,西部地区在历史上多无力自给,都必须靠国家和东部及内地各省区的支持。在20世纪之末,各兄弟省区,特别是东部和沿海发达地区,更应该认识到发展西部地区的重要意义,进一步从财力、物力和人力上大力支持西部地区的现代化建设。
三、经济和文化发展相协调
(一)文化模式与经济发展
人类学家在研究社会和文化时特别强调全貌观或整体观(holism),即强调一个社会中各种不同层面的因素之间的关联性。美国人类学大师博厄斯(F.Boas)的弟子、人类学家和语言学家萨皮尔(E.Sapir)认为人类的行为与语言的语法一样,在不知不觉中形成一种“模式”(pattern),这种模式在文化上即成为一个社会的“风尚”(style)。一个民族或一个社会的文化,都具有与众不同的模式。博厄斯的另一个弟子本尼迪克特(R.Benedict)在萨皮尔研究的基础上,较为具体地提出“文化模式”理论。她认为一种文化和一个人一样,各有其大体一致的思想和行动的模式。每个民族,由于心理特点不同,具有自己独特的文化模式,每一种文化模式都是一个独立的体系,有共同的民族性格和文化行为,有其不同其他文化的突出的一面。两种文化的不同,并不是因为一个或若干特质的有无,而是因为许多特质的趋向不同。因此,文化人类学家所要研究的单位,并不是文化特质或社会制度,而是一个社会的整体的文化模式。博厄斯的另一个弟子克罗伯(A.L.Kroeber)从文化结构和文化功能的角度解释文化模式,把文化中的那些稳定的关系和结构看成是一种模式,并把文化模式分成四种类型。
虽然人类学家对文化模式的解释不完全相同,但都认为,不同社会都具有不同的文化模式,同一文化体系内的各部分都是相互关联、相互作用的。所以,在考虑某一地区或某一民族的经济文化发展时,不能不考虑其文化模式中的结构和功能,应注重某一民族的文化模式中的各个方面的协调发展,才能保持社会体系的和谐,才有可能使整个社会持续、稳定地发展。
中国东部的文化模式与西部的文化模式就有很大的差别。即使是西部地区,各民族的文化模式也各有特色,如藏族文化模式就与维吾尔族的文化模式有明显的不同。哈萨克族与维吾尔族虽然同属突厥语族,信仰同一种宗教,但由于经济生活不同,维吾尔族主要从事农业,而哈萨克放主要从事牧业,其文化模式也有所不同,民族性格和文化行为都表现出较大的差异。
经济是文化的基础,有什么样的经济形态,就有什么样的文化形态。农业经济必然形成具有农业特色的文化模式,游牧经济也必然形成游牧特色的文化模式。同样,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人们所形成的是具有计划经济特色的心理特征和行为模式,如“大锅饭”,“铁饭碗”,“官本位”,“等、靠、要”等观念,都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产物。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人们所具有的是“开放”、“竞争”、“高效”、“创新”、“进取”等观念和意识。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不能只考虑体制的转换,同时应考虑心理、意识和行为方式的转换;不能只考虑发展经济,同时应考虑发展和变革民族文化的其他方面。
(二)传统文化模式——现代文化模式
尽管每一种文化有其自己的模式,但各种文化模式也有其共性,即传统性与现代性。因而从文化的这种性质来看,文化又可分为传统文化模式与现代文化模式。所谓传统文化模式,即与农业为主的社会相适应的社会文化模式,它具有保守性、专制性、宗教性、封闭性、地域性、集体性、延续性等。所谓现代文化模式,即与现代发达社会相适应的社会文化模式,它具有商品性、竞争性、民主性、科学性、世俗性、开放性等等。
在现代化过程中,传统文化模式如何向现代文化模式转换,是学术界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事实上,两者是既离不开、也摆不脱的。“传统与现代性是现代化过程中生生不断的‘连续体’,背弃了传统的现代化是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化,而背向现代化的传统则是自取灭亡的传统。”〔28〕现代化的本质,是适应现代世界发展趋势而不断革新。但现代模式不可能建立在空中楼阁上,必须在传统模式基础上进行构建和创造。历史上成功的现代化运动大多是一个双向运动过程,即传统因素与现代因素相反相成,既善于克服传统因素对现代化运动的阻力,也善于使传统文明转换成现代文明。正如金耀基先生所说:“中国的现代化所意含的不是消极地对传统的巨大摧毁,而是积极地去发掘如何使传统成为获取当代中国目标的发酵剂,也即如何使传统发生正面的功能。”〔29〕
改革开放十多年来,中国西部地区各民族的传统模式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逐渐向现代模式转换,但其转换速度远不及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缩小东西部差距,必须十分重视各民族的传统模式向现代模式的转换。
传统模式向现代模式转换,首先必须分析哪些文化因素是与现代社会相适应,应该继承和发扬的;哪些文化因素是阻碍现代化建设,应该抛弃的;哪些文化因素虽然看来已经过时,但与现代化建设没有冲突,仍可以保留的。例如,礼俗文化,时代性不强,与现代化没有多大冲突。各个发达国家的礼俗文化均不相同,它没有共同的模式。而许多习俗,如塔吉克族路不拾遗,夜不闭户,不偷、不盗、不抢的良好的社会风尚,正是当前精神文明建设所十分需要的,不仅不能抛弃,而且应该大力弘扬和光大。再如哈萨克、柯尔克孜等族的好客习俗,相互济助习俗,扶弱帮穷习俗,集体主义意识等;维吾尔、乌孜别克等族的经商意识,敬老意识,乐助人、轻回报等意识,都是现代社会所需要的。有些文化现象,如宗教信仰,虽然缺乏科学性,但它在世界各国的现代社会中普遍存在,正当的、合法的宗教信仰并不与现代化相冲突,重要的是如何由宿命论、迷信和宗教狂热向理性化、世俗化转变,使宗教信仰成为一种纯粹的精神寄托。当然,与现代化不相冲突的各种传统文化因素,也不能丝毫不动地继承下来,而应当加以革新,使之更有利于现代化的发展,使其升华为更高一级的文明。
西部地区传统模式向现代模式转换的关键是改革与现代社会不相适应的各种传统文化因素。它主要表现在如下几方面:
其一,商品意识差。由于封闭、单一的自然经济,西部地区的不少民族历史上没有形成过真正的商品经济。在本世纪50年代前,与其他民族和内地的交换主要是以物易物,以马、牛、羊、羊皮等畜产品换取布、盐、茶、粮食和日用品等。这种交换方式仍属于原始的贸易方式。50年代前,在哈萨克、柯尔克孜、藏、鄂伦春、鄂温克等民族中几乎是找不到商人。他们耻于经商,羞于经商,甚至认为经商是低贱的,瞧不起商人,认为通过做买卖赚别人的钱是不道德、不光彩的。自己财物有剩余的话,宁可送人,也不愿意出售给别人。这种重义轻财、轻商贱利的古朴的民风长期延续了下来。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自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来,随着市场、物价的放开,大量个体商贩的涌入,使广大牧民饲养的羊、牛、马及其畜副产品有可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商品的机会,西部地区的一些民族传统的思想观念才有了较大的变化,有了初步的商品意识。但与东部地区的汉族比较起来,仍然差别很大。尤其是牧区,更为明显。牧民卖羊给个体户,不是按重量,而是按头数估算,也不会讨价还价,觉得价钱比国营单位(如食品公司等)高一些就成了。各种畜副产品也不会加工成商品出售,以很低的价钱卖给个体户。
其二,竞争意识淡薄。本世纪50年代前,西部地区的不少民族民风淳朴,与世无争,有乐且乐,知足常乐。50年代后由于长期在体制上实行“一大二公三统四平”的原则,缺少竞争机制,干和不干一个样,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在这种情况下,没有竞争的环境和条件,因而也就无法形成相互竞争的意识。改革开放以来,在其他民族的影响下,原来不会经商的民族的一些人开始走出毡房,学做买卖,出售羊肉、畜副产品、刺绣品等,有的还开起了饭馆。但从事这些商业活功的人毕竞很少,无法与东部地区的民族相比。尤其是牧区,自己养了很多羊,但自己不拿去卖,以很低的价钱卖给其他民族的个体户,如果他们经营意识、能力强,直接把牲畜或肉拿到市场上出售,将会增加一大笔收入。
竞争意识淡薄的另一种表现形式是不会与其他民族竞争开发自己身边土地上的各种宝藏。新疆地区有许多矿产资源,有金、宝石等珍贵矿产,有许多名贵药材。80年代起,“采金热”、“采宝石热”兴起,内地的汉族、回族等个体手工开采者蜂拥而至,但当地民族自己不去开采、挖掘,只会看着别人在土地上淘金、挖宝石和挖药材等。市场经济是竞争的经济,如不提高竞争意识,就无法在激烈的竞争中生存。
其三,依赖意识严重。它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依赖自然,靠天吃饭。西部地区是国家的主牧区,大多数牧民至今依然是靠天养羊,过着千百年遗传下来的“逐水草而徙”的游牧生活。他们自己不想去改变也没有能力去改变这种落后的生产方式。二是依赖国家,“等、靠、要”意识产重,近几年来西部一些地区出现争当贫困县的反常现象。有的县被列为“贫困县”后,反竞相庆贺。在东部和沿海,“官本位”的观念越来越淡薄,而在西部,“官本位”观念依然很浓。我们在新疆调查时,了解到不少优秀教师弃教从政,而不是像其他地区那样弃教从商。在东部和沿海发达地区,遇事找市场,出钱买咨询,逐渐养成一种习惯,而在西部地区,从生产到出售,从柴米油盐到婚丧嫁娶,个人事、家事、村事、乡事,无事不找政府和领导。如不改变依赖、依附意识,不树立自主、自信、自强的现代意识,西部地区的发展是比较困难的。
其四,积累和再生产意识缺乏。按照一般的观念,人们收入的增多就能促成较多的储蓄及更多的投资,从而使生产得到更大的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也就会不断地提高。这一有利的经济循环是完全合理有效的。但一些地区或一些民族的价值观念却不同,他们认为收入的增多应该首先用于娱乐和吃喝,何必把金钱累积起来或拿去投资呢?这样,理性的经济循环便在此中断了,生产也就无法进一步发展,现代化也就遥遥无期。例如,居住在马来西亚半岛南部的柔佛州(Johore)的马来人,以种植橡胶为生计,他们大多居住在交通不便的山麓地区,种植古老的低产橡胶树,生产方法也十分原始,因此,生活水平极为低下。1957年,马来西亚独立后,政府努力发展农村经济,贷款给这些胶农,换种高产优质的新橡胶树。另一方面政府又开辟公路,发展交通,以便降低运输成本。这些努力都完全合乎现代经济的发展原则,而地方政府在执行政策时也很认真。数年之后,新树已出胶,公路也修到各乡村,但胶农经济状况并未改善,平常的生活比以前更困难了,发展农村经济的计划大半落空。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细加考察之后,发现妨碍这一计划实现的主要原因是马来人的价值观念和传统的生活态度。在新树产胶和公路修通之后,农民的收入确实增加不少,但马来农民并未利用这些增加的收入再投进促使经济进一步发展的生产中,而是完全用于娱乐上。原先在公路未通之前,他们或是每周或两三周到镇上去看一次戏,公路畅通后,他们可以每晚都到镇上去看戏,这样,所有的收入都花在娱乐上了。〔30〕中国西部地区的一些民族的价值观念也与此相似。据我们调查,西部地区牧区自牲畜作价归户以来,牧民的牲畜头数迅速增加但牧民真正富起来的并不多。不少家庭有温饱就心满意足了,不思积蓄,不求发展。他们不是把剩余的资金积累起来和扩大再生产,而是花在送礼、喝酒、奢办婚丧嫁娶等活动上。不少人一旦手中有钱,便买酒畅饮。一旦有客人到来,便宰羊招待。不少人在婚丧喜庆中互相攀比,大吃大喝之风愈演愈烈,有些人一年辛勤劳动的成果有很大部分花在炫耀性的浪费上,用于人情应酬上。若谁家有喜庆宴客,不待主人邀请,也不管平时是否与主人认识,自已就去;过往路人往往也应邀入席,共同吃喝,一视同仁。这样,一年到头送不完的礼,喝不完的酒,收入大部分花在请客送礼等方面。在物质财富还不很丰富、人们生活还较困难的情况下,这种“穷大方”、“穷体面”、“比排场”的做法,过多地消耗了不太丰富的社会财富,制约了扩大再生产的能力,严重影响了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阻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
经济是文化的基础,每一个民族都在其经济基础上形成具有特色的文化模式。在这个文化模式内,各部分是相互关联、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的。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必须与文化发展相协调,亦即物质文明建设必须与精神文明建设相协调。
四、结 语
综上所述,逐步缩小东西部的差距,防止两极分化,是保障国家统一和稳定的重要一环。西部地区自然环境、人口素质、价值观念和生活态度等都与东部地区不同,其发展模式也不可能相同。西部地区如果没有国家和东部发达地区的支持,是无法跟上现代化潮流的。西部地区的发展,必须采用外源性变迁和内源性变迁相结合的方式,只靠一种变迁的方式是难于发展西部地区的。在有条件的地方,应大量吸收国外资金、技术和人才;在无条件的地方,应主要引进国内发达地区科研单位的技术、人才和资金。在目前情况下,自身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搞好基础设施,完善内部发展的机制,是西部发展的重要环节。只有内外两方面共同发挥作用,西部地区才有可能实现经济和文化现代化。
从文化的角度来看,人的观念是文化的核心,是文化的深层结构。人的观念的发展、变化,必然引起整个文化模式的变迁和转换。也就是说,传统文化模式向现代文化模式转换,关键在于人的观念的现代化。从社会的角度来看,社会是由各种社会团体组成的,而各种社会团体是由人组成的。社会经济的现代化,最重要的是人的现代化。社会经济的现代化与人的现代化应该是同步的,密不可分的。我们不可能先进行经济现代化建设,然后再去造就现代化的人;也不可能先造就现代化的人,然后再进行经济现代化建设。从现代化的构成因素来看,现代化的主体是人。没有人的现代化,就谈不上真正的现代化。在现代世界上,有不少国家,虽然资源相当缺乏,但却早就进入了现代化国家的行列;也有不少国家,蕴藏着丰富的地下和地上资源,而没有成为现代化的国家。这些都与人是否现代化密切相关。中国西部地区如果没有人的现代化,优越的自然资源也就不可能转化为现代化的生产力。干部和群众不转换与现代社会不相适应的传统的心理和行为模式,不仅无法跟上全国现代化的潮流,甚至连自已原有的优势也可能丧失。因此,必须在经济现代化建设的同时,通过各种方式革新人的观念,丰富科学知识,使之逐步成为现代的人,从而使其传统的文化模式转换为现代的文化模式。人的观念的革新,首先应变更价值观念和生活态度,努力提高人们的竞争意识和市场意识。观念不更新,也就没有勇于改革、勇于进取的精神,也就难以改革不合理的各项制度,难以转换经营机制,难以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知识不更新,就难于在当代高度科学化、信息化的世界中竞争。只有观念现代化,知识科学化,全民族、全社会才有可能现代化。
注释:
〔1〕罗荣渠:《现代化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9—15页。
〔2〕威廉·A·哈维兰著、王铭铭等译:《当代人类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576页。
〔3〕杨国枢:《现代化的心理适应》,台北巨流图书公司1978年版,第24页。
〔4〕Lewis·Osar:La Vida:a Puerto Rican Farmily in the culture of Poverty-san Juan and New York.London,1967。
〔5〕参看罗荣渠:《现代化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16一119页。
〔6〕郝时远等:《中国少数民族现状与发展调查研究丛书·新巴尔虎有旗蒙古族卷》,民族出版社1997年版,第260页。
〔7〕郝时远等:《中国少数民族现状与发展调查研究丛书·新巴尔虎右旗蒙古族卷》,民族出版社1997年版,第233-238页。
〔8〕肖怀远主编:《西藏农牧区改革与发展》,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94-195页。
〔9〕邓艾:《草原牧业的发展与转型——肃南裕固族自治县畜牧业市场化专题研究》,《甘肃民族研究》1994年第2期。
〔10〕罗发辉:《甘南牧区草原建设与发展畜牧业研究》,《甘肃民族研究》1996年第3-4期。
〔11〕〔12〕《史记》卷30《平平准书》。
〔13〕张穆:《蒙古游牧记》卷1。
〔14〕参看张羽新:《清朝前期的边疆政策》,《中国古代边疆政策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
〔15〕松筠:《西陲总统事略》卷1。
〔16〕《清高宗御制诗》4集,卷3。
〔17〕刘锦棠:《请拨部款弥补新疆所欠厘金并接济军饷折》,《刘襄勤公全集》卷4,光绪二十四年长沙刻本,第2-4页。
〔18〕参见《清德宗实录》卷354、卷355、卷357、卷359。
〔19〕《新疆图志》卷51,第23页。
〔20〕刘锦棠:《刘襄勤公全集》卷6第5—7页。
〔21〕刘锦棠:《南路已修成城署,经费恳饬部核销,并请饬催各省关欠解银两以清垫款折》,《刘襄勤公全集》卷15,第42—44页。
〔22〕《清高宗实录》卷892,第51页。
〔23〕《清高宗实录》卷893,第9页。
〔24〕《清高宗实录》卷907,第2页。
〔25〕《科布多办事大臣清安、额尔庆额奏中俄界务重勘情形折》,《清季外交史料》(光绪朝)卷30,第18-19页。
〔26〕《伊犁将军金顺等奏勘分科界必先安插蒙、哈请款抚恤折》,《清季外交史料》(光绪朝)卷31,第28-31页。
〔27〕《清德宗实录》卷162,第17-18页。
〔28〕罗荣渠:《现代化新论》,第376页。
〔29〕金耀基:《中国现代化与知识分子》,香港时报出版公司1984年版,第8页。
〔30〕李亦园:《人类学与现代社会》,台湾水牛图书出版有限公司1984年版,第33一34页。
标签:经济建设论文; 社会因素论文; 新疆历史论文; 新疆生活论文; 中国东部论文; 现代化理论论文; 经济论文; 社会变迁论文; 西部建设论文; 社会企业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