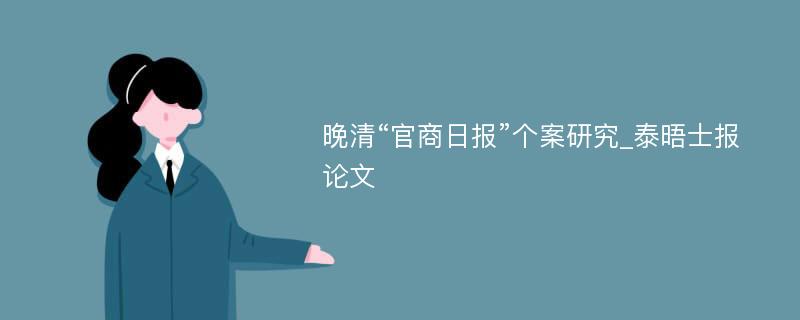
清末“官营商报”案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官营论文,清末论文,商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清末是近代报业急剧发展阶段,也是报案的高发时期。在众多报案中,多见清政府捕人、封馆和罚金等手段,通过官款收买报馆的做法并不常见,抑或多有而不为人知,但“官营商报”案是重要的一例。该案涉及到多个具有全国影响力的报纸,且受到御史、谘议局和报界三股力量披露和追究,一时成为轰动事件,使清廷不得不谕令两江总督张人骏核查此事,最后只好以收回官款,退归商办而结束。“官营商报”案的重要研究价值,不仅仅在于它在众多报案中极具独特性,影响也很大,而且还在于,该案有众多其他报案不具备但却值得关注的新因素。此外,它牵涉清政府的部门较多,是一个观察清末政府与报馆关系的极好案例。由于学界目前尚未有人对该案加以专门研究,故笔者撰此拙文,以求抛砖引玉。 一、垫补商报官款消息的披露 “官营商报”案是清末引起全国关注的一件大案,其信息的披露有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御史胡思敬在参奏端方的折文中提及此事,但没有引起外界的广泛注意。第二阶段,《南洋官报》刊载了垫补报馆款项使用内容的江苏清理财政清单。这样,津贴官款的来源、数额及所受贴补之报馆等具体信息被披露。此后,江苏谘议局议员见此消息后马上提出革除官营商报议案,此后,江苏谘议局不断追查,媒体广泛报道,此案遂成为当时重要的新闻事件。 宣统元年五月初八,御史胡思敬在参劾两江总督端方的折文中,指责端方“贿通报馆”,控诉其“公行贿赂”“营私舞弊”①等十罪二十二款,请求清廷特派查办大臣,调取各部案卷,以备质对。胡思敬在参奏折中提及了端方收买的各报及每年所支津贴的数额,并指责端方此举是为行一己之私。奏折上至清廷后,清廷谕令两江总督张人骏“确查具奏”。与此同时,两江总督端方改调直隶总督,而在两广总督任上的张人骏被调至两江。张人骏接到奏折时已是六月十二日,当时人在广州,尚未来得及接任两江总督之职。因此将调查端方官款结纳报馆等事交于护理两江总督、布政使樊增祥调查。张人骏主导的调查历时半载,直到十一月他才奏覆清廷,称端方“尚无罔利行私”。②也就是说,御史胡思敬参奏端方徇私收买报馆之举,张人骏和清廷并不以此为罪。这样,御史参奏一途,虽对此事有所披露,但并没有使该事件被外界广泛知晓,事情没有被追查下去。 江苏谘议局的介入使事情有了转机。宣统元年九月,江苏谘议局从《南洋官报》所载江南宁属清理财政局移请江南财政总局照覆文中发现,江苏有官款垫补商报行为,并查得官费津贴来源、数额以及津贴的报馆对象。其具体情况是:上海之《中外日报》《舆论时事报》《申报》,或完全是官款或半是官款。各报按月由江苏官方津贴之款,多少不等。上海《泰晤士报》由江苏官方勒派衙、署、局、所,以及官立学堂担任贴款。至于垫款数额,据谘议局查明,宣统元年二月一个月中,给《申报》馆垫款湘平银一万八千九百余两,历年垫入《中外日报》《时事报》等馆者亦为数不小。上海《泰晤士报》由江宁财政局一处津贴银三千六百两,另外还勒令全省衙署、局、所、学堂等各处提供津贴。另外,谘议局还查见各报馆用途未明经费湘平银九千六百两。谘议局对官款垫补报馆一事的最初反应是:“以为官自解其私囊,虽官冒商名,淆乱清议,情理大有不合,然人民无担负义务之关系,业已隐忍相安。”③尽管意识到官方资金贴补民间报馆会淆乱清议,不合情理,但遗憾的是谘议局并没有对此加以追究。但当看到贴补报馆的经费并非官员个人私产而是苏省人民缴纳的官款时,谘议局对此事反应非常激烈,按照《谘议局章程》赋予谘议局的权力,江苏谘议局便开始对江苏官方的错误做法加以制止。以章程第二十三条规定“谘议局议定不可行事件,得呈请督抚更正施行”的权利,谘议局以“宪政”“国法”“税则”和“政体”等标准议定了官款垫补商报行为不可行之原因以及更正方法。至此,“官营商报”案进入谘议局议事日程,谘议局对此展开讨论、调查并形成决议,然后提请江苏巡抚和两江总督对此事回应,该案遂成为重要的政治事件。同时,该案被报纸广泛报道,迅速扩散,也成为报界一个舆论热点。 二、谘议局的纠查 江苏谘议局对官款使用的关注和追查,对“官营商报”一案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江苏谘议局对官营商报一事,反应非常迅速。官款垫补商报的消息刊载于《南洋官报》第55期,其发行时间是宣统元年九月二十日。④议员于定一和钱以振向谘议局提交议案,《时报》馆三十日便在“地方新闻”栏刊出,可见于、钱二人见此官款流入报馆消息便马上行动提出了议案。十月初四日,江苏谘议局已对该议案讨论并形成决议,启动了谘议局对官营商报一事的追责。 议员于定一和钱以振提交谘议局讨论的议案,以报律和法律为依据对官款垫补商报一事提出了强有力的质问,并要求相关经办人承担责任,收回官款。议案内容如下: —官报由官负责,商报由商负责。官冒商名,行销报纸,查上年军机大臣以暗通报馆获罪,⑤现在官营商报,岁支巨万,明见报销,是否国家报律所许? —报馆营业,非国家行政经费,乃令人民强加负担,吾民不能承认。 —营业必有盈亏,官营商报,乃令人民岁输数万两,比于天府正供,是何法律? —外国报纸,无论文字不同,阅看者少,即官长皆能读西文,亦无强令阅看之理。宁、苏两属官署局所,勒派每年万余两之上海泰晤士报贴款,应即日停贴。 —上海各种官冒商名之报,应即日退还商人,停支官款。 —上海各种官冒商名之报,所有官入之垫款,应勒令提还。若不能提还,应即查明原经手之员赔款。⑥ 此议案提交后,谘议局迅速将此事安排进议事日程加以讨论。十月初四日江苏谘议局优先讨论议决革除官营商报,在于、钱二人议案的基础上形成了如下决议: (甲)不可行之理由 —官报由官负责,商报由商负责,官冒商名,行销报纸,无此宪政。 —报馆营业,非国家行政经费,乃令本省强加负担,无此税则。 —营业必有盈亏,官营商报,乃令本省岁输数万两,比于天府正供,无此国法。 —外国报纸,无论文字不同,阅看者少,即官长皆能读西文,亦无强令阅看之理,宁苏两属官署局所,以及官立学堂,勒派每年万余两之上海泰晤士报贴款,剋剥僚属,间接取盈于人民,驱本省官民悉为外商牛马,无此政体。 (乙)更正之方法 —上海官冒商名之《中外日报》、《舆论时事报》、《申报》,应即日退还商人,停支官款。 —上海官冒商名之《中外日报》、《舆论时事报》、《申报》,所有官入之垫款,勒令提还,若不能提还,应即查明原经受之员赔缴。 —上海泰晤士报之贴款,应通饬衙署局所及官立学堂,即日停贴。⑦ 议决案由于、钱二人议案的质问改为以“宪政”“税则”“国法”和“政体”等法律与制度原则下对官营商报行为的否定和问责,要求总督和巡抚立即更正,态度相当坚定。谘议局的决议两天后送达江督张人骏和巡抚瑞澂。谘议局一边等督抚的回应,同时对该案继续追查。后续查得上年苏松太道台蔡乃煌,以上海各报昌言无忌,据事直书,有碍行政,于是将《中外日报》和《舆论报》两报购回自办,后又将《申报》归南北洋合资筹办,接着又将《时事报》《沪报》一并买回归并。先后所购各报,共付股本月费两项银十六万七百四十一两九钱八分,均在苏松太道经理各省解到开浚黄浦费息款项下挪借。该款自光绪三十四年四月份起,每年由江海关道捐廉摊还银一万两。至宣统元年四月,已还银一万两。计十七年之后方能摊还完毕。挪借之款,并无利息。此事均详奉前两江总督端方札准,并咨外务部立案。 事情至此,超出了谘议局的意料,出现了新变化,即官款垫补商报的行为,并非是蔡乃煌或端方的个人行为,也并非秘密运作,而是经由端方批准,业已报部备案。在这种情况下,初四议决案中的决议就需要修正,因此谘议局于十月十五日会议提出紧急动议案,续行议决官营商报案办法九条。内容如下: —《舆论报》、《沪报》既经归并入《舆论时事报》、《中外日报》之内,报已消灭,其股本股息,应向《舆论时事报》、《中外日报》两馆清算。 —《申报》既系南北洋合资筹办,除移直隶咨议局提议外,应将南洋官款一万八千八百余两之本息,向《申报》馆清算。 —南北洋官办之《申报》,应正名为《南北洋官办申报》。苏松太道流摊十七年之款所办之《中外日报》、《舆论时事报》,应正名为《苏松太道办中外日报》、《苏松太道办舆论时事报》。 —浚浦项下借款十六万七百四十一两九钱八分,既奉大部准予免息,国家每年受亏非细。查报馆本系营业,入款本称股本,则《中外日报》、《舆论时事报》,自应缴纳官息,以普通股息七厘计算,应缴息银一万一千数百两。以此息款岁提一万两,照案摊还浚浦局借款,可省苏松太道之流摊,亦为官轻累之一法。如苏松太道必欲捐廉以急公议,应请将《中外日报》、《舆论时事报》应缴官息,拨充本省行政经费,而免除本省人民他项杂碎负担,俾沾苏松太道捐廉办公之惠。 —《申报》官款本息,除北洋自行清算外,南洋官款,应请制台饬属清算。 —《中外日报》、《舆论时事报》、《申报》既系咨部立案官款办理之报,应请制抚台饬各该报馆照官报体例办理,所有应公布之行政事件,发交各该报馆登载。 —官长监督人民,个人不法,可依法律惩治,团体不法,可依法律解散,无冷嘲热讽之理。嗣后《中外日报》、《舆论时事报》、《申报》等各官报,除发布公共事件之外,如有不伦之语,不合官报体裁,应治以相当之罪。 —上海《泰晤士报》津贴,不得勒派各衙署局所及官立学堂,应径用官款,归交际费项内支销。 —前案所议提还垫款及经手赔缴各节,查各该官报既系咨部立案所办,原案乙项所开更正之方法,与其第一、第二两条文,自应取消。其余议决案原文,仍请制台将本议案加入,一并将本省官营商报办法更正施行。⑧ 本次决议,放弃了若报馆不能退回官款则由经手官员赔缴的要求。因为此时已查得并非官员私自收买报馆,而是公职行为。在已查事实的基础上,谘议局只得承认《舆论报》《沪报》并入《舆论时事报》《中外日报》的事实。虽然两报已消失,但谘议局并不打算放弃追回之前贴补的官款,本次决议中第一条即要求,原本注入该报的资金,要从并入的报馆股息中清算。 由于官款使用经过前两江总督端方行咨外务部立案,履行了行政程序,官款与商报结合已是事实。在这种情况下,江苏谘议局对应当追回的权利依然紧追,比如对《中外日报》和《舆论时事报》,要求官款贴补报馆盈利后应分得股息;收回的股息将被拨充本省办公经费,以减轻苏省人民的财税负担;另外,官款既贴补于报馆,报馆应体现出受官款资助的事实,体现的办法,一是更改报名,将报名加注官方标签,如要求《中外日报》与《舆论时事报》正名为《苏松太道办中外日报》《苏松太道办舆论时事报》等。另一个体现是,被资助报刊,应遵循官报的体例。谘议局要求加注官办标签是有合理根据的。因为清末所办官报,清政府责令按照《北洋官报》的体例为范本,因此体例与民间商办报刊有较大的区别。同时,官报不能刊发议论文字,主要刊载政府公文。所以谘议局在决议中不依不饶,要求被资助报刊改变体例,要求“所有应公布之行政事件,发交各该报馆登载”,算得上振振有词。这样,被资助之各报,再不能以商报的面貌和形式出现在报界,即令官方资本不退出,官方也不能再借商报表达自己的立场。所以,谘议局决议对官款使用的限制和官报体例的要求,对官股退出商报形成了倒逼之势。 需要指出的是,在肯定谘议局职权范围内对官款贴补报馆不正当使用行为监督和追责的同时,也要看到谘议局对非官款贴补报馆行为的反应。贴补上海《泰晤士报》的款项,来源于官方对各衙署局所及学堂的摊派。虽然此项津贴不属官款,但谘议局反对江苏官方克扣僚属的行为。对上海《泰晤士报》的贴款,谘议局议决“径用官款”以取代摊派。也就是说,谘议局认可了资本津贴上海《泰晤士报》的行为。谘议局态度由第一次议决案中责令停贴到第二次决议中“径用官款”,前后发生很大转变。这一转变,可能是由于谘议局认同了江苏官方鼓励官场和学堂购阅上海《泰晤士报》,是“开通民智”之举。清末时期,基于报纸是传播新知、沟通内外之有效工具的认知,官方鼓励学生读报,并要求各新立学堂设立阅报室。阅报室允准学生前往披览;也有学堂将所购报章发交各斋学生次第传阅。⑨袁世凯所办学堂甚至设有读报课程,读报乃学习任务。上述各例皆为官方推动学生读报以广见闻之举。如果说鼓励学生读报是为开通“民”智的话,那么责令官员读报则是为开通“官”智。袁世凯从义和团事件时就看到官员的愚昧,曾提出过建仕学院,要对官吏进行培训。他尤其强调仕学院要“多置译成新书”,⑩使官员读译书以了解时代和外部信息。当然,阅报更是有效提高官员认知水平的手段。基于鼓励读报提高官民智识的视角看,官款用于购阅上海《泰晤士报》之举,是合理的。所以,谘议局最后议决停止江苏官方对各衙署局所和学堂的摊派,授权江苏督抚用官款津贴上海《泰晤士报》,并指定了支出官款的款项。 三、报界反应 报界对“官营商报”案的发生和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南洋官报》刊发了江南宁属清理财政局移请江苏财政总局照覆文及清理财政的清单,将官款资助报馆的信息披露,才有后续谘议局的议决追责。所以《南洋官报》是本案发生的重要关节点。本案的后续发展,报界也起着重要的作用。正是各报不断报道,使本案在更广范围为社会周知,进而对清政府形成强大的舆论压力,迫使后者对此事作出回应。张人骏回覆清廷谕旨的折内,建议将报馆退归商办,其原因就是报刊对此事大量报道后,被购回各报“不居其名,而又群知为官报”,(11)造成清政府很尴尬的处境,不得已只好退归商办、收回垫款。可以看出,报界的报道扩大了官营商报信息的传播,也影响到本案的发展方向和最终结果。 但报界对“官营商报”案的报道,由于各报立场不同、关注点的差异及与本案关联度的大小等众多因素的存在,各报的反应和报道体现出很大不同。下面笔者拟从华文大报、西文外媒和涉事报刊三个方面,观察报界对此案的反应。 华文报刊数量众多,因此本文选择上海《时报》和天津《大公报》分别作为上海和北方报纸代表来分析。《时报》是清末上海三大报纸之一,《大公报》则是北方影响最大的报纸。从两报对本案的报道情况,可以观察清末舆论对“官营商报”案的态度及关注程度。 《时报》本是江浙立宪派的大本营,江浙立宪派领袖张謇,是江苏谘议局议长。因此《时报》对江苏谘议局极为关注。因江苏谘议局追责而迅速成为政治事件和新闻事件的“官营商报”案,自然是《时报》持续报道的对象。《时报》对此案关注力度颇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即时追踪信息 江苏谘议局对“官营商报”案的提案和会议进程,《时报》都及时跟进。比如九月三十日在“地方要闻”栏刊载《上海官办之报馆听者》一文,报道了谘议局议员于定一和钱以振两人“革除官营商报”的提案。《时报》的报道很有创意,文中是议案的内容,但给加了标题,似是对当事各报的讲话或命令,间接以两议员的议案内容表达自己态度。待十月初四谘议局形成决议后,《时报》于十月初九在第三版“地方要闻”栏刊载《江苏谘议局议决革除上海官办各报案》一文,将谘议局的议决内容全文照登。谘议局查清官款垫拨商报情形后续议此案,又通过新的决议。《时报》遂于十月十七日以《江苏谘议局议员于定一、钱以振提出续查官营商报成案补议办法九条之紧急动议案》为题,刊载了动议案全文。可以说,《时报》在官营商报问题的报道上,是非常及时且不吝惜版面的。 栏目多样 《时报》对“官营商报”案报道的栏目多样化,是其他报纸无法相比的。《时报》报道过与此案内容有关的栏目有“地方要闻”“时评”“专件”“寸铁”“专电”“奏折”等。报道形式多样、立体,信息比较灵活。 评论多 除了对事件客观记述的新闻报道,《时报》还发表了多篇评论。“时评”是《时报》的专长,在当时报界一枝独秀,极为出色。“时评”栏对官营商报有不少精彩言论。如十月初七日第五版包天笑撰写的时评:“报馆之馆,从食从官,或曰:官食欤?食官欤?曰:此可作两解。右行则为官食。以今日之报馆,常并吞于官,蚕食于官也。左行则为食官。言今日之报馆,资官津贴,则食于官者也。”(12)包天笑以报馆的“馆”字为题作妙解,轻而易举地将报馆受官场和资本双重节制的事实表现出来。另一则时评说:“今有作新拇战者,以食指为官,以大指为谘议局,以小指为报馆。官遇谘议局,则官输,以谘议局能监督官也;以谘议局遇报馆,则谘议局输,以报馆能评论谘议局也;报馆遇官,则报馆输,以官能收买报馆也。”(13)此评将报馆、谘议局与官方三者的关系,比作手指游戏,揭示出三者的相互节制关系。而这三者,正是官营商报案的不同主体,他们在本案中的关系和地位,也由包天笑的寥寥数字而得以彰显。另外一则时评,则是对报律不能约束官员染指报馆行为的讽刺、失望和不满,同时也是对前两江总督端方和苏松太道台蔡乃煌挪用官款、收买报馆和压制报界言论的批评和揭露。评论中说: 今方修改报律时,应加一条曰:如各报有昌言无忌,据事直书者,由官出资买回自办。 今方修改报律时,应加一条曰:倘官员中有愿办报者,得以国家公款挪借,随后摊还,并无利息。 今方修改报律时,应加一条曰:凡官员之收买报馆者,得以收买之费,摊派后任分偿,先行咨部立案。(14) 评论栏目是报纸观点和立场的体现。较之新闻栏的报道,时评尤凸显报纸对事件的关注。《时报》刊发的时评数量与该报对“官营商报”案重视的程度是相匹配的。 报道的持续性 《时报》对此事追踪的时间跨度,从宣统元年九月三十日议员首提革除官营商报议案开始,到庚戌年正月廿七日江苏谘议局议案一览表,还有一笔该案内容,记载“第七十二:修改前呈革除官营商报案(于定一)可决”。(15)《时报》从官营商报案事发,到谘议局各场会议讨论表决,再到谘议局闭会时该案的进展,以及后续两江总督张人骏向清廷奏覆此事折文中的内容和江春霖的参奏,都作了追踪报道。这一点同其他报纸在该案成为事件热点时报道一二的表现形成了鲜明对比。 《大公报》是清末北方影响最大的报纸,一向以敢言著称,在言论界颇有影响。由于该报位居北方,与事发地南京和上海空间距离较远,从地缘上来讲,它对本案的报道不占优势。不过,因为该报对此案极为重视,所以其新闻性质的报道并不少。如十月十八日的“要闻”栏,以《端督之一波又起》为题的一则简要新闻,内容为:“江苏谘议局因端督在任时,曾以官款协助上海报界,现议员提出抗议,拟追还此项公款,否则要求端督赔偿云。”(16)文字寥寥无几,但言简意赅,将端方在两江总督任时,以官款协助上海报界,现遭谘议局追讨的情况讲得清清楚楚。在张人骏调查本案阶段,《大公报》听闻蔡乃煌派人携重金至南京运动张人骏以求隐讳其劣迹而固保其地位,(17)遂将此消息披露报端。江春霖上疏参奏蔡乃煌后,《大公报》亦密切追踪报道,前后发过三次“要闻”,及时报道该案的进展。直至庚戌年二月廿六日,该报还刊出《请看蔡道之内援》的要闻,内容为:“江侍御春霖前曾奏参沪道蔡乃煌各节,至今蔡仍安然无事,昨闻政府诸公又有拟保该道为帮办禁烟大臣之说。若然,则蔡道之内援就此一斑可见。”(18)此文既是对“官营商报”案后续发展的关注,同时也指出了此事目前的结果。 值得注意的是,《大公报》发表了一系列与“官营商报”案相关的时评。十月十二日的评论是针对官方资本与民间报馆结合的问题表达看法,其文曰:“凡报官办而招商股者,其势难。商办而招官股者,其势易。非官股之独能踊跃也,一入官股,则一切商报皆可渐化而为官报,较之官家自办者,用力少而成功多,宜乎全国报纸之毫无生气也。”(19)官商资本结合,其结果往往商股地位被动,报纸独立性丧失,舆论“毫无生气”,严重危害报界。 《大公报》十月二十七日的“闲评一”《为地择人》,则是对制造“官营商报”案的罪魁祸首蔡乃煌的批评和讽刺,也是对他收买和封禁报馆行为的披露。文中说:“吾人始闻沪道调津之说,初不之信,继而思之,乃知其说之非无也。沪道蔡乃煌,素以收买报馆、封禁报馆,深得政府之信任。现在天津报馆日见发达,大小各报,将近十种,其声势之大,几与沪上各报相埒。使以蔡乃煌调至他处,未免有人地不宜之慨。惟有调任津道,庶可大展其才,俟其办有成效,然后再调相宜之处,以便将全国报馆一网打尽云。”(20)同一天的“闲评二”批评对象也是蔡乃煌,内容为:“沪道蔡乃煌受任年余,专以收买报馆为事,先后承办上海《中外日报》《申报》及《舆论时事报》,业已消费江苏官款二十余万。兹经江苏谘议局告发,舆论为之不平,因而沪道有他调之说。惟自吾人观之,沪道既热心办报,维持公益,与其改调他省,不如使之专充三报馆总办耳。”(21)蔡乃煌专任上海多年,于上海报界影响最大。此间发生的每起报案,都与蔡乃煌有或多或少的关系。“官营商报”事又是蔡乃煌一手经办,《大公报》对蔡染指报馆不满,因此以嘲讽的言辞封其为“三报馆总办”,同时也表达了对传闻蔡乃煌即将赴任天津可能对天津报界造成毁灭性摧残的担忧。之后,《大公报》听闻民政部肃亲王善耆有参劾蔡乃煌的行动,对此评论说,“不禁心有所惧”,该报不担心蔡乃煌会被革职,而惧怕肃亲王将会成为陈启泰第二。(22)因为在本案之前江苏巡抚陈启泰曾经参奏蔡乃煌,但因蔡乃煌与两江总督端方交好,朝中亦有靠山,最终陈启泰的参劾并没有捍动蔡乃煌,反被作为下属的蔡乃煌气死。《大公报》以此为题,其实是对蔡乃煌名声较恶却因朝中有人地位根深蒂固而未受惩处的不满。在御史江春霖因本案奏参蔡乃煌后,《大公报》即以《报馆与流氓》为题置评: 蔡乃煌之摧残舆论收买报馆,久为天下所共愤。乃迟至今日始有揭参之案,始有查办之命,政府之重视蔡乃煌,于此可见。 蔡乃煌之言曰,政府之视沪道,实较一军机大臣为重,吾敢易一言曰,政府之视报馆,实较一广东流氓不如。(23) 《大公报》丝毫不掩饰对蔡乃煌的差评,将祖籍广东的蔡乃煌视为“流氓”,同时,时评也表达了对政府罔顾报馆权益、不予处置蔡乃煌的不满。 以《时报》和《大公报》为代表的华文报刊,是本案最主要的报道主体,是官款购买和津贴商报信息的主要传播者,也是该案社会舆论的主要生成力量,同时也是该案发展的重要牵引力量。 外媒与中文报章相比,其关注视角明显不同。下面以在华较有影响的《北华捷报》和《德文新报》为例来谈西文外媒对本案的反应。 《北华捷报》(The North Chinese herald and supreme court & consular gazette)创办于1850年,是中国近代最有影响力的外文报刊之一。宣统元年的“官营商报”案,《北华捷报》也比较关注。它于西历十一月二十日发表了以《报纸津贴》(Press Subsides)为题的文章,内容是江苏谘议局议员于定一和钱以振九月提交革除官营商报的议案全文。它将议案各条款忠实而详细地翻译成英文,没有任何删减增添。此后,该报还有一篇内容较短的报道,仍然是以“Press Subsides”为题,内容是关于十月初四日江苏谘议局的决议。这篇刊载于西历十一月二十七日(宣统元年十月十五日)的短文与上篇报道不同,仅报道了决议案全文的一部分。提及的内容概括为:谘议局通过了终止苏省地方衙署局所学堂等负担外报之贴款和资助上海各报之官款的决议。谘议局认为剋剥僚属、取盈于人民来贴补外报,驱本省官民悉为外商牛马,无此政体。内容仅此而已。有意思的是,该文直接引用了谘议局决议中的“驱本省官民悉为外商牛马(drive the people and make them cows and horses to foreign merchants)”(24)一句。这可以看出,《北华捷报》作为西人在华创办的报刊,它的外商身份和所处的立场与位置,使得它比较关注谘议局和江苏官方如何处理资助外报以及前者对外报的态度这一与自身关系密切的问题。 1886年创刊于上海的《德文新报》,是近代中国最早也是出版时间最长的德文报纸。“官营商报”案发后,该报发文表达了对该案的看法。它说:“江南各省要求官员退出报刊,撤回资本。但这看起来无法实现。因为这些官员形式上撤出报刊,将资金以亲朋的名义继续资助报刊,他们不能失去自己在报刊中的影响力,也不愿放弃从中的所得利益。真令人难以理解,地方机构上怎么能做出这样的决议。中国的官员当然不会自己出手经商,但这并不妨碍他们以入股的形式参与到商业公司之中。”(25)这样的话,“那些受官员资助的报刊必须为其资助者说话。”(26)报刊必须为资助者说话而丧失独立、自由的言论,又进一步导致报界了无生气,难以发展:“大部分的中国报刊已经变得毫无个性和原则了。以前,中国报刊的态度都是进步的,而现在,他们的态度是保守还是进步,则要取决于其背后的资助官员。中国报刊停滞不前了。”(27)文中不仅指出普遍存在的官方、资本与报刊之间的紧张关系,同时它以局外人的身份对当时国内报界作了鸟瞰式的评论,指出了官方资本对报馆渗透的事实及其普遍性,以及近年来这种做法对报界已造成“报界了无生气”的可见的危害。 外媒对“官营商报”案报道,尽管内容不多,但仍体现出对本案的关注和重视。 涉事的报纸 本案的涉事报纸在案件发生发展过程中有完全不同的反应。“官营商报”案中涉事的报纸,包括《中外日报》《申报》及《舆论时事报》,其实还应包括《新闻报》。后者虽没支用官款,但该报老板福开森,参与了官款收回各报的经营。这些报纸既已被收归官办或与官方关系密切,它们对本案的态度与上述民办大报完全不同。而且,它们本身是丑闻的主角,各报没有自曝其丑的勇气,因此对本案很少报道和置评。 作为清末报界翘楚的《申报》,它对本案极少的报道中有一个值得关注的有趣表现。它在十月初二的“各省开办咨议局”栏下的“江苏咨议局议案”部分,全文刊出了于定一和钱以振两议员提交的质疑用官款垫补商报合法性以及追讨事件责任的议案内容。不过,该议案没有提及被资助的上海各报名称,《申报》报道中自然也没有相关内容。而接下来的报道是十月初六日“紧要新闻”栏对初四日江苏谘议局的议场纪事,记载了议场上议员对本案的讨论,即:“议员均谓此案应指明某报及其凭据。然后从事决议。四十七号议员言:南洋官报载明清理财政官指驳财政局关于报馆之款有三项。一垫款,一津贴,一但称上海各报经费。应先呈请督抚查明究系何报经费再议办法。”(28)有意思的是,十月初二报道中将江苏谘议局两议员的议案全文刊载,而之后对十月初四江苏谘议局的活动并没有完全报道,新闻内容只是初四日江苏谘议局就此案所议及决议等全部内容中的一小部分。其实,初四日的决议案对款项来源及其对应资助的是上海哪个报馆,都清清楚楚,不存在不知道哪些报馆的问题。这次报道不像上次一样刊登议案或决议全文,故意将议案中《申报》的信息隐而不宣。再之后,江苏谘议局续查“官营商报”案的重要决议,该报也没有只字片语的报道,更不用提详细追踪事件的发展,而恰恰在这两个决议中,都明确指出了《申报》是被资助的报馆,而且有切实的证据,公布了资助款的数额及其来源。可见,《申报》的报道是对本案信息有意识地作了过滤。无论是此处的遮蔽消息还是它后续的沉默,这些行为本身就是对接受官款资助事实的明晰的表达。 同《申报》报道过程中故意隐藏该报与本案关系的行为相比,《舆论时事报》与本案关系撇得更清,报道中几乎没有该案的任何内容。同样是报案,它对同时期被封禁的《民呼日报》和《民吁日报》,却用了大量的篇幅持续地详细报道。至于《新闻报》上有关“官营商报”案内容,与其说是对本案的报道,不如说是关注江苏谘议局动向。该案仅有的几次信息,都是在江苏谘议局某场纪事的报道中。江苏谘议局每场讨论的事项众多,议革官营商报之事仅是其中之一。也就是说,《新闻报》中官办商报的内容,是报道江苏谘议局活动时的无意识结果,并非主动传播本案信息的有意识行为。 报界不同主体对本案的报道,共同构建了“官营商报”案的舆论。因为这几份报纸,无论在上海还是在全国都有很大的影响力。西文外媒对此案的关注,扩大了本案在非华语圈的传播,在引起更广范围的注意和讨论方面,自有一定的影响。 报界为“官营商报”案的报道不仅扩大了该案的传播区域,而且表达了报界对官方干涉报馆的不满,支持了谘议局对官款津贴报馆和官营商报行为的追责,声援了御史对涉事官员的参劾,另外,也构成了迫令政府处理此案的舆论压力。 四、御史参劾 御史是影响“官营商报”案发展的三股力量之一。 最早参劾此事的是御史胡思敬。早在宣统元年五月八日,胡思敬参劾端方多款罪行,其中有“贿通报馆”和“营私舞弊”(29)之罪多条。关于端方营私舞弊一罪,胡思敬称:“(端方)恐报章举发,则奸迹尽露,密令上海道蔡乃煌,以重金购买报馆,前后费四五十万。各报既购归官办,而造谣言猖狂如故。去年两宫大丧,各报诬蔑宫廷之事有非臣子所忍闻者,该督不加禁止,唯一己藏私则障护唯谨,报馆不敢议及一字。又将《新闻》《时事》《舆论》三报,交洋人福开森办,给予津贴。其《申报》《中外日报》等,亦各有津贴,每岁需十余万金。”(30)胡思敬在折文中明确指出了购买和津贴的报馆对象,指出了被购报馆性质已为官办,比较难得的是,胡思敬提供了报馆被购以后的经营人信息,即《新闻》《时事》《舆论》三报的经营人为福开森。胡思敬参奏的上述内容,其实已说出了“官营商报”之事的大部分信息。这些信息中,购买《新闻报》的内容恐怕不实。其依据有二:其一,谘议局调查的结果中并没有购买《新闻报》的纪录,谘议局的信息之所以更准确,是因为谘议局最初议决案提交督抚后,督抚对此作出了回应。如果《新闻报》确实被江苏官方购买,那么在谘议局的续行决议中会列出该报的信息。而实际上并没有,由此可断定胡思敬称端方购买《新闻报》的内容不实。其二,福开森本是《新闻报》创办人,他本人与端方关系密切,如果端方想让福开森的《新闻报》替自己说话,没有必要通过购回报馆再交于其经营的行为来实现。除购买《新闻报》内容不确外,“重金购买报馆,前后费四五十万”这条,与谘议局议决案中的内容也有出入,同江苏清理财政局的数字也不相同。但无论如何,胡思敬参奏的奏折包含了本案的许多重要信息,对本案有重要意义。但胡思敬所列有关本案信息的目的,是为了证明端方“营私舞弊”,而不是对官营商报行为予以追究。所以张人骏后来的调查仅对端方此举是否营私舞弊作出回应,其他应当追问的问题没有作出回答。而且上述参奏内容淹没在他所参端方的众多罪状中,没有被更多的人注意,更难以向外界扩散。 胡思敬参奏后,清政府谕令两江总督张人骏予以核查。张人骏于十一月十二日向清廷覆陈,称蔡乃煌之所以购买各报,是因为“报馆妄论时政,且西报于交涉事件,每多颠倒”,因此将报馆购回“藉以抵制横议”。(31)至于购买报馆之股本,其来源有三:除南北洋大臣及云贵总督拨助外,由道库在浚浦息款项下垫银十六万余两。另有每年不足三万两银的开支由江南财政局及道库捐贴。前述行为经端方咨明外务部备案,被资助各报收回官办。张人骏认为:“所需股本既系南北洋大臣及云贵总督合筹咨部立案,其为非端方密令上海道私购。”(32)并称前述事实“自属可信”。(33)也就是说,调查结果认为端方此举并非“营私舞弊”,也非“秘密”运作,故胡思敬奏参端方“营私舞弊”的罪状不成立。 张人骏的奏折很快载于当月的《政治官报》。御史江春霖对张人骏的调查结果很不满意,遂于十九日就官营商报事上《劾苏松太道蔡乃煌疏》,参劾经手此事的道蔡乃煌。江春霖指出,若张人骏所覆属实,即可视作蔡乃煌“通同作弊之实据”。(34)不过,江春霖没有谴责官方“抵制横议”之行为,他更质疑张人骏称蔡乃煌等购买商报官办是为“藉抵横议”之目的。其理由是:其一,若商报果有横议,按律可治罪,封禁即可,根本不必花费巨款购买。并以当时京城封禁的《京报》《国报》《大同报》和上海查封的《民呼报》《民吁报》等为例力证,政府为抵制报馆议论通常采取的手段为封禁报馆,而不是购回自办。其二,既购为官报,则应援照官报事例,奏明民政部或督抚立案,而蔡乃煌等并没有这样做,只是仅咨外务部了事。其实,江春霖认为蔡乃煌此举是洗白外务部:“自外务部卖路、卖矿、卖界、秘密主义,神鬼不知,独报馆时发其覆。……而总理该部之亲王,则军机大臣之亲王也。”(35)外务部总理大臣为奕劻,又是军机大臣,是端方和蔡乃煌朝中的靠山。所以,江春霖认为,蔡乃煌将给外务部惹事的上海报馆收买,“藉抵横议”是其一,实则是为私利而互相标榜,抵排异己,暗中向奕劻输送利益。江春霖还不满张人骏听信蔡乃煌的欺饰之词为蔡辩护。同时要求清廷“将苏松太道蔡乃煌严加惩处”,并“勒缴垫款,立停报纸”,(36)否则“诚恐物议难平,人心不服。”(37)江春霖极力呼吁严惩蔡乃煌,追回垫款,报纸停止官办,平息物议。 江春霖十一月十九日请旨“严惩、追款、停报”的奏疏,清廷虽饬令张人骏查覆,(38)但江春霖“待命二旬,未蒙训示”,(39)一直没有等到清廷该给的说法。于是,他于十二月初九上《再劾苏松太道蔡乃煌疏》,再次参劾蔡乃煌。这次,于“官营商报”案外,揭参了蔡乃煌的其他罪行,如卖公地以充私囊、违诏旨而弛禁烟、玩要工而糜钜币、引劣员以误新政、摧舆论以媚外人、比匪类以占优差和纵属员以倡败俗等七项罪行。这些罪行,是为上次参蔡不成而增添的加持力量。同时,江春霖再次将此事与军机大臣瞿鸿禨暗通报馆被革职一事相较,他认为暗通报馆者已经治罪,而私买报馆性质更严重,更应严惩,再次恳请清廷查办蔡乃煌。此疏的命运,据《大公报》十二月十四日报道,说“原折留中未发”,(40)但这消息确否,《大公报》也不敢肯定,说后续探访,但也没见下文。《大公报》庚戌年二月初七日依然称,江春霖参劾蔡乃煌“至今依然没有下文”。(41) 但据《大清宣统政纪》己酉年(即宣统元年)十一月十九日记载,张人骏奏称:“各报既经收归官办,虽不居其名,而又群知为官报,办法诚有未善。应请一律退归商办,收还垫款。”(42)至于要求查办蔡乃煌一项,张人骏疏文中说,蔡乃煌“无私擅纠结实据。应免予置议。”(43)根据日期看,此折与江春霖上疏为同一日,不可能是对江春霖奏疏作出的回应。仅就目前的资料判断,张人骏此奏,很可能是对清廷要求查覆此事以及江苏谘议局十月份两次连续议决此事和报界揭批此事而向清政府汇报的善后结果。还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江春霖奏参了军机大臣奕劻,很快被罢官归乡,之后也没有再对此案续参。 “官营商报”经各方协力,最后使官款退回,报馆归于商办,但胡思敬和江春霖希望惩办蔡乃煌的目的仍没达到,虽有将蔡调离的传言,不过蔡乃煌依旧在上海道任上。 在清末报案中,“官营商报”案非常特殊。它特殊到,若是时间推迟或提前几年,可能就不会有本案发生的机会,或者其后续发展路径也会与此不同。这是因为它发生于清廷仿行预备立宪时期,新的政治环境下新出现的事物,如蝴蝶效应一般,一系列貌似不相干的因素相互牵联而使本案有了意想不到的发展。 “官营商报”案的发生,关键点在于江南宁属清理财政局清理财政时发现官款使用存在问题。以前外界虽然对蔡乃煌和端方干预报馆的行为早有耳闻,但没有直接证据。即使参劾端方“贿通报馆”“营私舞弊”的御史胡思敬,奏折中列出资助报馆的信息也不完备。而江南宁属清理财政局移交江南财政总局的覆文中,指出了用于报馆的问题款项,是江南宁属清理财政局发现,有杂项册列支提还申报馆垫款,规折湘平银一万八千九百余两。还有上海《泰晤士报》津贴银三千六百两。宁属清理财政局于此表示不解并追问:“查报馆垫款,何以由公家拨还,请将原案移送本局备阅,仍将起末根由详细见復。”(44)要求江苏官方对这一问题作出回复。要知道,为宪政预备而设的清理财政局,光绪三十四年奏请设立,宣统元年才刚刚开始运转。正是清理财政局对以往混乱财政的清查,官款进入报馆之事才被发现。 其实,清理财政局发现官垫商报的行为与此事被外界周知,中间还有一个关键的环节,就是官报将财政局文件向社会公开。这一举措得益于清廷下诏宣布预备立宪时提出的“庶政公诸舆论”。清政府要求,此后不涉政治和外交机密的各类政府电文、奏牍等行政公文,都应刊载于报端公诸舆论,即政务向社会公开。而承担这一任务的载体便是官报。因此清廷谕令中央和地方都须创设官报,并严格限定官报体例,定位官报的主要职责为刊发奏议、法令等公文。在这样的背景下,江南宁属清理财政局移送江苏财政总局的覆文,得以在《南洋官报》等报刊媒体公布,官垫商报的行为亦因此被江苏谘议局等外界知晓。之后,同样是得益于清廷要求“庶政公诸舆论”,张人骏调查此案回覆清廷的奏折,《政治官报》刊发公布,御史江春霖才因之有参奏蔡乃煌的后续行动。相较于以御史胡思敬五月八日参奏端方“贿通报馆”“营私舞弊”不为外界所知而结果不了了之,报纸刊载官款资助报馆消息被外界周知后有了谘议局追责的后续结果,反映出《南洋官报》对资助款项信息的公布也是“官营商报”案后续发展的一个关键环节。 另外,本案如果没有江苏谘议局对此事不依不饶地追查、开会讨论和议决,官营商报的问题就不会被舆论聚焦,官营商报的也就不会成为影响全国的报案。所以,江苏谘议局的作用也尤为重要。具有地方议会性质的谘议局,是清政府宪政清单中的一项重要内容,清廷严令各省于宣统元年九月初一之前必须筹办完毕。江苏谘议局于九月初一开局,刚刚开局不到一个月的谘议局,其议员于定一和钱以振便看到《南洋官报》九月二十日刊载的江南清理财政局移交总局的本省财政清理的信息。而议决本省财政正是谘议局的重要职权,因此两议员针对垫补商报等官款不合理使用之事提交议案,以求追回官款。又由于江苏谘议局为各省谘议局之翘楚,对宪政抱有期待的上海及其他各地的报界自然十分关注。因此该局对“官营商报”案的议决成为报馆报道的对象,“官营商报”遂成为重要的政治事件和新闻事件。 “官营商报”案中参与追查的三股力量——御史、谘议局和报界,虽然都是要结束官营商报的局面,但由于各方权责及立场不同,其具体诉求有明显差异。御史奏劾端方和蔡乃煌,是将官营商报一事作为二人的污点,要求惩办清廷官员,目标不在争取报馆自由而在于净化官场环境。谘议局追查此事,重在要求追款和报馆退归商办,并不关心舆论环境和官场生态,其注意力集中于监督本省财政,密切注意官款使用是否合法。而报界则不太关注官款不合法使用,而更提防官款向报馆渗透对舆论的影响,以及官员和资本对报界的危害,目标是争取报界自身发展的良好环境。御史、议员、报纸三方共同为一事呼吁努力,是清末从未有过的景观。 此案最后以收回官款、报馆退归商办结束,这一结果,虽可见预备立宪下新因素对此案的影响,但也不能忽视旧力量的强大。比如在如此大的舆论压力下,清政府依然不肯治罪于蔡乃煌可能表明在收购上海各报这件事上蔡乃煌并不是主谋,或不是唯一主谋,这就可以解释清廷为何对江春霖参劾蔡的疏文留中不发,不对外界公布的原因。 另外一个亦需留意并继续追问的问题是,资助《申报》的官款,来自三方,除了两江总督端方以外,还有南北洋大臣和云贵总督所拨的官款。有意思的是,远在西南边陲的云贵总督伙同两江总督资助上海报馆,向报馆施加影响,可以窥见地方官员左右报馆和掌控舆论的欲求。云贵居西南内陆,也谋求在全国舆论中心的上海对有重要影响的报馆用资本暗中经营,这种行为在各省督抚方面,是常态还是偶尔有之?由于资料匮乏,笔者目前无法回答这一问题。但不管是哪种情况,对清末报界的发展来说都不是好事。 ①《大清宣统政纪》卷十三,己酉年五月丙辰(初八)。 ②《大清宣统政纪》卷二十五,己酉年十一月乙卯。 ③《东方杂志》1909年第12期,第408页。 ④关于《南洋官报》所载官款垫补商报信息的时间,江苏谘议局十月初四日议决案中的相关表述称:“据前月十五日发行之南洋官报,所载本省清理财政局移请财政总局照覆文内,查见二月一个月中,已有申报馆垫款湘平银一万八千九百余两……”(见《上海报界之一斑》,《东方杂志》1909年第12期,第408页)即江苏谘议局说是从九月十五日的《南洋官报》得来的信息。据本人查阅《南洋官报》,此文并非载于该报九月十五之第54期,而是载于九月二十日发行之第55期,见“两江奏牍”栏,文章标题是《江南宁属财政局 移江南财政总局请查照单开逐款见复并将常年收款比较细册一并送局备核文(附粘单)》。所以十月初四日谘议局决议案中提及《南洋官报》刊载该文的时间有误,各报对谘议局决议案转载时沿用了谘议局决议案中的时间,因此亦有误。 ⑤指军机大臣瞿鸿禨以暗通报馆,授意言官,阴传外援罪名被开缺回籍一事。 ⑥《上海官办之报馆听者》,《时报》己酉年九月三十日,“地方要闻”。 ⑦《上海报界之一斑》,《东方杂志》1909年第12期,第408-409页。 ⑧《东方杂志》1909年第12期,第409-410页。 ⑨廖一中、罗真容整理:《袁世凯奏议》,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584页。 ⑩沈祖宪等著:《容菴弟子记》,台北:文星书店,1962年,第124页。 (11)《大清宣统政纪》卷二十六,己酉年十一月乙丑。 (12)《时报》己酉年十月初七,第五版,“寸铁”(笑)。 (13)《时报》己酉年十月十八日,第五版,“寸铁”(笑)。 (14)《时报》己酉年十月十九日,第五版,“寸铁”(笑)。 (15)《江苏谘议局议案一览表》,《时报》庚戌年正月廿七日,第五版。 (16)《端督之一波又起》,《大公报》己酉年十月十八日,第2646号,“要闻”。 (17)《蔡乃煌运动张督之述闻》,《大公报》己酉年十一月十七日,第2674号,“要闻”。 (18)《请看蔡道之内援》,《大公报》,庚戌年二月廿六日,“要闻”。 (19)《大公报》己酉年十月十二日,第2640号,“闲评二”。 (20)《为地择人》,《大公报》己酉年十月二十七日,第2655号,“闲评一”。 (21)《三报馆总办》,《大公报》己酉年十月二十七日,第2655号,“闲评二”。 (22)《第二陈伯平》,《大公报》己酉年十一月十八日,第2675号,“闲评二”。 (23)《报馆与流氓》,《大公报》己酉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第2682号,“闲评二” (24)“Press subsides”,The North Chinese herald and super court & consular gazette.Nov.27. (25)Amtlich unterstützte chinesische zeitungen.Der Ostasiatische Lloyd.3.Dezember 1909,S.1119-1120.转引自牛海坤著:《〈德文新报〉研究:1886-1917》,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94页。 (26)Amtlich unterstützte chinesische zeitungen.Der Ostasiatische Lloyd.3.Dezember 1909,S.1119-1120.转引自牛海坤著:《〈德文新报〉研究:1886-1917》,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94页。 (27)Amtlich unterstützte chinesische zeitungen.Der Ostasiatische Lloyd.3.Dezember 1909,S.1119-1120.转引自牛海坤著:《〈德文新报〉研究:1886-1917》,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94页。 (28)《江苏谘议局初四日议场纪事》,《申报》宣统元年十月初六,第二张第二版。“紧要新闻二”。 (29)胡思敬:《劾两江总督端方折》,《退庐全集》(笺牍·奏疏),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四十五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70年,第717页。 (30)胡思敬:《劾两江总督端方折》,《退庐全集》(笺牍·奏疏),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四十五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70年,第721-722页。 (31)张人骏:《两江总督张人骏奏查明大员被参各款据实覆陈折》,《政治官报》宣统元年十一月十二日,第229页。 (32)张人骏:《两江总督张人骏奏查明大员被参各款据实覆陈折》,《政治官报》宣统元年十一月十二日,第230页。 (33)张人骏:《两江总督张人骏奏查明大员被参各款据实覆陈折》,《政治官报》宣统元年十一月十二日,第230页。 (34)江春霖:《劾苏松太道蔡乃煌疏》宣统元年十一月十九日,朱维幹等编校:《江春霖集》卷一,马来西亚与兴安会馆总会文化委员会,1990年3月,第195页。 (35)江春霖:《劾苏松太道蔡乃煌疏》宣统元年十一月十九日,朱维幹等编校:《江春霖集》卷一,马来西亚与兴安会馆总会文化委员会,1990年3月,第196页。 (36)江春霖:《劾苏松太道蔡乃煌疏》宣统元年十一月十九日,朱维幹等编校:《江春霖集》卷一,马来西亚与兴安会馆总会文化委员会,1990年3月,第197页。 (37)江春霖:《劾苏松太道蔡乃煌疏》宣统元年十一月十九日,朱维幹等编校:《江春霖集》卷一,马来西亚与兴安会馆总会文化委员会,1990年3月,第197页。 (38)据《大公报》十二月初十报道:“前有江侍御春霖奏参沪道之案,已饬查覆。尚未具奏。兹于日昨又由军机大臣廷寄两江总督秘要电旨一道,探之内廷人云,此亦系上月某科御史参劾江苏某大员之奏折,今始谕交江督查办,内容秘密,未易探悉。” (39)《再劾苏松太道蔡乃煌疏》,宣统元年十二月初九日,朱维幹等编校:《江春霖集》卷一,马来西亚与兴安会馆总会文化委员会,1990年3月,第199页。 (40)《江侍御封奏之述闻》,《大公报》己酉年十二月十四,“要闻”。 (41)《蔡乃煌与某邸之比较》,《大公报》庚戌年二曰初七日,“闲评二”。 (42)《大清宣统政纪》卷二十六,己酉年十一月乙丑。 (43)《大清宣统政纪》卷26,宣统元年十一月乙丑。 (44)《江南宁属清理财政局移江南财政总局文》,《顺天时报》宣统元年十一月十九日“各省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