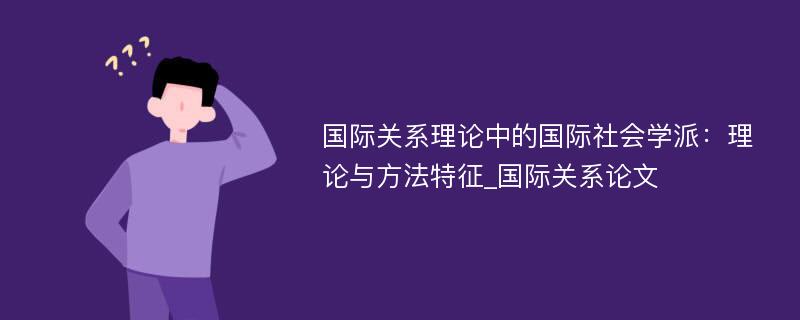
国际关系理论中的国际社会学派:理论及方法论特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方法论论文,理论论文,国际关系论文,学派论文,国际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国际关系理论中的国际社会学派,又被称做“英国学派”。国际关系研究的英国学派在整个冷战时期就已经存在,它至少有两点与以美国国际关系学者占主导的其他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流派明显不同:一方面,它拒绝了行为主义革命的挑战,并且继续强调以人类理解力、判断力、规范和历史等为基础的传统方法;另一方面,它拒绝在严格的现实主义与严格的自由主义国际关系观之间进行任何严格的区分。由于“英国学派”这一名称的字面含义过于狭窄(它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其主要代表人物中有些并非来自英格兰区域或联合王国本土;相反,该流派的一些著名代表来自澳大利亚、加拿大和南非等地),因此不少学者更愿意用另外一个名称——国际社会学派。本文倾向使用国际社会学派这个术语。
国际社会学派强调对世界政治进行历史的和制度性的分析,尤其重视对塑造世界政治至关重要的各种思想和意识形态的研究。总体上,该学派有三个基本假设:第一,它宣称国际关系是人类关系的一个分支,其核心是诸如相互依赖、安全、秩序和正义等基本价值;第二,它是以人为分析中心的学说:它号召国际关系学者去解释卷入国际关系中的人的思想和行动;第三,它接受国际无政府状态的前提,相信世界政治是一种无政府状态的社会,但具有国务人员执行对外政策所运用的独特准则、规范和制度。(注:Robert Jackson and George Sorensen,Introductionto International Relations,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p.139.)国际社会学派的经典作家很多,这里主要结合20世纪两个最具代表性的国际社会学派学者马丁·怀特(Martin Wight)和赫德利·布尔(Hedley Bull)的有关论述,对该学派的基本理论主张及方法论特征进行探讨。
一 国际社会学派与三种理论传统
怀特理解的国际政治是具有明显自身特点、问题和语言的“一个人类经验的领域”。(注:Martin Wight,International Theory:The ThreeTraditions,Leicester University Press,1991,p.1.)他认为最杰出的古典国际关系理论家(如马基雅维利、格劳秀斯和康德)的主要思想分别属于现实主义、理性主义和革命主义三种基本类型:现实主义者是指那些强调和集中关注“国际无政府状态”方面的人;理性主义者是指那些强调和关注“国际对话和交流”方面的人;而革命主义者是指那些强调和集中关注国际社会“道义统一性”的人。(注:Martin Wight,ibid,pp.7~8.)他强调现实主义、理性主义和革命主义的概念是观察国家间关系的三种不同方式,也是国际关系的基础性思想,这三种思想不是相互孤立的,而是处于对话之中,国际关系学者应当听到这三种不同声音。
现实主义把国家视为追求自身利益的权力机构,国家间的竞争和冲突是其相互关系中“生来固有的”,国际关系仅仅是手段性的关系,这就是马基雅维利的现实主义观。现实主义强调“无政府状态、权力政治和战争因素”,它更关注实际怎样(即“是什么”),而不是关注理想状态(即“应当是什么”)。现实主义往往对人性持悲观主义态度,这暗示着世界政治不能进步,而总是一个不断重现和重复的领域。极端的现实主义甚至否认国际社会的存在,认为只存在霍布斯描述的自然状态,惟一的政治社会和实际上的道义共同体就是国家,国家之上或国家之间没有国际义务。
理性主义把国家视为根据国际法和外交实践运作的合法组织,它把国际关系看做基于相互承认的主权国家权威按规则管理的活动,这是格劳秀斯的理性主义观。理性主义理论家相信人是理性的,人可以辨明善行,可以从自己的错误和他人那里学到一些东西。即使在国际无政府状态下没有共同政府,人们也可以理智地设法生活在一起。极端的理性主义相信国家间可以是相互尊重、和谐和法治的完美世界。这样,理性主义就界定了国际政治的一条“中间道路”,把悲观主义的现实主义和乐观主义的革命主义区分开了。
革命主义降低了国家的重要性,强调人的重要性,认为人构成一个基本的“世界共同体”或者“人类共同体”,该共同体比国际社会更重要。这就是康德的革命主义观。革命主义理论家使自己认同人性,并相信超越国家之上的人类社会的“道义统一性”。(注:Martin Wight,ibid,pp.8~12.)他们是世界主义思想家,而不是国家中心主义思想家,其国际理论具有一种渐进的、甚至是传教士式的特点,因为他们旨在使世界变得更美好。革命性的社会变化是其目标,无论是基于革命性的宗教,还是基于革命性的意识形态,都涉及某种理想世界的产生。革命主义者对人性持乐观态度:他们相信人类的完美性,国际历史的最终目的是使人类得到满足和自由。极端的革命主义则认为,地球上推一真正的社会是由每一个人组成的世界社会。(注:Robert Jackson and George Sorensen,Introduction toInternational Relations,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p.148.)
怀特把国际关系视为现实主义、理性主义和革命主义之间永不停顿的对话。现实主义强调无政府状态和权力政治;理性主义强调社会和国际法;革命主义强调人道主义、人权和人类正义。单单通过这些理论归纳中的任何一个都不能充分理解国际关系,这三种思想对于全面均衡地理解国际关系都是非常必要的。国际社会理论应当是对这三种不同理论观点之间对话和交流的一种探索,它们都分别代表了一种各具特色的关于外交政策和其他国际人类活动的规范性主张。国际社会学派理论的关键是这些主要思想在世界政治中的作用。尽管历史受到重视,但是思想史处于该理论传统的核心。该学派强调,不能简单地说这些思想中哪一种是“真”,哪一种是“假”,因为它们仅仅代表了相互竞争的不同的世界政治基本道义观。每种思想都不完善,因为它只是抓住了国际关系的一个层面。每种思想本身都是一种不充分的国际关系理论,但它们合在一起就可以在国际关系理论中发挥一种必不可少的作用。
二 国际社会学派关于国际社会的界定
国际社会学派理论的核心概念就是国际社会。国际政治被该学派理解为缺乏等级制权威的一个特殊政治分支,没有一个高于主权国家的世界政府。但是,仍然有一些由国家创立和共享的、并有助于塑造国家关系的共同利益、制度、规则和组织。这种国际社会条件被赫德利·布尔概括为“无政府社会”。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并非意味着混乱无序,而是具有某些准则、制度和价值规范可循,只不过是缺乏一个统一的世界政府而已。
布尔对“国际体系”和“国际社会”做了重要区分。他认为,当两个或多个国家相互间具有足够联系,并且充分影响相互间的决定,以至于使每一方的行为成为另一方考虑的必要因素时,国际体系就形成了……国际社会是在这种条件下才存在:即当一组国家意识到某些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在它们感觉到它们自己受相互关系中的一套共同准则约束并且分享那些共同机制的运作益处时,才形成一个社会。(注:Hedley Bull,The Anarchical Society:A Study of Order in World Politics,2nd end.Macmillan,1995,pp.9~13.)从该区分中可见,国际社会学派认定国际体系是一个比国际社会更基础的概念。布尔等人从历史角度考察后认为,欧洲的扩张开始于15世纪,这时国际体系便处于创造的过程中,而国际社会仍远没有出现,真正全球性的国际社会是在19世纪后期才开始形成的。(注:参阅王逸舟著:《西方国际政治学:历史与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73页。)就此而言,国际体系在历史上早于国际社会而出现。按照该学派的理解,国际社会首先在欧洲出现,这是与欧洲近代国际体系的“先进性”和首创性联系在一起的,并且认为欧洲国际社会仅仅是更大的国际体系的一部分。
由于强调“国际社会”是国际关系的核心问题和理论思考的基本出发点,以布尔为代表的国际社会学派理论家对“国际社会”这个关键概念做了特别界定:它是“一个由国家组成的集团(或者更一般地讲,一个由独立的政治共同体组成的集团),这个集团不只构成了一个体系(即每个个体的行为都构成其他个体权衡的必要因素),而且通过对话和共同规则及制度,建立了引导相互关系及行为的准则,所有成员都认识到,他们的共同利益在于维护这些安排。”(注:参阅王逸舟著:《西方国际政治学:历史与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72~373页。)在这种国际社会里,主权国家在交往中遵循特定的准则,服从一定的目标,从事彼此间的合作,形成一种特殊的共同体。与这种国际社会相适应的国际关系,特别需要尊重道德和国际法,需要建立起一整套与之相关联的运行机制和国际规范。这样,“国际关系一个未言明的事实是,它既不是霍布斯所描述的无政府状态下的相互冲突局面,也不是康德所说的简单超越国际无政府状态、实现联邦制或其他形式的自由联合,而是主权国家在没有统一国际政府情况下的合作与协调式的共处。”(注:参阅王逸舟著:《西方国际政治学:历史与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65页。)
国际社会学派把国际关系看做是主权国家组成的国际社会,国家和国务人员的对外政策往往是其分析焦点。他们认为国际关系由国务人员的对外政策和活动构成,这些国务人员代表以领土为基地的政治系统采取行动,这些政治系统相互独立,并且不从属任何高于它们自己的权威机构,即它们是主权国家。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跨国公司等虽然是涉及国际关系的重要人类组织,但它们从属于主权国家,它们不能完全独立于国家而行动。这就是国际社会学派视主权国家为世界政治基础的主要原因,这也是他们分析国际社会的基本图景。
三 国际社会学派关于基本价值的分析
如果说怀特着重思考了国际关系中那些基础性思想的能动的相互作用,那么,布尔则极力构建一种比较系统的国际社会理论。国际社会学派认为国际关系是涉及基本价值的人类活动,对秩序、正义、国家主权和人权这些基本价值的讨论是该学派理论的重要内容。
在各种基本价值中,布尔特别关注国际秩序和国际正义。他所谓的“国际秩序”,是指支持国际社会基本目标的国际活动的模式和安排;他所说的“国际正义”,是指授予国家和民族权利和义务(如自决权利、不干涉权利和所有主权国家被平等对待的权利)的道义准则。(注:Hedley Bull,The Anarchical Society:A Study ofOrder in World Politics,2nd edn.Macmillan,1995,p.78.)布尔认为,无政府社会的要点是促进和保护国际秩序,国际秩序被界定为国际活动的一种模式或安排,它支持国际社会那些基本的、主要的或普遍的目标。他确定了四种目标:维持国际社会;拥护成员国的独立;维护和平;帮助保护所有社会生活的规范基础,包括暴力的限制(体现在战争法中)、信守承诺(体现在互惠性原则中)及所有权的稳定性(体现在相互承认国家主权的原则中)。布尔认为这些都是无政府社会的最根本目标,所有这些目标都具有道义性特点,它们不仅仅是手段性的或完全自利性的,既是为他人也是为自己。这些主张体现了国际社会学派对世界政治进行规范分析的倾向。
布尔还区分了世界政治的三种秩序:(注:Hedley Bull,ibid,pp.3~21.)一是“社会生活秩序”(order in social life),无论采取何种形式,它都是人类关系的一个基本要素;二是“国际秩序”(international order),它是国际体系或国际社会中国家间的秩序;三是“世界秩序”(world order),它是作为整体的全人类之间的秩序。他进一步指出,“世界秩序比国际秩序更重要、更根本,因为整个人类大社会的最终单位不是国家,而是单个的个人”,国家和国际社会只是暂时的——它们仅仅是人类关系的历史性安排,但是“单个的个人……是永久的和不可毁灭的,在某种意义上由个人组成的团体则不是”。这就是布尔国际关系理论中的世界主义倾向。但是,布尔的大多数分析主要是关于国家和国际社会。他特别强调,维持国际秩序的责任属于大国,并且是通过管理它们相互间的关系实现的。大国的这种特殊作用和责任来源于国家间权力深刻不平等的现实。布尔通过历史分析认为,尽管大国的重要使命是维持均势并防止任何大国失去控制而造成灾难,但许多大国的行为表明它们在国际社会中常常表现得并不真正负责任:在他看来,两次世界大战、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标志着大国责任的深刻失败。
布尔强调国际社会不仅关注秩序,而且关注正义。他界定了各种各样的正义概念,但他特别区分了国际关系中的“交换正义”(commutative justice)和“分配正义”(distributive justice)。交换正义是关于程序和互惠的正义,它包括国家间要求和反要求的过程。国家如同市场中的公司,每个公司在经济竞争的框架内尽最大努力争取成功,这预先假定了一个公平的比赛场地:所有的公司都根据市场的相同规则比赛;同样,所有的国家按照国际社会的同一规则比赛,正义就是比赛规则的公平性,即同样的规则以同样的方式适用于任何人。国际社会的比赛规则通过国际法和外交实践来表达。这就是交换正义,它是国际正义的主要形式。分配正义是关于好处的,它涉及好处应当如何在国家间分配的问题,正如一种想法所说的,“正义要求把经济资源从富国转移到穷国”,这样,分配正义就强调:穷国和弱国应得到特别待遇,如发展援助等。这意味着不是所有国家都按照相同的规则进行比赛,有些国家取得特殊待遇。与交换正义相比,分配正义处于次要地位,因为分配正义涉及的规范事务获得解决的最合适框架是主权国家,分配正义通常被理解为国内政治事务而不是国际政治事务。但是,随着全球日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分配正义的问题已经日益侵蚀到国际关系中。(注:Robert Jackson and George Sorensen,Introductionto International Relations,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pp.156~157.)
正如区分三种秩序那样,布尔区分了世界政治中三个层次的正义:一是“国际正义”,它基本上包括国家主权平等的观念;二是“个人正义”,它基本上是涉及人权的思想;三是“世界正义”,它基本上包括对整个世界来说什么是正确的或好的,如在全球环境标准上表现很明显。从历史上看,国际正义通常在世界政治中占主导,自20世纪起,后两种层次的正义已经变得更突出,但它们还没有取代国际正义这个层次,因为世界政治中的大多数正义问题仍然是在国际正义的层次上阐述的。布尔在结束对秩序和正义的讨论时还考察了这两种价值在世界政治中的相对分量,秩序被认为是更根本性的,“秩序是实现其他价值的条件”,(注:Hedley Bull,op cit.p.93.)即秩序优先于正义。但他特别强调这只是个一般性的论断,在特定情况下正义也许是第一位的。例如,人们普遍认为,有关亚非一些民族的自决和国家主权的国际正义在道义上优先于西方殖民主义在那些地区的国际秩序。这里,布尔的主要观点是世界政治既涉及秩序又包括正义问题,如果只专注一种价值而排斥另一种价值,就不能充分理解世界政治。”
与正义和秩序密切相关的国家主权和人权这两个基本价值受到国际社会学派另一代表人物约翰·文森特(John Vincent)的特别强调。他在《人权与国际关系》的专著中较详细地阐述了人权的理论、实践和政策。根据文森特的理解,一方面,国家应当相互尊重独立,这是国家主权和不干涉的基本价值;另一方面,国际关系不仅涉及国家,而且涉及个人,不管他们是哪个国家的公民,他们都拥有人权。他认为随着20世纪后半期许多关于人权的国际宣言和公约的增加,国内社会和国际社会之间的“边界”已经变得更加模糊,因为关于人权的国际法开始让国家接受外界监督并推动超越不干涉原则的趋向。在不干涉权利和人权之间有时会有冲突,当这种情况发生时,这些价值中哪些应当有优先权?如果人权在一国内部受到大规模侵害,能否有一种人道主义干预?这是当前国际关系中十分复杂的基本价值冲突之一。国际社会学派对这些问题主要作出了两种回答:一是多元主义(pluralist)的回答,它强调国家主权的重要性,认为国际社会中的权利和义务授予了主权国家,个人仅有他们自己国家所给予的权利。因此,尊重主权和不干涉原则总是第一位的,国家无权因人道理由干涉他国。二是社会连带主义(solidarism)的回答,强调作为国际社会根本成员的个人的重要性,认为国家既有权利也有义务进行干预,以便缓和人类不幸的极端情况。用文森特的话说就是,“这是人道主义干涉的理论:如果某个国家因其所作所为而激起人类良知的义愤,局外人即有责任作出反应。”(注:[英]R.J.文森特著:《人权与国际关系》,知识出版社,1998年中文版,第175页。)应当指出,近年来西方国家宣称的“人权高于主权”、“人权无国界”等论调与国际社会学派的这种人道主义干涉理论有密切的理论渊源。换言之,国际社会理论的这种主张对近年来西方国家对外政策中奉行的新干涉主义有较大影响。
四 国际社会学派理论的方法论特征
国际社会学派主要从历史、哲学、法律、社会学等视角阐述其理论主张,具有浓厚的欧洲传统学派特色。就方法论而言,国际社会学派属于国际关系理论中的传统主义。布尔把这种传统的国际社会理论方法概括为:它来源于“哲学、历史和法律”,它尤其体现了明确依靠“使用判断力”。(注:Hedley Bull,"International Theory:The Case fora Classical Approach",in K.Knorr and J.N.Rosenau(eds.),Contending Approaches to International Politics.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69.P.20.)布尔所谓的“使用判断力”是指,国际关系学者应充分理解:对外政策有时向有关的国务人员(特别是国家领导人)提出了困难的道义选择,即关于相互冲突的政治价值和目标的选择,如对外政策中关于参战的决定和参加人道主义干预的那些决定。
传统主义和行为主义之间的争论被称为国际关系理论的第二次大论战。(第一次大论战是指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的争论)。与第一次论战相比,第二次大论战更多地表现为方法论的争论。传统主义基本上是以人为中心的方法,强调释义性分析、规范分析和历史的具体的分析方法;行为主义则主要是以结构为中心的方法,强调解释性分析、实证分析和分析抽象的方法。(注:Robert Jackson and George Sorensen,ibid,p141.)在这场论战中,国际社会学派基本上是坚定地站在传统主义一方。
国际社会学派强调理解国际社会不是应用社会科学模型的问题,而是一个熟悉国际关系史的问题。该学派理论家尤其重视近现代欧洲国际关系史和欧洲政治思想史,强调欧洲的历史经验在塑造其“国际社会”观念中的启迪作用。他们认为,主权的独立国家,近代的国家间体系,依照国际法和国际惯例相互交往的准则,以及一整套制度性规则等等内容,仅仅是建立国际社会的必要条件;真正实现这个社会,还必须依靠共同的文化和心理基础,依靠共同的思想和价值观念,或者至少依靠对这些文化心理结构和思想价值的先进性的某种承认或认同。(注:王逸舟著:《西方国际政治学:历史与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67页。)因此,该学派特别注意总结和分析欧洲国家体系和世界其他主要国家体系的历史经验,并在其理论体系中对国际法、国际规范及西方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等都予以高度重视。
国际社会学派没有把国际关系理论看做是运用和验证模型和假设的一种价值中立的科学。他们不像行为主义那样极力追求以所谓的“科学方法”去解释国际关系;相反,他们谋求尽力理解和诠释国际关系的自身含义。例如,按照国际社会学派的方法,对干预和人权问题可以进行规范研究,即进行哲学的、历史的和法律上的研究,但是不能对它们进行行为主义式的“科学研究”,因为这些问题根本上是涉及价值规范的人类事务,对它们不可能有价值中立的科学回答,也不可能有抽象的或一般性的回答。又如,深受行为主义影响的新现实主义代表人物肯尼思·沃尔兹在其名著《国际政治理论》中有这样的主张:由于有一种按照“法则似的规律”运作的国际政治“结构”,因而从国际政治的“科学”理论中推导出各种“预见”是可能的。国际社会学派理论家从根本上不同意此观点,他们看不到根据自然科学的模式构筑国际关系“法则”的任何可能性。对他们而言,那种行为主义的方法是有缺陷的:因为它是建立在对国际关系特点的一种理性误解的基础上的。国家不是独自存在的,国家不能脱离人类(国民及其政府)而存在,国民和政府组成国家并代表国家行动。因此,对国际社会学派来讲,国际关系完全是一个人类关系的领域,是发生在特定历史时代并涉及准则、规范和价值的人类关系的一个特殊分支,主张国际关系理论是强调理解性的而不是解释性的政治理论分支。换言之,他们认为国际关系是一个涉及规范的主题,不可能用非规范性术语来充分理解它,行为主义所追求的价值中立难以真正理解国际关系的本质,因为绝大多数国际活动都具有重要的规范性因素,而这些因素都是国际社会学派的关注点。
总之,国际社会学派通过坚定地拒绝行为主义的方法而坚持了传统主义的方法,从而使该学派的理论在行为主义挑战面前继续保持了自己的特色。与深受行为主义影响的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学派相比,国际社会学派的方法论明显具有传统主义的特征,这也是它在当代国际关系理论中颇具特色的一个重要体现。
五 对国际社会学派的简要评判
国际社会学派体现了传统国际关系学术研究的一条“中间道路”:它在传统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之间开辟了一个领域,并将此领域建设成为一个有显著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
国际社会学派承认权力在国际事务中的重要性,也关注国家和国家体系,但又摈弃了现实主义关于世界政治就是霍布斯描述的自然状态、当中没有任何国际规范和准则的狭隘观点,认为权力和法律都是国际关系的重要特点。当然,该学派也承认个人的重要性。但与很多自由主义者不同,他们往往把政府间组织和非政府间组织看做是世界政治的边缘性特点而不是核心特点。他们强调国家间关系,然而对跨国关系的重要性重视不足。该学派承认国际体系的主要因素既有现实主义因素(权力、国家利益),也有自由主义因素(准则、国际法)。因此,它建立在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基础上,并且以不同于二者的另一种方式综合并扩展了它们的观点。这在一定程度上为国际关系研究增添了一种新的视角。它强调国际社会中既有冲突,又有合作,既有国家,也有个人,主张需要对产生于复杂形势下的国际问题和对外政策困境进行整体的和历史的分析,这对于当代国际关系研究具有重要理论启发价值。此外,国际社会学派提出有关“国家/社会”关系的一些有价值的议题,特别是关于“国际社会”命题对于人们观察现实世界的力量分布和政治态度,提供了一个不无益处的视角。(注:参阅王逸舟著:《西方国际政治学:历史与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77~381页。)
尽管国际社会学派试图提供一种全面理解国际关系的理论,并且为此做出很大努力,提出了不少有启发性的思想,但是,由于理论的局限性,它自然也受到其他学派的批评。现实主义对布尔所描述的“国际社会”特点(国家在相互关系中受共同准则的约束,并且拥有共同机制的运作)深表怀疑,认为国家只受各自国家利益的约束,国际社会学派所谓的国家也受其他某些准则限制的论证不足,认为当国际义务和国家利益之间有冲突时,后者往往占上风,因为国家的最根本关注总是自己的利益,特别是生存与安全。鉴于国际社会学派试图把现实主义、理性主义和革命主义结合在一个单一的框架内,鉴于它既强调国际秩序,又强调国际正义,现实主义批评国际社会理论具有严重的不连贯性。自由主义则批评国际社会学派对国际关系中的国内政治作用缺乏兴趣,认为国际社会理论在国际关系和国家的内部政治之间划分了一条明显的界限,对国家对外政策的国内方面考察不足;他们还批评国际社会学派不能解释国际关系中的渐进性变化。此外,国际政治经济学(IPE)针对国际社会学派的主要批评是,认为国际社会理论忽视了国际关系中的经济方面和社会—阶级方面,认为怀特和布尔等人把他们的最主要关注放到国际政治上,而极大地忽视了国际经济。(注:关于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国际政治经济学对国际社会学派比较详细的批评,参阅Robert Jackson andGeorge Sorensen,Introduction to International Relations,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pp.166~170.)不管这些批评是否完全有道理,但至少向我们提示了这样的信息:国际社会学派和其他理论流派一样也不是完美无瑕。正是这些不同争论推动了国际关系理论的不断丰富和发展。
在承认该学派有启迪价值的同时,也应该清醒地看到它的某些思想对当代国际关系可能产生的一些负面影响。由于该学派强调西方文明价值规范和欧洲的历史经验在塑造他们所说的“国际社会”的关键作用,这就使他们的理论主张不可避免地带有“欧洲中心主义”或“白人至上主义”的思想色彩。正如有学者指出的,英国学派最初的“国际社会”构想,完全是一种排他式的“欧洲中心”模式。(注:参阅王逸舟著:《西方国际政治学:历史与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78页。)虽然有学者开始承认文明差异和“异质文化”的存在也可以是建立国际社会的出发点,但国际社会学派的主流思想从内心深处仍然是崇尚西方的文明和价值规范,谋求构建一个以西方价值规范为主导的国际关系体系。就此而言,这种理论明显地在突出西方的文明优越感,当然难以使目前大多数非西方文明国家认可。与之相联系,国际社会理论的一些主张明显为国际干涉打开大门。如果按照西方价值标准构建国际社会框架,极可能为西方国家以人权和人道主义为借口进行所谓“合理的、合法的干涉”提供理论依据。冷战结束后西方国家对外政策中“新干涉主义”的盛行不能说与国际社会理论的某些主张无关。完全以西方的人权标准来衡量当今国际社会,自然有许多所谓“不达标、不合格”的成员,但如果借此作为推行人道主义干预的理由,只能使国际社会出现更多的动荡和不安。近年来西方在世界许多地区的所谓人道干预的种种教训已经有力地说明了这一点。
标签:国际关系论文; 世界政治论文; 世界主义论文; 行为主义理论论文; 社会学论文; 时政外交论文; 国际秩序论文; 经济学派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社会关系论文; 理性主义论文; 历史学论文; 国际政治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