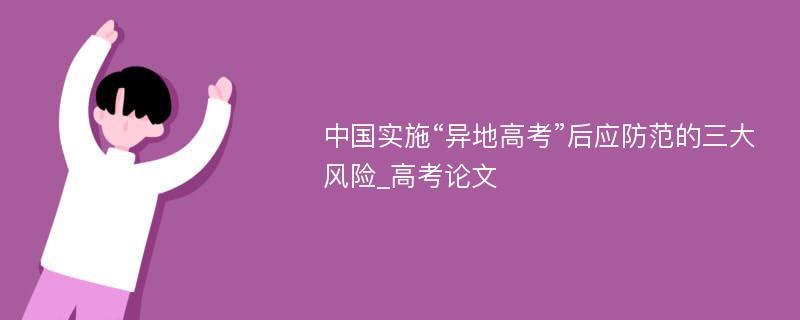
中国实施“异地高考”政策后亟待预防的三重风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异地论文,中国论文,风险论文,政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尽管2013年初,中国一线中心城市出台的“异地高考”公共政策限制标准依然很高,甚至像北京这样的中心城市根本就没有提及普通高校层次招收非本地户籍生源参加本地高考的相关准入标准问题,但总体而论,大多数省市在年初陆续出台的“异地高考”公共政策还是明确了“开放性”的异地高考价值导向。无论这种开放是有限度的还是彻底性的,其重要功效是宣告了在关于“异地高考”这场激烈的时局争鸣中,单纯行政性的政策“堵截”与选择性“无视”是无效的,唯有公共治理式的“开放”与有效性“回应”才是可行的。由此,关于“异地高考”的命题争鸣注定需要升级到崭新的2.0版本,即由以前“堵”与“开”的二元对立式价值性问题讨论(1.0版本)过渡到“如何开”的具体性问题破解(2.0版本),究竟是“有限度的疏导式放开”还是“彻底性的洪流式放开”,前者是从城市资源扩量难的进路出发,后者是从个体权利真正实现的进路出发,这些相互交叉平行的问题研究进路无疑成为困惑“异地高考”政策设计者的新命题。基于此,我们需要暂时抛开为2.0版本的各种问题匆忙找寻灵丹妙药的对策式研究思路,而转入讨论彻底放开或有限度放开之后可能面临的各种风险,希冀在明确不同维度的可能风险之后进而能够化解2.0版本中的各种危机。
一、“异地高考”公共政策的彻底放开或者有限度放开并不能使中国城市的中低层群体获益,相反很可能成为共同的牺牲者
从社会阶层的角度来看待异地高考问题,不难发现,即便“异地高考”政策彻底无门槛地放开,真正受益的阶层群体也是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占优势的群体,而城乡社会中真正的中低层群体与这种城市教育资源的利益流出是无关的,甚至很可能成为这种利益流出的牺牲者。面对大批量的外来高考移民,城市中低层群体曾因城市教育资源总量大而附带受益的唯一优势将不复存在。因为能够进入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就读且就考的高考移民,绝大多数都是在中国其他地区占有各种不同资本的优势阶层,在资本相互转化尚需不菲成本的中国社会,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的优势阶层无疑会通过更轻便有利的方式完成家族内部的文化资本积累。事实上,中国社会阶层真正完成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的优势积累也仅仅是近10年以来的事,在短短的10年中,刚刚完成经济资本与社会资本积累的新富阶层又在进一步大规模完成中国式的文化资本积累与转化,这对于教育资源特别是国内优质教育机会资源和教育服务资源总体不足的当下中国而言,要满足这种不断膨胀的教育需求无疑是困难的,因此摆在这批资本优势阶层面前的路无疑有两条:一是送子女出国留学以完成文化资本的积累。近年来出国留学的重心愈来愈低,全国各地纷纷举办以高中生为主体的国际班或者国际学校,这批低龄高中学生之所以选择出国留洋,原因是其在与国内同龄人激烈竞争的高考中处于劣势,很难获得进入名牌大学就读的机会。与此同时,这批新富阶层又基于自身所把持的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通过就业、薪酬、培训、媒介等管道无限夸大洋学历的社会含金量,使其在社会阶层的流动中愈来愈扮演核心的群体认同符号。另一条路是通过“购房”、“关系”等管道入户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或者入户高考受特殊照顾而更容易考上的民族、边远地区来参加“异地高考”,对他们而言,直接在北京、上海这样的中心城市接受优质的高中教育,甚至义务教育无疑更好。而“异地高考”政策一旦彻底放开,甚至即便是有条件的高门槛放开,也会进一步降低这批高考移民的文化资本积累与转化成本,而在教育机会资源总量固定的城市中,由此受到损害的无疑是城市中低阶层。
事实上,“一直行走在路上”的中国教育公平之路的确不可能一蹴而就,它毕竟是社会公平体系的一个子系统,“教育优先”与“教育公平”作为社会公平基石的国家性承诺并不意味着教育在事实上不受到社会现实复杂利益博弈因素的掣肘。教育无论如何强调形式与程序公平,都无法回避其实质意义上要履行的阶层再生产和文化再生产功能,而这种再生产的编码管道与筛选手段注定要被社会优势阶层所赋值,无论这种赋值是显性的还是隐性的。
二、一般的城市外来务工人员并不能在这种彻底放开或者有限度放开的“异地高考”政策中真正获益,相反很可能遭遇“二次剥夺”
表面上看,城市外来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如果能够在北京、上海入读高中且就地参加高考,无疑能够在亲情上得到极大的满足,但这种满足感将很快被城市高成本的生活负担、不公正的身份歧视、城市社会中被资本系统化了的各式区隔以及多数以上学业成绩落后的事实所抵消,大多数一般的城市外来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将会在这种社会生态中成为“入不了城又回不了乡”的城市“蝙蝠”,这种社会生态对随迁子女在“阶层再生产”与“文化再生产”方面所造成的身份意识认同的恶性效果无疑比学校教育更大。同时,彻底放开的“异地高考”也很难真正提升随迁子女被重点大学录取的比例,形式上合法的高考制度设计在实质上隐藏了知识层面中的不公正性。大量的实证研究表明,重点大学的录取比例分层与社会优势阶层的结构分布是趋同的,即越是优势的社会阶层其子女越可能被重点大学录取,而对于城乡社会中的最底层来说,其子女重点大学的录取比例最低,这种状况不仅在高考中有所反映,甚至在义务教育阶段中也有类似的明晰分层。
笔者曾于2011年对中国中部的D县和西部的X县进行实证调研后发现,父母属于外出务工人员的子女学困率较之公务员、专业技术人员、企业员工、自雇以及务农等其他社会职业,都分别属于最高(D县父亲为外出打工的子女其学困率达14.21%,母亲为13.21%;X县父亲为14.83%,母亲为14.53%)。同时,父母属于外出务工人员的子女厌学率也是最高的,且学困率和厌学率还与父母亲受教育程度成反比(D县父亲受教育程度在小学及以下的,其子女学困率高达14.06%、厌学率高达19.35%;母亲教育程度在小学及以下的,其子女学困率高达15.91%,厌学率高达15.29%;父亲受教育程度在大专及以上的,其子女学困率仅4.46%,厌学率仅7.79%;母亲受教育程度在大专及以上的,其子女学困率仅3.50%,厌学率仅8.80%。而X县此类资料分别为13.76%、16.26%、14.31%、13.37%、7.36%、3.07%、7.53%和4.4%)。[1]笔者于2012年对国家中心城市C市进行调研后同样发现,在该市全国著名的教育文化区中,外来打工人员子女较之其他社会职业子女的学困率、厌学率也是最高,而学困率和厌学率仍然与父母亲的受教育程度成反比。可见,如果仅是单纯放开“异地高考”,而不对总体上受教育程度不高的外来务工人员子女采取有针对性的教育补偿或者更高质量的教育服务,那么这批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将很难在教育结果层面上考入重点大学,从而实现教育意义上的阶层向上流动。同时,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在面对其他不断涌入的拥有各式资本优势的高考移民时,其应对挑战的能力将更为脆弱,此时,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将遭遇事实上的“二次剥夺”。一方面,在移入城市参加高考的竞争将更为激烈,当前一线城市的教育溢出利益将很快被蜂拥而入的利益群体所抵消;另一方面,在移入城市接受教育,且不论这种教育对外来务工人员子女是否真正是高质量的(事实上,在城市教育扩容难的当下,人口涌入将进一步加剧城市的大班额状况,人均受教育服务的质量也被迫下降),也不论一般的外来务工人员家庭是否能够承担城市高额的教育负担,即便当外来务工人员子女想退出城市而返回老家参加高考,也几乎不大可能,因为他们已经很难适应各省不同的高考模式,而在老家,他们同样也面临一大批在利益核算中有利可图以至于对该省高考模式驾轻就熟的高考移民们。
三、“异地高考”政策的彻底放开或者有限度的放开将进一步加剧中国农村社会的衰败和农村教育的衰落
如果我们跳出利益群体之争,而从国家的整体视角出发来理性看待中国的教育整体,不难发现,作为具有强政策引导性的“异地高考”如果彻底放开,将极有可能进一步加剧中国农村社会的衰败和农村教育的衰落。伴随着中国社会三十年的整体结构变迁,县以下的中国农村社会无疑被作为大城市“人”、“财”、“物”等资源的蓄水池而存在,城市源源不断地从农村社会单向吸纳资源要素,中国农村社会的传统宗族共同体形态在上世纪90年代短暂恢复后又在农村人口大量外出务工的时代潮流中迅速解体,农村只剩下大量的老人、小孩以及少量的妇女,这些弱势群体几乎都是以原子化的状态散落在中国村落小区之中,传统意义上的教化与仪式逐渐变成私人家庭的内部事宜,村庄的公共性在这种个体化的力量增长中渐趋消弭。在原子化的村庄中,个人只关心私人利益,以致他们很难形成地方性的利益组织以缓冲行政权力和市场权力的单向度垂直控制,他们几乎成为村庄公共事务的局外人,除非这种公共事务直接关乎个人利益。在这样的村落政治生态背景中,我们才可以理解为何十年来中国农村学校布局结构调整能够如此迅速,而2012年校车事故频发后,农村学校为何又能够在村落社会中迅速地恢复。乡校之所以能够在村落社会中轻易出入实质上正是源于行政力量对村落社会的全面控制与过度渗透,地方保护性力量明显不足。在行政力量深刻控制村落的当下,如果彻底放开“异地高考”,无疑将进一步吸纳农村中大量的剩余小孩和少量妇女进入城市,前者以就学的名义进城,后者以照顾孩子的名义进城,农村将彻底成为名副其实的空壳村和老人村,中国教育将进一步出现结构性匮乏与拥堵并存的现象,乡校因生源不足而进一步撤并,而在城市,大班额现象将进一步突出,农村教育将进一步衰落直至终结,而作为村落社会的文化子宫与公共空间,学校的终结在本质上意味着村落的终结。
另外,普通中国人最重视代际阶层的上升流动,即便这种代际流动仅仅是短距离上升流动,他们也能够得以满足。而在农村社会,在参军越来越难以改变身份的今天,教育几乎成为唯一能够实现代际上升流动的管道。因此,在孩子没有被宣告教育失败而被迫淘汰出教育筛选体系之前,外出务工人员家庭最重视的仍是下一代的子女教育问题,因此从城市中赚得的大量收入几乎有一大半都用在了子女的教育投资上,在“异地高考”尚未放开的情况下,这些孩子无疑大多都是在县以下的学校学习和生活,城市单向从农村攫取的资源通过外出打工人员所赚取的收入而源源不断地回流给子女,子女因为在县以下接受教育和生活又将这些大量的城市资金回流到县及县以下的农村社会。这样,城市对农村通过外来务工人员这一中介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反哺,从而盘活了县及县以下的产业链,为农村社会提供了大量的就业岗位,实现了城乡社会内部资源要素的良性循环。如果“异地高考”彻底放开,这条城乡社会相互流动的资源链条无疑将被切断,农村社会必将进一步走向衰败。
随着中国新生代移民对旧生代移民的快速更替,这种加速中国农村社会衰败和农村教育衰落的趋势将更为明显。一份遍及北京、上海、重庆等全国13个省、直辖市涉及2501名新生代农民工的实证调研资料表明,[2]当前新生代外出农民工将在城市中务工所赚取收入的主要部分用于城市消费的比例已占该群体的40.6%,而主要邮寄回家的仅占32.3%,这与老一代农民工几乎百分百地将城市收入的主要部分邮寄回家的状况形成鲜明对比。这一方面源于城市社会通过权力和资本抬高城市生活成本,据调研资料表明,高达56%的农民工受访者将其在城市中的日常消费(包括衣、食、交通等开支)列为其收入的最大开销,还不算在城市中的其它消费,如聚会、手机和上网以及学习进修等开支;另一方面,新生代农民工较之老一代农民工更与农业、农村、农民三位一体的中国式农耕生活疏远,其深层意义上具有更为强烈地融入城市和适应城市的主动性,[3]在价值观念上自我意识过于凸显,主流价值观渐趋弱化,[4]更追求个体满足、瞬时享乐和身份认同。同时,新生代农民工的受教育程度相对更高,外部普遍性知识较之存在于乡土中的地方性知识对其影响更深,他们天然地在“亲城逆农”的城市现代性意识建构中完成了其注定的乡土叛逃。数据显示,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农民工,其将收入主要用于城市消费的比重越大(小学以下学历的为32.61%,而大专及以上为57.79%),同时邮寄回家的比重越小(小学以下学历的为41.40%,大专及以上的为13.03%)。可见,如果彻底放开“异地高考”,这条自发的城市资源向农村回流的资金生态链将在新生代农民工难以抑制的城市狂热中彻底断裂,农村社会和农村教育不可抑制地将走向衰退。
当“异地高考”政策彻底或者有限度地放开之后,以上三重危机无疑是相关政策在下一步精细化研发和具体化操作时需要深入考虑的,如何预防性地化解这些潜在风险,从而更好地破解“异地高考”这一难题,决定了“异地高考”公共政策的成败与否,而厘清这种复杂性则是深化“异地高考”政策设计的关键一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