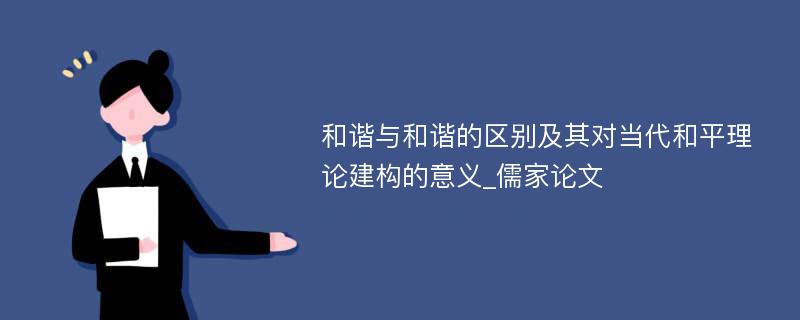
“和同之辨”及其对当代和平理论构建的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其对论文,当代论文,和平论文,意义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和平”问题,作为世纪之交的世界性主题之一,已越来越受到人们的普遍关注和高度重视。但是,在对这一问题的所有回应中,理论的回应却犹显平乏。这一情形与当代和平理论的构建不能从传统文化中吸取有意义的思想资源不无关系。笔者认为,“和”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个重要观念不仅造就了中华民族爱好和平的民族性格,而且古代哲人们对这一观念的理论探讨及其特有的理论形式即“和同之辨”,对当代和平理论的构建提供了十分重要的思想资源和非常有意义的启示。
一 “和”观念的起源及其文化意蕴
欲明了“和同之辨”的思想意蕴,必须从“和”观念的产生及其文化意蕴开始。“和”,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是一个非常古老的观念。它最早根植于中国早期的农耕文明中,与早期人类的物质生活、文化生活和宗法奴隶制有着密切的联系。
从辞源学的角度看,“和”之为字,在先秦经传中有三种写法,写作楷书,即和、盉、龢。“和”字在先秦经传中所存在的上述字型之异,我认为是值得玩味的,它提供了一个搞清楚“和”观念起源的线索。《说文》认为,“凡和之属,皆从禾。”“和”字实际上是人类生活需要同农业生产之间关系的反映,它代表着主体与客体之间的价值联系。如“和”,从禾口,“口”,《说文》曰:“口,人所言食也。”故“和”的原初之义是客体的“禾”满足了主体人的物质生活需要,可以说此“和”乃“饮食之和”也;而“盉”,从禾皿,皿是古代的一种酒器或调具,也与饮食有关,可归于“饮食之和”之例;而“龢”字与和、盉不同,它从龠禾,《说文》认为,“龠,乐之竹管,三孔,以和众声也”,与音乐艺术有关,它满足的是人类的精神生活需要,可称之为“音乐之和”。综合言之,“和”之为字,其含义的产生确与中国古代农业生产有着密切的关联,“和”者合也,协调也,相应也,和谐也,便是“和”字的主要含义。
从文献学的角度看,“和”的思想在《易经》、《尚书》等古文献中不仅屡被提及,而且又有新的发展。《易·中孚》九二爻辞曰:“鸣鹤在阳,其子和之”;《易·兑》初九爻辞曰:“和兑,吉”。《尚书》中“和”字共44见,如“自作不和,尔惟和哉。尔室不睦,尔惟和哉。尔邑克明,尔惟克勤乃事”(注:《尚书·多方》。),其意谓只有身心和顺,家庭才能和睦,才能治理好邑邦,是儒家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意;又如,“时惟尔初,不克敬于和,则无我怨”(注:《尚书·多方》。),意谓若不从始起就克敬上天之命,以和为本,将会受到上天的惩罚。由是可知,“和”的观念发展至三代时,已受到思想家们的高度重视,他们已着眼于从伦理政治的角度来探讨“和”的意义,发展出了“身心之和”和“人伦之和”两层新的涵义,并把“和”当作“敬”的对象来对待,这使“和”已开始具有了本体论的倾向。这样,我们便看到“和”观念在其产生之初已具备了自然和谐、社会和谐和精神和谐等文化意蕴。而后来的“和同之辨”就是在这些思想的基础上展开的。
二 “和同之辨”的三种理论形态
春秋时期,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一个新旧交替的时期,无论是政治、经济还是文化,都表现出了一种多元并起而旧有秩序失范的态势。这一社会历史特点给思想家们提出的问题是,如何将社会系统内部各元素组合成一个具有较强整合功能的稳定的结构形式来消解原有秩序的失范,以达到社会和平发展的目的。而肇端于史伯一直延至于孔子后学的“和同之辨”,便是当时思想家们对这一问题的一种回应。这种回应表现为三种理论形式。
1.“和平论”
由上可知,“和”观念的起源与农业生产有着内在的关联,人们对“和”的认识最初来自于饮食之和与音乐之和,所以,从饮食和音乐的角度来说,“和”成了州鸠、史伯与晏婴等思想家的重要说“和”方式,这一点也就使得“和同之辨”的展开在理论上表现为一种可名之为“和平论”的特征。
州鸠说“和”以音乐为例,他说“声应相保曰和”(注:《左传·昭公二十一年》。)。所谓“声应相保”,是指各乐音元素之间应彼此协和相互呼应之意。怎样才能协和呢?州鸠提出了“细过其主妨于正”、“细大不逾主曰平”的原则(注:《左传·昭公二十一年》。),即各乐音元素在构成音乐时,必须以主音(宫音)为主,细音(羽音)为辅,细音的音高程度不得超过主音,否则有喧宾夺主之嫌,妨碍了和谐音乐的“正”“平”要求。这表明,州鸠对“和”的理解着重于“主音有序”的意义,“和”是“和正”与“和平”之义。
史伯和晏婴说“和”亦如州鸠,是始于声味,而终于政治,不过,二人又提出了与“和”相对峙的范畴——“同”,首倡“和同之辨”。首先,他们对“和”的性质作了高度的抽象与概括,提出:“以他平他谓之和”(注:见《国语·郑语》。)。所谓“以他平他”之“他”,是指不同的事物,或一个系统内部各种不同的要素,从性质上来讲,“他”意味着“异”,从数量上说,“他”是“多”,“以他平他”就是指系统内部各要素之间要保持一种平衡协调的关系,这方是“和”。只有“和”,系统才能稳定,事物才能发展。史、晏举例说,“和”就如五行中的土与金木水火相杂以成百物,就如烹饪中五味要以各种调料才能做成,就如音乐中的宫音与商、角、征、羽音相配才能成和弦,还如婚嫁中的同姓不婚而必求于异姓,以及求财必于“有方”等一样、必须以“他”为基础,于“他”与“他”之间求得一种平衡关系,这才是“和”,否则只是“同”。所谓“同”,就是同一事物的简单相加或相济,就是“我”(而非“他”)与“我”的结合。而“我”只是一,所以,“同”实际上是一种排“他”性的自我同一,是一种“专同”(注:《左传·景公二十年》。)。正是在上述和同之辨的基础上,史、晏提出了“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著名命题,充分肯定了“和”才是事物发展的内在根据,是系统成为具有活力的生命统一体的原因,否定了“同”的价值。
其次,史、晏探讨了达到“和”的路径与方法。有关这一问题,可从两个方面看。第一,史、晏二人之辨虽不及州鸠明确地提出了“细不逾主”的等级层次论原则来作为系统和谐的基础,但他们并未将系统内各元素看作是毫无分别的等值元。第二,由于史、晏所辨针对的是当时政治上的过分专制所造成的各种弊病,这需要他们从不同于州鸠的角度来防止等级层次论向寡头断层论的转化,因此,他们和同之辨的重心便不是在系统的等级层次意义上,而是在系统的平衡性意义上。正是因为如此,史、晏二人提出了“泄其过”与“济不及”的方法(注:《左传·景公二十年》。)。所谓“泄其过”就是去掉多余的,而“济不及”就是弥补不足的。可见,这一方法的实质就是要使事物的发展保持一定的度,使之处于一种平衡状态,即“以他平他”是也。
我们知道,任何和谐的系统都必须符合平衡性原则和等级性原则两个方面,而州鸠、史、晏三人的“和同之辨”就相继将此两项原则给提出来了,但相对而言,他们更为注重平衡性原则的意义,所以,我们认为,他们的“和同之辨”实际上可以称之为“和平论”。
2.“和中论”
孔子及其儒家既继承了史、晏等人的“和平论”思想,又通过与同时代思想家的“和同之辨”,将原来的“和平”思想发展为“和中”思想,实现了“和”与中庸之道的融合。
孔子的“和同之辨”是在三个层面上展开的。第一,就如何处理人际关系来展开“和同之辨”。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注:《论语·子路》。)又曰:君子“群而不党”(注:《论语·为政》。)、“周而不比”(注:《论语·卫灵公》。)、“泰而不骄”(注:《论语·子路》。),可见,孔子有关“和同之辨”的着眼点已与史、晏有所不同,后者主要是关注政治上的君臣关系,而前者则关注日常生活中的人伦关系,因此,孔子所提出的“和同”思想就具有一种原则的普遍性。这样,孔子的“和而不同”便可理解为:既不盲目地附和他人的意见,能提出不同意见,有自己的独立见解,又能兼容不同的意见,不要求他人与自己简单地同一或一致;“同而不和”也可理解为:既盲目地迎合与附合他人的意见,只发表相同的意见,不提不同的意见,又只把自己一个人的意见看作为正确的意见,排斥和打击不同的意见和持不同意见的人。约言之,“和而不同”是一种多样性的统一性,而“同而不和”则是一种单元性的一统性。
第二,就君子独立人格的养成来展开“和同之辨”。如何才能“和而不同”呢?孔子认为关键在于成就君子人格,而君子人格的养成,必须从仁、知两方面着手。因为惟其成为仁者,才可能勇于提出不同的意见,才能有宽容的心境去兼容不同的意见;也惟其成为知者,才能对事物有独到的见解,才能鉴别不同意见的不同价值。为此,孔子特别地推出“狂狷”人格来反对“乡原”(注:《论语·子路》曰:“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论语·阳货》曰:“乡原,德之贼也。”),因为后者就是典型的“同而不和”者,而前者虽与君子尚有距离,但却具备了“和而不同”的品格。由是可知,孔子的“和同之辨”是从伦理道德哲学的方面对史、晏的“和同”理论作了丰富和发展。后来,孟子和《中庸》顺从这一路向,将“和而不同”发展成一种道德主体性的“中和”之学。
第三,从中庸学的角度进一步探讨了“和”的构建标准问题。孔子及儒家对“和”的标准问题十分关注,强调以“中”来建“和”。有关这一问题,他们是就“和”与礼的关系来展开讨论的。在《论语》中,孔子的学生有子曾云:“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之,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注:《论语·学而》。)这段话,我们以为可作为儒家“和中”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首先,儒家认为,礼作为一种伦理形式,它的结构是十分严密的,其功能在于“辨异”,在于将尊卑贵贱等级区分开来,并以此来解构系统中的混元倾向,使系统在有序中获得稳定的同时发挥其最大的功能。正因为此,“礼之为体”便具有“严”的特征(注:见《论语·学而》朱熹注。)。“严”是礼的客观特征,与之相应的主观要求便是“敬”,“凡礼之体主于敬”,“敬者礼所以立也”(注:见《论语·学而》朱熹注。)。儒家强调礼之严、敬,其目的在于倡导一种社会系统的有序和谐与稳定,这一点可视做是对传统的系统构成原则——等级原则的坚持。但是,更有意义的是,儒家在坚持等级原则的同时,又看到了这一原则对系统功能的负面影响,这就是“礼胜则离”(注:见《论语·学而》朱熹注。),即如果过分强调礼的严敬,系统中各元素的粘合力不强,就容易产生一种结构性离散,而要防止这种离散,就必须把系统的另一原则即平衡性原则引入进来,这一原则儒家表述为“和为贵”。关于“和为贵”,我们认为应从两方面去看,一是,从礼的目的来看,礼的功能虽然是“严”,但其目的却是为了社会的有序与和谐,因此,“和为贵”的首要意涵是指礼的终极目的是要实现社会和谐。二是,从礼之用即礼的具体实践过程来看,礼在坚持等级性原则的同时,应注重平衡性原则的意义,因此,“和为贵”在这里的意涵是要以“和”即平衡性原则作为系统的主要原则来坚持。总言之,正是从“和”是礼的目的,也是实现这一目的主要方式而言,儒家才说“和为贵”。
其次,尽管儒家视“和为贵”,但若徒知“和之为贵而一于和”(注:见《论语·学而》朱熹注。),则“亦不可行也”。这是因为,“和”作为一种平衡性原则是从饮食之和与音乐之和中提炼出来的,《礼记》有所谓“礼辨异,乐和同”之说,“和者,乐之所由生也”(注:见《论语·学而》朱熹注。),这是儒家的基本共识。“和”的功能主要是“和同”,它强调的是系统内部各元素之间的相互依赖性,是要于“他”、多或异之中寻找平衡结合点,所以,它突出了系统构成的平衡性原则。从“和为贵”来看,这一原则是系统构成的主要原则,但是,它却非唯一的原则,因为,“和”作为一项单独的原则,它也有缺陷,即它具有混淆事物差别的倾向,容易抹煞事物的个性差异,在处理人伦关系中,它易于流同为不讲是非原则的“乡原”,这就是孔子所谓之“同而不和”,所以,儒家认为,必须以礼来“节和”,即坚持等级性原则的“主音有序”来防止其向“同流”合污转化。
由上可知,儒家的“和同之辨”比之史、晏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即①“和”作为目的性的地位被确定;②“和”作为达成目的的方法论原则即平衡性原则的主导地位得到贞定;③礼作为等级性原则是“和”内各元素进行组合的具体标准,即“礼所以制中也”;④在平衡性原则与等级性原则之间也存在着如何平衡的问题即如何中庸的问题;⑤“和”的实现有赖于主体内在之和即“中”的呈现与挺立。所以,我们认为,从儒家的“和同之辨”重在对“和”的标准(“中”)、“和”的二原则的中庸及“和”的主体性挺立(“未发之中”)的关注来看,它可称作为“和中论”。
3.“和一论”
在儒家“和同之辨”中,以荀子为代表的另一派儒家因过于强调礼的意义,所以,提出了以“和一论”为特征的“和同”理论。荀子曰:“乐合同,礼别异。”(注:《荀子·乐论》。)从表面上看与前儒之说并无什么不同,但应注意的是,荀子讲“合同”,是以性恶论为基础的,其逻辑是:正因为人性恶,所以人各为己,造成“分”的状态,但“分”是不利于人之“生”的本性的,所以必须“群”。但如何才能“群”?荀子认为必须以“义”。所谓“义”,实际上就是“礼义”,而礼义的功能是“别异”。“别异”既维护了人类存在的原生态——“分”,又克服了原生态之“分”的无序缺陷,所以礼义之“分”是一种有序之“分”,也是一种有利于人类发展之“分”。荀子把这种由“义”或礼所造成的“分”与“群”相等同,并又把这种“群”之“分”当作是“和”的基础,提出了他的“和一”之说,曰:“故义以分则和,和则一,一则多力,多力则强,强则胜物”(注:《荀子·王制》。),“故先王案为制礼义以分之,使有贵贱之等,长幼之差,皆使人载其事而各得其宜,然后使谷禄多少厚薄之称,是夫群居和一之道也。”(注:《荀子·荣辱》。)
由荀子的“和一”之道可知,在以礼义为“和”的根本点上,荀子违儒不远;但所不同者是,因荀子以性恶为其“和一”说的基础,“和”作为善的存在形式只是后天人为即“伪”的结果,它缺乏孟子人性善的内在根据作支撑,这样,“和”的实现便只是主体依其道德理性并通过对礼义的遵守的结果。而我们知道,一旦礼成了“和”的唯一标准与实现途径,则“和”与“同”之别就不复存在了,因为缺少了依仁而来的主体独立人格的挺立,“和而不同”便是不可能的。既然“和”、“同”之别已不复存在,则有关系统构建所应遵循的两项原则便只需一个即只需等级性原则就够了,而等级性原则建立的关键在于“定一”即于系统内各元素中确立一个主要的元素作为统领其他元素的标准,如州鸠的“主音有序”说。荀子也说:“故乐乾,审一以定和者也。”(注:《荀子·乐论》。)“审一以定和”,就是把“和”的建立放在“多”向“一”的看齐上,在这里,“他”与多、异已不再是“和”的基础,而是“和”的对立物,是“和”需要以“一”去消解的因素。
很显然,荀子“和一论”的提出,实际上是适应了封建专制主义对儒家“和同之辨”的一种思想要求。随着秦汉专制主义政治体制的建立,这种在荀子那里尚还“朦胧”的思想要求终于被明确地表述为“专则和”的观念,《后汉书》曰:“夫任一人则政专,任数人则相倚,政专则和谐,相倚则违戾。”(注:《后汉书·仲长统传》。)这样,“和同之辨”在中国思想史上便告了一段落。不过,需要说明的是,“和同之辨”在上述政治哲学领域的终结并不意味着儒家便放弃了对这一问题的关怀,事实是,自此以后,儒家把对这一问题的关切重心转向了“身心之和”的构建上。
三 “和同之辨”的现实意义
“和同之辨”对当代社会的和平理论构建提供了十分有益的思想资源。
首先,由上可知,“和同之辨”的最重要的结论之一是“和为贵”,根据这一思想,我们应当重视和平对于全球社会发展的意义。我们之所以要和平,而不要战争与冲突,是因为,根据“和同之辨”的认识,“和实生物”,“和”“能丰长而物归之”,换言之,“和”是一种有利于事物发展的状态,在“和”的环境中,人类的创造力能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人类所创造的文明成果能够得到最有效地正向积累;尤其是在一个全球问题日趋严重的当代社会里,没有和平,那将意味着人类自身的毁灭性灾难的来临,因为,目前人类所拥有的武器炸药足可以将地球毁灭好几次。由此可知,“和为贵”的思想实际上可以将“和平”这一当代国际社会的主题同另一主题——“发展”相连结,所以,我们必须重视和平的价值,使“和为贵”的思想成为全球社会的普遍共识,这是和平问题得以解决的前提。
其次,“和同之辨”中颇富理论构建意义的是它提出了“以他平他谓之和”的思想,这一思想可以为当代和平理论的基础性原则即平等互利原则提供很有说服力的论证。和平之所以要以平等为基础,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处于全球社会系统内的各民族国家是“他”性的或各有自身特殊利益的存在,这一事实虽然意味着对立与冲突是难以消除的因素,但因这种“他”性的存在又处于一种相互依存的关系之中,特别是全球问题及全球一体化趋势的加剧,使这种相互依存关系更为突显。这样,和平必须以平等或“以他平他”为基础不仅成了客观事实,而且也因这一客观事实使“他”与“他”之间的平等成为可能。意识到这一点,我们在处理当代国际关系时,就应不分国家大小,民族强弱,一律予以平等地对待。
再次,“和同之辨”的核心思想是“和而不同”论,这一思想对构建一种“什么样的当代和平”这一问题提供富有启发性的思索。“和同之辨”虽然重视“和”的价值与意义,但它强调“和”必须以“他”、异或多为基础,既反对那种一味地求“和”与“知和而和”的作法,主张以礼来节之,又反对那种将“和”流于“同”的作法,主张建构一种有序的动态的和谐系统。这种和谐的意义在于:一方面,“和”的建立是在“他”或异的基础上建成的,这就意味着和谐的达成并不是一个和谐的过程,“和”实际上是一种对立基础上的统一。另一方面,“和”的建立也并不意味着“他”或异的消失,“和”作为一种共性,其中包含有个性,儒家提出“和而不同”之论,其意义就在于肯定了“和”或共性并不妨碍“不同”或个性的存在与发展,且唯其有“不同”或个性的存在,“和”才是真正具有动态意义的“和”。因此,从前一方面来看,当代和平的构建必须注意到各民族国家的历史文化特点,对和平的制度安排即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必须尽可能地兼容各民族的不同特点。从后一方面来看,和平的构建应该允许各民族国家保留自己的不同意见和不同民族特色,应该为各民族国家之间的“不同”展开对话或交流提供新的契机与新的场所。总而言之,“和而不同”思想要求我们在构建当代和平的过程中始终必须坚持以对话为主的构建方式。
第四,“和同之辨”对系统构建的等级原则的强调,对于今日大国在和平构建中的地位问题也提供了有参考价值的意见。“和同之辨”是为有序和谐立论的,或者更准确地说它是欲通过对“和”、“同”的分辨以避免系统内各要素的趋同或“和一”来建立一种具有最大功能与效应的有序社会结构,这样,它在对平等原则进行强调的同时,又未尝放弃对等级原则的注重。这一等级原则简言之就是所谓“主音有序”原则,“细大不逾主曰平”的原则,即强调系统中的某一个要素对于“和”之系统构建的主导地位。由这一观点出发,在当代和平的构建活动中,虽然各民族国家都有权和有能力且有必要来参予这一活动,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们都能发挥同样重要的影响,毫无疑问的是,大国的影响要比小国和弱国大得多。正因为大国对当代和平的构建具有如此重要的影响,所以作为大国就应该担负起和平的主要责任。但是,也正如孔子的“和同之辨”有可能走向荀子的“和一之道”一样,我们必须注意到:大国作为和平责任的主要承担者并不意味着它就有权只根据自己的需要来定立某种和平的实现模式,尤其是在一个多极化的今日世界,和平更不可能是由某一个大国来充当世界警察就可以维护的。
第五,儒家“和同之辨”把“和”的构建由人伦关系领域延伸到人类的精神生活领域,提出了“和中论”,由此,我们可以发展出一种对当代和平的维护具有重要意义的普遍伦理即和平伦理。因为,由上可知,和平,它作为最有利于人类生存与发展的一种方式,它的实现,除了各种条件外,还少不了一种对人类生命权利的人道主义支援;又,和平,它要以“他”为基础,以平等为前提,而平等作为一种伦理要求,它的实现既有赖于一种休戚与共的人类生存处境这一客观事实的出现,同时又有赖于人类主体道德精神的提升;再又,和平,它是一种统一性的多样性,是以人类个性的发展和丰富为目标的,而这一目标的达成,既需要人类建立起和平共处的理性共识,又需要人类宽容精神的普遍觉醒,而后者是与人类主体道德的不断提升密不可分的。所有这些,都确实需要我们重视一种和平伦理精神的构建。
综上所述,中国传统的“和同之辨”首先从“和为贵”的前提出发,将“和”(和平)与“生”(发展)相联结,然后在此基础上讨论了如何建立一种有序动态和谐的问题,提出了平衡性原则和等级性原则相统一的思想,平衡性原则是为了避免“和”沦落为“同”或“一”,等级性原则是为了避免“和”成为“和稀泥”;并从人伦之和与身心之和的双层角度探讨了“和”的实现的可能性及其应注意的问题,它对当代世界的和平理论构建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标签:儒家论文; 和平与发展论文; 社会观念论文; 孔子论文; 和为贵论文; 论语·学而论文; 荀子论文; 国学论文; 论语·子路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