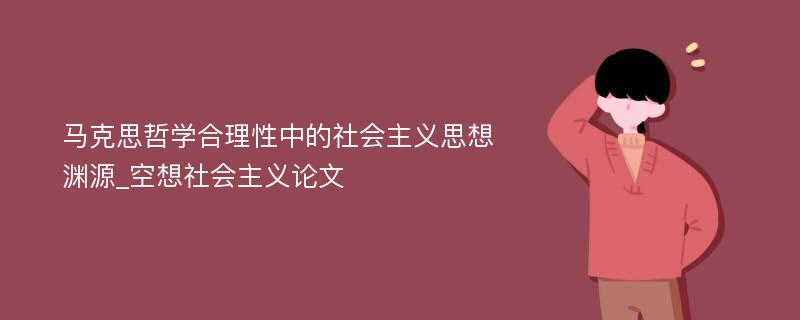
马克思哲学理性中的社会主义思想渊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论文,渊源论文,理性论文,哲学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长期以来,我国学术界在解读马克思的哲学思想时,大多从马克思与德国古典哲学家特别是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关系的角度来厘定马克思哲学发展的线索及其本质,青年马克思对欧洲空想社会主义及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思想的扬弃与其哲学思想发展之间的关系问题始终在人们的解读视域之外,似乎空想社会主义思想仅仅是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来源,古典经济学仅仅是马克思科学的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来源,这种研究方法的局限在于:由于未能深入到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完整境域之中,因而不容易把握马克思哲学革命的真实内涵。为此,本文试图从社会主义思想史的线索来补充对这一点的阐释,以期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一)
19世纪上半叶欧洲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大体可分为三大类:一、立足于不变的人性观点展开对资本主义制度中各种非人性现象的批判,并以此来展开自己的社会主义观点。这一派的代表人物是傅立叶(及其门徒)和魏特林等人;二、从科学、道德、工业三个角度笼统地展开一种历史主义的观点,认为资本主义社会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但它还尚未使上述三个层面的内容获得充分地展开,以此为基础,他们提出了一种以工业家、银行家的历史作用为基础的社会主义观点。圣西门及其门徒是这一派的核心代表;三、立足于人的性格必将随着社会环境的改变而得到改变的观点,把注意力集中在对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环境的(形而上学)批判上面,并进而提出了自己的社会主义观点。欧文及欧文主义者是这一派的代表人物。马克思对上述这些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的批判性吸收的过程是很复杂的。
严格地说,在1844年马克思展开对市民社会及其理论表现——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之前,西欧各国(主要是法、德、英三国)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基本上没有对马克思的哲学发展产生影响。马克思早在1842年夏、秋之际就已经了解了包括傅立叶、圣西门、勒鲁、孔西得朗、蒲鲁东、安凡丹在内的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的思想,同时也已经开始接触魏特林的德国空想社会主义思想(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30—134页。),并且,最迟到1843年9月, 马克思还掌握了卡贝、德萨米的空想共产主义思想(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16页。)。但在1844年之前,这些思想对马克思的哲学视域来说具有很大的异域性,1842年的《莱茵报》时期,马克思说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在理论上不具有现实性,并且还“彻底批判了这种思想”(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33页。)。1843年9 月在《德法年鉴》书信中,马克思尽管部分地承认了这些人所做的工作,但在总体上依然说这些人的思想是教条主义的(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16页。)。依我之见,其根本原因在于马克思这时在研究对象方面还尚未与空想社会主义者同步,他还没有进入到批判现实市民社会的理论视域之中,这在客观上是跟当时德国社会所呈现给马克思的批判对象本身的局限性直接相关的。
(二)
1843年底1844年初开始,马克思着手进行对市民社会的批判,这既是他整个黑格尔法哲学批判计划中的一部分,同时又跟青年恩格斯和赫斯对他的影响有很大的联系。这一理论视域一旦打开,空想社会主义思想便不再对马克思具有异域性了。
首先,关于劳动异化的问题,马克思把赫斯的金钱异化推进到了劳动异化的层次,这标志了马克思的创新。但应该看到,这一思想的很多原始观点是由傅立叶主义者和魏特林提供的。具体地说,一、傅立叶已经明确地指出了劳动权在人的权利中的本质地位。作为对法国大革命中就已经提出的劳动权问题的理论总结和发展,傅立叶指出:“关于人的权利,我们辩论了几百年,可是没有承认人有一个真正的权利——劳动权,没有劳动权,一切其余的权利就没有丝毫价值。”(注:引自卢森贝:《政治经济学史》第三卷,三联书店1960年版,第133页。) 傅立叶的理论贡献还表现在把劳动权与社会的根本改造联系起来,在他看来,能否实现劳动权是和谐社会与现实社会之间的分水岭。二、傅立叶尽管是从自然情欲的角度来理解人的本质,但他实际上已经提供了一套完整的从人的本质出发批判私有制社会的理论模式。按照傅立叶的看法,在所谓的文明社会中,人的本性(人的自然情欲)一向受到歪曲,它无法按照它内在的自由本性发挥出来,只有在未来的协作社会里人的本性才可能完全自由地发扬光大。三、德国的魏特林在发展法国空想社会主义思想方面也是有较好表现的。魏特林的理论成就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1.明确地从劳动产品和劳动活动两个层次来批判私有制社会的不平等。尽管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中的不少人都涉及到了上述这两个理论视域,但明确地提出这一点的,当数魏特林,“产生这种持续的坏时代的原因仅仅是产品的分配和享用不平等,以及生产这些产品的劳动的分配不平等;而维持这种可恶的混乱状态的手段则是金钱”(注:魏特林:《现实的人类和理想的人类。一个贫苦罪人的福音》,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 第9页。)。2.魏特林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无产阶级革命与社会主义之间的必然联系问题。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尽管都谈到了工人的悲惨命运问题,但在他们的理论中这只是说明工人是应当怜悯的,社会是应当重组的,工人阶级革命的理论线索始终没有出现。但魏特林则不同,他明确地提出了解决私有制问题的唯一手段是无产阶级革命,他这样告诉工人:“你们的希望仅仅在于你们的剑。他们同你们之间的每一次妥协都是为了加害于你们。你们已经一次又一次地有过这种经验,现在是你们从这些经验中吸取教益的时候了。真理必须用鲜血来开辟道路”(注:魏特林:《现实的人类和理想的人类。一个贫苦罪人的福音》,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21页。)。综上所述可见,有赫斯的哲学可作参考,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下简称《手稿》中得出劳动异化的理论应当说不是特别困难的。其前两个观点无疑来自于对魏特林空想共产主义观点的哲学改造,后两个异化的观点则得益于对赫斯哲学观点则得益于对赫斯哲学观点的发展及对傅立叶空想社会主义观点的哲学改造。
其次,我们来看看《手稿》中马克思对人的本质的理解。众所周知,马克思在《手稿》中在人的本质的问题上超越费尔巴哈之处就在于从“社会”的角度来发展了费尔巴哈的“类”的概念。而在我看来,马克思这方面的理论发展跟空想社会主义者已经得出的一些理论成果也有很大的关系。一般而言,几乎所有的法德空想社会主义都谈到了只有在真正的社会中才可能实现人的本性的思想,但这里我们要特别提出的是蒲鲁东和勒鲁的思想。这两位思想家不仅一般地谈到了人的社会性问题,而且还对这一问题作出了较为详细的分析。在《什么是所有权》中,蒲鲁东认真地研究了人的社会性的三个级别,明确地提出了这样一些观点:“实行正义就是服从社会性的本能;完成正义的行为就是做一个社会性的行为。”(注:蒲鲁东:《什么是所有权》,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241页。)“人如果不为社会工作就不成其为人; 而社会则是依靠它的各部分的力量的平衡与和谐才得以维持的。”(注:蒲鲁东:《什么是所有权》,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 第253页。)我这里所说的公道就是拉丁人所说的人道,即人所独有的那种社会性。”(注:蒲鲁东:《什么是所有权》,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255(注1)页。)“人必须生活在两种状态的任何一种状态中:在社会中或在社会之外。在社会中,地位必需是平等的。……在社会之外,人就是象一种原料、一种资本化的工具,并且往往是一件笨重而无用的家具。”(注:蒲鲁东:《什么是所有权》,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257(注1)页。)这些观点对马克思从社会的角度来阐释人的类本质并以此为基础来阐发异化劳动理论显然是有很大帮助的。
勒鲁在《论平等》一书中则着重论述了社会与个人之间的辩证关系。在勒鲁看来,社会这个总体之所以能够存在,只是因为它反映在个别人的身上,反映在真正生存的人的身上。没有人就不成其为社会,“真正生存的只是组成社会的人。就社会本身而言,它并非一个真正存在的有生命的实体。”(注:勒鲁:《论平等》,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94页。)马克思在《手稿》中则指出:应当避免把社会当作抽象的东西同个人对立起来,个人是社会存在物(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2页。)。 尽管他们两人在这一问题上的思维层次显然是不相同的,但可以认为,马克思从勒鲁的思想中汲取了重要的思想养料(青年马克思不仅读过勒鲁的著作,而且在1844年3月23日还会见了勒鲁,在会晤时他们就许多理论问题交换了意见)。
第三,关于《手稿》中的共产主义思想。马克思在《手稿》中的共产主义思想可以概括为这样一个核心观点,即自然主义和人道主义的统一。马克思说:“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0 页。)。空想共产主义者卡贝的哲学和道德观点可以概括如下:“如果我们注意到乐善好施的自然界给人类的财富,以及自然界为了使这些财富成为人类的工具和向导而赋与人类的才能或理性,那就不能认定人类在地球上是不幸的;如果我们注意到了人根本是社会的生物,因此也是以善意和同情来对待伙伴的生物,那就不能假定人本性是恶的。”(注:转引自卢森贝:《政治经济学史》第三卷,三联书店1960年版,第193 页。)对比之下不难看出,卡贝的观点很可能对马克思《手稿》中的共产主义思想产生过影响。
需要强调的是,笔者所说的这种“影响”只是理论素材及思路方面的影响,而决不体现在基本的哲学方法方面。在我看来,马克思在《手稿》中基本上是按照以前批判政治国家的方法来批判市民社会的。他对资本主义经济现实的研究只是为了把它作为一个控诉对象,其目的在于“从中引出作为它的应有的和最终目的的”真正的社会的内涵。因此,空想社会主义者的观点必然只能在马克思的哲学视域中充当理论素材的角色。马克思在《手稿》中的显性理论逻辑是不折不扣的人本主义哲学逻辑。
上述这种理论特点一方面为马克思日后超出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奠定了重要的方法论基础,另一方面也决定了马克思在《手稿》时期对法德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的阅读必然是有选择性的。如他对圣西门主义者的评价是很低的,事实上是把他们与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放在一类人中间的(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10 页。)。圣西门主义者的方法论,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与马克思后来所发展出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处于同一理论方向上的,即是一种历史主义的方法论,然而,《手稿》时期的马克思在方法论上恰恰是和傅立叶主义者相接近的,其根本原因在于马克思此时的哲学思维方式也是以不变的人性为基础的。这种状况在《神圣家族》依然没有得到彻底的改变,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依然特别强调法国18世纪唯物主义是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在我看来,这是一个标志,说明在马克思的哲学思维中,人本主义的方法论还没能从根本上褪去。与此相联系的是,马克思还没能获得对圣西门主义的正确评价(注:在谈到与法国唯物主义相联系的法国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时,马克思甚至根本不提圣西门主义者的名字。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2卷,第167页。)。在这一意义上,我们可以说, 马克思什么时候得出了对圣西门主义的相对合理性的正确认识,他什么时候就开始走上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道路了。
(三)
上述这一过程是从1845年春天开始的。在1845年3 月所写的《评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著作〈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以下简称《评李斯特》)中,马克思事实上已经看出圣西门主义者在方法论上的某些可取之处(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 259页。),与此相关联,马克思在《评李斯特》中事实上也的确已经在不少问题上站到了从现实出发的历史逻辑之上。只要仔细阅读该书第二章,便不难看出这点。这一过程的时间跨度约从1845 年3月至《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写作。在写作《评李斯特》的时候,马克思已经阅读了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布雷的著作(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265 页。)。但在我看来,还尚未阅读汤普逊的著作。布雷与汤普逊尽管同为欧文主义者,但汤普逊除了从伦理的角度之外,还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角度来考察分配问题。而后一条线索在布雷的观点中则是不具备的。因此,在其代表作《劳动的弊害及其消除方法》一书中,布雷一方面深刻地指出了只有从经济领域出发才能有力地批判私有制度,“如果我们在经济学家的领域中用他们自己的武器去攻打他们,那就可以摆脱他们经常喜欢搬用的什么空想家、空论家那套废话。只要经济学家们不想否认或推翻他们自己的论点所依据的那种公认的真理和原则,那末他们就决不能推翻我们按照这种方法所得出的结论”(注:转引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11页。),并且他还指出“直至今天,我们一直在遵循这种最不公正的交换制度;工人们交给资本家一年的劳动,但只换得半年的价值。”(注:转引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12页。)但另一方面,在论及私有制度必须改变的理论依据时,布雷却只是说“只有实施劳动和交换的平等才能改善这种情况并保证人们有真正的权利平等……生产者只要努力(也只有他们努力才能自救),就能永远打碎束缚他们的锁链”(注:转引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13页。)。
与此相对应的是,在《评李斯特》中,马克思一方面已经抛弃了抽象的劳动概念,把劳动理解为“非自由的、非人的、非社会的、被私有财产所决定的并且创造私有财产的活动”,并且已经立足于现实的经济领域来理解私有制的废除问题,废除私有财产“只有通过劳动本身才有可能,就是说,只有通过社会的物质活动才有可能”,但另一方面,当马克思谈到废除私有制度的理论根据时,却依然没能获得十分清晰的理论思路。他认为只要认识到工业中存在着的“消灭工业并为人的生存奠定基础”的力量,那么,“对工业的这种估价同时也就是承认废除工业的时刻已经到了,……因为一旦人们不再把工业看作买卖利益而是看作人的发展,就会把人而不是把买卖利益当作原则,并向工业中只有同工业本身相矛盾才能发展的东西提供与应该发展的东西相适应的基础”(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257页。)。这表明, 当马克思把整个人类历史而不只是把私有制社会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时,从现实的经济领域出发的历史主义方法还没有完全凸现出来。这跟布雷在方法论上的理论进度应当说是一致的。再仔细分析,我们还会发现这样一条线索:布雷只是笼统地说生产者只要努力就能永远打碎束缚他们的锁链,马克思把这一点阐释为,“凡是民族作为民族所做的事情,都是他们为人类社会而做的事情,他们的全部价值仅仅在于:每个民族都为其他民族完成了人类从中经历了自己发展的一个主要的使命(主要的方面)。因此,在英国的工业,法国的政治和德国的哲学制定出来之后,它们就是为全世界制定的了”(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 第257页。)。德国的“人”的哲学在马克思此时的思路中依然没有完全丧失作用。这跟他还没有完全得出科学的历史主义观点是相一致的。总体上说,《评李斯特》处于马克思哲学思想的过渡阶段。
马克思的1844—1847年笔记本显示:在写作《提纲》之前,马克思读过汤普逊的著作,而且还从汤普逊的著作中作了整整一页的关于李嘉图的摘录(注:参见《马列主义研究资料》1984年第1期,第22 页。)。在汤普逊的思想中,从生产力与分配方式的关系的角度来批判现实社会的理论线索已经非常明显了,“这里〈汤普逊的著作〉在考察实际积累和分配时,总是把它们和生产力联系起来,放在从属于生产力的位置。但几乎所有其他的体系,在考察生产力时,都是把生产力同积累和现有分配方式的永久化联系起来,把生产力放在从属于它们的位置。和维持这个现有的分配方式相比,整个人类不断反复发生的贫困或昌盛,被认为是不值一顾的。他们要永远维持强权、欺骗和冒险的结果,把这叫做安全。为了维持这种虚假的安全,人类的全部生产力就毫不怜惜地被当作牺牲品了。”(注:汤普逊:《财富分配原理的研究》,转引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第360页。)当然,汤普逊对财富、 分配等概念的理解,正象与他同时代的其他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一样,是非历史的、形而上学的,因此,汤普逊的思路不可能被马克思机械地搬用,但不可否认的是,这对马克思彻底地摆脱人本主义的历史观并走上从现实出发的科学历史观是起非常重要的影响作用的。在这之前,马克思已经从劳动活动和劳动产品两个角度对私有制度进行了批判(尽管是哲学人本主义的),已经具有了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并且还具有黑格尔辩证法的背景知识(这种背景知识一旦被激活就会出现在马克思的思想前台),另外,在《评李斯特》中马克思事实上已经为获得科学的历史观做了许多的准备工作,以上述这些因素为基础形成“加工”汤普逊的新思路。在我看来,就是马克思彻底获得科学历史观的根本原因。从马克思的1844—1847年笔记本可以看出,在摘录了汤普逊著作之后不久,马克思就写下《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然后又有一段经济学著作的研读时期,之后便是《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写作。这说明,上述那个“加工”过程大约持续了半年多的时间,《提纲》是马克思新的哲学思想的一个初步总结,“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这一观点凝炼了马克思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然后再经过一段时间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反映这一研究的文本是马克思的“曼彻斯特笔记”),以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为线索的科学历史观便最终出现在马克思的思想之中。
作为结论,我的观点是,马克思是一位天才但不是先知,他正是在不断地吸收并超越其他思想家的观点的基础之上才成为伟人的。从哲学的线索来看,欧洲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对青年马克思的哲学转变曾产生过较大的影响。
标签:空想社会主义论文; 傅立叶论文; 哲学研究论文; 社会主义社会论文; 社会主义革命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 恩格斯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