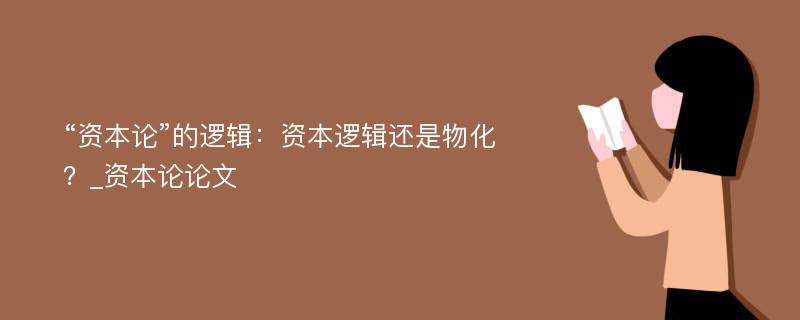
《资本论》逻辑:资本逻辑还是“物象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逻辑论文,物象论文,资本论论文,资本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当前,《资本论》哲学研究和资本逻辑研究已经成为学界研究焦点。但研究中的一些基础性概念的内涵及相互关系问题仍是关键性难题,有待深入研讨。特别是“《资本论》的逻辑”[1](P290)和“资本逻辑”之间是何种关系?与此相关的深层问题是,《资本论》的核心逻辑是资本逻辑还是“物象化”、“物化”?这些问题都需要对《资本论》及手稿的再研究。笼统地说,资本逻辑是“现实具体”,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规律、历史逻辑。而《资本论》逻辑则是“思想具体”,是范畴体系的理论逻辑。《资本论》逻辑(作为思想具体)是对资本逻辑(作为现实具体)的总体“再现”,而所谓“物象化”和“物化”只是资本逻辑的一种效应。 另外,目前学界研究较多的是从《资本论》手稿特别是《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去谈论资本逻辑创造文明与自我限制的二重性,而对《资本论》三卷中资本逻辑的研究比较薄弱。在本文中,我们以《资本论》三卷为中心,力图澄清《资本论》逻辑、资本逻辑与物象化三者之间的深层关系。 一、《资本论》第一卷对资本逻辑的本质再现 究竟什么是《资本论》所再现的资本逻辑?让我们先从第一卷本身的理论逻辑来予以把握。从总体上看,《资本论》第一卷从本质维度再现了资本逻辑。虽然《资本论》第一卷是以商品二重性为起点,但却经由劳动二重性走向了资本主义生产二重性的分析。在这一系列的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范畴运动中,资本逻辑(作为“资本一般”)得到了本质性的再现。 劳动二重性学说构成了《资本论》的枢纽,其中也蕴含着资本逻辑的萌芽和秘密。马克思曾指出“劳动二重性”理论是《资本论》的“三个崭新的因素”之一,“实际上,对问题的批判性理解的全部秘密就在于此”。[2](P466-467)因此,“劳动二重性”论是理解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枢纽,因而也就构成了《资本论》第一卷的基本线索。《资本论》第一卷正是先从“商品二重性”追溯到“劳动二重性”,经由“劳动二重性”即“具体劳动”与“抽象劳动”的矛盾而引入“私人劳动”与“社会劳动”的矛盾,再进展至资本主义生产中“价值增殖”与“劳动过程”、“必要劳动”与“剩余劳动”的矛盾。由此,《资本论》第一卷便一步步地从抽象范畴上升到具体范畴,通过范畴运动及其思想逻辑再现出资本主义直接生产过程的现实总体及内在结构,揭示了资本主义剩余价值规律这一历史逻辑。应当注意,这里的“劳动二重性”,不应该解读为任何时代的“劳动过程”都具有的超历史的一般属性,而应该理解为“资本基础上的生产劳动的二重性”这一特殊的历史属性。因而,“劳动二重性”作为枢纽联结而成的《资本论》理论总体之中所蕴藏的正是一种历史性的真理——资本逻辑及其二重性。劳动二重性是一般商品经济的内在矛盾,但还不是资本逻辑本身,仅仅是蕴含着资本主义生产的矛盾的萌芽形式。在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中,劳动二重性就发展为其特殊形式:资本主义生产的二重性即价值增殖与劳动过程的矛盾。而资本主义生产的二重性则构成了资本逻辑的核心内容。 具体来看,《资本论》第一卷的各个范畴环节都再现着资本逻辑发展的各个现实环节。《资本论》第一卷的范畴逻辑对资本逻辑的再现,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从商品、货币、资本的生产等抽象范畴上升到资本再生产、积累的具体范畴的概念生成体系。 “第一篇商品和货币”基于劳动价值论阐发了商品一般论和货币一般论,其中蕴含着资本逻辑的萌芽形式。该篇集中论述的商品经济一般的价值规律是一种内含矛盾运动的趋势。这一趋势表现为,从商品到货币的发展,从商品二重性到劳动二重性的演进,从价值与使用价值、抽象劳动与具体劳动的矛盾上升到社会劳动与私人劳动的矛盾。从而,为进一步上升到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矛盾奠定了基础。 “第二篇货币转化为资本”是第一卷承上启下的核心枢纽,它阐发了劳动价值论到资本增殖论的转变,再现了资本逻辑的简单本质。该篇通过分析“资本总公式的矛盾”,揭示出资本区别于商品、货币等非资本的一般本性(“资本一般”)即购买劳动力商品进行生产以实现自我增殖。由此,范畴运动从商品二重性、劳动二重性上升到资本生产的二重性,再现出价值规律向价值增殖规律、剩余价值规律的转化。而价值增殖规律构成了资本逻辑的简单本质。 从第三篇至第六篇阐发了剩余价值论的基本原理,再现了资本逻辑的简单本质的直接展开形式。这一部分包括“第三篇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第四篇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第五篇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第六篇工资”,系统阐发了资本主义生产的二重性即价值增殖与劳动过程,从价值增殖角度对资本进行了内在区分即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分析了劳动时间的内部结构即必要劳动时间与剩余劳动时间,从劳动生产率提高与价值增殖的关系角度出发探讨了剩余价值生产的两种形式即绝对剩余价值生产与相对剩余价值生产。[3](P219-220)由此,便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的二重性矛盾,再现了资本逻辑简单本质的直接展开形式。 仅仅停留于对资本逻辑的简单本质和直接展开形式把握是不够的,还必须上升到对其反思性的本质和更复杂的展开形式的把握。“第七篇资本的积累过程”阐发了资本积累论和原始积累论,再现了资本逻辑的复杂形式及其扬弃趋势。通过从“资本主义生产”这一静态的抽象范畴上升到“再生产”和“积累”等动态往复的具体范畴,揭示了资本积累的实质即剩余价值资本化的扩大再生产,阐发了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即在资本积累进程中,资本可变部分相对减少,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相对过剩人口累进生产)。与范畴运动的逻辑演进相配合,还从历史角度分析了原始积累即资本产生史,并且揭示出资本主义积累的基本矛盾及其自我扬弃的历史趋势。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即生产力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正是资本逻辑的简单本质(价值增殖规律)的复杂展开形式,因而资本主义自我扬弃趋势也就构成了资本逻辑的历史命运。由此,“第七篇”便再现了资本逻辑的反思性本质、复杂展开形式与历史命运。 由上可见,资本逻辑及其超越便构成了统摄《资本论》第一卷的核心主题。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主要是从资本生产的二重性出发来透视资本主义社会机体的,从而再现出资本逻辑这一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运行发展的基本规律。《资本论》第一卷的核心线索是,从价值规律到价值增殖规律的转化发展,从商品生产过程二重性(商品二重性、劳动二重性)到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二重性(劳动过程与价值增殖、必要劳动与剩余劳动)再到资本主义再生产和积累的基本矛盾(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运动。具体来看,第一卷从分析商品的二重性(资本主义社会一切矛盾的细胞形式、萌芽形式)开始,分析这一矛盾如何外化为商品和货币的矛盾,买和卖、生产和流通、私人劳动与社会劳动的矛盾,由此引出资本总公式的矛盾、资本和雇佣劳动的矛盾。于是,商品生产过程的二重性即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便转化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二重性即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劳动过程实际是生产力发挥作用的过程,价值增殖过程实际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挥作用的过程。所以,生产过程二重性实际是资本主义积累的基本矛盾(生产力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私有制之间的矛盾)发挥作用的过程。这一基本矛盾最终推动资本主义社会走向灭亡。[4](P214) 那么,究竟应当如何理解《资本论》中再现出来的资本逻辑呢?所谓资本逻辑其实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规律即价值增殖规律。不同于一般价值规律,价值增殖规律的特殊本质、核心内涵在于:资本主义生产中劳动过程与价值增殖过程的二重性矛盾。资本主义生产的二重性在再生产和积累中进一步发展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即生产力的社会化趋势与资本主义私有制之间的矛盾。一言以蔽之,资本逻辑是一个复杂的规律体系,其中包含着规律的各个实现环节:资本逻辑的简单本质是价值增殖规律,直接展开形式是资本主义生产二重性,而复杂展开形式是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 资本逻辑的核心内容是,价值增殖规律展开为资本主义生产二重性。资本主义生产是劳动过程与价值增殖这两个方面对立统一的过程。一方面,在资本基础上的生产是人与自然之间的劳动过程,其核心是劳动的物化,即具体劳动生产商品的使用价值、物质属性的过程。另一方面,在资本基础上的生产又是价值增殖过程,其核心是劳动的抽象化,即抽象劳动生产商品的价值、社会属性的过程。因而,资本主义生产是劳动过程与价值增殖既对立又统一的矛盾结合体。这一矛盾的统一性在于:二者之间的“目的—手段”的支配关系。价值增殖作为目的支配劳动过程,内在地制约着劳动过程的发生发展;劳动过程作为手段服从于价值增殖,以价值增殖(剩余价值生产)为最高目的。值得注意的是,资本主义生产的二重性恰恰规定着资本生产不同于其他任何社会形式的生产方式的特殊本质。按照马克思的历史性观点,古代社会的生产的最高目的是使用价值,而只有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目的是价值或交换价值,价值增殖支配着使用价值生产过程。资本主义社会就是资本统治的社会形态,要把握这一社会的本质,就必须抓住资本主义生产二重性。 资本主义生产二重性内含二元矛盾、相互分离的发展趋势。作为二重性的存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不可能无止境发展下去,它必然包含着自我矛盾,在自己本身中不断遭遇发展的内在界限。马克思反复强调:“资本是一个活生生的矛盾”,[5](P405)“资本本身就是矛盾”,[5](P542)“资本主义生产的真正限制是资本自身”。[6](P278)资本主义生产的二重性矛盾实质上构成了资本逻辑的核心内容,进而构成了资本逻辑的内在界限。资本逻辑的矛盾性表现为价值增殖与劳动过程、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创造文明与对抗分裂的“目的—手段”关系的历史辩证法。在资本主义生产中,价值增殖是目的,发展劳动生产力是手段。而历史的发展趋势则是价值增殖作为手段服从于发展生产力这一目的,并最终扬弃资本的价值增殖。 二、《资本论》一至三卷对资本逻辑的总体再现 探究《资本论》哲学特别是资本逻辑问题,只根据《资本论》第一卷,而不把握《资本论》四册或四卷的总体是行不通的。《资本论》第一卷只是对资本逻辑比较抽象的再现,没有穷尽资本逻辑的总体面貌,并没有完成对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总过程的具体再现。仅仅从第一卷中资本主义生产二重性来把握资本逻辑显然是不够的。本文中,我们将作为理论史部分(历史文献部分)的《资本论》第四册或第四卷与作为理论部分的《资本论》前三卷或三册暂且分析开来,集中探讨《资本论》前三卷对资本逻辑的总体再现。 《资本论》三卷的理论逻辑构成了对资本逻辑的总体再现。资本逻辑在《资本论》中的再现不是在第一卷一蹴而就的,而是贯穿于整个三卷结构中,从抽象到具体,不断上升,不断发展。其基本线索是,资本主义直接生产过程——包含了直接生产过程的流通过程——包含了生产和流通的生产总过程。这一线索蕴含着三重含义:第一,资本形式的不断转化,从生产过程中的资本(可变资本与不变资本)到流通过程中的资本(生产资本、商品资本和货币资本)、社会总资本(两个生产部类的资本),再独立化为商业资本(商品经营资本、货币经营资本)、生息资本(借贷资本、银行资本、虚拟资本)。第二,资本价值增殖规律的不断揭示和展开,从第一卷剩余价值的生产到第二卷剩余价值在流通中实现再到第三卷剩余价值在转化形式(利润、平均利润及各种收入)中分配。第三,资本主义生产基本矛盾的不断展开,从第一卷的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二重性与基本矛盾,到第二卷的循环周转过程的矛盾、社会总资本再生产流通的矛盾,直至第三卷中生产总过程的矛盾。《资本论》一至三卷的经济范畴的辩证转化过程构成了资本范畴的展开形式,具体再现了资本逻辑或价值增殖规律辩证发展的各个环节。 具体来看,《资本论》第一卷在直接生产领域中,再现了从商品生产过程二重性(商品二重性、劳动二重性)到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二重性(劳动过程与价值增殖、必要劳动与剩余劳动)再到资本主义再生产和积累的基本矛盾(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运动。从价值与使用价值的矛盾到抽象劳动与具体劳动的矛盾,再到价值增殖与劳动过程、剩余劳动与必要劳动、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的不断上升运动,再现了从价值规律向价值增殖规律的发展。其中,从价值增殖的角度即可变资本与不变资本相区分的角度提出了分析资本构成的一系列概念(技术构成、价值构成以及有机构成),为第二卷和第三卷更具体地再现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奠定了基础。 《资本论》第二卷则在(包含了直接生产过程的)流通领域,再现了资本流通(循环与周转)、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对于发展劳动生产力的关系进而对于价值增殖的辩证关系。其中,“第一篇资本形态变化及其循环”联系资本的物质形态运动来研究资本本身的运动及其形式更替,从而再现了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物质产物与价值增殖过程的价值产物在流通领域中的对立统一关系。“第二篇资本周转”从劳动过程中发挥机能方式和价值转移(流通)方式的角度区分了固定资本与流动资本,从而再现了资本周转对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作用。“第三篇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则从劳动过程中发挥机能方式的角度区分了社会生产的两个部类(生产资料生产部类和生活资料生产部类),并进而从价值增殖角度探讨了两个部类之间的交换规律。 《资本论》第三卷在(包含了直接生产、流通和分配的)生产总过程的层面上,再现了剩余价值的各种转化形式、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在生产总过程上的发展形式,再现了价值增殖规律在总体层面上的内在矛盾与历史过渡性质。“第一篇剩余价值转化为利润和剩余价值率转化为利润率”、“第二篇利润转化为平均利润”、“第三篇利润率趋向下降的规律”在剩余价值转化为利润进而转化为平均利润的基础上,再现了资本主义的劳动过程与价值增殖、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基本矛盾在生产总过程上的发展:资本有机构成提高所引发的资本生产过剩和危机。而“第四篇商品资本和货币资本转化为商品经营资本和货币经营资本(商人资本)”、“第五篇利润分为利息和企业主收入。生息资本”、“第五篇利润分为利息和企业主收入。生息资本(续)”、“第六篇超额利润转化为地租”、“第七篇各种收入及其源泉”则通过探究利润的各种转化形式即利息、企业主收入和地租,再现了剩余价值在其转化形式中的逐步独立化、外表化和神秘化,从而实现了对资本价值增殖规律、劳动过程与价值增殖二重性矛盾的遮蔽。 由上可见,《资本论》三卷对资本逻辑的再现,不是简单的、静止的,而从抽象上升到具体、从简单综合为复杂、从本质生成出表象、从内部联系展开为外部表现形式的范畴运动过程。其基本方向是,多样性综合为具体总体,达到思想具体对现实具体的总体再现。这是一个不断上升与综合的发展过程。或者按照黑格尔《逻辑学》中的说法,这是一个“圆圈的圆圈”,螺旋式上升的范畴运动过程。第一卷(“内圈”)再现出简单的、抽象的、本质的东西。由第一卷(“内圈”)向第二、三卷(“外圈”)的展开,再现出复杂的、具体的、表象的东西,因而就越来越接近现象的东西。第二、三卷并没有丢掉第一卷,而是在第一卷的规定上再加上新的规定,使第一卷的本质规定不断丰富和充实起来。[4](P7) 综上,《资本论》三卷的逻辑进程和范畴运动,既是从抽象范畴上升到具体总体,又是从简单本质综合出复杂多样的表象。第一卷与第二、三卷综合起来就能够再现出资本逻辑从简单本质到复杂表象的总体。如果说资本逻辑是一个有机总体(人体),那么,《资本论》第一卷再现了它的骨骼系统,第二卷就进一步再现了包含骨骼的肌肉系统,而第三卷则再现了包含骨骼和肌肉的表皮系统。[5](P51)可以说,如同剩余价值理论一样,资本逻辑也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资本逻辑涵盖第一卷至第三卷所再现的简单本质与复杂表象的总体联系,而狭义的资本逻辑仅仅指第一卷所再现的简单本质及其展开形式,它构成了广义资本逻辑的内核。要言之,从总体上看资本逻辑,是从本质到表象、从内部联系到外部表现形式的“转化生成”逻辑。 三、资本逻辑与“物象化” 拜物教论、物化论或物象化论(以下合称为“物象化论”)是目前国内外一种极为流行的《资本论》哲学研究路径。在这种研究路径看来,《资本论》逻辑是拜物教论逻辑或物化论、物象化论逻辑,即《资本论》的基本逻辑是从商品拜物教批判到货币拜物教批判再到资本拜物教批判的层叠高涨。因而,资本逻辑的核心就是物化或物象化。这一观点肇始于卢卡奇、科尔施开启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由日本学者广松涉、望月清司等发展为“物象化论”,国内不少学者也在此基础上进行了深入研究。一般来说,物化或物象化的基本规定是,在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条件下,人与人的特定社会联系颠倒地表现为事物与事物的社会关系(即物象化),并进而颠倒地表现为物本身的自然属性(即物化)。 那么,《资本论》逻辑究竟是不是这种物象化批判呢?更进一步地,《资本论》所再现的资本逻辑是否就是物象化逻辑呢?对此问题,我们不能简单肯定或否定,而需要更具体的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的特殊规律显然是比拜物教、物象化或物化更为深刻的一个层面。因此,问题的实质还是在于,如何理解资本逻辑与物象化逻辑的关系。 我们认为,在《资本论》的共时结构中,资本逻辑与物象化既紧密联系,又相互区别。二者的联系在于,资本逻辑是资本主义生产的本质逻辑,而物象化则是资本主义生产的“效果”逻辑;物象化是资本逻辑的社会效应。二者的区别在于,资本逻辑是从本质到表象、从内部联系到外部表现形式的“转化生成”逻辑,而物象化则是从本质到“物象”的“颠倒表现”关系。资本逻辑中从本质到表象的“转化生成”构成了物象化中从本质到物象的“颠倒表现”的根基。要言之,资本逻辑与物象化是根与枝、母与子、因与果的关系。相应地,《资本论》的核心逻辑是对资本逻辑的再现,而不是拜物教批判或物象化批判。资本逻辑是《资本论》的“主”逻辑,而物象化是《资本论》的“副”逻辑。 首先,从概念上就可以初步辨明资本逻辑与物象化二者间的关系。“资本逻辑”指的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特有规律即资本区别于非资本(“商品”“货币”等)的“资本一般”。而“物象化”指的是商品经济的一般规律,而不是区别于商品经济的“资本一般”、“资本本性”。如果我们退而求其次,认为《资本论》逻辑是“资本拜物教”或“资本物象化”(而非“拜物教一般”、“物象化一般”),资本逻辑的核心是资本物象化,那么也无济于事。因为,“资本拜物教”或“资本物象化”之所以是其自身,恰恰取决于“资本”这个限定性,这个特殊的、区别于“商品”、“货币”的“资本一般”。要说明“资本拜物教”或“资本物象化”范畴,恰恰需要首先阐明“资本”及“资本逻辑”等范畴。要言之,“资本”、“资本逻辑”是比“物象化”更深刻地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本质特性的范畴,而“物象化”则是派生性范畴。 其次,《资本论》三卷的文本逻辑也再现了资本逻辑与物象化之间根源与效应的关系。例如《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篇先讲商品二重性、劳动二重性,最后再讲商品拜物教,在逻辑上已经将商品拜物教置于商品生产二重性的根基之上。与此相应,《资本论》三卷第五篇也是先讲资本的转化形式即生息资本、剩余价值的转化形式即利息,而后再明确讲资本拜物教问题。 具体来看,《资本论》三卷再现了资本逻辑从本质到表象、从内部联系到外部表现形式的“转化生成”过程。先从资本的转化形式来看,第一卷中生产过程中的资本(可变资本与不变资本),到第二卷中转化为流通过程中的资本(生产资本、商品资本和货币资本)、社会总资本(两个生产部类的资本),再到第三卷中独立化为商业资本(商品经营资本、货币经营资本)、生息资本(借贷资本、银行资本、虚拟资本)。相应地,再从剩余价值的转化形式来看,第一卷作为“本质”、“内部联系”的剩余价值直接生产过程,发展到第二卷作为“表现形式”的剩余价值流通和实现过程,再发展出第三卷剩余价值的转化形式利润以及利润的各种转化形式(平均利润分割为企业主收入和利息,超额利润转化为地租)等层层叠叠的“外部表现形式”,最后返回到社会有机体的表面即生产当事人的日常观念,及其在古典经济学庸俗因素、庸俗派经济学中的理论表现。虽然,马克思思想发展的线索是从资本主义社会表象入手,探寻其背后的本质,而《资本论》的叙述体系则是从社会本质重返社会表象,具体再现出本质生成出表象的社会存在论结构。 进而,《资本论》三卷还再现了物象化即从本质到“物象”,从人与人的社会联系到物与物的社会关系、物的自然属性的“颠倒表现”过程。在物象化结构中,社会生产的内部联系颠倒地反映为外部“物象”,超感觉的社会关系颠倒地表现为可感觉的事物与事物的社会关系甚至物本身的自然属性。从而,可感觉之物就系统地遮蔽了超感觉的社会关系及社会总体。在这种着了魔的颠倒的世界中,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交换关系及其内部联系(剩余价值生产、流通、实现、分配过程及其各种转化形式)颠倒地表现为简单流通表象中的“人格”与“物象”(自由平等的交换和所有权),甚至进一步颠倒地表现为商品的自然物质属性(例如“三位一体”公式:资本、土地和劳动三种物质因素分别表现为产生利息、地租和工资三种收入的独立源泉)。由此,作为特定生产关系的资本,就颠倒地表现为作为生产要素的“物”本身的属性,从而获得自然性、永恒性和神秘性的外观,成为自行增殖的“物神”。 综合上述两方面可以发现,资本逻辑作为根源产生出了物象化、物化效应。所谓物象化,其实就是在资本逻辑(从本质到表象的转化生成)基础上发生的从本质到物象的颠倒表现关系。正如马克思所说:“利润分割为企业主收入和利息……就完成了剩余价值形式的独立化,完成了它的形式对于它的实体,对于它的本质的硬化。”[6](P939)正是在资本逻辑从本质向表象的转化生成的基础上,才有本质对物象的颠倒表现关系,才有各种表现形式的“独立化”和“硬化”效应。以剩余价值的转化形式为例就可以清晰看出二者的关系:企业主收入、利息和地租等收入(作为外部表现形式)都是剩余价值(内部联系、生产关系)转化生成的结果。而只有在剩余价值转化为各种收入、资本主义生产的内部联系转化为外部表现形式的基础上,才会发生生产关系(剩余价值)颠倒地表现为“物与物的社会关系”(收入形式中商品、货币的物象关系)甚至颠倒地表现为“物”(作为收入源泉的货币、生产资料、土地)本身的属性这样的物象化、物化效应。 反过来看,作为资本逻辑的重要效应,物象化和物化以神秘化的方式维系着资本对世界的统治。马克思指出,在“三位一体”公式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神秘化,社会关系的物化,物质的生产关系和它们的历史社会规定性的直接融合已经完成:这是一个着了魔的、颠倒的、倒立着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资本先生和土地太太,作为社会的人物,同时又直接作为单纯的物,在兴妖作怪”。[6](P940)《资本论》第三卷“第四十八章三位一体的公式”集中表明,资本逻辑中价值增殖对劳动过程、社会形式对物质内容、生产关系对生产过程、生产力的“目的—手段”支配关系并不是直接明白地表现出来的,而是呈现为一种颠倒的表现关系,以至于发生了“直接融合”。在资本主义生产总过程中,特定价值增殖过程颠倒地表现为“一般劳动过程”甚至其物质要素,特定社会形式颠倒地表现为“一般物质内容”,特定生产关系颠倒地表现为“一般生产过程”,特定生产关系的流通颠倒地表现为“简单流通”。由此便产生出拜物教的“假象世界”,以及生产当事人的“生产一般”、“流通一般”和“资本是自行增殖的物”等拜物教观念。由此,资本逻辑中的支配关系衍生出了颠倒的物象化、物化关系,而相应地,物象化、物化中颠倒的表现关系就系统地遮蔽和实现着资本逻辑中的支配关系。要言之,在《资本论》共时结构中,资本逻辑是物象化的根源,而物象化是资本逻辑的产物,二者紧密联系,相互支撑,形成了资本统治的整体结构。 《资本论》逻辑与资本逻辑的统一,是思想具体与现实具体、理论逻辑与历史逻辑通过再现达成的统一。《资本论》的理论逻辑再现出资本从本质到表象的整体运动规律。再现中的统一不是一成不变的抽象同一,而是在矛盾中不断运动发展的统一。《资本论》三卷理论逻辑对资本逻辑的再现,是未完成的,同时也是开放性的。如果说1858年形成的“六册计划”(资本、土地所有权、雇佣劳动、国家、对外贸易、世界市场)构成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著作的最初研究纲领,那么《资本论》仅仅是完成了其中第一册《资本》甚至是其第一篇《资本一般》的内容。这意味着,《资本论》三卷并不是一个完成了的、封闭的“圆圈”,而是一种生成式的、开放式的再现。19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马克思在《人类学笔记》、《历史学笔记》等文献中对东方社会问题、西方古代近代史中上层建筑领域进行了一系列探索。其意义可能在于,马克思准备在时间和空间上拓展《资本论》的理论视域及其对资本逻辑的再现:一方面,从当代资本主义境遇回溯到早先的前资本主义历史起源之点;另一方面,从当前西欧区域的资本主义转向资本主义在广大非西方社会以致全球的扩张。可见,《资本论》对资本逻辑的再现是开放性的,立足当下同时回溯往古、面向未来。因而,在当代境遇中不断推进《资本论》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再现过程,关注资本逻辑的当代发展及其与政治、文化的关系的新变化,是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关键。标签:资本论论文; 资本有机构成论文; 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论文; 剩余价值理论论文; 资本主义社会论文; 剩余价值规律论文; 劳动二重性论文; 商品价值论文; 本质主义论文; 商品货币论文; 关系逻辑论文; 历史规律论文; 经济论文; 货币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