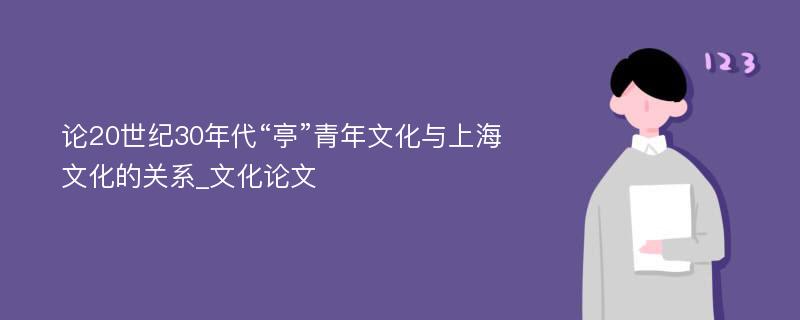
论30年代“亭子间”青年文化与上海文化的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亭子间论文,上海论文,文化与论文,年代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5310(2014)-07-0009-06 自从1938年毛泽东把由上海等大城市奔赴延安的左翼文化人称为“亭子间的人”[1]以来,30年代作家、30年代文学与上海特有的建筑空间“亭子间”的关系,就受到人们的注意,但所论又往往失之笼统,甚至常给人一种30年代作家无不曾住亭子间的印象。如李欧梵说“一个典型上海作家生活和工作的地方是所谓的‘亭子间’”[2],这无疑近于误解:自己寓所的结构“含有”亭子间,与自己的寓所“是”亭子间,这是两个概念,而现代上海作家中不住或不曾住亭子间的大有人在,而这部分上海作家往往是最有成就和文坛影响力的。小小亭子间作为一种文化意象和隐喻空间,具有重要的文化意义。几乎每一个文艺生命诞生、成长于30年代的“左联”或左翼作家,都曾把亭子间作为他们在上海的第一个落脚点,作为进入上海城市社会和文化界的起点,几乎都有过亭子间经验。本文所谓“亭子间文化”乃是指30年代从“亭子间”这类上海的恶劣物质生存环境中创造出来的一种带有边缘性和激进性的青年文化,主要是就一种生活方式及一种带有青年文化特征的上海左翼文化形式而言的。[3]那么,作为青年文化的“亭子间文化”与它的“社会主体文化”——上海文化产生了怎样的互动?这种互动对30年代左翼文化运动又有着怎样的影响?本文拟就此问题作一初步探讨。 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居住亭子间,是和居住者近乎赤贫的经济地位和无名小辈的文坛地位直接联系着的。“亭子间常常成为上海许多受过教育的年轻人的家。这些年轻人不少是来自乡下小镇,留在上海工作(多数从事文学、新闻出版和教育方面的职业)。他们的收入使他们只租得起亭子间。”[4]在30年代,蜗居上海亭子间进行文化创造的最大文人群体,不是一般成名已久、获得了一定文坛地位的文化人,而基本上是手中物质资源和文坛名望都缺乏的外地来沪的左翼青年文化人。正如研究者注意到的那样,“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说,真正的‘亭子间作家’是指一批来到上海,生活无着,徘徊于文坛边缘或刚刚崭露头角的文学青年”,因而“把‘亭子间作家’作为‘典型上海作家’的一个象征或隐喻的本身,反映了我们以往文学史的贫乏”。[5]需要补充的是,之所以有“以往文学史的贫乏”的现象,原因在于:所谓亭子间作家乃是以30年代左翼文化人为主体的,当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革命成功后,政治权力的易手决定了话语权力的归属,以往的左翼文化就获得了绝对的合法性;作为掌握话语权者充分运用对文化史阐释的话语权的自然体现,这种文学史论述的“贫乏”表现就不可避免了。 亭子间代表了一般左翼青年文化人所处的相类的恶劣居住和生存环境,它既是一个实体空间,又是一个文化隐喻。就参与群体的年龄特征以及在上海城市语境中滋生的生活方式的双重意义而言,20世纪30年代在上海蔚为大观的左翼文化主要是一种青年文化(youth culture)。这场左翼文化运动的参与者主要是外地来沪的青年知识分子,历史证明这个特殊群体能够将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产生的带有激进性的利益需求和价值观念,提升到文化意义上进行理论综合,从而使左翼文化具有了青年亚文化的特征。通过左翼青年知识分子的“整合”作用,左翼的青年文化最终产生。它也就是我们所谓的“亭子间文化”。 虽然上海的亭子间居住起来冬冷夏热,局促憋闷,条件相当恶劣,但一种文化因它而起,这本身就是上海文化不拘一格、海纳百川的体现。“一个小弄堂里,一座双开间石库门住宅,楼下是店堂……旧上海的文化,相当一部分就是这类屋檐下产生的。”[6]柯灵的这番话道出了30年代上海在文化创造方面的不一般的小人物做大事业、小建筑出大文化的活跃局面。这种活跃局面,其实也可以看成是青年的活跃。例如30年代的左翼文化人基本都是年轻人,“左联”的成员除了寥寥数人年龄接近或超出40岁之外,大都在30岁之下。显然,处于青年年龄段的作家,在30年代上海文坛占据着数量意义上的主流。不过,30年代栖身亭子间的文化人中,基本没有“五四”时期即成名的、积累下文化资本的文化人,而主要是被从“五四”到“五卅”的激进时代浪潮唤起和推动、在20年代后期和30年代才投身文化事业的青年。左翼青年文化人的经济地位和物质生活在上海社会的边缘化,总是伴随着他们在上海的文化资本的边缘化,或者说他们的经济地位和物质生活的边缘化,乃是他们文化资本的边缘化的反映。 30年代的亭子间文化虽然是一种边缘性的青年文化,却也不停地尝试向上海文坛的中心进入,并具有成效。许多完成了文化资本的初步积累、创作上较有成就的左翼青年文化人,原本是亭子间作家,而终于走过了从上海文坛的边缘到中心地带的一段路程。他们跨过了上海文坛设下的种种障碍,而这种跨越通常是艰难的。30年代的上海,以身份为基础的不平等在日常生活中已经较具弥散性。在文坛上,任何一份商业性文学刊物,都极为注重成名作家的市场价值和读者号召力,从而导致报刊编辑方面相对于文章内容和质量而更看重作者名字的普遍现象。如鲁迅所言,上海刊物“大抵有些一派专卖”而“每一书店,都有‘文化统制’,所以对于不是一气的人,非常讨厌”[7],书店之间“都有壁垒”,并且“上海读者,还是看名字的,作者姓名陌生,他们即不大买了”[8]。以大型文学杂志《文学》为例,它虽然带有进步色彩,但仍是一家循商业市场机制运作的重视读者口味和市场接受的刊物,它的权威地位使在其上发表作品对年轻左翼文化人而言意味着“跳龙门”,然而它的用稿范围却难称广泛,较为讲求人脉关系、侧重成名作家,“是只愿登熟人和名人的作品的,缺稿时,万不得已才发表点无名的青年作者的稿子”。[9]萧军曾不无痛切地指出30年代“成百上千的文学爱好者、写作者想要‘跳龙门’,总是跳不上去”的客观事实,并以《文学》为例,把原因主要归咎于这些大刊物使用“介绍制”的用稿惯例。[10] 作为亭子间文化创造主体的一般左翼青年文化人,与上海的成名文化人在文化资本上的这种不对称,决定了作为组织、集团和阵营的左翼文化在上海社会、上海文坛的文化创造成绩总是参差不齐,整体上差强人意。相反,主要以与“左联”等组织的联系相对松散的个人形式存在的左翼文化活动,如大作家鲁迅、茅盾等的文化活动,反而产生了很大影响。其中文化资本正扮演了杠杆作用。其实讨论所谓左联当初应该“关门”、“开门”与否的问题,也应该考虑到当时那些在文坛拥有相当地位和影响力的文化人们(如郑振铎、巴金、叶圣陶等)相对一般左联成员而言的这种文化资本不对称的因素。情况正如一位左联成员后来所言:“如何开门?问题也并不简单。有属于组织上的问题,也有属于文学观点上的分歧,有些不是‘左联’的作家,也还不是那么容易接近的。”[11]这是当时的客观现实,“不是那么容易接近”,实际上道出了亭子间作家和非亭子间作家之间存在着文化资本等差的三昧。 青年文化在整体上应该能够体现青年群体基本的价值观念与行为规范,是一种亚文化形态,一般认为它具有鲜明的对位性特征,即它与社会主体文化相对应,“一方面具有反抗性、冲突性因素,但同时也包含了接受性、继承性因素”。[12]而作为青年文化的“亭子间文化”与它的“社会主体文化”——上海文化的关系,也并不例外。 亭子间文化作为一种青年文化模态,拥有一种与一般上海市民生活有所差异的生活方式,用一种或许有所夸大和不够确切的提法,就是具有了一定程度的“族群”特征。根据夏衍的说法,亭子间文化人从日常吃穿住用,到生活目标追求,交往习惯等,往往与上海一般市民不同。除了往往是外地人、经济拮据、住亭子间、常吃包饭、罗宋菜外,又往往单身住在上海,身份、职业不明确或者简直无业,日常起居和活动规律不合一般上海市民习惯,衣着装束也常与一般市民不同,喜欢掼艺术家的派头,如留蓄长发,穿乌克兰式的衬衫,戴大红色的领带等。这种差异还体现在对传统文化习俗的态度方面,诸如中秋节往往不吃月饼、过年不请客餐聚、不鸣放鞭炮等等,[13]说明了亭子间文化是一种以“新”为导向的文化。尤其当左翼青年文化人身处上海社会基层的工人和市民大众中时,这种“非我族类”的差异感、闯入感和突兀感更为强烈。丁玲曾这样谈及她受“左联”组织委派到上海工厂区和“大世界”游乐场做工作时的尴尬感受:“在三十年代,知识分子要到工人当中去很不容易。我去时总换上布旗袍、平底鞋,可是走路的样子就不像工人,很引人注意。再说,人家都是相互认识的,你到那里去,左右不认人,又不像从农村来走亲戚的……”;“为了到群众中去了解大众的文学,我们还专门去大世界做调查研究。我从十七岁到上海,还从来没有到过大世界。那是群众娱乐的地方,也有流氓阿飞。一个穿着时髦的妇女走进去,就会有不三不四的人要跟你白相。周文同我一起去,他人老实,土头土脑,上海人叫阿木林,不像到那个地方去的人,也不像是陪我去的人。……”[14]丁玲在这里描述的情景富有隐喻意味,让人联想到30年代左翼青年文化的高级文化本质,以及它在面对上海社会真实的底层及其文化时的某种无力感和陌生感、慌乱感。正如曹聚仁所感慨,上海的“白相”去处“大世界”,“那里是流氓的天地,不会卖文人的账,连郭沫若鲁迅都不相干”。[15] 在人际交往方面,亭子间文化显现鲜明的匿名性特征。由于左翼青年文化人基本上都来自外地,因而在上海的社会人际交往一般局限在相同气类的文化人中间。对很多左翼青年而言,“作家”、“文人”、“艺术家”等往往只是最表面和掩护性的身份描述,很多人还从事革命实际工作,出于政治和人身安全考虑,他们与人交往一般带有明显的匿名性。事实上,即使左翼文化人之间,除非特别熟稔,否则也是基本不随便问及居住地址、真实姓名、籍贯、与某某的真实关系等内容的。萧军初到上海时,不明就里,在不熟悉的人面前宣布自己的住址,即被叶紫讥为“阿木林”,使萧军明白当时上海一般亭子间左翼文化人“社会生活以及社交生活”并不“一般”,感慨之间“有的只是一种工作上的关系,组织上的关系。除此之外,个人间一种抒情式的交往,人与人之间所谓一般的‘友谊’是不存在的……一个电话号码,一个通讯地址……就是一切的联系关系。某个茶馆,某处街头,某个场所……就是‘接头’的地方”。[10]在那个动辄得咎、人人自危的恐怖年代,即使是非左翼的作家,人际交往也往往小心翼翼。例如许广平曾谈到当时并不属于左翼的青年文人徐诗荃“在上海行踪甚秘,住处也无人知道。时或一来寓所,但有事时总是我们没有法去寻的。也因为这样的青年朋友不少,所以并不怪异”[16]。30年代曾常以佛理“讽劝”鲁迅“参禅悟道”、“少争闲气”的徐诗荃尚且如此,一般左翼文化人的情况更可想而知了。 必须注意的是,左翼青年文化人人际交往的匿名性特征,不仅是政治压力的结果,还是融入上海城市社会生活后的一种必然选择。当左翼青年文化人进入上海后,面对这样一个高度复杂和异质化、包罗万象的城市世界,面对周围人、事、物高度集聚的生存环境,必然感到“大上海”中个人的渺小。由于个人的一切难以如在传统乡村社会一般受到关注,从而使他们与整个上海社会的疏离感增强。当时一般上海市民之间接触和交往往往是匿名、短暂、局限的,往往是基于职业的往来和角色互动的需要,而不是建立在个性需求或情感表达的基础上。可以想象左翼青年文化人也需要顺应上海社会通行的那种依据其特定身份而非他们原有的个性的交往方式,从而往往忽略隐伏其后的个人特异性,他们也同样按其所扮演的社会角色来看待人和被看待,由此增长了一种工具式的对待他人的态度。在政治环境和城市社会生活的双重压力下导致的匿名性特征,对他们个人来说自有其积极意义,那就是留给他们个人的精神和情感的自由空间扩大了,自我选择的余地扩大了,传统的历史和文化因袭的精神负担比较小,个人可以较无挂碍地在“大上海”“闯荡”。亭子间里的左翼青年文化人跻身于城市的茫茫人群,栖身逼仄阴暗的亭子间,依托相对松散的人际关系,他们是在如此条件下,创造、认同并传播亭子间文化观念、价值体系以及行为方式的。 亭子间文化的社会交往方面呈现出的匿名性、短暂性,是政治和上海城市生活双重压力下的产物,然而,左翼青年文化人不仅具有如一般上海市民般的交际上的匿名性一面,还具有异于上海一般市民交际生活表现的活泼与率性的一面。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亭子间文化,其姿态透露出波希米亚(Bohemia)气质特有的那种崇尚个性、浪漫、自由的一面,这又与上海的宽容、自由、开放、活泼、不拘一格的整体文化氛围相协调。亭子间作为上海的一种建筑实体空间,具有了具体而微地展现上海城市文化的特有氛围的意义。如萧军所言,30年代“在上海的左翼作家们”,“除开一些资格比较老的,出过一些书的,能够有些‘版税’收入,勉强可以不太紧张,日子过得从容些以外,绝大多数全是‘民不聊生’”。[10]虽然近乎赤贫,但他们的精神面貌却有着青年特有的乐观与自信,无畏与坚强,活泼与率性。作为上海社会的一类群体或曰族群,他们彼此之间也有较多的互帮互助。唐弢这样回顾30年代他的少年情怀:“那时少年气盛,不知道什么叫困难,我想,如果有人说月亮可以摘到手,大概也会下决心试一试的吧。”[17]可以说道出了蜗居在亭子间中的一般左翼青年文化人的共同心声。施蛰存曾这样忆及在左翼电影演员王莹30年代上海简陋居室中的“沙龙”般的盛况:“当时王莹住在环龙路(今南昌路),一家白俄开的小公寓里。一个小房间,不过六七平方米,仅容文艺电影界的朋友。这个小房间,最多只能容宾主四人,所以前客必须让位给后客。王莹煮一壶咖啡,和来客聊天,经常要谈到十一二点钟才把客人送走。”[18]而当1929年谢冰莹的亲戚劝说她报考北京的女子师范大学时,她曾十分犹豫,她“不愿意离开这个文人荟萃之地,她觉得上海是文人的摇篮,亭子间的生活再苦,但不受别人限制的生活是自由的、痛快的”[19]。这些都说明亭子间无疑具有了一种文化空间的魅力和意味。当时左翼文艺青年“生活上一般都很穷苦,彼此互相帮助临时解决一下吃饭问题、交房租的问题也是经常的。但大家都很乐观积极”[11]。例如周扬住在北四川路附近的时候,“经常到法租界来跑一趟,工作之后,没钱坐车回家”,常常去找关露“借几毛钱做车钱”。[20]即使在亭子间这样的阴暗逼仄的环境里,左翼文化人仍然营造了一种宽松、自由的氛围,体现了亭子间文化的浪漫性的一面。亭子间里的左翼青年文化人,照样享受到了上海城市的自由空气。 从以上所述,可以看到30年代左翼青年文化人的社会交往呈现出了两面性,其既有政治上的自我保护意识和城市生活意识支配下的匿名性和现实性,又不乏青年特有的活泼率性和浪漫性的“抒情式的交往”。前一方面体现了亭子间文化相对上海文化而具有的接受性、继承性因素,后一方面则体现了亭子间文化相对上海文化而具有的反抗性、冲突性因素,具体而微地反映了亭子间文化在上海文化系统中的青年亚文化属性。作为激进青年创造的一种左翼文化形式,亭子间文化必然有一种对以市民意识为核心价值的上海文化的批判、反抗的姿态。但作为在上海城市生活语境中产生、发展并与上海城市气氛融为一体的青年文化,可以想见亭子间文化其实又有着一种接受、顺应乃至继承上海文化的姿态,它有着隐隐然以上海文化为背景和参照系的一面。 譬如,30年代萧军、萧红的上海生活,并非仅仅租住亭子间以及筹措生活用具、向鲁迅借得生活费之类这样简单,萧军还面临针对他的关乎“野气”、“匪气”、土气、“阿木林”(上海话中乡下傻瓜之意)等的较大困扰。叶紫和黄源,是萧军到上海后经过鲁迅结识的,属于他在上海最早的朋友。在鲁迅授意下,他们也负有帮助萧军尽快熟悉和适应上海的“责任”。叶紫常常半开玩笑地称萧军为“阿木林”,告诉萧军说一般上海文化人说他“浑身一股‘大兵’的劲儿,又像‘土匪’!……”说萧军不如那些人“斯文”;而黄源和萧军闲谈时,同样说他“野气太重”。萧军由此自感“一个‘东北佬’初到上海滩,‘野里野气,憨头憨脑’……总该是被人看不入眼的”,甚至“有一些淡淡的‘悲哀’”。[10]很显然,叶紫、黄源这两位萧军在上海的最早的朋友兼城市“向导”的看法,已经造成了萧军上海生活的一定心理压力。 从东北乍到上海的萧军,因其身上浓郁的“野气”和“匪气”,实际上被目为上海文化人、上海文化人格的一个“他者”,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一个“外来的‘闯入者’”[21]——这更是一种文化心理意义上的“闯入”。而他在上海经过鲁迅结识、熟悉的左翼青年文化人叶紫、黄源,不约而同都以一种接受、顺应乃至继承上海文化的姿态,以一种“上海式”的眼光看待萧军的粗豪性格。他们对萧军“野气”、“匪气”、土气的批评,对他“阿木林”的揶揄,明白无误地以上海文化为标准、背景和参照系。叶紫、黄源他们,同样为外地来沪的青年文化人,只不过早些时候从外地来到上海。即使在和萧军订交当时,他们也都尚属于上海文坛上的“小角色”,就三位青年的思想倾向和实际境遇来说,说是同列于亭子间文化的创造主体也并不过分。可以想见,当初还是“新上海”的时候,如果用他们衡量萧军的标准和尺度来衡量他们自己,也多少是“阿木林”、多少带点野气和土气、多少不如“老上海”的文化人“斯文”的。事实应该是,在叶紫、黄源等青年文化人从外地来到上海、进入文化界、积累文化资本的过程中,参与了对亭子间文化的塑造,也受到上海文化的主流观念的有力制约,并接受了一些来自于上海文化的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使其身份也从“新上海”变成了“老上海”,从而自觉或不自觉地以上海文化人格模式去衡量萧军了。这里,体现出亭子间文化作为青年文化与上海文化既关联又相互独立,并在这种关系中展开互动。亭子间文化既反抗、批判上海文化,又接受、顺应、继承上海文化,具有上海文化的某种亚文化的属性。萧军曾就叶紫、黄源的讥嘲写信向鲁迅求教意见,鲁迅意谓:“‘土匪气’很好,何必克服它,但乱撞是不行的”,[22]“所谓‘野气’,大约即是指和上海一般人的言动不同之点,黄(源)大约看惯了上海的‘作家’,所以觉得你有些特别。……这‘野气’要不要故意改它呢?我看不要故意改。但如上海住得久了,受环境的影响,是略略会有些变化的。除非不和社会接触。但是,装假固然不好,处处坦白,也不成,这要看是什么时候。和朋友谈心,不必留心,但和敌人对面,却必须刻刻防备。我们和朋友在一起,可以脱掉衣服,但上阵要穿甲。……所谓文坛,其实也如此(因为文人也是中国人,不见得就和商人之类两样),鬼魅多得很。”[23]鲁迅把萧军身上所谓的“野气”、“匪气”与上海文化人格自身特点相联系,并指出如果久在上海居住,必然会受环境影响,“会有些变化”,叶紫、黄源的看法就是因为他们已经“看惯了”上海文化人。鲁迅实际上点出了上海文化对居处上海的人们的制约和塑造作用,是抓到了根本的。但是,他虽然不欣赏上海文化人的“斯文”,不赞成用上海的标准去修正萧军的性格,却也并不认为萧军的“野气”、“匪气”应该始终如故,而是建议萧军对自己的“野气”、“匪气”的外露增强策略性和灵活性。说到底,鲁迅对这个问题的思考,还是在朋友—敌人、下阵脱衣—上阵穿甲的分野中进行的,这是符合他一贯的精神界战士性格的,他把有关上海文化人格的思考,自然引入到他的社会批评和文化批评的思想战场上去了。 曾有研究者指出,上海的知识分子“没有北京学院派知识分子那样明显高于大众的经济地位,相对独立的生存空间、文化空间和生活方式,缺乏明显的阶层性和优越感——在文化人格上,这正是作为知识分子角色意识的精英意识。在一体化的城市生活方式中,他们实际上置身于市民社会之中,与市民生活浑为一体”[24]。这用来形容一切近现代上海的知识分子或许稍嫌绝对,但仅就上海30年代的左翼青年文化人而言却十分精当。从上述亭子间文化对上海文化的接受、顺应、继承的一面看,它应该可以被视为“置身于市民社会之中,与市民生活浑为一体”了。 收稿日期:2014-05-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