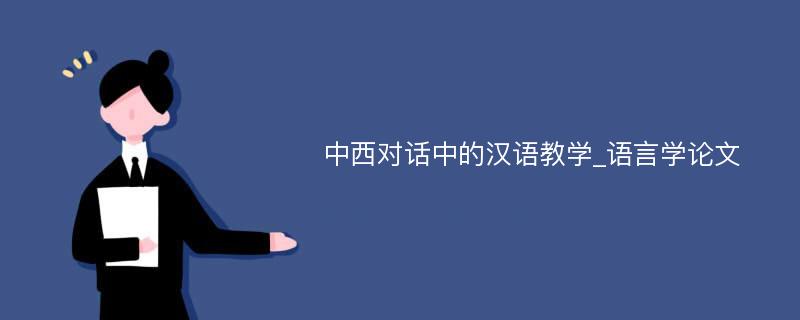
东西方对话中的中国语言教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东西方论文,中国论文,语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语
中外语文研究的传统差异很大。以古希腊、古罗马为代表的欧洲语文学重点研究语法和语音,因为希腊语和罗马语的屈折变化使得阅读典籍的困难主要集中在语法的形态变化以及由此引起的读音变化。中国语文不存在这一问题,作为孤立语的汉语很少有形态变化,阅读典籍的困难主要集中在语义方面,也即字义。比如,出于阅读先秦典籍的需要,学者们专注汉字形体、古代读音和意义的分析,形成了统称“小学”的文字、音韵、训诂的传统语文学。所以,中国的语文学不但发源于训诂学,而且始终将其作为重要的研究内容。由于中外语文在传统研究对象上的差异以及近现代中外语言学发展的不平衡,中国的汉语教学呈现形而上的“语文性”,而西方的母语教学则更符合语言存在(本体)的“语言性”。
二、中外语言教学的共性与个性
人类具有共同的生理和心理基础,而语言又是一项具有生理和心理基础的知识结构和知识系统,这就证明了人类语言共性系统的存在,比如语言符号的普遍性——音、形、义:符号的扩展、历时变化、层次结构、基本语义概念、语法的递归性、习得的可能性等等,而作为语言之间差异的语言个性毕竟是非本质的边缘性规则和参数。所以,探索语言普遍规律的科学语言学以及具有普遍意义的教学理论和模式完全可以成立。
中外语言教学内容都涉及听、说、读、写等语言基本技能的训练,这就是语言符号系统的共性在语言教学中的反映,也即编码—解码—再编码的本质和过程。近十几年来国外新的语言教学理论和模式不断出现,中国语文教学界也自主设计或引进学习了不胜计数的新教学法,概括起来不出三类:1.提示型教学——教师处于教学的中心,实施提示、说明、报告、讲解。这是一种受纳性学习;2.自主型教学——淡化教师的主导地位,教师根据教科书及其他学习手段实施间接指导,学生独立解决教师提出的问题。这是一种生产性学习;3.共同解决型教学——介于上述两个基本教学形态之间,教师通过与学生对话和讨论实施教学。受纳性和生产性学习兼而有之。所以,就一般的教学理念和教学方法而言,中外语言教学的共性远远大于个性。
对于中(小)学的学生而言,母语的基本习得过程早已经结束,其普遍语法已经转变为具体语言的个别语法。母语习得的关键阶段结束之后(大约是五、六岁之后),语言学习的性质便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从以前依靠语言习得机制的“自动参与”变成了一种非自动的认知活动,语言个性开始显现。这势必要影响教学指导思想、教学方式和教学内容,语言教学和学习也变得不那么单纯了。
语言是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的一面镜子,语言教学对此必然会有所反射。作为18世纪启蒙主义的一种延伸,新人文主义在教学论上采取了“形式训练”的立场,而形式训练说是由笛卡儿等哲学家的唯理论,特别是康德批判主义的认识论与论理学所构成的(乔姆斯基提出的转换生成语法“使十七至十八世纪的唯理语法复活了”)。这些唯理主义与批判主义将素材与思维、感觉与悟性、感性与理性二元化地区别对立起来,提出了思维和理性的“形式”,用以区别认识与行为的“实质”。形式训练的本质表现于以语言为中介,实现概念的大量扩充、规则的精确思考、客观逻辑的快速使用。总之,形式训练就是以语言形式训练为依托的悟性能力与理性能力的形式训练。
无论时代如何变化,无论出现何种与之反动的学说,西方这种传统语言哲学思想的内核一直绵延不断地反映在语言学研究和语言教学之中,并通过语言提高了民族的认识水平,极大地促进了自然科学的发展。中国语言教学的语文学或经学传统及倾向有利于学生国学基础的建立,这与西方近代民族主义语言观上的民族精神和民族感情要求也有相通之处。然而,中国语文教学容易忽视形式语言符号的使用和认知,并对中国学生的科学性思维造成相当大的限制,不利于学生将来创立“发现模式”。形式语言符号使用和认知的缺陷甚至使得中国学术界很多人读不懂学术论文,更谈不上听觉接受了。“萨丕尔—沃尔夫假说”以及语言相对论说明了这一点,中国和美国大学生的语言形式对比实验结果也说明了这一点。中西认知科学以及认知语言学不平衡的发展水平表明,中国语言学界普遍欠缺的逻辑语言的掌握和使用能力,已经影响和制约了中国在自然语言的计算机理解和识别方面的研究。
科学哲学研究的一个重大课题是科学的解释究竟有哪些形式与结构。夏佩尔为此提出了三个科学理论问题:1.科学合理性的公设或假设;2.科学推理的可概括性公设或假设;3.科学推理原则的可系统化公设或假设(Shapere D.Scientific Theofies and Their Dommns.2nd Ed,Univenity of Illionia Press,1977:PP518-565)。这三个问题无一不需要以形式语言符号为平台的精确与外化的阐释和展示,如果不具备对形式语言符号的认知和使用能力,不仅无法解决上述问题,而且对已出现的解决方法也难以进行认识和判断。在分析哲学中假设式和绝对式推理均具有可能性,依据就在于是“揭示含义”还是“陈述证明”,它们的区别是方法论的区别。然而,分析哲学中大量的推理模式无疑具有演绎性质,因为在“揭示含义”和“陈述证明”的系统内部,任何形式化的论证必然具有演绎性质。演绎模式以一般原则为目标,具有更大的空间和自由度从事全局性问题的研究,因而倾向于分析意义的概念和内涵,表现为“语义上升”;归纳模式以局部语境为依托,并使其单称直觉(确定性和无条件性的直觉)只适合于这种局部语境,因而对个别实例所提供的证据感兴趣,倾向于分析特殊类别词语的意义,表现为“语义下降”。至于中国的哲学思想,则“以令人吃惊的固执态度拒绝诉诸语言与文字”(钱冠连《中国哲学的不同语言走向》,《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1.6,PPI-4),在研究方法和研究对象上重感悟,重人生与人文精神,对形式语言符号没有任何要求,因为“内圣外王”之道乃“道可道,非常道”之道。而诉诸高度符号化、逻辑化和严密形式论证的西方哲学转向语言分析则是一种必然现象。中西哲学思想的不同取向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各自科学技术的发展进程。通俗一点说,中国影视界的“大刀长矛”取向和西方影视界的“坚船利炮”取向其实是令人十分震撼的对照,可我们中间又有几人能够真正理性地意识到这一点呢?如果这个世界上没有“物竞天择”,没有“鸦片战争”,我们就是自觉回到(但不是被打回去!)石器时代生活也无所谓。语文教学“回归传统”可谓冠冕堂堂,但“大刀长矛”耍得再漂亮,在“坚船利炮”面前意味着什么,恐怕连三岁小儿都明白。问题的严重性恰恰在于,小儿们“大刀长矛”的意识不断被强化,“坚船利炮”的意识自然就会弱化。表面追求传统实际上就是寻求不自信的遮掩物,而更多的则是闭塞的说教心理基质所使然。中国人不会丢弃传统,有关人士大可放心。当我们全力追求并最终到达现代化目标时,我们会发现,传统一时一刻都没有离开过我们。需要指出的是,上述认识切不可单纯地理解为“工具说”和“理性说”那种非此即彼的关系。
中外语言无疑存在差异,并影响到语言学研究和语言教学研究,但这种个性差异不宜过分强调,忽视语言及语言教学的共性研究将使中国语言学及语言教学偏离语言作为全人类共同生物属性一部分的认识方法,从而走向孤立主义的道路。西方科学的发展证明了数理逻辑理论和语言符号理论的重要性,中国语言文字也完全适用于数理逻辑理论和语言符号理论。这牵涉到对“理论源于实践,理论指导实践”这一思维定式的再认识问题。但现阶段这对很多人来说既难理解又无法接受,甚至不可想象。
三、语言的交际功能教学
语言是一个信息系统,这是全人类语言的共同特征。语言信息的交流主要是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存在于人脑中的语言信息系统既能生成语言,又能理解语言;既有生成的信息加工过程,又有理解信息的加工过程,同时还存在信息的反馈监控过程。语言是人类的交际工具,语言也是人类认识世界和艺术创作的工具,但交际性是语言的首要功能。学习语言的首要和直接目标就是解决交际问题。人类语言始于口语,口语是语言的基本形式,与书面语相比,它是第一性的;在当今社会,口语仍然是人类最常见的交际形式。丹麦语言学家叶斯柏森指出:“在我们所谓的文明生活中,印刷品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受过教育的人容易忘记语言原来就是说话,即主要是会话(对话),而写的(及印刷的)文字,只是一种说的和听到的话语的替代物,这种替代物在许多方面是很有价值的,但在另一方面却是贫乏的”。(O.Jespersen.Essentials of English Grammar.London,1938:17)叶斯柏森所说的“替代物”一直处于中国语文教学的中心地位。语言教学更不能偏离其宗旨,把本来作为交际工具的语言变成一门令人茫然的应试玄学。
中国语言教学中的口语交际能力训练向来是薄弱环节,其后果在我们的生活中随处可见,而给我们刺激最大的就是电视主持人的话语能力。那些被评选或认可的国家级的“最佳”和“铁嘴”电视主持人,脱稿进行现场直播时,甚至与西方和俄罗斯业余的电视主持人相比,在语速、语流连贯性、信息量、表现力上还存在相当大的差距。除外部制约因素外,语言问题是症结所在。现在中国的中学语文教材增加了“口语交际”的内容,这是进步,但还很单薄,缺乏系统的训练和有效的理论指导。
随着外语教学中交际法的出现和应用,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心语言学习者的口语交际能力。以往乃至目前人们研究语言主要侧重语音、词汇、语法方面的错误分析,完全专注于语言系统的教授,未能认识到语言应用的重要性。随着语用学的产生,人们开始重视语言中的使用和理解问题,开拓了语言教学研究的领域,提高了语言教学及研究的理论水平,甚至将其与社会语言学、心理语言学等交叉研究学科联系起来,目的就在于探讨语言学习者在特定的语境下如何实施言语行为以及如何理解该行为的问题。
语篇分析或话语语言学的研究已有20年以上的历史。口语语篇分析或口语话语语言学理论对语言教学具有相当大的适用性,因为口语语篇分析或口语话语分析有助于对学生语言口语特点和口语能力进行研究,以便在教学中有针对性地解决实际存在的问题。在语篇分析或话语语言学的研究过程中,语言学习者的口语能力一直是关注的焦点之一,出现了以下各种颇受瞩目的分析方法:会话分析法,重点在于观察语言学习者口语交际时所表现出来的言语行为模式,如话轮的转换、话题的改变等等;口语语篇分析法,注重分析方法的系统性与结构性;语用分析法;交际应变分析法,以实验性或仿实验性的方法收集语言学习者口语交际的原始资料,分析其如何变化会话方式及策略。
口语语篇分析或口语话语分析方法使我们得以揭示口语会话的内部结构,对语言学习者的口语特点和能力具有较强的描述性,该方法也具有明显的系统性,有利于将语言的功能与话题、交际目的或言语意向以及言语的各种社会因素结合在一起,并划分出口语语篇或口语话语相应的各种不同层次。语言口语教学的主要内容当属语境句,语境句充分体现了口语的特点,也符合新格赖斯会话含意语用推导机制。当考察口语语境句时,说话人在语境的强有力支持下,以经济的无标记空位语句实现其言语行为,以最小的语言形式传达最大的语言信息,并达到交际目的。从受话人角度看,他总是通过惟一特定的理解来扩展说话人话语的信息和内容,直至确定说话人真正的言语意向,也即将信息扩大至最大的极限。口语教学在强调发话人的同时,也要考虑受话人因素,不可忽略言语认知问题,否则有导致交际失误的可能,因为交际失误的原因不仅仅产生于说话人一方,还会产生于由受话人共同参与的交际双方。
对语言学习者口语交际能力的检验,不能仅仅通过语音、词汇量及语法知识得到实现,甚至其口语流利程度也不能完全证明检验的信度。特别需要考虑的是他们言语意向的实现能力,以及自然深入的会话能力、逆反式会话能力、提高会话效率的能力、强化对方反应的能力等等。只有对语言学习者口语交际能力进行全面准确的检验,并获得可信的结果,才能设置相应的课程,选用相应的教材以及采用相应的教学方法。
四、结语
随着语言学理论研究的发展,我们对语言本质的认识在不断加深,这有利于我们提高语言教学和研究的水平。20世纪后期,西方教育科学领域发生了重要的“范式转换”,开始由探究普适性的教育规律转向寻求情境化的教育意义,并明显地反映在课程与教学研究领域。课程研究开始超越“开发范式”,走向“理解范式”,也即将课程作为一种多元“文本”来理解的研究范式。(E·多尔《后现代课程观》,教育科学出版社,2001,P1)在这一背景下,东西方文化在课程与教学智慧方面的对话更加令人瞩目,现象学、存在主义、解释学、后现代、全球化的课程与教学理论都与此相关。包括语文在内的中国课程与教学研究要面对现实,既扬弃中国传统课程与教学话语,又与西方文化体系中的课程与教学话语展开真正意义上的对话,在“扬弃”与“对话”中建构科学的课程与教学理论和实践体系。
标签:语言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