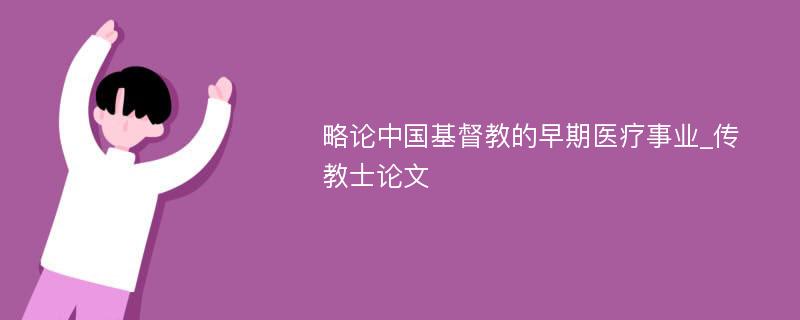
基督教在华早期医疗事业论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基督教论文,在华论文,事业论文,医疗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1834年美国公理会派遣伯驾(Peter Parker)来华,是为第一个来华的传教医生。次年他在广州创立眼科医院(亦称新豆栏医局),由此开始了近代中国的教会医疗事业。为什么教会医疗事业能在近代中国产生发展呢?
首先从宗教而言,很多流布甚广的宗教在其传播过程中除注重灵魂拯救外,还注重治病救人,这是众多宗教传教的通用方式。如我国的道教就相当注重医药;与基督教相比,佛教的“医疗组织则有更早的历史”(注:李约瑟著,劳陇译《四海之内》三联书店1992年北京第三次印刷P183。)。在《圣经》中的《马太福音》《马可福音》都有关于耶稣传教时给人治病的记录,这也正是以后基督教徒利用医药传教的教义依据。而且基督教自从进入中国以来就利用医药辅助传教。唐代景教的传教方法不外两种:“一为翻译经典,一为医治疾病”,而且景教徒中“往往有精通医术之人”(注:王治心《中国基督教史纲》文海出版社版 P40—41。)。元代的也里可温于此也有举措。明清之际的耶稣会士虽注重天文、历法、算学等辅助传教,但对医学也有所注意,如邓玉函曾译《泰西人身说概》;传教士还为康熙帝治过病。由此看来近代以来传教士利用医药传教是其宗教本身的要求,而其之所以得到广泛发展则又与当时的社会有关。
其次,近代传教士注重医学传教与中国的基督教政策有关。康熙以来的禁教政策使传教活动遭到很大的阻碍。1807年马礼逊来华便发现难以进行传教,于是1820年与东印度公司的医生合开诊所,以博得华人的好感与信任,从而便于传教。1835年12月郭雷枢在《中国丛报》上呼吁英美派医生来华传教,称“请医务界的善士来行好事,以博取人民的信任,为此而为……基督教铺平道路”(注:转见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12月第三次印刷P275。)。这说明医学传教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消解中国人对基督教的排斥。然而鸦片战争后,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定使清政府不得不给传教士诸多特权,医学传教从此处于不平等条约的庇护之下。不过此后医学传教的发展仍与中国的社会生活、医药卫生有关。
再次,中国的医药卫生与生活环境为医学传教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前提。中国的传统医学源远流长,有一套独特的理论体系。但它的产生与巫医有密切的关系,发展过程又受到佛教医学、道教乃至理学的影响(注:参见陈邦贤《中国医学史》(上海书店1984年版)的有关论述。),因此有不少的缺陷,而且有不少的迷信色彩。表现在社会上领域就是“巫医盛行”。以至于到了清代“巫医之术犹盛于江淮”(注:转见陈乐平《出入“命门”—中国医学文化学导论》上海三联书店1997年第二次印刷P77。),19世纪70 年代许多上海的医生“第知敬吕纯阳而不知敬张仲景”(注:《申报》同治壬申九月廿一日,癸酉二月十五日。)。而且各地卫生状况又很差。不惟如此,中国的医事制度也比较落后。虽然各省都设有官医,另设有施医局,但大都有名无实,因此广大民众有病难医。特别是近代以来,社会的流动性日益增强,对医疗卫生提出了新的要求。这也为教会医疗在中国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必要前提。然而就传教士而言,初到之时很难适应中国的生活环境,许多人因水土不服而患病;或者因环境恶劣而病故,如初到江南的传教士“过早死亡的原因之一”就是因为环境恶劣(注:(法)史式徽《江南传教史》(第一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版P 5。)。 这也是医学传教士来华原因之一。如圣公会在华的第一个主教文惠廉早在1855年以前曾屡次向布道会建议,派医生到中国开办医药事业,因为“医药事业可为教会开传道之门”。“同时工作人员有水土不服而致病者,亦可有专医调治”(注:林步基等编辑《中华圣公会江苏教区九十年历史》1935年10月P8— 9。)。
复次,当时西方社会的发展为教会医疗事业提供了可能。18世纪末19世纪初工业革命的发展带动了西方社会的进步,医药科学也得到了很大发展。然而工业革命同时也导致了工人贫困,于是许多教会“出于对物质生活贫困的人的同情,为帮助他们,就开始建立相应的制度和机构,恰如他们关心个人的灵魂那样,他们也同样关心个人的身体”(注:罗纳德·L·约翰斯通著,尹今黎、 张蕾译《社会中的宗教》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P309—P310。)。因此诸如医院、孤儿院等社会服务应运而生。此外,19世纪中叶欧洲社会流行的“常识哲学”对传教士产生了重大影响。以至于传教士主张“在传教的同时也辅之以西方人文和自然科学知识”(注:顾卫民《基督教与近代中国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P222。)。这一切都有利于医药传教的进行。
二
从1835年伯驾创立近代中国第一个教会医院后,随着医学传教士的纷纷东来,到1887年教会医疗事业在中国得到相当程度的发展。医学传教士不仅创办诊所、医院,而且进行医学教育。以1860年为界,早期医疗事业又可分为两个时期。
(一)初创时期(1834—1860)
1835年底,伯驾的眼科医院开诊后,由于免费治疗,因此有不少人前往就治。“三个星期内就有四百五十人次来该医局看病,病人要求治眼病,也要求治疗别种疾病”(注:转见顾长声《从马礼逊到司徒雷登》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P74。)。但是由于清廷的禁教, 伯驾等人也不敢在医院公开传教。1835年底郭雷枢在《中国丛报》上发表文章呼吁欧洲多派人才来华。1838年2月21日郭雷枢、 伯驾等传教士与东印度公司的医生、商人发起组织了中华医学传道会,以郭氏为会长,其宗旨是:“鼓励医士来华,并在华人中行医”。(注:Armold Foster B.A,Christian Progress in China,The Religious Tract Society 1889P162。)此后由于广州医院维修,伯驾又到澳门开了一所医院,但不久因伯驾离去而停开。1839年早期医学传教士中的雒魏林、合信先后来华。雒氏来华后,受中华医学传道会的指派到澳门重开医院,但他仅维持几个月就离去;合信来华后也到澳门重开该院。鸦片战争爆发后伯驾回国,广州的眼科医院停开。(注:Armold
Foster B.A,ChristianProgress in China,The Religious Tract Society 1889 P 163。)战争期间,雒魏林曾在定海开设一医院,1841年因英军撤离而停办。鸦片战争结束后,传教士的活动又活跃起来,1842年1月21 日伯驾来华重开广州医院,同年医学传教士高民、玛高温先后来华,并在厦门、宁波一带施医传教,雒魏林重开定海医院。
而且鸦片战争后,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定使传教士获得诸多特权。他们不仅可以在通商口岸传教,而且医学传教也获得了条约保护。《中美望厦条约》规定:“合众国民人在五港口贸易,或久居,或暂住,均准其租赁民房,或租地自行建楼,并设立医院、礼拜堂及殡葬之地”。《中法黄埔条约》也规定:“佛兰西人亦一体可以建造礼拜堂、医人院、同急院、学房、坟地各项”。1847年挪瑞两国通过条约获得了设立医院的权利(注: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年10月北京第二次印刷P54 P62 P74。 )。条约的规定为设立医院提供了依据,实际上为医学传教提供了法律保护。
此后,在此特权保护之下,传教士在通商口岸进行医学传教,并设立医院、诊所(注:本文以下所列教会医院的创办年代以The Chinese Medical Directory (Compiled by H.P.Chu,The ChineseMedical Association,Shanghai 1934)为据。)。1843年玛高温在宁波设一医院,是为华美医院之前身;1844年雒魏林到上海设一诊所,是为以后仁济医院的前身;同年高民在厦门正式设一医院;1848年合信在广州开办惠爱医院;1850年温敦到达福州,是为第一个到达该地的医学传教士。1854年嘉约翰来华,入伯驾的医局工作,次年伯驾离开后由其负责该院。在此影响下,天主教徒也认为“医院是其陆续应办的事业”。(注:(法)史式徽《江南传教史》(第一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版 P56。)在教会医院里,经常有传教士来向病人传教,医学传教士有时也向他们传教。就连王韬也在日记中提到曾多次到仁济医院听过讲《圣经》。
不过19世纪50年代的环境对传教士来说是喜忧参半的。一方面战争给医学传教带来了不少麻烦,如广州眼科医院于1856年因战火而停办(1859年由嘉约翰重办,定名博济医院);另一方面战争又为医药传教提供了机会,以上海为例“由于太平军叛乱战争,迫使外乡人大量地涌入上海”,天主教“神父们又有了从事慈善救济工作的机会”,(注:(法)史式徽《江南传教史》(第一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 年版 P215。) 上海的天主教充分利用这个时机, 并在董家渡设立了医院。雒魏林的医院也曾在小刀会起义期间救治过不少伤员。1860年以前,教会医疗事业虽由广州、澳门一隅发展到五个通商口岸,但总的来说发展缓慢。这固然与时局、语言障碍等有关,但与医学传教士来华较少也不无干系。除创办医院外,这一时期传教士还招华人在医院习医,以便培养助手,同时也开始了近代基督教在华医学教育。
第二次鸦片战争给医学传教赋予了新的权利。由于新开了许多口岸,传教士可以进入这些新口岸。而且中美《天津条约》规定“大合众国民人在通商各港口贸易,或久居,或暂住,均准其租赁民房,或租地自行建楼,并设立医馆、礼拜堂及殡葬之处”。《中英天津条约》、《中法天津条约》也有类似规定。(注: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年10月北京第二次印刷P91 P106。)1860年各国与华签定的北京条约承认了天津条约有效,并获得在内地自由传教的权利。此后不少国家纷纷效尤,获取了此项特权。这就为教会医疗事业初步发展提供了特殊的有利条件。
(二)初步发展时期(1860—1887)
1860年后,医学传教士不断来华,并深入到新开口岸与内地城市,医学传教得到初步发展,以后的一些著名医院相继建立或建立起其雏形一诊所。(下文所列医院有的从严格意义上讲只能是诊所)
19世纪60年代医学传教发展缓慢。教会医院除了上海新设同仁医院(1867)、福州设塔亭医院(1866)外,超出原来五口设有:北京基督教会医院(1861,为以后协和医院的前身)、汉口仁济医院(1866)、汕头福音医院(1867)、天津基督教伦敦会医院(1868)。这除了其专业所限以及中国人对基督教的态度外,还与积极派医学传教士的美国有关,因为美国南北战争的进行影响了医学传教士的派遣。但是医学传教日益受到各教派的重视。
进入70年代以后传教医师逐渐增多。1874年有10个,1881年有19个(注:Kenneth Scott Latourette,A History of Christian Missionsin China,London Society for promoting Christian Knowledge 1929 P452。),7年内增加了9个。 而且传教士因自由传教权的获得,也逐步与上层社会接触以寻求支持。如马根济因治好李鸿章夫人的病而得到李的支持,从而为天津的医学传教提供了方便。因此70年代以后教会医疗事业得到较快发展。沿海省份设有:杭州广济医院(1871)、福建古田怀礼医院(1874)等。而且此时教会医院日益深入内陆。地处内地的武汉在70年代就设有三处:汉口普爱妇孺医院(1878)、汉口普爱医院(1874)、武昌同仁医院(1873)。就连长江上游的宜昌也有普爱医院(1878)、普济医院(1879)。而在1877年在华传教士大会召开前,中国共有教会医院16处, 诊所 24 处。 (注: Kenneth ScottLatourette,A History of Christian Mission s in China, London Society for promoting Christian Knowledge 1929 P452。)可见70年代教会医疗事业得到了相当的发展。1880年到1887年教会医疗事业得到较快发展,除在东南沿海得到发展外,日益向内地和北方发展。这时东南沿海设有:上海西门妇孺医院(1884)、苏州博习医院(1882)、汕头益世医院(1885)、海南那大医院(1881)、福音医院(1885)等。内地设有:武昌昙华林医院(1885)等。北方设有:山东的临清华美医院(1880)、德县卫氏博济医院(1884)、天津妇孺医院(1882),北京美国同仁医院(1886),盛京施医院(1883)等。
伴随着教会医院的发展,医学教育也得到了很大发展。这一时期不少医院除招收学徒外,还设医药班以专门培养学生,这为以后众多正式医学校的建立打下了基础。如博济医院于1866年正式创办了南华医学校,为近代中国最早的教会医学校。此外有的医学传教士还带中国人出国学医。
基于以上发展,1886年在华医学传教士组织了中华博医会,从此教会医疗事业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三
由上述可以看出,早期医疗事业经历了一个艰难的发展过程,分布区域也相当有限。这固然与医学的特殊性、中国人对西医的态度有关,但它毕竟得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不过不应忽视的是,早期教会医疗事业水平还是相当有限的,以教会医院为例,苏州博习医院创立时,“各公会在华设立施诊所颇多,正式医院则仅设于沿海四埠。自上海至北京距离约二千里之内地,迄无一正式之医院”。(注:《中华监理公会年议会五十周纪念刊》民国二十四年十月P42。 )就连著名的上海仁济医院,其病房也很不卫生(注:《申报》同治壬申九月廿一日,癸酉二月十五日。)。但是作为一项特殊事业,早期教会医疗事业对近代中国产生了重大影响。
首先,它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传教活动的进行。基督教作为一种外来文化,一开始就遇到中国人本能的反对。但传教士的医疗活动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华人对传教士的看法。由于不少人感受到西方医学的灵验,他们往往从很远的地方到教会办的诊所或医院去就治。有人因此而成为信徒,不过成为信徒的情况起初并不突出。这固然与传教医生忙于治病无暇传教有关,但与中国人的实用主义、禁教政策也有关系。但是教会医疗事业的确使华人逐步改变了对传教士的认识,为传教士的传教活动提供了方便。他们有时还为传教士摆脱困境,如一个叫Rev.Charles Wenyon的医学传教士因外出而被当地人围攻, 此时一个被他诊治过的商人出来解围才得以离去(注: Armold Foster B.A, Christian Progress in China,The Religious Tract Society 1889 P178。)。
其次,它还对中西文化交流作出了贡献。早期医学传教固然有许多缺陷,但是一系列诊所、医院的设立却给中国人带来了近代西方医学,使他们接触到西方医学科学。而且医学传教士在治病之外还向中国人教授近代医学,不仅培养了中国第一批西医人才,而且有利于近代医学在中国的传播。如乙醚1846年才在波士顿首次使用,伯驾的一个中国学生竟于1847年就在中国使用。(注:China Christian Year Book,1931,P358。)医学传教士在传教治病外, 他们还译著了许多著作。这以合信、嘉约翰、德贞等为代表。以合信为例,他被称为模范传教医生、第一个为中国著作医学书的人(注:Christian Progress in China P163,China Christian Year Book,1931 P356。), 他先后译著有《全体新论》《西医略论》《妇婴新说》《内科新说》等,与其有交往的王韬称其作“笔墨简洁,讲论精核,真传作也”。(注:方行、汤志钧整理《王韬日记》中华书局1987年版P55。 )这些著作影响甚远,当合信“始著《全体新论》时,远近翕然,购者不惮重价”。该书后被刊入《海山仙馆丛书》,“流传最广”(注:王韬《瀛壖杂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P119。)。嘉约翰在1887年以前也著书甚丰。此外尚有Dr .Dugeon、Dr.Osgood、Hunter、Porter等也多从事过医学著作的编写与翻译(注:China Christian Year Book,1931,P356—357。)。他们的这些工作为近代医学传入中国作出了不可忽视的贡献。
再次,医学传教事业与晚清政治有密切的关系。医学传教作为传教事业的一部分,随西力东渐而来,因此与晚清政治不无关系。
这首先可从清政府对其政策变化中看出。起初清政府禁教时,医学传教自然受到很大限制。鸦片战争后,清政府虽然迫于不平等条约的束缚,给于西方以传教与设医院的特权,但是直到19世纪50年代官方仍是限制。1850年官方对福州神光寺传教士的态度是:向城厢居民遍为告述,仍以士民公议为词,不准赴该寺听经就医”(注:《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中华书局1979年版卷3 P83。)。但天津条约、 北京条约又迫使清政府承认自由传教与设立医院。此后加之医学传教的效果日渐显露,其除受中国官方保护外,与官方的关系日益亲密。马根济之与李鸿章就是一个特例。此外有些地方官还对教会医院以支持,如当美国传教士在福州设医院时,“闽督部院亦曾捐助五百洋元”。(注:朱士嘉编《十九世纪美国侵华档案史料选辑》(下册)中华书局1959年版P460。)有些医学传教士还被官方聘用,如马根济曾帮李鸿章创办医学校,德贞也曾在同文馆任教习多年。可见在西力东渐过程,清政府对早期医学传教经历了以下变化:排斥——被迫接受与抗拒——接受与保护。这种政策变化对教会医疗事业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同时我们还应看到早期医学传教与教案有不可分隔的关系。 正如1913年一位西方人所说,“在反对外国人的动乱中,医院有时是一种引起动乱的原因”(注:F.L.Hawks Pott,The Emergency in China,New York,Missionary Education Movem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Canada 1913 P221。)。笔者认为它与教案有如下两种关系。 一是教会医院引起教案。由于长期以来,中国人总以为外国人挖眼剖心以做药,因此一开始对医院有颇多怀疑。故当教会与民间发生冲突时,有人再以此加以煽动。教案因此而起。此外有时国人对教会医院的怀疑也直接引起教案,“扬州教案由西医割验死胎,酒沁瓶中为士人所窥而起”(注:李刚已《教务纪略》文海出版社版P323。)。二是教案引起对医院的破坏。许多次教案发生时,国人对教会公产一并加以破坏,教会医院往往横遭破坏,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此种关系可谓城门失火,殃及池鱼。
另外不少早期医学传教士由于对中国社会了解较多,往往参于本国的对华交涉,有的后来还充任本国的外交官或领事,对中外关系产生了一定影响。这以伯驾最为有名。早在顾盛使华时,他就参于其中,充任秘书与翻译,而且《望厦条约》中关于设立教堂、医院的规定还他有关,原因就是“由于中国的一个低级钦差感激巴驾博士替他父母看病的缘故”,“才在这位中国人的建议下,被列进顾盛条约的第十七条”(注:泰勒·丹涅特著姚曾廙译《美国人在东亚》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P475。)。1855年伯驾离开教会进入外交界,任美国驻华全权委员,对中美关系产生了很大影响。此外费煦等也曾任美国驻华的副领事等等。
总而言之,早期医学传教在近代中国的发展,不仅创立了一批教会医院、诊所,而且传播了近代医学知识;它不仅影响了中国人对西方的看法,而且对传教以至中国政治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一切为医学传教在近代中国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