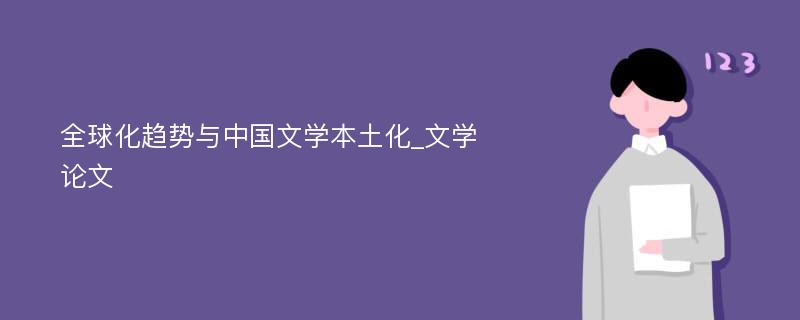
全球化趋势与本土化的中国文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本土化论文,中国文学论文,趋势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随着全球化浪潮的到来,中国社会的传统壁垒正经受着巨大的冲击。经济一体化、科技现代性和审美现代性等问题的提出,更使处于转型期的中国当代文学,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但值得注意的是,当代文学究竟做出了怎样的回应,它们的真实表现是什么?当代文学和它的作家们是如人们所言进一步走向了审美经验的全球化呢?还是正在进行文学本土化的艰苦努力和探索?在这一过程中,作家中是否存在不可逾越的“代际”鸿沟,所谓的代沟能够成为衡量不同作家群审美追求的外在标准吗?如果不能,那么“新生代”、“60年代”或“70年代”作家真正的文学价值又在哪里?这些问题,都值得重新讨论和辨析。
一、意识形态的调整和文学世界的重建
在德里克看来,意识形态本身就是一种全球化现象。作为意识形态的不同形态,殖民主义、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都曾经是全球化的产物并以某种方式为其成型做出了努力。亨廷顿也认为,革命不是历史惯性的产物,而是现代化进程的直接结果。但他更关心的,与其是“革命必须对现代性说些什么”,“还不如说控制革命出现的方式”是什么,即它的具体社会实践及话语方式。(注:(美)阿里夫·德里克:《后革命氛围》第9、12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90年代初,中国社会的权威意识形态明显由紧张转向了松驰。改革开放的继续深入,尤其是全球化和城市化的来临,西方高新技术和跨国资本的大面积输入中国,和大众文化及传媒的蓬勃发展,使得意识形态制度不再以强加的方式决定社会的精神生产,人们开始重新考虑文学世界重建的工作。然而,积累了几十年而且已经高度体制化和成熟化的意识形态出现的“危机”,并非人们想象的马上就陷于崩溃的状态。事实上也不是那么简单。相反,它会以各种公开和隐蔽的面目在新的历史中“重现”。典型的表现,莫过于1993年前后权威意识形态和知识分子群体对贾平凹小说《废都》的共同压制与指责,王朔在《渴望》和他一系列小说中对知识分子精英形象的嘲笑,“二王”的论争,“马桥词典事件”,以及90年代末先锋诗坛内部爆发的“知识分子写作”与“民间立场”之争。在全球化这一文化霸权压制下,中国权威的意识形态的影响力似乎正日益减弱。但上述错综复杂的文学现象,又无处不显示着它巨大的“身影”和旺盛的生命力。这些都使人坚定不移地相信,在数十年的社会实践中,权威意识形态不仅在社会的层面上成功地形成了自己独具特色的体制化,而且也在人们(包括知识分子群体)的历史观念和内心世界中成功地实现了它的体制化。尤其是,这一本土化的“中国经验”,已经越来越深地和深然不觉地嵌入到中国当代作家的文学叙事和批评活动当中。
张炜、陈忠实、莫言、余华和刘震云被认为是用“乡土中国”的诗意化描写和反抗现代性,和对全球化趋势做出强烈反应的作家。在90年代,他们都试图借虚构的故乡神话来叙述自己的“老中国”故事。他们的特异表现,使人不由得联想起曾经深刻怀疑过民初甚嚣尘上的现代性的章太炎、周树人。张炜在一篇题为《诗人为什么不愤怒》的文章中说:“快放开喉咙,快领受原本属于你的那一份光荣!你害怕了吗?你既然不怕牺牲,又怎么能怕殉道?我不单是痴迷于你的吟哦,我还要与你同行!”(注:参见愚士编:《以笔为旗的世纪末批判》第201页, 湖南文艺出版社,1997。)其实,他本人就是一位有着浓厚的诗人兼哲人气质的小说家。在《秋天的愤怒》等作品的视域里,给人深刻印象的是作者对“土地”命运的思索和忧郁。渗透在《白鹿原》字里行间的,与其是白鹿原这块土地生生不息的悲歌,莫如是陈忠实爱恨交加之中的清醒与反省,和更深一层的矛盾与困惑。1998年版的“内容说明”,点出的正是这部雄奇长幅画卷的“文眼”:“主人公六娶六丧,神秘的序曲预示着不祥。一个家族两代子孙,为争夺白鹿原的统治代代争斗不已,上演了一幕幕惊心动魄的活剧:巧取风水池,恶施美人计,孝子为匪,亲翁杀媳,兄弟相煎,情人反目……大革命、日寇入侵,三年内战,白鹿原翻云覆雨,王旗变幻,家仇国恨交错缠结,冤冤相报代代不已……古老的土地在新生的阵痛中颤栗。”
事实上,对50—70年代改造中国传统宗族社会的持续不断的社会实践予以深切关注,同时以个人叙事颠覆国家叙事的,还有莫言、余华和刘震云等人。在我看来,他们试图用经过“叙事化”处理的意识形态写作,来挑剔、拆卸和消解权威的意识形态;或者是在通过极端个人化的文学叙事,质疑曾经被奉为国家神话的宏大叙事,进而还原“50—70年代”中国乡村这段本来是喜剧性的、同时散发着质朴和深沉的宗法制气息的“历史”。于是,对90年代的读者而言,莫言《丰乳肥臀》中那个“母亲”的形态(实际是大地的意象)是十分陌生的。她性感、粗野、母性十足,充满原汁原味的蓬勃的生命力和乡村的气息。她完全不去理会那道“母亲——大地——国家——现代政党——”的僵硬公式。她扭动着肥大无比的性感的臀部走在高密土地上的信心十足的身影,无疑是对国家叙事的戏弄和改写。余华的《活着》、《在细雨中呼喊》和堪称本时期小说“绝笔”的《许三观卖血记》,刘震云的《故乡相处流传》、《故乡天下黄花》、《温故一九四二》和多卷本的《故乡面与花朵》,这些小说文本与其是嘲弄的,还不如说是暖昧的;它们的丰富性与其是借小说的意识形态来颠覆生活中的意识形态,还不如说作家所选择的“旁观者”和“读者”的立场。在《许三观卖血记》意大利版和德文版的“自序”中,余华曾声称他只是一个被动的“叙述者”。(注:《余华文集·许三观卖血记》,南海出版公司,1998。)但他又承认:“长期以来,我的作品都是源出于和现实的那一层紧张关系。我沉缅于想象之中,又被现实紧紧控制,我明确感受着自我的分裂,我无法使自己变得纯粹。”(注:《活着·前言》,长江文艺出版社,1993。)在《活着》中,主人公福贵把服从国家的主体当成放弃个人幸福的绝对前提:1958年,他的五亩地全部划到了人民公社的名下;在60年代初的大饥荒中,他不仅饿死了女人,还不明不白地葬送了儿子和女儿……福贵与新时代之间出现了一种极其奇怪的悖论关系:新时代本应按照它的崭新理论让人获得“新生”的,但却把福贵们带向了残酷的和无奈的死。而令许三观苦恼的是怎样把血“卖出去”,他的一生可以说就是一部最终失败了的卖血史。但“重写”历史的记忆,在意识形态性中反观每个人的命运,并不等于要重复70年代末干预生活的文学实践。也不意味着否定自己曾拥有的“历史”。在这些作家的心目中,“作家的使命不是发泄,不是控诉或者揭露,他应该向人们展示高尚。”在他们对文学本土化的理解中,“高尚”的命题“不是那种单纯的美好,而是对一切事物理解之后的超然,对善与恶一视同仁,用同情的目光看待世界。”(注:《活着·前言》,长江文艺出版社,1993。)
但是,无论是革命的现代性,还是全球化所包含的现代性,都是以取消或同化“地方性”和“本土性”为目的的。中国革命的现代性工程,是通过“全民总动员”的激进方式,把每个中国人编排在大大小小严密的组织,例如单位、工厂、学校和生产队等形形色色的现代化的“符号”里。90年代中国作家的文学书写,却令人惊讶地出现了关于“故乡”的重新命名:例如张炜的“胶东”,陈忠实的“关中”,莫言的“高密”,余华的“余姚”和刘震云的“王楼乡”,等等。几十年来极端发展的现代性,使中国文学走向了被现代性所长期遮蔽的“乡土性”,或曰“本土性”。正像李瓯梵注意到的:“历史都是国家民族的历史,即所谓‘大叙事’;而当‘大叙事’走到尽头时,就要用老照片来代表个人回忆,或某一个集体、家庭的回忆,用这种办法来对抗国家、民族的大叙事。”(注:李瓯梵:《当代中国文化的现代性和后现代性》,《文学评论》1999年5期。)需要讨论的问题是:革命的现代性, 即权威的意识形态性是否如有的人所说走向了“终结”?如果说中国社会的现代性本来就存在着西方文化视角无法理解的复杂性和多变性,那它在近期中国文学中的矛盾和表现又在哪里?
二、都市化语境中的“个人体验”
90年代中期后,中国社会大大加快了现代城市扩张的速度。高层建筑大面积崛起,地铁和轻轨铁路正从地下或地上向城市的腹部与郊外延伸,排名前列的世界著名银行、大公司纷纷进入中国市场,报业、出版、电脑等信息网络犹如蜘蛛般遍布每一个家庭。偌大的中国,俨然陷入了全球化趋势的汪洋大海中。在此背景中,都市白领(包括文化、科技和经济白领)作为一个新的社会阶层迅速走上了现代的舞台,而以注重个人体验和个人感受的新生代、60年代和70年代出生的作家群也在极短时间内成为文坛的又一个“亮点”。
以另类的文学姿态与知青文学、先锋文学和新历史主义文学划清界限,成为这些新一代作家的普遍策略。对意识形态的嘲弄,对传统道德不屑一顾,把欲望、本能和反集体的情绪赤裸裸的表现出来,是他们对文学主题的重新预设,事实上也成为他们小说的叙事结构和细节。作为这一派作家的代表人物,韩东、朱文、鲁羊、李冯、李大卫强调对个人生存状态的体验,有意与他们成长的历史保持距离。这种与传统社会的意识形态之间产生的陌生感,似乎与美国“垮掉派”作家同社会关系的“短路”现象有几分相象。其实,它主要来自90年代典型的“中国语境”。朱文就曾说,他理解的个人的“孤独感”,是那种“一小撮人在大多数人中的感受”。 (注:朱文:《答贺绍俊先生九问》, 《山花》1999年7期。)在小说《人民到底需不需要桑拿》中, 朱文塑造了一个近于疯狂的下岗干部的形象。他神秘莫测然而极其亢奋地走访这座城市的大街小巷,核实桑拿浴池的数目,虽然不能改变社会发展的轨道,然而却从中获得了报复的快感。像朱文大多数作品一样,他的主人公身上往往有一个虚拟的自我。面对意识形态的控制日益失效后的混乱状况,他以愤怒的口吻,对人性的全部弱点进行了彻底的展露;同时,又以超然的冷漠回击了社会的冷漠。在这里,“酒巴”、“舞厅”、“街头”等的存在不过突出了朱文们文学观察的日常性,但是与真正意义上都市白领们相比,这种日常性又分明显示了他们作为作家精神生活“二难”的境况。比如,在讨论小说写作的日常性问题时,这些青年作家都明确表示了相左的意见:“为什么这个世界我们说它是个大千世界?英雄的生活或革命者的生活是否具有日常性?一个死囚在死号里每天看晚报,手淫是否具有日常性?军人在战场上每天枪林弹雨,这也是他的日常生活。我们不能说哪一种生活是日常生活,所以我反对这种元日常生活的态度。”(注:李大卫、李洱、李冯、李敬泽、邱华栋:《日常生活——对话之二),《山花》1999年2期。)因此, 不能简单把他们的行动解释为他们的思想,把他们反传统的冲动一律视为文化上的“弑父”。他们与余华、莫言、刘震云的差异主要还在理解生活的角度上,是叙事手段的细碎感、杂乱感和破裂性,正像有人评价的那样:“他们有一种比余华们来的更冷峻而彻底的现实态度。”(注:陈晓明:《“历史终结”之后:九十年代文学虚构的危机》,《文学评论》1999年5期。)
确实,和韩东、朱文们相比,卫慧、棉棉、丁天、陈家桥等70年代出生作家似乎离本土化的文学写作越来越远。当他们刚出生不久,中国就开始了20世纪又一次更加急切和“跳跃式”的现代化冲动。作为在全球化经济和文化传播中成长的一代作家,他们似乎也在远离50—70年代为我们几代人准备的那份厚重的“革命遗产”。齐红说:“如果说六十年代的作家们对于苦难与荒诞年代的记忆也仅仅是一幅发黄的童年时期的画面,但他们仍然在这画面中感觉到那个时代的可怖以及这一切对于人性的压抑与摧残”,对70年代的作家而言,历史只意味着“一种少年式的忧愁,是一个人成长过程中的小小的挫伤”。(注:齐红:《漂流: 认同或反抗——关于“七十年代出生”写作者的笔记》, 《山花》1998年9期。)换言之, 他们是以与历史为断裂的方式成长为一代新人的。青春期的孤独和焦虑感,成为卫慧《像卫慧那么疯狂》、《蝴蝶的尖叫》等作品人物基本的生存方式和经验。这些碎片化的人生故事,讲述的无非是年轻女孩在歌厅酒巴与男人们纠缠不清的情爱。生活最时髦的时尚,与少女们内心尖锐的伤痛混为一体,成为先锋性的文学审美经验;个人的幻觉在世纪末情调的裹挟中,展现了极其“现代”的都市口味与风情。棉棉笔下出现的是迅速走向都市化的上海的大背景。在《告诉我通向一个威士忌的路》中,“面条”的妈妈被轮奸的记忆,成为年轻人之死的唯一依据。但他的另一篇《啦啦啦》,则放肆地表露出对现实生存规则无所顾忌的亵渎和不屑。而周洁茹的《点灯说话》,展示的则是滑板、手提电话和电脑上网这一充满物质诱惑的世界。无意义的同性恋,在商场偷窃,空虚之中的一场激情宣泄,尽管充斥在这批青年作家随心所欲的叙述中,颓废和没落的外表下,仍然难以遮掩他们内心孤高的秉质。但这些关于城市边缘人的叙事,的确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传统经典文学的审美趣味,改变了人物的叙述模式和价值追求,呈现了人与意识形态化的当代文学几乎截然不同的社会场景。
也许人们会提出一个纯粹是文学史的问题,这是否意味着小说又回到30年代的新感觉派那里?它是简单的雷同和重复呢,还是要打碎文学传统,而重建了另一种文学的秩序?在30年代前后将近10年的现代化进程中,中国的现代主义文学出现了一个短暂的高潮。而在现代化前沿的上海,则出现了小说的新感觉派和现代诗派。严家炎认为:“中国新感觉派创作的第一个显著特色,是在快速的节奏中表现现代大都市的生活,尤其是表现半殖民地都市的畸形和病态方面。”它的“小说场景,涉及赛马场、夜总会、电影院、大旅馆、小轿车、富豪别墅、滨海浴场、特快列车等现代都市生活的各个方面,其中心主题则是暴露资产阶级男女的堕落和荒淫”,他们的作品,“存在着相当突出的颓废、悲观乃至绝望、色情的倾向。”(注:严家炎:《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第141、16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 )吴晓东指出:新感觉派作家“出没于喧嚣骚动的十里洋场,尽情享受现代都市物质和商业文明,同时又受西方现代艺术尤其是电影的熏陶,具有鲜明的文学先锋意识。”而且,“擅长于捕捉都市化意象”、“在文本形式层面整合现代都市的体验和感性”和“小说叙事模式与都市生活范型之间的内在对称性”,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他们现代意义的审美倾向和文体风格。(注:参见程光炜、吴晓东、孔庆东、郜元宝、刘勇:《中国现代文学史》第178—181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
中国的历史是以“循环式”的存在方式展现自己的面貌的,20年世纪数次现代化进程的发生和变奏也不例外。虽然文学的表现在不同的时空背景下有它自己的独特性,然而并未完全脱离文学史的轨道成为真正的“另类”。另类文学不妨夸张的先锋姿态,却总是以相反的效果提醒人们联想起文学史的“先例”。不错, 90 年代的中国文化语境毕竟与30年代有了极大的不同,但它却共同拥有同一个“后进国家”的历史命运。以研究后进国家“现代化”而著称的A·R·德赛先生曾提醒人们注意这样一个也许很残酷的现实:国家现代化的“挫折”和“中断”;由于尖锐地意识到贫困、艰难和低水平的生活,民间社会与权威意识形态上层处于激化状态的矛盾;由此引起而无法摆脱的根深蒂固的民族历史归宿的宿命感,等等,(注:亨廷顿等著:《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经验的再探讨》第26—45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这些因素从根本上规定了中国先锋文学的历史性格和文化性格,在某种程度上,也构成它基本的创作诉求和艺术目标。所以,无论是“乡土中国”的历史情结,还是强调个人体验和另类的写作实验;无论声称自己的“代际”断裂,还是为了文坛策略而夸张“新生代”的姿态,最终,它们都指向了全球化进程中独一份的“中国经验”。它们的话语方式,无一例外都是典型的中国的、本土的和文化的,是与全球化趋势冲突和互动的“地方性”的。
三、当前中国文学的叙事化倾向
在全球化的语境中,作为第三世界文化的中国文学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由此产生了一种新的叙事的可能性。这是因为,意识形态体制在市场经济冲击下出现的分化和弱化,导致了它与正在蓬勃发展的市民社会的进一步剥离。然而,正如前面所说,意识形态并没有完全放弃对文化生产的控制,包括对市民“公共生活空间”的控制。它也没有真正“终结”和“退场”。而是由前台转向了后台,由单一和单调的主流形态转移到五光十色的电影强档、广告和娱乐节目中间,以多元的、含混的和相对主义的面目出现在社会面前。像德里克所看到的那样:“自从八十年代再次开放后,尤其是进入九十年代,中国的大门完全对资本主义敞开,成为全球资本的重要(如果不是唯一的话)角逐场。沿海地区经济与许多地区经济(日本,南朝鲜,等等)联为一体,国家政治界限出现了严重问题。散居世界各地的中国人,包括东亚、东南亚国家以及海外华人,积极参与中国经济,将界限问题进一步复杂化。”(注:《后革命氛围》第73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但他也提醒人们去注意另一个事实:民族经济的全球化与国际化虽然削弱了自主自足的观念,结果却导致民族文化的重建,以抵御危及民族存在的全球力量。必须提到的是,90年代对国家元叙事的普遍怀疑,催生了当代文学中的多种声音,多元文化和个人主义叙事开始出现。这里既有由传统现实主义转轨而出的“三套马车”现象,有关注性别生存境遇的女性小说,有上述论及的新生代作家,也有“重返”或“重读”历史的各色艺术表现,例如,叶兆言的《王金发考》、《赛珍珠考》,苏童描绘清末民初家族生态状况的系列作品,刘震云关于“故乡”的诸多中长篇小说,等等。
文学叙事的象征化、多层次化和模糊含混化,是由“界限问题”的日趋复杂化决定的。在这里,阶级身份和价值观的优越性、优先权,不再是支配文学创作的关键因素,国家历史和日常生活的戏剧化与夸张化,也不足以决定作品的审美形态和基本取向。与此同时,把历史叙事多元化,甚至进行重新拼接与拆解组装,从多个角度进入对历史和人物命运的观察和描写过程,已普遍为人们所习惯和接受。在评论界和研究界兴起的对“十七年”红色经典的“重读热”,是其中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有人进入对文革文学“潜在状态”和写作的挖掘工作,有人对50—70年代文艺体制展开了深入研究,有人注意到这一时期文学的左翼文化资源及其历史效应,而有的人甚至对姚文元“批判文体”的修辞效果表示出浓厚兴趣。在《南方文坛》、《山花》等刊物上,对“当代文学关键词”的梳理,对“民间意义”的重新阐释,也显示了文学叙事的进一步发展。但问题的复杂性在于,叙事化倾向的完成必须得力于它多种复杂的结构性转换,在个人与民族之间,在今天与过去不同的时空条件下,在接受跨国技术和资本而又不愿真正认同西方霸权的矛盾过程中,这种结构性转换使得作家的创作进入了多重历史“覆盖”和“交接”的叙事状态。例如,早被认定是辛亥革命“异类”和文化“殖民者”的王金发和赛珍珠,其历史形象经过叶兆言重新修改和塑造,产生了复杂而新鲜的阅读效果。同时也产生了价值的相对主义倾向——由此获得了阐释空间的“最大化”。在80年代,刘震云是典型的传统乡村道德的讴歌诗人和现代文明(官场社会)的批判者。90年代后,他先后创作了一批以“故乡”为主题的叙事小说(我更倾向把这类小说称作“叙事小说”,而非新历史主义小说)。刚开始,刘震云企图讲述一部20世纪被迫“现代化”的乡土中国的历史,然而他发现,即使这种历史也得依靠“叙事”来完成。它必须服从文学叙事的游戏规则。于是,他把全部心力倾注在最大化的多卷本叙事小说《故乡面与花朵》之中。他采用福克纳散点透视和打破时空关系的小说结构,以20世纪末中国式的黑色幽默来重新拼接个人与国家民族的关系,目的则是为了颠覆历史的逻辑。历史虽被叙事颠覆:但它的碎片却真实地散落到了人们心灵的各个角落。它并没有被叙事从民族大记忆的硬盘上删除。
在这种情况下理解当前文学的叙事倾向,说明真正的“个人写作”和“另类写作”的概念是很难成立的。其实,即使是极力主张这一姿态的女性小说,也难以在性别的“镜像”中建立独一无二的价值系统和符号系统。例如,徐坤、林白、陈染和海男等人带着强烈自叙传色彩的小说。她们富有挑战性的作品,不过是对一种“莫须有”生活的叙事,是在用叙事的语言组织一个想象的世界。这里面,是下意识的性幻觉,是自残的暴力,是倒错的性别混乱或者认同,是巧妙设计的一个又一个所谓的“个人事件”,更是对男性中心的注定没有结局的挑战;这里面,充斥着对个人生活历史的“改写”,满贮着自欺的眼泪,是对历史逻辑无望的逃避,和对国家元叙事力不从心的反抗和越轨。比如,林白《一个人的战争》中对W大学的回忆,她那游侠般的四川之行, 陈染《私人生活》中的叙事假相,等等。另外,新近出现的实在是清末谴责小说翻版的“官场小说”,如王跃文的《国画》、李佩甫的《羊的门》、张宁的《软弱》等,试图在脱轨的历史之外建立自己的叙事可能性。和刘震云、陈忠实的文学叙事有所不同的是,王跃文们在作品中并没有重建历史的强烈冲动,他们的目的是要在“现实主义”的叙事中将其彻底损毁。这些,都反映了最近创作中出现的“后历史化”的重组与努力。但我更倾向于认为,叙事之所以成为当前文学创作的重要现象,反映的正是全球化趋势下权威意识形态进一步的弱化和价值目标的丧失,社会在价值冲突中的失调与混乱。元叙事的失语,为文学充分走向叙事化提供了现实条件和生产的环境。而这正是文学叙事化的美学魅力所在。
然而,中国文学日渐高涨的叙事化(非价值化)也要为此付出想象不到的代价。进入21世纪以来,社会在逐步摆脱韦伯所言的卡里斯马型的意识形态之后,正向着“合理性”的状态艰难地前行。回望刚刚掀过的历史的一页,人们难免会为当代中国文学没有为那惊心魄的革命记忆留下伟大的作品而遗憾。而大众文化、公共空间和交往方式,将会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到来进一步使人们的情感和思想趋向于缺乏个性的一体化。在日常萎缩的文学空间中,叙事化的倾向将会把文学带向哪里,这个问题势必会引起人们的关切和讨论。正像当代中国思想文化解构的历史阶段行将转向整合一样,叙事并不是当代文学最终的目的。这就使经过意识形态文化急剧调整之后的当代中国文学,需要寻找新的思想文化资源和言说方式,以面对这一世纪的全球化挑战。
标签:文学论文; 中国文学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全球化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文化论文; 刘震云论文; 本土化论文; 历史论文; 作家论文; 现代性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