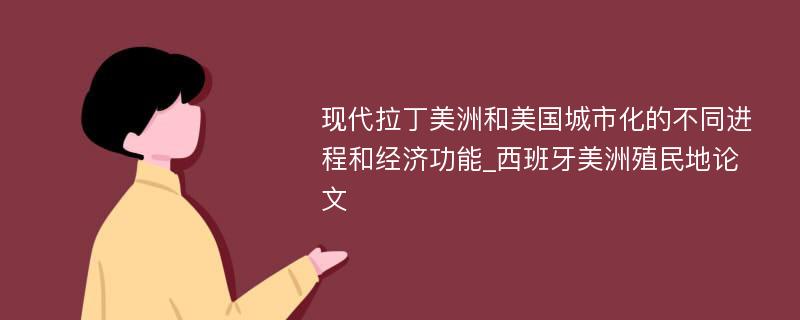
近代拉美与美国城市化的不同进程与经济职能,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拉美论文,美国论文,近代论文,职能论文,进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代美洲发展史上的城市化一直是个重要的社会经济现象。但是,由于历史传统和现实因素的作用,关于城市的概念和实践,拉丁美洲与盎格鲁美洲之间很早就存在着差异。从殖民地时代起,前者就将城市视为殖民帝国的政治和宗教核心;而后者关注清教徒的“山巅之城”理想的实现和商业活动。独立后,特别是到19世纪后期,美国的城市化与工业化同步快速推进,成为新的经济生长点;而拉丁美洲的城市化先于工业化,是传统城市模式的扩展,主要表现为人口集中和城市规模的扩大。显然,城市化的不同进程和职能,也是造成拉美与美国社会经济差异扩大的重要因素之一。对此,我们有必要进行深入的分析研究。
一 拉丁美洲与盎格鲁美洲关于城市的概念的差异
早在殖民地时期,拉丁美洲和盎格鲁美洲就先后创建了一大批城镇,这些城镇在有关地区承担了不同的社会经济职能。16世纪初,西班牙在美洲进行征服和殖民的同时,还持续不断地进行建城活动。其首要目的是要把城市作为向新大陆扩张的核心。在美洲大陆,1524年西班牙殖民者按照他们自己所设计的蓝图重建了阿兹特克人首都特诺奇蒂特兰,即今墨西哥城。从此该城成为西班牙人征服今墨西哥全境、美国西南部及中美洲北部的行动基地。他们以墨西哥城为出发点,建立了瓜达拉哈拉、普埃布拉、瓦哈卡、危地马拉城、恰帕斯王家城镇和瓜那华托矿区。在南美洲,1535年西班牙人建成利马,此后又建立了智利的圣地亚哥、康塞普西翁、拉塞雷纳、拉巴斯、科恰潘帕和波托西矿区。西班牙人又从秘鲁出发,先后建立了一大批城市。(注:Jorge E.Hardoy,ElUrbanizacion,Inser tado en America Latina en su Arquitectura,Compilada por Roberto Segre,Siglo XXI editories,Mexico,1983,pp48~51.)16世纪形成的城市网一直存在到殖民地末期,并保持到20世纪初。而英属北美殖民地城市网的形成则较晚。其最早的城市是由西班牙人在1565年建成的圣奥古斯丁,位于今佛罗里达州。纽约、波士顿和费城都建成于17世纪。到1775年,纽约市人口仅2.5万人,波士顿为1.6万人,最大城市费城也只有4万人。(注:Bayrd Still,Urban America,a History with Documents.Brow and Company,Boston,1974,P.12.)
从文化传统看,拉丁美洲殖民地时期的城市是伊比利亚半岛的中世纪建筑在精神和物质上最明显的延伸的产物。其主要特点是:城市的网状布局整齐划一;城市中心极为重要,其大广场不像欧洲那样作为市场,而是市民的政治和宗教生活的中心,在那里建有壮丽的大教堂和宏大的总督府或省府大楼,所以成为权威的象征。实际上,在美洲只有西班牙才带来这种城市的宏伟的形貌。与此相对照,无论是在巴西的葡萄牙人、还是在波士顿的英国人或在新阿姆斯特丹的荷兰人,在他们建立的首批城市中都有弯弯曲曲的陋巷。(注:Luis Weckmann,La HerenciaMedieval de Mexico,Tomo Ⅱ,El Colegio de Mexico,1983,pp521~522.)特别是新英格兰的清教徒拒绝采用英国国教的建筑艺术,因此他们建成的四方形教堂——“集会场所”非常简陋,而这些教堂还兼作城镇会议和立法会议的大厅。英国与荷兰的殖民地城市都明显具有商业的特征。由此看来,从殖民地初期起,西班牙美洲的城市创建就特别关注其政治和宗教的作用,而盎格鲁美洲则坚持清教徒的理想和城市的商业功能,这种城市观念的差异源自美洲各殖民地不同的文化背景。
西班牙王室和殖民者在美洲的城市创建活动,既反映了中世纪末期西班牙帝王的统治意志,又是对欧洲各种古典的和基督教的原理运用的产物。
从其理论来源看,西班牙美洲的城市概念源自欧洲的各种古典的和基督教的原理。其中首先是希腊的城邦观念,即城邦是农业与城市的共同体,其基础不是人们所自愿达成的“契约”,而是承担各种职能的群体组合而成的“政治”实体。其次是罗马帝国的观念,自治市是“开化”农村居民的手段;它既是帝国的组成部分,又是人类世界的组成部分。再就是奥古斯丁的天堂观,即以基督教的至善典范对抗卑鄙罪恶的世俗城市。最后是伊甸园式的人间天堂之太平盛世观,这种乐园将在教会的指导下,在海外新皈依天主教的人们中间兴盛起来。(注:〔英〕莱斯利·贝瑟尔主编:《剑桥拉丁美洲史》,第2卷,第70~71页,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1997。)显然,上述的伊比利亚城市文化传统为西班牙殖民者和城市创建者所继承,并被运用到美洲殖民地的城市创建活动中。这种文化传统观念与北美的英国清教徒移民的城市观念形成鲜明的对照。
英属北美城镇观念源自清教徒的宗教理想。17世纪初,为逃避宗教迫害而移居北美的英国清教徒首先关注的是建立自己理想的“天国”,正如美国历史学家丹尼尔·布尔斯廷所说的,新英格兰清教徒教区(或曰“山巅之城”)首先是布道和教育的中心,它们的特点是简朴而实用,其“礼拜堂是有意按犹太教会堂的格局来兴建的,它基本是一个教育场所。在这里,全社区的居民了解到自己应尽的义务;不同的人找到不同的皈依途径,所以他们能更好地在荒野上建立自己的天国,建立他们心目中的‘山巅之城’,而其他人也可以从他们经验中得到启示。在新英格兰,礼拜堂既是城镇的地理中心,也是城镇的社会中心,而布道则是礼拜堂的中心活动”。(注:〔美〕丹尼尔·布尔斯廷:《美国人·开拓历程》,第14页,北京,三联书店,1993。)
盎格鲁美洲清教徒所创建的“山巅之城”,尽管存在中世纪社会的从属关系的残余,但是,除了父母与子女关系之外,一切关系都是由人们自愿达成的“契约”决定的。社区是神圣秩序的体现,而不是神圣秩序的复制品,从这个意义上说,社区是没有“共同”特征的。与此同时,从母体社区迁出的人们都可以建立新的社区,并由此开始同上帝的独立自主的关系。显然,这一切体现了新兴资产阶级的自由原则。与此相反,在西班牙的各级殖民政权的严密控制下,其美洲殖民地的城镇则具有共同的特征,它们都是西班牙帝国和天主教会秩序的缩影。
此外,盎格鲁美洲殖民地的城市也是活跃的商业中心。例如,波士顿由于其居民冲破宗主国的禁令而发展起造船业,而在北美相互竞争的海港中一直处于领先地位。经过发展,它成为北美的一个巨大的“商品城”。欧洲的大部分商品首先运到波士顿,再由此运往其他殖民地。虽然费城和纽约的商业也很活跃,但是中部殖民地和南、北卡罗来纳的商品都是通过波士顿的商船运往西印度群岛和欧洲的。波士顿也同新英格兰较小的城镇保持商业关系,其商人通过用欧洲进口货物来交换邻近地区的木材和其他多余的产品而发财致富。(注:〔美〕纳尔逊·曼弗雷德·布莱克:《美国社会生活与思想史》,上册,第74~75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通过以上实例,我们可以看到,盎格鲁美洲的城市不仅是清教徒的布道和教育中心,而且也是殖民地的商业中心。这就为独立后美国的城市承担重要的经济职能奠定了基础。
如果将英属北美城镇的商业活动与西班牙美洲城市所特有的农业及政治控制进行比较,我们就不难发现,前者是商业资本主义早期形式的起源地,而后者则是强占土地及其资源的出发点;前者是建立新的经济和法律秩序的起点,后者是维持殖民帝国秩序的工具。
二 19世纪美国和拉美城市化发展的不同进程
恩格斯指出:“在美国这片得天独厚的土地上,没有中世纪的废墟挡路,有史以来就已经有了17世纪孕育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因素……”(注:恩格斯:《美国工人运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38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因此,美国的城市化是在起点高、发展快的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结构中推进的。
从19世纪初起,美国的工业革命就从东向西扩展,并全面带动了城市化进程,而城市化反过来又推动了工业化的迅速发展。这样,工业化和城市化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两者都促使美国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的工业社会转型。与此相比较,19世纪后期,即在初级产品出口型经济高潮时期,拉丁美洲的城市化主要是由外部因素推动的。正如詹姆斯·R.斯科比所分析的,“欧洲市场和企业对拉美能够生产的各类食品和原料的日益增长的需求,再加之拉美的城市居民对国外制造品所形成的购买力,开始促进贸易的发展,使之达到了在殖民地时代难以想像的水平。同时,新技术也促使商业活动进一步加强。”(注:〔英〕莱斯利·贝瑟尔主编:《剑桥拉丁美洲史》,第4卷,第231页,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1997。)这一切因素都刺激了拉美城市的扩展。但是,这种城市化主要体现在农村人口向城市集中和商业的增长方面,而很少涉及城市工业能力的增强。因此,这就难以带动整个社会经济的转型。19世纪,在发达的市场经济刺激下,美国的城市化从东向西迅猛推进:东北部传统的商业城市率先成为工业革命的摇篮;而后西部城市化与工业化同步发展的潮流迅速扩展。特别是西部的城市化是沿着一条独特的道路扩展的,也就是土地投机商和铁路公司按照市场经济原则来推动城市选址、规划和营建活动。正如丹尼尔·布尔斯廷所指出的,在美国西部,“新的城市在原来一无所有的地方迅速发展起来,它们没有历史但有着无限的前景。它们是美国实业家们最早的自然聚集处。当实业家起初出现的时候,他们的主要商品是土地,其次是交通运输。土地权和运输权从政治象征和相传动产转变成单纯的商品,这也是美国特有的一种现象”。(注:〔美〕丹尼尔·布尔斯廷:《美国人·建国历程》,第140页,北京,三联书店,1993。)
美国西部城市化是同土地大规模投机活动密切相关的。关于两者的相互关系,美国学者作了以下的阐述:“城市化与土地投机的交集点主要体现在土地、人口和资本三大经济要素的流动,因为城市化的前提是农业用地不断成为工业用地,农村人口不断流向城市,而这种土地与人口的流动又必须由大量的资金予以推动和支持。19世纪美国的土地投机正是从正面激励和推动了土地、人口和资本流动的城市化导向,为美国西部由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从农村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过渡贡献了力量。”(注:〔美〕洪朝辉:《土地投机与19世纪美国西部城市化》,载于王旭、黄柯可主编:《城市社会的变迁》,第49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独立后美国持续向西扩张,获得了辽阔的领土。对于这些土地,初期的政府“难以执行任何庞大的殖民开拓计划,但由于为有效的占有创造了一些必要的条件,它为个人的和集团的活动铺平了道路”。(注:〔美〕查尔斯·比尔德、玛丽·比尔德:《美国文明的兴起》(第一卷 农业时代),第492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这样,1785年颁布的《土地条例》启动了出售公共土地的进程,为土地投机商购买640英亩以上的大片西部土地提供了法律基础。
借助于1785年的《土地条例》,土地投机集团大规模介入西部土地市场,为了促使土地价格上涨,它们参与城市化进程。据估计,到1836年联邦政府出售和处理西部公共土地约3800万英亩,其中约2900万英亩落到土地投机者手中。除此之外,各铁路公司也积极参与土地投机活动,由于获得政府的大量赠地,它们拥有的土地面积非常巨大。1850~1871年它们获得的赠地高达13140万英亩,其中堪萨斯州10家铁路公司就获得了834.66万英亩。(注:〔美〕洪朝辉:《土地投机与19世纪美国西部城市化》,载于王旭、黄柯可主编:《城市社会的变迁》,第50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为了促使它们所掌握的这批土地价格上扬,各土地投机集团从一开始就介入了城镇的选址、规划、营建和投资活动。因此,一些土地投机者实际上成为西部城市化的规划者和推动者。例如,威廉·拉里默将军(1809~1875)就是参与西部城市创建活动的土地投机者。他在一封寄往东部的信件(1855年5月23日)中简述了他的土地投机与城市创建活动:“我在内布拉斯加州的拉普拉特取得了两块土地的产权……我们设计了一座城镇,我当选为那家开发公司的董事长,拥有这个城镇的1/3……我确实非常喜欢这个地方……我相信我在这里几年内就可以大展宏图。”(注:〔美〕丹尼尔·布尔斯廷:《美国人·建国历程》,第144~145页,北京,三联书店,1993。)
在西部城市化过程中,铁路公司利用铁路修筑和所控制的巨大地产,积极从事所谓的“镇址”投机活动,这在客观上促进了城市化的发展。19世纪中期,密苏里州的堪萨斯城作为西部铁路的一个中心和地区首府而崛起,它提供了一座城市的发展与铁路计划关系密切的最好例证。这个社区起初只不过是一个边境仓库所在地。19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随着贸易活动从圣路易斯河向密苏里河转移,一些小型贸易社区开始在密苏里河西岸出现。1838年建镇的堪萨斯开始成为货物的中转站,50年代随着贸易的扩展和移民的迁入,小镇开始发展,一些本地地产主和来自东部的投资者认为西部城市具有无限前景,所以规划通过铁路修建来创建一座地区性城市。这项计划虽然被内战所打断,但是战后堪萨斯城的地产主又提出修筑铁路计划,这就使得该城迅速发展,人口从50年代的4500人增至1880年的55785人。同时,该城的肉类包装设备工业得到快速发展。(注:Charles N.Claab and Theodore Brown,A History ofUrban American,The Maccmillan Company,Collier-MaccmillanLimited,London,1969,pp114,116.)通过这些实例,我们可以看到,西部城市化的启动并非联邦政府的行为,而是土地投机集团和铁路公司通过土地市场炒作而实现的。
在推动西部城市化发展方面,土地投机集团在吸引外国移民和东部居民移居西部城镇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就像美国历史学家所说的,“地产公司有助于激发向西前进的道路”(注:〔美〕查尔斯·比尔德、玛丽·比尔德:《美国文明的兴起》(第一卷 农业时代),第491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
除了土地和人口流动之外,西部城镇开发和营建所需的巨额资金也主要来自土地投机集团的炒作活动。美国学者指出,19世纪美国经历了狂热的城市建设,那些富有创业精神而又足智多谋的投资者购买土地来规划新城市,然后以高价出售给其他渴求能获得更大利益的投机商。正是这种期望推动了地产业的迅速发展。这种地产炒作不仅使投机者获取了高额的利润,而且也为城市建设筹集到了足够的资金。
总之,19世纪美国西部的城市化主要是由土地投机者和铁路公司推动的,联邦政府只是提供法律保障。城市化道路不仅加速了西部各城市的规划和建设速度,同时带动了工业化进程和自然资源的充分开发及利用。
与美国的城市化不同,19世纪后期拉美城市化则主要是在初级产品出口高潮的推动下启动的,表现为传统城市的扩展及其贸易与政治作用的加强。这一时期,欧洲工业国需要拉美生产的各种原料和食物,同时寻求扩大销售市场。由此出现的进出口高潮刺激了欧洲的、特别是英国的资本投向拉美国家的一些首要城市,用于银行和保险公司的创办、铁路和港口的修建等。一些城市的扩展还推动了城市基本设施的建设,如供水、排水、交通运输和以后的电力事业。由此可见,拉美城市扩展的动力主要来自外部。特别是铁路和轮船的使用从根本上改变了拉美国家的运输条件,使得铁路沿线的城市和港口城市快速发展。例如,1863年竣工的智利圣地亚哥至瓦尔帕莱索的铁路,使得瓦尔帕莱索的人口在1850~1870年间增长了1倍。此外,1870年建成的从罗萨里奥通向阿根廷内地的铁路,使得罗萨里奥的规模在随后的10年内几乎扩大了1倍。(注:〔英〕莱斯利·贝瑟尔主编:《剑桥拉丁美洲史》,第4卷,第232页,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1997。)
在19世纪后期拉美城市化进程中,各国首都最早得到显著的发展。它们吸纳了大部分外国投资,从而有条件修建各种设施来处理进出口业务,同时又拥有大量的中上层阶级成员消费从欧洲进口的商品。其中发展最快的是沿海城市,如:布宜诺斯艾利斯、蒙得维的亚、里约热内卢、利马及其邻近的卡亚俄港、加拉加斯及其邻近的出口港拉瓜依拉。连接海港铁路的修建也促使了内陆首都及其出口港的发展,如墨西哥城和韦拉克鲁斯。
19世纪后期,欧洲移民的涌入也是推动拉美城市化的重要因素。当时欧洲一些地区存在着日益恶化的社会经济状况,如意大利南部各省、西班牙的埃斯特雷马杜拉、安达卢西亚和卡斯蒂利亚地区。1860~1913年间,意大利人和西班牙人构成了阿根廷、巴西南部各省和乌拉圭的欧洲移民人口的2/3。同时,这些拉美国家也吸收了西班牙的加泰罗尼亚和北部及东南部的商人、熟练工人以及意大利中部的手工业者。在阿根廷和乌拉圭沿海、巴西南部和古巴一些地区的城镇,欧洲移民有着巨大的影响。实际上,一些城市的扩展是在移民的推动下实现的,突出的有阿根廷的布宜诺斯艾利斯、罗萨里奥、圣菲和拉普拉塔,乌拉圭的蒙得维的亚,巴西的里约热内卢、圣保罗、桑托斯和阿雷格里港以及古巴的哈瓦那。在这些城市中移民一般占全城人口的30%~50%,他们控制了零售业和一些工业(如建筑业),并推动了面向地方市场的消费品生产。(注:Jorge E.Hardoy,El Urbanizacion,Inser tado en AmericaLatina en su Arquitectura,Compilada por Roberto Segre,SigloXXI editories,Mexico,1983,pp55.)
到20世纪初,拉美城市化已取得显著的进展,但这主要体现在各主要城市人口大量增长上。1900年,布宜诺斯艾利斯成为拉美人口最多的城市,估计有86.7万人,其次为里约热内卢,61.9万人,墨西哥城,54.1万人,蒙得维的亚,30.9万人,圣地亚哥,28.7万人。此外,还有一些重要城市圣保罗(23.9万人)、哈瓦那(23.6万人)、萨尔瓦多(20.8万人)、利马(13万人)、累西腓(11.3万人),上述10大城市的全部人口占拉美总人口的6%。(注:Jorge E.Hardoy,El Urbanizacion,Inser tado en America Latina en su Arquitectura,Compilada porRoberto Segre,Siglo XXI editories,Mexico,1983,pp57.)
通过以上比较分析,我们不难发现,19世纪美国和拉美的城市化的动力和进程明显不同:在美国,内部发达的市场经济既是城市发展的动力,又是发展的准则;同时,城市化与工业化同步发展,这就促使国家从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转型。而在拉美,外部因素,特别是英国资本和技术,推动传统城市发生规模和形貌上的变化,刺激人口集中到主要城市。因此,这只是量的变化,带动不了整个社会的转型。
三 美国和拉美城市化的不同经济职能
如前所述,19世纪美国的城市化与工业化同步发展,其东北部城市是工业革命的摇篮,中西部新兴城市成为新的经济生长点,带动周围地区的资源开发和利用。与此相比较,同一时期拉美的城市则是在外部因素刺激下,扩展其传统的经济职能:商业、官僚机构和初级工业活动的中心。
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美国东北部的新英格兰地区率先成为美国工业革命的摇篮,这应归因于大西洋沿岸集中了一批重要的城市,如:波士顿、费城、纽约、巴尔的摩等。它们原先或是内外贸易中心,或是政治文化核心。这些城市为工业革命的启动准备了必要条件。
首先,它们吸引了各种人才,为工厂制的创立提供了丰富的管理和技术人才。正如美国历史学家所指出的,“自从1812年战争以来,新英格兰和中部大西洋沿岸各州那些日趋繁荣的城市,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这里居住着美国工业革命的先锋——那些献身于促进企业以及利用科学技术来提高生产率和利润、减轻劳动负担、使人类生活更加舒适等目的的人们。他们的努力逐渐使那些在殖民时期几乎普及各处的家庭制造业变成了过时的体制。(注:〔美〕J.布卢姆等人:《美国的历程》,上册,第340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他们所创立的工厂制,就是在规模和复杂程度日益增长的工厂里集中利用机器生产大批产品。这样,以机械化和专业化为基本特征的工业革命首先兴起于东北部的主要城市,并由此扩展到全地区乃至全国。
其次,东北部城市为工业化准备了基本设施和市场。19世纪初那里的城市已设立了银行和大规模销售工业产品的商业设施。除此之外,城市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市场,沿海发达的交通运输扩展了地区性的市场,而陆地上的大车道则开辟了内地市场。总之,东北部的城市为工业革命的启动和发展提供了一切必要的条件。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到1815年以后,在东北部的城市中制造业超过了商业,成为最重要的经济企业。例如,匹兹堡已成为一座重要的城市,它不仅拥有玻璃厂、纺织厂和机械车间,而且成为轧钢中心。
东北部的城市孕育了工业革命,而工业化又推动了城市化的发展。“因为工业和运输的革命,这个国家逐渐失去它的乡村特色。1790年只有3%的人口住在这些地方,这样的城市社区网1790年为6个,1860年增加到141个。”(注:〔美〕纳尔逊·曼弗雷德·布莱克:《美国社会生活与思想史》,上册,第297~298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1790年至1860年间,东北部的一些重要城市人口明显增长。纽约的人口从3.3万人增至9.6万人,费城从4.2万人增至9.1万人,巴尔的摩在1810年就发展为美国第三大城市,其人口为3.5万人,而波士顿有3.3万人。(注:〔美〕纳尔逊·曼弗雷德·布莱克:《美国社会生活与思想史》,上册,第297~298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
到19世纪中后期,伴随着强劲的西进运动,中西部的城市化与工业化也快速发展。向西进军的移民不仅将大平原地区和密西西比河流域开发为重要的谷物产地,而且还将资金和技术带到西部,开矿建厂,从而推动一批工业城市兴起。到1860年,辛辛那提已发展为全国第六大城市,人口达到16.1万。此外,圣路易斯的人口也达到16万,芝加哥有10.9万,布法罗为8.1万。(注:〔美〕纳尔逊·曼弗雷德·布莱克:《美国社会生活与思想史》,上册,第297~298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
在全美经济高速发展的背景下,19世纪后期西部的工业城市异军突起。这些城市都在短期内发展成为以机器工业为基础的工业城市。例如,芝加哥发展为拥有多样化工业的城市,包括肉类加工、家具制造、钢铁冶炼、机车制造等,到20世纪初,在全国10大城市中有4座位于中西部。芝加哥已成为全国第二大城市。
由此看来,在19世纪美国城市化进程中,无论是东北部殖民地时代建成的城市,还是中西部新兴的城市,基本上都与工业化进程同步发展。特别是西部一些城市从一开始就建立在工业经济的基础上,它们起点高、发展快,因此这些城市很快就成为新的经济生长点。它们不仅是工业生产中心,而且也带动了周围地区的农牧业开发。到19世纪末,当西部工矿业城市对农产品的需求日益增长时,从落基山到密西西比河之间的辽阔地区就被拓殖为小麦和玉米产区。
与19世纪美国的城市化和工业化同步发展不同,同一时期的拉美城市化却是先于工业化,因为那里城市的经济职能只是传统城市特点的延伸。关于拉美城市化特点的研究,阿根廷学者提出以下见解:“在拉丁美洲,城市化先于工业化,而对其分析不能脱离全地区每个国家发展战略的分析。”(注:Jorge E.Hardoy,El Urbanizacion,Inser tadoen America Latina en su Arquitectura,Compilada por RobertoSegre,Siglo XXI editories,Mexico,1983,pp58.)显然,这一见解是合理的。因此,我们应以近现代拉美发展的宏观格局为背景来分析研究该地区的城市化特点。
事实上,拉美国家独立后不可能轻而易举地摒弃已存在几个世纪的殖民地时代的社会经济遗产,不可能轻而易举地弥补落后于现代化、初级技术与先进技术之间的裂隙。由于所述的现实,独立后拉美国家不得不维持殖民地时代的初级产品出口型的经济模式。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拉美城市化只是一种没有工业化的传统城市的扩展,主要表现为人口的增长和城市规模的扩大。至于城市是发展还是停滞,“主要取决于这些城市及它们所在的地区纳入世界经济一体化的程度,而世界经济受到欧洲和北美工业化国家的控制,人口的增长和伴之而来的城市发展是在由于日益扩大的农矿产品出口而带来的经济繁荣中出现的。城市发展的不足则表明这些城市孤立于世界贸易之外或表明对所生产的某一原料的价值或竞争优势的丧失”。(注:〔英〕莱斯利·贝瑟尔主编:《剑桥拉丁美洲史》,第4卷,第246页,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1997。)
在上述的宏观经济背景下,拉美城市仍然承担其传统的职能:商业、官僚机构和初级工业活动的中心。按照詹姆斯·R.斯科比的研究,19世纪拉美的城市可分为四大类。(注:〔英〕莱斯利·贝瑟尔主编:《剑桥拉丁美洲史》,第4卷,第247~255页,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1997。)第一类为商业一官僚型城市。包括各国的首都、省府或州府。它们大部分曾是西班牙或葡萄牙各级殖民政权的所在地,独立后成为新生国家的首都,继续控制所在地区的商业和财源,并行使政府职能。一些国家的首都都集中了相当多的人口,并且其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在不断增长,如1870~1930年间,布宜诺斯艾利斯从10.8%增至18.3%,蒙得维的亚从25%提高到33%。(注:〔英〕莱斯利·贝瑟尔主编:《剑桥拉丁美洲史》,第4卷,第248页,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1997。)
这类城市主要依靠初级产品出口来促进自身的发展。其中布宜诺斯艾利斯最为典型。它通过港口控制全国不断增加的农牧业产品冻肉、羊毛、皮革和小麦的出口,垄断外国消费品的进口,借此得到空前的发展。其繁荣又吸引了大量欧洲移民和外国资本,这就为商业和交通运输等基础设施以及城市的现代化提供了必要资金。这样,经济上的优势又加强了布宜诺斯艾利斯作为国家首都的地位,同时更增强了官僚统治职能的重要性。
第二类为商业—工业—官僚型城市。在拉美这类城市并不多,因为工业职能作为拉美城市发展中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的情况是少见的。这类城市中圣保罗是典型一例,它的迅速发展主要归因于咖啡的生产和出口。圣保罗作为州政府所在地,拥有良好的商业基础设施,不仅为咖啡产品出口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而且又借助出口带动了工业发展。一些咖啡生产者将其部分利润投入到本地的纺织和食品加工业以及建筑、瓷器、玻璃制品、木材加工和初级化学工业部门,这就使得圣保罗转变为商业—工业—官僚型城市,同时又推动人口向该城集中,1870年圣保罗只有3万人,到1930年达到100万人。
在拉美,类似圣保罗城市发展模式的还有哥伦比亚的麦德林和墨西哥的蒙特雷。它们都具有重要的工业职能。它们的发展经历表明,在初级产品出口型经济条件下只要充分发挥自身的力量,工业可以成为城市化进程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第三类为商业—矿业型城市。它们主要分布在智利北部的硝矿区、委内瑞拉和墨西哥的石油产地,以及秘鲁、玻利维亚、墨西哥和智利中部的铜、锡、银和金矿的高原地区。还有亚马孙丛林区的采胶站和村庄。矿产的开采、提炼和初步加工吸引了劳动力,而这些劳动力反过来又成为城市劳务和商品的消费者。但是,这些城市的兴衰都取决于世界市场对其矿产品的需求状况。
第四类是商业型城市。在拉美城市中,这类城市占大多数,商业活动是其惟一的重要职能。有些城市是农业区一些重要产品的集散地,所述产品包括巴西和哥伦比亚的咖啡,秘鲁北部沿海地区的蔗糖,墨西哥北部、委内瑞拉内地、巴西南部、阿根廷中部的牛群,乌拉圭、阿根廷南部的羊群,以及智利中部和阿根廷潘帕斯草原地区的小麦。在有关地区,一些交通运输线路的交叉点有利于较大城镇的发展,但是其繁荣最终取决于大城市所控制的城市网络的运转,有时也有赖于国外市场的需求。
总之,拉美各类城市的繁荣和发展,在不同程度上都有赖于国外市场,特别是对于矿业中心和小型商业城镇来说,世界市场价格的涨跌都会直接影响它们的兴衰。即使是较大的商业城市和许多商业—官僚型城市,它们的增长也取决于国际市场对本地产品的需求。因此,拉美城市的地位都较脆弱,易受外部因素的冲击。
通过以上的分析比较,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近代拉美与美国城市化发展模式明显不同:拉美城市是前工业经济的产物,主要继承中世纪末期伊比利亚传统的城市特点,承担了商业和政治中心的职能;而美国城市既是工业革命的摇篮,又是发达的市场经济的产儿,在19世纪美国社会经济高速发展的进程中它们是重要的新的经济生长点,这种城市化有能力推动美国从农村社会转变为城市社会,从农业经济转变为工业经济。
标签:西班牙美洲殖民地论文; 拉美国家论文; 西班牙经济论文; 英国殖民地论文; 经济论文; 美国铁路论文; 殖民地历史论文; 美洲文明论文; 欧洲城市论文; 城镇人口论文; 经济学论文; 商业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