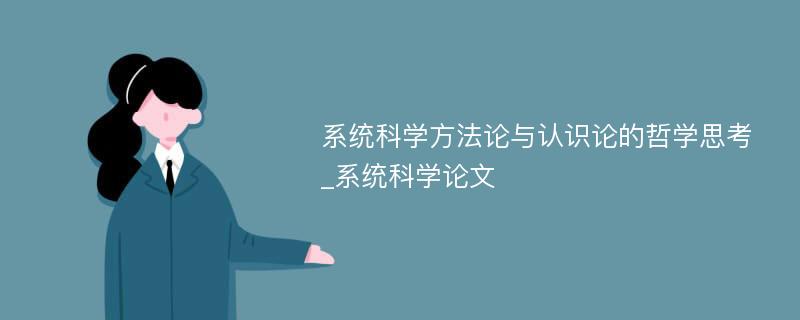
系统科学中的方法论与认识论的哲学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方法论论文,认识论论文,哲学论文,科学论文,系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117(2000)04-0025-06
0.引言
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汇流,科学与技术、各门学科之间的相互渗透密切相关,导致了以系统综合为标志的学科大发展时代的来临。为此,有必要对系统科学体系中的种种问题进行探讨。
就客观世界来说,系统是“无时不有,无处不在”的。例如:小至一个细胞可以视为一个系统。大至整个宇宙世界也可以视为一个系统。一个人,一个单位,一个国家都可以视为一个一个的系统。这里所说的系统,其具体表现形式还不是系统的科学概念。所谓系统的科学概念是指:系统是由若干互相联系、互相作用的要素所组成的具有特定功能的有机整体。用“一般系统论”的创始人贝塔朗菲(L.V.Betalungphi)的话说,系统应该是“相互作用诸要素的整体”。由此可见,系统的整体性便是系统科学的中心,系统科学的主要任务是以系统为研究对象,从整体出发来研究系统整体和组成系统整体的各要素之间的相互联系,从本质上说明其形式、结构、功能、行为和动态,以把握系统整体,达到稳定、优化的目的。
无论从事科学研究,还是从事其它各种实践,方法都是特别重要的。众所周知,系统科学是一种重要的方法论,它具有与其它科学认识类型和形式不同的特殊属性,它抛弃了片面的、局部的分析,也扬弃了线性因果关系的研究方法的弊端,而把主要重点放在分析对象的综合属性上,放在揭示其多种多样的联系与结构上。因而,系统科学为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提供了新思路、新方法、新途径,沟通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联系,它使人们摆脱了传统方法的束缚,摒弃了那种把本来是运动着、活的有机整体的动态问题,看成是静止的、孤立的、形而上学的方法论观点,如实地把研究对象视为完整的有机体和复杂的综合巨系统,找到了解决具有行为目的的控制系统、通讯系统以及复杂巨系统的新方法,从而成功地把定量分析的方法引入迄今仍盛行的只进行定性考察的学科中,使科学研究的方法产生了质的飞跃。
现在系统科学的基本概念、理论和方法已成为很多现代科学的基础。各个学科,包括自然科学、社会科学都在讲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并希望系统科学能够对解决复杂系统、巨系统中的问题提供指导性理论和方法。
在中国掀起的关于控制论、信息论、系统论这“三论”的热潮,就说明了上述研究方法已经引起我国学者们的广泛关注。事实上,“三论”的核心是一个系统问题,它只能说是统一的系统方法的几个不同侧面。由于系统论侧重于研究结构方面的问题,而结构将会产生功能,从而产生控制问题。因此,控制论可以被看作是系统论的分支,它研究系统的功能方面。由于控制必然涉及到信息的搜集与传递,控制论又与信息论有着密切的关系。
1.科学的整体认识方法论
系统科学的理论与技术成果,正给世界科学技术带来巨大的变化,它以不同于传统方法的独特姿态,冲击着人类旧有的思维方式。系统科学方法实质上是一种整体认识方法。它强调认识事物的整体性应以事物客观的相互作用关系为基础。从而掌握事物的运动变化规律,进而认识事物的本质。但该认识方法与以还原论为基础的分析认识方法是相互对立的。
整体认识论方法的思想,早在中西哲学史上很早就有了萌芽,然而,它到20世纪初才正式跨入科学的宝殿。那么,我们要问:是什么内部机制限制了它的发展?在19世纪自然科学迅速发展时期,分析认识方法在科研中大显身手,整体认识方法论却被冷落,原因何在?要回答上述问题,我们应先从系统科学理论本身来考虑。
1.1系统科学理论与系统方法
控制论、系统论、信息论是当今世界上新兴的三大学科,它们之间具有不可分割的关系,因其若干基本概念、基本思想、基本方法都是类同的,从而形成为系统范畴研究的一组科学技术学科。
当前,“三论”正在走向趋同,形成更高层次的系统科学。它们的研究对象是一切具有系统性质的整体事物、过程、问题和技术。它揭示一般系统的性质、规律和特征,研究这些理论在各具体学科中的普遍适合性意义和科学技术方法论上的同一性原则,并在最高层次上为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进行概括和总结。
由上述可知,系统科学是一般系统范畴上的科学技术体系。依钱学森教授的观点,它应包括工程技术、技术科学、基础科学和哲学四个层次上的所有以系统方法为方法论指导、以系统对象为研究目的的系统科学体系[1](P57)
系统科学方法也称为系统方法,它普遍适用于自然科学、技术科学和社会科学。所以,它是属于如同数学方法、逻辑方法等那种具有跨学科适用性的一般科学方法。
原苏联和我国许多学者认为,将系统科学哲学层次上的系统方法论高度概括总结,科学地充实发展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形成最高层次上的系统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应该是今后的系统理论和系统哲学的研究方向。从现代科学的发展和研究看,科学哲学意义上的系统化观点在现代科学体系的发展中,正在不断得到充实和完善,其主要思想可以表述如下:
(1)所谓系统是指以相互作用关系联系在一起的若干要素所组成的功能性整体。尽管国内外对“系统”概念有各种描述,但都离不开“整体性”、“功能性”、“相互作用”关系和“联系”这样一些基本概念,它们是系统概念的主要内涵。刘永清教授[2](《序言》P1)早在1959年研究长江三峡升船机的电力拖动系统时,在解决非线性控制系统中提出了大型动力系统的“李雅普诺夫(Liapunov)函数分解法”、“分解等价法”,从而使中国学者在1959~1965年首次在国际上开辟了大型动力系统稳定性这一领域的研究工作。(注:刘永清教授在1959年提出的大系统的“李雅普诺夫函数分解法”、“分解等价法”不但在自动控制、计算机、化工、电力大系统中,理论联系实际地发展了这一学科,而且在国际上是领先的开创性工作,呗笠(Bailey)在1966年才提出此问题;瑟姆普森(Thompson)在1970年也提出标量和的李雅普诺夫函数法。)他提出的复合大系统就是由若干个相互关联的子系统所组成,它具有规模庞大、结构复杂、功能综合、因素众多的特点。显然大系统的要领也具有上面所述的一些基本概念的特点。
(2)所谓系统方法,就是按照事物本身的系统性,把对象放在系统的形式中加以科学考察的一种方法。也就是说,它的认识方法是从系统科学的观点出发,综合地、精确地考察对象,着重整体与部分(要素),部分与部分之间,以及整体与外部环境之间的相互制约关系。其显著特点是它的整体性、综合性和最优化性。[1](P76);[3](P118)如变结构控制理论就是一种控制系统的综合方法,此法的优点是变结构控制(VSC)易于实现,且其滑动模态对加给系统的干扰和系统的摄动具有完全的自适应性,此法对任何非线性系统都适用。[4](PⅣ)带有滞后变的变结构控制是针对滑动运动中由于切换装置有惯性和时延(滞后)而提出的。状态变量滑动时,控制量以有限的频率在切换曲面(切换流形)附近来回切换及其滞后影响而产生抖动现象,这就需要研究滞后变结构控制系统的综合。这一新兴学科是近七八年内才提出来的。[5](P6);[6];[7]
(3)系统的构成,一般认为具有层次性,即每一系统是由若干个要素所组成,而每一系统又是更高层次系统的要素,这实际上指系统构成的纵向层次性,即互相作用的分量(子系统)的不均匀结构。[2](P152)系统内的某些要素同时又为其它系统的成分。从而使大系统的构成具有横向层次性。系统结构是由要素之间在时间和空间方面的有机联系,它是由相互作用方式、顺序而形成的。系统的结构具有稳定性、可变性(动态性)、开放性和封闭性的特征。
(4)系统的性质,在于它的整体性(如整体稳定性),这体现在它的功能、行为和结构等几个主要方面。系统的性质并不是它构成要素性质的简单总和,而是系统机制的特性。我们认为,系统机制是在系统结构基础上的功能联系机制和行为规定,因而,它也决定了系统与环境的特定关系或相互作用关系。所以,系统要素中每一项要素的变化或要素间相互关系的改变,都可能造成系统性质的改变,甚至出现另一种系统的新性质。
“系统的外部环境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过程的秩序和能力,称为系统的功能。”换句话说,系统的功能具体表现为系统对物质、能量、信息的转换能力和对环境的作用方式,即它在不同环境发生相互作用时表现出来的规定性。系统功能反应表现了系统的行为特征。按照N.维纳等人的观点,“行为就是一个实体相对于它的环境做出的任何变化”。[8](P410)换句话说,系统行为就是系统功能的外在表现。因此,系统结构是系统机制的基础,系统机制决定了系统功能的特征,从而也决定了系统的行为方式。
系统内部变化和系统对外界相互作用过程中发生联系的媒介叫信息。广义的信息就是系统机制中的相互作用方式被转化为信息联系的方式。因此,系统机制便成为信息联系机制。此信息概念包括了信息质的各种内容和形式(信息的、统计的、力学的、电学的、观念的等等)它是“系统确定程度”(即特殊程度、组织程度和有序程度)的标记。[3](P124)
所谓信息方法是指运用信息的观点,把系统看作是借助于信息的获取、传送、加工、处理而实现其目的性运动的一种研究方法”。用信息方法进行系统研究,便是广义信息论科学,即现代信息论。
现代控制论的基本理论是将“目的性”赋予系统机制的行为目标,以反馈控制系统实现系统行为和目的性机制。它的主要技术思想和研究方法是综合运用类比法、功能模拟法、信息方法和反馈控制原理。系统方法论同样是控制论研究的基本指导思想和方法论原则。
综上所述,系统概念、系统方法论是系统科学理论上升到哲学层次上的高度概括和抽象。系统论是关于一般系统的系统科学;信息论、控制论分别是关于信息系统、控制系统范畴上的系统科学。总之,“三论”在系统科学体系中都有自己所适用的特殊领域,其中,控制论与信息论又包含在一般系统论之中,所以“三论”也可以说成是一论,即系统论,它是系统科学体系中的一组联系紧密的学科。
系统论、控制论和信息论之间在基本思想和方法上的一致性和紧密关系,我们可从它们的产生历史和内容结构上直接看出。
控制论是由美国数学家N.维纳(N.Vena)创立的一门“关于在动物和机器中控制和通讯的科学”。[9](P3)维纳从1919年开始研究勒贝格(Lebesgue)积分时,就开始萌发了控制论思想。他在研究大量数学、物理问题的过程中,总结了自牛顿(Newton)以来的科学思想和科学方法论的发展趋势,发现需要一种全新的思想方法来解决实践中大量有关自控系统的问题,而该系统的特点又是要根据周围环境的某些变化来决定和调整自己的运动。[1](P46-47)二次大战期间,他参加了一系列重要的军工通讯机械系统的控制研究(如防空自控火炮系统、通讯网络系统、无人看管的变电站系统等)。为进行随机过程的预测,他提出了著名的“滤波理论”,这对他创立控制理论具有决定性意义。1948年,他与罗森勃品特·毕格罗(Lousenbolute Bigror)合作,在《美国科学哲学》上发表了控制论的第一篇论文《行为、目的和目的论》。维纳在他的控制论中,以动物和机器之间在某些行为反应上的类同为基础进行类比,把生物学、数学、机械工程等学科综合起来,把自控机器系统中的反馈要领引入动物自控行为,说明动物生理机能的自我控制;同时又把动物的“目的性行为”赋予机器,作为机器系统的自控目标,即将“二者之中的某些控制加以类比,从而抓住一切通讯和控制系统所共有的特点进行概括。”[9](P3)
维纳的控制论中的两个基本要领是控制系统的信息和反馈。“信息就是我们对外界交换来的东西。”[10](P6)而“反馈就是一种把系统的过去演绎再插进它里面去以控制这个系统的方法,即一种能用过去的演绎来调节未来行为的性能。”[10](P22)这样,控制系统行为和目的性机制(即模型跟踪控制问题)就可以建立在系统对外界环境的反馈信息基础上。显然,维纳等人的“目的”与“目的性行为”的要领是按反馈原理来定义的。
控制论专家W·罗什·艾仁比(W.Lowsi Asibi)研究了动态系统中稳定性与变化规律的控制过程。他的系统平衡态与非平衡态之间的关系理论,在控制意义上得到了很好的阐述。他创造性地应用和发展了产生于控制系统研究中的许多特殊研究方法,如功能模拟法、类比法等,并对系统理论作出了巨大贡献。
客观事物的运动规律是复杂的和多样的,一般地说,由于动力系统中的变量的测量、设备的物理特性、物质与信号的传递等因素的存在,系统中总是不可避免地存在滞后现象。亦即事物的发展趋势不但依赖于当前的状态,而且还依赖于事物过去的历史[11](P2),这就出现了带有时滞的动力系统问题。如人口发展动力系统就是时滞动力系统。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出现了越来越多的维数较高(即规模庞大)、结构复杂、功能综合、因素众多的大型动力系统。[12](P259)1959年,秦元勋教授研究飞机自动驾驶仪的设计问题时,提出了有六个自由度的运动稳定性纵横向各有三个自由度的子系统的运动稳定性问题。这种从物理分解原则上升到数学分解原则的做法,是国内外首次提出的大型动力系统的稳定性分解概念。伯黎(Baily)在1966年提出了类似的稳定性分解概念。秦教授首先使用了比较原理和向量李雅普诺夫函数。此后,刘永清、高存臣创造性地发展了稳定性分解法,在国内外首次提出了滞后大系统稳定性的“李雅普诺夫函数分解等价法”、“频率域分解等价法”,并成功地应用到若干滞后大型控制系统与滞后复合变结构控制系统中,创造性地丰富和发展了关系现代控制系统(包括大型控制系统、变结构控制系统)研究的许多崭新的研究方法。如:积分补偿器法;边界层法;谱可控法等。[13];[5]从而为控制理论作出了重大贡献。
为解决通讯应用中的技术问题,美国数学家C.申农(C.Shanoo)创立了“信息论”。[5]继申农之后,物理学家L.布里源(L.Blloeyur)建立了“信息熵”的概念。国家科委主任宋健称“这是伟大的创造”。布里源把信息与系统秩序联系起来,得到了“信息负熵原理”。即系统对信息的输入将导致系统秩序与结构变化的增加,所以信息具有对系统的组织能力。总之,熵是从有序到无序,是从增熵方向去看不确定性,而负熵是从无序走向有序,是从减熵方向去看不确定性的消失。知道了系统的无序性,同时又知道了系统的有序性,这正是从对立统一的观点出发,辩证综合看待问题的具体表现。[12](P321-326)
显然,独立产生的控制论与信息论,在它们的发展中,已经广泛应用了系统论的思想和方法,它们的许多思想和原理又直接促进了“一般系统论”学科的发展。最早在普通意义上提出“一般系统论”的是奥地利生物学家L.贝塔朗菲。他从生命整体出发,以整体认识论方法把生命与环境作为一个大系统来研究,认为生命是一个开放的体系,能同环境进行物质、能量、信息交换,是向增加有序方向发展的。他把生命现象的有序性与目的性同系统的稳定性联系起来,阐述了系统发展的辩证观。自L.贝塔朗菲的“一般系统论”建立以后,在一切对象性的一般系统论范畴上,许多学者采取不同的方法,从不同侧面对一般系统的性质进行了研究,建立了不同形式的一般系统论。如M.麦萨洛维奇(M.Mearovichi)的“数学一般系统论”;A.N.乌约莫夫(A.N.Wooyormenve)的“参考模型一般系统论”[1](P35);W.N.萨多夫斯基(W.N.Sadorfsikii)的一般方法论范畴上建立的“一般系统论”的“元理论”等。这些研究以目前正在深入研究的成果,同时形成了今天较为完整的现代系统理论。
综上所述,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三者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它们在内容上是交融的,在基本思想、基本方法与基本概念上是类同的,在学术思想上是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这反映了现代科学发展的时代性与综合性特征。同时,也使我们清楚地认识到,正是由“三论”在“系统”要领与“系统方法”上的完全一致,才使这三门学科成为新方法论的一组现代科学。
1.2在操作意义上看系统整体思想的发展
科学体系的逻辑结构与数理逻辑一样,其主体内容、研究方向以及层次是由立论范畴和操作水平决定的。同一立论范畴中的不同操作水平,或同一操作水平上的不同立论范畴内,在一般情况下并不具备可比性。因此,对于某些互相矛盾的结论不宜判别谁是谁非。关于它们各自体系内的科学结论,相互比较时应理解为是对同一问题从不同角度、不同层次、不同操作标准上的认识结果。我们要认识与把握世界就要把相对真理向高层次、多角度、综合化的方向推进和发展,以求人类认识的深刻化、整体化。
爱因斯坦(A.Einstein)在光速上(即以光信号测度的操作标准)研究时、空和质量的关系,在1905年与1916年分别提出了狭义相对论与广义相对论。[12](P134)从而从古典物理学中发展出理论物理学,使物理世界的面貌在相对论范畴上焕然一新。
人类认识世界、观察事物的认识方法与思想方法也与操作工具有关,即能够使用的操作标准的水平和类型影响着人类研究事物的思想认识方法。人们考察事物的认识方法一般有两种:一种是分析认识论方法;一种是整体认识论方法。所谓分析认识论方法(或纵向思维方法)是把认识对象的整体加以分解,再进行单因素(或几个因素)的考察,层层剖析,逐一突破,最终总结归纳,从而实现从个性到共性、特殊到一般的认识目的。实践证明,分析综合的纵向思维方法是一种非常有效的认识事物的方法,自然科学的发展事实及其丰硕成果就是最好的说明。然而,世界的复杂性仅靠分析认识方法是不够的,因为世界中的事物是互相联系、不断运动发展的有机统一整体。而整体所具有的一些特征并不存在于分离的部分之中,如果把整体中各组成分分割开来,有些整体属性便会消失,从而就把握不住整体事物的真相。因此,认识事物必须从整体上去把握,这样的认识观点在哲学上通常称为整体认识论(或称横向思维方法)。目前,我们正在研究的带有时滞的中立型变结构控制系统(或控制大系统)的镇定与综合(或分散变结构控制器的设计)。[7];[13]正是应用了现代整体认识论的思想方法。
1.3科学的整体认识方法论
从整体思想的阐述中,我们已经看到,所谓系统方法就是指系统科学(包括“三论”)基础上概括出来的一般科学方法。它的基础是系统科学体系中各学科已经取得的理论成果与技术实践成就,所以它具有客观实在性基础。系统科学各学科范畴分属于技术科学、技术基础科学、基础理论科学和科学哲学四个层次。最后一个层次介于纯科学和纯哲学之间,是系统科学中的哲学问题,其核心是对系统方法论的哲学研究。所以哲学性很强的系统方法及其它的方法论,不同于其它的一般科学方法(如数学方法、逻辑方法等),特别是系统方法中的整体认识观和辩证法思想,更使它带有普遍适应性的哲学意义。
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哲学,既是科学的世界观,又是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科学认识方法论,这已被实践所证实。但列宁以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对整体认识思想、系统观念等只作了一般原则性描述。现在对系统方法的研究表明,系统方法是符合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理和总体精神的。由于它是对自然科学最新成就的方法论总结,所以就更具有时代的适应性,更易于被人接受,更有利于辩证唯物主义的普及。因此,科学地捍卫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时代要求和将现代科学方法上升到哲学高度并加以认识提高的迫切需要,都向我们明确提出了这样一个重要任务:吸取现代系统方法论思想,合理地对待各种整体认识论思想的精华,在辩证唯物主义思想指导下,进行哲学上的高度提炼和总结,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就是说,将系统科学方法论及其他整体认识思想纳入马克思主义哲学范畴进行升华和提高,使之成为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科学的整体认识方法论。
2.系统科学方法的哲学思考
系统科学理论成果带来的方法论冲击,首先表现在对系统科学方法的哲学反思上。这些思考的新成果能否在已有的哲学范畴中得到理解?就是说它与传统的哲学概念是否会互相抵触?若有抵触是新思想有问题?还是传统哲学范畴需要新思考?我们从科学与哲学的多个范畴出发,初步探讨系统科学方法的哲学意义和哲学性质后,认为系统科学方法的哲学价值在大部分传统哲学范畴中不会发生冲突,没有根本性的矛盾。
由于篇幅的限制,关于系统对象认识的主观性与客观性、系统认识中的整体界域、系统认识的检验标准、系统整体的形式属性、功能属性、功能行为与目的性机制等将在另文论述,兹不多述。
收稿日期:2000-05-06
标签:系统科学论文; 系统论论文; 控制论论文; 信息论论文; 认识论论文; 哲学研究论文; 科学论文; 理论体系论文; 思考方法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