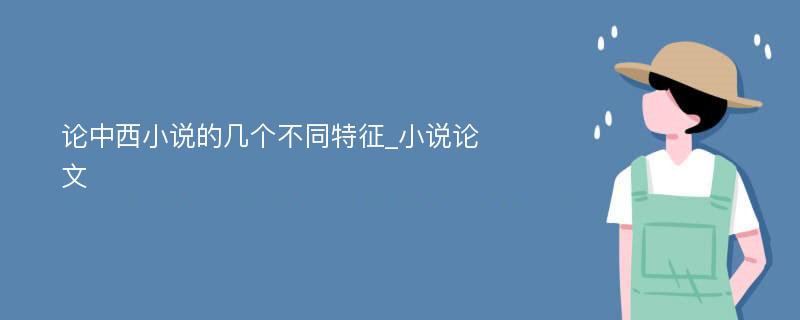
再论中西长篇小说若干不同特色,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长篇小说论文,中西论文,特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93年也是在这个刊物上,笔者曾就中西长篇小说的比较,发表了几点看法,那是属于艺术形式方面的。这篇也谈比较,但侧重于思想内容。由于中西长篇小说数量极多,类似这样的比较,必然挂一漏万,故仅就其中若干方面着眼,能否抓出一点规律性的东西来,还有待于读者的教正。
骑士传奇与武侠小说
西方早期小说出现过骑士传奇的系统,中国则有武侠小说,《三国演义》、《水浒传》之类便是。西方的骑士传奇同中国的武侠小说在内容上有一定的相似性。一是忠君,都宣扬忠君爱主的正统观念;二是护教,中国的武侠小说虽不如西方骑士传奇基督教色彩的浓厚,但道教神仙也是书中英雄的保护神。孔明、吴用都有“仙气”。如同上帝保护骑士,九天玄女娘娘也赠宋江三卷天书。西方的骑士为基督教而战,《三国》、《水浒》的英雄豪杰虽没有为道教而战,但也是道教的忠诚信徒。三是行侠,西方的骑士讲究“侠义”精神,后起的模仿者堂·吉诃德更是把这种精神发挥得淋漓尽致。西方的骑士与中国的武侠都很有点江湖义气,园桌武士与亚瑟王大多生死与共,刘关张有“桃园三结义”,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只求同年同月同日死”。四是虚构,西方中古英雄史诗还保存不少史实,发展到骑士传奇,虚构情节越来越多。《三国演义》据陈寿《三国志》及裴松之的注释写成,虚构部分仅占30%。后起的《水浒传》则有大量虚构,北宋宋江起义的史实只不过是依稀的影子。五是源远流长,西方的骑士传奇可以追溯到中古英雄史诗,甚至更早。中国的游侠传统更可以上溯到《史记·游侠列传》。
然而西方的骑士传奇与中国的武侠小说也有重大的区别。西方的“骑士”是由国王、贵族、大主教封定的,中国的“侠客”只是民间的称呼,多来自下层民众,即太史公之所谓“布衣之侠”。还有一个重要的区别是对待女性的态度大不相同,这点不可不加注意。西方的骑士传奇歌颂女性。骑士以忠于女性、崇拜女性为自己的天职,这当然是指自己的心上人。后起的模仿者堂·吉诃德对腌肉村姑的神往与崇拜,可谓是骑士精神登峰造极的表现。中国武侠小说的英雄几乎无一是女性的崇拜者,梁山好汉只忠于宋公明,绝不忠于什么贵妇。武松杀嫂、杨雄杀妻、宋江杀阎婆惜等,都是血淋淋的令人恐怖。西方骑士传奇歌颂“偷情”,《亚瑟王之死》及其他著名传奇都有大量这方面的描写。郎世乐一方面忠于亚瑟王,一方面又与王后桂乃芬大偷其情,悲欢离合、缠绵悱恻的渲染描写,令读者难忘。关公被曹操俘虏后,曹操故意让关公与两位嫂嫂同住一地,想搞点桃色新闻,关公则秉烛站立于两位嫂嫂门外,自夜达旦,不踏入嫂嫂房门半步,让奸诈的曹操白费心机。
中西武侠小说作家对待女性态度不同,写法也不同。中国的《三国演义》、《水浒传》,除了貂婵这个女性写得有点声色以外,其他女性人物,罕见有着重渲染者。即使是貂婵,也不过作为王允的“工具”,让董卓与吕布闹矛盾,破坏其团结,其实十分可怜。西方骑士传奇的作者每每对绝色的女性大加渲染,这在中国古典诗词中有类似现象,而罗贯中、施耐庵却不屑为之的。西方有一部著名骑士传奇《特列斯当与伊瑟》,写伊瑟的出场十分精彩。骑士英雄特列斯当与王后伊瑟有私,被马克王逐出朝廷。特列斯当念念不忘伊瑟,与好友卡埃敦在树林守候着随马克王出猎的心上人。只见国王的随从走过去了,王后的仪仗队走过去了,远远来了一位骑在骏马上的丽人,卡埃敦惊为天人,乃叹曰:“真王后也!”然而来者只是王后伊瑟的贴身婢女嘉湄。接着又过来一位骑银马的妙龄女郎,她长得比阳春白雪还白,樱唇比三月玫瑰还红,眼睛亮得如同清泉反映的星星,卡尔敦第二次认错了人,来者乃王后伊瑟的忠心伴娘白兰仙。最后,“路上猛然出现一片奇彩,仿佛枝叶间突然迸出万道霞光:金发伊瑟终于驾临。”《三国演义》写刘玄德三顾草庐,第一次入山认错了人。第二次入山再认错了人。到得草庐,第三次还是认错了人,把弟弟(诸葛均)当哥哥(诸葛亮)了,气得张飞、关羽要放把火把草庐烧了。刘备三人从孔明家中失望出来,正要上马回程,只见一老者骑驴吟诗而来,真乃仙风道骨,非比凡人。刘备便说:“此真卧龙矣!”滚鞍下马便拜,第四次认错人,来者乃孔明的岳父。直到第三次入山,才见到真卧龙。中西武侠小说都擅于铺垫,但《特列斯当与伊瑟》是为了美化女性,“千呼万唤始出来”的是伊瑟。《三国演义》是为了美化男性,“千呼万唤始出来”的是孔明。
西方的骑士传奇到了文艺复兴时期受到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致命的打击,以后便消声匿迹。近代小说起来,骑士传奇便死了。浪漫主义小说虽然又回到中古,只是回光返照。中国的武侠小说与西方不同,不是死亡,而是分化。自《水浒传》出后,又出现了《荡寇志》、《三侠五义》之类的小说,是对《水浒传》的反动。鲁迅对这种分化讲得很精辟。他说:“书中所述的侠客,大半粗豪,很象《水浒》中底人物,故其事实虽然来自《龙图公案》,而源流则仍出于《水浒》。不过,《水浒》中的人物在反抗政府,而这一类书中底人物,则帮助政府,这是作者思想的大不同处。中国“现代武侠小说”则继承了《水浒传》“反抗政府”的传统,梁斌的《红旗谱》、姚雪垠的《李自成》就是最典型的例子。
概言之,西方的骑士传奇与中国的武侠小说最早的土壤都是封建社会,忠君、护教、行侠的主题与之不可分。但西方是基督教,中国是本土的道教;西方有“骑士精神”,中国有“宋明理学”,作品的内容又并不完全相同。中国的武侠小说从源头上说是“布衣之侠”,中国农民起义规模之大,时间之长,改朝换代力量之猛烈均为世界历史之最。故举凡武侠小说的主题多与农民起义有关,在这个方面,我们的武侠小说比诸西方骑士传奇有更深广的民主传统。一部《水浒传》继承“布衣之侠”的传统,发扬了中国历代农民起义的造反精神,使后人得有写作上的榜样可依,它的悲剧意识,也给后人以多方面的启示。而西方的骑士传奇却歌颂“垂死的阶级”,当新生社会力量起来,骑士传奇便与骑士一同死亡。作为一种文学现象,何以一存一亡,一仍有生命力,一已成为昔日的陈迹?一种文学现象的兴亡盛衰,说到底还是与社会的发展及或一阶级在历史上的作用有关联。
宗教小说与伦理小说
西方多宗教小说,因基督教是西方文化的基础、精神的支柱。西方小说的正面主人公有不少是基督教徒,“原罪说”与“信仰得救”是其永恒的、普遍的主题。堂·吉诃德具有坚定的信仰,基督教义是他行侠的指南。简·爱在上帝的指引下得到爱情与幸福。狄更斯和陀斯妥耶夫斯基笔下的正面人物全是天使的化身。安娜·卡列尼娜卧轨自杀时最后一个动作是划十字。《复活》中的聂赫留杂夫因信仰而“复活”。耶稣的原型一再在西方小说中出现。显克维奇的《你往何处去》中的基督对弟子彼得说:“既然你离开了我的人民,我就要到罗马去,让他们再把我钉上十字架!”《断头台》写了耶稣与彼拉多的辩论。耶稣说:“要想让人类皈依真理,我没有第二条路可以选择,只有用自身的死换取对真理的确认。”再次响起《你往何处去》的声音。百川归大海,西方小说中美好的思想,诸如人道主义、博爱、舍己为人、献身精神、忏悔意识、自强不息等等,都可以而且必然归属于基督教思想范畴。如果将目光放大,收入《神曲》、《浮士德》、《荒原》,西方文学的宗教性更为光采夺目。
基督教文学的特点是寓言性,故西方长篇小说家最擅于用象征手法表现小说的主题。文艺复兴时期的《巨人传》是寓言,“巨人”、“德廉美修道院”、“神瓶”象征着新人、理想国、知识与智慧。17世纪的《天路历程》从头到尾都是寓言。18世纪《格列佛游记》最后部分也是寓言,是对“人类”堕落根源的探索。19世纪美国小说家霍桑的《红字》、麦尔维尔的《白鲸》、前苏联名作家艾赫玛托夫的《断头台》,书名就有寓言性。福克纳的不少小说从篇名、人名、地名都有寓言性,他的系列小说被称为“神话王国”。《去吧,摩西》、《押沙龙,押沙龙》都是《圣经》的人名。《喧哗与骚动》的四个乐章均与基督教节日相关。乔伊斯的《尤利西斯》是现代人类的寓言。英国戈尔丁的《蝇王》的“野兽”、“蝇王”象征人性恶,整部小说是对当代充满战争杀机的人类前途的探索。
中国小说多为伦理小说而非宗教小说。中国古典长篇小说以儒家思想为主体,《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的忠义观念一脉相承,“忠义”是伦理观念而非宗教观念。中国长篇小说中的正面人物依靠伦理观念去行动,去取得心理平衡。关公被曹操围困在山上,是投降还是战到底,结果抬起头来投降,因为这是“降汉不降曹”,关公就是这样取得心理平衡的。林冲夜奔梁山,是什么力量支持他造反?是“替天行道”,“天”与“好皇帝”是同义词。儒家的伦理观念强调中庸之道,中和之美。孔明明知阿斗不成器,还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宋江饮毒酒也不反皇帝。孙大圣戴上紧箍后仍虎虎生威,一路降魔斩怪,不减闹天宫当年的英雄本色。这一切,都符合儒家的伦理标准:做什么事都有个原则管住,不能过头,才合乎中庸之道。中国长篇小说中的正面人物多有克己精神,这种精神也来自伦理观念而非来自宗教观念。儒家又讲“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儒林外史》中的王冕,就是儒家又一个方面的伦理典范。只有《红楼梦》发出了与传统格格不入的声音,一首“好了歌”宣告儒家伦理观念已被佛教色空观念所打败。《红楼梦》可说是中国古典小说中唯一一部宗教性小说。因为它的主旨与出路都不在于伦理而在于宗教。
中国诗歌讲究含蓄,但中国长篇小说讲究明白,与诗歌正相反。中国古典小说家除曹雪芹外,无一人把小说写成寓言,与西方大不相同。中国古代小说家虽不入三教九流,但也是“文以载道”的信仰者,包括《金瓶梅》的作者,原意也是戒荒淫。儒家的道理可不是老庄佛学的道理,是要讲得具体明白透彻的。小说家的“文”也要具体明白透彻,这就从根本上排斥了寓言性。“五四”以后新文学的主流,其伦理意识极为明确,小说家罕有写寓言小说者。解放后一大批革命小说的伦理意识更是极其鲜明,几乎杜绝一切寓言小说。新时期小说家坚信“文以载道”者甚众,他们大都有自己的“道”,而且很爱在小说中发议论,比老前辈们有过之而无不及。80年代中期以降,出现若干寓言小说,有的有道家色彩,是一个新现象。
西方宗教性小说与中国伦理性小说孰优孰劣,不能一概而论,因为其中还有个艺术标准、审美评价的问题。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评论的,就是西方的古典及现代的小说名家、中国古典及现代的小说名家,大抵都具有坚定的信仰,宗教的也好、伦理的、政治的也好,大抵持之以恒,而且都擅于美化自己的信仰,因此,自有一种真诚的美,从而长久地打动人心。西方的狄更斯、雨果,中国的巴金就如此。西方的宗教性小说与中国的伦理性小说都是有信念的小说,有信念总比没信念好,最简单的理由是迄今为止传世的中西小说名著大抵都闪耀着理性的光辉。都有人道主义精神。
单纯性格小说与复杂性格小说
所谓“单纯性格”,就是人物善恶分明。所谓“复杂性格”,就是人物孰善孰恶难以判断。应该说,在中西长篇小说史中,无论中国的还是西方的,都同时有这两类性格的存在,这是一个基本事实。
中国古典长篇小说一贯具有正反分明的人物系统。第一部小说《三国演义》就“忠奸分明”。《水浒传》、《西游记》无不如此。西方古典长篇小说当然也有一个正反分明的人物系统。从文艺复兴到19世纪,西方小说家所塑造的正面人物,可以开列一张很长的名单。巴尔扎克在《人间喜剧》序言中郑重声明,他书中的正面人物多于反面人物。现代名著就不能区分善恶两类人物了么?《喧哗与骚动》及《百年孤独》这两部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经典之作给予了正面的回答。前者有黑人迪尔西,福克纳说:“迪尔西是我自己最喜爱的人物之一,因为她勇敢、大胆、豪爽、温存、诚实。她比我自己勇敢得多,也豪爽得多。”《百年孤独》中有乌苏娜,这位活了一百多岁的布恩蒂亚家族之母有“理性的光辉”,是这个家族的“根”。
从所周知,俄国19世纪的陀斯妥耶夫斯基极擅写复杂的性格。他宣传“人类心灵的两重性”,他笔下的人物由善到恶、由恶生善的心理变化令人吃惊、令人信服。但是,正是他的小说,始终有一个正面人物体系在,如《白痴》中的梅思金公爵(作者称他为“十全十美的人物”)、《罪与罚》中的索尼娅、《卡拉玛佐夫兄弟》中的阿廖沙。正因为有了这个正面人物体系存在,陀氏小说才具有不朽的道德力量。这似乎应是一个客观的评价。
中国古典小说在《金瓶梅》、《红楼梦》以前,人物性格比较单纯,《金瓶梅》、《红楼梦》中有些人物的性格就相对复杂一些。中国新文学的几部已有定评的小说及解放后一批写革命与战争的小说中的人物性格比较单纯,新时期长篇小说中的人物性格就相对复杂一些。西方小说从文艺复兴到浪漫主义,一般地说,人物性格都比较单纯,如党·吉诃德,内心透明如水晶。鲁滨逊、汤姆、琼斯与苏菲亚、维特与绿蒂、帕美拉等等,性格都不复杂。西方小说从批判现实主义开始,人物性格就相对复杂一些,如于连、希勒克列夫、包法利夫人、安娜·卡列尼娜等等,内心中的善恶斗争就比较激烈。
总的来说,西方长篇小说自19世纪后期始,人们性格比较复杂,可称为复杂性格的小说。而中国长篇小说从古典小说到新文学的小说,人物性格比较单纯,可称为单纯性格的小说。截至新时期文学以前,中国长篇小说少有亦好亦坏、亦善亦恶、内心分裂、多重人格的人物形象。古典小说中曹操的性格相当丰满,但并不复杂,基本特征是奸诈,在大众心目中,他是反面角色是无疑的。王熙凤与薛宝钗的性格要复杂些,王熙凤是“机关算尽太聪明”,这就是很有些城府了。薛宝钗城府更深,她与林黛玉争夺宝玉之战表面上真是做到不动声色。但越到后来,这两个女性变得越单纯,作者的笔调也越柔和了。贾宝玉与林黛玉内心充满矛盾与痛苦,但善恶分明,人格绝不分裂。要在这对痴儿女身上找“灵与肉”、“上帝与魔鬼”的斗争是徒劳的。《子夜》中的吴荪甫是悲剧形象,他要振兴民族工业而不能。赵伯韬是他的对立面,茅盾要否定的,是“买办资本家”而非“民族资本家”。
中西小说人物性格单纯与复杂的评价,仁者见仁,知者见知,不必强求统一。但是,有两个与之相关的问题倒值得探讨。
第一,中西小说人物性格虽有单纯复杂的区分,但中西小说家对笔下的人物总有一个是非爱憎的判断。综观中西长篇小说史,中西小说家所赞美的大体上都是人类自身的美德,所同情的大体上都是“悲惨世界”与“艰难时世”下的被侮辱与被损害者。中西小说中的确有一类“复杂性格”,不好用传统意义的正反面人物去区分,但其中一定有被作家所同情所怜悯的人物,也一定有被作家所鄙视唾弃的人物。小说中的人物的善恶可以转化,作家的笔调也随之变化。因此,复杂性格的是非善恶只是难以区分不是不可区分,作家的爱憎评价只是不易发现并非没有。这类小说例子很多,既适用于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也适用于乔依斯的《尤利西斯》;既适用于《金瓶梅》,也适用于铁凝的《玫瑰门》和王安忆的《米尼》。因此,“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的无善恶是非的观念,不适用于中西小说中任何一类人物,也不适用于中西小说家任何一方。因为这并不符合中西长篇小说的基本实际情况,也抹杀了中西长篇小说家的艺术良知。
第二,人物性格的复杂与单纯从审美角度上看并无高下优劣之分。“单纯”不是“简单化”而是典型化,“复杂”也绝非最高档次的典型。把善与恶、真与假、美与丑加以高度典型化,就是“单纯”。中国小说中正面人物系统的“单纯”的特色是人物毕生坚持一个信念,力求保持内心的平衡与和谐。林黛玉临死前对紫鹃说:“我的身子是干净的,你好歹叫他们送我回去!”《李自成》中的红娘子,压下杀夫之仇,对闯王尽忠到底。就是当代一批写“受难知识分子”的小说,其中的正面人物即使蒙大冤枉、陷大苦难、历大痛苦,仍以国家民族命运为重,忧国忧民的理想主义熠熠发光。
中国小说正面人物性格单纯的原因与中国哲学大有关系。儒家讲正心修身、克己复礼,老庄佛学讲无为、超然、出世,现代革命者讲“自我修养”,中国知识分子素来讲“内美”、“气节”、“慎独”,出发点虽各不相同,但“去恶从善”却一致。而且中国人民群众素有忠奸分明的审美观念,作家也有同样的审美观念,受中国哲学与民心的影响,中国作家从古到今,其理想主义比西方更多一些,禁欲主义比西方作家更多一些。中国哲学向来就有“隐恶扬善”的传统,作家总要把正面人物、被同情被怜悯的人物写得好一些、美一些,中国作家的笔更擅于选择,更擅于化复杂为单纯。
西方小说人物性格复杂的原因与基督教的“原罪说”及弗洛伊德的泛性论有关。这两种理论都把人格分裂为两个。然而,“原罪”可以因信仰而得救,这就从根本上保证了人性可向善。此乃西方小说许多正面人物的“根子”,也是人物性格从复杂到单纯的公式的思想基础。至于弗洛伊德的泛性论则宣告人心中的“魔鬼”(里比多)是永远驱除不去,无药可医的。人性复杂与人性恶遂成了同义词,比基督教义有过之而无不及。“原罪说”与弗洛伊德的理论的根本不妥之处在于不符合“人”的实质,因为“罪恶”决非人与生俱来的本质。“原罪说”与弗洛伊德的理论也不适用于文学评论的全部,因为作家有选择的权利,尽管人心有善恶斗争,但西方作家同样可以“隐恶扬善”,不写假丑恶而写真善美。西方的耶稣及圣母的原型一再地、反复地、大量地在历代小说中不断出现,就是一个强有力的例证。
我们主张描写人性的真实,特别反对与深恶痛绝把性格脸谱化,高度评价西方小说家笔下复杂性格的艺术美。但我们也绝不能忽视中国小说家尤其是古典小说家笔下单纯性格的艺术美。去恶从善是中国小说正面人物的美德,隐恶扬善(用鲁迅的话说就是“删削些黑暗,装点些欢容,使作品比较的显出若干亮色”)是中国小说家的美德,要求善恶分明是中国人民朴素的审美心理,这些并非污水,不能泼出去。倘若把人格分裂、多重人格作为最高档次的典型加以鼓吹,忽视了性格的单纯美,尤其是小说中正面人物的单纯美,就会导致另一种观念论,贬低以致否定中国以及西方小说史上大量存在的单纯性格的艺术美及正面人物不朽的道德力量。这种理论会把小说家引入歧途,陷自己以及笔下人物于黑暗罪恶的深渊,于己于读者于社会国家人类前途均不利,这应该也是一个比较的结论。
标签:小说论文; 文学论文; 长篇小说论文; 中国宗教论文; 三国演义论文; 读书论文; 寓言论文; 金瓶梅论文; 水浒传论文; 作家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