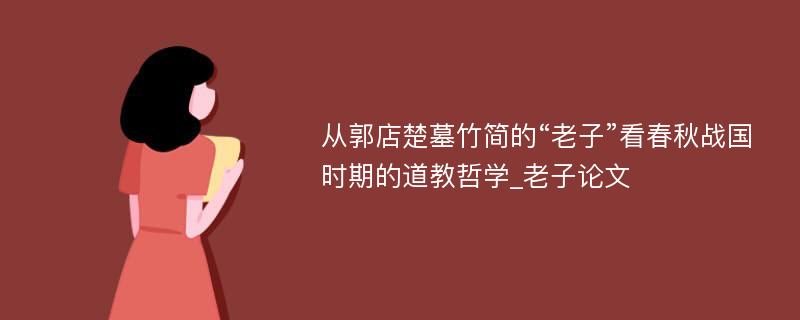
从郭店楚墓竹简本《老子》看春秋战国之际道家哲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竹简论文,春秋战国论文,道家论文,老子论文,哲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湖北荆门郭店一号战国楚墓竹简共有七百三十支(《语丛》四第27正背仅计1支,含残片27),其中《老子》共七十一简(注:据荆门市博物馆《郭店楚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98年版,第3~108页图版。)。这样,从文献上看,有了多种《老子》可供比较研究:竹简本《老子》、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帛书甲本《老子》、帛书乙本《老子》、王弼本《老子》、傅奕本《老子》、河上公本《老子》等等。郭店一号楚墓下葬年代在战国中期偏后,约在公元前300年左右。(注:参见刘彬徽《关于郭店楚简年代及相关问题的讨论》,载《简帛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51页。)比抄写时间更早些,形成这种思想和著述其书,当在春秋后期、战国初期。从时间序列上看,由目前见到的最早的传本到各种后出的传本有可能形成不同的传本系统。根据郭沂同志的研究,“竹简《老子》属于一个早已失传的传本系统,它出自春秋末期与孔子同时的老聃。帛书本和各种传世本属于另一个传本系统,它出自战国中期与秦献公同时的太史儋。”(注:郭沂:《郭店竹简与先秦学术思想》,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50页。)至少,研究简本,较之于帛书本、王本等后出本,更接近原本,更接近老聃,这是没有问题的。
“德”的各种含义
王本八十一章,《道经》在前。《韩非子》的《解老》、《喻老》,帛书甲、乙本均《德经》在前,都可以说以相当于王本的三十八章“上德不德,是以有德”开始,又以帛乙本最为显豁。竹简本《老子》原书释文分甲乙丙三大组,含十二个拼联组,不管是按李学勤先生以甲组第二、三、五拼联组为上篇,还是按郭沂先生统观三个大组,从而分成四篇三十四章,都是以第21简开头,李先生以21简为第一大组(甲组)上篇首章,郭先生以21简为第一篇第一章。故可确定竹简本以“有状混成,先天地生”开头,相当于王本二十五章“有物混成,先天地生”。荆门市博物馆编本以“绝智弃辩,民利百倍”,即以相当于王本的第十九章开头。按郭先生统观三大组而分四篇之法,王本三十八章在竹简本无说法。如果以竹简本34章计,前17章有王本三十八章以后《德经》内容者共7章,占47.2%,后17章有王本三十八章以后《德经》内容者共11章,占64.1%。还很难说孰前孰后,但可以这样说:竹简本34章去掉重复的一章(第二篇第六章与第四篇第四章内容相同,都是王本六十四章的内容)得33章,《德经》内容共17章,占一半略多。至少可以这样说,竹简本《德经》的内容和《道经》的内容是平衡的。我们认为,从全书内容平衡这一点看,竹简本《老子》已是另一传本系统的全本,而非抄节本。王本五十五章的《德经》内容在竹简本第一篇第四章:“含德之厚者,比于赤子。”虽然难以据此断定竹简本《老子》也是《德经》在前,但可认为竹简本《老子》很重视《德经》的内容。竹简本《老子》的《德经》既在前,又在后,弥漫全书,正是“另一个传本系统”的又一证明。
竹简本全书的“德”字有:
含德之厚者,比于赤子。(第一篇第四章)
善建者不拔,善保者不脱,子孙以其祭祀不辍。修之身,其德乃真;修之家,其德有余;修之乡,其德乃长;修之邦,其德乃丰;修之天下,[其德乃博。](第三篇第八章)
上德如谷,-大白如辱,广德如不足,建德如[偷,质]贞如渝,大方无隅。(第三篇第九章)
以上的“德”字,很难说就是后来的“道德观念”、“品行”、“贞操”之“德”,而是远早于“道德观念”的某种“客体实在”和“存真”的理性范畴,字面意义可释为“性状”、“品状”、“情性”、“属性”、“规则”、“规范”。第一例是个比喻句,被比对象是“含德之厚者”,比喻词是“赤子”(婴儿),下文还有“似婴儿又如何”的一系列二层比喻词——因其无求无欲,不犯众物,故众物也不犯它,连蜂蝎虫蛇也不咬他,猛禽猛兽也不吃他;不懂男女交合也会因精气至足而自然勃起。此外还有说明词——因其身心和谐而终日无忧无虑;处世和谐,认识和谐,体态和谐而做到“常、明、祥、强”。由上述一系列比喻词和说明词来求解被比对象“含德之厚者”,显然被比对象不只是,甚至不是指“德行深厚者”,而是指特有某种情状、性状,有知性、心性,甚至是合乎某种自然规律的。竹简本的“德”,源自物性、人性、人物之性,如以后来的“道德观念”、“贞操”之“德”为基准对比言之,竹简本的“德”是被老聃本体化、物化、具象化了的“德”。
第三篇第八章中的“德”应是具体指某件事、某一类事、某种做法。文中有六个“其”字,第一个“其”用作代词表领属,构成短语“其祭祀”作介词“以”的宾语,可译作“善建的人们的、善保的人们的,他们的”。这种用法上古常见。《左传·僖公二十二年》:“彼众我寡,及其未既济也,请击之。”句中“其”貌似宾语“他们”,实际上是“其未既济”作宾语,“其”处领属格。又《僖公二十八年》:“三月丙午,入曹,数之以其不用僖负羁而乘轩车者三百人也。”(注:《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版,第1813页下、1824页中。)周法高将此例作为“‘其’字所构成的子句为介词‘以’之宾语”(注:周法高:《中国古代语法:称代编》,第106页。)。甚确。帛书本、王本因不明上古“领属格‘其’可构成子句作句中宾语”这一语法现象的复杂性,仅知上古“其”很少,或没有直接作宾语的,将“以其祭祀”误解成上古极少、后代才有的“‘其’直接作宾语”而删之,都变成了“以祭祀”三字,这正好说明帛书本和王本都是从后代“其”字用法的视角来看待上古“其”字的用法的。由于“其”字作宾语很晚,一般以为至魏晋方普遍出现,从而又可推证郭店本要比帛书本早了许多。既然郭店本第一个“其”亦处领属格,这样就与后面五个“其”(明显处于领属格)完全一致。这就看出在语法逻辑上,郭店本较删除“其”的帛书本和王本要严密得多。现在回过头来说“德”字的意义。当从领属格“其”字入手解读“德”字。后面五个“其”字句可释为“身之德乃真,家之德有余,乡之德乃长(长久),邦之德乃丰(合乎祭祀之礼,丰厚),天下之德乃博(普遍,广大无边)”。五个“其”字句说明“德”的效用和价值评判应当“合乎真,使有余,保长久,合礼仪,求广大”。如果从价值论看,这里的“德”也是本体化、物化、具象化的。
第一个“其”字句可解读为“后代子孙以(继承)先辈们(指善建者、善保者)的祭祀而不停止”。前面三句讲了三件事:善于建树的人不可拔除,善于保持的人不可离弃,后代子孙继承他们的礼仪精神而不停止。从文气上看,紧接着讲后人“修之身、修之家”等,十分贯通。三件事实际上是两件事:善于建树、善于保持,因为祭祀之礼仪精神都贯彻了“善建”和“善保”,又因上古领属格“其”的意义和指示代词“这”、“那”的意义是相通的。所以,五个“其德”既可如上文释为“身之德、家之德、乡之德……”也可释为“那个德”,其=那个,德=善于建树、善于保持和继承这种精神。用“那个德”的含义代入五个“其”字句,就成了“那善于建树和保持之德就会真切、就会有余、就会长久、就会丰厚实在、就会推广开去而普遍广大”。五个“其”字句解读得怡然理顺。由此可见,第三篇第八章中的五个“德”字可具体确指为“建树,保持,不停止先祖们的祭祀,并使合乎礼仪”。还有一个诠释证据:“之”字何解?此处的“之”字由物主代词“它”转为指示代词“那”,之=那个(德)。“修之身”犹“修之于身”,犹“修那个德于身”。下同。由“之”字的用法,也可知“德”就是指上文的“善建、善保”等。特别是第五个“之”、“其”字句,可直接解释为“修那个德于国家,国家之德就会更合乎祭祀礼仪而变得丰厚实在”,由六个“其”字、五个“之”字的诠释,进而获知“德”即指上文的“善建、善保、善祭祀”,可见“德”的内容是具体的行为、做法、事件,“德”完全是发生在实际生活中的行为和事件。“德”的实际化、事件化是上文讲到的物化的“德”的必然结果,两者在逻辑上是相通的。第三篇第八章还有六个“以”字句:“[以家观]家,以乡观乡,以邦观邦,以天下观天下。吾何以知天[下哉?以此。]”这六句话当然绝对不是同义语反复,故应解释为“以一乡之德是否长久来观察一乡,以一国之德是否丰厚来观察一国,以天下之德是否宏博广大来观察天下,我用什么来了解天下,我就是用‘德’的实行情况来知道的”。“德”是观察问题的窗口、视点、方法。六个“以”字句都是以客观情形来观察客体对象。郭店本和帛书本、王本相比较,无“以身观身”一句,表明春秋老子不以“自身‘德’的实行是否真切”来观察和判断自身,即不从主体客观情形,或者说主体实存来观察主体,只以客观情形来观察客体。
第三篇第九章的三个“德”字,将“德”分成三类,并各各描摹其状况。分类和描摹的结果,使人得到“德”处于辩证状态的结论。分类有高尚之德、广大之德、刚健之德,其状况是负面的描摹和说明,五个“如”字句的内容,都是正面对象用负面之物、之情形来比喻。高尚的德如卑下的山谷,最洁白的如同染黑一样,广大的德好像不足,刚健的德显得很苟且怠惰,质地纯洁好像反倒是容易生变之物。这样,被比对象的说明完全具象化了。被比对象在理性上是辩证的,却是非常具体的、形象的,几乎是物化形态的。
综上所述,从郭店老子“德”的物化、事件化,“德”作为价值评判着眼于客观情形和客体来看,我们不能不说春秋战国之际的老子是唯物的。从“德”的分类描摹和作比说明看,“德”本身也是处于辩证运动状态的——它的实际化,实行过程是观察问题的方法,用作认知切入点和判别标准的是它的价值观,具象化则是它的表述方式或外化,而它的本体化则是它的哲学形态,这种哲学形态又始终是贴近形象化的。“德”具有某种物象意义。
人之道和“自然”之道的对待和融合
郭店本《老子》有25个“道”字。郭店本《老子》把“道”看作一种状态,第一篇第一章讲“道”的本体是一种“有状混成”的状态,其时历“先天地生”,其存在情形“寂寥,独立,不改”,可见其无声、无形、不受外物支配、本性不变。其功能和价值“可以为天下母”,其无名,但可逊称之,强称之,“未知其名,字之曰道,吾强为之名曰大”。其“强为之名”的名称竟然也能暗合其大循环运动本性:“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大”本身就是一种状况,“天大,地大,道大,王亦大。”四对象之“四大”的组合,第四对象尤其应引起我们注意:“国中有四大焉,王居一焉。”上古“人”与“王”一样,都是有身份者。故从运动论的角度看,可以将四对象间的逻辑关系依线性顺序描摹如下:“人(王)至于天,天至于地,地至于道,道至于自然。”从表达上看,这一运动的线性逻辑关系是:“天—地—道—王(人)”,“人(王)—天—地—道—自然”。在运动论逻辑顺序中“人(王)”被凸显出来。从而提示我们,研究“道”必须回答人与道,人与天和地,人与自然,道与天和地,道与自然的关系。郭店本《老子》原文已从存在论的角度说明了另一种逻辑顺序:“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即“人(王)—地—天—道—自然”。这一顺序好像与运动论的顺序相反,实际上并不矛盾,运动有大循环在内,故能“人(王)至于天”等等。存在是对象本身的排列顺序,这一顺序同样突出“人(王)”,要求人们回答人与天地、自然的关系。故谓第一篇第一章是全书总纲,总纲之“总”是“人(王)”。
第一篇的中心要旨是为了讲“人(王)”而讲“道”,故第四章就引进“德”。末七章“功遂身退,天之道也”,明明是讲人之“道”,却名之曰“天之道”,可证篇内及于天道都是为了讲人道的。除第一章总纲外,其余六章有第四章讲“德”,第五章讲名与生命、生命与财产,第七章讲富贵不当骄,功成应身退。第六章讲“道”的运动和作用,是王本《德经》部分的内容。第三章是讲到了“天道员员”(“圆”的古字),但文中“致虚,恒也;守中,笃也”的主体仍然是讲人的,足见“天道”是“人之道”的补证。如此看来,第一篇除总纲讲“人(王)”以外,其余的六章,也有五章是讲“人之道”的。有理由认为,郭店本《老子》反映出来的春秋之“道”首先是“人之道”。“道法自然”一语,既然“道”首先是“人之道”,所取法的“自然”就不可能完全是大自然,或者说,天、地、自然都是作比于人,补证于人的。“自然”一词,郭店本《老子》当主要指人、人间之事、带有一定的自然特征的必然性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即使完全是在讲天地大自然,也是“人化”的自然,正如前面讲“德”是指“物化了的德”一样,讲“自然”是指“人化了的自然”。春秋老聃是把大自然加以人化,把客观世界加以主体化,同时又把人间之德加以物化,把主体精神世界加以客体化的第一人。这也是春秋之“道”与传统儒家能够互补的原始逻辑基础。
第二篇共十四章,无一不是讲人之道当保朴寡欲,像那洪荒无言的自然。论证方法是从有道或无道的种种表现、后果,来说明人之道、道应当如何如何,即人之道、道怎么样。归纳起来,讲了以下六个问题:
一是道的属性的表现形态。最重要的就是“视素保朴,少私寡欲”。春秋《老子》把“民利、无盗贼、孝慈”作为社会理想“状”况的目标,如何实现?在主体精神世界内的途径是“绝知(智)弃辩、绝巧弃利、绝伪弃虑”。(二篇一章)值得注意的是无帛甲乙本、王本第十九章的“绝圣、绝仁弃义、文不足”等说法。这有力地说明了春秋《老子》本身就是儒道互补的,不排斥圣、仁义、文。春秋“弃辩”一说,郭沂同志已指出,可与《史记·孔子世家》所记载的老子向孔子痛斥“博辩”为“发人之恶者”相互发明。(注:郭沂:《郭店竹简与先秦学术思想》,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64~65页。)既要“保朴”、“寡欲”,就会竭力批判“甚欲”之罪,“不知足”之害(二篇三章),这是逻辑的必然。
二是用具象思维,由江海处百川下而成为百川王,推说上古原始民主中的主体精神之“道”:自觉谦退处下。“圣人之在民前也,以身后之;其在民上也,以言下之。”这样才能做到“其在民上也,民弗厚也;其在民前也,民弗害也。天下乐进而弗厌”(二篇二章)。今本都作“是以圣人之欲上民也,必以其言下之;其欲先民也,必以身后之”之类。郭店本所言“自然”、自觉,今本之“欲”字与“寡欲”相背,“必”字有强使之意。可见郭店本的“道”有原始民主之意义,其所取法的“自然”都有主体自觉之意义。
三是“道”的效用论、目的论。最大的效用和目的是用来辅佐人主,而辅佐人主当“以道不以兵”。如达到目的,成功者不以此夸耀,不以此骄傲自满,“-是谓果而不强”(二篇四章),这就叫成功而不逞强。这样做对辅佐成功者个人来说,事情便有好报。这里有四个层面:道——道的实行,效用和目的——实行者个人之德——个人的结果。重心在道和德的实行论、效用论。士之守道,“微妙玄达,深不可识”(二篇五章),也是这个意思。不过对“上古之善为士者”的“微妙玄达”作了更具体的描述:迟疑就像冬天涉水过河,混沌就像浊水,等等。(注:郭沂:《郭店竹简与先秦学术思想》,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78页。)把玄妙深奥之“道”说得明白至可垂手而得。值得注意的是,郭店本《老子》“道”字的写法,大部分同王本作“道”,但第二篇第四章“以道佐人主”,第五章“保此道者,不欲尚盈”一语中的“道”字,写作从“行”从“人”字,是“道”字的异体字。这一异体字,甲骨文中已有此字,宋代郭忠恕《汗简》和夏竦《古文四声韵》都说出自《古老子》、《古尚书》。(注:廖名春先生已指出这一点,参见廖名春《楚简老子校释》九,载《简帛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88页。)郭店竹简《六德》讲论儒家,也用此异体字,并说这个异体的“道”字既指“群物”即万物的道,也是指“唯人”的道。(注:参见廖名春《楚简老子校释》九,载《简帛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88页。)郭店本《老子》第二篇第四章、第五章的两个“道”字的异体字,颇可证明郭店本《老子》的“道”既是物道,更是人道。
四是“道”的人哲学层面与外物“自然”层面共居,而形成物我相融、人物互渗、主客共存的“自然”。例如:讲圣人“无为,故无败”。从人我主体方面讲,有“无为”、“无执”、“慎终如始”、“欲不欲”、“不贵”、“教不教”,有了这么多的念想、愿望,“是故圣人能辅万物之自然,而弗能为”(二篇六章)。这里的“自然”,是万物本来的样子,是外物本身,是纯客体,与第一篇第一章“道法自然”之“自然”意义上有区别。这里是在主客体对比中用“自然”一词,并非在“自然”总体意义上使用该词语。从本章“圣人无为”、“圣人欲不欲……”、“圣人能辅(顺应)”“(圣人)弗能为”等语看,“自然”之总体只能是主客体共生的。又如:侯王守“无为”之“道”而“万物将自化”,“化而欲作,将镇之以无名之朴”(二篇七章)。这里的“万物”、“自”、“化”和“欲作”之前的空语类、物主代词“之”所指内容,都是大部指人事的,是“人化、化人”而侯王“镇之”。“侯王如能守之,万物将自宾”一语(二篇十章)在人与物的对比中,明谓万物可处于陪从的宾位。在圣人之“我”与民之间,可谓一体应“道”,无事、无为、好静、欲不欲,以使民“自富、自化、自正、自朴”,最终归于“道”(二篇十四章)。可见春秋老子的心目中,事合并于物,物淹没于事,事系于人。主体在主客体融合中往往处于主导地位,这正是中国传统哲学中的创造性哲学的渊源。“自宾”宾位之说,更是留下了巨大的创造空间。晚近龚自珍提出“宾宾”之说(注:参见《龚定庵全集类编》,中国书店1991年影印版,第105页。),向封建传统挑战,正是这一哲学创造精神的继承。又如:讲圣人临事把“无为”当作有为,“犹难之,故终无难”(二篇八章)。较之《论语·季氏》临事而惧,“陈力就列,不能者止”,则更深邃,且完全哲学化了。遇事“无为”、“犹难之”,以朴素精微之道结合于事体,仍然是人本主体哲学的反映。春秋老子正是在其自身的逻辑原点上开始与儒家道德实行哲学相通融的。
五是客观辩证对待万事万物的态度与人本主体、人物互渗之道的关系,是说明和被说明、启示和被启示的相承逻辑关系。美丑、善恶、有无、难易、长短、高下、音声、先后,无不处于辩证对待之中。“是以圣人”担当起符合道的“无为”的事业,实行符合道的“不言”的教化(二篇九章)。辩证对待与“道”之间的逻辑关系的形成,是主体之人对客体之“状”的认知,这种认知是直观的、悟性的。人对外物之“状”的直观认知、知性悟解,便在认识论的层面上产生了物我相融、道德一贯、人物互渗。“万物作而弗始也,为而弗恃,成而弗居”,正是这种相融、一贯、互渗之“状”的话语。
六是名制契约、规章制度也是一种“道”,所谓“始制有名”。“道”之人本性灼然可见。名制之于万民百姓,犹道之在天下,好比小溪流流入大江海,无所不在,名即道也。道本无为,故用名制规约万民,应适可而止(二篇十一章)。对道的认知,无须用名,名即道也。于“道”“知之者弗言,言之者弗知”(二篇十三章)。得道者闭门塞听,和光同尘,削锐解纷,“是谓玄同”,道本无为,道知“弗言”而无名,道人“玄同”。本体、认识、实行者恒相一致。
第三篇讲道、人体自然、德统一于“啬”(爱惜精气)。治人事天之道——啬(人体自然)——德(早归于道,早服)——治国之本(母)——长生久视之道(三篇一章)。这一逻辑结构仍可见“道”和“自然”的人本性。保守精气(啬)是修道,故郭店本紧接着有“修道和求知正相反”说。“学者日益,为道者日损。”(三篇二章)对“为道者”来说,因为他追求“无为”,故“绝学无忧”。一章乃至整个第三篇以“啬”为纲,二章承之讲修道,修道有“绝学”。是由“啬”绝学,是“道绝学”。老学史上的公案“绝学无忧”的位置(注:郭沂:《郭店竹简与先秦学术思想》,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03页。),由郭店本是可以得到合理解决的。正因为是“道绝学”,而非“知绝学”,故不能理解为春秋老子排斥学问知识,而是一种道、德的人本自然之“状”,径直言之是修道的手段。如果说三篇二章由“道无为”至“道绝学”是逻辑一贯,三篇三章由“道无为、道泯灭”(唯唯诺诺与厉声斥责、美与恶无大差别)至“道人畏”也是逻辑一贯。“人之所畏,亦不可以不畏”一语,正是讲修道者畏惧背离“道无为”。先秦“民”为万民,“人”为高人,此处高人之“人”正指修道者。“人之所畏”二句,历来不得其解,由人本性“道、德、无为、自然”观之,春秋老子正好讲了两个平行的逻辑一贯:“道绝学”和“道人畏”。循此而下,“道人宠辱”(三篇四章)、慎言自处之道(三篇五章)、圆满不露之道(三篇六章)、清净无为(三篇七章)、以“善建善保”之德治天下(三篇八章)、士德上中下与“道始无名”(三篇九章),都是讲“道、德、无为、自然”之理及其内质和实行中的对待。
第四篇讲政治之道。内容是奴隶制度下的原始民主,事业成功了,百姓却说我们本来就是如此。“成事遂功,而百姓曰我自然也。”(四篇一章)犹言君主、治理者皆可有可无,这既是民主之极致,更是原始民主的哲学升华。“我自然”三字,再次证明春秋老子的“自然”之道本身的群体集合的主体性。春秋老子的政治哲学恰恰就是“道”哲学,仁义、孝慈是受道的支配的,“大道废,安有仁义”一语,正是此意。春秋老子在“道”哲学层面上肯定仁义、孝慈等传统,与儒家在其道德本体“仁”的实行中肯定传统,也是互补的。四篇一章“太上下知有之,其次亲誉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之句式,尤像《左传·襄公二十四年》“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立言”、《墨子·亲士》“太上无败,其次败而有以成”之句式,清人已注意到这种比较。清毕沅《墨子校注》引《文选》李善注:“河上公注老子云:太上谓太古无名之君也。”此可为郭店本《老子》是春秋战国之际的《老子》提供证据。高亨在《老子正诂》中曾经引用《太平御览》的材料,证明《老子》一书出自春秋末。《太平御览》卷五百十三引《墨子》的话说:“老子曰:道冲而用之,有弗盈。”高说正可与此互相发明。春秋老子的政治之道如何实行?圣人执守平淡无味的大道(四篇二章)、以人为本,恬淡处置战争(四篇三章)、处事无为无执,“能辅万物之自然而弗敢为”(四篇四章),即任其“自然”。治事言“万物之自然”,主要指人事之“自然”甚明。
人德的物化和物道的人化的认识和历史原因
从以上内证的挖掘和分析看,春秋战国之际的《老子》德性的物化、客体化和道性的人化、主体化是非常明显的。德性的物化有利于构建范围宽广、乃至于无所不包的德性伦理体系,道性的人化更有利于构建道性人伦体系,同样也有利于构建普遍人化的物理体系和“自然哲学”体系。这三种道德、物理体系的构建都离不开“人”,离不开“人”的放大,离不开彼之时代的人文精神的缔结和张扬。但如前所说,那个时代的“人”主要是指大大小小的统治者,“人”与“民”是有区别的。伦理物理相互整合,并循此建立道德观念,也应该说是上古共有的。亚里士多德说过:“一切德性,只要某物以它为德性,它就不但要使该物状况良好,并且要给予该物以优秀的功能。例如眼睛的德性,就不但要使双目明亮,还要让它功能良好(眼睛的德性,就意味着视力敏锐)。马的德性也是这样,它要使马成为一匹良马。”这里的“德性”决不限于人伦道德领域,几乎全是指物理性。现在,我们要分析一下春秋战国之际的《老子》以物性言德性,以人性言道性的原因。
首先,这与上古人类的具象思维极有关系。文字是记录语言的工具,道德是规范行为的范式。文字是怎样产生的?汉代许慎《说文叙》讲论文字的产生,是远古人类观察到天上的日月星辰及其运行,观察到地上的鸟兽的蹄印,“近取诸身,远取诸物”,引起人们的最初反思,“于是始作《易》八卦”,用来表达那些很有代表性的、典型的事物的形相:象。后来又有结绳而治,因反思本身的逐渐进步,最后得以“初造书契”产生了文字。由此推证德性的认知,也是首先看见许多外物,许多事件,颜色、大小、软硬、高下、长短、难易,初名物性曰“德”,当然是可以的,后来连类而及命名人事、人性曰“德”,当然也是可以的。认知中的“移情”“移位”,或者说,是具象思维过程中的主体观念的观照和理性把握相结合,使人事、人性之“德”也一律打上物情、物性之“德”的烙印,也应该说是必然的。既有“象”,就一定有形象,有美。事实上,上古人们是以具象和美的眼光来观察万事万物的。春秋中期的《诗经》充满美情、美声、美色,就是最好的证据。以具象和美认知,必然于人伦德性既识其美,也说其物象物性,于物性之道既识其物理,也说其美情、美声色。值得注意的是,春秋《老子》把“状”作为知“道”的逻辑起点,“状”中有物,‘状”中有象,“状”中有美声色。可以说,春秋《老子》的基础定位就是具象和美,就是主客体结合。德性含物性是必然的。
对客观事物的认识打上主体、主观的烙印,是先民们对宇宙统一性的认识,“天人合一”就是这种表达。朱熹解释“天”的含意至少有三种:“要人自看得分晓,也有说苍苍者,也有说主宰者,也有单训义理时。”(注:《朱子语类》,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一册卷一,第5页。)一是客观自然之天,二是主宰世界的天神之天,三是理念之天。第一种以荀子为代表,第二种以董仲舒为代表,第三种以朱熹理学为代表,还有:一、二种的结合孔子居多,二、三种的结合思孟学派、宋代陆学、明代王学居多,一、三种的结合正可以春秋老子为代表,春秋老子的“天”既是客观的,也是理念的。十分可贵的是,春秋老子从天地未分之时讲论“天”,即“先天地生”的“天下母”,那是一种状态,所谓“有状混成”。我们不能不承认,这是对宇宙统一性的一种描述。从最根本的道理讲,宇宙的统一性存在于它的物质的多样性。但“状”、状态本身也是一种“物质多样性”。此外,从宇宙史看,各别宇宙是有它的历史发展过程的。例如,太阳有60亿年的历史,地球有50亿年的历史,至于河外星系,那又另作别论,一讲历史,就意味着有它的开始,太阳有它的初始“状”,地球有它的初始“状”,各别宇宙太阳、地球的初始“状”不是经验的,它是一个待证明,而又很难用,或者说不可能用经验加以说明的问题。在经验不可企及之处,借用逻辑的推证,并使推证越出经验之外,是可以理解的。由此可见,春秋老子在德性和道性问题上主客观并存,是有它的宇宙观和认识论层面上的原因的。
从春秋《老子》产生的历史文化背景看,上承远古至文王、武王,下启战国纷争。今存《尚书》五十八篇,起于《虞夏书》而结于《周书·秦誓》僖公三十三年(前627年),所记载的历史,是春秋《老子》的思想土壤。彼之原始民主和家天下,乃至酝酿天下大祸害的时代,形成了哲学家的概括和答卷。虽然郭店本《老子》无明显引《尚书》的文字(注:陈梦家曾考出《论语》等引《尚书》168条,无《老子》。见《尚书通论》,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5页。重要的是,郭店竹简《缁衣》引《尚书》,是真正的古文《尚书》。见刘桓《读郭店楚墓竹简札记》,载《简帛研究》,广西师大出版社2001年版,第65页。),但郭店《老子》第一篇第一章“王亦大”义即“人亦大”,“人法地,地法天”,突出一个“人”的概念和“人”字,正与《尚书·泰誓》“惟人万物之灵”,《孝经》“天地之性人为贵”如出一辙。《泰誓》作于周文王十一年,《孝经》据《汉书·艺文志》为孔子所作。又郭店《老子》第二篇第四章、第五章两个“道”字的异体字与《古尚书》用字同,甚至同于甲骨文,都可窥见郭店《老子》所反映的时代为上古。从“哲学家的概括和答卷”这一层面看,春秋《老子》回复到往古以至于洪荒自然年代,以古史和自然史解释当世,以原始民主范畴现实种种不当,以哲学家特有的理念救治社会恶弊,以“道”、“德”、“自然”等语境反映并企求消解矛盾,以不同于儒、墨的玄思及其外化摄入社会存在,以具象思维的观照和理性的结合形成诗学般的宇宙,如此等等,都和《尚书》所描述的时代:尧舜禅让,大禹治水,汤诰天道,福善祸淫,周公辅政,唯德其物,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许多学者在研究王本《老子》所体现的哲学思想时,都把老子思想和春秋时代的种种社会背景和文化思想联系起来。(注:参见陈鼓应《老子注译及评介》,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71、73、96、100、118页。)而在春秋《老子》那里,道、德、自然等作为哲学理念本身,又都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