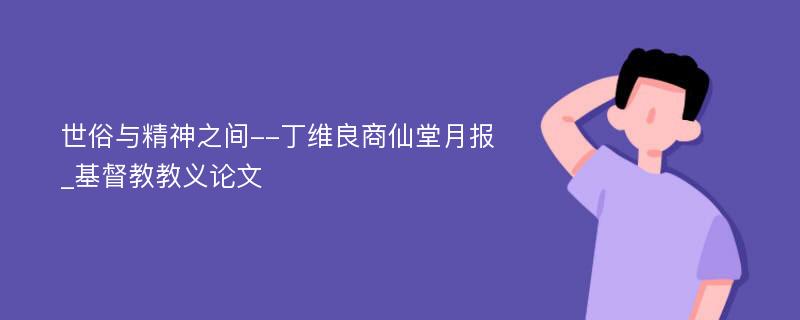
世俗与属灵之间:丁韪良与《尚贤堂月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月报论文,世俗论文,属灵论文,丁韪良论文,尚贤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06)03—0103—06
丁韪良(W.A.P.Martin,1827—1916年)是晚清在华最活跃、最有影响的美国新教长老会传教士之一。他早年在宁波、上海以及北京等地传教,后脱离长老会任京师同文馆总教习,完全转向世俗活动。在同文馆任上丁韪良以译介西方“实学”(或“世俗科学”)如公法、富国策、格致以及创办《中西闻见录》而闻名于世。1894年5月他因病返美并于次年正式辞同文馆总教习职。1897年1月丁韪良重返中国并于1898年8月被任命为京师大学堂西总教习。众所周知,1897年1月到1898年8月是康、梁发动的维新运动在中国如火如荼展开并达到高潮之时。当时一些知名的在华外国传教士如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李佳白(Gilbert Reid )等都积极参与了“救时”的变法游说活动,而作为在华传教士头面人物的丁韪良似乎没有一点作为,这显然不合情理。遗憾的是,限于资料,学术界对于丁韪良在维新运动时期的思想以及活动情况的研究一直付之阙如。① 笔者新近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发现的丁韪良这一时期主持的《尚贤堂月报》(后改名《新学月报》,1897 年6月至1898年5 月)则有助于我们深入了解丁韪良从同文馆离职后的活动情况以及传教思想的变化,从而填补他生平中的一段空白。
一、从“由格物而推及造物”到“格物以造物为宗”——丁韪良与《尚贤堂月报》的创办
1897年6月, 丁韪良正式在北京宣武门内绒绒胡同后小六部口西的尚贤堂(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② 筹办处创办《尚贤堂月报》,这是继19世纪70年代《中西闻见录》后丁韪良创办的又一份刊物。关于《尚贤堂月报》创立的背景和经过,丁韪良在创刊号“告白”中有明确交代:
按《华北月报》,本华北书会所出,词意浅近,宜于教中子弟长进道德。至去岁转托本堂(即尚贤堂)启东李佳白先生督理之,忽见改弦易辙,局面视前顿异,奚止唅之化为雀而飞腾也。既论学问之虚实,又觇时政之得失,其笔力颇为士大夫所首肯。惜启东问讣,不得已而回国。适值余旋华,书会即请接办。余视为善举而勉从之。不料复据书会致意,请将《(华北)月报》复其本来面目,俾教中善男信女,咸得受益。余熟思之,窃谓与其复旧,不如出新,遂将《华北月报》交回书会。拟自来月起,刊印《尚贤堂月报》,分送以代之。至新报与旧报,其异同之处,姑不赘言,俟报送到,一览自明。夫消遣之策,莫妙于造报。余既辞官守,又无教差,惟有一心注于《(尚贤堂)月报》,遂不觉老忧俱忘。[1](1,P1)
由此不难看出,此时“既辞官守,又无教差”的丁韪良原本是要督理李佳白转托的华北书会(The North China Tract Society)的《华北月报》,只因不满华北书会改变李佳白督理《华北月报》时所秉持的世俗化编辑方针,才在尚贤堂筹备处创办了《尚贤堂月报》。李佳白(启东)系美国长老会传教士,迄今研究戊戌变法的专著一般都将李佳白视为与李提摩太以及伊藤博文齐名并对戊戌变法影响最大的三位外国人之一。[2] 这一时期,李佳白正在迎合中国上层的维新思潮,以“救时”为己任,活跃于上流社会,积极筹办尚贤堂和为变法出谋划策。由李佳白委托丁韪良办理《华北月报》,足见丁韪良这一时期的活动与李佳白有关。一些零星资料也证实了丁韪良在这一时期除继续挂名美以美会汇文书馆(Peking University)的董事外,[3](1897—04—03) 主要活动是帮李佳白筹办尚贤堂。
丁韪良不满华北书会的保守态度,辞去《华北月报》的编辑工作,转而创办《尚贤堂月报》,表明他仍在坚持同文馆时期试图单靠宣传西方世俗科学而令中国皈依基督教的“由格物而推及造物”的世俗化立场。但又不仅仅止于此,实际上我们发现丁韪良这一时期对自己完全世俗化的思想也有所修正和调整,由过去的“由格物而推及造物”单靠“实学”皈依中国的世俗派做法转到主张“科学如矢之翼,而基督教则如矢之的”(“格物以造物为宗”)的世俗与属灵并重的中间立场。丁韪良在1897年1月的一次讲演中,面对教会内部世俗与属灵两派之争时, 表达了明确的折中态度。他一方面强调福音是目的、手段和力量,另一方面又主张“为了给基督赢得世界,就必须有各种各样的辅助影响与福音同行”。在西方世俗科学与福音的关系上,他着重强调了“西方科学是传播福音的辅助手段”,“科学如矢之翼,而基督教则如矢之的”。③ 丁韪良的这种调整和转变本质上是从消极的单靠普及和推广西方实用的世俗知识转到积极强调基督教教义的根本地位,除了是迫于教会内部属灵派的压力与属灵派妥协外,也是出于对他同文馆时期完全世俗派做法的反思并应对这一时期中国流行的对抗基督教的“中体西用论”。④ 丁韪良创办的《尚贤堂月报》,其内也明显反映了他这一时期传教思想的变化,即“格物以造物为宗”,“新学”要以“道学”为本。
二、《尚贤堂月报》的内容:“新学”、“道学”并举以“救时”
《尚贤堂月报》大致每月20日前出版,篇幅约11页,全年12期。 从第三本(1897年8月)起改名《新学月报》。尽管丁韪良对《尚贤堂月报》这一基督教文学事业十分看重,一度谢绝了盛宣怀要他担任上海南洋公学校长的邀请,[3](1897—09—25) 但《尚贤堂月报》却只出了12期就停刊了,其中主要原因可能一是资金问题,二是人手少,三是稿源不足。丁韪良主办《尚贤堂月报》,只有登州文会馆的毕业生,后任京师大学堂算学教习的山东高密人綦策鳌一人襄助。丁韪良自称“督理”,称綦策鳌为“副理”。《尚贤堂月报》的作者不多,除丁韪良、綦策鳌外,署名者尚有潞河书院院长谢子容(M.E.Sheffield)、宛平郭家声、怀定牧师(J.Whiting)、大兴李道衡、潞河书院教习丁立瑞以及梁启超。除梁启超外,其他撰稿者多为传教士和教徒。
按照丁韪良在创刊号上“告白”的说法,《尚贤堂月报》的内容可粗略分为时论类(或政论类)、新学(格致或实学)类、新闻类,其主题可以归结为“新学”、“道学”并举以“救时”。
(一)时论:“以兴利除害为宗旨”。
《尚贤堂月报》最突出的是政论部分,这在《中西闻见录》中是不多见的。政论多这一特点既与丁韪良这一时期力图影响中国上层,进而推动中国的基督化有关,也与中国士大夫阶层甲午之后热衷于议政有关。政论的主要内容是强调变革以“救时”,变革的最根本手段是以基督教来振兴中国,其他的变革则都是次枝末节。当时中国的士大夫之谈时务者,均以自强为急务,以西法之当行,而“独于泰西之教则谓为利国而宜行者罕见,谓为病国而宜禁者多”。丁韪良指出这是由于他们见识不广之故,他明确指出西方的富强,其本在于“泰西之教”,“新学、新法以及新政,莫不由之”,“彼採西法而欲遣西教者,何异栽树而拔其本乎?”[1](7,P9)
从法、德、俄、英、美五大国的历史经验看,丁韪良认为,西方新政可供中国维新之借鉴者有“修律法、兴学校、创机器”三大端。泰西新政“以更正律例为团结人心之第一要义”,“以振兴学校为化导人心之绝大关键”,至于“创新机”则“便”于士、农、工、商、甚至于“御侮捍国”。“律例、学校者,新政之体也,创造机器者,新政之用也;体用兼营,国势巩固,行新政者之所为,措天下于磐石之安也。”[1](2,P2) 振兴学校具体到中国如何做,丁韪良坚持他在同文馆时提出的“科学渗入科举”(“稍用西术于科场”)主张,“非新学不取士”,达到“旧学不废,新学自兴”的目的。这是他数十年前主持同文馆时与总理衙门成员宝筠、沈桂芬讨论后所得出的一个“旧瓶装新酒”的妥协方案,即利用原有的科举制形式而增加西方新的科学内容。
对于西方之政体以及政党制度,丁韪良认为各国政体有民主、君主以及君民共主之分,而政党也相应有“守旧”、“维新”之分,但“维新者,并非蔑视旧章,乃真有见于弊之当除;守旧者,亦非固执,乃恐骤变而激乱,不如缓图之为妥”,二者之异同在于“维新者欲兴利除弊,守旧者恐其涉于鲁莽,如谷之未熟先割而多方阻挠,此其异者也。迨至利己兴,弊已除,则两党悉无违言,此其同者也。”“二党之爱国,所见只分迟速,别无悬殊也”。两党只是考虑问题的角度以及方法不同,并非有本质的区别。但另一方面,丁韪良又强调实行民主制度的益处。他指出西方允许在野党自由发表言论可以判别官吏之贤否,可以彰显“政治之得失”,可以“开聪明而启智慧”。
至于中国是否应该学习西方的政党民主制度,丁韪良分别以土耳其和日本学习欧美民主制度的失败以及成功经验,提出应谨慎从事,“是举之有关于其国之教化民情者,亦不得不详为审察矣”。[1](12,PP9—10) 时值中国维新派与顽固派激烈斗争之际,丁韪良表面上似乎持一种中立立场,但他强调允许言论自由、维护民主制度,主张立党为公,这无疑又是对维新派的支持。
在外交方面,丁韪良强调中国当权者要守之以信,他说历史发展到今天,已经有公法、条约以维持邦交,再加有“文学以会通之”,“邦交之道,可谓无憾”,“所可惜者,限界未豁,则猜忌易生,猜忌一生,则到处棘手耳。苟能大张文教,广兴实学,遐迩一体,中外褆福。俾尔我臣民,悉泯诈虞,则大同之象,无间东西矣”。[1](3,P2)
军事改革方面,丁韪良附和孙家鼐提出的“奏请变通武场考试以及技勇旧制”两折,就改革武举制度提出了“非学(专门)不取,非新(武器)不用”的“变通武场说”,特别以长平之战、法德之战等古今中外之例从反面强调武政变革的重要性。[1](2,P2) 丁韪良不赞同甲午后中国国内重建海军的呼吁,而主张重点应放在建设整顿陆军,鼓励学习科技,“如其添制兵舰,不如鼓舞实学,整顿陆师,二者立则本固”。[1](9,P7)
在经济方面,丁韪良发挥中国古代的“三宝论”,提出了农、工、商并举发展,从而“广其土地,和辑其人民,整饬其政事”的“新三宝论”。[1](5,P1) 丁韪良还呼吁举办邮政、电报以及铁路等近代化事业,[1](2,P11) 主张中国应该不顾其他国家的阻力,修筑卢汉铁路以及排除“隐忧”,修筑经东三省的俄国西伯利亚铁路“借俄而御俄”。[1](2,P2) 此外,清政府要学习西方,奖励新发明,施行、保护专利法,鼓励人们创造发明的积极性。[1](2,P2)
(二)新学(实学):“阐明各国新学,为补旧学之不足”。
与《中西闻见录》相比,丁韪良在编辑《尚贤堂月报》(《新学月报》)时,新学是“阐发格致各理”以“启蒙愚蒙,增益智慧”[6] 的手段,目标是克服中国人的迷信,并以皈依基督教为归宿,即“格物以造物为宗”。
新学的内容主要以格致、富国策(政治经济学)以及基督教心理学为主,格致占相当重要的一部分。他摘引了一篇发表在《万国公报》上探讨格致与基督教文明关系的文章,该文探讨了基督教国家富强的原因,强调基督教国家今日“文明丕焕”,“要皆在于格致端其本也”。格致首先能让人驱除迷信而笃信基督教,其次,能给人类带来富强而进入文明社会。该文最后指出:“今之论教化者,窃见泰西诸国,文明日盛,富强日著,权力日充,以为我中国所不能及,岂知彼之所以能致此者,亦不过专精格致,务求真实,广行仁爱,使人自立,如是而已,非有他道。夫物有本末,格致其本也,教化其末也;事有始终,格致始事也,教化终事也。世有以整顿教化为己任者,尚其知所先后而于格物致知之学,一加之意乎?”[1] (6,P10)
在格致中,天文学说是重点介绍的学科,“窃谓实学各种,天文为冠,特因其道高远,其理深妙,解者无几,好者尤鲜”。实际上中国人因秉持天人感应的观念,从皇帝到一般老百姓对天文都极为重视,而其中的迷信成分恰恰构成对基督教文明传播的最大障碍,因此从明末来华的天主教传教士到晚清来华的基督教传教士无不着意于介绍西方的天文学说,丁韪良对介绍西方天文学的热衷,其目的亦在此。从第2本起一直到第10本,丁韪良连续9期登载了他自己撰写的《天文新说》。《天文新说》以留洋归来的陈先生(代表西学、新学)与北京的李先生(代表中学、旧学)二人问答的形式分别介绍了地球、月球、太阳、恒星、行星等天体和星系的一般知识以及西方的天文学说如开普勒定律(刻白尔三纲)、力热转化定律等,意在消除中国人的迷信观念。丁韪良还直言不讳地对“风水”学说提出批评。[1](7,P5)
新学中,富国策仍旧是丁韪良十分关注的重点。富国策即西方的古典政治经济学。丁韪良自己曾翻译了法思德著的《富国策》,首次向中国介绍了西方当时主流的政治经济学。在《尚贤堂月报》中,丁韪良虽自己没有撰文,但却连载了谢卫楼(D.Z.Sheffield)撰写的《富国策摘要》,表明他仍旧重视这门学问。
基督教心理学是丁韪良新学传播的一个主要部分,他后期发表的基督教心理学方面的重要著作《性学举隅》,即先以《性学发轫》为题在《尚贤堂月报》(《新学月报》)连载。《性学发轫》(《性学举隅》)实际上是《天道溯原》中论述“心才”和“德才”部分的扩充。
(三)新闻:“旁稽六洲时政,借鉴事务之因革”。
新闻报道也是《尚贤堂月报》(《新学月报》)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意在给中国正在进行的维新运动提供时务资讯。与《中西闻见录》相比,《尚贤堂月报》的新闻来源较为广泛,既有译自西文报纸(含在中国本土出版)的,也有摘自中国本土出版的教会中文报纸的。但与《中西闻见录》不同的是,新闻涉及的国家较少,多集中于西方大国,此外海外华侨受迫害的报道也没有了,国际外交方面的新闻报道也往往只有一句话或寥寥数语。
新闻中,介绍格致或新学在各国的进展情况的仍有相当一部分内容,也有一些新发明和新发明的推广方面的新闻,如马可尼的发明无线电报,[1](1,P7) 无线电报在日本的试验等等。一些格致新闻则意在破除中国人的迷信。丁韪良在新闻中对一些奇怪的自然现象如日食、地陷、下泥雨等进行了科学的解释,以消除国人的疑虑。如光绪二十四年戊戌正月,有日食发生,这在中国人中引起骚动,以为祸之将至。丁韪良以西方天文学说和康乾盛世的同样例子予以释疑,指出日食系自然现象,与吉凶无关。[1](8,P12) 另一些格致新闻则鼓励中国人接受新事物,如富尔顿发明轮船载客的故事等。[1](2,P10)
各国的改革、进步、工商业情况也是丁韪良新闻报道关注的一个方面。在新闻报道中,暹罗、日本、俄国已经替代《中西闻见录》中的波斯、巴西以及古巴等成为中国学习的典范。丁韪良赞扬了暹罗王赴英国参加英国女皇庆典的做法,称此举“诚也、明也,非诌也。况暹廷更拟由英至美,采风取法,以强其国,操心危,虑患深,实具卓识,又安可以仰息他人希图苟安者例之乎?”[1](1,P9) 他还介绍了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所进行的“大一统”、“正刑律”、“设议院”、“息教案”等政治改革,并特别赞扬藤博文接受基督教的立场。[1](10,PP6—7) 俄国“更正狱吏”、“振兴农务”、“大核户口”、“龙江开田”的革新做法也值得中国仿效,丁韪良在报道时特别赞赏“俄人之勇于前进也”。[1](3,P9)
文化教育、学术活动也是新闻报道的一个方面。文化报道仍然以办报为中心,特别强调办报要不拘于本国挑选人才,“求新诸国以新报之有益也,不惟任本国人为之,且任他国人代为之”,如美国的一份新报的馆主为英国人,日本亦有外人办报。丁韪良从旁观者清的角度出发,认为外人办报对国家有好处,犹如“借助他山”,其隐含的意思是中国也应该“借助他山”,让外人来办报。[1](1,P9)
一如在《中西闻见录》中所做的那样,丁韪良继续关注西人对中国以及东方的研究活动,企图以此激励中国人对西方的学术兴趣。他以各国都设立东学会以及朝廷、总统都予以重视为由,指出“方当实学宜兴之际,试问中华学士亦如此力求西学否,中华政府亦如此重视西学否?”丁韪良甚至建议中国驻外国使节在各国都城设立西学会,每五年则邀集会员在北京开会,政府隆礼以遇之。[1](7,P10;10,P11) 北京东方学会的活动是学术报道的另一个中心。他还将自己在北京东方学会上宣读的关于中国古代的发明以及发现的论文观点以“新学新术多原于中华论”为题摘要发表在《新学月报》上。
教会新闻很多,这是《中西闻见录》所没有的。李佳白的尚贤堂、传教士在各地举办的学堂、医院等教会事业是报道的重点。在这些涉及基督教的新闻中,丁韪良也总是借题发挥,不忘记为基督教辩护或阐释基督教教义。在一篇报道天津望海楼教堂重建的新闻末尾,丁韪良评论火烧望海楼教堂是因为“不解格物化学”之故,以致惹出事端。[1](2,P10) 在报道1897年4月的天津善会火灾时,丁韪良评论道:“天道无亲,常与善人,报施不爽”,“天地为一大机器耳,机之运行有定理”,“不能以眼前祸福定善恶”,关键在于来生的报应。[1](2,P4)
各国时事也是新闻报道中的一个组成部分,通常置于《尚贤堂月报》之末尾,内容有各国政要的行踪、各国国内新闻等。外交方面则有各国元首的对外访问,派驻公使,交涉、通商以及殖民地事务等。与《中西闻见录》中尽量避免评论中国与西方冲突事件的做法不同,这一时期丁韪良不再保持中立,而是从传教士的立场出发,在涉及传教士的中外冲突事件中明确进行表态。在《新学月报》中,他以答读者问的形式对1897年11月22日德国占领胶州湾的事件作出了肯定的评价。他认为德国占领胶州湾,系因其传教士在山东曹州被害,有合理的借口。他指出今后中国避免“兵端”的惟一办法是“认真保护(传教士)而已”。[1](7,P12)
三、《尚贤堂月报》之评价
《尚贤堂月报》以“新学”、“道学”并举以“救时”,与丁韪良以前主办的《中西闻见录》相比,反映出丁韪良在19世纪90年代活动的一些新的特征。
第一,《尚贤堂月报》在许多方面可以看成是《中西闻见录》的延续,如在宣传西方的“新学”(“实学”)、介绍各国进步等方面,有些内容甚至就是《中西闻见录》的深化或翻版,从《尚贤堂月报》中我们可以看到《中西闻见录》的影子。
第二,《尚贤堂月报》也表现出许多不同的特点,从而体现了丁韪良在90年代的思想特征。从《尚贤堂月报》的内容上看,包含格致以及其他西方物质文明在内的“新学”仍是丁韪良所追求的,但同时丁韪良没有忘记大力宣传基督教教义,注重将基督教文明作为一个整体,强调西方的格致或其他的物质文明只是整个基督教文明中的一个次要部分,也即格致只是手段,只是“用”和“末”,而基督教才是目的,才是“体”,才是“本”。丁韪良借用了这一时期中国士大夫中盛行的体用、本末说,显然是对他们“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一思潮作出的反应。在中国士大夫心里,“西学”所指的仅仅是西方的科学。将西方的科学与基督教割裂开来,这是丁韪良所不愿意看到的。重视世俗知识与灵性的皈依的结合是丁韪良这一阶段传教的特点,与他在同文馆时期的纯传授世俗知识的做法形成鲜明的对比,这是他传教手段上的一个重大转变。此外,丁韪良明显加大了政论的力度。但丁韪良在改革上仍然追求过渡论、渐进论,这与他在同文馆的教育改革上的做法是一致的,也与他洋务派的密切交往有关。
第四,在《尚贤堂月报》中,丁韪良不再像在《中西闻见录》中所做的那样,公开在中文中批评“西学中源论”或“西学东来说”,反而大张旗鼓地撰文承认西方确有一部分知识源于中国古代文明,试图利用中国各阶层普遍接受的观点作为一个历史依据,在甲午战后鼓励中国人向西方学习。
第五,丁韪良在《尚贤堂月报》上的观点对维新运动有一定的影响。限于资料,在现有的论文和书籍如汤志钧先生的《戊戌变法人物传稿》、王树槐先生的《外人与戊戌变法》以及美国学者Ralph Covell的丁韪良传记中,我们几乎看不到丁韪良在维新运动中的作为。实际上,公认的对维新运动影响颇大的李提摩太、李佳白当时在北京停留的时间并不长,相反丁韪良则从1897年初就一直呆在北京。虽然我们看不到丁韪良与康有为、梁启超等人有直接的交往,但通过《尚贤堂月报》的内容,我们还是能够看到丁韪良透过该杂志对维新运动所产生的影响,而并非是一个旁观者。《尚贤堂月报》在戊戌变法前发表的许多鼓吹改革的观点直接附和和赞同维新派,有些观点无疑对维新派有所启示;康有为以日本、俄国改革为例的“仿洋改制”思想,很难说未曾受到这份杂志的影响。而且《尚贤堂月报》地处戊戌变法的所在地北京,这无疑较设在上海的《万国公报》、《时务报》有地域优势。丁韪良被任命为京师大学堂总教习一职,反证出他对戊戌变法的影响。
当然,与《中西闻见录》刊行的19世纪70年代相比,这一时期中国人接受西方知识的渠道要多得多了,中国人自己就办了许多有影响的报纸如《时务报》等,《尚贤堂月报》不再是中国人获取信息的惟一渠道,甚至《尚贤堂月报》有时还转引一些省报的报道。《尚贤堂月报》的相对地位要较《中西闻见录》低,而且由于其将科学与基督教直接绑在一起,无疑也会激起一部分中国士大夫的反感,从而削弱其在传播西方科学、推进维新上的作用。
注释:
① 关于丁韪良研究的重要成果,有王维俭《丁韪良和京师同文馆》,《中山大学学报》1984年第2期;孙邦华《简论丁韪良》,《史林》1999年第4期;王文兵《丁韪良与〈中西闻见录〉》,《汉学研究》第8卷,中华书局,2004年,第503—548页;王文兵《丁韪良与中国》,南开大学未发表的博士论文,2005年;Ralph Covell:“W.A.P.Martin:the Pioneer of Progress of China”,Christian University Press,1978年。其中Ralph Covell作的丁韪良传记尤其值得一提,该书从丁韪良与中国近代的变革这一视角描述了丁韪良的一生,据丁韪良传记词条编撰者Ernst Schwintzer的观点,该书最有价值的部分在于深入论述了同文馆时期丁韪良身份向世俗的转变及其原因。参见J.Garraty和M.Carnes编辑:American National Biography,Vol.14,Oxford,1999,第613页。这些文章或专著对丁韪良早期在同文馆的活动、传教思想以及创办《中西闻见录》等有深入的研究。相形之下,学术界对于丁韪良维新时期的活动则几乎未曾涉及,对于《尚贤堂月报》(《新学月报》)亦无人知晓。
② 所谓的尚贤堂是一种类似于学校的机构,系李佳白为力行其“救时”方略,“实事求是,以期培养人才,裨益全局”而设。按照李佳白的设想,尚贤堂内设有中西上等人士会晤公所,以联情谊和消除民教隔阂;另设藏书馆、学馆、洋文学馆、格致书院并刊刻时贤所著新策和做抚危济困等善事。其章程宗旨有四:一是所作所为“专求有益中国,有利革民”;二是“广设善法,调剂于彼此之间,务令中外民教底于和洽”;三是“期于恢拓学士之志量,研炼儒者之才能,俾上行下效,使中人以上之人智能日增,即资之以变化庸众”;四是“往来交接”,“总以劝善为本,无论砥砺德行,讲求道艺,期乎扩充旧识,启迪新知”。参见李佳白《尚贤堂文录:京师拟设尚贤堂章程序》,《万国公报》卷102,光绪二十三年六月。 又见《京师拟创尚贤堂小记附章程 删改〈申报〉译文》,林乐知等译,《万国公报》卷101,光绪二十三年五月。设立尚贤堂的大体计划在1895年6月就已经有了, 此时李佳白虽然没有提到尚贤堂的名称,但是已经提到了建立综合性学院、藏书楼和演讲厅,参见The Peking and Tientsin Times,1895年6月22日。1897年3月(光绪二十三年二月十八日)设立尚贤堂的计划正式得到总署批准,见李佳白《尚贤堂文录:京师拟设尚贤堂章程序》,《万国公报》卷102,光绪二十三年六月。另见1897年4月10日The Peking and Tientsin Times报道。
③ 丁韪良:“Western Science as Auxiliary to the Spread of Gospel”,The Chinese Recorder,XXVIII(Mar.,1897),PP111—116。中国学者过去多笼统地将此文中的观点仅仅理解为丁韪良重视利用世俗科学传教并反过来解释丁韪良之前在同文馆时期的世俗活动,这种理解似是而非,模糊了丁韪良一生前后期在传教思想上的变化。参见王维俭《丁韪良与京师同文馆》,《中山大学学报》1984年第2期;孙邦华《简论丁韪良》,《史林》1999年第4期。
④ 丁韪良1877年提交给上海首次新教传教士大会的“论世俗文学”一文在会上受到批评。这篇文章虽收入丁韪良《翰林集》第一编(1880年),但丁韪良后来出版的文集却未再收入该文;90年代甚至有中国人向他提出“敬神之道,今之格物家,非皆置之度外乎”的问题,中国受众的反应显然令丁韪良反思了他以前的做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