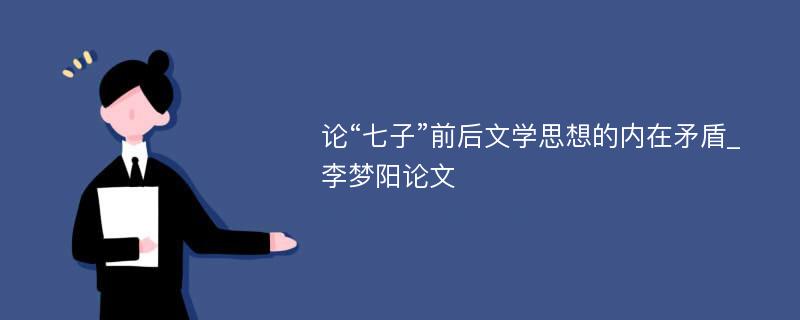
略论前后七子文学思想的内在矛盾,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七子论文,矛盾论文,思想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 明代文学研究者多以为前后七子重复古摸拟,缺乏艺术个性,其实他们并非轻视个性与创造精神,只是出于时代原因,其文学思想存在着无法克服的矛盾。前七子经历了由“弘治中兴”到正德昏愦王朝的变迁,文学风格表现为追求雅正雄壮的审美理想与愤激悲凉的创作现实难之以统一;后七子身处主威臣谄,排陷激烈的嘉靖朝后期,文学风格表现为强调个人才情与取法传统格调之不能协调。尽管如此,他们在文学道路上,还是朝着突出个性、才情的方向蹒跚地前进。
〔关 键 词〕 前后七子 文学思想 理想 现实 才情 格调
凡谈论明代前后七子者,莫不对其复古模拟大张挞伐,并责其创作缺乏艺术个性。其实,前后七子并非不看重自我个性与创造精神,而是其自身的文学思想存在着无法克服的内在矛盾,从而导致其创作的缺陷。而且,学者们在谈论前后七子时,往往笼统地视为一体,这是很不合适的。仅就其文学思想所存在的矛盾而言,他们之间亦有较大区别:前七子主要表现为理想与现实之无法统一,后七子则表现为才情与格调法度之无法协调,其原因则在于各自所处的时代不同。本文拟对此不同分别加以论述。
一 理想与现实间的冲突
以李梦阳、何景明为首的前七子文学复古思潮形成于明代弘治年间,其诱发因素则是所谓的“弘治中兴”。弘治皇帝在中国历史上并不能算是大有作为的皇帝,尽管他较其前后的君主更能克己为国,诸如准时出席经筵,不断发布减免水旱灾害地区赋税的诏令,虚心听取臣子们的各种建议与劝谏,在个人生活上终生只守着皇后一人而没有嫔妃的记载,但这些充其量只说明他是位兢兢业业的守成之君,而离所谓“中兴”之君尚有相当距离。然而在文人心目中,弘治之年已属难得之盛世。诚如李梦阳所言:“是时国家承平百三十年余矣,治体宽裕,生养繁殖,斧斤穷于深谷,马牛遍满阡陌。即闾阎而贱视绮罗,粱肉縻烂之,可谓极治。然是时海内无盗贼干戈之警,百官委蛇于公朝,入则振珮,出则鸣珂。进退理乱弗婴于心。盖暇则酒食会聚,讨订文史,朋讲群咏,深钩颐剖,乃咸得大肆于弘学。”〔1〕故空同吟诗作文之目的便是要“休令黼黻犯岑寂,要与琬琰增嶙峋”〔2〕。 但他们与台阁体不同之处在于其除鼓吹休明外,同时要以诗文兴起士人节操志气,培养国家元气,从而辅佐皇上以达汉唐盛世。康海曾明确要求诗文应浑厚尔雅,读之令人兴起志意,反之则将于士气不利,因为“弃朴趋末则淳厚蚀,务细博奇则闳伟散,脂韦浮沉则刚毅亡,即谗履伪则强奋息”〔3〕。故前七子论诗文虽多涉于风格,其终极目光则始终在于复兴古道以达治世。诚如黄省曾致李梦阳信中所言:“不复古文,安复古道哉?”〔4〕
正是出于此一目的,前七子对诗文审美风格之要求为:雅正、博大、雄浑、婉壮。如空同所言:“夫诗有七难,格古,调逸,气舒,句浑,音圆,思冲,情以发之,七者备而后诗昌也。”〔5〕梦阳所言之意境实则是以雅正为归,即婉转质朴,情深浑融之和乐境界,也就是传统诗教所言的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中和之美,只是较传统诗教更突出盛大雄壮之气势而已。自宋代以来,追求此种盛唐雄大壮丽之诗风者代不乏人,从宋人严羽之讲兴象,到明前期林鸿、高棅之以盛唐为极则,可谓七子之前响。略早于梦阳的李东阳则将此种审美理想喻之为五音中之宫声,所谓“诗有五声,全备者少,惟得宫声者为最优,盖可以兼众声也”〔6〕。后七子成员对此亦多有强调,谢榛曰:“体贵正大, 志贵高远,气贵雄浑,韵贵隽永。”〔7〕而合乎此理想者无疑为汉文唐诗,诚如后七子首领王世贞所言:“盛唐之于诗也,其气完,其声铿以平,其色丽以雅,其力沉而雄,其意融而无迹,故曰盛唐其则也。”〔8〕从文学自身讲,上述诸家所言之审美理想确实诱人,它注重情志之纯正高雅,境界之雄浑阔大,风格之婉丽含蓄,较之宋儒文以害道或文以载道之文学观显然更合乎审美之法则,故其在当时理所当然地为广大文人所折服,遂形成一股强劲的复古思潮。此种复古意识非但在诗文界广为流行,且渗透至戏曲小说领域。时人对戏曲家“犹有金元风范”之赞叹,对说部中“京本”、“京师老郎”之重视,均为复古心理之反映。
但复古派的此种审美追求无疑埋伏着深刻的危机,因为理想的诱人并不能解决创作中的难题。这并非复古诸子缺乏才气与信心,而是缺乏产生此种审美风格的文化土壤。弘治中兴随着孝宗的去世而泡影般消逝,由于明武宗纵欲尚武的荒唐举措而导致了阉宦专权与朝政混乱。前七子中大多被迫害贬斥,故而他们所可能拥有的情感显然非豪迈雄壮而是愤激悲凉。从自豪自信到愤激悲凉,这的确是弘治、正德二朝士人心态发展变化的基本图式。以李梦阳为例,他素以直言敢谏称,早在弘治末年即以弹劾贵戚张鹤龄入狱而享誉文臣间。正德二年,他又率先提议弹劾刘瑾而再次入狱。他曾自述曰:“尝自负丈夫在世,必不以富贵死生毁誉动心,而后天下事可济也。于是义所当往,违群不恤;豪势苟加,去就以之。”〔9〕当然,此种耿直强劲中亦并非毫无矫情成分, 只是这种矫情多是为社会效果计,故而才直言不讳曰:“宁伪行欺世而不可使天下无信道之名,宁矫死干誉而不可使天下无伏义之称。”〔10〕但他的忠直虽见赏于虚怀纳谏的明孝宗,在正德朝却倍受摧折。他虽有孤贞自持的节操,却无法改变朝政日非的现实,于是便转向愤激:“壮士愤国难,抚剑但徘徊。白日悠西倾,怆惋肝肺摧。”〔11〕李梦阳的愤激正是来源于由时代落差导致的希望破灭。他认为弘治朝乃中兴之时,故时时梦到彼时的美景,而眼见正德朝的混乱,遂产生今非昔比之感。当年写《洛阳陌》时他表示:“举手谢乡人,荣耀但区区。丈夫树名勋,所志在唐虞。扬袂径北去,万里谁能拘。”〔12〕不料等待他的却是正德间的入狱与革职。什么个人的“名勋”,国家的“唐虞”均已成为泡影。于是李梦阳的心态也就由愤激转向悲凉。在罢官居家时,他常常披衣夜起,面对寒声湿气,聆听雁叫蛩鸣,忍受着沉闷孤寂的折磨,渴望“谁能奋长剑,割破黑云层”〔13〕。他有时也极力自我开释,欲学邵雍筑安乐窝以自适,可终于阻不断“悲凉气转增”〔14〕。故而愤闷悲凉构成其诗作的晚年基调。李梦阳一生倡唐诗之正大雄浑,并不惜刻意摹仿,最终却不得不落脚于愤激悲凉的变徵之音,而此方为其诗的真情所在。李梦阳诗文风格的由典正转向愤激悲凉,正典型地代表了从弘治到正德由正到变的时代位移。此种转换又何止空同子一人,当时文人虽心态各不相同,诸如大复之凄惋,康海之放浪等,但在愤激悲凉上却均与梦阳同。
对创作上的此种转变他们自身亦并非毫无觉察。由形式上观:“诗倡和莫盛于弘治……自正德丁卯(二年)之变,缙绅罹惨毒之祸,于是士始皆以言为讳,重足累息,而前诸倡和者亦各萍梗散矣。”〔15〕满腹是昔盛今衰的体验。由风格上观,李梦阳更深知正、变之势不可挡,故在其《张生诗序》中曰:“故声,时则易;情,时则迁;常则正,迁则变;正则典,变则激;典则和,激则愤。故正之世,二南锵于房中,雅颂铿于庙庭;而其变也,风刺忧惧之音作,而来仪率舞之奏亡矣。”〔16〕以此段文字概括梦阳本人的创作风格演变亦极恰切。很难设想,对人有着如此冷峻清晰认识的李梦阳,对自身之转变会毫无觉察!
在创作上已悄然变易而在理论上仍持守弥坚,这就是前七子理论与创作或曰理想与现实之间无法克服的矛盾。其实,此种矛盾在其诗文创作本身亦有充分的体现。其中最典型者要算李梦阳自觉向杜甫诗风靠近的事例。尽管他在个人气质上更接近李白之狂,并当真写过不少水平不低的仿李之作,但其诗作悲愤沉郁的色调更倾向于杜甫。老杜无疑是盛唐土壤哺育出的伟大诗人,而其诗歌成就却主要在安史之乱后取得。他写战乱流离,写关怀国事,从而构成其沉郁顿挫的风格,此已非盛世之音而是战乱中之变徵之调。空同辈与杜甫之不同处,在于其弘治间所感受之气象完全无法与盛唐相提并论,故其诗作情调亦远无法与杜甫相比。如他们欲学杜诗之讽喻现实,但现实之混乱已远非讽喻所能凑效,则此类讽喻难免有些不痛不痒。明武宗于大内练兵,空同作《内教场歌》讽之曰:“雕弓豹鞬骑白马,大明门前马不下。径入内伐鼓, 大同耶?宣府耶?将军者谁也?武臣不习威,奈彼四夷。西门树旗,皇介夜驰;鸣炮烈火,嗟嗟辛苦。”〔17〕诗写得古朴雅正,含蓄蕴藉,然讽喻之意甚明。但明武宗不是周天子甚或孝宗亦不如。李梦阳不是质问如此在大内兴师动众,“大同耶?宣府耶?将军者谁耶?”武宗犹如从中获得启示,他先搬至宣府而不回大内,再至大同而与蒙古骑兵亲自开战,并自称威武大将军朱寿。这也难怪,大臣们措辞严厉的大量奏章尚未能令这位荒唐浪漫的皇上回心转意,空同的数首谏诗岂能解决问题。面对一个荒唐的君主,身处一个混乱的时代,大声疾呼尚不足振聋发聩,何况半吞半吐。一方面是对弘治中兴的留恋与固执,另一方面又感受到时代的变易与自身处境之窘迫,此种心态的矛盾造成了空同许多诗作在情感基调上大起大落的转换,即起以雄壮盛大而结以凄惨悲凉。《梁园歌》效太白之诗风,初读颇有声势,细品则多感伤怅惆:“独立天地间,长啸视今古,城隅落落一堆土,千年谁继白与甫。”〔18〕其中不乏高傲的情怀与挺拔特出的精神,然读者所感受到的却依然是一位感伤而孤独的文人形象。又如其《与骆子游三山陂三首其二》曰:“丘壑胸应满,乾坤独眼真。扬鞭指河洛,立马说周秦。古墓笙歌地,前朝战伐尘。秋风飒飒起,白草正愁人。”〔19〕前半本有扬鞭河洛、立马周秦之宏大气魄,但所言非周秦之盛壮,而是顿生今昔沧桑之感慨,最终仍落脚于秋风白草之凄然境界中。
其实有此情调者又决不限于空同一人,何景明诗作繁多,而其中“繁华旧时事,回首一长嗟”二句是其最典型之情调。繁华已去,惟余嗟叹之情,然又留恋不舍;雅颂已尽,仅剩变徵之音,却又牵挂于情。此诚如空同所言:“欲向仙郎夸白雪,阳春久已绝人传。”复古派之前七子本欲做白雪阳春雅调传入,却又时露薤露蒿里悲音,此种由矛盾心态所导致的文学思想的矛盾的确是他们自身所无法克服的。
二 诗人才情与格调法度的矛盾
前七子均经历过弘治、正德之际的巨大转折,中兴之梦时时萦绕心中,故而重气节操守热衷于现实政治。而在政治理想失望之后,遂造成心态的愤激与悲凉。后七子却无缘感受到弘治朝的从容和谐,他们身处主威臣谄、排陷激烈的嘉靖朝后期,不少人被权相严嵩所排挤,因而亦大都抱有愤激的心态。他们孤高傲世,不媚权贵的气节虽不弱于前七子,但对于中兴的愿望已不甚强烈,对于政治的兴趣已不甚浓厚,而更看重自身的文学才能。李攀龙曾论诗曰:“诗可以怨,一有嗟叹,即有咏歌,言危则性情峻洁,语深则意气激烈,能使人有孤臣孽子摈弃而不容之感,遁世绝俗之悲,泯而不滓,蝉蜕之外者,诗也。”〔20〕在这遗世独立的孤傲心态中,不仅透露出对政治前途的失望,同时也在淡化政治的内容。王世贞甚至对诗之教化作用亦一并轻视曰:“于麟之所取则以能工于辞不悖其体而已,非必尽合于古所谓发乎情止乎礼义,兴观群怨之用备而后为诗也。”〔21〕曾饱读诗书并经过科场反复拼搏的后七子当然本不乏经国济世的追求,但在权臣的排挤下,不得不替悲伤的自我多寻一条人生出路:“夫君子得志则精涣而为功,不得志则精敛而为言,此屈信之大变通于微权者也。”〔22〕如今恰是其政治不得志之时,无疑须“精敛而为言”,故其所重者惟在其创作才能而已。鉴于此,后七子一般反对以实用标准衡人论文,认为文人犹如麟凤,虽无益于政治实用却自显其华丽高贵。他们反复强调的是:“雕虫一代虽贵,倚马千言自才。”〔23〕“寥落文章事,相逢白首新。微吾竟长夜,念尔和《阳春》。”〔24〕“冥思何可测,奇语颇自惊。……功名亦垂世,无乃非其情。”〔25〕其目光已非功名之垂世,而是文章之荣身,表现着他们对自身才气自我肯定、自我欣赏的心态。在后七子那里,“才情”既是其相互联结的纽带,又是其价值取向的核心。
后七子既然已偏离政治此一中心而更重自我才情,便顺理成章地更重视诗之文采与节奏。如谢榛《四溟诗话》、王世贞《艺苑卮言》等诗论著作,都对诗歌谋篇布局技巧与韵律节奏安排的研讨明显较前七子增多。谢榛述其评诗标准曰:“凡作近体,诵要好,听要好,观要好,讲要好。诵之行云流水,听之金声玉振,观之烟霞散绮,讲之独茧抽丝,此诗家四关,使一关未过,则非佳句矣。”〔26〕李攀龙甚至说李梦阳之诗文佳处乃“视古修辞,宁失诸理”,而唐宋派诸人之所以倡言信口而谈乃是由于“惮于修辞”而才所不至。〔27〕可见其对诗文技巧的重视程度。就创作成就而言,于麟之七言律诗最为时人所欣赏,其原因即在于音韵的“俊洁响亮”〔28〕。后七子强调诗人之才情应予尊重,诗歌应具有文学色彩与音乐美,并对此进行深入探讨与大胆实践,这对突出作家的自我个性,争取文学的独立地位,提高文学的创作水平,显然均有积极意义。
然而,后七子从重诗人才情到重文采与技巧,再转而强调才学与模仿,从而走向才情的反面,将本是统一的两种因素却摆在了对立的地位。究其原因,则在于复古心态之顽强,并由此导致模拟之结果。复古派的主模拟历来有两种不同方式,如前七子中李梦阳主模拟而何景明主创造即是。后七子之李攀龙有似空同,为诗作文若能达优孟之仿孙叔敖而逼真即可,而谢榛则主张熟读各大家诗文以得其神气,从而自成一家。其实就实质而言均为自觉认同传统之风格体制而忽视其自身价值,结果势必损斫自己的才情个性。此种趋古心理形成的原因有二:(一)认为古人的诗文已尽善尽美,后人无法出其范围。于麟曰:“今之不能子长文章者曰:“法自己立矣,安在引于绳墨?即所用心非不濯濯,唯新是图。不知其言终日,卒未尝一语不出于古人,而诚无他自异也。徒以子长所逡巡不为者,彼方且得意为之,若是其自异尔,奈何欲自掩于博物君子也。”〔29〕可见若欲达古作者水平,务须广读博学,然后择其正者而仿之,不可自出心裁而为古人所笑。(二)古法非古人所有而是实物之自则。王世贞曰:“诗不云乎?有物有则。夫近体为律,夫律,法也。法家严而寡恩。又于乐亦为律,律亦乐法也。其翕纯皦绎,秩然而不可乱也。”〔30〕既然存有上述二因,则诗人惟有入于古人与法中驰骋才情而无须自立门户了。其实他们并非不知个人才情与古人格调之间存有矛盾,谢榛曾曰:“诗固有定体,人各有悟性。”〔31〕王世贞晚年亦曾喜东坡诗文而在创作上时有突破格调之处。然而他们在理论上却又始终不取意而取格。此背后实涉及价值观之问题,复古派虽已意识到个人才情的重要与文学的独立地位,但此种对自我价值之体认仍属浅表性的,诸如个体人格的保存与发扬,个体性情的愉悦满足与生命的意义,个人与社会的关系等等自我深层内涵,却尚未及进入其视野中。故而他们便不得不到古人处求得认同。古人古作经由历史的长期积淀已被视为楷模,认同于传统格调即可取得与之相同起码相近的价值与地位,于是便自甘于作古人奴仆而不惜损伤自我之才情。
后七子中亦有欲统一才情与格调法度者,王世贞即具此倾向。元美出生于人文荟萃之吴中,兼之士族家庭的良好教育,遂使其在倡言格调的同时,仍存留有吴中文人重才情意趣的倾向,故其言格调远较于麟通达:“才生思,思生调,调生格。思即才之用,调即思之境,格即调之界。”〔32〕在才思调格之序列安排中,作者主观才情显然已被置于首位,故而元美的诗作常有逾出理想格调之外者:“夫仆之病在好尽意而工引事,尽意而工事则不能无出入于格。以故诗有堕元白或晚季近代者,文有堕六朝或唐宋者。”〔33〕“工事”尤执于形式技巧,“尽意”则已重情思之表达。元美之能偶尔突破格调限制,与其诗作目的部分出于自娱有关。元美一生多历变故磨难,其父被朝廷处死,晚年又郁郁不得志,故其为诗文有时不免作为破闷消愁之寄托,所谓“大要用自愉耳”〔34〕。然元美的矛盾在于,既颇知格调为才思之产物,却又不肯越之以任才:“夫格者才之御也,调者气之规也。……今子能抑才以就格,完气以成调,几于纯矣。”〔35〕绕过一大圈却又回到原处,古人格调又成为其首要因素与终极标准。
王世贞徘徊于才情与格调法度之间,究竟欲以何者为主?他对此未作正面回答而采取“剂”之理论以求折衷:“夫辞不必尽废旧而能致新,格不必趋古而能无下,因遇见象,因意见法,巧不累体,豪不病韵,乃可言剂也。”〔36〕其主旨在于意融法中而不出法外,做到不法而法,不意而意;既要“有物有则”,又须“无臭无声”。可知“剂”非意与法之杂糅,而系浑然无迹之自然高古。故元美分诗文为三等:“情景妙合,风格自上,不为古役,不堕蹊径者,最也;随旨成分,随分成诣,门户既立,声实可观者,次也;或为闰继,实则盗魁,外堪皮相,中乃肤立;以此言家,久必败矣。”〔37〕如此言诗形似圆满无懈可击,细究则实非通论。既照顾才情又不背传统格调,虽言之成理,然行之颇艰,王世贞本人便感叹“庶几未之逮也,而窃有志焉”。究其原因,则“剂”之理论说到底仍为模仿理论之精致表现而已,其目的仍为“不孜孜求工于抵掌效颦之似,大较气完而辞畅,出之自才,止之自格,人不得大历而后名之”〔38〕。可见其理想境界依然为盛唐之格调,所谓“自才”、“自格”无非是熟玩古人诗法格调后,达到一种随心所欲而不逾古人之矩的程度而已。有时元美看似通达,然一遇格调问题便甚为审慎。如其晚年爱东坡诗文颇甚,赞叹“苏公才甚高,蓄甚博,而出之甚达而又甚易”〔39〕。然在其为朋友所选宋人诗集作序时,却又转而论曰:“余所以抑宋者,为惜格也。然而代不能废人,人不能废篇,篇不能废句。盖不止前数公而已。此语于格之外者也。今夫取食色之重者,与礼之轻者比,奚啻食色重。夫医师不以参苓而捐溲勃,大官不以八珍而捐胡禄障泥,为能盖用之也。虽然以彼为我则可,可我为彼则不可,子正非求为伸宋者也,将善用宋者也。”〔40〕不废宋诗而承认格为有文,自然较之汉以后无文、唐以后无诗的偏激之论更为圆融。然宋诗(自然包括苏轼的作品)充其量只可作为溲勃之类的辅佐,论正宗与主导仍须注目于盛唐。此处所言“以彼为我”之“我”决非自我之才情个性,而是“我”所持守之盛唐高格雅调。此可知王世贞直到晚年仍未放弃对格调的追求。没有真正从人生价值观上领悟到自我个性与才情之重要,便决不可能真正出现重作家主体性灵才情的文学思想。而造成后七子才情与格调之矛盾无法克服的根本原因,显然是其哲学人生观的陈旧。
通过对前后七子文学思想所存在的内在矛盾探讨,我们发现了他们在文学道路上的蹒跚步履,但从中似乎尚可引出两点有价值的结论:一是在步履蹒跚的“之”字形轨迹中,依然可见出文学思想正虽则缓慢却又无可挽回地向着突出自我个性才情的方向发展。前七子虽眷恋于雅正之理想却不能不表现出自我之凄凉真情,后七子虽仍醉心于格调法度却已较前七子更注重作家才情性灵的表现,都预示着晚明重性情重自我的文学思潮的来临。尽管前后七子的重主体性情的倾向还只是一叶不起眼的秋萍,却昭示着一个新时期的到来。二是要真正形成自我表现的文学思想,必须具备新的哲学人生观。后来的李贽、袁氏三兄弟、汤显祖诸人,之所以较前后七子更注重作家主体自我,乃是由于他们饱受王学的影响,以李贽的童心说作为其人生观的基础,从而形成了其自我愉悦的文学目的论、突出主观性灵的作家本体论、注重自然抒发的文学表现论及重情重趣的文学审美论这样系统的文学思想。前后七子不具备这样的哲学观人生观,形不成系统的重自我价值的文学思想,其内在矛盾自然是无法克服的。
注释:
〔1〕《空同先生集》,卷五十一,《熊士选诗序》。
〔2〕《空同先生集》,卷十九..《一代文人之盛兼寓祝望焉耳》。
〔3〕《对山文集》,卷四,《陕西壬午乡举同年会录序》。
〔4〕《空同先生集》附录。
〔5〕《空同先生集》,卷四十七,《潜虬山人记》。
〔6〕《怀麓堂诗话》。
〔7〕《四溟诗话》,卷一。
〔8〕〔30〕《弇州山人四部稿》,卷六十五, 《徐汝思诗集序》。
〔9〕《空同先生集》,卷六十二。
〔10〕《空同先生集》,卷四十《大梁书院田碑》。
〔11〕《空同先生集》,卷十,《杂诗》三十二首其十三。
〔12〕《空同先生集》,卷六。
〔13〕《空同先生集》,卷二十八,《秋雨夜起》。
〔14〕《空同先生集》,卷二十七,《深秋独夜》。
〔15〕《空同先生集》,卷五十八,《朝正倡和诗跋》。
〔16〕《空同先生集》,卷五十。
〔17〕《空同先生集》,卷五。
〔18〕《空同先生集》,卷二十二。
〔19〕《空同先生集》,卷二十三。
〔20〕《沧溟先生集》,卷十六,《送宗子相序》。
〔21〕《弇州山人四部稿》,卷六十七,《古今诗删序》。
〔22〕《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七十一,《王氏金虎集序》。
〔23〕《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三十二,《自嘲》。
〔24〕《沧溟先生集》,卷六,《寄元美》。
〔25〕《宗子相集》,卷四,《李郎中攀龙》。
〔26〕《四溟诗话》,卷一。
〔27〕《沧溟先生集》,卷十六,《送王元美序》。
〔28〕王世懋:《艺圃撷余》。
〔29〕《沧溟先生集》,卷二十五,《王氏存笥稿跋》。
〔31〕《四溟诗话》,卷四。
〔32〕《艺苑卮言》。
〔33〕《弇州山人续稿》,卷二○○,《屠长卿》廿二札其一。
〔34〕《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一二一,《沈嘉则诗选序》。
〔35〕《弇州山人续稿》,卷四十,《沈嘉则诗选序》。
〔36〕《弇州山人四部稿》,卷六十八,《黄淳父集序》。
〔37〕《艺苑卮言》,卷五。
〔38〕《弇州山人续稿》,卷四十五,《方鸿胪息机堂集序》。
〔39〕《弇州山人续稿》,卷四十二,《苏长公外纪序》。
〔40〕《弇州山人续稿》,卷四十一,《宋诗选序》。
标签:李梦阳论文; 文学论文; 弘治中兴论文; 弇州山人四部稿论文; 艺术论文; 文化论文; 读书论文; 四溟诗话论文; 艺苑卮言论文; 复古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