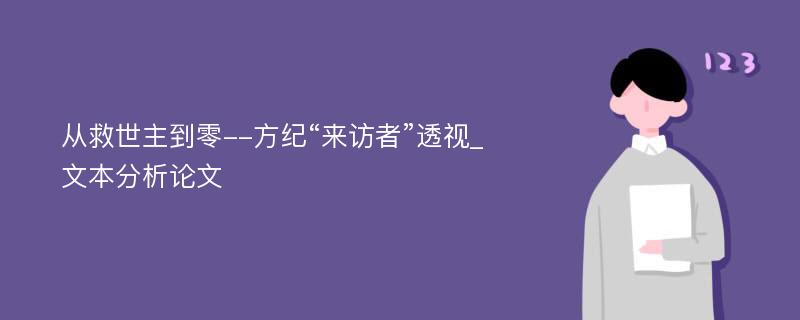
从拯救者到零余者——方纪《来访者》透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来访者论文,透视论文,者到零余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57年岁末,方纪写毕《来访者》。小说讲述了青年知识者康敏夫因无力承受与一位女艺人情感的聚合离散遂自虐自戕的故事。无论从哪个角度看,这篇后来发表于《收获》杂志上的小说都是“十七年文学”中的一个异数:倘若将彼时创作的情感基调比拟为明朗阳光普照,那么《来访者》则酷似徘徊于明暗之间的一个幽魂①。彼时主流题材在“工农兵”的一统领地里高歌猛进、乐不思出,《来访者》却遁入了“右派”题材的无底洞;彼时文学“正典”业已轻车熟路于“革命现实主义”的单向度历史叙事中,《来访者》却有意无意地逸出此种创作方法的路标,衍射出陀斯妥耶夫斯基式的复调论辩光芒。因此种种的独异意味,笔者特将《来访者》从“十七年文学”的泛论中抽离出来,凭藉文本细读,烛照彼时知识分子叙事那层层幽邃的暗影。
一、拯救者?沦落人?
《来访者》开篇,青年知识者康敏夫与唱大鼓的女艺人偶然邂逅,同坠爱河。令人不禁遥忆起上世纪30年代张恨水《啼笑因缘》中樊家树与沈凤喜的相知相恋。男主人公同是大学生,女主人公同为唱大鼓的民间女艺人,二作的人物身份何其相似。不止是人物身份契合,由此漾开的一个名谓“拯救”的母题竟也远隔新旧时代而暗然相通:《啼笑因缘》中的“拯救”彰显于外且贯穿文本始终,樊家树一心要将被逼为妾的沈凤喜从苦海中拯救出来,终因力不从心而长恨绵绵②;《来访者》中的“拯救”情节同样贯穿文本却显得波折横生,暧昧交错。文本伊始,康敏夫自觉充当了将女艺人从其封建继母编织的精神牢笼里拯救出来的角色,然而随着情节推进,女艺人逐渐悟出自己已“是工人阶级”,自我才是真正的拯救者;不仅如此,知识者康敏夫反而身陷“个人主义”泥潭且不能自拔,最终被送至劳教,俨然成为需要众人拯救的沦落人。因拯救者角色置换而引发的吊诡在此发人深省。
《来访者》中究竟谁是拯救者?这一看似无足轻重的发问,拈连出时代对阶级定位的沧桑变迁。在某种程度上,启蒙与拯救是一巢之雀,《啼笑因缘》诞生的30年代,知识分子启蒙的火种方兴未艾,尽管樊家树最终陷于失败,似乎喻示着拯救力量的势单力薄,但知识分子是拯救者这一阶级定位毋庸置疑。时至新中国、新时代,尤其是1957年以后,知识分子陡然从高高在上的启蒙者精英地位坠落,沦为需要向工农兵学习、被工农兵改造的“被拯救者”。此点经由“反右”运动(“右派分子”均系知识分子),俨然已成彼时社会共识。
值得关注的是,康敏夫情感支配地位的由强转弱,拯救角色的由施予转为乞求几乎于一个瞬间完成,它源自一次与女艺人眼睛的“对读”:“那是怎样的眼睛呵!坦白,深沉,像往常一样;但是我完全不认识了,是那样的坚强,有力”;“而我,在她的眼里,是那样渺小,可怜,微不足道”。一个曾经最熟悉的爱人突然变得陌生,这被加缪视为本体论意义上的世界的荒谬。在《来访者》里,作者无意关注情感“陌生化”的丰富性,而旨在凸现“陌生化”内蕴的明晰性:先前,知识者的精神强大与女艺人的柔弱可怜不过是虚幻假相;随着个体精神的不断敞开,康敏夫体内的种种属于所谓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脆弱与神经质肆意膨胀,而女艺人体内的那种无产阶级血液的健康性终于流溢而出。由此体现出的阶级属性与精神气质的捆绑、辨证,可谓是“十七年文学”文本的一个通例。然而,作为个案的是,《来访者》并未开门见山地昭示康敏夫的被拯救角色,而是让他一直携带着昔日樊家树的影子,行文过半,才将“拯救者”的假像蜕变为“被拯救者”的真身。
作者对“被拯救者”身份的定义何故一再犹豫?或许这份犹豫恰恰透露出作者内心深处挥之不去的知识者情结,心底仍然惯性地共振着“五四”以来中国知识分子作为民众的启蒙者、拯救者的强劲心跳,却不得不猛醒于“反右”运动对于知识分子的意识形态棒喝。因此,瞬间置换的断裂感似乎昭示着律令意识尚未沉潜为作者的下意识——《来访者》其实是心向五四,被名曰“反右”的飓风刮得一步步退至时代所设定的知识分子主动接受“改造”的“必由之途”,由此呈现出的角色置换的纠葛与延宕也就不言而喻。
二、零余者
倘若将《来访者》里的康敏夫置于文学史人物形象的长河中,不难发觉他与“零余者”的血脉相承。早在20年代,郁达夫便已完成了“零余者”人物谱系。康敏夫情感的炽烈、神经的过敏、肉身的孱弱自是郁氏《沉沦》一类小说中“我”、于质夫形象的移形;其在社会面前的孤傲、孤冷及至碰壁,亦显然承袭了“零余者”的性格与宿命。然而,笔者想要深究的是,置身于不同的时代语境,“零余者”内在意义所发生的变异。
零余者又名“多余的人”,游离于社会之外,于社会“无用”是他们的共性。然而在西方现代文化语境中,个体于社会的“有用”、“无用”却并非价值取向褒贬绝对的两极。福科曾论及整个现代社会机制如同一个庞大的理性机器,个体的“有用”对社会而言就是成为机器的“齿轮”,与之周而复始的运行③。马尔库塞也一再地谈到个体融入现代社会的过程是一个或多或少的心灵“异化”过程④——二者均批判了个体削去自身灵性,沦为社会“工具理性”一类的“有用”。值得关注的是,彼时意识形态对“有用”、“无用”的价值取向在某种向度上恰恰是反“西化”语境的:时代车轮滚滚前行,一切个体毋庸置疑应该甘为社会机器的“齿轮”“螺丝钉”,伴随着列车“有用”地前行;倘有个体跳离列车,在明示自己“无用”的同时即宣判了自身违逆社会的反动身份。
言及20年代“零余者”产生的原因时,时论无一例外地将其化约为“时代病”,由是折射出生成忧郁症的社会母体。倘若说郁达夫创作零余者们的意义尚可用折射旧时代本身的病态做辩护,那么,方纪塑造新时代的零余者之举则难免被视为“居心叵测”,因其不自觉间影射了时代的病症。尽管方纪叙写康敏夫不证自明是新时代无可容忍的敌人——“我自杀了两次——这在你看来等于犯罪,不是吗?”在康敏夫的自述前,分明已兀立着跳离社会列车的自杀行径等同于敌人犯罪的主流意识形态镜像。《来访者》将拯救者与零余者捆绑一处意味着作者对时代先兆的敏感:如果说旧时代的知识分子尚可在社会中心振臂高呼“拯救”,或于时代精神领地的边缘位置徘徊,那么,此刻等待他们的则是被彻底地从精神领地放逐出境。
三、阶级意识?女性意识?
论及《来访者》,明尼苏达大学的学者戴克却另辟蹊径,分外关注康敏夫的男性知识者身份,其婚恋情变的故事亦生成了她女性主义的批评演绎。置于女性主义批评视阈,我们自然可对文本作如下解读:康敏夫与女艺人的情爱控制力是一个此消彼长的过程,女艺人自我精神力的渐次强大,意味着其女性独立意识的觉醒与萌生;她的娜拉式出走既未受挫也无回归,注释着新时代的女性已然提升地位,可以无需男性接济而独立生活了。戴克在分析《来访者》时,则指出小说中康敏夫“男性叙述者忏悔的口气、回顾的姿态听来或看来也许动人,却可能是种廉价的救赎手段”,以解脱他的不义⑤。论文词锋犀利,直捣男权阵营。
然而细读文本,不难发觉女艺人出走前后判若两人:此前是温文尔雅弱女子,此后是言行铿锵女强人,于电光石火的瞬间蜕变完成,节奏之快恰似魔剧院中的“变脸”。然而它果真缘于女性独立意识的觉醒?试将焦点对准出走后的女艺人:果断的举动,坚定的语气,个体情感的收敛,外形内核分明叠印着彼时文学中的女革命者的影像。反观出走前的女艺人对男性拯救的期盼,不由让人联想到同时期小说《青春之歌》里那个刚出场时稚气未褪、天真柔弱的林道静。在某种程度上,《来访者》也规划出一条女艺人的“成长”轨迹,只是她的成长并未历经林道静式的漫漫长路,而是在作者瞬间的拟想中得以实现。昔日未经世事的女艺人成长为工人阶级的女斗士,应归结为她的阶级身份的自觉而非性别意识的萌生。同理,促成其从小家庭中“出走”的缘由,与其说是因着“女性独立意识的觉醒”,不如说缘于其无产阶级意识的被时代激活,缘于其对新社会以集体生活为能事的“革命大家庭”的向往。
戴克的女性主义批评将性别作为“焦点”的同时,往往形成了其他身份的“盲点”。对于阶级意识至上、性别意识淡化(所谓“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的“十七年文学”文本,使用纯粹女性主义的批评策略难免喧宾夺主。
四、“右派分子”的精神剪影
小说一开始,身为“党委机关”干部的“我”初会“来访者”康敏夫,就不无“警惕”地将其与右派分子联系在一起:“要知道,这事发生在今年六月初。正在‘大鸣大放’,右派分子猖狂进攻,反右派斗争还没有开始的时候。”——“我”的第一印象既属感觉的“过敏”,更是理念的预设;尽管连彼时批判《来访者》的文章都觉得这种联系“十分生硬”⑥,但作者显然出于配合时政的需要(亦未尝不隐含为笔下的知识者叙事、抒情赢得某种合法性的动机),及至结尾,还是让“我”最终不证自明地看穿了其“右派”精神面目:“他和那些右派分子,在精神上,是那么相像。他生活的目的,只为了他自己;一切美好的,有用的,他都要占有;他损害别人,满足自己;占有别人的心,并把人毁灭掉!”
回溯文学史中的右派题材,张贤亮的著作颇引人注目,《灵与肉》、《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在将“右派分子”的肉体受难与精神苦刑刻画得灵肉毕现。值得注意的是,文学创作中多写“右派”被打入另册、送至劳动教养后的经历,且每每极度清晰、细致;却鲜有描述其之所以被划成“右派”的言行,偶有触及也语焉不详、失之含混。恰如《来访者》中的康敏夫,作者殚精竭虑,却欲加之罪,徒患无辞:写其取名康敏夫——共产者,“在20年代到30年代,这多半是些拿革命玩票的公子哥儿式冒充的虚无主义者”;写其眼神“闪出那种像磷火一样的绿色的光”(无奈之际竟然袭用了鲁迅状写“孤独者”魏连殳的笔意)……如果不是最终赖有反右派斗争的“照妖镜”将其罩定,那么,作者心目中的康敏夫始终“就像一个影子,一个幽灵,飘飘荡荡”。是的,作者连同那个时代正是凭藉了不无过敏的“妖魔化”的政治想象,才抽象出了康敏夫面目不清、行踪飘忽、难以坐实、无可赋形的“右派分子”精神剪影。
方纪所以没有“写实”,而选择了写意,一方面透露了所谓“右派分子”罪状的莫须有;另一方面恰恰折射出发动这场运动的隐秘心理:康敏夫个人意识强烈,心理“阴暗”,身为知识分子的他竟然不自量力想当“工人阶级”(女艺人自谓)生活道路的导引者,岂有如此之理?
五、主流意识形态叙事与知识分子叙事
《来访者》文本呈现在外的是一个嵌套式叙事结构。“党委机关”干部“我”是全文(或谓故事外)的叙述主体,康敏夫则以客体的身份在“我”的叙述、思索、评判中踽踽独行。而在“来访者”的回忆、陈述中,康敏夫又转换为嵌套在故事内的叙述主体,他不时地猜测、揣度作为客体的“我”的价值判断,不时地向“我”“出于职务关系”养成的冷默挑衅:“你明白吗?”“你不要总是对我摇头吧!”“你不要笑!”“对我的不幸,一点也不同情?”挥之不去的屏障与隔膜始终横亘在他们对彼此的读解中。康敏夫的主体叙述,时刻敏感着“我”的立场的无情;“我”在片刻感动于康敏夫的推心置腹后,最终还是理念先行,将他归属为第一感觉中的“右派”典型。对方始终以“他者”的身份出现在彼此的读解里,透露出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与个人话语先在的沟通困境。
值得关注的是,在各自的主体叙述中,康敏夫与“我”都最大程度地敞开了彼此的“声音”,在主体声音强劲驰骋的话语声场里,作为主体的聆听者的“我”与作为被言说的康敏夫时刻“在场”,蛰伏在话语声场的幽深处。嵌套式结构形成的双叙述主体,以及客体与主体的潜在“对话”,有意无意地衍射出陀斯妥耶夫斯基小说式的复调光芒。联系前文言及的方纪内心深处未泯的知识分子情结,似可推断出作者在执守主流意识形态立场、话语、视角时,无意中分身为二,难能可贵地保留了知识分子叙事的视角。
因此,在双重视角与复调结构的统摄下,形成了“我”与康敏夫在文本中的平等叙事地位。代表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我”的误读、误判并不全然构成对康敏夫“声音”的抹杀,而是形成了文本内部的对峙与论辩、挑战与妥协。耐人寻味的是,因着文本的复调特性,话语的交锋并未构成彼此的削弱,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彼此补充、彼此增强,共同丰富、拓展了文本的意蕴及张力。
对于这场文本内部的权利场竞逐,两种话语未可轻言谁胜谁负。且看下列情节:“我”听完康敏夫梦魇般的经历,“感到又激动又疲倦,像做了一个不祥的梦”,此刻的内心悬置于一种混沌且真实的敞开状态,它意味着先在的种种偏见与理念预设暂且被温情浸润,一种源自人性的强音触动了“我”的心魂。此后,强音逐渐消散终至细不可闻,“我”对康敏夫的态度转了一大圈,重归原点:认定他是“右派”典型。个中缘由我们可在文本的蛛丝马迹中依稀见出:“完全女人见识,就是不会从政治上看问题。”“反右派斗争越深入,这个人的面目,在我心里就越清楚了。”——“我”的评价态度昭然若揭,政治意识形态是“我”评价某个人的最高价值标准,“我”并非做事轻率、了无情感,而是将一切情感的、感觉的因素都让位给了前者。因此,置于政治意识形态立场,“我”的强势声音完全能压过康;倘若依照情感、人性的价值取向,“我”则无疑落在了复调话语论辩的弱势地位。
这在文末尤为明显:爱子心切的康敏夫,要求看看他与女艺人所生的孩子,女干部一时“心软”,应允了;未料康要带走孩子,争夺中,孩子母亲给了他一耳光。这样的结局赢得了“我”与“管文艺工作”的女同志的轻松一笑。缘于故事外讲述者“我”“用带有他自己的偏见和个人利益的扭曲了的看法来观察和评价他自己的动机以及其他人物的动机和行为”,此处便造成了艾布拉姆斯所谓的文本的“结构反讽”:两位干部如释重负的胜利者欢笑,不仅难以让读者随之莞尔、轻松释然,相反,那笑声反衬了康敏夫欲哭无泪的沉重感,形成了喜剧外形、悲剧内核的反讽效果。
对于“十七年文学”的研究,至今仍未彻底摆脱失之简化的泛政治话语评判,至今犹缺乏深刻细致的文化透视与审美阐释。其实,“十七年文学”文本中,政治意识形态并非总像某些研究者们臆想的那样压倒了一切,其与文学审美之间多有抵牾撕扯、相悖相克,同时却亦促成了某种潜隐暧昧的思想内涵、形式内蕴相衍相生。后者构成了“十七年文学”的“潜文本”⑦。
如上所述,笔者运用散点透视的方式读解十七年期间公开发表的小说《来访者》,本意并不限于对这一久为历史尘灰蒙蔽之作的打捞拾遗;而恰是试图“以文为孔”,触探、穿透“十七年文学”中那些幽冥深邃的视景、盲区。笔者发现,因着作者创作心态的矛盾游离、笔下人物性格的多重混血、小说主题与二三十年代故事原型的呼应质诘、叙述主体与客体的复调论辩——有意无意间改写了作者源于彼时主流意识形态的既定创作意图,令小说平添出何其复杂、何其深长的文化意味与审美意味。
注释:
①方纪:《来访者》,刊于《收获》1958年第3期。如果说,英国情报部门所编刊物《苦果》收入社会主义中国两篇半作品,其中一篇便是《来访者》,尚可视为出于不无偏至的西方政治动机,那么,此小说为观点相对平正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瞩目,则足以印证其引人思辨的文学史意义。
②张恨水:《啼笑因缘》,上海三友书社,1930年版。
③米歇尔·福科:《什么是启蒙?》,收入汪晖、陈燕谷主编《文化与公共性》,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427页。
④参阅赫伯特·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版,第11~12页。
⑤转引自王德威《想像中国的方法》,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367页。
⑥罗荪:《“来访者”是一篇对新社会的“控诉书”》,《收获》1958年第4期,第314页。
⑦“潜文本”说参阅程光炜《文学想像与文学国家》,河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7~2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