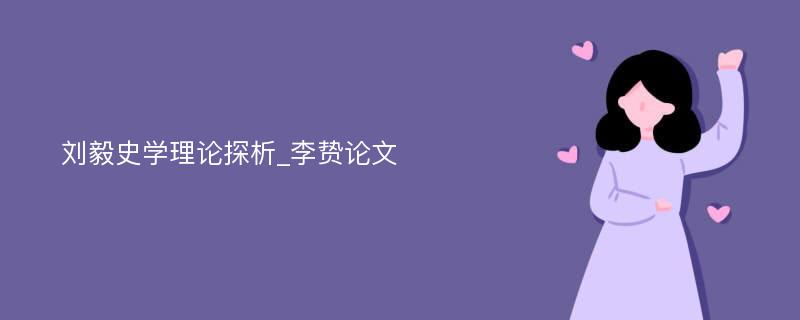
李贽史论评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论论文,李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摘要 本文从史学思想史的角度,对李贽的历史评论著作进行了较为全面系统的分析和述评,认为他不仅是思想家和哲学家的代表人物,也是明代中后期著名的史学家,他把社会批判的思想融入史学领域,开辟了利用历史编纂与评论来全面表达政治见解的新思路,有其重要的史学意义。
关键词 史学思想、经史相为表里、历史批判精神
自1905年,《国粹学报》重印《焚书·序》,并刊载了刘师培为之撰写的“激进派第一人”的评论开始,一个曾遭诋毁而归于沉寂三百余年的李贽,又重新伴随着反清爱国运动呼声的高涨响彻历史论坛。人们没有忘记,当十六世纪中国封建社会步入由盛转衰之年,曾经是这位不屈于封建专制淫威的“叛逆者”,口诛笔伐,犀利陈言,淋漓尽致地痛砭时弊,抨击延续了千百年之久的封建礼教对人性的压抑和摧残;人们更没有忘记,在一场新的文化启蒙运动同二十世纪一起到来之际,重印这位进步思想家的著作序言,对于唤起民众向封建势力作最后的一击所赋予的特殊意义。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历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们对这位曾占据昔日论坛的思想先驱,由最初含有的鼓舞战斗激情的时代特征,转入到现代科学意义的冷静思考和全面评价。作为政治思想家来说,李贽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启蒙进步作用,迄今为人们所认同;作为哲学家,他在辩证思维方面的杰出成就也为人们所肯定。本文要说明的是,李贽与明代中后期史学的关系,即他的历史评论对明季史学的影响,这是尚待深入研究的问题。应该看到,李贽的史论是明代史学的重要组成,其原因不仅因为他的历史评论占其著述中之大成,而且就史学思想性方面的成就来说,它上承两宋时期的“鉴古资治”之道,下开明末清初的“经世致用”之先,将社会批判的思想引入到史学领域,实现了社会观与历史观的有机结合,对于明季后史学思想的发展与嬗变是有直接影响的。
一、李贽史论的发议原则
李贽(1527—1602年),号卓吾,别号温陵居士,明福建泉州府晋江县人。二十六岁中举,未赴京会试,选授教谕,后转他职。五十一岁时官至云南姚安府知府。二十余年的为官生涯使他认识到社会现实的虚伪、丑恶与黑暗,不愿同流合污;五十四岁时毅然辞官,避居深山,阅《藏经》不出。晚年著书讲学,对位于当时统治思想的程朱理学极力批判,由此触怒封建统治势力,屡遭迫害,最后死于狱中。李贽作为封建后期著名的思想家,是反对封建专制思想的重要人物。就学术传承渊源上说,他在思想上受着王阳明学说的影响,但更直接地是继承了泰州学派王艮(心斋)、何心隐的思想传统。侯外先生在《中国思想通史》第四卷中这样说道:“在明末的社会矛盾激烈化的时代,泰州学派的后起之秀李贽继承了泰州学派王艮、何心隐的思想传统,并进一步予以发展,从而建立了反道学的思想体系。”因此,李贽的史论同其它著作一样,无疑成为揭露封建黑暗统治的真实记录。
李贽史论的代表作有《藏书》68卷,《续藏书》27卷。《藏书》上起战国,下迄于元,涉及八百余重要历史人物,各采辑史实,编为纪传;纪传之中又各立名目,系以叙论。《续藏书》专录明代万历前之史实,辑录六百余人的传纪而成。从编撰体例上看,二书合并,即为一部贯通古今的纪传体评论。此外,李贽还在《焚书》的“杂述”、“读史”和《续焚书》的“论汇”、“读史汇”等篇,以及其它一些论著、书札和文集里,也穿插有对历史的评述与见解。
李贽史论的发议原则,与他的反传统的社会批判论有密切联系。从思想史的意义考察,李贽颇具影响的论述是提出了痛斥虚伪、褒扬纯真的“童心说”,以及社会上崇尚功利的主张,这与传统的所谓“义理”的说教形成尖锐的对立,成为其反对封建专制理论的核心内容,与此相承的史论,自然引发出了他的历史价值观,而具体内容则充分体现在对王朝更迭、历史进程、人物评价、史书编纂等方面的认识上。
关于李贽社会批判思想的研究,学术界已有较系统的评说,兹不赘述。但要补充的是,由于“童心说”与崇尚功利的主张,实为同一思想的两个方面,前者是从理性思维的角度考虑,后者是由社会存在的前提出发,就历史观而言,二者结合即成为否定传统史书编纂中的义例说及正统论的依据。因此,可以这样说,任何思想家的政治主张都不是孤立的,其对社会现实的态度也包含有对既往过去的反省。为发挥其社会批判的功能,需要对历史的进程按自己的理论构架作出解释。这样,李贽的史论与一般的史书已有明显不同,他不是为历史纪实去秉笔,而是为阐明其历史见解来发议;他不是要以史学家的地位名垂于史,而是欲借助史论作为申明其政治主张和社会思想的工具。由此,李贽史论的发议原则自然贯穿着历史批判的精神。
二、李贽史论的史学意义
李贽作为封建时代的进步思想家、史学家,他的史论集中体现了其史学思想,即在治史目的、识史原理、评史标准、撰史方法上,显示出一种不同于前人的新思路。
(1)、治史目的:“经史相为表里”与“治贵适时, 学必经世”说
李贽治史的目的,不是为学术而学术,实为阐明其政治主张,为社会现实服务。他对这一点极不含糊,曾直言不讳地称《明灯道古录》、《藏书》等为“万世治平之书”〔1〕,并在“经史相为表里”〔2〕一文中,充分表达了该思想。
经、史一物也。史而不经,则为秽史矣,何以垂戒鉴乎?经而不史,则为说白话矣,何以彰事实乎?故《春秋》一经,春秋一时之史也。《诗经》、《书经》,二帝三王以来之史也。而《易经》则又示人以经之所从出,史之所从来,为道屡迁,变易匪常,不可以一定执也。故谓六经皆史可也。
关于经与史的关系前人已有评说。南宋吕祖谦即已提出“观史先自书始”,明代的王阳明、王世贞也都论及过。《传习录》记载:王阳明答复其学生关于“先儒论《六经》以《春秋》为史,史专记事,恐与《五经》事体终或稍异”的提问时说:“以事言为之史,以道言为之经。事即道。《春秋》亦经,《五经》亦史。”其意思是说,史与经是从不同的角度看,以事的角度可说是史,以道的角度可称为经。在这里,王阳明只是说明《五经》可以称史,但没否定其经的地位,相反他还强调了被先儒怀疑为不是经的《春秋》也是经。《续藏书·尚书王公传》云:王世贞说:“《六经》,史之言理者也。”《纲鉴会纂·序》又称:“史学之在今日倍急于经,而不可以一日而去者也,故曰君子贵读史。”其言史急于经,是从二者对比的角度上说的,故就经与史的意义上看,关系仍有区别。李贽的“六经皆史”论述,可谓前进了一步,他称经与史是“相力表里”的;表彰经义,里衬内容,这实际上已有将逻辑的抽象与历史的具体结合的含义,进一步剖析可表述如次:第一,经与史有分别,又无分别,不可以一定执也。第二,经重在“义”,史重在“鉴”,经史相互为同;“史”而“经”,达经义,“经”而“史”,经“义”得彰。第三,经有一时之史,有二帝三王以来之史;《易》探讨了经与史的关系,揭示了经与史的由来,说明了世事上“为道屡迁,变易匪常”的道理;第四,“经”非尊崇,“六经皆史”。社会在发展进步,评史的标准也须之变化,不能固定在一种模式上,这就是“不可以一定执也”的深刻含义。李贽以“经史一物”为出发点,气现实与历史紧密结合,通过治史修书阐述其社会观点,达到评史与论政的统一,为现实政治服务。很显然,这一思想的理论价值就在于将封建时代至高无上的神圣“经典”,还本为社会中人的活动的史实载体,这对史学批评史的发展具有各级的意义。李贽的这种见解,是针对宋明以来社会时尚那种流于空疏的学风而民,他鄙视儒生读书只会背诵程朱注解,誊录经典片断章句,依仿陈言规迹往事,整天高谈空疏无用,对社会实际毫无补益的“义理”、“性命”之类的废话,置“四海穷困”于不顾。他特举宋时南迁、国难当头之际,程朱理学的伪君子无一条转危为安、富国强兵之策,仅以正心城意之论劝人主去内侍中之小人的烩措加以嘲讽,并与之相对地提出“治贵适时,学必经世”的主张〔3〕,提倡面对现实,因时而为,有用于社会。
怎样才能有用于社会呢?李贽发挥了泰州学派王艮的“百姓日用”之学与何心隐的“与百姓同欲”的主张〔4〕,他的“经世经”,也自然先从人们最平常的日用之需开始。《焚书·答邓石阳》说:
穿衣吃饭,即是人格物理,除却穿衣吃饭,无伦物矣。世间种种,皆衣与饭类耳。故举衣与饭,而世间种种自然在其中。非衣饭之外,更有所谓种种绝与百姓不相同者也。
对此又在同书《杂说·兵食论》中说:
至矣!圣人鼓舞万民之术也。盖可使之由者同井之田,而不可使之知者则六艺之精,孝弟忠信之行也。
这就明确指出,人的物质生活物质利益,是首先要正视和解决的问题,它不仅是人的自然属性,也是社会发展的原本动力。任何朝代的统治者,都应以满足于下百姓的穿衣吃饭、治生产业愿望为首任;要关心人民疾苦,关心社会的生产的生活,而不是违背这些基本道理,却让人们去顺从统治者的利益和愿望,遵循什么礼义和教化。因此,李贽认为,重视人的社会生产和生活的价值功能,以恤民体民的下策为保障,将这些原则贯穿到社会历史领域,作为考究时代进步与否的参照,就是典型的“经世”之论。依据此理,学以致用,贵在裙带,是李贽价值取向的判别准则,他的史论也反映出这种思想;用他自己的话说:其“万世治平之书”为“欲讲修、齐、治、平之学者,则不可一日不呈于目”〔5〕的。晚明兴起的一股反省既往,旨在拯救危机的实学思潮,具有鲜明的“黜虚”色彩,天下学者多“务求实用”〔6〕,学术风气的转变对明季史学产生的积极影响是不言自喻的。但是,也要指出,李贽居于“王学”学脉之上,他与泰州学派有其相似的一点即援儒入佛的思想,从而认为出世入世都是道。因此,他的“经世之论”又间杂有出世的因素,这在其晚年的思想中多有体现。
⑵、识史原理:“也世推移,其道必尔”与“质文递变”的历史发展观
李贽依据自己的“经世”原则,将其用于考察社会历史的发展过程,他在《战国论》中说:
夫春秋之后为战国,既为战国之时,则自有战国之策。盖与世推移,其道必尔。如此者非可以春秋之治治之也明矣。况三王之世欤?〔7〕
李贽肯定春秋代替“三王”,战国代替春秋是历史的必然,并认为历史的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对于历史的进程,李贽在《藏书》卷首的《世纪总论》中阐述了其看法。
一治一乱若循环。自战国以来,不知凡几治几乱矣。方其乱也,得保首领,已为幸矣。幸而治,则一饱而足,更不知其为粗粝也;一睡为安,更不知其是广厦也。此其极质极野无文之时也。非好野也,其势不得不。虽至于质之极,而不自知也。迨子若孙,则异是矣。耳不闻金鼓之声,足不履得阵之险,惟知安饱是适而已,则其势不极文固不止也。所谓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必巨,虽神圣在上,不能反之于质与也。然文极而天下之乱复起矣。英雄并生,逐鹿不已,虽圣人亦顺之尔。者乃以忠质文并言,不知何说;又谓以忠易质,以质捄文,是尤不根之甚矣。夫人生斯世,惟是质文两者;两者之生,原于治乱,其质也。乱之终而治之始也,乃其中心之不得不质者也。非矫也,其积渐而至于文也,治之极而乱之兆也,乃其中心之不能不文者也。皆忠也……群雄未死,则祸乱不息;乱离未甚,则神圣不生。一文一质,一治一乱,于斯见矣。
这是一段体现李贽识史原理的评论,认为历史是按“一文一质,一治一乱”的相互交替发展的。所谓“文”,就是社会历史的鼎盛期,它的出现是由于新王朝鉴于前朝的统治经验,伴随着开业君主的励精图治而来,这就是“治”。所谓“质”,就是历史发展的衰落期,它的出现又是由于王朝统治者面对社会的繁荣,不思进取,穷奢极侈,民不聊生,激起反抗,“英雄并生,逐鹿不已”,终至丧失天下,这就是“乱”。对此,虽“神圣在上”,亦无能为力,只得顺应其势。李贽在总论中特举秦时,“其文极矣”;汉兴,“天子不能具钧驷”,至武帝时“陈陈相因,贯朽粟腐”的史实,来证明历史的这种盛衰起伏的进程。
李贽所言的文质交替,治乱相生,是对以往历史的总结性论述,也是对司马迁“见盛观衰”原则的继承性应用。可以明显看出,李贽将朝代更换的砂因归结为社会的力量;是人的因素,确实看到了问题的所在,这与他的重视社会环境中人的作用的一贯性主张极为吻合,表明其历史发展观已含有“时势造英雄”的相互思想,同时,这也是对前代以来的“三统”、“三正”论,即将朝代的更替附会为“天意”的说法的有力批判。另外,李贽还认识到统治阶级的“极文”引起人民的反抗,乃致天下大乱,这也与他的恤民主张有密切的联系。
李贽在重视社会历史发展中人的因素的同时, 曾体察到有一种不可替代之势在支配社会的运行,即为“天道”。对人事而言的文质顺势为者谓之强,其中充满着竞争和淘汰的际遇。他在《李氏文集》卷19《明杰道古录》一文说:
夫栽培倾覆,天必因材,而况于人乎?强弱众寡,其材定矣。强者, 弱之归,不归必并之;众者,寡之附,不附即吞之。此天道也,虽圣人其能违天乎哉?
李贽将物竞天择的原则用于人世间,肯定了所存在的历史发展有一定的趋势,即能者为尊、强者混一的这样一条规律,特别是当社会处于治乱交替之时,最容易“英雄并生”。他在论述此方面最能体现顺应“天道”之为的强人时,尤赞管仲,称春秋时“五霸迭兴,更相雄长,夹辅王室,以藩屏周”的功劳,实由“管仲相醒所谓首任其事也。”〔8〕“天道”与人事的结合,是李贽历史发展观的重要认识;因时而为,发挥才能,则是这一思想的实质内容,这对于他的评论历史人物的是非衡准,无疑具有着指导性的意义。
(3)、评史标准:不“践迹”、“执一”的传统观念大胆予以否定,提出“不蹈故袭,不践往迹”〔9〕,“不执一说便可通行,不定死法便足活世”〔10〕的主张,并以此提出品评历史是
非的衡准。他在写《藏书》时曾说:
山中寂寞无侣,时时取史册披阅,得与其人会觌,亦志快乐。非谓有志于博学宏词科也。尝谓载籍所称,不但赫然可纪述于后者是大圣人;纵遗臭万年,绝无足录,其精神巧思,亦能令人心羡。况真正圣贤,不免被人细摘;或以浮名传颂,而其实索然,自古至今,多少冤屈,谁与辨雪!故读史时真如与百千万人作对敌,一经对垒,自然献俘授首,殊有绝致,未易告语。〔11〕
李贽修史的目的至为明显,并非“有志于博学宏词”,而拟“与百千万人作对敌”,即要为传统观念定性的历史冤案平反。对于是非品评的标准,他在《藏书世纪列传总目前论》中作了明确阐述:就原则而言,则“今日之是非,谓予李卓吾一人之是非”为准;就时代划分,又是针对“后三代,汉、唐、宋是也。”因为此间千百余年,“咸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故未尝有是非耳。”这样,李贽提出的新的是非观自然具有了“颠倒千万世之是非,而复非是予之所非是焉”的气魄。
李贽是非标准的总体原则是体民情,尚功用,重才智,非说教。确切地表述就是:人或一切事物的存在价值,只有通过是否有用于社会这把标尺来衡量,社会功能是检验人间是非原则的衡准,以此为据,他在《藏书·世纪列传总目后论》中阐述了这一观点。
圣主不世出,贤主不恒有。若皆如汉祖孝文孝武之神圣、孝昭孝宣之贤明,则又何患乎其无臣也。惟圣主难逢而贤主亦难遇,然后大臣之道斯为美矣。故传大臣。大臣之道非一,有因时而若无能者,有忍辱而若自污者,有结主而若媚,有容人而若愚,有忠诚而若可欺以罔者;随其资之所及,极其力之所造,皆可以辅危乱而致太平。如诸葛孔明之辅刘禅,可以观矣。非谓必兼全五者,而后足当大臣之名也。大臣又不可得,于是又思其次,其次则名臣是已。故传名臣。夫大臣之难遘,亦犹圣主之难遭也。倘得名臣以辅之,亦可以辅幼弱而致富强。然名臣未心知学而实自有学,自儒者出而求志达道之学兴矣。故传儒臣。儒臣虽名为学而实不知学,往往学步失故,践迹而不能造其域。卒为名臣所嗤笑也。自儒者以文学名为儒,故用武者遂以不文名为武,而文武从此分矣。故传武臣。夫圣主之王也,居为后先疏附,出为奔走御侮,曷有二也。……武臣之兴,起于危乱。危乱之来,由于嬖臣。故传亲臣,传近臣,传外臣。外臣者,隐处之臣也。天下乱则贤人隐,故以外臣终焉。
这段议论紧系世纪列传总目而发,表明了篇中涉及的八百余历史人物分类的标准和排比先后的依据,而通过总体上的排列顺序,又体现出作者褒贬毁誉的是非原则。可以看出,自“世纪”之后,各臣的排比是视其辅君位置的重要程度而论,含有是否有用于社会的检验因素。君主之下列大臣,是由于“大臣之道非一”,尚可“随其资之所及,极其力之所造,皆可以辅危乱而致太平。”这无疑寄寓有个人才能于其中的作用。大臣之下列名臣,是名臣“亦可以辅幼弱而致富强,其地位几乎与大臣等同;名臣后之儒臣,是由于“以文学名”而文武分途,含职业化的意义而非显位置的重要;武臣起,能担负为圣主之王业“奔走御侮”之任,但武臣之职又意味兵戎干戈,危乱接踵而至;亲臣、近臣、外臣伴随着天下危乱而生,予示社会开始转入衰势,等待下一轮“圣主”收拾河山,重开基业。自此,历史阶段的周期“以外臣终焉”。李贽将人物褒贬的是非原则融入治乱交替的历史过程,这种独具匠心的编撰构思,增强了史论发议的评说力度。
以上述是非原则为准,李贽重点肯定的历史人物,有几类是值得提出来的:
①体恤民情,常以有利于百姓生计着想的君王。如赞汉高祖入关时,约法三章,除秦苛政,乃“王者之师”〔12〕;称赞汉文帝的与民休养生息,行黄老无为之治,并于临终遗诏时,“身崩而念在民”〔13〕;颂武则天“有专以爱养人才为心,安民为念如武氏者乎?”〔14〕赞宋太祖告诫部将,“切勿暴掠生民”为“圣主推戴”〔15〕。
②见识独到,不泥古人,有所作为者。如称颂秦始皇统一之功绩为“千古一帝”,汉高祖为“神圣开基”〔16〕;赞李斯“五帝不相复,三代不相袭,各以治”〔17〕的观点;另在《焚书》卷5《读史》中, 对贾谊、晁错等有见识,有作为的大臣,亦予以赞赏。
③因时改革,善用才智,有助国用者。如赞李悝变法,“行之魏国,国以富强。”〔18〕称吴起“料敌制胜,号知兵矣。”〔19〕誉商鞅“相秦不过十年,能使秦立致富强,成帝业。”〔20〕桑弘羊用均输、平准之法,“不待加赋,而国用自足。”〔21〕张居正的改革为“大有助于社稷者。”〔22〕
④起于乱世,功业未成,但事迹悲壮者。如《藏书世纪列传总目》列群雄于首,以彰其事。赞陈胜“匹夫首倡”,项羽“英雄草创”,李密“因乱使智”,窦建德“亡命草创”等,将其一并列入“世纪”人物,与历代帝王同。此外,李贽还对顺势而为之“因时大臣”、好施巧计之“智谋名臣”、戎马倥偬之“大将武臣”,以及在文史、工艺、科技等方面有所造诣者,亦给予肯定的历史地位。
与赞誉者相反,李贽对那些无才无学而专以道德相标榜者极为鄙视,称其为伪君子。他在《续焚书》卷2 《三教归儒说》中指出:“夫惟无才无学,若不以讲圣人道学之名要之,则终身贫且贱焉,耻矣。”并斥责他们“阳为道学,阴为富贵;被服儒雅,行若狗彘。”从这些论述都可看出,李贽评史的标准,言微意深,富有新创,其实质为通过“谓一人之是非”的评价原则,藉以反对封建名教,冲破思想蕃篱,就时代而言,他的见解确实是发人深省的。
(4)、撰史方法:“笔削诸史, 断以己意”与贯通古今的纪传体评论的创例
李贽精心编纂的两《藏书》,依古人修史贯通古今之例,择众家之长,创已意之新,叙人载以传纪,述事系以编年,发议融汇其间;通过人物的前后排列,事件的纵横比较,议论的褒贬毁誉,以表达历史见解。他在治史之时,注重博览群书,独立思考,提倡怀疑精神。他对司马迁著史自出手眼,不践前迹尤为赞许,在《藏书》卷40《司马迁传》中,针对班固称其“是非谬于圣人”的指责,反驳说:
班氏以此为真足以讥迁也。当也!不知适足以彰迁之不朽而已,使迁而不残陋,不疏略,不轻信,不是非谬于圣人。何足以为迁乎。则兹史固不待作也。迁、固之悬绝,正在于此。这段议论,表面上是对司马迁的赞誉,实际上则是李贽本身著书发议的指导思想。他的《藏书世纪列传总目》的前、后论,不仅表达出其历史发展观与人物评价的是非原则,也是该书撰述凡例的纲目。就《藏书》的纪传体例来看,受司马迁的影响较为明显,但在内容的表述上,也受着《通鉴》的启发。如总目的“世纪”人物,相当于《史纪》的“本纪”、“世家”,其排列顺序依朝代的先后为据,而“诸臣”的排列分类已体现出褒贬的原则;对于人物活动及事件的表述,全书则据编年来安排,其中夹附议论和述评。这种融记叙、评论于一体的贯通古今的史书编纂,不仅为一种创例,而且其具有的历史批判精神在中国史学思想史上,无疑产生着“推倒一世之智勇,开拓万古之心胸”〔23〕的启蒙作用。如果说中国史学史上史论体系的发展,经过了由最初短篇散章形式到整体评述的专论阶段,那么李贽则将这种专论,由以往那种纯粹的评论得失、借鉴经验的“资治”,引入到新的思想领域,因为从社会观、价值观和历史观上对整个时代展开的全面批判,是从李贽开始的,所以他的史论在思想性方面的成就,应该是极具影响的。
李贽的史论在技术性方面有如下特点:
①有目的的选编史料。李贽《藏书》的取材范围,其序言有“笔削诸史,断以己意”,可知其参阅读书不少,但主要取之于历代正史中的纪传、编年二种,这在他的《世纪列传总目》留有明显痕迹。对史料的选择,李贽极注重为阐述其政治观点服务。如,他称《诗》、《书》为古代“二帝三王以来之史也”,由于其评论的范围在“后三代”,即汉、唐、宋朝,故省去不录。又如,对孟轲“亚圣”的传纪,为加重史论的份量,通篇借其本人及他人之语,并附己论全然以代而事迹则舍之不录〔24〕。
②辩证的对比方法。李贽懂得用辩证对比方法来看待人物和事件,通过对比而体现出是非、优劣、强弱等差别。如,称秦始皇“千古一帝”是由于其开创的统一大业具有深远意义;同样,隋文帝虽然也统一南北,但从篡弑得来,故《藏书总目》称其“不得比秦始称帝矣”。又如,对于最简单的“死”字,李贽也按气节、功名、事业的对比原则,列举归纳出五个等级的结局,以阐明其生死观〔25〕。此外,在义与利、德与才、学与用、治与乱等问题上,李贽的史论都有很精采的论述,增强了说服力。
③由表及里、层层递进的论述。李贽的史论,见解独到,言微意深,与其由表及里、层层递进的评论技巧很有关系。如《藏书》卷3 《汉孝文皇帝》云:“历代诏令多文饰,惟孝文诏书,字字由肺肠,读之令人深快,予故备载之。孝文深得退一步法,自然脚跟稳实,故其诏令不虚也!学者未知黄帝老子之实,谓之异端杨朱氏,能令天下祸败。吁!请细观之,毋但哺前人糟粕也。”李贽由汉文帝诏令简洁务实发议,借之赞扬其与民休养生息的政治,最后引发出借评汉文帝面对盲从古人成说者嘲讽的寓意,并以此达到赞颂黄老因时无为之治的目的。
④坚持史识见解的原则性。李贽总的思想为重才轻德,但涉及史识见解的重大问题时,则坚持原则。如《焚书》卷5 《贾谊》云:“班氏文儒耳,只宜依司马氏例以成一代之史,不宜自立论也。立论则不免搀杂别项经史闻见,反成秽物也。班氏文采甚美,其与孝武以前人物,尽依司马氏之旧,又甚有见,但不宜更添论赞于后也。何也?论赞须具旷古隻眼,非区区有文才者所能措也。”班固“文采甚美”,但“经史闻见”搀杂上儒生思想,故其立论与司马迁“是非谬于圣人”的看法相比,全然不可同日而语。在史识见解上,不依才气出众或“甚有见”而让步,这是李贽的卓识。
⑤编纂史书技术环节的处理独具创见。如《藏书》断代另辟蹊径,将南北朝上限溯至西晋亡后,并某种程度排除夷夏之别偏见,给北部各族建立的国家以一定历史地位,对少数民族历史人物予以肯定或同情,称蒙古人建立的元朝为“华夷一统”等。此外,采辑史料亦精心删节处理,内容简洁,脉络清晰,纪传均可单独成篇。在人物的评述中有借喻手法:借孔子赞管仲语讥讽儒家弟子的“践迹”之举,借评韩信突出汉高祖的猜疑;《续藏书》中借评宋濂之死、汤和之保富贵以暗示明太祖的残酷与刻薄,多伏妙笔。
以上四方面的探析,基本概括了李贽的史学思想,其精华则体现在它的历史批判精方面,这在中国史学思想史上是占有重要地位的。从史学史的纵向考察,明代史学已呈现摆脱两宋史学的“义理”化〔26〕倾向而“进一步走向社会深层的趋势和特点”,其中经济史论著的繁富是一个重要层面〔27〕,联系李贽史论含有的务实重用的积极因素,无论在学风还是指导思想方面,与其都是一脉相承的,它对于清初史学的“经世”思潮,同样具有着影响。因此,就史学意义说;第一,李贽“笔削诸史,断以已意,”否定了传统史书编纂中义例正统的论说及纲常名分的序列,在编纂中开了贯通古今的纪传体评论的创例,〔28〕其字行间蕴涵的历史批判精神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对突破传统思想的束缚具有早期的启蒙作用。第二,李贽的“治贵适时,学必经世”的主张,以重视人的社会生活和生产的价值功能来代替封建传统伦理的空洞说教,不仅是学风上的黜虚务实,更是史学发展面临转折、走向社会深层的时代要求,体现出明代史学视角的深刻变化。第三,就文献资料的保存或考订角度而言,这不为李贽所长,但他开辟的利用历史编纂与评论全面表达政治见解的新思路,则为明初以来史学著述“苍白的阶段”〔29〕注入活力,推动着明季后史学的“经世”化的发展。
四、李贽史论的历史局限
李贽的史论以评史与论政的结合,充分展现出历史批判的精神,其思想性方面的成就,是史学发展史上的重要阶段。但是,由于特定的历史环境,李贽的思想仍不可避免地受到客观条件的制约,其史论还具有较大的历史局限。
首先,李贽所处之世是理学横流、正统思想暴露出极大虚伪性的时代。从实质说,他的史论的出发点是要以真反假,抨击封建专制的虚伪,揭露统治阶级言行不一的骗人说教,而不是改变封建传统的伦理体系,更不能摧毁封建社会的统治秩序。这样,他提出的反对封建专制,尊重人的价值,关心社会生产和生活等主张,还是得由明君贤相、能臣美吏这套封建机制来实施,来保障。故李贽史论的思想主线,仍体现着君、臣、民的隶属关系。这就是他在《藏书》中既反专权,又称“圣主”,既同情农民起义,又视其为“盗贼”的原因所在。
其次,对历史是非的衡准,由于主观上的感情色彩,难免在批判中带有过激倾向,存有一定的错误与偏见。如在义利之辩方面,尽管有力地冲击了理学道德观的虚伪,但对那些好施奸计、有才无德之人,就有不适当拔高的误导,忽视了传统道德作为一种精神规范,在稳定与平衡社会机制方面所起的积极功用。
再次,对当代的人物评论有讳避思想。如《藏书》与《续藏书》比较,其观点已有较大不同,《续藏书》里对明代人物体现出“扬善不刺恶”的色彩,冲淡了其历史批判的精神。
最后,由于长期遭受排挤,为世所不容,加上佛、老思想的感染,李贽的内心又时有超脱尘世的消积情绪,产生了入世与出世的矛盾。
李贽史论的历史局限,正是他人生悲剧的根源所在,而透过个人的坎坷遭遇,又体现着整个民族历史的步履蹒跚;这种赋予着沉重包袱的时代特征,使无数仁人志士的探索追求,都因无法挣脱传统藩篱的羁绊而付诸流水。这样,李贽史论的社会意义,又为我们留下无尽的深沉思考,而批判性地继承和发扬民族优良传统,则是历史工作者长期而艰巨的任务。
注释:
〔1〕《续焚书》卷1《与耿子健》。
〔2〕《焚书》卷5《经史相为表里》。
〔3〕《藏书》卷35《儒臣传·赵汝愚》。
〔4〕见侯外卢《中国思想通史》第4卷第22、23两章 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
〔5〕《续焚书》卷2《自刻说书序》。
〔6〕《徐光启集》卷2《几何原本杂议》。
〔7〕、〔8〕《焚书》卷3《战国论》。
〔9〕《焚书》卷1《与耿司寇告别》。
〔10〕、〔24〕《藏书》卷32《孟轲传》。
〔11〕《续焚书》卷1《与焦弱侯》。
〔12〕《藏书》卷2《汉高祖皇帝》。
〔13〕《藏书》卷3《汉孝文皇帝》。
〔14〕《藏书》卷56《李勣》。
〔15〕《藏书》卷8《宋太祖皇帝》。
〔16〕《藏书·世纪列传总目》。
〔17〕《藏书》卷2《秦始皇帝》。
〔18〕《藏书》卷17《李悝》。
〔19〕《藏书》卷47《吴起》。
〔20〕〔21〕《藏书》卷17《富国名臣总论》。
〔22〕《藏书》卷3《何心隐论》。
〔23〕李中黄:《逸楼四论·论文》 引自《李贽研究参考资料》第2辑 厦门大学出版社。
〔25〕《焚书》卷4《五死篇》。
〔26〕吴怀祺:《宋代史学思想史》第1 章《绪论》黄山书社1992年版。
〔27〕瞿林东:《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纵横》第242页 中华书局1994年版。
〔28〕张舜徽:《訒庵学术讲论集》第316页 岳麓书社1992 年版。
〔29〕白寿彝:《中国史学史》第1册第79 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标签:李贽论文; 历史论文; 读书论文; 文化论文; 焚书论文; 续藏书论文; 五经论文; 藏书论文; 明朝历史论文; 历史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