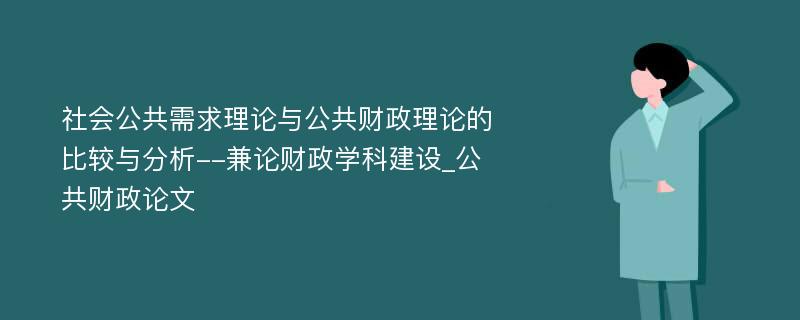
社会共同需要论与公共财政论的比较及分析——兼谈对财政学科建设的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学科建设论文,公共财政论文,财政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公共财政产生于西方社会,具有鲜明的市场经济特征,这决定了大胆吸收借鉴西方的公共理论来构建与我国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公共财政理论已是大势所趋,也是当务之急。但由于经济理论基础及相关的政治制度、意识形态上的根本差异,决定了对西方财政理论既不能排斥而要借鉴,又不能照搬而要消化吸收。这就为我国财政学界提出了崭新的课题,那就是如何实现西方公共财政论与我国传统财政理论的融合与创新,从而构建并发展我国新的财政学科体系。
因此,我国财政学者开始探寻传统的财政理论与西方公共财政论的共同点,力求得到一个最佳切入点实现双方的融合。在这背景下,产生于改革开放初期的社会共同需要论又重新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和思考。有的学者认为“共同需要说实际上是建立在公共品理论基础上的”,“90年代之后,共同需要说又有进一步的发展”(丛树海1998)。而有的年轻学者则大胆假设“在共同需要论的基础上发展公共财政论很可能是中国财政学的发展趋势”(杨志勇1998)。
社会共同需要论作为对财政本质问题研究的八大流派之一产生于80年代初期,它的提出也曾对财政理论研究和活跃学术讨论产生过较大的影响,其完善的和有代表性的理论体系体现在《理论财政学》这一名作中(何振一著,中国财经出版社1987年版)。本文也主要以此书论点为主要依据比较共同需要论与西方公共财政论并对两者关系予以简要分析,进而谈谈对我国财政学科建设思考的一已之浅见。
一、两论的比较
(一)两种理论的相同之处或相似之处
1.都认为财政产生与存在的目的就是为了满足社会共同需要(或公共需要)。社会共同需要论认为财政一般本质或称内涵的两个基本特征之一就是“满足社会共同事务消费需要”即社会共同需要(注:参阅何振一著《理论财政学》P3,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7年版。),其后又采用历史分析方法具体论述了人类社会各时期的社会共同需要决定了财政的起源及发展(注:何振一著《理论财政学》P17-39,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7年版。)。西方财政理论是与资本和市场相伴随而产生的,其一开始就是要解决如何为市场服务问题。因而公共财政论认为市场失效决定了公共财政的产生及发展。“市场失效”表明私人部门无法提供具有社会共同消费性质的公共产品而只能通过财政的非市场活动来完成,这就实际上规定了公共财政产生与存在就是为了提供满足社会共同需要的公共服务。
在对社会共同需要(或公共需要)含义上,双方基本是吻合的。社会共同需要论“它不是全社会个人需要的加总,而是一般的社会需要”,“是相对应于个人消费需要的社会共同需要”(注:何振一著《理论财政学》P6,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7年版。)。而在公共财政论看来,公共需要是对立于私人产品消费需要的公共产品消费的需要。
对于社会共同需要(或称公共需要)的外延,双方都以变化发展的眼光看待其范围。社会共同需要论认为社会共同需要随社会发展的历史阶段而变化,从而产生了财政分配范围的变化(注:何振一著《理论财政学》P4,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7年版。)。而公共财政论则始终遵循“市场失效”准则,其公共需要的范围也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市场失效”范围的变化而变化,经历了由自由主义时期的“小政府小财政”到干预时期的“大政府大财政”的转变。
2.在分析国家与财政关系问题上的看法有一定的相似之处。在社会共同需要论看来,国家不是研究的起点,而是社会发展出现了社会共同需要而产生的(何振一1982),而到了阶级社会,“不是国家创造了阶级财政,相反是阶级财政为国家的产生奠定了经济基础”(注:何振一著《理论财政学》P31,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7年版。)。在公共财政论看来,国家也不是分析的起点,它首先论证了公共经济的存在,是先通过个人的联合集体行动说明了公共经济的涵义,然后才指出国家与公共经济的关系:即公共产品的提供主要应由国家来承担。因此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没有公共财政就没有国家(张馨1993第21页)。
(二)两种理论的不同之处
1.双方理论研究对象的根本不同。社会共同需要论是财政一般本质的研究,即对人类社会几千年历史不同社会形态下财政本质的共性研究,这也正是共同需要论学者所言的“财政一般”(注:何振一著《理论财政学》P2,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7年版。)。与其不同的是,公共财政论研究的是市场经济体制这一特定条件下财政模式问题,也可以认为是财政特殊本质或财政类型(张馨1997)。与此相应的,双方思维模式与方法则迥异。社会共同需要论采用历史分析方法,从原始社会开始以纵贯几千年的分析方法来论证财政的起源、产生与发展以及各个发展阶段(社会形态)的特殊性质。而公共财政论则紧紧围绕市场经济这一基点,从市场有效——市场失效——公共或国家的介入——公共财政的产生、存在与发展,始终是在市场经济这一特定条件下以服务于市场经济这一基点来展开分析。
2.在对待国家财政阶级性上态度不同。社会共同需要论虽然认为财政是先于国家产生的,但它认为国家产生以后财政就打上了鲜明的阶级烙印,在不同的阶级国家掌握下财政就具有了不同的阶级性质(何振一1982)。并且它还认为“资产阶级学者的不正确性就在于它抹煞了社会的阶级性,否定了阶级社会下社会共同需要的阶级性”(注:何振一著《理论财政学》P7,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7年版。)。因此该论认为进入阶级社会后,社会共同需要性质发生了改变,财政尽管也有一定公共性,但阶级性则是根本的和主要的。
公共财政论中的“公共”是与“私人”相对立的涵义。公共财政是否定了封建君主私人财务性质“家计财政”的产物(张馨1997),是对所有市场主体一视同仁征税和一视同仁提供服务的“公共”。因此,它是掩盖和否定财政阶级性的。从根本上看,这种“公共”观根源于西方“社会契约论”的国家学说。
3.对财政活动性质看法不同。社会共同需要论认为财政本质是“社会再生产过程中为满足社会共同需要而形成的社会集中化的分配关系”(注:何振一著《理论财政学》P3,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7年版。)。与国家分配论相同的是,它同样认为财政处于社会再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四环节中的分配环节,财政活动性质是一种分配行为,而不是一种生产性的活动。尽管它不认为这种分配的主体就一定是国家。
而在公共财政论看来。财政活动的性质是一种提供公共产品的生产性活动。它回答和解决的是公共产品的生产、提供和消费问题,并通过林达尔模型分析了公共产品的“税收价格”问题,从而实现了“模拟市场”交换。由此看来,公共财政论认为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一样参与了生产活动,财政提供公共产品的过程本身就是一个完整的再生产过程。
4.双方基础理论依据不同。社会共同需要论是以劳动价值论和马克思国家学说为理论基础的。公共财政论是以边际效用价值论和社会契约论学说为理论基础的。而正是基础理论上的差异决定了双方对财政活动性质和对国家财政阶级性看法上的差异。
二、比较后的分析
从两种理论的比较中可以看出,两者尽管有某些相同或相似之处,但却有着根本性的差别,其中最主要的差别就在于研究对象的根本不同:一个是对财政一般本质的研究,是财政一般;一个是对市场经济下财政特殊本质(或称财政类型)的研究,是财政特殊。社会共同需要论产生于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改革开放初期,而成熟并完善于80年代中期,集大成于《理论财政学》(何振一著)一书和《共同体、共同需要与财政》(罗彤1987)等文章中。尽管在其理论形成中可能受到西方财政理论的启发和影响,从共同需要角度分析问题,但其基本上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国家学说、价值理论和社会再生产理论为理论基础,最终得出了“财政是社会再生产过程中为满足社会共同需要而形成的社会集中化的分配关系”财政一般本质的结论。而公共财政论是根源于西方市场经济的产生与发展,经过西方经济理论界两个多世纪的发展,从亚当斯密将公共支出与市场失效相联系开始,到19世纪80年代奥意学者将边际效用论运用到财政领域,才形成了系统的公共产品理论的经济学基础(张馨1995),又经过威克塞尔、林达尔、庇古、凯恩斯等人的发展而得以成熟和完善,形成了一套与马克思主义完全不同的财政学说体系。在我国市场化取向的改革实践推动下,真正系统介绍和分析西方公共财政论则是90年代之后的事了,大规模地探讨和争论公共产品理论的借鉴意义则是近两三年才开始的。笔者认为,对西方公共财政理论的介绍与借鉴并不能认为是我国社会共同需要论的进一步发展。双方一系列根本看法上的差异表明认为“90年代之后,共同需要论又有进一步发展”(丛树海1998)的看法未免失之偏颇。同时,在社会共同需要论看来,“社会共同需要是一个理论抽象,是一般的社会需要”、“是维持一定社会存在、一定社会再生产的正常进行,必须由社会集中组织的事务的需要”(注:何振一著《理论财政学》P6,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7年版。)。由于社会共同需要论与西方公共财政论经济理论基础不同,且又不是从市场经济的特定角度来立论,它没有也不可能象公共财政论一样得出经过严格客观性标准(即非排它性与非对抗性)界定的公共产品概念,更不能形成公共产品的理论。
既然社会共同需要论研究的是一般本质,公共财政论研究的是市场经济下的财政类型。两者又都认为财政产生与存在的目的是为了满足社会共同需要(或公共需要),那么是否就可以得出“中国财政学的发展趋势是在共同需要论的基础上发展公共财政论”(杨志勇1998)的结论呢?对此笔者同样不能苟同。
按社会共同需要论的历史分析法,财政可分为原始社会的原始财政和阶级社会的国家财政。它并认为在原始社会下,社会共同需要才是反映社会总体利益与个人利益相一致的全体人民需要,而在阶级社会下社会共同需要从本质上说是剥削阶级总体需要,其表现形式也成为国家实现职能的需要。我们暂时抛开原始社会后期农村公社中存在的是财政分配范畴(何振一1982)还是仅仅是财政关系的萌芽(赵春新1986)不谈,在国家出现后,社会共同需要变形为国家需要,阶级社会财政成为国家为实现其职能而进行的分配关系。因而它对阶级社会下财政的看法与国家分配论并无根本区别了。进一步看,正由于对社会共同需要的看法未能自圆其说地贯彻始终,就表明与国家分配论相比,社会共同需要论与公共财政论之间并无更多的相通之处,以共同需要论取代国家分配论的财政本质观,并在此基础上发展我国公共财政论的设想是没有充分依据的。
三、对财政学科建设的思考
财政本质问题,向来是我国传统财政学的基础理论,是财政学科体系的基石。在大规模讨论和争鸣中形成了众多流派,其中国家分配论长期乃至至今仍处于主流学派地位。虽然国家分配论产生并确立于计划经济时期,带有强烈的计划体制下的“国家财政”类型的基本特征和内容(注:张馨《公共财政与国家财政关系析辩》,载《财政研究》1997年11期。),而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受到冲击。但其对财政本质的认识则是对几千年来所有财政类型的抽象,反映了财政的一般。我国传统财政理论以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和社会再生产理论为基础,不仅国家分配论,而且包括社会共同需要论、剩余产品论等都认为财政是一种分配行为。但纵观几千年的中外财政史,没有任何非财政分配是由国家进行的,也没有任何国家进行的分配不是财政分配。“国家分配论”的分析经过层层“剥笋”式解剖,在“最深层次的本质联系”上清晰地得出了“财政是以国家为主体的分配”的结论(注:邓子基著《财政学原理》经济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一章第二节。),从而正确把握了财政本质。
数百年来市场经济在西方的发展历程表明,只有公共财政才能适应于、服务于并最终有利于市场经济的存在和发展。建立与我国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公共财政已是大势所趋。因此,倡导和支持“公共财政论”学者认为,应在“国家分配论”财政本质观基础上,通过否定“国家财政”类型观并确立“公共财政”类型观,构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我国公共财政理论。这无疑是积极的、有益的。但笔者认为要实现中西财政理论的融合与创新,并从而创立新的财政学科体系,将是一项艰辛复杂的任务。如前文对社会共同需要论与西方公共财政论差异比较的结论一样,对这些差异(对财政阶级性看法的差异、对财政活动性质看法的差异),国家分配论与公共财政论之间也同样存在,从根本上看是双方基础理论上的差异。因而要在中西融合基础上构建我国新的财政学科体系,要正确定位我国的公共财政理论,就不能不面对中西财政理论双方在基础理论上差异所可能带来的障碍。
(一)主要障碍并非来自国家学说上的分歧及财政阶级性与公共性的争议。
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国家学说与西方社会契约论国家学说直接影响着双方财政基础理论,导致了对财政阶级性与公共性的见解分歧。因此在前一段对借鉴西方公共财政理论的争论中,该问题成为一个焦点。但笔者认为它不会对构建我国公共财政理论构成主要障碍。
1.正确认识西方财政理论“公共观”的合理性与虚伪性
(1)其合理性根植于市场经济体制。公共财政产生并发展于西方市场经济条件下。从市场经济这一角度看,它具有服务于市场经济的公共性,这一公共性是对立于私人性而言的,并非对立于从生产资料占有方式角度看的阶级性。以非排它性与非对抗性为特征的“公共产品”消费对象是所有市场活动主体,它区别于私人产品,因而谓之“公共”。建立于为市场正常运转提供公共产品的公共财政则严格区别于仅为私人服务的“家计财政”和为国家自身服务的“国家财政”类型(张馨1997),因此谓之“公共”。从这一角度看,“公共观”有其合理性。
(2)其虚伪性源于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有制。财政是国家收支,是政府活动,而西方财政理论要以公共活动为分析基点,自然要由公共国家观与之相适应,因此作为社会契约论的公共国家学说就成为其基础理论依据之一。这种国家学说是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国家学说相违背的。从生产关系角度看,产生并发展于西方资本主义私有制下的公共财政必然带有阶级性。资产阶级统治要通过资产阶级国家弥补市场失效的“公共”活动来实现。财政的公共性事实上维护并体现了资本主义制度的阶级性和剥削性,并以公共名义掩盖了其阶级性和剥削性,而这正是其财政公共观的虚伪性表现。
2.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共财政的合理性与真实性
由于市场经济体制上的共性,使西方财政理论“公共观”的合理性在我国得以继承,表现为逐步否定计划体制下只为国家自身和国有经济服务的“国家财政”类型,代之以为市场提供公共服务、弥补市场失效的“公共财政”类型。同时我国建立于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基础之上的社会主义制度事实上批判并否定了西方财政“公共观”中的虚伪性,而代之以真实性,服务于发展生产力为根本目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全体人民当家理财的公共财政具备了实质上的“公共”内涵。由此可见,尽管西方公共财政以社会契约论为基础理论之一。但如从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出发,正确看待其公共性,并没有理由否定公共财政在我国市场经济条件下存在的合理性。
(二)根本障碍来自劳动价值论与边际效用价值论的分歧
该分歧深刻影响着双方理论及方法体系,决定着“国家分配论”财政本质与“公共财政”财政类型多大程度上的相容性,决定着我国公共财政理论发展的根本方向。
1.形成理论体系上的差别:财政是分配活动还是经济生产活动
我国传统财政理论(不论是国家分配论还是共同需要论)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在这一价值理论下只有物质产品的生产才是生产活动,财政则是非生产性的活动,依据马克思社会再生产理论四个环节的划分,财政都是对社会产品(物质产品)的分配活动,涉及的仅是分配环节。而西方公共财政论建立在边际效用价值论上,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对个人是有效用的从而也是有价值的,因而国家活动是生产性的。财政活动是公共产品的生产、提供和消费的完整过程。
理论体系上的这一差别,将使构建我国公共财政理论面临如何正确定位问题。一种方向是只承认西方公共财政也是分配活动,公共财政不同于公共部门经济,公共财政只是分配提供生产公共产品的资金,而不回答“生产什么”、“如何生产”、“为谁生产”等问题(潘贤掌1998)。这个方向是能与“国家分配论”本质观相衔接,但事实上只是一厢情愿地以我国传统理论来框定西方公共财政仅仅是分配活动,即便做这一框定也实际上否定了西方建立在边际效用论上的微观经济分析能为我所用。另一种方向是否定财政只是一种分配活动。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由MPS向SMA转变,公共服务支出形式上为M实质上为C,财政部门取得税收再作为公共服务的“再生产”之用(钱伯海和孙碧秋1997)。但这种方向事实上已经否定了国家分配论的财政本质观。而且该观点建立于社会劳动价值论基础上(注:钱伯海著《社会劳动价值论》,中国经济出版社1997年版。),而与西方非劳动价值论完全不同,实际上也否定了西方建立在边际效用价值论基础上的公共产品微观分析能为我所用。
2.形成方法体系上的差别:微观经济分析的不同
西方公共财政论的核心理论——公共产品论在边际效用价值论上建立了一套微观经济分析方法和效率评价标准。边际效用论引入财政学,使私人效率准则运用到公共产品最佳供应上来,使以个人需要为基点的微观经济方法体系适用于公共活动分析,并从而建立了相应的数学模型和数量分析方法,也形成了衡量资源配置效率的标准—帕累托准则。我国传统财政理论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而形成分配关系本质观,难以对财政非物质生产活动进行价值评定,也就难以形成完善系统的微观分析方法和衡量资源配置的效率标准。因而要建立我国市场经济下的公共财政理论,是否能接受西方公共财政论的微观分析方法和效率评价标准?如果能接受,则事实上将与国家分配论一般本质观相悖。如果不接受,又如何建立一套建立于劳动价值论上的衡量资源配置的效率标准和相应的市场失效的概念体系?如果无法做到这一点,我国的公共财政理论能说得上真正是以市场分析为基点的吗?
综上所述,要实现中西财政融合与创新,要在我国传统财政本质观上构建我国的公共财政理论,主要将面临价值理论差异上的重大理论障碍。事实上就要求回答作为西方公共财政理论核心的公共产品论在我国有多大适用性问题,而非泛泛地谈借鉴意义。它能否成为正在构建中的我国公共财政论的理论核心?我国公共财政论能否不以西方公共产品论为理论核心?只有对此予以讨论并认真回答,才有助于解决我国公共财政论的方向定位和市场基点问题。否则不论是在社会共同需要论上发展公共财政论,还是在坚持国家分配论财政本质观下建立适合于我国市场经济的公共财政论都容易陷入难以自圆其说的二元悖论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