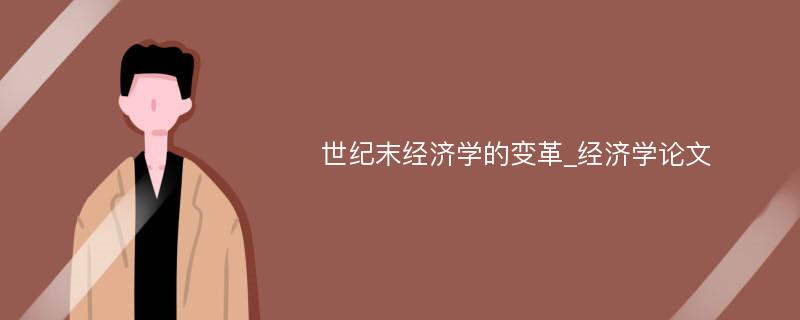
经济学世纪末的变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世纪末论文,经济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两个多世纪以来,由亚当·斯密创立的经济学体系,经过从古典到新古典众多经济学家的不断补充、改造和完善,已成为社会科学中颇具科学外观的学科。新古典经济学家对古典经济理论进行了形式化和精确化的改造。然而,他们对经济学的这种贡献,在许多人的眼里却并不值得称道。用美国学者艾克纳的话说:“它除了建立在一系列形而上学的,从而非科学的公理基础上的一系列演绎推理而外,经济学几乎一无所有。”(注:艾克纳:《经济学为什么还不是科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80页。)当然,这里指的是主流经济学。
在经济学的发展,尤其是20世纪的经济学发展中还存在着另一努力方向。这就是通过对现实世界的经验观察和建立在这种观察基础上的严肃思考,寻找对真实发生着的经济活动的经济学理解。进行这一努力的,是一批被称作“非主流”的经济学家。他们的努力已经积累了丰富的成果,而且他们已经成为现代经济学发展的一股强有力的推动力量。在世纪之交,当许多人对经济学忧心忡忡的时候,他们的工作向人们展示了经济学的新世纪曙光。
一、主流经济学的乌托邦性质
在学派林立的西方经济学界,有一个公认的“主流派”——新古典学派。它不仅占据了大学的讲坛,而且对西方经济学理论和西方各国政府的经济政策都产生了重大影响。然而,这个广为流传的主流经济学所描述的世界,与人们生活于其中的现实经济社会并不存在太多的真实联系。在很大程度上,它只是从经济学家的头脑中产生的乌托邦世界,具有突出的非现实特征。如果说古典经济学家是在用眼睛观察加上大脑的思考,再加上某些天才的猜测,努力向人们提供一种对于人类经济活动的某种理解或知识,那么主流经济学家所做的则是尽力显示他们的智慧成就,努力使经济学成为一门“艺术”而不全然是“科学”。许多经济学家中肯地指出,现代主流经济学更多的是“在大学的象牙塔中构思出来的”“逻辑精品”(注:马拉伯:《迷惘的预言家》, 海南出版社1997年版,第3页。)。其乌托邦性质尽显其中,这突出地表现在:
首先,现代主流经济学理论大厦的基础是一系列远离实际的假设。毫无疑问,作为研究方法,理论研究不能没有假设,但假设绝不是可以随意设定的。假设要反映客观世界的本质,这是奈特、西蒙等人不断地告诫人们的。而新古典主义者似乎并不愿意这样做,他们声称理论的假定并不重要,而且“一般地说,某一理论越是杰出,那么它的‘假设’就越超脱现实。”(注:弗里德曼:《弗里德曼文萃》,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第202页。 )现代主流经济学的理论体系正是建立在一系列“超脱现实”的假定之上的,如完全市场、完全理性的“经济人”、对称信息、稳定的自身一致的偏好等。一旦失去这些假定,主流经济学的釜底之薪也就不复存在了。
其次,形而上学的分析方法。“供求分析是经济学的看家本事”(注:汪丁丁:《我思考的经济学》,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7页。),对于新古典经济学来说,这“基本的一招”又是和一般均衡联系在一起的。一般均衡的浓厚的形而上学性质早已被许多国内外学者明确地指出。汪丁丁认为,“在经济学里,作为经济学基础的‘一般均衡’是一个基于乌托邦的理论状态。”(注:汪丁丁:《永远的徘徊》,四川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2页。)一般均衡起源于瓦尔拉斯, 人们将其视为想象力的产物。但是,50年代以后,主流经济学家就不再这样认为了。因为,1954年阿罗和德布鲁通过《竞争经济的均衡的存在性》给一般均衡的存在提供了一个“确定的”数学证明。实际上,一般均衡存在性的证明依赖于特定的限制条件,具体地说,只有具备了完全市场、对称信息和完全理性经济人的条件,才有一般均衡的存在。而问题的症结正在于此。西蒙指出,一般均衡的证明“虽然在数学上精巧漂亮”,但是它“是否与现实有什么关系,我们可以而且已经提出了疑问。或许,有人之所以攀登某些智慧的高峰,无非是因为那些高峰的存在——无非是因为攀登高峰能使人感到刺激和振奋。”(注:西蒙:《现代决策理论的基石》,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第65页。)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主流经济学理论在实践中的失败。20世纪以来,主流经济学家扮演了使人类走向效率和福利的向导的角色,他们或者担任政府要职,或者作为顾问频频向政府献计献策。但是,无论是在反垄断,还是在反经济周期上,他们只取得过有限的成功。而60年代以后,在对付经济停滞、失业率上升、通货膨胀加剧等问题上,也难以开出有效的药方。
除了上述方面之外,主流经济学的乌托邦性质还表现在纯数学推导、纯逻辑演绎等方面。当它在这些方面取得“成功”之时,也注定了必然要面对“危机”的来临。
二、经济学的非主流发展方向
从一定意义上讲,经济学在其发展的各个时期,总会产生一个主流派。但是,经济学的发展并不是完全由主流派学者推动的,非主流派学者同样发挥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而且常常是关键性的。20世纪以来,一批非主流经济学家,如哈耶克、熊彼特、西蒙、科斯等用事实证明了这一点。他们从现实出发,在对主流经济学的批判和反思中,创立了自己的理论,并日益受到经济学界的关注。在此我们仅举几例做一简要说明。
在经济学理论中,“理性”的重要性早已引起了人们的关注,而经济学对理性问题的探讨,至少已持续了近百年之久。但是,长期以来,占统治地位的“理性”解释是主流学派的“完全理性”观念。它构成了主流经济学理论的硬核,是主流经济学的基础性概念之一。当主流经济学家还在相信并且维护这一概念的时候,西蒙在《管理行为》(1947)一书中,提出了有限理性学说。在西蒙看来,“古典经济理论对人的智力做了极其苛刻的假定,为的是产生那些非常动人的数学模型,用来表示简化的世界。”(注:西蒙:《现代决策理论的基石》,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前言。)而人类的行为特征却并非如此。西蒙用“有限理性”代替了“完全理性”,用“追求满意”代替了“最优”。因为有限理性真实地刻画了人类的行为特征,所以它的迅速传播,以及它对经济学和其他相关学科的深刻影响就不难理解了。
新制度经济学(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将被主流经济学视为既定的外生变量而排除在经济分析之外的因素,纳入理论分析之中并使之内生化。新制度经济学派虽然与主流经济学保持着某种“血缘关系”,但是它指出了主流经济学的偏狭性,并通过引入产权、交易成本、契约、科层等概念对新古典经济学进行了补充和修正,特别是对长期以来被主流经济学所忽视的领域——企业或组织、权利配置、制度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深入且富有成效的研究。
以哈耶克、米塞斯等为代表的奥地利学派是一个历史较长且影响较大的非主流派。其理论体系,尤其是哈耶克的思想触角涉及了广泛的领域。这里仅从有限的方面做一概括:第一,协调和秩序的经济观。在哈耶克看来,社会经济生活自发形成一种协调和经济秩序或叫作“扩展秩序”,它远比任何人为的设计更为复杂和有效。第二,个人主义的哲学信仰和方法论基础。哈耶克认为,真正的个人主义是经济运行的深层基础,是形成社会秩序的根本前提。第三,有限度的人类理性。(注:在对人类理性问题的认识上,奥地利学派的早期代表人物与哈耶克是有所不同的。)哈耶克认为,人类理性所能理解和创造的东西是有限的,“自负的理性”常常试图设计或重建社会,然而,“在我们竭尽全力地根据一些崇高的理解缔造我们的未来时,我们却实际上不知不觉地创造出与我们一直为之奋斗的东西截然相反的结果。”(注:哈耶克:《通往奴役的道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4页。)第四,知识、价格与分散化的体制。哈耶克将知识分为理论知识和特殊知识,后一种知识是大量的和重要的;价格是利用这一知识的机制;“我们需要分散化是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保证特殊时间和地点情况的知识被迅速地利用。”毫无疑问,奥地利学派,尤其是哈耶克的理论的影响是广泛而深刻的。
与上述经济学派别具有相似重要性和同样重大影响的其他学派,还包括熊彼特的创新理论,布坎南的公共选择理论,以巴兰、斯威齐等为代表的新左派经济理论等。所有这些非主流派的经济理论都在力图克服经济学的乌托邦性质,增强人们对现实经济活动的理解,以及为扩展人们关于人类行为的经济学知识做出了重要贡献。
三、世纪末的经济学变革
我们认为,经济学不能只在形式化的路径上发展,因为这终将被锁定(Lock-in),变革或重构经济学的时代已经到来, 但这绝不可能一蹴而就。
首先,由于经济学是一门经验科学,而不是一门逻辑学(当然它需要逻辑),所以幻想仅仅通过在思维或逻辑方向上的努力来实现经济学的变革和发展,是不现实的。脱离社会实际的理性思维不可能使经济学从空想变成科学。重构经济学要求经济学家走了思辩的王国,走出自己构筑起来的象牙塔。世界是复杂的,而尤其复杂的是人类的行为世界。那些机械的、决定论式的规律在这里充其量只有有限的解释力。人是有意志、有目的的行为主体,其行为并非总是可以用机械的互动机制、线性变动模型和微分方程式的推算来描绘。 任何武断的假设和简单的抽象,都可能是差之毫厘而谬以千里。
其次,实现经济的变革,要求经济学家跨跃人为设置的“学科”的鸿沟。19世纪科学史的一个突出成就是知识的学科化和专业化发展。这曾极大地促进了知识的传播、积累和创新。但是,学科化和专业化的长期发展所产生的一个孪生之弊是造成了学科之间的封闭和隔离,由此产生的学科间交流和融合的障碍已经成为科学进步和知识扩展的制约因素。这曾经引起一些敏感的学者,如孔德、杜克海姆、韦伯、海德格尔等人的极大忧虑。到了20世纪后半期则引发了世界科学领域中关于学科划分与专业化的有效性的争论,其结果是科学界出现了学科整合和跨学科研究的潮流。美国社会学家华勒斯坦指出,“为了在知识领域里取得富于成果的进展”,有必要在“如何消除19世纪出现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这三个假想的自律领域之间的人为分离”上达成共识。(注:华勒斯坦:《开放社会科学》,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82页。)
最后,一个重要的问题是竞争性学术环境的建设。竞争性的学术环境之于科学发展,犹如市场竞争之于经济发展,不可或缺。但是,这种环境在目前阶段还并非现实。有学者对美国的状况进行研究后发现,“与强调价格理论范式的个人选择、自由进出等自由竞争观念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经济学界严格而又特别刻板的等级制”,“我们可以用寡头垄断来描述经济学界的状况。”(注:艾克纳:《经济学为什么还不是科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8、35页。)这种情况对科学发展的危害不言自明,尤其是对面临变革或处于变革过程中的科学来说更是如此。
四、经济学在中国发展的若干问题
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是一个令中国经济学者深长思之的问题,虽然人们的结论并不相同。在这里,我们只是就经济学在中国发展所面临的若干问题提出自己的思考。
首先,经济学在中国发展的“规范化”问题。近年在中国经济学发展的讨论中,实现中国经济学的“规范化”的呼声很高。在我们看来,经济研究的规范化不仅是必要的,而且具有紧迫性。但是,“规范化”并不是一个笼统的概念,它不能不涉及到如何规范,以及实现以什么或以谁为标准的规范化问题。在某些规范化主张的背后,我们不难体会到这种含义,即实现中国经济学的规范化就是要使我们的经济研究与西方经济学“接轨”。而在这类关于规范化的说明中,“西方经济学”一词基本上等价于新古典经济学。如果这种规范化的主张的确有此含义的话,那么我们不赞同这样的主张。前面关于“主流经济学的乌托邦性质”的说明就是我们不赞同的理由。我们认为,如果说经济学研究有什么范式,那么这个范式不是别的,而只能是建立在对经验事实观察和分析基础上的理性思考。
其次,经济学研究的分工(专业化)与协作问题。分工对于经济发展的作用已经得到经济学家充分的肯定。同样,分工在其他领域也表现出了值得肯定的作用。中国的经济学研究缺乏分工,并长期以来制约着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因此,经济建设中存在的现象—低水平重复—也出现在经济学建设中,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不能没有经济学家之间的分工。当然,缺乏分工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是由分工和专业化所造成的知识的局部化。因此,我们既要看到分工促进科学发展的一面,也要看到由分工过细和分工的累积发展所造成的不利于科学发展的一面。我们认为,应当提倡经济学家之间的分工,同时又要防止和克服因知识面和研究领域过分狭窄而产生的学科间相互交流和吸收的障碍。对于想对经济学的发展做出贡献的学者来说,精深与博大同样重要。
最后,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过程中,对西方经济学的学习和吸收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我国经济学界基本上有两种意见:一是认为西方经济学的一般原理是带有“普遍性”的东西,因此对我们是适用的;二是认为西方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是与西方国家的体制、价值观念等相联系的,因而基本上不适用于对中国经济的研究。这两种意见反映了对西方经济学的不同评价。我们认为,西方经济学不是一个确切的概念,谈论对西方经济学的学习和吸收,关键是要有分析地做出选择。西方主流经济学中也不乏科学的成分,但无论对其一般原理,还是对其研究方法,都不能迷信地学习和全面地吸收。同时,如果对西方非主流经济学抱有偏见或无暇顾及,那将是一种偏误。归根结底,中国的经济学者只有坚持并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的理论,扎根于本国的实际,解放思想,勇于探索,才能有所创新,从而才能使经济理论对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具有解释力和预言力,而这才是经济学作为经验科学的致用之处。
标签:经济学论文; 西方经济学论文; 哈耶克论文; 科学论文; 理论经济学论文; 理性选择理论论文; 经济论文; 变革管理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