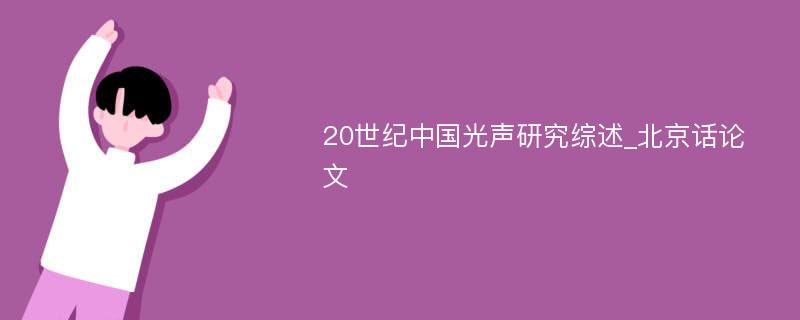
20世纪汉语轻声研究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汉语论文,轻声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H14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979 (2002)03-0043-05
轻声是汉语语音的重要现象,也是20世纪汉语语音研究的一个聚焦领域。据初步统计,20世纪研究轻声的专论有82篇。(注:这项统计只含专论,不包括散论和分论,比如各现代汉语教材都含轻声,讨论汉语声调的一些论著也含轻声,但都不在统计之列。)我们将20世纪分为五个时段,各段发表的篇数如下:
年代 1949前 1950-1966 1967-1978 1979-1989 1990-2000
篇数4 14 3 27 34
这些数字的起伏反映了20世纪汉语轻声研究的兴-衰-兴过程。个中原因无须细说。如果以1978年为界,前70多年共有21篇, 后20 年有61篇。前70年与后20年不仅数量悬殊,研究内容也明显不同。1978年前轻声的研究以感悟的客观描写为主,集中于轻声的读音、轻声的作用和轻声词的类型等方面。1978年后的研究以实证和理论探索为主,焦点有三:一是轻声的声学性质,借助于语音实验仪器以及计算机软件,研究轻声的音高、音强、音长、音色,取得相关数据;二是轻声属性及其定位;三是轻声探因探源。前后两个时期的研究有交叉。
为方便阐述,下文以专题为纲,以时间为序进行讨论。分5 个方面:一、轻声的读音、作用和分类研究;二、轻声声学性质的研究;三、轻声属性的定位研究;四、轻声发生的原因、机制及轻声探源;五、轻声是一种综合范畴。
一 轻声的读音、作用和分类研究
赵元任先生首开轻声研究先河。他于1922、1929、1933年发表的《国语罗马字的研究》、《北平语调的研究》和《汉语的字调和语调》先后讨论了轻声问题。这些论述包括:1.轻声音节的调值变化规则和元音变化规则;2.轻声类别和轻声词范围;3.轻声和轻音的关系。这些论述为后来的研究奠定了良好基础。有些观点至今仍熠熠闪光。
关于轻声音变。赵元任先生指出,“轻音字有中、高,低三种读法”,阴平、阳平后的轻声读半低音2;上声后是半高音4,“和前面半截子上声一起构成一个完整的上声”;[1,743]去声后是低音1。 这一规则至今仍被普遍使用。同时列出四条元音音变规则:ia变ie,ua变uo,ai变ei,语助词的韵母变e。
关于轻声类别和轻声词范围。他将轻声分作“永远轻读的”和“偶尔轻读的”两类。同时列出6类可类推的轻声词:语助词,“但是、 后头、我们”等“虚字词尾”,动词后的趋向动词,表方位的后置词,不特指的作宾语的代词,“要不要”式中的后二字。
赵元任先生关于轻声和轻音的论述在第三节介绍。
此后,轻声的研究围绕着上述问题逐步扩展延伸。张洵如1947年和1956年研究了轻声分辨词义的功能。承融1959年将可类推的轻声词由上述6类扩展为15类。随后,学术界进一步探究轻声音节的音变, 发现除了韵母所发生的主要元音央化外,清辅音声母还同步弱化为浊辅音,即b d g z zh j等6个不送气清塞音和塞擦音变为同部位的浊辅音。这些研究成果被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高校现代汉语教材所采用,沿用至今。80年代中,人们又发现,轻声音节还伴有增音、减音、脱落等音变现象。比如,轻声词“玻璃”后字读lin,“璃”li读轻声后增加了韵尾-n。再如轻声词“告诉”变为“告送”,“诉”su读轻声后增加舌根鼻音韵尾-ng,变作“送”sung;甚至脱落,单剩“告”。
1962年,林焘先生找到了轻音与语法的一个交接点。他在文献中有三个重要论断。第一,语音结构有层次,轻声与非轻声音节不在同一语音层次,轻声音节逐渐失去独立性而依附于前一个音节;第二,轻声音节的音长和音高变化证明它与前一音节已合为同一个语音单位,证据是:1.音长缩短,双音节轻声词语约为非轻声双音节词语的一半;2.轻声音节的调值与前一音节合成一个完整的声调模型,比如[上声+轻声]是[21+4],与完整上声的[214]相同,[去声+轻声]是[53 /52+1],与去声的[51]相同;这说明,轻声音节与前一个音节结构紧密,已构成一个语音单位;第三,普通话轻音有语调轻音和结构轻音两类(代词和副词通常读成语调轻音),结构轻音能反映出语音结构的层次,对分析语法结构有帮助。林先生根据结构轻音将“住在北京”类结构分析为动宾结构:住在/北京(宾语)。理由是,“在”是结构轻音,依附于“住”,“住在”成为一个语法结构体,与“北京”构成动宾关系。这个结论得到了语法界的热烈响应。将轻声当作语法分类和分析的参照物,是语音研究与语法研究相结合的范例,有方法论的意义。这种研究方法后来被语法界普遍采用。
二 轻声声学性质的研究
轻声声学性质的研究在80、90年代经过实验语音学的努力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这些研究成果推进了学术界对轻声本质的认识。主要有:1.音强不是轻声的本质属性;2.轻声与音长和音高关系密切;3.轻声音高有曲线变化,即有调形,不是传统认定的一个点;4.证实了轻声音节的元辅音音色的伴随性变化:主要元音央化,不送气塞音、塞擦音浊化,此外还发现鼻音韵尾有时会脱落。这些成果刷新了人们对轻声的认识,尤其关于轻声与音强关系的结论,纠正了过去对轻声由音强决定的误解。在这些研究中,影响比较大的有:林茂灿、严景助的《北京话轻声的声学性质》,林焘的《探讨北京话轻声性质的初步实验》,曹剑芬的《普通话轻声音节特性分析》,杨顺安的《普通话轻声音节的规则合成》。他们分别对北京话轻声做了声学分析、听辨实验和合成实验,从不同角度研究轻声的音长、音高、音色和音强。他们的结论有的很接近,有的有分歧。下面分述。
音长。曹剑芬声学分析的结论是:轻声音节的长度大约为正常音节的五分之三,林茂灿、严景助测定为45%。杨顺安用一般音节二分之一的音长合成轻声,听感自然。林焘的听辨实验证明,北京话双音节“重重”型第二音节的音长越短,听成轻声的比率就越高,并且没有例外。他们的不同研究一致证明,音长缩短是构成轻声的重要因素。
音高。关于音高的实验研究结论有两点很集中:一、轻声音高随着时长的变化发生变化,这证明轻声有调形,并非原先认定的音高变化无调域,仅为一个音高点;二、轻声的音高曲线取决于前一个音节,阴平、阳平、去声后是降调,上声后是平调(或先平后降,或先平后升)。关于音高的分歧主要有三点。第一,音高和音长哪个是轻声的首要特性。实验证明,音高和音长都是构成轻声的重要因素,但哪个是首要因素,看法不一。林焘认为,对声调语言而言,音高和音长有明确分工,“音高的变化在重音音节中已经起了非常重要的辨义作用,在分辨轻重音时以音长为主”,[7,37]音高的升降在轻声听辨中虽然也起作用, 但比较小,远没有音长重要。他认为音长是轻声的第一特性。曹剑芬认为,音长和音高是构成轻声的两个重要因素,但“或许还是音高的作用更大些”。[8,5]第二,轻声调形(型)在分辨轻声中的作用。林焘听辨实验的结论是:听辨中调型的升降起一定作用,但要受音长的制约,音长越短,调型升降对听辨所起的作用就越小,“调型的升降显然不是轻音的本质特点”。[7,37 ]但曹剑芬认为“调形可能对轻声的听辨具有重要作用”。[8,6]第三,测定的轻声调值不统一。见下表。
作者 阴平后轻声 阳平后轻声 上声后轻声 去声后轻声
林茂灿41 5144/33/3221
王韫佳41 5233 21[10]
曹剑芬51 5245 31
高玉振41 5135 31[11]
(注:表中的“/”代表“或”。表中曹剑芬和高玉振的五度制数据系笔者据曹文高文——文献[8][11]的相关数据所折算。 )(注:计算方法:取F[,0]最高值和最低值的对数差除5,计算出5 度各自的范围,再将轻声的F[,0]值换算为5度值。)
音色。用实验证实了轻声音节音色的变化:不送气清塞音和塞擦音常浊化,曹剑芬统计浊化比例约60%;主要元音央化,复合元音动程缩小,韵母鼻韵尾会消失。
音强。一致认为不是轻声的本质特征:轻声音节的音强不一定就比非轻声音节弱。
杨顺安根据普遍认同的轻声特性,制定出合成轻声音节的一套方案,合成了《普通话常用轻声词汇》中的双音节词语,合成结果“大多数都较为清晰、自然,其中的轻声音节,在音强、音高、音长和音色方面,都比较满意”。
三 轻声属性定位研究
对轻声现象的定位,大致有三种说法:调类说,变调说,轻音说。
调类说。50年代张洵如先生认为轻声是北京话的第5个调类, 到90年代仍有人呼吁“请立轻声为第五声调”。轻声在阴阳上去后各有各的调型、调值,调型不固定,调值不统一,难以类型化。因此,调类说的赞同者不多。
变调说。80、90年代的高校现代汉语教材一般将轻声归为“音变”,与典型的变调并列。将轻声看作声调的一种变化,有一个重要支撑点,即语音实验证明音高是构成轻声的一个要素。所谓变调,就是原有音高模型发生了变化,这是“变调”概念的立论点。在这一根本点上,轻声与一般变调没有大的差异。轻声与一般变调的差异主要有四点:1.变调位置不同:一般变调的位置可前可后,而轻声一定在后;2.引起变化的条件不同:一般变调受制于语音环境,如上上相连、去去相连的变调,后字声调是前字变调的条件,而轻声却因语法身份(词缀或虚词)或自身语义的虚化或轻重韵律需要而变调;3.轻声不仅声调变,连同音长、音色、音强都有变化,而一般变调只是单纯的音高变;4.变化后的负荷不同,轻声负载着一定语法、语义内容,而一般变调是纯语音行为,没有附加值。笔者认为,这四点差异属于“怎样变”“变后如何”“有无变化的伙伴”等非立论基点的差异,并不涉及“音高模型变”这一基点,因此,轻声“变调”说的立论基础与一般变调相同,应该可以成立。实际上,与一般变调不同的变调现象不止轻声,还有其他情况。在综合了各种变调现象后,有人将变调分为三类:语音变调、语汇变调和语法变调,轻声属于语汇变调。反对轻声“变调”说者,大约将变调限制在“语音变调”范围内了。当然,轻声的音高变化与语音变调有不同的音长模式。但事实上,轻声的音高变化还有另一种模式,即与语音变调相类的模式,这就是轻声的“非轻读”变调,“非轻读”轻声的音高模型与一般变调并无二致。如果轻声不归变调,这类“非轻读”轻声如何解释?又如何处置?“非轻读”轻声详见第五节。
轻音说。此说的前提是汉语有词重音。关于汉语的重音,历来看法不一。主张有词重音者,如黎锦熙,徐世荣等。赵元任不仅肯定汉语有重音(他称作“声调重音”),而且用声调重音解释轻声的发生:“声调重音起的作用如此之大,使得非重读音节不但元音趋于模糊,而且失掉了原有的声调,通常剩下一个短平调,其高低由前面的音节来决定。”[17,743]而高名凯、 石安石《语言学概论》则否认汉语有词重音:“汉语没有词重音。”
近20年来,大凡讨论轻声的论著多肯定汉语有重音,只是分类不同。有的认为有重、轻两类,有的认为有重、次重(中重)、轻三类,有的分作四类:重、次重(中重)、次轻、轻。或者从其他角度分类。厉为民认为有三类:词重音,对比重音(逻辑重音)和偶发重音(轻声偶发重音)。林茂灿按两个层次分作3大类6小类:正常重音(有强、中、次中三小类),对比重音,弱重音(轻声)。他详细描写了第一个层次的三类重音的声学特征。
对汉语重音无论二分、三分、四分还是六分,都将轻声归作最弱的一类。即视轻声为一种轻音。但逆定理不成立:轻音不等于轻声。
巴维尔引用“音节音量”概念,运用音节音量计算公式(注:音节音量V=F[,0]×A×T,F[,0]为基频,A为振幅,T为时长。 )计算北京话音节,将北京话音节分为强音节、弱音节、减音节(大致对应于重音节,中音节,轻音节,笔者注)。减音节最容易失去声调,变成轻声。
轻声的轻音说和变调说并非你存我亡、我存你亡的对立。二说只是研究视角不同。
四 轻声发生的原因、机制及轻声探源
关于轻声发生的原因,一致的看法是:轻声因轻音而发生。
由于轻声是一个关涉语音、词汇、语法的综合概念,因此对轻声发生原因和机制的研究有多种角度。声学方面的研究结论是,由于轻音音节的能量减弱,发生后延协同发音,于是音长缩短,元音的声学空间减小,随之元音简缩甚至丢失,音高变化幅度也一同减小,那些最弱的轻音便成为轻声。
从生理方面解释轻声的发生,是省力原则的作用:重音费力,轻音省力,二者交替出现,使发音器官实现张弛交换,造成间歇,使发音器官不至劳累,从而保证长时间说话的生理机能。
从语言角度看,大量出现的复音词为轻声的出现创造了条件。轻声的依附性决定它的出现必得有依附对象,而复音词提供了这一条件。北方方言口语中活跃的词汇是产生轻声词的温床,而语义虚化是轻声产生的一种诱因。
关于轻声的发生机制,巴维尔提出“重音左移”的假说:由于重音向左移动而造成声调特征永久性失落,于是出现轻声。这种重音左移是北京话形式化的语音标记。他将轻声形成的过程归纳成逐渐推进的5 个阶段:语法结构松散的抑扬格强弱模式(如“你看”)→语法结构紧凑的抑扬格强弱模式(如“服输”)→结构形式化、介于抑扬格和扬抑格之间的强弱模式(如“就是”)→紧密的构形结构、扬抑格(“爱情”)→完全形式化的结构、扬抑格(“车子”),轻声是该过程发展到音节融合之前的最后结果。
相对于轻声的共时发生研究,其历时来源研究就薄弱得多。
根据现有研究判断,轻声的出现不晚于明朝。李荣先生考证了明朝小说《金瓶梅词话》中的“晓得、家火、横竖、央告”等词的异文,确定为“晓的、家活、横是、央及”,与现在语言相联系,认为这些词的后字异文当时读轻声。作者谨慎地称此为假说。如果此说成立,这便是明代有轻声的证据。
五 轻声是一种综合范畴
当人们聚焦于轻声的非声调属性讨论时,轻声的一些异常的声调表现被陆续发现。1987年曹德和报告了巴里坤汉语方言轻声不轻、读高降调的事实,刘俐李1988年发现焉耆汉语方言的相类事实,比如,“桃子、孩子”的“子”读高降调53。王旭东1992年报告和分析了北京话轻声去化现象,即“读轻为去”,比如轻声词“朋友”的“友”读为去声。其中的一些词经过几十年的轻声去化后,其去声读音已被审定为规范音,如“绩”“迹”。2000年魏刚强系统梳理了轻声的各种现象,区别出“调值的轻声和调类的轻声”,“调值的轻声指连读时读得很短的字调,即使原调类依然保持;调类的轻声指失去原调类的字调,即使调值并不短”。调类是一种音系范畴,而调值是这种范畴的表现形式。同一个调类可以用不同的调值表现,如北京话上声调类可有214、35、21 等不同调值;而同一个调值也可以服务于不同调类,如北京话的35既服务于阳平,也服务于上声。同理,轻声作为一种调类,既可以用轻读调值表达,也可以用重读调值表达。北京话的轻声调类通常用轻读调值表达,如“姐姐”“桌子”等,而“石榴”“玫瑰”“稀罕”这类读去声的轻声词,其轻声则用非轻读表达。调值的轻声和调类的轻声在各方言中以不同的方式存在,有的方言只有调值的轻声,有的方言只有调类的轻声,有的方言二者并存,或包含,或交叉。魏文推测出8 种可能出现的方式,并找到了7种方言实例,将魏文的概括表照录如下:
从两种轻声的关系看相关的轻声现象(A表示调值的轻声,B表示调类的轻声)
编号意义 方言现象
代表方言
1AB不相容调值轻短的字都不失原调,失去原调的字调值都不轻短 ?
2AB交叉 调值轻短的字不都失去原调,失去原调的字调值不都轻短北京话
3A包含B 失去原调的字调值都轻短,调值轻短的字不都失去原调 娄底话
4A包含于B调值轻短的字都失去原调,失去原调的字调值不都轻短 万荣话
5AB重合 调值轻短的字都失去原调,失去原调的字调值都轻短北京话
6有A无B 调值轻短的字都不失原调,没有失去原调的字 浏阳话
7无A有B 失去原调的字调值都不轻短,没有调值轻短的字上海话
8无AB没有调值轻短的字和失去原调的字
广州话
笔者认为,轻声不是纯语音现象,而是一种关涉语音、语义、语法的综合范畴。作为一种语言范畴,它必有自身属性,轻声的特性表现在形式和内容两方面。在语音形式上,无论轻读轻声还是非轻读轻声,一律失去原声调,用相同或相类的一种或几种调形表达,其中轻读是其原发形式。轻声的轻读这一表达形式在语音层面与属于韵律范畴的轻音重合。轻声处于音步结构尾部,通常,音步尾部是用力消退阶段,轻声处在发音用力减弱的位置,弱化为轻音,这合乎音理。但处在相同位置的非轻读轻声为什么不弱化?此间的道理尚不清楚,需要继续研究。轻声的内容特性是,负载特定的类型化或形式化的语义——语汇义或语法义,比如指小义或特定情意义,词缀或虚词的形式标记,等。
标签:北京话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