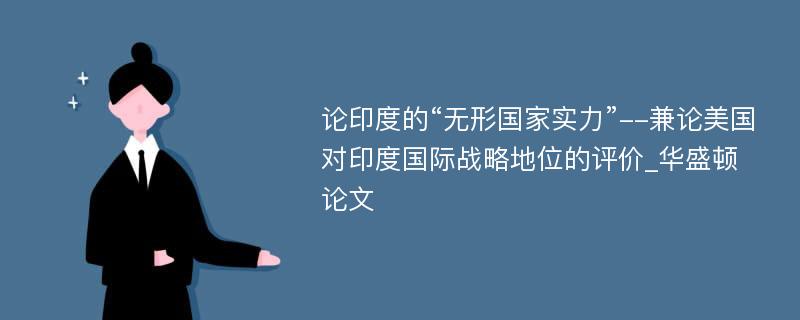
试评印度的“无形国力”——兼论美国对印度的国际战略地位的评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印度论文,美国论文,国力论文,战略地位论文,评价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南亚“处于美国对外优先考虑问题表的中高偏上的位置”,“美国在南亚还没有具体的政策,只有一些主张和倾向”(注:(美)斯·菲·科恩:《美国学者谈南亚有关问题》,《南亚研究季刊》1993年第4期。),这是美国南亚问题专家科恩教授的看法。美国决策层战略远见和战略运筹能力的不足,表现在南亚问题上,而又不仅限于南亚问题。白宫的高级谋士布热津斯基尖锐地批评美国政府“没有一个单一有效的协调一致的制订战略性计划的机制”,他提醒美国朝野人士注意,“在一个只对美国一国依赖性越来越大的世界上”,必须“使美国能够发挥有效的全球战略领导作用”,因为“没有战略的领导作用,往往是不稳固的,而且是有矛盾的。”(注:兹·布热津斯基:《地缘政治的支点》,《华盛顿季刊》1996年秋季号。)
体现布热津斯基的战略思想的美国战略和国际研究中心的对外政策研究报告,虽然内容比较广泛,却不大容易看出它重评和调整南亚政策的明晰思路。该报告关于对亚洲政策的建议中简单地提到“为南亚制定一项通盘的战略”(注:《进入21世纪后的对外政策——美国的领导地位面临的挑战》,美国新闻署1996年10月4日华盛顿电。), 但未阐明这项战略的要旨及其现实依据。报告草拟人所设想的未来世界将是一个“冲突减少到最低限底,经济机会增加到最大限度,民主的价值观占主导地位”的世界(注:《进入21世纪后的对外政策——美国的领导地位面临的挑战》,美国新闻署1996年10月4日华盛顿电。)。 被尼克松称作“世界最大的民主国家”、“一个有巨大希望和巨大痛苦的国家”(注:理·尼克松:《1999——不战而胜》第9章《第三世界战场》,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的印度,与美国的全球战略利益有着紧密的关系。美国既力图“在允许彼此进入美国和外国市场的基础上继续扩大、加强国际贸易、投资体系”、“增加工业化民主国家数目”(注:《进入21世纪后的对外政策——美国的领导地位面临的挑战》,美国新闻署1996年10月4 日华盛顿电。),自然地把南亚经济的改善和发展视为美国在“全球的问题和机会”方面的“重大利益”(注:《进入21世纪后的对外政策——美国的领导地位面临的挑战》,美国新闻署1996年10月4日华盛顿电。),这是美印两国利益的主要的共同点。但是, 这份报告又明确地把“遏止核武器和导弹技术的扩散”列为美国在亚洲的“重大利益”,“促进人权”也属于美国全球性的“重大利益”(注:《进入21世纪后的对外政策——美国的领导地位面临的挑战》,美国新闻署1996年10月4 日华盛顿电。) ,这在不同程度上与印度的国策和战略是相互抵触的。
美国在“冷战后时代”确立的战略目标是:保持美国的唯一超级大国地位与全面优势,保证美国在世界政治、经济体系中的领导作用,建立一整套符合美国政治模式与价值取向的国际秩序。考察90年代美国南亚政策的调整和美印关系的升温,是不能离开这个大背景的。近年来美国出现了认为美印间已形成“战略伙伴关系”、要求印度能同其他大国一起,“在保持南亚地区之外的力量平衡方面发挥作用”(注:(美)弗·弗兰克尔:《印美关系:未来即现在》,《华盛顿季刊》1996年秋季号。)的论调,这既是受美国上层统治集团建立“单极世界”和“民主市场国家大家庭”的欲求所驱动,也是基于美国对印度的国力和国际战略地位的看来是偏高了的评估。
在南亚和全球战略问题的研究中,印度国力的评估问题之所以10分重视而迫切,是因为:在印度争当“世界级强国”的呼声影响之下,美国已有一些人士提出“从全球角度出发,把总的美印关系的重要性放在更突出的地位”,建议美国不但“认可印度在南亚主导地位”,而且“还认可印度作为世界大国的特征”(注:(美)弗·弗兰克尔:《印美关系:未来即现在》,《华盛顿季刊》1996年秋季号。)。早在10多年以前,就曾经有过这样的声音,那时美国有人主张调整美国在亚洲的战略态势,听任印度控制或搞垮巴基斯坦,以求在“坚实的根基”之上改进美印关系,促成两国利益的一致,这样可“使美国的亚洲政策处于在地缘政治上更为高屋建瓴的地位”(注:(美)理·内桑斯:《印度和巴基斯坦》,收入美国大西洋理事会论文集《美中关系未来十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减少苏联的影响,牵制和平衡中国。但当时这种缺乏现实可行性的设想,也只是把“最终接受印度作为本(南亚)地区的首要大国”(注:(美)理·内桑斯:《印度和巴基斯坦》,收入美国大西洋理事会论文集《美中关系未来十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作为目标。
假如今天美国决策者在制定作为“下一个美国世纪”(注:克里斯托弗任美国国务卿时一次讲话中的提法,见美国新闻署1996年1月19 日电讯。)的全球战略的有机组成部分的“通盘的南亚战略”时,真的要突破“过时的(南亚)地区观念”,“把它(印度)视为亚太区域的大强国”(注:(美)弗·弗兰克尔:《印美关系:未来即现在》,《华盛顿季刊》1996年秋季号。),那么,就绝不能不对印度的国力和战略地位作出科学的论证与准确的评估。
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决定和制约其国策与战略的主要的客观条件或物质基础。对综合国力作何估量,如何加以运用,能在多大的程度上使之优化和增值,是国家决策者的战略素养和战略运筹能力的集中表现。
目前世界各国在综合国力问题的研究中,有着不尽相同的评估标准、指标体系与测算方法。1990年美国前助理国防部长、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所采用的评估方法,可以简称为《2·7》分法,即:将国家的综合力量划分为“硬力量”与“软力量”两个方面,“硬力量”由基本资源、军事、经济、科技力量四项构成,“软力量”由国家凝聚力、文化全球性普及、国际机构中的作用三项构成(注:见《世界箴言》杂志1990年3月号。)。1991年, 约瑟夫·奈在他的代表性著作《美国定能领导世界吗》中又使用《2·7》分法来评估和比较美国与它的主要对手的国力。“硬力量”被称为“有形方面”的国力,“软力量”被称作“无形方面”的国力(注:(美)约瑟夫·奈:《美国定能领导世界吗》第三部分《新的挑战》,军事译文出版社。)。约瑟夫·奈的论著表现出大美国主义的极端情绪与对社会主义国家、第三世界国家实行和平演变与“同化”的战略意图,但他的《2·7》分法毕竟为考察和评估本国或外国的国力提供了一种可供参考的新的视角和新的方法。如果考虑到印度作为发展中大国和地区强国的地位,考虑到它的综合国力构成困素的复杂性与软硬力量的不均衡、不协调状态,那么,《2·7》分法尽管存在若干不足之处,试用它来测算印度的国力,可能还是具有一定的现实针对性和可操作性,而且有助于比较全面地、接近客观实际地分析和认识印度的国情、国力与国策。
从40年代末期开始,“尼赫鲁时代”为一个独立自主、繁荣富强的印度奠定了初步的基础,英·甘地母子执政的20多年间印度的综合国力有了大幅度的增长。据我国国力学专家、《综合国力论》作者吴硕风测算,印度的综合国力在70年代居世界第15位,而到80年代末就跃升至第9位。按照国际上通行的说法,80年代的印度是世界第9工业国,与英国差距不大;是第4军事大国,仅次于中国;是第8科技大国,超过巴西、加拿大。印美经济实力的差距较明显地缩短了。但是,印度的“有形国力”与“无形国力”两个方面的发展和增长是不均匀、不平衡的,而且有疏离和脱节的迹象。70~80年代国力的跃升,主要地是由科技力量(尤其是尖端技术和军事技术)加速推进的。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印度高级研究中心主任弗·弗兰克尔教授写道,美、印领导人曾经断言,“从长远看,印度将成为一个亚洲大国,这一估计是在印度众多的人口、巨大的经济潜力及其科技实力的基础上作出的。”(注:(美)弗·弗兰克尔:《印美关系:未来即现在》,《华盛顿季刊》1996年秋季号。)事实上,印度领导层和美国的有关人士对印度“无形方面”的国力的重视程度比不上对待“有形方面”的国力,印度政府和主要政党在印度国力问题的认识和处理上存在着片面、偏颇之处,至今未能在改善和增进“无形国力”方面采取一套正确的方针与有力的措施。
标签:华盛顿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