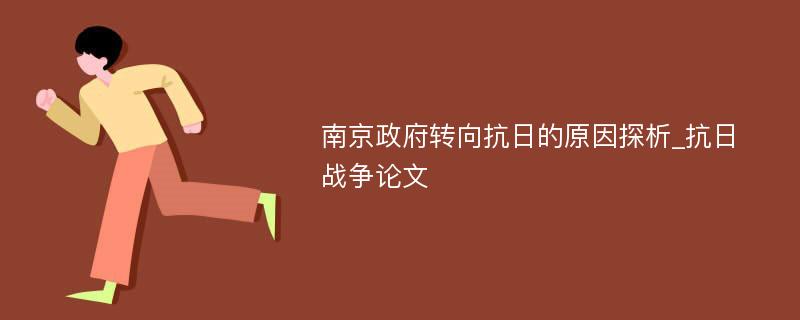
论南京政府转向抗日的原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南京论文,原因论文,政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日本的侵华政策和行动
“九一八”事变以来中日关系的发展表明,南京政府制定何种对日政策取决于日本侵华的程度和规模。“九一八”事变后,日本走上武力侵华道路,第一步目标是中国东北地区。华北是其下一个目标。至1935年秋,日本采取政治压迫、军事威胁、经济侵略三管齐下的方式,力图使华北地区以“自治”的名义从中国分离出来,成为受日本庇护的第二个“满洲国”,进而达到它蚕食中国,最终鲸吞中国的侵略目的。
1.在政治上。1935年9月24日, 日本中国驻屯军司令官多田骏就华北问题发表谈话,声称“必须对组织华北五省联合自治团体的工作予以指导”,“逐渐使华北明朗化”(注:《华北事变资料选编》,河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16页)。10月4日,日本冈田启介内阁通过《鼓励华北自主案》。公然将华北归入日本的势力范围。为实现侵略目的,日本在华北挑起一连串事端,展开各种形式的侵略活动,逐步攫取华北主权。1936年起,日本加大分离华北的力度。1936年1月13日, 日本政府发出第一次《处理华北纲要》,明确指出“自治的区域,以华北五省为目标,先求逐步完成冀察两省及平津两市的自治,进而使其他三省自然地与之合流。”“大使馆的武官和驻扎南京的武官,应适时地使南京政权理解华北自治的必要性,强迫它承认自治权限的六个项目,至少要抑制妨碍自治的阴谋活动。”(注:复旦大学历史系编译《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史料汇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91—193、195页。) 为了加强对冀察政务委员会的控制,努力使其成为一个亲日机构,日本于1936年3月成立北平特务机关,受日本中国驻屯军司令官领导,负责对冀察政务委员会的内部指导和对日本顾问的管理。1月21日,日本外相广田弘毅在日本国会发表演说时重申和进一步解释了所谓“对华三原则”,即:1)中国取缔一切排日运动;2)承认“满洲国”,建立日“满”华经济合作;3)中日共同防共。 其要害在于压迫中国承认伪“满洲国”,并且在华北地区提出了进一步的侵略要求。他威胁说:“如果中国不承认满洲国的存在,和它建立邦交,不进而调和双方的利害,那就无法根本解决”。“这个时期,在原则上有必要采取措施,不使华北方面因日满华三国的关系而发生变化。”(注:复旦大学历史系编译《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史料汇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91—193、 195页。)尽管自“九一八”事变以来,南京政府没有以实力收复东北的决心和行动,但决不承认伪“满洲国”却是其一贯方针,现在日本在这个问题上如此进逼,并且把侵略魔爪伸向华北,这是南京政府所不能容忍的。
2.在军事上。为了配合分离华北的野心,加快侵华步伐。1936 年4月17日,日本内阁决定向中国华北增兵。18日,陆军中央部发布陆甲第六号军令,将中国驻屯军司令官由军部任命的“委任职”改为由天皇直接委任的“亲补职”,使之在职权上与关东军平级并增强约三倍的兵力,同时变更驻屯军的一年交替制为永驻制(注: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编、田琪之译《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1卷第1分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65、67页。)。通过此次增兵,日本在华北的中国驻屯军兵力大大加强,加上有实力雄厚的关东军作后援,日本军方认为必要时可以用武力实现其侵占华北的企图(注: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编、田琪之译《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1卷第1分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65、67页。)。并且日本违反《辛丑条约》的规定,将增兵一部分非法配置在北平西南战略要冲丰台。日本增兵华北,引起了南京政府和冀察当局极大的不安和警惕,不得不重新考虑其对日政策。
3.在经济上。这时期,日本对华经济侵略更是步步进逼,其侵略重点在华北地区。其一,破坏中国的币制改革。1935年11月,中国政府为整顿财政金融,断然实施币制改革。11月9日,日本外务省发表谈话,指责中国币制改革事先未与日方“协议”并取得合作,同时对传闻中的英国对华借款表示“始终持反对之态度”(注:日本外务省编《日本外交年表并主要文书(1840—1945)》下册,第308页。)。 日本政府唆使在华日商银行,抵制法币政策。日本军方更是明确表示“尤其应注重者,为对于与日满有密切关系之华北,强行将现银送出,使华北经济陷于混乱,重苦民众,遂将迫入社会的政治的混乱之境遇,为日本所不能默视”(注:《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丛编》,第2辑第二十册, 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3所南京史料整理处编印,第428页。)。俨然将华北纳入日本的势力范围。日方还积极策划华北“币制自主”,1935年12月,制定《华北自主币制施行计划纲领案》,提出在华北建立新的金融中心,建立“华北公库”为唯一通货发行机关并驱逐法币。其二,加强经济扩张。1935年12月,由日本政府批准,由“南满铁道株式会社”投资成立兴中公司,作为向华北进行经济扩张的机构。兴中公司成立之初,资本为一千万元,到1936年急剧增至一亿元(注:上海银行周报社《银行周报》,20卷40期。)。其三,冀东走私。殷汝耕的“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成立后,在日方的唆使下,擅自制定极低的“关税”,致使日本商品大量从冀东涌入,时称“冀东走私”。这使南京政府蒙受巨大的损失,据当时中国海关当局统计,因为华北走私使海关关税蒙受的损失,1935年8月至1936年4月,为二千五百万元,1936年4月一个月即损失八百万元(注:《日人操纵下之华北走私问题(1936年5月)》,见《民国档案》1987年第4期。)。更有甚者,中国方面对走私的缉查遭到的日方的武力干涉,南京政府财政部总税务司在1936年所写的报告中称:“津海、泰皇岛两关缉私职务,因日人无理干涉,完全无法执行,以致华北一带,私运日益披猖,实为海关有史以来所未见。”(注:转引自张宪文主编《中华民国史纲》,河南人民出版社,第435页。) 关税收入是南京政府维持其统治的主要经济支柱,日本在华北的武装走私和经济侵略,极大地动摇了南京政府的统治基础,为南京政府所不能容忍。
维持和巩固以蒋介石为核心的国民党一党独裁统治,是南京政府制定一切政策的出发点,其对日政策的制定亦不例外。应该承认蒋介石对日本的侵华野心,虽说不上“洞悉其奸”,还是有相当深刻的认识,蒋一再强调日本的侵略是永无止境的,不征服整个中国是不会善罢甘休的。蒋也意识到中日难免一战,但他考虑内政外交政策的着眼点在于如何维护其统治。南京政府“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既违背了广大人民的意愿,也不可能缓和中日矛盾,只会进一步激发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欲望,是注定要失败的。华北事变以来的事态发展表明,日本的对华侵略已经超出了南京政府可以容忍的限度。当时的华北五省,煤产量占全国的45.3%,铁占全国的45.9%,盐占25.7%,进出口贸易额占全国的20.6%,铁路为33.3%,公路为15.2%,小麦28.9%,小米63.3%,高粱为50.9%,玉米36.7%,棉花33.7%(注:商务印书馆《东方杂志》33卷第7号。)。华北整个经济实力占全国的三分之一,仅从经济角度考虑,如果失去华北,南京政府就得垮台。日本分离华北的侵略企图直接威胁到南京政府的统治,南京政府对日妥协退让的道路已经走到尽头。中日关系已到没有调和的余地,南京政府只有抗战一途。
总之,1935年8月至1936年7月一年来,中日关系的走向表明,南京政府与日本摊牌,转变其对日政策的时刻正在到来。南京政府的这种政策转变能否实现还取决于国内的政治局势。
二、中国国内的政治局势
当时中国国内的政治形势,朝着有利于抗战的方向发展。
1.从1935年底起,全国各界民众的抗日救亡运动形成高潮。1935年12月,爆发了“一二九”学生爱国民主运动,标志着全国抗日民主运动高潮的到来。随之在全国掀起了一个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潮,全国各界民众都走上了抗日救亡的政治舞台,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站出来,抗日救亡,发表自己独立的政治观点。1936年5月31日至6月1日,在上海召开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大会, 将原来比较分散的爱国民众运动汇聚成一股更为壮观的洪流,推动国内的抗日救亡运动新高潮持续地向纵深发展。南京政府意识到如果继续奉行妥协退让的对日政策,它就会被人民反抗的浪潮冲垮。
2.国共关系出现转机,国共两党开始秘密接触。国共关系是影响南京政府制定对日政策的一个主要因素。这一时期,国共关系发生了重大转变。中国共产党方面,在1935年的“八一宣言”中提出了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得到国内各阶层的广泛拥护和响应。同年12月,中共中央在陕北瓦窑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根据国内政治形势的特点和阶级关系的新变化,制定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新策略,即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确定,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政策的明显转变。1936年开始,中国共产党逐步由“反蒋抗日”、“逼蒋抗日”转为“联蒋抗日”。4月9日,毛泽东等致电工农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指出目前“中心口号在停止内战,在这口号之外,同时发布主张内战的讨蒋令,在今天是不适当的。”(注:参见《文献和研究》1985年第3期。)5月5日, 中国共产党以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和中国人民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名义向国民党南京政府发出《停战议和一致抗日》的通电,指出:“我们愿意在一个月内与所有一切进攻抗日红军的武装队伍,实行停战议和,以达到停战抗日的目的”(注:《六大以来》上册,人民出版社,第762页。)。7月,中共中央致电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指出:“只要你们立即停止进攻红军和苏区,立即动员全国对日抗战,并实现民主自由与制裁汉奸,我们和红军不仅不妨碍你的抗日,用一切力量援助你们,并愿和你们密切合作”(注:《周恩来年谱》第313—314页。)。中国共产党的上述政策和行动,既极大地鼓舞了全国各界人民团结抗日的信心,推动了全国抗救亡运动的发展;也影响到国民党内部,对南京政府对日政策的转变,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
3.国民党内部趋于统一,南京政府权威上升。南京政府不是一个有绝对权威的、高度统一的强有力的中央政权。自1927年4 月南京政府建立以来,国民党内部各政治派系,军事派系之间内争不息,混战不断,地方实力始终存在,他们与中央政权或貌合神离,或分庭抗礼,明争暗斗,互相之间隔阂很深,这种复杂的政治格局,必然影响到南京政府对日政策的制订和实施。
华北事变后事态发生极大的变化。首先由宋哲元等二十九军高级将领为核心的冀察地方当局凭借军事实力和华北所处的特殊地位,在对日外交上有很大的自主权,并不完全听命于南京政府。但宋哲元毕竟是一位有民族气节的爱国将领,二十九军有抗战的光荣传统,宋哲元集团出掌华北政权有自己的打算。当日本方面意识到冀察当局不是它言听计从的傀儡政权,采取了压迫策略时,宋哲元抗日的态度就强硬起来。5 月,就日军增兵华北,宋哲元发表力保主权的谈话,声明“华北外交刻所争者,为保全全国主权问题,凡不损我国主权者,方可本平等互惠原则向前去做。”(注:(台)《抗战前华北政局史料》,正中书局,第763页。)5月30日晚,宋哲元在北平召集秦德纯、肖振瀛、张息忠、冯治安、刘汝明、赵登禹等二十九军高级将领开会,决定“一切事项均应下最大决心,以彻底保全我国主权为前提,向前努力的奋斗。在平等互惠之原则下,方能与日方谈合作,以事实辟外传之谣言,保障地方治安,谋人心之安定。”(注:国闻周报社《国闻周报》第13卷第22期。)宋哲元的二十九军是华北地方实力派的中坚力量,它拥护中央政府,抵抗日本侵略,推动了南京政府转向抗战。
九一八事变时,阎锡山与日本暗中往来,潜回山西重掌晋绥政权。辛亥革命以来,阎锡山一直控制着山西,视山西为其禁脔,不容别人插手,更不用说外国势力。阎考虑一切的出发点,就是如何保住山西地盘,日本策划华北自治,向阎施加压力,企图染指山西,为阎锡山的不能容忍。从1936年起,阎一反常态,提出了“守土抗战”“牺牲救国”的口号,并下决心“不惜牺牲生命来救山西……谁敢侵略我们,我们就打倒谁。”(注:(台)《阎百川先生言论类编》第3卷,第564页。)中国共产党也因势利导,东征红军西渡回师不久,毛泽东致信阎锡山,表示红军西渡是为了停止内战“促致贵部及蒋氏的觉悟,达到共同抗日之目的。”(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书信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4页。)这对阎锡山触动很大,阎在日本、中共、蒋介石三种力量中反复衡量,认为日本对他威胁最大,因此,采取联共抗日的策略。
南京政府建立以来,国民党内部派系斗争异常激烈。两广当局凭借国民党西南执行部和西南政务委员会这党政两块牌子,一直呈半独立状态。1936年5、6月,两广当局打起“抗日救国”旗号,请南京政府准其“北上抗日,收复失地”。并成立了军事委员会和抗日救国军。事变爆发后,蒋介石和两广地方当局迫于全国人民要求和平解决事变的压力,双方做出一些妥协,最终和平解决两广事变。两广事变的解决,加强了南京政府对日采取强硬政策的实力。
南京政府的势力达到西南地区。以四川为核心的西南地区,在历史上往往成为抗击外来势力的最后基地,据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1935年以前,南京政府的势力被摒除于西南之外,川、滇、黔为地方实力派控制的地盘,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给国民党中央势力进入西南地区提供了契机。在追剿红军的过程中,南京政府完成了对西南地区的控制,增强了中央政府的实力,并有可能将西南地区建设为未来抗战的战略后方。诚如蒋介石所言:“到了二十四年,进入四川,这才真正找到了可以持久抵抗的后方。”(注:《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结》第14 卷第653页。)中央政府有效控制西南地区为其对日采取强硬政策提供了信心。1936 年7月,蒋介石对即将离任的南京政府财政顾问、英国人李滋罗斯说:“对日抗战是不可避免的。……当战争来临时,我将在临海地区做可能的最激烈的抵抗,然后逐步向内陆撤退,继续抵抗。最后将在西部某省可能是四川,继续维持一个自由中国,以待英美的参战,共同抵抗侵略者。”(注:参见《军事史林》1989年第4期。)
三、苏英美对日本侵华的态度
苏联:九一八事变后,苏联出于国家安全的考虑,在远东尽量避免与日本发生直接的武装冲突,以避免两线作战。苏联采取两手政策:一方面,设法与日本保持和平关系,另一方面,推动中国抗战。这一政策的目的是为了维护苏联的安全,但对中国全面抗战局面的形成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1935年10月9日, 国民政府的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通过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探询苏联的援华态度,问如若中国被迫武装抗日,“中国政府能否经过新疆从苏联方面得到军需品?”苏联方面的回答是不仅同意卖给中国军需品,而且希望签订贸易协定和互不侵犯条约(注:参见曹学思、徐广文主编《民国外交简史》第375页。)。从1936年起,苏联开始把援助中国纳入保卫自身安全和实现其“先欧后亚”的世界战略的轨道,通过增强对中国抗日战争的援助,达到利用中国牵制日本,使其无力“北进”的目的。
英美:由于日本对华侵略,损害了英美在华利益,英美政府对日本侵华的态度有了明显改变,从1935年11月起,英美就向日本提出了一系列抗议,同时加强了自己在华的经济实力,以对付日本的经济侵略。到1936年,美国在华投资为218842000美元,占各国在华投资总数的12 %;英国在华投资为1077611000美元,占各国在华投资总数的58.9%(注:陈真等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第283页。)。英国帮助中国进行币制改革,由于英国在华经济力量强大,特别是金融力量雄厚,没有英国的支持,南京政府的法币制度无法实行。另外,英国还向中国保证不与日本商谈有损于中国的协议,1936年2月11日, 中国驻英大使代表南京政府询问英国方面,假如日本政府向英国政府建议,英国对日本在华北的活动不过问,日本则尊重英国在华南的权利,在这样的情况下,英国会持什么态度?(英日)是否已经达成这类妥协?英国外交大臣艾登回答,并没有达成这类妥协,即使日方提出,我们肯定也不会同意,因为它和我们承担义务的九国公约的条款相抵触(注:《艾登致贾德干电(1936年2月11日)》,见《民国档案》1989年第4期。)。1935年12月5日, 美国国务卿赫尔就中国华北局势向报界发表谈话指出:在中国华北地区,有“相当多的美国侨民,若干美国财产和大量美国商业和文化活动。美国政府因此正密切地注视着该地区内发生的事情”(注:《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年版,第480页。)。1936年初,南京政府根据美国财经顾问杨格的建议,把三十八种债券,除去其中少数几种具有特殊性质的之外,按照满期日子的远近,分成五组。五种债券的偿还期限均予以延长,称为“统一公债”,共计十四亿六千万元,利率一律六厘。统一公债使债务支出减少约年达八千五百万元, 还大大简化了债务结构,6月间掉换债券工作如期完成(注:(美)杨格著, 陈译宪、陈霞飞译《一九二七~一九三七年中国财政经济情况》,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1年版,第116页。)。这项措施,减轻了南京政府的财政压力。5月8日,中美签订《中美白银协定》,规定美国政府以市场平均价格向中国购买白银,其价款用美元支付并存入纽约的美国银行,作为中国发行法币的外汇储备,以维持法币与美元的汇率。同时美国同意以中国出售的五千万盎斯白银作抵押,予以中国二千万美元的贷款。
众所周知,英美对南京政府有很大的影响,英美采取支持中国反对日本侵略的立场,使南京政府深受鼓舞,对其转变对日政策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
在日本帝国主义策动华北五省“自治运动”进入高潮,民族危机日益加深的背景下,1935年11月,中国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南京召开。会议主要议题之一是制定对日政策,蒋介石在关于对外关系的讲演中称:“和平未到完全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亦决不轻言牺牲。”但同时表示:“和平有和平之限度,牺牲有牺牲之决心”,若到了和平绝望的时期与牺牲的最后关头,则“当听命党国,下最后之决心”(注: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册,光明日报社1985年版。)。这表明,一方面,国民党南京政府对中日妥协仍抱有一定幻想,没有完全放弃这方面的努力。另一方面,以此次大会为契机,南京政府对日政策发生某些重大变化,从妥协退让转向决心抵抗。五全大会后,南京政府的人事有了较大变动,特别对行政院进行改组,蒋介石取代汪精卫任行政院院长,南京政府的改组,反映了几个值得注意的新动向:1)在国民党内部, 抗日的力量在上升,大部分部长由亲英美派人士担任,亲日派遭到排斥; 2)改组后的南京政府中,包括国民党各派系的成员,党内团结,有所加强; 3)政府机构中罗致了少数“学界名流”,如王世杰、翁文灏等,表现了一点开明的姿态。所以当时舆论评介“此次中枢的新组织,惹起一般国际上的注意,各国都认为比较举国一致的政府”(注:《国闻周报》第12卷第50期。)。
1936年7月10日至14日,中国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在南京召开,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监察委员共一百七十二人出席会议。这次会议是自从1927年4月南京政府建立以来,国民党第一次比较统一的中央全会,各方代表在国难日亟,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时刻,终于愿意捐弃前嫌,共商救亡之策。在会议上,蒋介石对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提出的中日关系的“最后关头”一词作了明确说明:“中央对于外交所抱的最低限度,就是保持领土主权的完整。任何国家要来侵害我们领土主权,我们绝不能容忍,我们绝不签订任何损害我们领土主权的协定,并绝对不容忍任何损害我们领土主权的事实。再说明白些,假如有人强迫我们签订承认伪国等损害领土主权的时候,就是我们不能容忍的时候,就是我们最后牺牲的时候。”(注: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抗战时期·绪编(三)》第666页。)
全会宣言指出:“中国目前形势,非以决死之心求生存,则不能得安全之保障,非举国一致以整齐之步骤挽救,则将无逃于各个击破之危机。……对外决不容许任何分割领土主权之事实。亦决不签订任何侵害领土主权之协定。遇有领土主权被侵害之事实发生。如用尽政治方法而无效,危及国家民族之根本生存时,则必出以最后牺牲之决心,绝无丝毫犹豫之余地。”(注: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册,光明日报社1985年版。)日本一直在逼迫南京政府承认“满洲国”,日本在华北的侵略活动更严重侵害了中国的领土完整和国家主权。五届二中全会对外政策表明南京政府的对日政策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妥协退让的对日政策被摒弃。
标签:抗日战争论文; 日本中国论文; 日本政治论文; 1935年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英国政治论文; 蒋介石论文; 宋哲元论文; 国民党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