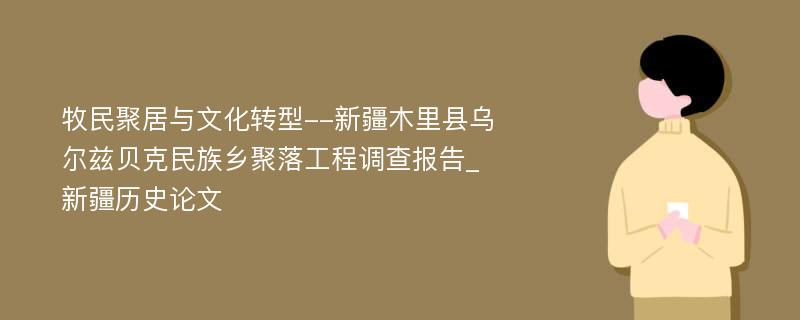
牧民定居与文化转型——新疆木垒县乌孜别克民族乡定居工程的考察报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乌孜别克论文,民族乡论文,牧民论文,新疆论文,考察报告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5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681(2007)01-0047-04
我们的牧民定居作主要是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实施的,至今已有近二十年的历程。那么,牧民定居居交往如何,从游牧到定居,经过文化上的转型,他们是否适应了新的生活方式?带着这些问题,我们选择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木垒县和该县多孜别克乡进行了田野调查。
一、木垒县和乌孜别克民族乡概况
1.木垒县位于天山北麓东段、准噶尔盆地东南缘
东与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接壤,西与奇台县毗邻,南与吐鲁番地区的鄯善县隔山相望,东北与蒙古人民共和国交界,北与青河县相接,为国家级贫困县。
1999年全县总人口为87489人,主体民族——哈萨克族人口为20167人,占总人口的23.05%;乌孜别克族人口为1206人,占总人口的1.38%。在总人口中,农业人口占77.4%,牧业人口占21.5%。
木垒县主要种植小麦、豌豆、玉米、油料、土豆和其它经济作物,由于山地面积大,天然森林茂密,矿产资源和旅游资源也比较丰富。
2.乌孜别克民族乡
乌孜别克民族乡隶属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木垒哈萨克自治县,成立于1987年7月,是全国唯一的乌孜别克民族乡,也是一个居住分散、以牧为主、农牧结合及重点扶贫的贫困乡(是木垒哈萨克自治县四个贫困牧区乡之一)。
乌孜别克民族乡成立初始,乡政府设在距木垒县城西南方向57公里的深山沟-大南沟村(即我们使用的最新版本的《新疆地图册》中的位置,西安地图出版社)。乡政府下辖东沟和大南沟两个村民委员会,七个村民小组,其中纯牧业小组六个、半农半牧小组一个。当时的基本情况是:以畜牧为主,畜产品比较单一,主要有绵羊毛、山羊绒、骆驼皮、骆驼毛等,1981-1985年人均收入一直徘徊在80元左右;两个村不通水、不通电、不通公路,没有一所医院,看病至少要走20公里到乡医院就医,村里的群众半年看不上一场电影;两村各有一所小学,但入学率只有50%,巩固率也只有84%,1986年开始试办寄宿制以后,学生入学率达到了80%;有乡干部11人,其中乌孜别克族5人,村干部10人。
由于木垒县贫困人口的80%以上居住在牧区,而贫困的根源又在于传统的游牧方式。为使牧民逐步实现定居摆脱贫困,木垒哈萨克自治县的各级领导经研究决定把乡政府搬迁到距县城以北13公里处的阿克喀巴克村,1989年从新户乡划出5000亩戈壁,1997年又划出一万亩土地归乌孜别克乡,以建立牧民定居点,种植饲草料和农作物之用。分别于1989年和1997年两次大规模修建牧民定居点,先后共解决258户(占总户数的45%)牧民的定居问题,现在山上还有236户未搬迁,但基本实现了分散定居。
全乡现设三个行政村(东沟村,南沟村,阿克喀巴克村),居住着乌孜别克、哈萨克、塔塔尔、维、汉、回等六个民族,共582户3093人,其中农牧户531户,2936人,乌孜别克族925人,占总人口的29.9%。全乡总面积209万亩,其中可使用草场面积104万亩,占总面积的49.76%,人均占有草场337.33亩;有可耕地15000亩,已开垦耕地6838亩,人均耕地2.23亩。
乌孜别克民族乡的乌孜别克族已基本哈萨克比,与哈族通婚,讲哈语。
二、搬迁定居——现代化的实验
我们这次调查,目的之一就是考察这里的牧民定居与文化适应完成的情况。
进行移民搬迁,就是让牧民放弃熟悉的文化模式,去适应另一种全新的文化模式在这一过程中政府是倡导者也是组织者,牧民是实践者也是接受者;政府是实施主体,牧民是作用客体。在这一对矛盾结构中,政府与牧民的关系互动如何将决定着这场类似现代化试验过程的效果与目标。
基于这种考虑,我们对牧民定居工程的双方,即工程的实施方—政府与接受方—牧民进行了考察。
1.政府方面
为了改变这种面貌,木垒县各级领导班子达成共识,让牧民放弃游牧实行定居。
他们的主要做法是:一是在搬迁定居工作中采取了“一打破三统一,四先四后四当年,四通四有四配套的原则,即:打破行政界限,对定居工作实施统一规划,统一搬迁,统一修建;先弱后强,先治坡后治窝,先生产后定居,先脱贫后完善;力争当年搬迁,当年生产,当年见效,当年脱贫;使牧民新村通路、通电、通水、通邮;人均有住房20平方米,10头牲畜,5亩地,每户有大棚暖圈和青贮池各1座;把牧民新村建成学校、医院、粮站、兽医站四配套的设施齐全,格局合理的新村落。截止2001年仍有236户牧民未搬迁,但也实行了分散定居,牧民新村已为他们盖了100套新房。”二是实行领导干部包扶到户责任制,县级领导每人包5户,科级领导每人包4户,结对子、当户主、保脱贫,签订了责任状。县委、政府要求,全县各级干部、各族群众必须坚决克服安于现状,不求进取的思想,牢固树立自强不息,真抓实干的作风。从1997年3月20日-1999年10月1日,全县党政领导干部取消双休日,并实行脱贫攻坚倒计时,采取“定目标,抓人头,上虎背”的办法,从县级领导到每一位副科级干部,人人都有硬任务,人人都有考核指标,按照责任状每年考核一次,如完不成任务,降级降职。同时要求各级干部不论困难有多大,必须做到思想作风不滑坡。三是成立脱贫攻坚指挥部,分别由副县级领导任总指挥副总指挥,抽调有关部门领导,组织强有力的班子,驻到乡村抓脱贫。同时,从农区村级干部中选拔16名优秀干部,到牧区任乡长助理,兼村委会领导主要抓定居牧民的房屋、暖圈、微贮池建设。四是动员农区和包扶单位,党政机关支援牧区建设。农区向牧区捐草,党政机关干部到牧民定居点帮助修暖圈、微贮池、修路植树。五是加大教育扶贫力度。全县党政机关、事业单位的干部、职工每人包扶1名困难户辍学儿童(共1022名)包扶到完成9年义务教育为止。六是实施10项脱贫致富重点工程,改善生产条件。这十项工程是:10万亩喷灌工程、博斯坦水库修复工程、牧民定居工程、电力增容工程、县乡道路工程、龙王庙水库除险加固工程、现代畜牧业工程、5万亩经济林工程、阿魏茹致富工程、英格堡水库修建工程。这10项工程中有4项是增水节水工程。
的确,为了使这些牧民尽快适应定居生活,县上、乡上的干部还做了大量具体工作。如,牧民们在从事农业生产的初始阶段只知道晴天浇一遍水,不知道阴天刮风晚上也要浇水,包户的各族干部于是手把手地教牧民们农业生产技术:从浇水、施肥、到田间管理各方面都亲自指导,春耕时节更是没白天没黑夜地帮牧民们干活。一些干部风趣地总结说,“我们春天是播种机,秋天是收割机。”再如,号召定居时,县上抽调的干部冬天骑着马进山挨家挨户地做牧民的搬迁工作,有的家反复5、6次去做工作才勉强同意下山;有时父亲的工作做不通就做儿子的工作;转场时民政上又动员大家捐衣捐物。难能可贵的是,在乡政府办公大院建设上大家齐心协力、自力更生,硬是将大院铺上草坪,栽上树木,现已初具规模,与荒凉的奇台县塔塔尔乡政府大院形成强烈对比。
2.牧民方面
牧民们经历的过程大致是由不适应到逐步适应的过程,并显现出愿意主动适应的迹象。定居工作是在政府的“以农养牧,以牧促农”的方针下进行的,牧民们做出的回应是先让一部分年轻人下山,剩下的人留在山上继续他们的传统生活。这样就避免了牧民对陌生环境的不适应,促使他们尽快投入到新的生产生活中。牧民们一般可分得十几亩地,再多了种不了,因为这里缺水。起初的不适应是可以理解的:有人嫌农活太累又回到山上,于是乡里再派人上山去叫;有些分到地的牧民不愿种地,就把地包给外面来干活的汉族农民,自己每年只得一两麻袋粮食,后来一看不划算,就自己种。因为他看到别的牧民种地后收获的粮食比自己要多得多。后来,经过干部们帮助,又过了一年大部分搬迁牧民已逐步熟悉劳作,再由他们带动其它人。木垒县民宗局李主任对我们说,定居有一大好处是牧民们从此可以相互攀比家产、摆设,利于各种信息的交流。以前山上一个家庭十几口人养100来只羊,现在一部分可以种地,所产饲料又可多喂200只羊,劳动力既可以合理搭配,抗灾能力也提高了,牧民们是会算这个账的。
对于牧民们来说,他们以前的生活、生产无一不来自大自然——在山上吃水、烧柴免费,与山下社会的交换大多用钱来完成;劳动对象源自自然的物种,他们的生产更由于季节的更替而迁移。他们习惯了大自然的给予,对他们进行搬迁也完全是政府行为,是一种“外力”,如何将这种“外力”变为他们“主动的行为”的确是一场革命。有牧民说:“我们在山上住得好好的,为啥要下去?羊群就是我们的财富,草原就是我们的家!”。但是经过干部们的不断努力,终于有部分年轻点的牧民告别自己的大家,携儿带女,带着家当搬到了为他们建造的新居。因此,他们起初做出的选择是比较谨慎的:留下一部分亲属,另一部分下山,以免到时没有回旋余地。
已适应定居的牧民现已主动到乡镇农经站询问种什么作物能赚钱,这在当初是不可想象的。他们现在已开始种植特色农产品,如天山白花豆、阿魏茹,搞特色养殖,如土鸡、肉兔等。不少聪明的牧民还发现只种小麦不划算,种草才赚钱。认为一亩草可喂5-6只羊、大畜2-3头,获纯利近2000元,得出的结论是:必须扩大草料种植面积,将牧草、玉米、苜蓿的比例调整适当。这在新疆草场载畜量过大,草场退化的情况下能有这样的胆识实在难能可贵。我们可以设想,不久的将来定居的牧民在这片绿色的草地收获自己的喜悦,届时他们的身份也将发生变化,已不再是传统的“牧民”,与他们的先辈有着本质不同的是这片草地是他们人工创造的。毫无疑问,在提倡绿色、健康消费的年代,木垒的牧民遇到了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除了农业,一些牧民还将目光投向三产。先前耻于经商的牧民现已办起了商店、开起了面粉加工点、食堂,政府适时引导搞起了定期的集市,使山上、山下的牧民对定居阿吾勒的向心力进一步增强。
牧民们定居后还有一个显著变化是庭院里种满了各类蔬菜。牧民们也开始吃炒菜了、吃米饭了,用他们自己的话说,就是不用一天三顿都吃馕了!
为了验证这种信息的准确性,也出于人类学方法论的“后院禁忌”提示,① 我们还在县、乡陪同人员不在场的情况下,随意走访了几户没有列入我们调查计划的牧民家,以补充原有方法的局限。在牧民穆合塔拉木家。我们看到二亩多的院子里不仅种上了榆树、白杨树、沙枣树,而且还有大葱、土豆、地膜玉米;那汗家有苹果树、榆叶梅(我们注意到他们并不知道这花的名称,只知挺好看)、喇叭花,还有全村唯一已挂果的葡萄架,院里种有南瓜、西红柿、大葱、胡萝卜,还养了不少鸡。那汗的儿子哈力木拉提给我们介绍说,家里还有30只羊、5头牛,共种40亩地,其中玉米10亩,其余全为苜蓿。看得出,哈力木拉提作为一名新疆林业学校的毕业生、作为乡团委副书记以及其父为乡学校教师这一背景决定了他们家在牧民新村里的模范示范作用。对此,乡党委副书记阿迪力补充说,“由于那汗家的葡萄栽培获得成功,周围的邻居都去参观。今年乡上准备自行种70亩葡萄,可拉来的苗木牧民们争着要,于是乡上就把大部分给了牧民。我们哈族有一个特点就是亲眼见的东西才是真实的,跟你们汉族‘耳听为虚、眼见为实’一样!”
定居牧民的院落大致是以住房为中心,分前后两个院。前院大多种菜、农作物,后院是牲畜暖棚。小块麦场,有的还有阿魏菇棚。不过院里的功能划分还不是很清晰,显得有些凌乱,甚至在前院菜地上也种上玉米,收获后的地里任凭杂草丛生;院墙处栽的树木也参差不齐,缺乏修整。但无论如何,树是人种的,庄稼也是人种的,蔬菜也是人种的,与以往完全靠“自然”吃饭有了质的区别。我们问他们是否还愿意回到山上放羊,他们都表示坚决定居。看得出这是他们的真心话。眼明的人都能算出定居牧民家的收入远远高于山上的牧民。我们走访的几家粗略统计一下,至少年收入都在万元以上。
日常生活中的一些小发明、小创造往往还可以体现该群体对一种陌生文化模式的适应性创造和接纳。我们在一户人家看到一种推拉式馕坑,与我们以往见到的馕坑有明显区别。传统的馕坑都是有砖或土块垒成一锥形体,顶部开一口,从中加柴烧热内部,然后将和好的面团放入坑内四壁即可。这种推拉式馕坑则从一旁开口,如同新疆冬日取暖做饭常见的铁炉一般,只是这种馕坑的开口比较大,中间置一铁板,比较利于点火。待馕坑烧热后,将面团放入铁板推入炉内,再用铁皮封口。这种馕坑显然比传统的馕坑更便于掌握火候,拆卸也比较方便,无疑是一种创新。
再如,调查时我们注意到才办完婚礼的一户人家的新房和门廊上张贴的双“喜”字,问主人是否知道这字的含义,主人说不知道,只是看到汉族人家办喜事都要贴这个,再说也挺好看的,就贴了。而在其他传统维吾尔、哈萨克社区我们很少见到这种装饰,说明牧民在实现定居的过程中是在开放性地吸收着不同的文化要素为我所用的。因此,在这一过程中,牧民并不是被动的改变者,他们部分地已参与了自我的文化转型和适应。
牧民的定居生活是在政府的干预下进行的,这种干预实际上是在引导一种文化变迁行为的发生。作为当事人主体的牧民所做出的各种反应又都是可以理解的。牧民选择让年轻人先下山适应定居的生活,老年人和儿童则留下来的方式,这样使人们不至于造成太大的冲击感和不适应感,从而使得传统文化既可以得以保留又便于接纳新内容,两者的矛盾易于做到沟通和解决。对此,政府方面给予了相当的宽容和理解,并未采取过于强制性的措施和粗暴的做法,牧民们也切实感受到政府对他们的态度是真心的。
三、结论与讨论
1.定居过程中牧民的文化适应与转型完成得如何?
我们知道,文化是运动着的,运动包含变化,发展又是其必然规律。每个民族的文化如果千篇一律,一成不变,那么这种文化必然面临被淘汰,只有通过反复的实践,人类群体才有可能找到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在这期间,如果有走在前面的民族适事予以协助,或者主流文化为其提供多种选择与参照,这样的外力介入可能会促使其文化的变化。但是无论如何我们也不能想像一名哈萨克族主妇穿着汉族社区家庭主妇的装束,说着带有各自方言的汉语。因为这不叫文化的发展而是文化的复制,自然不符合文化发展的一般规律。因为文化具有传承性,尽管可以发生变化,但某种特性一般不会改变。因此,考察牧民的文化适应情况只有在政府与牧民的互动过程中才可能易于把握。要考虑牧民会接受哪些、不接受哪些要素和现象?是否产生适应另一种文化模式的“新传统”、“新习俗”?是否得体?如果没有,说明这种“变迁”的基础是脆弱的、不牢固的。这几年兴起的参与式发展理论深刻地揭示了这种变迁模式的重要性。
从牧民方面看,在政府倡导的定居过程中,牧民们没有选择家庭整体搬迁的激进做法,而是采取大家搬到山下务农、小家仍在山上放牧的方式,既保留原有牧业文化传统,又便于适应新的生计方式,政府方面对此予以了肯定。这可以看作是牧民对不明朗前途的一种策略性应对。
牧民在日常生活中的各种喜好选择与适应性的创造发明也说明,在政府主导的定居工程中,牧民并不是被动的改变者,他们已部分地参与了自我的文化转型和变迁。牧民在自家庭院栽树引水、农牧业并举等行为均显示了他们对定居生活的逐步适应和由此获得的信心。
因此,这里的牧民是在传统的基础上通过开放性的吸收周边民族的文化来适应一种新的文化模式并且有所创新。传统在这里可以理解为既包括原有价值观念也包括一个族群的历史记忆建构再利用问题。据此,我们有理由相信这种变化过程是真实的也是可行的。可以说,参与式发展的深度和广度可能将是今后牧民完成进一步文化转型的关键所在。
2.对于“定居”的再认识
首先,传统上我们是在“畜牧——落后,农耕——先进”这种观念支配下来看待游牧文明的。事实上,游牧文明同样可以看作是在不同生态环境下人类智慧的结晶,包含了充分的价值。例如,自清末以来内蒙地区的广泛垦殖行为的负面效果已彰现无疑,以至于国家提出通过“退耕还林,退耕还草”的办法使之不再对当地和北京的生态环境构成威胁。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定居农耕”这种方式只是人类顺应自然的一种方式而已,有其适用的层次和范围,一味地将这种模式推崇到及致化,显然有些偏执。另一方面,正是这种观点导致我们片面地认为游牧生计方式是我们理解的“贫困”产生的根本原因。而根据UNDP的定义,所谓人类贫困,实质上是对人类基本权利或能力的一种剥夺,而不仅仅是通常意义上的收入低下,这种剥夺才是导致人类不安全的深层根源。② 故,这里面还有如何发挥实施对象的主观能动性和发展权利的尊重保护问题。
其次,或许中国的农业文明历史悠久的缘故,我们对牧民定居的普遍看法就是从事农耕,这与国外一些国家的做法形成了比较大的差距。例如,前苏联和美国是通过工业化与城市化来完成的(在跨境民族的比较中能够深刻地看到这一点)。
国内的牧民定居工作主要是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由政府主导实施的。由于内蒙古地区距内地近、完全或者大部分已实现了定居,这一工程的重点便转向新疆等地的若干属游牧文化类型的民族。定居作为一种生活方式无可非议,但是我们要讨论的是定居的生计模式选择方式,即:往哪发展的问题。也就是说,现当代的技术手段的利用可能会与某个社会当时占主导地位的话语结构密切相关。显然,我们是将农业生活作为牧民定居后的主要内容来开展的,甚至可以不去考虑当地是否具备农耕条件(如奇台县塔塔尔乡的例子)。只是为了证明一种模式的优越而进行推广,丝毫不去考虑本地这种盆地草原游牧文化类型特点对于实行定居可能会出现的便利与不足因素等都说明我们的思维定势限制了我们对某种模式的判断与选择。
因此,对于“定居”、如何“定居”之类的问题我们有必要进一步地反思。
注释:
①国外人类学中把不愿让别人看见的东西称为文化的“后院”(back region),各种文化的“后院”有所不同,但,都对此有种警觉与防范意识,目的是为了调节给外人的印象,即实行“印象管理”(impression management)。Friedl.john,The Human Portrait:Introduction to Cultural Anthropology[M].Prentice-Hall,Inc,Englewood Cliff,New Jersey,1981.32-33.
②UNDP Overcoming Human Poverty,UNDP POVERTY REPORT 2000,NEW YOR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