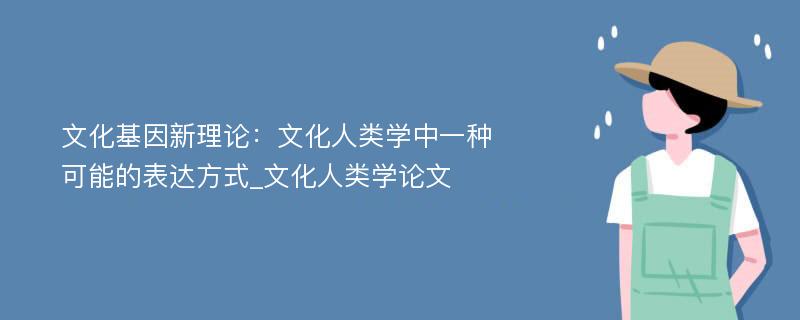
文化基因新论:文化人类学的一种可能表达路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化论文,新论论文,人类学论文,基因论文,路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奥地利生物遗传学家孟德尔(Gregor Johann Mendel),最早提出了生物遗传基因的概念,开启了生物遗传基因研究的大门。一门新的科学——生物遗传学逐步兴起,影响日益广泛。现代生物遗传学已经证明,基因(遗传因子)是有遗传效应的DNA片段,是控制生物性状的基本遗传单位。因此,生物基因是表征“生物本性”存在的一种基本方式。如果与生物基因相类比的话,是不是也存在一个可用来表征人类“文化本性”、深刻影响文化性质的基本文化单位——文化基因?人类文化是不是可以在文化基因的认知与表述中得以重新考量?如果可能,将为文化人类学研究文化提供一种新的表达路径。
一、国内外有关文化基因的研究
国外有关文化基因的研究主要以“谜米”(meme,国内学界一般将meme译为“谜米”)研究的形式体现出来。“谜米”研究,是一种基于复制传播认知的具有传播学性质的研究。“谜米”一词是英国生物学家和行为生态学家道金斯(Richard Dawkins)在1976年出版的《自私的基因》①一书中创造的。道金斯认为,文化中也有类似于生物基因那样的复制,“谜米”即指这样的文化复制行为。《自私的基因》是一个普及生物基因知识的生物学读本。在书中,道金斯使用了一个社会伦理学上的比喻,说生物基因是“自私”的,以此来解读人的生物性,并希望借助“谜米”这样的东西来修复人性中的生物性缺陷。由此可以看出,该书带有一定程度的社会进化论色彩。“谜米”一词的出现,很快引发了一股全球性的“谜米”研究热潮。
1998年,道金斯的学生苏珊·布莱克摩尔(Susan Blackmore)出版了专著《谜米机器——文化之社会传递过程的“基因学”》,希望建立一种“谜米学理论”,以此来解读人类文化的进化。她认为,文化复制始终是一种建立在模仿基础上的复制,这种复制对于人类文化具有重要影响;人既是生物基因的机器,也是文化“谜米”的机器,而且只有这两种复制共同存在才可以构成完整的“人”。②这样的“谜米学理论”,与其说是宣扬社会文化进化论,不如说是在复制传播认知基础上的传播学。
概而言之,国外的“谜米”研究,是文化复制类似于生物基因复制的一种概念表述,是文化之社会传递过程的“基因学”,对于研究人类文化的进化有着明确的意义和影响。“谜米”研究,从文化养成和传播上触动了人类文化本性深处,因为人们可以在传递和复制文化的过程中选择、“改善”自己的文化。诚如道金斯所言:“在这个世界上,只有我们,我们人类,能够反抗自私的复制基因的暴政。”③可以说,“谜米”的出现,是当代达尔文主义者对于文化进行解释的一个重要窗口。当代达尔文主义者把生物进化的理论直接引用到人类文化进化的论述中,把人类文化的演进视为一种类似于生物进化的过程,并且利用现代基因科学的遗传学说,强化了社会文化进化论学说,“谜米”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的一种文化借喻。这个借喻最初的目的是希望人类文化中存在基因那样的东西,从而“修正”人类生物基因的“缺陷”。但是,这里有一个基础性的概念置换,即把“自私”的社会伦理的概念,置换为生物基因的复制和复制选择的概念。因此,在一定意义上讲,道金斯把生物基因描述为“自私”并以此来论述人类文化进化的意义也是存在问题的。
总之,自1976年“谜米”一词出现后,国外的“谜米”研究一直围绕文化复制和传播机制来进行,“小心”地“限制”在文化交流和传输路径之上,是一种传播学意义上的学问。
中国的文化基因研究,有着比较广泛的展开,既有传播学意义上的,也有文化结构意义上的。1981年,在道金斯《自私的基因》一书刚被翻译成中文后,“谜米”很快就变成了中国人所理解的“文化基因”一词的代名词,且被广泛传播和应用。米文平、刘长林较早使用了文化基因一词。④之后,国内有三类学术群体在进行文化基因的研究:哲学学者和理论学者,如刘长林等,以文化基因论来宣扬社会文化进化论;⑤文化史学者,如刘植惠等,梳理传统文化的谱系,从文化传承的角度来论说文化基因的意义;⑥民族学者、文化人类学者,如徐杰舜等,认为人类文化结构中存在本性因素,并且可以影响文化的基本存在。⑦在中国,目前有两种关于文化基因研究的路径:一种是“谜米”的路径,以中国的哲学家为研究主体;另一种是自在的受基因科学发展影响所致的文化基因研究,以民族学家和文化人类学家为主体。这两种研究都把自己的研究当做文化基因研究,前者注重思维模式的研究,认为哲学领域才会涉及文化的基本因素问题;后者关注的是文化的结构构成,探寻在这样的结构中有没有类似于基因的结构,并以此来论述人类文化的最为深层次中的普遍性。
强调复制和传播的文化基因研究很难涉及文化基本性质的理解与文化基因图谱的“建设”,没有办法解决“文化人”在未来的存在意义和路径问题;强调思维模式的以哲学为起点的文化基因研究,也未涉及文化结构的基本性质,无力解决文化基因研究中的许多根本问题,而其中所谓的“文化基本因素”研究,事实上与“文化结构”研究相去甚远。
本文从文化人类学的视野出发,试图揭示和引发一种新的文化基因研究,以寻求人类文化中一种最为初始的具有普遍性的意义结构。这种结构可以普遍影响人类文化的基本建构和表现形式,可以在最为初始的状态中加以认知和表述,对人类所有的文化类型有着基础性意义。
二、结构人类学与文化基因的认知与表述
1865年,孟德尔的“基因思想”还仅仅是一种逻辑推理的产物。这个伟大的思想在20世纪初期通过遗传学家摩尔根(Thomas Hunt Morgan)的果蝇遗传实验得到了科学实证,成为一种科学。随着分子遗传学的发展,尤其是双螺旋结构学说提出以后,人们才真正认识了基因的本质。基因是表征“生物本性”存在的一种基本方式。这种认识,对于人类文化而言,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在文化人类学中,关于文化相似性有两种观点:一是说文化相似性由文化传播所带来;一是说文化相似性来自相似的历史发展阶段。前者引出了文化中心论,后者引出了文化相对论。在这样的讨论中,涉及了文化圈和文化区的概念,即一个文化体存在会有一定的范畴,表现为一种形式,而文化圈和文化区概念本身也都具有相似性的意义。在人类生物基因科学的启示下,我们可以大胆地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或者假设:为什么文化相似性不是某种文化基因的存在带来的呢?
人类历史可以追随到上万年之前,可以直接用文字来记录的人类文明史也有数千年之久。可以说,在这个过程中,人类文化也积淀了或者说也“进化”了许多类似于DNA的具有复制功能的片段。当然,这样的“文化复制”并不能与DNA复制作等同理解。在某种意义上讲,这种文化基因思想在文化人类学历史上曾有过一定程度的展示,那就是结构人类学。可以说,结构人类学的出现,开启了文化人类学中从文化基因角度研究人类文化的先河。
“结构主义学派产生于20世纪40年代至20世纪50年代……结构主义者们认为,在人类社会文化的表面结构之后,都隐藏着一种真正的社会结构,人类学研究的任务就是要用建立模式的方法去分析、说明和揭示这种结构,并揭示人类的思维结构。结构主义的代表人物主要是法国的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英国人类学家利奇也被认为是代表人物之一”。⑧结构主义最初是从语言分析开始的,文化人类学家主要将其用于婚姻和仪式的研究。结构主义首先是一种方法论。正如索绪尔等人把结构主义的研究方法应用到语言学研究中一样,列维—斯特劳斯亦把结构主义的研究方法应用到文化人类学研究中,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使结构主义人类学成为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文化人类学学派之一。
列维—斯特劳斯认为,社会是由文化关系构成的,而文化关系则表现为各种文化活动,即人类从事的物质生产与精神思维活动。这一切活动都贯穿着一个基本的因素——信码(符号),不同的思维“型式”(type)或心态是这些信码的不同排列和组合。他通过对亲属关系、思维“型式”和神话系统进行深入研究,试图找到对全人类(不同民族、不同时代)的心智普遍有效的思维结构及构成原则。他认为,在人类文化中,处于人类心智活动深层的那个普遍结构在无意识地发生作用。⑨
在结构主义人类学的表述中,可以看到这样一种努力,即在人类社会和文化中,寻找一种能够解释人类文化基本规律和因素的结构,回答人类文化中是不是存在类似于生物基因的东西的问题,以此更为深刻地理解人类文化。虽然很难说我们已经找到了准确描述“文化DNA片段”的形式,但毋庸置疑的是,结构人类学的这些努力已经在向这个方向前进。当然,我们也可能永远无法准确描述它,因为人类文化的核心从内容到形式都是观念的和精神的。
在结构主义人类学的表述中,符码的存在一定会走向结构。把文化的一系列表现看成是一系列的符码,涉及的一定是结构的意义。在列维—斯特劳斯看来,事物都是一个个相互“对向”(apposition)存在的,并且以此来显示它的文化意义;当一个“对向”事物在失去原来的“对向”事物后,可以获得新的“对向”事物,从而产生新的文化解释和新的文化意义。⑩这样的结构,是不是可视为“文化基因双螺旋体”的一种表述?
在索绪尔研究的引导下,人类文化的研究走向了符号,符号学的产生使人们在人类文化的认知上有了一个符码意识,即人类文化可以被视为一系列的符码存在,人们可以在一系列的符码中理解人类文化的一切。这种符码意识使人们可以在一般的文字文本中“抽象”出一系列的符码,建立符码系统,并以此来分列文化,建立符码文本,分析和研究文化。这是文化编码的一种尝试,有些繁琐和复杂,更像一些智者的文化游戏,但它的文化指向是正确的,文化研究需要这样的编码。因为文化基因的存在形式(如果它的确可以被准确描述的话)应该是一系列的文化编码。它不一定是生物基因的双螺旋体的编码排列,不一定具有如生物基因那样精确的复制功能及自我复制的原始动能。重要的是,要在这样的认识中深刻地理解文化及其意义,而不是简单地借喻生物基因的自我复制功能来想象性地“类比”文化基因。
三、文化人类学与文化基因的认知及表述
现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发展已经为人类文化基因结构谱系的描述提供了一定的可能性。至少在人类文化发展的一些基本点上,相关研究已经取得了显著进步。有关人类起源研究的重大进展,以及文化演化、涵化、传递、复制、编码问题的深入讨论等,在一定程度上为今天的文化基因新论做了最好的理论与实践准备,因为这些研究主要关注的就是“文化本性”问题及人类文化的基本结构问题。结构主义人类学论述了文化的结构,揭示了结构的基本形式。这是文化基因新论的曙光,表明人类文化是可以从文化基因的角度加以理解的。
从文化人类学的视域来看,可以认为人类文化是被人类自身“结构”起来的,是人类自身结构化的产物。因此,人类文化可以通过分析结构加以研究。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分析,只在婚姻和神话中发现和分析了人类文化的结构性质。在某种意义上讲,人类文化是可以全部结构化的,可以在一个具有共通性的基础上被认识。在人类工具的使用过程中,工具的物质形态逐步被“磨灭”,但是,工具的形式却可以留存下来,并且可以依靠另外的物质来复制其物质形态,使这个工具的形式在新的材料下重现。这个时候,可以发现,这个工具形式的延续有了一个重大的意义。最初创造这个工具的人已经死去,但他却在这个工具的形式中“存活”了下来,看见这个被复制的工具就可以意识到他的存在。人在工具的形式存在上意识到人的存在,这也为人类提供了一个认识自身的最为基础的可能性。这种意识直接成为人类文化中精神和价值意义的源头,在此基础上人类文化逐步建立起自己的复杂系统。工具的形式存在,就是人类文化基因的一种存在状态,可以代代传承下去。这也是我们今天可以把生物基因和文化基因进行类比性表述的基本前提。
文化人类学的一个基本观点在于,人类文化是人类人性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文化性和生物性共同组成了人性。人类的基因图谱(生物基因图谱)是表示人类体质因素的图谱,但那不是人的完整表达。因为如果不能同时体现文化性和生物性,人是不完全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人类的文化基因应该是存在的,这也是人之为人的根本所在。现代生物技术的发展,或许可以把人类自己造自己的“神话”变为现实,但这里有一个问题,即通过这种方式复制出来的人是文化性和生物性兼具的完整意义上的人吗?
另外,文化基因也是可以被表述的。虽然还不能建立类似于生物基因那样的完整图谱来准确描述它,但它的一些基本概念和相关概念,如文化基因的原点、节点、支点、衍生点等,可以在文化人类学的宏阔视域中加以具体表述。
文化基因的原点(也可称为基点和原始发生点),是文化结构的起源点,比如神话传说中的“从前”,爱因斯坦所说的光在弯曲后重新汇聚的那个点(即宇宙学上称为的奇点)。人类的文化结构存在这样的原点,但这不是人类文化的初始点,人类文化的初始点在于没有结构的“自意识”。这个原点出现前,人类是存在自身文化的,只不过是一些散漫性的前文化。也就是说,在这个原点出现之前,人类已经有了前文化的存在,储备了人类文化基因的许多要素。
文化基因的原点,即文化结构的起源点,其结构性缘何而来?笔者认为,是从“围猎”而来。作为人类,已经不能满足于从单纯的工具力量中带来的力量,而需要寻求统一的一致性的“围猎”,即需要一定的文化结构将持有工具的人“结构”起来,成为一种新的力量形式,这就是人类文化原点出现的基本原因和基本动力。这个变化带来了两个结果:一是由此把人类从“半人”带向了“人”,使人类在具有生物属性的同时具有了文化属性,从而成为完整意义上的人;二是使人类文化具有了结构性质,具有了文化基因的性质——人类在维持这个文化结构力量的时候,使其具有了可复制性(传递)。否则,这个文化的结构性就没有意义了,而这种性质正好体现了类似于生物基因的性质。文化基因之所以称为文化基因,就是它一定具有可复制(传递)的性质。这种复制,是潜在的和相对自主的,一旦启动,就会自主凝结一切文化能量,最终形成一个文化形式的机制存在,而且是不可逆转的。
文化基因的原点之基本内容就是世界起源的解说和人类起源的解说。这两个解说是关联一体的,有什么样的世界起源,就会有什么样的人类起源。而人类文化可以用文化基因来做普遍性解释的依据在于,不管何种世界起源和人类起源,这两种起源解释都会在所有文化式样中存在,成为人类生存于自身文化之中的基本理由。科学文化也没有“逃出”这个文化基因的限制。
文化基因的原点是一个基点,亦即文化基因的结构性基点。在这个基点上,人类文化出现结构性特征。这个基点成为某一文化形式的原始发生点,即这一文化形式要在这一点上“生长”自己的文化了。在这一点上,首先形成了一种可被称为信仰块的文化事物。这个信仰块的性质如何,会决定性地影响后续的一切文化“生长”。这有点像土豆的种块,如果种块饱满而强大,这个文化体就“生长”得很好。在这个信仰块上,会生发出许多“苞芽”,这些“苞芽”的数量和质量,基本决定了这一文化体的内在性质。这样的“生长”对于人类的文化体来说,只有一次的生长机会,也是不可逆转的。当信仰块在原点中“生长”出来之后,会迅速生长出许多节点,这些节点为这一文化体的“生长”提供诸多可能性。不管今后的文化发展情形如何,这些节点都是关键性的存在。
这些从信仰块中“生长”出来的节点,会在未来形成许多支点,正如树木生长过程中出现的不同枝杈一样。
在文化基因的表述概念中,还可以讨论“衍生点”的问题,即在所谓的文化发展中去寻找的文化“展演点”和“衍生点”。很多民间信仰文化都是在一个基本的信仰文化平台上建立起来的,都会在其信仰文化的平台上“展演”与“衍生”,出现文化“展演”的可能性。
原点、节点、支点、衍生点是所有人类文化体共有的结构性事物,是人类文化的基本结构。在所有的不同性质的文化体中,都有这样的存在,它们决定了文化演化的进程,是一个文化体之所以成为一个文化体的根本存在,所有的文化体都要以原点、节点、支点、衍生点的形式来发展自己的文化体。
总之,人类文化可以从文化人类学的视域出发,在文化基因的认知与表述中得以重新考量,由此也为文化人类学研究文化提供了一条可能的新路径。
四、文化基因新论的实践意义
在以上文化基因新论的理论认知中,原点、节点、支点、衍生点在解读人类文化中有着广泛的实践意义。
原点的历史影像在某些方面可能并不是太清晰,但对于世界起源和人类起源的描述却是非常重要的。今天,每一种能够成为独立类型的文化都有自己独特的起源描述。当起源描述被某个人类群体承认和接受之后,这个群体的文化结构就可以建立起来,文化基因也因此有了存在的理由与依据。科学时代是以真理和理性为基础的时代,也需要或者说受到文化原点性质的文化基因驱动,因为科学时代需要世界起源和人类起源的真实描述,在此基础上科学时代的文化类型才可能真正确立起来。
从原点的角度来看,巫术应该得到重新理解。巫术不是一种与科学相对立的“迷信”,而是人类实现文化结构性的一种最早努力。人类简单的个体性工具力量借助巫术等文化结构手段结合成为群体性工具力量,来完成狩猎等生产活动,这与群体性动物利用动物的习性实现群体“狩猎”有了本质的不同。也正是巫术的主观性决定了今天人类的文化创造性、想象力,从想象到实践、从巫术到科学也可以被理解为人类文化基因发展的基本路径。
节点在认识人类文化的演化中也有新的启示。节点的出现,影响了某些文化类型几千年甚至更长的历史历程。在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有文字记录的文化群体是以黄帝、炎帝和蚩尤为首的三个群体。文字记录中都说前二者在武力上打败了蚩尤,形成了今天中国文化版图的基本格局。但是,从根本上讲,蚩尤不是被武力打败的,而是被一种文化策略——“妖魔化”——打败的。正是这个“文化节点”,几千年一直像一个魔咒一样笼罩在蚩尤族群之后裔的文化上,直接影响华夏人对待蚩尤族群之后裔的文化策略。
支点、衍生点对于文化现象上的研究也具有新的发现和阐释的可能,比如审美和实用功能之间的关系理解,戏剧与仪式神性之间的关系理解,以及文化保有与变迁之间的关系理解等。人们已经习惯于以现代审美的观点来看待古代器物上的图案和色彩等原始艺术。可以说,这些原始的图案和色彩是在具有实用功能的文化支点上生长出来的事物。因此,若不理解支点下面的文化,则很难真正体会其审美价值。在中国南方的不少地方,可以看到祭祀仪式中出现的戏剧。它们演出的本意是给神看的,在一定程度上戏剧就是仪式的延续,这样的戏剧自然是神性的,但同时也是世俗的,因为正是文化基因中的支点生长了这样的事物,使其成为世俗戏剧的原始形态。作为文化支点上的更小的但更具有发展性的衍生点,比如少数民族民间仪式中的服饰、歌舞、竞技等,它们一方面与其本体紧密相连,一方面则容易发生变异,对于理解文化保有与变迁有着特殊作用。
文化基因是文化类型的存在根本,每一种能够成为独立文化类型的文化都深深根源于自己的文化基因特性之中。西方文化中心论中有这样一种观点,即人类的语言是从图形符号逐步进化而来的,最后发展成为拼音文字,因而西方的拼音文字是目前世界上最为先进的文字形式。这个观点直接影响着全世界。韩国的文字在试图拼音化,中国有些人也在试图这样做。事实上,拼音文字并不是从图形文字进化而来的,而是源于最初的生理感知形式。欧美的文明源头非常重视声音的意义,重视“听”(如“上帝的福音”);而以中国为代表的东亚文明源头则比较注重图形的意义,重视“看”(如中国传统信仰中的偶像崇拜)。由此,才有了语言符号记录形式中声音文字和图形文字的区别,二者之间并不存在所谓的进化关系,这是由各自的文化基因特性所决定的。文化基因新论并不支持独立的文化类型之间的相互进化论断,正如树木不是小草进化来的一样。可以说,文化基因新论在批驳西方文化中心论中也有重要意义。
五、结语
人类文化存在“文化本性”,即人类文化有自己的文化基因“图谱”,从而决定着其文化的基本性质;人类的文化基因可以被“遗传和复制”(传递),人类文化的延续就是“遗传和复制”(传递)所致;人类的文化基因可以被认知和“解码”(表述),可以在这种认知和“解码”(表述)中更为深刻地理解自身文化;在人类文化“遗传和复制”(传递)中可以部分修正基因构件,由此使人类文化的发展更为符合基本人性。目前来看,可以阐发人类文化基因存在的意义,能够部分解读文化基因中可以成为原点、节点、支点、衍生点的事物,但还不能准确描述出如生物基因那样的人类文化基因“图谱”。文化基因的视角在人类未来的文化演进和理解中是有意义的,至少可以为文化人类学研究文化提供一条新的可能路径。事实上,本文也只是从文化人类学的视野出发,试图揭示和引发本文所论的这样一种文化基因研究,目的在于抛砖引玉,为展开广泛深入的文化基因研究提供线索和基础。
注释:
①参见[英]R.道金斯著,卢允中、张岱云译:《自私的基因》,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
②参见[英]苏珊·布莱克摩尔著、高申春等译:《谜米机器——文化之社会传递过程的“基因学”》,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2页。
③[英]R.道金斯著,卢允中、张岱云译:《自私的基因》,第281页。
④参见米文平:《欧厥律即今鄂温克——兼论古民俗中的文化基因》,《北方文物》1988年第2期;刘长林:《宇宙基因·社会基因·文化基因》,《哲学动态》1988年第11期。
⑤参见刘长林:《宇宙基因·社会基因·文化基因》,《哲学动态》1988年第11期。
⑥参见刘植惠:《知识基因探索》,《情报理论与实践》1998年第1-6期、1999年第1-6期。
⑦参见徐杰舜:《文化基因:五论中华民族从多元走向一体》,《湖北民族学院学报》2008年第3期。
⑧林耀华:《民族学通论》,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30页。
⑨参见[法]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著,陆小禾、黄锡光等译:《结构人类学》,文化艺术出版社1989年版,第73页。
⑩参见[法]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著,陆小禾、黄锡光等译:《结构人类学》,第76页。
标签:文化人类学论文; 文化论文; 生物科学论文; 结构主义理论论文; 人类学论文; 生物起源论文; 基因结构论文; 自私的基因论文; 科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