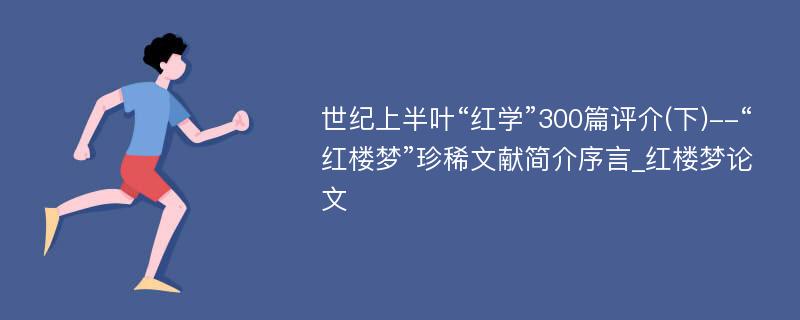
本世纪上半叶红学论评三百篇述略(之二)——《红楼梦稀见资料汇要》前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红楼梦论文,本世纪论文,之二论文,前言论文,百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六
考证作者家世和研究版本是新红学的主要贡献,本书既原则上不收胡、俞等诸红学大家的论著,因而这方面的文章自然相对地少。尽管如此,仍有一些重要篇什值得今人参考。
李玄伯《曹雪芹家世新考》和严微青《关于〈红楼梦〉作者家世的新材料》发表于三十年代,(注:李玄伯《曹雪芹家世新考》,载1931年5月16日、23日《故宫周刊》八十四、八十五期; 严微青《关于〈红楼梦〉作者家世的新材料》,载1936年5月25 日《时代青年》创刊号)是曹家朱批奏折发现后较早的研究成果;四十年代初,又有周黎庵《谈清代织造世家曹氏》一文,也是根据这些新资料提出对雪芹上几代家世看法的,徐文滢《〈红楼梦考证〉的商榷》肯定新资料提供的事实,对“自传说”则大持异议(注:周黎庵《谈清代织造世家曹氏》,载1940年2月《宇宙风乙刊》第二十一期, 徐文滢《〈红楼梦考证〉的商榷》载1942年3月上海《万象》第一卷第九期)。 故宫博物院所藏的这批文献资料,今天普通读者都能看到,家世研究业已极大地拓展和深化,但我们仍可从上述文章中了解当年获知这些新材料的兴奋和由此推导得出的论断。由对家世的探讨自然联系到雪芹的祖藉,李玄伯的文章提出了“曹寅实系丰润人而占籍汉军”, 正是曹雪芹祖籍丰润说的来源。 至1947年12月,北京《新民报副刊》有一署名守常的短文《曹雪芹籍贯》,主丰润说;同月在青岛《民言报》晚刊上刊有署名萍踪的《曹雪芹籍贯》,文更短,所见雷同于上文(注:守常《曹雪芹藉贯》,载1947年12月7日北京《新民报日刊》;萍踪《曹雪芹籍贯》,载1947年12月 23日青岛《民言报晚刊》)。青岛之文被时在山东大学的杨向奎所注意,致信胡适请问祖籍问题并转引该文,胡适因作复申述“曹雪芹的家世,倒数上去六代,都不能算是丰润人”。胡适的答复载1948年2月14 日《申报》“文史”第十期,今作为萍踪文之附录收存。关于祖籍问题,这一时期并未引起更多的讨论。
版本方面,容庚在二十年代有《红楼梦的本子问题质胡适之俞平伯先生》一文连载于北京大学的刊物,他以自己购得的一部旧钞本和排印的程本进行对校,中心意思在论证:“钞本当在程本之前,钞本已经是百二十回,则后四十回断不是高鹗所补作。”(注:容庚《红楼梦的本子问题质胡适之俞平伯先生》,载1925年11月、12月《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第一卷第五、六、九、十一期)对高鹗续作说持异议的还有宋孔显,他的题目即标举《红楼梦一百二十回均曹雪芹作》,不过论证的角度不同于容文,是从程高的序、引言以及前八十回也存在矛盾疏失等方面来加以说明的。(注:宋孔显《红楼梦一百二十回均曹雪芹作》,载1935年5月《青年界》第七卷第五号)关于正文的文字, 有一则短文很引人注目,这就是见于1924年《小说世界》上吴轩丞的《红楼梦之误字》,谓第十二回“是年冬底,林如海病重”,据作者在金陵四象桥下购得的一册《红楼梦》残钞本,其中“冬底之冬字,作八月二字,并写一格中”,于是原先“颇费猜疑”的时序上的矛盾得以解决,“不觉恍然大悟”。(注:吴轩丞《红楼梦之误字》,载1924年1 月上海《小说世界》第五卷第一期)吴轩丞即吴克歧,为《犬窝谭红》撰者,此处所举系残钞本重要异文之一。另有署名素痴的《跋今本〈红楼梦〉第一回》,指出今本《红楼梦》以“此开卷第一回也”起,而这起首一段本是评语的总序,“传钞者误以与正文相混,相沿至今”。(注:素痴《跋今本〈红楼梦〉第一回》,载1934年3月10 日天津《大公报》“图书副刊”第十七期)
关于所谓旧时真本的一则记载,见于境遍佛声《读红楼梦剳记》:“相传旧本红楼,末卷作袭人嫁琪官后,家道隆隆日起,袭人既享温饱,不复更忆故主,一日大雪,扶小婢出庭中赏雪,忽闻门外诵经化斋之声,声音甚熟习而一时不能记忆为谁,遂偕小婢启户审视,化斋者恰至门前,则门内为袭人,门外为宝玉,彼此相视,皆不能出一语,默对许时,二人因仆地而殁。以上所云,说甚奇特,与今本大异”。(注:境遍佛声《读红楼梦剳记》,载1917年3月《说丛》第一、 二期)另有三六桥本,情节与此不同,北大张琦翔文中提及,“在日本三六桥又有四十回本(按,似应作三十回本),传闻如此,未见本书”(注:张琪翔《读〈红楼梦〉札记》,载1943年6 月《北大文学》第一辑)今将张文收入备考。
后四十回问题自新红学家提出之后歧见极大,可谓南辕北辙、天上地下。持肯定意见的不乏名家,如吴宓认为“愚意后四十回并不劣于前八十回,但盛衰悲欢之变迁甚巨,书中情事自能使读者所感不同,即世中人实际之经验亦如此,岂必定属于另一人所撰作乎?”(注:吴宓《石头记评赞》,载1942年11月桂林《旅行杂志》第十六卷十一期)佩之谓“依全书结构而看,这书万万不是出于两人”(注:佩之《〈红楼梦〉新评》,载1920年6月25日《小说月报》第十一卷第六号)。 许多论者都是把全书作为一个整体来评价并激赏其续作和结局的,牟宗三的见解可作代表:“人们喜欢看《红楼梦》的前八十回,我则喜欢看后四十回。人们若有成见,以为曹雪芹的技术高,我则以为高鹗的见解高,技术也不低。前八十回固然一条活龙,铺排的面面俱到,天衣无缝;然而后四十回的点睛,却一点成功,顿时首尾活跃起来。我因为喜欢后四十回的点睛,所以随着也把前八十回高抬起来。不然,则前八十回却只是一个大龙身子,呆呆的在那里铺设着,虽然是活,却活得不灵”。“全书之有意义,全在高鹗之一点。”(注:牟宗三《红楼梦悲剧之演成》,载1935年12月15日、1936年1月15日《文哲月刊》第一卷第三期、 第四期)持贬抑和否定见解的,也很有力量。且看李辰冬的评论,他以为前八十回“所描写的是人类的灵魂,所以事实少而意象与情感多”;“自从八十一回以后,描写的完全是些事实,所以我们读的时候,味如嚼蜡,枯燥生涩,好像是从前八十回里取些事实,而把些事实写个结束罢了,引不起一点意象与情感。他所描写的是中国大家庭的琐事,而非人类的灵魂。前八十回的《红楼梦》是世界的作品,而后四十回是清初中国家庭的情形。前八十回能百读不厌,且每读一次都有些新的发现,而读后四十回的目的仅在知道故事的结束,结果知道了,没有再读的勇气。”后四十回的中心思想,以四个字了之,就是“福善祸淫”,(注:李辰冬《〈红楼梦〉辨证的再论识》,载1937年6月10 日《光明》第三卷第一号)李辰冬从思想、风格与环境来分析前后的异质,较之胡俞就版本、回目与故事情节等判别二者的不同更进一步。王璜从语言的角度断定全书决不是一个人所写,“最足以证明后四十回是高鹗续写的,却是书里的文字用语。高鹗只续完《红楼梦》的故事,却没法续用曹雪芹所采用的日常用语。后四十回的语言,单调而枯燥;续者虽深深感到语言的贫困,却没法一谋解放”。“后四十回的作者,虽能体会前八十回作者的用意,凑补这未完成的故事,但因不善采用这些贵族层的日常用语,(也可以说,根本不注意语言的运用),而遭受悲惨的失败。”(注:王璜《论〈红楼梦〉里的文学用语》,载1944年7月15 日《东方杂志》第四卷第十三号)有的论者贬斥更甚,谓“高鹗的国语程度,只不过四十分左右,而妄想弄巧,其成拙也当然,实在太看不过高鹗的横行无忌”。(注:华皎《红楼梦的语言及风格》,载1942年4 月南京《古今》第二期)更有人代贾宝玉拟“致高鹗的抗议书”说,“您把我硬拉下水去做和尚……也把我宝钗姐姐写得太不堪了”。(注:羽白《贾宝玉致高鹗的抗议书》,载1948年10月7 日北京《新民报日刊》)这虽近游戏文字,却也反映了对后四十回的看法。正反两面的论评尚多,不胜枚举。我们看双方的理由和语气,真是旗鼓相当,莫能相下,这种歧见和争论,一直延续到当代。
索隐派在这一时期虽不像清末那么风行,却连绵不断。本书收录了蔡元培1926年为寿鹏飞《红楼梦本事辨证》所作的序以及景梅九《红楼梦真谛》自序。蔡序谓寿著“为专演清世宗与诸兄弟争立之事,虽与余所见不尽同,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此类考据,本不易即有定论;各尊所闻以待读者之继续研求,方以多歧为贵,不取苟同也。”(注:蔡元培《红楼梦本事辨证序》载1928年1月9日天津《大公报》“文学周刊”第二期)景序作于1935年正当民族危亡之际,“迩来强寇侵凌,祸迫亡国,种族隐痛,突激心潮,回诵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颇觉原著者亡国悲恨难堪,而一腔红泪倾出双眸矣。盖荒者亡也,唐者中国也,荒唐者即亡国之谓,人世之酸辛莫甚于亡国”。“侬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侬知是谁。亡国之人真不知身死何所,瓜分耶,共管耶……昔者惟我独尊,今则寄人篱下矣。”文后有编者附言,谓读景著“始知《红楼梦》为民族革命文书,序文尤足唤醒我民众之精神”。(注:老梅《石头记真谛序文》,载1935年6月20 日南京《革命公论》第六期)由此可见,虽时移世迁,而索隐家心系时政,“持民族主义甚挚”的情怀,始终不改。清代索隐诸家的影响也一直存在,学者文士持此类观点者代不乏人,本文第二节曾述及中央大学文学院讨论会,系主任汪辟疆就发言称《红楼梦》“是一部民族史”,“作者有亡国之痛”,“应该要用读历史的眼光去读它”。更为有趣的是当学生提出“妙玉到哪儿去了”的问题时,汪先生答:“她回慈溪老家去了”!大家愕然。汪解释说,“因为相传《红楼梦》是说明珠家事的,宝玉是纳兰成德,妙玉便是姜西溟”,是成德的老师。据《郎潜纪闻》,一次成德提起“家大人”请“老师出山”当礼遇权贵之事,惹得西溟大怒,“卷起行李一气归隐慈溪,所以我说妙玉回到慈溪去了。”引起听众大笑。(注:中央大学文学院《第一次学术座谈会纪事》、《水浒传与红楼梦》、《汪辟疆先生的意见》、《十大问题》,载1944年4 月重庆书局发行《中国文学》创刊号“艺文丛话”)至四十年代后期,有一位署名湛庐的作者,在1947年的《北平时报》上一连二十二次揭载其索隐之心得,总题曰《红楼梦发微》,之前有一篇“我亦为红楼索隐”,(注:湛庐《我亦为“红楼梦”索隐》,载1947年8月5日《北平时报》)说自己之爱好《红楼梦》“因为它是民族意识特高的一部小说”,这方面的兴趣,完全受了蔡元培的影响。然其具体意见却不同于蔡,甚至相反。蔡以女子多指汉人,男子多指满人,“我认为作者的春秋笔意,绝对以男子代表汉人,为阳;以女子代表满人,为阴。”水来土淹,满人虽侵略华夏,汉人亦能抵抗、同化,“泥实为水和土而成”。(注:湛庐《红楼梦发微四——男女、阴阳》,载1947年8月19日《北平时报》)次年即1948年10月至11 月间,湛庐又在《华北日报》上连载“发微”,继续发挥红楼梦为民族小说,所隐为清初四朝之事的观点。他不同意索隐阻碍欣赏的说法,认为索隐工作与文学欣赏是一体的,“文学上出色的作品,所以才值得后人探索”(注:湛庐《红楼梦发微的缘起》,载1948年10月1日、8日、15日《华北日报》)。对于清代索隐盛行的原因,有一种解释颇为独特,认为是小说地位低下的反映,清代的读书人“一方面觉得《红楼梦》好,一方面又觉得《红楼梦》出身低贱”,就如老爷爱上了丫头,怎么办呢?只有“把《红楼梦》扶正,于是所谓索隐,所谓影射,便是这扶正的一种手段了”。“在我个人看来,《红楼梦》的索隐批评,实际便是这种轻蔑小说的潜在意识在作崇。 ”(注:桐君《红楼梦索隐》, 载1935年8月25 日上海《新中华》第三十六期“艺术漫谈”)这篇文章受到精神分析学说的影响,作为一则文学漫谈,不论是否谈到点子上,其探究索隐的批评心理的意向是显而易见的。
《红楼梦》的考证除了作者和版本两大方面外,小说本身还有许多问题足以引发人们考索的兴趣,诸如人物的原型问题、年龄问题、脚的问题、地点问题,等等。有一位作者,从十来种清人笔记中,提供了七位“与曹雪芹有关的女子”,(注:諟进《与曹雪芹有关的女子们》,载1944年7月青岛《民民民》第五期)或有中表之亲, 或为美姬情婢,“让有兴致的读者,自己去和《红楼梦》印证”,意在提供书中黛钗等人的原型。其他亦有论者指人物故事确有其人其事者,年龄问题则早就有人发现书中矛盾,如巧姐忽大忽小、宝玉元春究差几岁、黛玉年岁多处不合等等。(注:赵誉船《红楼梦中人年龄考证》,载1923年6 月21日天津《新民意报》副刊“朝霞”第十四号)有专文考订的,也有综论述及的,历来是细心读者的一大疑惑。说到《红楼梦》写女子是“天足”还是“缠足”,更是一个费解的闷葫芦,因其关系到满汉习俗,满人天足、汉人缠足,更成了人们颇感兴趣的一个小小热点,二十年代北京《益世报》上就刊出过“脚的研究”之讨论文章,(注:芙萍《红楼梦“脚”的研究》,载1929年4月14日北京《益世报》; 张笑侠《读〈红楼梦“脚”的研究〉以后》,载1929年5月29、30、31 日北京《益世报》;张笑侠《红楼梦“脚”有了铁证》,载1929年6月29、30日、7月1日北京《益世报》)大抵以主张天足占上风, 均以《红楼梦》中相关描写证之。以后余绪不绝。当代仍有论者做这方面文章,宜乎一观前人所论。地点问题更是一个新红学家业已提出,不断为人探讨的问题,主张南京说、北京说、西安说各有所据,还是李玄伯在两篇讨论地点问题的短文中所说合于情理,他以为小说并非传记,不必实指,“长安”“不过文章内泛用的京师而已”。(注:李玄伯《红楼梦的地点问题》,载1925年4月24日《晨报》“猛进”第八期; 李玄伯《再论红楼梦及其地点》,载1925年5月22 日《晨报》“猛进”第十二期)大观园座落何处同样是从清代起就众说纷纭的老话题,有随园说、什刹海说等,园中建筑和风光景物南北兼备,令人惝恍迷离。《大观园源流辨》堪称论析这一课题的很有说服力的文章。它从园林发展史的角度,指出“中国园林的发达有两个系统:一是苑囿式,一是庭园式”。前者起于秦汉,豁达雄大,北部各园多属之;后者自赵宋而后,形成幽深闲寂的风格,为南方庭园特色,重借景、工叠石。明清之际,燕京西部名园林立,造园艺术益臻成熟。由此“可知北京园林的发达,至康熙乾隆间而极盛。这个时期,北方苑囿系统的园林,大部分被庭园系统的因素浸润了。《红楼梦》大观园的规模就是在这个历史的根据下而产生的,它是溶和苑囿和庭园两种系统而成的一个私家园林。”它受当时皇家园林设计的影响极大,特别是稻香村观稼和栊翠庵建寺更非私家园林所能有。大观园的规模格局、景点布设、意境营造、材质图案等等,无不可以从当时的园林艺术中借鉴、汲取,进而脱胎、创造。作者申明这种研究不能助长索隐诸说,“我的本意只在辨明大观园之所以为大观园的客观根据,如果有奢望的话,亦只在使人不敢再任意瞎猜它就是谁的园林罢了。”(注:藏云《大观园源流辨》,载1935年7月14 日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第一六○期)无论对红学研究还是园林研究,这都是一篇很有学术价值的文章。
《红楼梦》的名物考索亦颇受关注。小说中写到的“洋货”,为中西文化交通史的研究者所重视,撰成专文,大有助于考订《红楼梦》所处的特定时代和社会生活。这方面早在二十年代就有人以《红楼梦里的西洋物质文明》(注:昌群《红楼梦里的西洋物质文明》,载 1928年6月上海《贡献》第三卷第二期)为题,摘出小说中八处写到西洋物品的地方与《清一统志》和《文献通考》中所载的外国贡品加以对照。到了四十年代,方豪撰写了《〈红楼梦〉新考》等多篇文章(注:方豪《红楼梦新考》,载1944年5月《说文明刊》第四卷合刊本; 方豪《康熙时曾经进入江宁织造局的西洋人》、《红楼梦所记钟表修理师》、《清初中国的自动机器》、《红楼梦九十二回所记汉宫春晓围屏的来历》,均载1948年5月北平上智编译馆《方豪文录》), 全面系统地梳理了《红楼梦》中的外国物品,分类考索其来源,所据资料不仅有清朝的官方档案和士人笔记,更有外国教会的文献和外籍教士的记录。这些资料不仅翔实丰富,而且有些为一般人难以见到,方豪以其与教会的缘分和精通拉丁语、法语、英语等多种外语,悉心收集、严密考订,作成此项研究,功不可没。《新考》是一篇近三万字的长文,包罗的外国物品的类别有呢布、钟表、工艺、食品、药品、动物、美术品等,尔后分别考索其何时传入,由何种途径传入,皇帝和王公大臣对此类西洋事物有何种反应,以此与小说中的相关描写对照印证。该文还有一节专述“《红楼梦》撰人与外国人的关系”,连同方豪的另一篇文章《康熙时曾经进入江宁织造局的西洋人》,提供了当时外国传教士在康熙南巡时“见驾”的情形,由此推论雪芹先人“俱有晤见西人之机会”,书中西洋物品之“来源虽非一途,但来自洋教士者必占多数,盖贡使寥寥可数,而又稍留即返,不若教士之常居中国,并有在‘内廷行走’者,且教士络绎而来,故西洋物品之传入宫中及显宦之手,亦源源不绝也。”这样的结论自有其合理性,所据资料对了解《红楼梦》的时代背景弥足珍贵。
论及《红楼梦》里医药的文章很少,有一篇以此为题且篇幅颇长之文,谓《红楼梦》作者虽渊博,“但他的对于医、药方面的知识,我觉得还是很平庸的”,(注:胡明树《论红楼梦里的医药》,载 1944年3月1日桂林《文艺杂志》第三卷第三期)所见与人不同,应备一说。
七
本书收入的文章中,有几种长篇论著应当给以专门的介绍,它们都是作者下了很大功夫、包含了各自研究心得的,分述如下。
张笑侠的《读红楼梦笔记》是一部评点式作品,全长约十余万字,在1928、1929年的天津《泰晤士报》“快哉亭”专栏中长期连载。其内容包括:第一章,红之谱,包括各家之家谱、全书之年谱、各人之年谱;第二章,红之表,包括各人生辰表、全书人名表、各人之下人表;第三章,红之评,包括全书之舛漏及总论;第四章,各人之小传。这一次序在发表过程中有所调整。第三、四章调换,第四章为总评(红之舛附入),篇幅最长,为全书主体。总评依小说回次,顺序而下,固然是对小说本身的评批,亦常对前人评批发表评论,如对太平闲人、护花主人、大某山民常持异议。这部“笔记”具有历来评点派作品之特色,即读书很细,间有独到之见而总体观之不免支离零碎,有时还颇拘迂,如说最难明白“宝玉黛玉宝钗及其他姐妹之才学,均不知其系由何处得来”。由于《笔记》篇幅太长且引述情节过多,本书仅节选若干。
本节要着重介绍的是以下三篇论文,即二十年代刘大杰的《红楼梦里重要问题的讨论及其艺术上的批评》,三十年代李长之的《红楼梦批判》,四十年代张天翼的《贾宝玉的出家》。
刘大杰这篇论文是为《晨报》七周年纪念而作的,发表在1925 年12月1日《晨报》增刊上。全文约三万五千字,分为十节;一、《红楼梦》的作者及其生平,二、曹雪芹与贾宝玉,三、《红楼梦》索隐之派别,四、高鹗续书之讨论,五、《红楼梦》的地点问题,六、《红楼梦》里性欲的描写,七、《红楼梦》之描写与结构,八、《红楼梦》的版本问题,九、《红楼梦》在中国文坛上的位置,十、余论。从上述小标题可以看出刘文的规模,涉及的问题相当全面。刘文汲取和肯定了前人的成果,多持平之论,比方他充分评价胡适的《红楼梦考证》,取用其在作者和家世方面的研究成果,同时校正了自传说,代之以“自叙传的小说”,将二者加以区别,“写贾宝玉的个性及身世,说取材于曹雪芹自己,当然是可以;说里面的贾宝玉,就是曹雪芹,那也就不对了”。又比方对索隐派,虽则认为它是附会,无助于发现红楼梦的价值,但是“索隐的先生们的原来的用意,确是想提高红楼梦的价值,他们这一点苦心,我们无论如何是应该了解的”,因而对索隐各派,给以介绍。再比如他认同后四十回比不上前八十回,高鹗的才情比不上曹雪芹,但这是因为“续书比原著难”,肯定高鹗打破了中国小说的团圆迷信,大胆地写黛玉病死、宝玉出家,眼光高出一般。同时,刘文也包含了他个人的独特见解,比方说他认为《红楼梦》的地点,在陕西的长安。又比方他认为《红楼梦》“强于描写个性,拙于描写风景”,描写大观园那些文字就很抽象,很精采,而描写个性则特别有力量,最深刻的是林黛玉、刘老老,王熙凤三个。作者亦长于叙事,“描写失意的事情比描写得意的事情,都要深刻而活动”。再比如论到《红楼梦》在中国文坛上的位置,可以与屈骚、史记、唐诗、宋词、元曲并列。“谁也应该承认它是第一等的作品。但是拿起世界文学批评的眼光来说话的时候,那就有点不同了”,它不能摆脱中国旧有的消极思想,故不能同世界第一等作品相提并论。总的说,在二十年代中期就有这样一篇相当全面而中肯的综论,殊为难得。
李长之的《红楼梦批判》发表于1933年,在3月4日出版的《清华周刊》三十九卷第一期和第七期上分两次刊出。全文约三万三千字,从第一节“引子”可知,该文是为“纪念伟大的天才曹雪芹逝世百七十年”而写的,以下的标目依次为:二、《红楼梦》作者对于文学的态度之考察,三、论《红楼梦》的文学技巧,其中分列,1、艺术家的看见,2、实生活中的活材料,3、活的语言之运用和国民文学,4、自然主义作风的成和败,5、深刻的心理分析,6、清晰的个性的人物。全文未完,作者在“暂跋”中写道,“就现在发表的说,只有全文的一少半。在论文学的技巧下,还有两个小题目,阐说红楼梦之悲剧的意义;和论文学的技巧相并列的还有三个大题目,一论红楼梦之内容,也就是论作者的思想和情绪,一论红楼梦的社会史的分析,一是总结论。在北平文化机关的‘装箱’空气中,我的文章材料也寄到远处了,因而暂结”。由此可以了解这篇文稿本应是一部十万字左右的著作,未能刊完是由于时局的原因。在已刊出的第一部分里,李长之以悲愤的心情痛感天才曹雪芹被国人冷遇和误解,呼吁要冲开一切,“和我们的天才握手”。他认为一百七十年来只有三件事可记:一是1797高鹗后四十回的完成,高鹗“非常了解曹雪芹,他本人的艺术的手腕也并不让于曹雪芹”,“他是曹雪芹死后的第一个知己”。后文甚至还比拟说“曹雪芹像托尔斯泰,高鹗像朵斯退益夫斯基”,高更能写精神的方面。一是1904年王国维作《红楼梦评论》,“这是第一个会赏鉴红楼梦的人。他完全拿了西洋美学的眼光,用着近代文艺批评的态度,来加以估量的。他敢说红楼梦是中国第一部艺术作品……他最了解红楼梦了。不但在过去,就在现在,也无人及他。”一是1928年“胡适作考证红楼梦的新材料,把他六年前的红楼梦考证更加确定了。他把红学打得一扫而空,他把作者的生活、背景,给人作出一个确然的轮廓”,“于是一切没有证据的,或者证据不可靠的,便都敛迹了”。李文第二部分考察红楼梦作者看重的是不计功利的纯文艺,反对陈套,要求艺术提高人的精神和表现理想。第三部分由于结合小说作了大量具体分析,因而所占篇幅亦最多。值得注意的是李长之对文学形式技巧的理解,认为形式可以消解内容,“我们对着一种大艺术品时,我们只就那形式,便获得了它的内容……我们的精神活动浸入埋伏于当前的即是艺术品的形式之中,我们与作者立在同一的情绪里,材料的痕迹化为乌有了”,“那内容在形式里已好好地传给你了”,这虽来自于大诗人席勒的启示,以其合于艺术的规律,李长之融会而施之于《红楼梦》,“岂是单单道着他的文学技巧”,“道着他的全部人生”。因而这大篇《红楼梦》文学技巧的具体分析便超越了评批式的就事论事的局限,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准。
张天翼《贾宝玉的出家》发表于1942年11月15日在桂林出版的《文学创作》第一卷第三期,后收入一本包括多篇论《红楼梦》人物的集子,就以“贾宝玉的出家”为书名,于1946年由东南出版社出版。张文约三万三千字,它并非是一篇单纯的人物论,而是由主人公的结局切入,以果求因,提示出人物和作品本身存在的深刻矛盾。文章先是嘲笑了那些“圆梦派”的续书作品,虽说是“圆”了,结果弄得贾宝玉不成其为贾宝玉,林黛宝不成其为林黛玉。继之进入正题,提出贾宝玉出家这个结局的意义比那样的团圆高明得多,解决的是“整个人生大道的大问题”。然而“宝玉出家以后怎样”?书中并无下文,参照作者笔下已经出家的两类人,已经暗示“这条路走不通”。虽则楔子中点明,一切都是前世因缘,梦幻而已,作家却把尘世生活表现得那么生动、亲切、温暖,“他倒是着眼在现世因缘,把因因果果抓得紧紧的,一步一步合理地发展下来的”,这是“本书极可贵的优点”。宝玉的出家正是诸般因果发展之必然,“他有他自己的世界,跟别人不同,可他实际上又生活在别人的世界里面”,他不就范就要超脱出去。文章揭示了人物自身以及作家对人物的态度存在的矛盾,认为那两首评批宝玉的《西江月》词“既不能视为反话,也不能把它当作正面的教训”,“作者对贾政,对贾宝玉,似乎各都给以同情、首肯……可贾政所代表的这个世界偏容不得贾宝玉型。这就不容易处理了。于是我们就只好跟着作者的笔——在这两者之间摆来摆去。”张天翼忠实地道出自己阅读的感受,“不肖种种大承笞挞”是全书中自己所喜欢段落的首选,“我总觉得这段描写,是全书中最悲剧性的东西”,“不瞒你说,我看到别的那些惨伤的场面——甚至晴雯之死、黛玉之死,也不及这里使我感动”。“这悲剧的成因,我想就是在于——他们有爱,而缺少彼此的了解。”作家的感情与理智不能一致,而创作又不能虚伪,导致了矛盾现象,即使叫“出家万岁”也还是并未找到出路。文章的结论,“这部作品是两重性的:非悲剧,亦非非悲剧。”对于后四十回则有十分风趣的批评,谓出家大不易,还得履行种种麻烦的手续,圆房、赶考,“自己看破了红尘,却一定要留个后代下来,以便在红尘里爬来爬去出风头”,难道成佛也讲求正途出身,还要惊动皇帝老子敕封文妙真人……兰桂齐芳,世界恢复老样子,出家就更冤更无谓了。看来续作者更热中于世间,心地极好,也是团圆派里的一位;他“总算是救出了红楼梦的故事坯子”,可原作的两重性矛看不见了,“不再徘徊于世间和出世间”,干脆回到了富贵场中。总之,张天翼以创作家的敏感和批评家的逻辑,处处从阅读的感受出发,无大幅引例和大段说理,娓娓道来,如剥茧抽丝,层层递进,在亲切幽默中使人憬然有悟。
以上三篇论文,尽管撰者学术个性不同,发表时间不同;然而都是力作,无论从广度或深度上,均堪称这一时期红学论文中重要的、有代表性的论著。
这里还应提及一篇专论即《红楼梦与中国经济》(注:王增宝等六人《〈红楼梦〉与中国经济》,载1944年2月、11 月重庆《新认识》第八卷第五、六期合刊、第九卷第二期),以经济的视角来论评,不说绝无仅有也十分稀见。该文从《红楼梦》这样一部文学巨著看中国社会,认为是不可多得的中国某一时期社会经济的实录,同时也提供了清代乾隆年间生产、流通、分配与消费方面的背景材料,可资参考。
此外,本书还收录了这一时期出版的几种《红楼梦》的序言,序言往往也是一种评论。如1923年许啸天的“新序”(注:许啸天《红楼梦新序》,载上海群学社1923年4 月版《红楼梦》卷首)猛烈抨击索隐家和考据家,认为不必迷信最初的版本,尽可按照文学上尽善尽美的理想大胆删改,因将《红楼梦》校成一个百回本。此举受到刘大杰的严厉谴责,指为版本史的耻事、“文艺界的公敌”(注:刘大杰《红楼梦里重要问题的讨论及其艺术上的批评》,载1925年12月1 日《晨报》七周年增刊)。三十年代茅盾的《节本红楼梦导言》概要表述了对《红楼梦》的见解及删节原则,是对“独秀先生提议”即他曾期望“有名手将《石头记》琐屑的故事尽量删削”(注:陈独秀《〈红楼梦〉新叙》,载上海亚东图书馆1921年5月初版《红楼梦》卷首)的一种回应。 此节本在当代曾经再版。
八
行文至此,读者对这部“汇要”大致有了一个轮廓,编者力求保存历史本来面貌的初衷也许能够得到读者的体察。
我们期望:
首先,本书至少可以作为一种资料长编,供研究本世纪上半叶红学发展的学者参考。前文曾经提到,这一时期的《红楼梦》研究少有政治的干扰和商业的炒作,因而保有其本分和本色。评论文章比较个性化,少八股气;既有学理探讨,亦不乏随笔感想;虽多歧见,而少意气。从总体上说,尽管数量质量远不能同近五十年相比,但仍有其值得珍视和发扬的风气和传统,应当受到治红楼梦学术史者的重视。
其次,对于广大《红楼梦》爱好者和研究者来说,具体切实地了解这段历史可以避免炒冷饭、走弯路,可以把起点置于前人的成果之上,收事半功倍之效。上文已经论及这一时期红学研究的多元和多层,不论是研究的范围还是研究的方法,都已相当广泛和多样,许多问题都已提出或涉及。大而言之,“《红楼梦》确实包含了‘文学’‘哲学’‘历史’的三项,不能够单单靠定了一途立论,不然怎么算得起‘横看成岭竖成峰’的书啊”(注:王小隐《读〈红楼梦〉剩语》,载1920年《新中国》第二卷第四、六、八期)这是一位论者1920年所撰文章的结束语,足见以文、史、哲多个层面去研读《红楼梦》,早在二十年代之初就被郑重提出了。小而言之,《红楼梦》中“脚”的问题,即女子是天足还是缠足,自二十年代至四十年代屡有讨论,前文已及。今天如果再把这些当成新鲜见解、独家发明,岂不有点可笑!
再次,对于一般读者,即使并不熟悉甚至未曾接触过《红楼梦》,本书也不失为一种有趣有益的读物。本书收录的一位作者,以他个人读过三十余遍《红楼梦》、接触过上百爱红者的经验,在心领神会之余,总结出如何读《红楼梦》的十四条建议,谓“应趁风和日暖时去读,来印证书中的明媚新鲜”;“应趁秋高气爽时去读,来印证书中的全声玉振”;“应趁风晨雨夕时去读,来印证书中的怨旷萧骚”;“应趁冬闺消寒时去读,来印证书中的温暖融和”;其第十四条曰,“红楼梦宜于升官发财时受罪入狱时读之,以便有缩手回头的机会”。还举出《红楼梦》可“移人性情”的十一项功能,如可医俗病、可医吝病、可医贪病……等等(注:木村《〈红楼梦〉读后记》载1947年11月台北《建国月刊》第一卷第二期)。看了这位论者的心得,真教人不由得不去翻看这部奇书,加入爱红者的行列。《红楼梦》的读者由此更加众多,阅读水平更加提高,不亦宜乎。
总之,本书果若能使人温故知新,各有所获,则编者于愿足矣。
最后,应当说明这样一项大型资料得以集结出版,没有人民文学出版社和中国艺术研究院的支持是不可能的事,而编委会全体成员的同心协力更是促其完竣的直接保证。尤其是林东海先生自七十年代初受命编辑《红楼梦研究资料》,经年累月孜孜于北图柏林寺报刊馆,为此书奠下基础,今主持编审,总揽其成,贡献良多。周绚隆同志担任本书责任编辑,整理校阅,细加厘订,作了大量工作。还应特别提到长期从事资料工作、埋头苦干甘愿奉献的刘伯渊君,本书的大量资料从收集、整理、复印、放大以及若干初步加工,无不渗透着他的辛劳和汗水,许多琐屑而具体的事务都由刘君承担。令人感佩。因此,本书的出版应归功于大家尤其是上述诸位,笔者所做十分有限。至于这篇前言挂一漏万、轻重失当、述评失误之处在所难免,文责所在,笔者当不能辞其咎。
限于闻见及各方面条件,本书从收录到编辑,难以尽善,恳请读者和方家批评赐正。
一九九八年八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