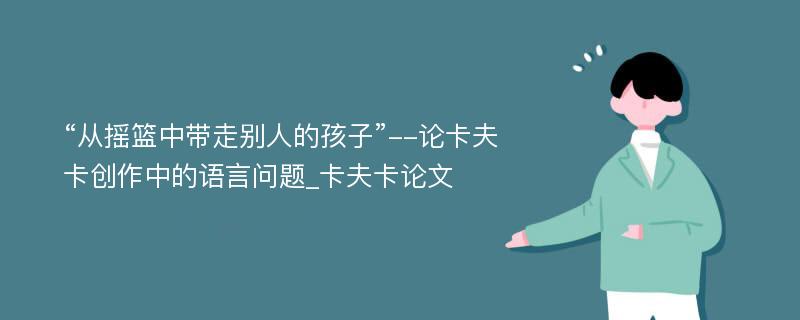
“从摇篮里抱走了别人的孩子”——论卡夫卡创作中的语言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走了论文,卡夫卡论文,语言论文,孩子论文,摇篮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本文将要探讨的并不是卡夫卡创作的语言风格或语言特色问题,而是有关卡夫卡的语言观,以及他的语言观如何贯彻和体现在他的创作中的问题。一个作家运用什么语言创作往往是命中注定的,譬如鲁迅之于中文,歌德之于德文,但丁之于意大利文,莎士比亚之于英文,托尔斯泰之于俄文。然而,世界上还有少数用非本民族母语进行创作的作家,并且,正是这种十分尴尬的处境构成了这些作家最动人的个性以及最突出的特征。在这方面表现最典型的,大概要属20世纪奥地利作家卡夫卡了。德勒兹与加塔利无疑注意到了这一点,他们在其合著的《卡夫卡:关于一种少数者的文学》一书中这样写道,“今天还有多少人生活在不属于他们自己的语言中?他们已不再了解,或者说他们根本就不了解他们自己的语言,而对于他们被迫使用的语言又知之甚少。这就是移民的问题,特别是这些移民的孩子的问题,少数者的问题,少数者文学的问题,当然也是我们所有人的问题:即如何将少数者文学与它自身的语言撕开,使文学向语言挑战,从而使之走上一条清醒的革命之路?在自己的语言中如何变成一个漫游者,一个移民,一个吉普赛人?卡夫卡的回答是:从摇篮里盗走孩子,在绳索上跳舞。”(注:Gilles Deleuae and Felex Guattari Kafka:Toward a Minor Literature,The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p.19,pp.17-21.)卡夫卡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犹太人,生活在主要说捷克语的布拉格,但他却用德语写作,这不能不影响到他的创作思想和创作风格。而对于这样一个并非仅仅属于语言特色,而更应该属于创作本体论的问题,以往的专家学者们却很少关注,这不能不说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情。本文便想从这一角度入手,对这一问题作些思考和探索。
一、“生与死之间的抉择”
卡夫卡是一个布拉格作家,他的一生除了去欧洲短暂的旅行外,一辈子都生活在布拉格,布拉格就像一个“小妇人的爪子”牢牢地抓住卡夫卡不放。卡夫卡在这里选择、创作、工作和生活。布拉格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它地处波希米亚高原中心,伏尔塔瓦河两岸,自古以来就是连接欧洲东西、南北的交通要地,流经布拉格的伏尔塔瓦河是南北欧洲之间的商路要津。布拉格的这种地理位置注定了它成为许多外国利益冲突的场所。公元9世纪叶普热美斯王朝在此建造了费赛拉德城堡。公元10世纪布拉格成了波希米亚王国的都城和商业贸易中心。1346—1378年,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兼波希米亚国王查理四世在此建都,把历代国王在此建造的城堡和宫殿联在一起,称为布拉格堡,并在老城区以南兴建新城区,因此,这里一度成为欧洲最大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之一。17世纪中叶,布拉格先后被撒克逊人和瑞典人占领。1918年布拉格成了捷克斯洛伐克首都。一千多年来,很少有欧洲的战争不影响到布拉格这座城市。
卡夫卡所处的时代,布拉格正处在多民族的分裂冲突之中。“少数民族之间几乎没有任何共同之处;他们与有生气、有民族主义抱负的绝大多数捷克人也没有多少共同之处。尽管知识界做了一些理想主义的尝试,以图达到合作的目的,但布拉格的状态仍然是四分五裂的——犹如一座特殊的温室,在这里,诸如社会主义、犹太主义、德国民族主义、玩世不恭的思想、人道主义、以及一切虚假的世界主义等各种信念都相互冲突。”(注:马·布雷德伯里、詹·麦克法兰《现代主义》,胡加峦等译,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109、110页。)政治、经济、军事的冲突必然会反映到文化领域,而在文化领域,冲突表现得最为集中、最为激烈的恐怕要算是有关语言的争端。语言的存亡往往代表着民族的存亡,用现在的话来说,争夺话语权的问题其实就是争夺生存权的问题。卡夫卡对语言的政治意义感受强烈。人们总是通过语言来追问身份,而政治不过是意识形态的质询。“语言之谜求助于政治考察,在那些民族热情高涨的地区尤其如此。”(注:David Suchoff,David Bruce,Critical Theory and the Novel:Mass Society and Culture Criticism in Dickens,Melville and Kafka,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1994,p.139.)卡夫卡说:“话语是生与死之间的抉择”;“语言是行动的开路先
锋,是引起大火的火星。”(注:叶廷芳编《卡夫卡全集》,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 版
,第5卷第332和352,第227、271、221、439、9页。)当代法国著名语言学家海然热 曾
严肃地问道,“仅就本世纪而言,为什么语言问题往往成为暴力冲突的导火线?”他 的
回答是,因为“语言的特征之一就是具有藏而不露的力量……语言的实践反映一种并 未
公开宣布的霸权”;“语言属于一种政治资本。任何语言政策都利用最忠诚的支持者 玩
弄权力游戏。”(注:海然热《语言人》,张祖建译,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265、26 6
、267页。)多少年来,用什么语言作为布拉格的官方用语一直是一个十分敏感并且十 分
重要的问题。而到了卡夫卡所处的时代,这种有关语言的争端表现得更为激烈,常常 成
为民族争端的导火索。每一个布拉格人都必须做出自己的选择,当然这种选择往往并 不
是自由的。捷克著名当代作家克里玛说,“对布拉格的精神和面貌最具影响力的不是 自
由,而是不自由,是生活的奴役,许多耻辱的失败和野蛮的军事占领。”(注:克里 玛
《布拉格精神》,崔卫平译,作家出版社1998年版,第45页。)卡夫卡就是在这种不 自
由中做出了他对语言的选择。
卡夫卡的父母都是犹太人。卡夫卡的祖先在由捷克农民包围着的犹太人居住区至少生活了一个世纪。“卡夫卡”这个姓,据说来源于捷克语“Kafkas”,意思为“穴鸟”。卡夫卡一家在家里常说捷克语,但接受的是德语教育,在正式场合都说德语。但是,卡夫卡说,“我从未在德国人民中生活过,德语是我的母语,因此对我来说是自然的。然而,捷克语却使我感到亲切得多。”(注:叶廷芳编《卡夫卡全集》,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5卷第332和352,第227、271、221、439、9页。)处在这种复杂的语言环境中的卡夫卡,精通或熟悉多种语言,“他精通德语速写,除了他的母语德语外,他还流利地掌握了捷克语,熟悉法语和英语,”(注:Ernst Pawel,The Nightmare of Reason:A life of Franz Kafka,New York,1984,p.102,p.240,pp.428-429,p.99,p.257.)1907年卡夫卡申请工作时,他在申请表中英语一栏里,填上了“好”。他还学习过意大利语、希腊语和拉丁语,至于希伯莱语,他天生就有一种亲切感,因此,学习这种语言他颇有天赋。
然而,在这么多他所熟悉或精通的语言中,卡夫卡为什么偏偏要选择德语写作呢?其实,与其说是卡夫卡选择了德语作为他的母语,不如说是德语选择了卡夫卡,因为卡夫卡当初根本就没有选择的自由。
在当时所谓的奥匈帝国,占人口多数的民族其实既不是奥地利人,也不是匈牙利人,而是捷克人、斯洛伐克人、克罗地亚人、路德尼斯人、斯洛维尼亚人、罗马尼亚人以及波兰人。早在1774年帝国就颁布了基本教育法案,其目的在于解决这些不同民族的文化同化问题,因为语言的分裂会导致政治的分裂以及管理上的问题。这样一来,所有的小学都规定德语为必修课,并将德语指令为中学以上的惟一教学用语。同时,在国家和政府机构的所有的商务活动中也都采用德语,这一政策实际上相当于强迫所有少数民族德语化。于是,少数民族语言便面临着灭绝的危险,语言的灭绝便意味着民族的消亡。因此,保存民族语言成了各少数民族的首要任务。
那些官僚机构中被异化了的无根的牺牲者,本能地依附于他们共同的语言,将语言作为连结他们的过去和未来的交接点。语言是存在的基础,知觉的前提,抢夺一个人的语言等于抢夺了他最重要的也是最基本的自我意识,因此保护民族语言的战斗就成了一个凝聚点,一开始是为了民族和文化的同一性而斗争,最后便发展为一种民族解放运动,正是这一运动毁灭了哈布斯堡王朝。
语言冲突不可避免地要发生在学校里。“捷克孩子属于捷克学校”,这句话成了捷克民族主义者和反对中央政府的领导者的战斗口号和行动纲领。与此同时,犹太人则又一次面临两难境地:是与德语同化,还是继续保持自己的语言文化传统?从整个中世纪到18世纪,犹太人一直忍受着被隔离的屈辱。但是,除了反犹太法案以及对犹太人的迫害外,犹太教传统一直在建构一种完整的生活,即在他们与基督教周边环境之间筑起一道清晰的分界线。只要犹太人还存在着,只要他们完整地保存他们的宗教传统,并将这种传统一代代传续下去,那么,不屈不挠地对年轻人进行犹太式教育就一直是犹太团体最关切的问题。这种教育涵盖了一切正式的场合,从最小的孩童时代开始,贯穿于他的一生。识字是作为真正的犹太人的一个方面,而最基本的要求是参加宗教仪式。在传统观念上,一个男人如果连犹太法典都不能阅读的话,那他就不是一个真正的犹太人。
同时,当时的统治者也认识到,如果广大的犹太人没有德国化,或与别的什么民族同化,那么,他们也就不会真正地地脱离他们的过去、他们的传统以及他们的语言。因此,哈布斯堡王朝出台了一套政策和法令,强化和突出了德语在奥匈帝国的至高无上的地位。这样,到了卡夫卡出生的那个年代,至少在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德语已经完全替代了意第绪语,这使得捷克人有充分的理由更加激烈地反对犹太人,而犹太人在缺乏选择的情况下越来越倾向于认同德国少数人的政治和文化,但这并不是一种平等的接受。
在文化上无根的犹太中产阶级,除了认同捷克语或德语外,别无选择。1880年的第一次语言普查,事实上不亚于一次面对公众督查的信仰表白,它同时也表现出这种两难处境。对这一问题的最初反应是,在波希米亚的犹太人中只有三分之一将捷克语作为他们的第一语言;而10年之后,便上升到超过了50%。布拉格的情况也是如此。1890年,城里大约25,000犹太人中有四分之一——这个数字一直稳定地保持到了1939年年底——在家里也只讲捷克语;而到了本世纪初,捷克语已经正式成为布拉格55%以上的犹太人的主要语言。
在卡夫卡的时代,这便是争取语言权力的斗争。这场斗争的目的已不再是为了争取语言的平等地位,而是为了取得捷克语在波希米亚的优先地位,这引发了捷克语与德语最为严峻的冲突。上大学时,卡夫卡听过奥古斯特·骚尔教授的德国语言文学课。骚尔教授曾以极度的热情给予德国文化最高的评价,在这种评价中暗含着某种文学种族主义及排犹主义,这首次激起了卡夫卡严肃地思考他在这种语言和文化中的位置。
1911年,卡夫卡大学毕业以后,当一个由八人组成的小型的东犹太人剧团来布拉格进行巡回演出时,卡夫卡仿佛得到了天启一样,对意第绪语有了全新的认识。“一些歌曲,一些孩子般欢笑的犹太语台词,站在舞台上的那个女人——因为她是犹太人,她吸引了我们这些观众,因为我们也是犹太人,一点也不羡慕基督徒,或者说对他们没有兴趣——使我们心灵颤动。”(注:《卡夫卡全集》,第6卷第65、26、47-48页。)当时,卡夫卡的内心压力已经达到了极点,他在失望、焦虑和写作中寻找着自我。他感觉到,与他那被忽略的童年的孤独的痛苦相比,存在的孤独更为深刻,也更为普遍。他在那些东犹太演员的身上发现了某种令人着魔的魅力:“他们将自己的精神与那种搅动他内心世界翻腾的精神结成血缘关系,言说他已失却了的语言,作为犹太人他们扎根于此,他们的身份在这里受到保护,犹太语的作用就在于此,这正如捷克语是捷克人的,德语是德国人的一样。”(注:Ernst Pawel,The Nightmare of Reason:A life of Franz Kafka,New York,1984,p.102,p.240,pp.428-429,p.99,p.257.)“一旦意第绪语言控制了你,意第绪语就是一切。”(注:叶廷芳编《卡夫卡全集》,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5卷第332和352,第227、271、221、439、9页。)从此以后,卡夫卡改变了对犹太复国主义的态度。尽管就其政治立场而言,他并没有成为一个犹太民族主义的积极支持者,但是,他对于通过犹太人自己的语言和社会结构来复兴真正的犹太文明,却有着浓厚的兴趣。尽管犹太复国主义的分裂主义者和资产阶级排斥他,但他已经认识到,在他所生活的这个世界里,迄今为止犹太复国主义者在为犹太人的生存和复活所进行的斗争中表现出了最强劲的活力。在看过第一场意第绪语剧后的几周里,他便开始研究犹太历史、文学和犹太教的起源,这种研究他后来坚持了一辈子。
愈到生命的最后时刻,卡夫卡愈向往“在自己的土地上用自己的语言建立一个犹太国家”,他认为这是解救已经陷入穷途末路的西方人的惟一办法。因此,当他重病在身时,他学习希伯莱语的热情反倒分外高涨。对此,他当时的希伯莱语教师普娅·门采尔博士回忆道,卡夫卡“每次上课之前总是收集好了一长串他想认识的单词。但他的肺却一直想放弃。每当他痛苦地咳嗽一次,我就想中断讲课。而他却瞧着我,说不出话来,用他那深邃的眼睛凝视着一个又一个单词向我请求。这仿佛表明,他将这些课程当作了一种神奇的治疗方法。他同他的父母住在一起,他母亲常常轻轻地推开门,提醒我让他休息。但他却不满足于此,他取得了很大进步;到最后他已经在读布里勒的小说。”(注:Ernst Pawel,The Nightmare of Reason:A life of Franz Kafka,New York,1984,p.102,p.240,pp.428-429,p.99,p.257.)
1924年3月,当卡夫卡由于病情恶化,不得已从柏林回到布拉格时,他移居巴勒斯坦的梦想彻底破灭了。他没有办法成为一个真正的犹太人,他清醒地认识到,用德语写作背叛了他作为犹太人的身份。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卡夫卡拼尽了他身上的最后一点力量,试图做出自己的选择,但他没能成功,死亡最终取消了他的选择。这也许要算是卡夫卡一生中最大的悲剧。
二、绳索上跳舞
作为卡夫卡那一代生活在欧洲的年轻的犹太人,他们既不像他们的祖辈那样相信犹太教,对宗教狂热而痴迷,也不像他们的父辈那样相信金钱的万能,尽量想摆脱他们身上的犹太人身份,他们中间许多人愿意献身于文学艺术,将写作当作“一种祈祷的方式”。卡夫卡的父辈们,自命不凡地满足于已经克服了卑微和贫困,强迫儿子们扮演他们决不希望扮演的角色。儿子们发现他们已被禁锢起来,根本不能表现自己,困在允诺和现实之间的陷阱中,于是,他们便将文学当成了走出绝境的通道。“对于卡夫卡的祖先们而言,词语就是筑起信仰大厦的砖石,而他们年轻的一代却用词语毁灭信仰,哀悼他们信仰的失落,最终用文学来取而代之。”(注:Ernst Pawel,The Nightmare of Reason:A life of Franz Kafka,New York,1984,p.102,p.240,pp.428-429,p.99,p.257.)卡夫卡认为,“语言具有驱邪祓魔的力量”;“彼德·汉德克以前的奥地利文学主要可被看作是修辞方面的驱魔仪式”(注:马·布雷德伯里、詹·麦克法兰《现代主义》,胡加峦等译,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109、110页。)。既然这个漂泊无定的被抛弃的犹太部落砸碎了它过去的偶像,开始用崇拜文学艺术代替崇拜上帝;既然文学艺术与语言有着那样水乳交融的联系,那么,语言也就成了犹太人的生死问题。在这种语言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卡夫卡自然对语言问题也十分敏感,并且,他很快就形成了一套自己独特的语言观。
首先,在语言与存在的关系问题上,卡夫卡认为语言就是存在的家,是存在的基石,人失去了语言,就失去了“家”,没有了立身之本。卡夫卡认为,最能体现人的本质的是人的语言,“语言固然是人类最普通之事,人人都会讲,如同每只老鼠都会叫一样。但只有当卡夫卡的女艺术家、老鼠歌唱家叫唤时,她的叫声才摆脱了日常生活的桎梏,从而也使我们获得了片刻的解放。”(注:艾里希·海勒语,见《卡夫卡全集》,第10卷第185页。)个人的完整性或完美无缺只能在他的母语中体现出来。他曾对他的女友密伦娜夫人说,“我想读您用捷克语写的东西,是因为它是您的母语,在那里密伦娜才是完美无缺的。”(注:叶廷芳编《卡夫卡全集》,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5卷第332和352,第227、271、221、439、9页。)在卡夫卡看来,任何个人的完美无缺都同他的母语是分不开的,人只有在他的母语中才能呈现出他的完整性和丰富性。“语言是故乡的有声的呼吸。可是我是个严重的哮喘病人,因为我既不懂捷克语,又不懂希伯莱语。两种语言我都学。但这好像梦似的。我们在外面怎么能找到应来自内心的东西呢?”(注:叶廷芳编《卡夫卡全集》,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5卷第332和352,第227、271、221、439、9页。)对于卡夫卡而言,从孩提时代起就一直萦绕在他心中的那份无论如何也摆脱不掉的孤独,其实也就是这种失去了“语言”之家后的孤独。作为一个西方犹太人,他一生下来就被各种陌生的语言包围着,在各种异国语言的裹挟下漂浮,无所归属。他所说的和他所写的语言,都不是他自己的,每当紧要关头,这种语言便在他的心灵深处背叛他、反对他。正是语言使卡夫卡开始思考他与母亲、他与父亲的关系,以及“他是谁”、犹太人的归属问题。而在一个丧失了希望和信仰的时代,这些问题又非常具有普遍意义。从某种意义上说,对于一个被异化了的西方犹太人的命运的思考,也就是对那些被异化了的西方人,乃至整个人类命运的思考。
作为一个说德语的犹太人,卡夫卡对犹太德语有着清醒而深刻的认识,而这一认识又几乎成为了卡夫卡思想和创作的基础,因此,在这里我们将尽可能完整地引用卡夫卡的有关论述。大约在1921年8月,卡夫卡在一封致布罗德的信中写道:
在这个德语犹太世界中几乎没有任何人除了讲犹太德语外还会别的什么。从最广义上来看,讲犹太德语是一种不得不拿过来的东西,即以喧哗或悄悄的或自我折磨的狂妄态度把一种别人的所有物拿过来,这种拿不是一种争取,而是通过(比较)仓促的抓攉而偷来的……我说这些并无反对讲犹太德语之意,犹太德语本身甚至是美妙的,它是书面德语和形态语言的一种有机结合,它也是一种细腻的语感的产物。这种语感认识到,在德语中,只有方言或最个性化的标准德语才是真正活着的,而其他的,所谓语言的中层仅仅是灰烬而已,只有在非凡活跃的犹太人手里面乱掏一气,它才会产生一种生命的假象。无论有趣还是可怕,事实便是如此。但犹太人却为何会不可抗拒地被吸引到那个方向去呢?德语文学早在犹太人获得自由之前便已存在,而且十分光辉灿烂。据我看,它一般首先不逊色于今日之丰富多彩,也许今日甚至倒是失去了许多昔日的丰富性。而这二者与犹太属性之间存在着联系,与年轻一代犹太人同其犹太属性的关系之间存在着联系,与这一代人可怕的内心状态之间存在着联系……
绝大多数开始用德语写作的人,都想摆脱他们的犹太人身份,他们通常会得到父亲们含糊的首肯(这含糊是令人气恼的)。他们想着摆脱,但他们的后腿仍然同他们父辈的犹太血统粘连在一起,而他们的前腿又没有探到坚实的地面。这种最后的绝望培育了他们的灵感。
这种灵感同其他任何一种同样值得尊敬,但进一步观察,便会发现一些可悲的特性。首先,尽管它表面上像是德语文学,但实际上成不了德语文学,这便是他们绝望的导火线。他们生活在三种不可能性中间:不写作的不可能,用德语写作的不可能,用其他语言写作的不可能。几乎可以加上第四种不可能性,即写作的不可能,所以说这是一种从所有方面看来都不可能的文学,一种吉普赛文学,它把德国孩子从摇篮中偷出,匆匆忙忙地安置一下,因为总得有人去绳索上跳舞……(注:《卡夫卡全集》,第7卷第419-421页。译文根据英译本有较大改动。)
犹太人用德语写作,是盗用了其他民族的遗产,“从摇篮里盗走了陌生人的婴儿”,因此,这个孩子是很难长大成人的,这就像在“绳索上跳舞”一样,稍有不慎就会摔得头破血流;并且,这个孩子即便长大了,也不属于自己,他跟自己没有血缘关系。更何况,犹太人永远也不可能摆脱他的犹太身份,永远也不可能摆脱犹太传统。这就决定了犹太作家写作的不可能性:“不写作的不可能,用德语写作的不可能,用其他语言写作的不可能”。如此看来,卡夫卡对自己作品的不满意,以及他总是不能完成他的作品,从卡夫卡的语言观上看也是必然的、无可选择的。
卡夫卡的这种语言观曾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当时著名作家卡尔·克劳斯的影响。克劳斯比卡夫卡年长9岁,他对语言的论述在当时非常有影响。他认为犹太人用德语写作是不恰当的,他们误用了其他民族的遗产。
在卡夫卡看来,只有用自己的语言创作的作品才属于自己。“用一种语言的形式和质料形成的文学,总带着它的模式的色彩和线条”;“每一种语言本身都是一种集体的表达艺术。其中隐藏着一些审美因素——语言的、节奏的、象征的、形态的——是不能和任何别的语言全部共有的。”(注:爱德华·萨丕尔《语言论》,陆卓元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199、201页。)卡夫卡自己的语言是犹太语,因此,他只有用犹太语创作才行。卡夫卡成年以后对这一点越发坚信不移。他一直坚持不懈地学习犹太语,最后他甚至都可以直接读犹太小说了。但他所掌握的犹太语的程度,还不足以让他用犹太语来写小说。如果卡夫卡果真能够像他自己所希望的那样,移居巴勒斯坦,在那里生活、工作,我们或许可以看到他用犹太语写的小说,但这一切由于他的过早谢世而不可能成为现实。卡夫卡最后的女友朵拉曾经这样说道:“对于卡夫卡来说,德语太现代、太新潮了,卡夫卡的整个世界都渴望一种更古老的语言,”(注:Noah Isenberg,Between Redemption and Doom:the Strains of Germen-Jewish Modernism,Lincoln and London: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1999,p.42.)这种语言就是犹太语。如此看来,写作和语言的矛盾应当是卡夫卡内心深处最重大的矛盾。而这不可能不体现在他的小说创作中。
虽然卡夫卡非常强调语言的存在论意义,但是,在言和意的关系上,在将语言作为媒介和工具时,卡夫卡又存在着深刻的危机意识。卡夫卡的思想曾受到奥地利哲学家马赫的影响。卡夫卡上大学时的科学教师戈特沃尔德是马赫理论的追随者。那时卡夫卡就对语言问题具有浓郁的兴趣,常就语言的哲学功能、力量和弱点等问题与同学们展开讨论(注:Frederik R.Karl,Franz Kafka,Representative Man,New York:Tichnor & Fields,1991,p.111.)。马赫认为,世界的真正要素不是物,而是颜色、压力、空间、时间这些我们称之为感觉的东西。世界便是由这些具有某种函数关系的感觉要素构成,科学知识决不是客观实在及其规律的反映,而只是对感觉要素的一种“方便的描述”,也就是一种“经济思维”。科学理论和知识由词语、概念构成,而这些词语和概念只不过是一些经济简便的符号。卡夫卡有一句与此类似的名言,“我写的与我说的不同,我说的与我想的不同,我想的与我应该想的不同,如此这般,陷入最深的黑暗之中。”(注:《卡夫卡全集》,第7卷第419-421页。译文根据英译本,略有改动。)这种“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的危机意识,卡夫卡有着深切的体验。他说,“对于超越物质世界的一切问题,语言仅能略示梗概,但几无半分正确可言,因为语言能够从物质世界取来论述的,仅限于它能够把握得住的事物,而它所能叙述的,也仅止于暗示而已。”(注:叶廷芳编《卡夫卡全集》,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5卷第332和352,第227、271、221、439、9页。)物质世界就好比是卡夫卡笔下的“城堡”,语言就好比是K试图进入城堡的种种努力,K能略示城堡的梗概,了解到他能够了解的有关城堡的一切,但是,城堡的中心他永远也进不去,非但如此,甚至连什么是真正的城堡,他也不知道。卡夫卡这种对语言的限度的认识,具有浓郁的现代意义色彩,同解构主义的语言观有许多相通之处。
在创作过程中卡夫卡也常常感到语言对思想的束缚,语言扭曲或改变了自己的思想。他说,“在写下东西的时候,感到越来越恐惧。这是可以理解的。每句话,在妖魔的手中转过来,翻过去,变成矛,掉过头来又刺向说话的人。”(注:《卡夫卡全集》,第6卷第468页。译文根据《卡夫卡日记书信选》(百花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第67页)作了改动。)又说,“我的力量连写成一个句子都不够。是呀,如果这涉及要说的话,如果写下一个单词,这就足够了,而且如果人们能在安详的意识中转过身去,完全用自己来充实这个单词就好了。”(注:《卡夫卡全集》,第6卷第65、26、47-48页。)卡夫卡手持语言的长矛对着外部世界,在漫无目的地上下求索一番之后,最后矛头却对准了自己。这就是卡夫卡的悲剧,这种悲剧其实也是语言的悲剧。
除此之外,卡夫卡还有许多其他的有关语言的精辟论断,譬如他说,“语言只借给活着的人一段不确定的时间。我们只能使用它。实际上,它属于死者和未出生者。占有语言必须小心谨慎”;“语言是重要的中间人,是媒介,是生动活泼的东西。但是,人们不能只把它当成手段来对待,人们必须体验它,忍受它。语言是一位永恒的情人”;“生活就是与其他事物的共处,是对话。”(注:《卡夫卡全集》,第5卷第349、441、333页。)1912年他还就意弟绪语发表过一次精彩的演讲,他表现得“潇洒幽雅、不无自豪”(注:布罗德《卡夫卡传》,叶廷芳等译,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109页。)。显然,语言与存在、语言与创作的关系,以及语言的局限和限度等问题一直是卡夫卡关注和思考的问题,而卡夫卡的这些关注和思考又必定在他的作品中有所反映。
三、语言的“城堡”
作为一个对社会现实观察十分深入、十分敏感的作家,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种十分复杂的语言背景以及十分尖锐的语言冲突,不可能不在卡夫卡的作品中得到某种程度的反映并留下某些痕迹。当然,卡夫卡的语言观也会直接影响并制约他的思想和创作。翻开卡夫卡的作品,我们马上便会注意到格里高尔的咕哝声、老鼠的口哨声、猿猴的咳嗽声以及那位从不演奏钢琴的钢琴家和从不歌唱的歌唱家,还有那些从不释放音乐的音乐狗……所有这些与卡夫卡独特的语言处境及他的语言观均不无关系。卡夫卡说,“我有时只是生活在一个小小的词语里,一个词语的元音里……,在一瞬间丢失了我无用的脑袋。第一个和最后一个字母就是我的鱼一般的感觉的开始和结束。”(注:《卡夫卡全集》,第6卷第65、26、47-48页。)因此,如果我们从语言学角度来解读卡夫卡的作品,那将不会是没有根据的;而且,由于这一角度一向被学者们所忽略,因而这种解读也将是新鲜而又独特的。
卡夫卡现存的最早的小说《一次战斗纪实》(大约写于1903至1904年冬天)就涉及到语言的疾病和语言的危机问题。小说中的胖子在听了祈祷者的倾诉之后,明白了祈祷者的问题所在:“这是大陆上的一种晕船病……这种晕船病的本质是:您忘记了事物的真正名称,现在,您急于给它们灌注偶然的名称。要快,要快!可是,您刚一离开它们,就又忘记了它们的名称。这就好比是被您称之为‘巴别塔’的田野里的白杨,因为您不知道,或不想知道,这是一棵白杨,它再次无名地摇动,依我看,您得把它叫做‘喝醉酒的诺亚’。”语言与实物、能指与所指的分离,就是现代人面临的语言的困境。“语言的疾病不仅是一种现代性疾病,它还贯穿在整个人类历史当中。”(注:Rolf J.Goebel,Constructing China:Kafka's Orientalist Discourse,Columbia,SC,USA:Camden House,1997,p.44.)胖子所期待的那种稳定、恰当的名称与真实意义之间的对应关系只不过是一种无法获得的理想。语言和现实分离后使得一切都变得不再真实,“月亮,你不再是月亮,但是,也许是我一时疏忽,把你——被称做月亮的东西——一直叫做月亮。当我把你称做‘被忘却的色彩奇特的纸灯笼’的时候,你为什么不再这样目空一切?当我把你叫做‘玛利亚圆柱’的时候,你为何差一点隐没?玛利亚圆柱,当我把你称做‘投下黄光的月亮’的时候,我再也看不到你那咄咄逼人的态度。”(注:《卡夫卡全集》,第1卷第255-256、260-261页。)月亮,只是我们偶然将它称做月亮,它才是月亮;如果我们将它称做“纸灯笼”或者“玛利亚圆柱”,它就不再是月亮。我们原以为我们和现实的关系十分牢靠,十分稳固。但其实不然,我们和世界的联系只是外表的联系,因为这种联系是通过语言建立起来的。
关于卡夫卡的代表作《变形记》,人们已有许多不同的分析和解释,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意见是:这是一则关于现代西方人的异化的寓言,“人变成甲虫”实质上是现代西方人生存状态和心灵感受的真实写照。这种理解和分析当然是不错的,不过,人何以被异化?人在异化后最不堪忍受的痛苦是什么?人的孤独感、恐惧感和灾难感的根源是什么?这些问题如果仅仅只从异化理论来理解,恐怕是不够的。我想,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将主人公的悲剧理解为一出语言的悲剧,也完全是符合作品实际的。小说开篇写道,“一天早晨,格里高尔·萨姆沙从不安的睡梦中醒来,发现自己躺在床上变成了一只巨大的甲虫。”变形后的主人公感觉最不能理解的是他自己的声音。“格里高尔听到自己的回答时大吃一惊,这分明是他从前的声音,但这个声音中却搀和着一种从下面发出的、无法压制下去的痛苦的叽喳声,这叽喳声简直是只在最初一瞬间让那句话保持清晰可听,随后便彻底毁了那句话的回音,以至人们竟不知道,人们是否听真切了。”(注:《卡夫卡全集》,第1卷第109、403页。)秘书主任在听了格里高尔的话后,不解地问格里高尔的父母亲,他们是否听懂了其中的哪怕一句。格里高尔的父母亲以及他的妹妹也都觉得格里高尔所说的话完全是一种“牲畜的声音”。最后,格里高尔也明白了,尽管他自己觉得他的话说得相当清楚,比从前清楚,但是,人们再也听不懂他的话了。更有甚者,既然他的话谁也听不懂,所以谁也不认为,连他的妹妹也不认为,他会听懂别人的话。原来,格里高尔的孤独感、焦虑感和恐惧感都源于人们听不懂他的话;反过来,正因为如此,人们也普遍认为,格里高尔听不懂人类的话。格里高尔的悲剧就在于这种语言的上隔阂和不理解,他的父亲和妹妹说,“如果他懂我们的话,那么倒也许可能和他达成一个协议。可是这……”而格里高尔多么希望父母亲能懂得他的请求,若是“可以和妹妹说话并感谢她为他所做的一切,他也许心里还会好受些。”格里高尔因为失去了语言,因而他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础,因此,最后他只好龟缩在房间的角落里,凄凉地死去。
《在流刑营》写一位“思想上全是欧洲那一套”的科考旅行家来到某流放地进行考察,亲眼见到某位上尉军官准备用一台特制的行刑器将一名冒犯上司的士兵残酷地折磨12小时,随后将他处死,但新司令上任后,却可能要废除这种刑罚制度。于是,上尉军官自己便毫不犹豫地欣然投入机器之中,同机器一起同归于尽。这部小说通常被看作是对司法机构的残酷和黑暗的揭露和批判,小说运用荒谬手法将现实生活中的非正义性作了绝妙的描写。然而,令人饶有兴趣的却是那架行刑机器用文字杀人,机器将法律条文刻在犯人的背上,直至犯人死亡。“一切都是为着文字设计的——但文字本身却是无法读懂的。”那些文字像迷宫一样密密麻麻地交织在一起,犯人通过自己的伤口来辨认这些文字,但这是不可能的。卡夫卡的这种做法“简直就是对现代语言蒙蔽方法的预言”(注:瓦尔特·比梅尔《当代艺术的哲学分析》,孙周兴等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16、35页。)。卡夫卡这样写恐怕不是偶然的。他早已看到了语言具有某种杀人的力量。
《城徽》是卡夫卡1920年写的一篇小小说。小说的开头是这样的:“起初,在建巴别塔的时候,一切还算井井有条;的确,这项工程也许过于庞大,人们太多地考虑到向导、译员、工匠的住处以及道路联络,以至于忘了尚须从事数百年自由的劳动。”(注:《卡夫卡全集》,第1卷第109、403页。)卡夫卡在小说的一开始就颠覆了圣经中巴别塔故事的基础;人类原初说的并非是一种语言,即亚当的语言,也就是上帝的语言。据圣经记载,语言起源于耶和华对各种事物的命名:“神用土所造成的野地各样走兽,和空中各样飞鸟,都带到那人(亚当)面前看他叫什么。那人怎样叫各样的活物,那就是它的名字。那人便给一切牲畜和空中飞鸟、野地走兽都起了名。”人类的语言由此诞生。由此看来,语言和事物的原初存在是自然的、和谐的,它们之间的关系是一一对应的,并且是唯一的,这中间不存在偶然性和任意性。而卡夫卡首先抛弃的,就是这种陈腐的有关语言起源的理论。在他看来,“多种语言并存原本是建造通天塔的前提条件”(注:Lorna Martens,Shadow lines:Austrian Literature from Freud to Kafka,Lincoln: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1996,p.202.)。卡夫卡已经敏锐地意识到了语言的危机,语言的偶然性和任意性等问题,而这正是20世纪欧洲学术界最为关注的问题之一。
《美国》描写16岁的少年卡尔·罗斯曼受到中年女仆的引诱后,被父亲放逐到美国的生活经历。但是,小说中的“美国”并不是指那个历史上、地理上的具体的美国,它只是一个语意漂浮的象征符号,批评家和读者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理解将其锚泊在任何一种稳定而清晰的意义上。譬如布罗德便认为小说探讨的是“个人进入人类社会的问题”,“同时也是个人进入天国的问题”;而更多的人却愿意将“美国”看作是一种人类美好社会的象征;也有人将小说当作是对美国社会的批评和揭露;当然,将“美国”当作是卡夫卡逃避布拉格的一种策略,或是一种对自由的向往,也不无道理。(注:Ernst Pawel,The Nightmare of Reason:A life of Franz Kafka,New York,1984,p.102,p.240,pp.428-429,p.99,p.257.)
《诉讼》与其说描写了一次有结果的审判,不如说表现了整个无结果的诉讼过程。主人公约瑟夫·K是一家大银行的首席业务助理,一天早晨他在自己的寓所里莫名其妙地被捕了。K究竟犯了什么罪,无人知道,甚至人们也无须知道,人们只知道他“犯罪”了这一“事实”。看来,这种犯罪不过是一种语言上的“犯罪”,并非事实上的犯罪;并且,这种逮捕也只是一种语言上的“逮捕”,并不是事实上的逮捕,但K并不愿意接受这一“事实”,他托关系,找门子,奋力为自己辩护,不过,据熟悉内情的画家介绍,他所希望获得的无罪判决有三种形式:一种是真正宣判无罪,另一种是表面宣判无罪,第三种是无限期延期审判。然而,在画家看来,第一种是完全不可能的,因为“任何人都无法促使法庭作出这样的判决”。这样一来,所谓“无罪判决”也只不过是语言上的无罪判决,并不是真正的无罪判决。语言上的判决看似虚空,但其效果往往也是斩钉截铁的,“写在纸上的东西是不会改变的,不同的看法往往反映的是人们的困惑。”(注:《卡夫卡全集》,第3卷第11、34、14、124、175页。)K于是看清了世界的本相:“谎言构成了世界的秩序。”(注:《卡夫卡全集》,第3卷第177页。)
《城堡》一开篇也涉及到语言问题。小说写K来到教堂后面的一所学校,“这时候学生正跟着老师走出来,学生在老师周围围了厚厚的一层,个个望着他,七嘴八舌讲个不停,他们说得很快,K一点也听不懂。”(注:卡夫卡《城堡》,韩耀成译,浙江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第10页。)孩子们重复的是父辈的语言,父辈的经验,而作为外乡人的K却不能进入这种语言和经验之内,因而K也就无法进入城堡。当然,这部小说更为突出的特点是,它与当代语言学理论,尤其是后现代主义的语言观非常吻合。小说的故事非常简单:土地测量员K深夜来到城堡附近的村庄,城堡近在咫尺,可是无论他怎样努力,也无法进入城堡。他在城堡附近的村子里转悠了一辈子,在生命弥留之际,有人告诉他,说:“虽然不能给予你在村中的合法居住权,但是考虑到某些其他情况,准许你在村里居住和工作。”长期以来评论家们对“城堡”的寓意一直争论不休。“城堡”就像一个失去了谜底的谜语,虽然各种猜法都有道理,但真正的谜底却无人能够猜中,或许“城堡”原本就不存在什么真正的谜底。如此说来,“城堡”就相当于后现代主义语言观中的“所指”,而K则相当于“能指”。K无法抵达城堡,就意味着能指永远也无法企及所指。卡夫卡的城堡就是这样一座语言的“城堡”。
以上我们从语言角度对卡夫卡的三部长篇小说以及几部主要的短篇小说进行了分析阐述,我们没有必要对卡夫卡的所有创作都从语言学角度一一进行分析。总之,卡夫卡虽然从摇篮里抱来了别人的“孩子”,但这“孩子”在他的精心培育下终于长大成人。尽管卡夫卡对这“孩子”总是不能满意,总希望有自己的真正的“孩子”,但这“孩子”由于在特殊的环境中长大,因此他是独一无二、无可摹仿的,并且他最终成了全世界的“孩子”。“简言之,布拉格德语是一种解辖域化语言,正好适合陌生人和少数人使用”;“德语在捷克斯洛伐克,作为一种与捷克语和意第绪语混合的变动不居的语言,它正好使卡夫卡有可能去创造。”(注:Gilles Deleuae and Felex Guattari Kafka:Toward a Minor Literature,The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p.19,pp.17-21.)词语就是主人,它能够直接创造形象和想象。卡夫卡用德语写作,这使他总感觉到自己像一个无家可归的人,非常不安和焦虑,但是,这种不安和焦虑成就了卡夫卡,使他不知不觉便抓住了人类心灵深处的痛苦和不幸。作为一个犹太人,卡夫卡用德语赋予了人类的这种痛苦和不幸一种最完满的形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