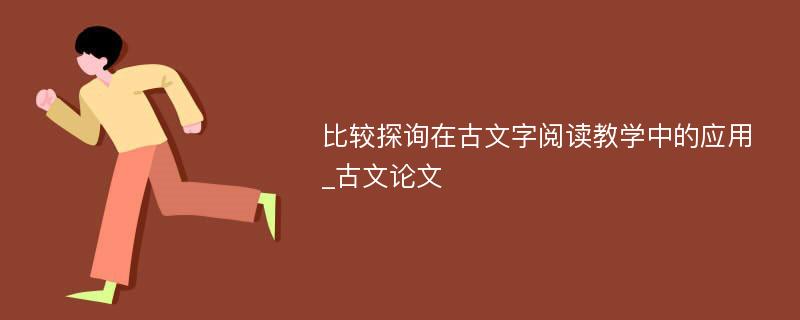
比较互勘在古文阅读及教学中的运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古文论文,教学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古文阅读或古文教学过程中,教师应具有辩证、联系的观点,具备比较、分析、鉴别的能力,在纷繁复杂的现象面前,或去其伪、存其真,或考其优、论其劣,或较其异、求其同,以便最终能够择善而从,或者触类旁通。
一、比较同一古书的各种不同版本,择其善者而读之
古书从前主要是以手工抄写而成。大约到了唐五代时,古人才正式使用雕版印刷技术刊行古典经籍。同一古书无论是传抄还是被刊刻,常形成各种不同的版本。各版本在文字上往往互有出入,不尽相同,但相对于古书的原初形貌来说,均不免有所错讹。那种错误较少、没有什么残缺的本子,可称之为“善本”。如张之洞《輶轩语·语学篇》“读书宜求善本”条云:“善本非纸白、版新之谓,谓其为前辈通人用古刻数本精校细勘付刊,不讹不阙之本也。”
阅读古文,首先应做的一个工作是,将古书的各种不同版本加以比较、甄别,从中选出善本作为阅读的对象。善本的文字错讹较少,一般没有残篇断句的现象,读者藉此可以较为容易地探得作者的本意。前人阅读古文,十分注重选择善本。如近人孙德谦说:
盖读书贵得善本。若读本而不得其善者,所读之书倘信以为善本,则所失匪浅,将有误读而误解,为人嗤鄙者矣。……夫古书而为善本,读之则有益;反言之,则读不善本者,必且无益而有损。(《古书读法略例》)
孙氏所言极是。阅读古文不求善本,只会是“无益而有损”。《颜氏家训·勉学篇》中记叙过这样一件事:
江南有一权贵,读误本《蜀都赋注》,解“蹲鸱,芋也”乃为“羊”字。人馈羊肉,答书云:“损惠蹲鸱。”举朝惊骇,不解事义。久后寻迹,方知如此。
故事是说,有个大人物读的《蜀都赋》的注释本,是一个有错误的本子,它把注解文字中的“芋”错成了“羊”,以致这位大人物以为古书上所讲的“蹲鸱”(本是芋头)是指羊肉,闹出了笑话。由此可见,误本很容易让人步入迷途,阅读古文当惟善本是求。
既然读书当择善本,那么怎样知道一部古书或一篇古文的不同传本何者为善、何者为劣呢?这要靠读者对各种传本进行认真的比较、分析,看何本的文字最为完备,残缺、脱漏的现象最少;然后比对有关文句,看何本的文字错讹现象最少。有了这些比较后,文字相对完备、错讹现象最少的本子就是我们所说的善本。举个例子如下:
曹植的作品集名曰《曹子建集》。就流传至今的《曹子建集》的各种版本看,数量不少,举其要者有:江安傅氏双鉴楼所藏明代活字本、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所藏宋刻本、清代丁晏《曹集铨评》本、《四部备要》排印本等。把这些不同版本放在一起比较、分析,我们可以发现,丁晏的《铨评》本据其他各种版本和相关古籍(如古代的类书)增辑了不少的佚篇残句,而且考辨各本文字的异同,写出了高质量的校勘记,因而无论是在文字的完备性上,还是在文字的正确性上,都是其他版本难以企及的。比如说,明活字本《曹子建集》尽管有它的优点,但还是不及《铨评》本。明活字本有很多重要的篇目失收(如《七步诗》等),而且文字上舛误不少,有时令人无法卒读。再比如说,《四部备要》本也不可与《铨评》本比肩,它有着与明活字本相同的很多错误,如“望城不过,面邑不游”(《应诏》)中的“邑”错为“色”、“或云沸潮涌”(《酒赋》)的“沸”错为“拂”。通过作上面的对勘辨析,最后就可确定《铨评》本是较好的版本,如读《曹子建集》就不妨选用它。
阅读古文时选择善本,有一个比较简便的办法,就是根据古今目录学家、古籍版本学家的介绍、评价来选定。古今的一些目录学家、版本学家对一些古籍的版本情况覃研有素,他们对一书的各种版本的优劣的评价具有很高的可信度,我们可据以确定善本。他们对古籍版本的意见可在其目录学著作或版本学著作(如《四库全书总目》、《贩书偶记》、《中国善本书提要》)中查得。如,欲读东汉文学家蔡邕的《蔡中郎集》,要知何本为善,就可查检张之洞著名的目录学著作《书目答问》。其书卷四有云:
《蔡中郎集》六卷。汉蔡邕。聊城杨氏仿宋本,附《独断》二卷。通行三本皆逊此。
由此可见,聊城杨氏仿宋本是比较好的本子。参阅这类著作,有一问题值得注意:这些著作把某个版本定为善本,有时是着眼于书籍的文物价值,即把刊刻精美或流传稀罕的本子视为善本,这和我们在上面从阅读的角度提出的“善本”标准不完全一致。
使用所谓“善本”,仍然需要进行比较互勘。任何善本难以达到十全十美的境地,仍不免存在讹、脱、衍、倒等方面的问题。因此,使用善本时还有必要将其他相关版本拿来比照、对读;遇有文字上的出入,要结合上下文意进行认真、冷静的分析,究其孰是孰非;如果是自己使用的善本有问题,还是应当依从别本的相关文字,并据其作出校正。例如:
古典小说《燕丹子》的版本,按照学人们的看法,应该是以清人孙星衍的校订本为善本。孙氏的校订本是怎样形成的呢?有关资料显示,他是以纪晓岚抄自《永乐大典》中的《燕丹子》为底本,然后参考其它资料对这个传抄本作出补正,形成了他的校订本;而孙氏用作底本的那个传抄本虽然源自《永乐大典》,但因误抄之故,它实际上与《永乐大典》原本的文字出入较大。这样一来,《燕丹子》的版本除了孙氏的校订本以外,至少还有原本《永乐大典》本。因此,阅读《燕丹子》而以孙氏校订本为善本时,应该把《永乐大典》本找来对勘,以便遇有文字出入时能够择善而从。如果把台湾世界书局影印的《永乐大典》中的《燕丹子》与孙氏校订本对勘、比照,真的还可发现文字上的相异之处。例如:
孙校本:(荆)轲左手把秦王,右手椹其胸。
《大典》本:(荆)轲左手把秦王,右手揕其胸。
结合语境,把两个版本的上述文字加以比对辨析,很容易看到《大典》本优于孙校本:孙校本作“椹”,意思是“砧板”或“箭靶”,明显于文义无所取;而《大典》本作“椹”,意思是“用刀或剑刺杀”,与语境十分相契。此外,还可在《战国策·燕策三》中找到一个有力的佐证:“(荆轲)因左手把秦王之袖,而右手持匕首揕抗之。”此正作“揕”。因此,在把孙校本作为善本阅读的时候,上述文字应以《大典》本的为是。
二、比较、分析古今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择其优者而用之
流传至今的很多古文,特别是古文中的名篇,历来有不少人从各个角度(如句读、词义、句义、文法、思想内容、艺术手法等)进行研究,累积了不少相关的研究成果。对此成果,我们今天应该善加利用。只需注意的是,对某些古文作品,学者们往往见仁见智,看法不太一致,甚至于相互抵牾。这些不同的观点,往往有的正确,有的则不太正确,甚至是错误的。因此,在参考、利用已有的相关研究成果而遇到异说并存、观点互歧的时候,不可盲从,而应抱一种去伪存真、取精用优的态度,把各家的成果摆在一块认真比较,并综合各方面因素加以推究、辨察,然后取其合理者、科学者从之;如果发现各家的观点有误而不堪择用,自己则应另辟蹊径,重新研治,以求得出正确的结论。以下,试从几个方面举出实例加以说明。
古文阅读或教学过程中,首先往往碰到的是断句标点问题。对某些古文,不仅古代的学者作有句读分析,而且今天的学者还作了明确的断句标点,但他们在断句或标点上也时或存在分歧,且其分歧往往引发不同的理解。这个时候,我们应该利用自己掌握的词汇、语法、音韵、历史文化等方面的知识,分析语境,以观何种断句、标点方式最能传达出古文作者的本意。如韩愈《师说》中“李氏子蟠”云云,目前可以见到两种断句、标点的方法,一是:“李氏子蟠,年十七,好古文六艺经传,皆通习之。”另一种是:“李氏子蟠,年十七,好古文,六艺经传皆通习之。”如果结合上下文意作比较分析,可以看出,前者的断句、标点存在着问题:一是不符合作者的本意,因为作者的意思只是说李氏子蟠喜好古文。二是与事理、情理相违,因为古文不存在六艺经传那样的科目,故以“通习”应之,明显不妥;再者,六艺经传虽是古时读书人必须课习的,但因其科目繁多,内容参差,很难让一个人都喜好。因此,此处当取第二种断句、标点的方法。
比起断句、标点来,对古文中词语的训释更容易产生分歧。在阅读和教学中,我们经常可以遇到这样的情形:对古文中的同一个词语,学者们作出的解释异说纷纭,莫衷一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参考他们的研究成果,必须悉心地比较、考论,作出正确的判断后再采择一家的可信之说。举例来讲,《论语·先进》中有一段话被中学语文教材选入,题作《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其中有云:
子路率尔而对曰:“千乘之国,摄乎大国之间,加之以师旅,因之以饥馑;由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夫子哂之。
其中“且知方”的“方”历来有不同的解释;就笔者之所见,至少有四种不同的解法:
一是以“义”释“方”。如三国何晏《论语集解》:“方,义方也”。清刘宝楠《论语正义》:“郑注此云:‘方,礼法也。’礼法即是义。”
二是以动词“向”释“方”,谓归向、向往。如朱熹《论语集注》:“方,向也。谓向义也。”
三是以“方向”释“方”。如郭锡良等先生《古代汉语》注:“方:方向。”
四是以“道理”释“方”。如杨伯峻先生《论语译注》译“且知方也”云:“而且懂得一些大道理。”现行高中语文课本注“知方”云:“知道为人的道理。”
以上四种解释,究竟该采信哪一种呢?如果认真比较、分析,就会发现第一种解释是最为妥切的。这是因为:
第一,训“方”为“义”,于古有据:不仅有古代训诂专书的解释可以稽考,而且亦有古代文献的相关用例可为参证。如《广雅·释诂》:“方,义也。”又如《左传·隐公三年》:“臣闻爱子,教之以义方。”此处“义方”为同义连文,故清人洪亮吉注云:“方,义也。”
第二,更为重要的是,将文中与“勇”对举的“方”释为“义”,能很好地体现古人“义”“勇”并重、以“义”制“勇”的伦理思想。考察古人的思想观念、伦理意识,不难发现,古人(特别是古代儒家)往往是将“勇”与“义”关联起来,言“勇”常及“义”。且看如下材料:
《论语·阳货》:“子路曰:君子尚勇乎?子曰:君子义以为上。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
《荀子·荣辱》:“轻死而暴,是小人之勇也。义之所在,不倾于权,不顾其利,举国而与之不为改视,重死而持义不桡,是士君子之勇也。”
《国语·周语下》:“言勇必及制。”三国韦昭注:“以义为制也。勇而不义非勇也。”
由此,不难看出古人(特别是儒家)伦理观念、人文取向上的如下两点:其一,在个体行为上,提倡“勇”与“义”的浑成、融合,无所偏废,以实现个体人格自我完善与个体人格社会化的结合、统一。其二,“勇”固然是值得称美的品质,但如果没有“义”的节制、约束,也会失去其道德价值。“义”是“勇”的准则,“勇”应服从于“义”,接受“义”的指导和制约。子路学宗儒家,不可能不受上述“义”“勇”并重、以“义”制“勇”的伦理意识的影响;在向孔子谈论自己的治国理想、提出“可使有勇”的时候,不可能不想到“可使有义”。况且,子路使用了“且”这一字眼,又明显是把“方”和“勇”对举,同样将“方”看得十分重要。因此,将此“方”字释为“义”,最为精审,能使子路之言与古人的义勇观相契合。
对于涉及全篇或者全书思想内容方面的各种说法,我们也要注意进行比较、勘覈和甄别,择善而从。比如说,李白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诗,一般人认为是写李白于阳春三月,在黄鹤楼上目送友人孟浩然渐渐远去的船帆,直到那船的影子消失在天边,表现出李白对友人依依不舍的惜别之情。但是,王达津先生提出了不同的说法(见1984年1月31日《光明日报》所载文章), 认为此诗不是写李白对孟浩然的依恋之情,而是写孟浩然告别李白时之所见、所感。他的主要依据是陆游《入蜀记》卷五的记述:
八月二十八日访黄鹤楼故址,太白送孟浩然诗云:“孤帆远映碧山尽,惟见长江天际流。”盖帆樯映远山尤可观,非江行久不能知也。
据此,王先生认为李白诗“全写浩然所见,他的用意不但在写旅人一路观赏武昌以下的青山,核心正是在写青山尽时,浩然回首瞻望黄鹤楼和故人。”又据李白“黄河之水天上来”之类诗句,认定“写江河天际流,却必当是指上游”,进而认为望见“长江天际流”的人是浩然,是他从下游向上游望,还说浩然“回首只见长江自天际浩渺下流,……黄鹤楼和故人都杳然不见了,无限离思,难以为怀”。
然则,究竟是一般人所持的看法对呢,还是王先生的新解正确?如果细察全诗并结合李白的其他作品加以论析,就知王说虽然新颖可喜,但不可取。对此,温洪隆先生曾撰文(见《华中师范学院学报》1984年第3期)作了令人信服的辨证,说:
陆游之说也未必就是定论。退一步讲,即使如陆游所言作“孤帆远映碧山尽”,但依其“帆樯映远山尤可观,非江行久不能知”之说,也是指在李白的视线内,见孟浩然所乘的孤帆与黄鹤楼以下远处的碧山相映照尤可观赏。
此外,李白《江夏行》有“去年下扬州,相送黄鹤楼。眼看帆去远,心逐江水流”等句,与送浩然的这首诗意境极似,但前者“眼看”云云也并不是写被送者从下游朝上游瞻望。最后,温先生还就诗的标题作了分析,认为标题所表达的意思是李白在黄鹤楼送别故人孟浩然到扬州去;如依王说,这首诗的作者就应是孟浩然,题目也应该改为《黄鹤楼别李白之广陵》。
在参考古今学人的相关研究成果时,我们会碰到这样一种情况:学者们对某一问题的看法不尽相同,甚至相反,而要把这不同的意见放在一起比较互勘,最后作出谁对谁错的判断,已是无法做到,因为我们今天所见的资料有限,已不足以支持我们作出这种判断。像这种情况,我们只能暂且存疑,或根据自己的看法姑且从其一说。如屈原有长诗《离骚》,这个诗题的“离骚”二字如何解释?如要参考古今学者的意见,则是五花八门,举其要者有“离忧说”“遭忧说”“牢骚说”“歌曲名说”“抒忧说”等。那么,这些不同的解释究竟是哪一种正确?就目前所见的传世文献资料来看,已是很难判定谁是谁非了;就是把笔墨官司再打下去,也难以分出胜负来。像这样的问题,也许永远是一个谜,无法破解;也许将来有朝一日发现了什么新资料,人们会解开疑团,得其正诂。而在目前,我们只能姑且从纷纭的异说中选择一种自认为有理的说法以作解释。
三、把内容或形式相关的古文作品进行比较、分析,以求相互发明参证
读书必须博观,读古书尤应如此。何以“博观”?一个重要的途径就是取内容或形式相关的古文来与所读之文相互比较、彼此参证。这样,有助于弄清和通达古文的义理,能收因彼见此、融会贯通之效。
从一些学人论述读书方法的言论来看,都很重视将内容或形式有关联的典籍、篇章合拢作比较,以求相互发明、印证。如著名文献学家张舜徽先生在《中国史籍校读法》中说:
在包含着丰富历史资料的古代书籍里,有不少的整部书或单篇写作,内容方面是大致相同或相近的。我们阅读时,便可把他们集中起来,彼此对勘,互相参证。这对于帮助理解,有很大的作用。……如《逸周书》有《官人篇》,《大戴礼记》也有《官人篇》;《荀子》有《劝学篇》,《大戴礼记》也有《劝学篇》;篇题既完全相同,文字也很少有异。至于篇题小异,而内容大致相同的,如《墨子》有《所染篇》,《吕氏春秋》有《当染篇》,都可综合起来,放在一块儿钻研,比较容易发现问题,解释疑难。
张先生所论甚是剀切。从阅读或教学实践来看,把内容或形式有关联的古文集中在一起进行比勘参证,至少有两方面的益处:
1.通过比较文字上的异同,于异文处可以发现文字错讹、脱衍等现象,以便校正,从而为读懂古文奠下基础。比如说,将《史记》和《汉书》参读比较,就有利于订正传本上的文字错讹。举一个例子,清代武英殿本《汉书·酷吏传》有云:
(尹齐)以刀笔吏,稍迁至御史,事张汤,汤素称以为廉武,帝使督盗贼。
按照武英殿本上的这段文字来理解,后两句的意思是说:张汤一向称道尹齐的廉洁勇武,汉武帝才让尹齐分管抓捕盗贼之事。但是,如将《史记·酷吏列传》找来对读,就会发现,按照武英殿本《汉书》文字所作的上述理解不合事实。《史记·酷吏列传》记尹齐之事云:“(尹齐)以刀笔稍迁至御史,事张汤,张汤数称以为廉武,使督盗贼。”另外,《汉书》、《史记》的《酷吏传》记述与尹齐同时代的另一酷吏王温舒的事迹时,说王“事张汤,迁为御史,督盗贼”。将这些材料加以比对参印,可以看到,使尹齐“督盗贼”的人并不是汉武帝,而应是张汤。这说明,武英殿本《汉书·酷吏传》“帝使督盗贼”的“帝”字可疑,应是一个多出的衍字,正如王念孙《读书杂志》所说:
“帝”字,后人所加。此言张汤素称尹齐之廉武,使之督盗贼,非谓武帝使督盗贼也。……后人误以“廉”字绝句,而以“武”字属下读,因妄加“帝”字耳。
这可谓讲明了清人所见《汉书·酷吏传》传本中出现衍文“帝”字的原因。
2.通过比证内容或形式相类的古文文句,可觅得正确阐释特定作品意义的线索和旁证。
在阅读和教学中,如要考求古代作品中某一词、句的意义,通过穷搜博讨,把古书中一些与所释之词、句相类的其他材料集中起来,放在一起比较互勘,往往能寻得作出正确训释的一些线索和依据。下举两例说明之。
姜夔《扬州慢》词云:“渐黄昏,清角吹寒,都在空城。”其中“寒”字,今人往往认为是指寒气、寒风等而言,如高中语文教材第三册注其中“清角吹寒”云:“凄清的戍角在寒气中吹着。”这明显是将其结构理解为“清角吹于寒”,并以“寒”指寒气,作补语。
其实,这种解释存在问题。如将古代作品中与“清角吹寒”相类的文句稍作搜集、比勘,就不难发现,其中的“吹”应指戍角吹出的声音,而“寒”是对吹出的声音进行陈述。古诗词中有“促柱弦始繁,短箫吹初亮”(南朝张嵊《短箫诗》),“玉龙吹怨,似替人幽咽”(宋仇远《醉江月》)之类文句,其中“短箫吹初亮”“玉龙吹怨”从内容到形式都无疑与“清角吹寒”相类,但它们都显以“吹”指乐器所吹出的声音,为句子的主语部分,且分别以“怨”“亮”作谓语,全句不能理解为“玉龙吹于怨”“短箫吹于初亮”。以此为参照,知“清角吹寒”也不当理解为“清角吹于寒”,而应以“吹”为主语成分,“寒”作谓语。至此,如果再将“清角吹寒”与宋词中“角声寒,夜阑珊”(唐婉《钗头凤》),“酒醒罗浮角声寒”(高观国《留春令》),“湘尾鼓声寒”(王庭珪《江城子》)之类文句相参较,又知其中充当谓语的“寒”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寒冷;此字实际上涉及“通感”这一艺术手法的运用,即把诉之于听觉器官的声音描写成触觉所能感知的现象,意谓声音凄楚苍凉。
再看一例。选自《左传》的《曹刿论战》有云:“吾视其辙乱,望其旗靡,故逐之。”对其中的“靡”,中学语文教材及许多古文选注本都解释为“倒下”。我们知道,训释古籍中的字词,当做到“揆之本文而协,验之他卷而通”(王引之语)。以“倒下”训“望其旗靡”之“靡”,虽然可以做到“揆之本文而协”,但如将古文中与“望其旗靡”之内容相类的句子比较互勘,就知它难于做到“验之他卷而通”。北魏温子异《韩陵山寺碑》:“靡旗蔽日,乱辙满野。”此处“靡旗”之“靡”当与“望其旗靡”之“靡”义同;但此“靡旗”之“靡”如作“倒下”讲,显不允当,因为倒卧的旗帜是不可能“蔽日”的。又如《左传·宣公十二年》:“吾闻致师者,御靡旌摩垒而还。”此处“靡”字如训作“倒下”,也不免使人心生疑惑:古人致师的目的本在于镇抑敌军气焰,鼓舞本军斗志;如果“致师者”(即挑战者)所举的旌旗是“倒下”的,又怎么可能威震敌军呢?由此推知,释“望其旗靡”之“靡”为“倒下”,不甚精当。欲得“靡”字正解,仍可通过比勘同类用例之法来推求。如上引“御靡旌摩垒而还”句,清人焦循注曰:“靡者,衺(邪)倚也。”可见“靡”有倾斜之义。如将此义施之于包括“望其旗靡”在内的与旌旗事相涉的文句,则无有不通者。
标签:古文论文; 读书论文; 文化论文; 李白论文; 文学论文; 永乐大典论文; 中国古代文学论文; 善本论文; 曹子建集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