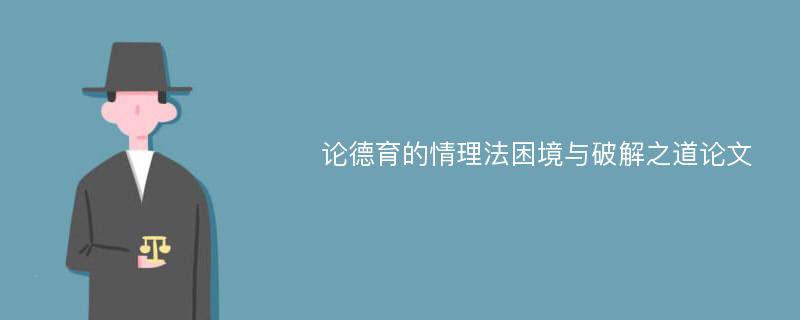
主持人语:
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人才是国家发展的第一资源。“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是办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根本问题。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性质决定了我国解决这个根本问题的方案与其他国家迥然不同。习近平总书记在学校思政课教师座谈会上指出:“我们党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必须培养一代又一代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立志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有用人才。”这一论断揭示了“立德树人”的明确内涵和本质要求,指明了道德教育在人才培养中的重要性。
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道德教育与教育伦理是我国高等教育研究的基本内容之一,也是理论界持续关注的重大理论课题。问题是时代的声音。当前我国处于社会转型发展阶段,学校道德教育与教育伦理面临一些新挑战,“道德困境”“道德冷漠”“学术诚信”“师德失范”等话题时常进入公众的视野,引发人们的思考,召唤理论界的关注与回应。深入研究新时代教育事业发展中的道德伦理问题是理论工作者肩负的学术使命。近年来,理论界围绕中国特色教育伦理理论体系建构、师德评价的标准与方法、立德树人的伦理价值和教育价值等前沿问题开展研究,提出了不少真知灼见,凝聚了学术共识,为有效破解当前道德教育与教育伦理面临的难题提供了智力支持。
[44] US Department of State, Testimony Before the House Committee on Foreign Affairs Subcommittee on Asia and the Pacific, February 5, 2014, https://2009-2017.state.gov/p/eap/rls/rm/2014/02/221293.htm.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大学首先要“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道德,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马克思主义是我国大学最鲜亮的底色,“彰显光明美好的德行”是高校师生共同的使命和追求。这组专题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探讨了高校道德教育与教育伦理问题。《论德育的情理法困境与破解之道》《具身道德的教育路径》主要从学理层面探讨“德育中的情理法统一”和“具身道德的价值”问题,对如何提升高校德育的实效性进行了有益的探索。《校园中的熟人道德与陌生人道德》主要从实践角度分析“道德关系理论”对道德提升的意义,提出了破解“道德困境”的有效途径。高校道德教育建设关键在教师,教育者必须首先受教育。《师德示范特征与教师性道德修养检讨》一文聚焦师德建设,提出“师德修养卓越化”重要命题,颇有见地。本专题文章涉及道德建设与教育伦理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涵盖道德建设的主体与客体,内容丰富,观点新颖,相信可以给读者带来启迪。
智慧校园的规划各有差异。每个高校可以根据自身的特点,综合考虑人才培养理念、办学特色和校园文化等特征,设计自己的业务架构、应用架构、资源架构和数据架构,设计出学校未来数年内操作性较强的智慧校园。以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技术为支撑,智慧校园应用软件架构如图2所示。
一个由12名专家组成的评审组于9月10日—14日在桑迪亚国家实验室(SNL)对B61-12延寿计划的电子、机械、热和飞行试验数据和分析结果进行了详细评审,确定B61-12延寿计划能够满足国防部的相关要求。评审组还评审了潘得克斯工厂的程序、培训工作开展情况和安全性,确认该厂已为启动最终生产认证工作做好了准备。
——双传学(南京大学)
论德育的情理法困境与破解之道
董云川a,韦玲b
(云南大学 a.高等教育研究院,昆明 650091;b.马克思主义学院,昆明 650500)
【摘 要】 “情”“理”“法”的融合生长是德育不断发展和突破的必由之路,“情理”总是渴望体谅与变通,“法”则表明无法宽容和放任。大学德育在理论和实践中不断遭遇“情理法”的缺失、僭越和冲突,导致德育实践产生异化,对人的塑造变为对人性的压制,德育目标难以取得个体的情感体验实现其内化,从而使道德教育失去原本的意义,道德目标滑向虚无。破除德育“情理法”困境,需要在对其进行准确阐述和定位的基础上探寻三者的融合之道,在融合中建立“以理为本、以法为界、以情为准”的新型德育观。
【关键词】 德育;情;理;法
趋于制度化的德育之“法”,使德育从“情理”中剥离,成为一种孤立的制度体系,表现为道德权威下的规训履行演变为徒劳的灌输与压制。在道德权威下的规训履行,借助于德育之“法”把既定的道德规范从外部强加给受教育者,对其进行规训,这个过程的特征表现为对人的支配和对人性的压制塑造,忽视了个体的“情理”因素,造成对个体价值选择和道德判断的遮蔽。规训的另一个表现是道德标准脱离德育“情理”而空泛化,使道德成为一种抽象的符号,丧失了教育功能。比如:“学习雷锋好榜样”从主题班会变为市中心的“学习雷锋时代广场”,“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的传统伦理演变为娱乐节目中的绕口令游戏,这样类似的道德说教的庸俗化,甚至泛娱乐化使道德标准已然丧失了其道德教化的功能,演变为一种外在化的规训。这种高、大、空的道德伦理和抽象空洞的道德规范,使强化、固化德育“情理”的德育之“法”从“情理”中剥离成为一种抽象的道德符号和失效的道德权威。
在教育管理和教学实践中,情理法的纠结不断浮出水面,大学德育同样面临着“情、理、法”缺失、僭越和冲突等问题。从德育语境看,由“情”与“理”所构建的道德观念体系,虽然以社会公认的价值准则为内核,但在指导和制约个体行为时,这种强制规范性往往与个体的“情理”因素产生矛盾。德育“情理法”的冲突与背离,表现为当德育设法试图对人以及人的存在作出超越“情理”的预设,并通过“法”的形式使其遵从时,德育目标、德育实践、德育效果之间往往出现德育逻辑的“混乱”与德育体系的“僵化”,要么导致德育实践产生异化,对人的塑造变为对人性的压制,要么德育目标难以取得个体的情感体验实现其内化,从而使道德教育失去原本的意义,道德目标滑向虚无。破除德育“情理法”困境,需要在对其进行准确阐述和定位的基础上探寻三者的融合之道。
一、德育情理法的理论与逻辑
何为德育之“情”?与西方的法理性社会不同,中国自古以来便是一个伦理性的国度,属于“情本体”而非“理本体”。中国传统价值观体系主要源于“情本体”的价值取向,情感因素是道德判断的重要内容。何为“情”?在人类社会的交往实践中,“情”作为一种通过适应、反思、选择后的本能反应,具有人之常情、人之本性、人的本能等义。“人情”也不仅仅局限于主观的随意性,而是指具有普遍意义的常情常理、民情民意、世情社情,道德礼仪、风俗习惯等,即民情、社会共识。德育之“情”就是基于特定个体的文化背景、生活经验、自身道德诉求之上的个体道德选择,这是德育“理法”协调的结果。在德育实践中,“情”属于一种弹性的道德判断,表现为个体依据自身的情感因素、特定的道德情境而做出的具有个体性因素的价值选择和道德判断。
与西方社会崇尚自然法的绝对权威不同,在中国人的情理法观念中,“国法”与“天理”“人情”密不可分,理想的状态应该是一种三位一体的复合的、多元的体系。西周统治者提出“以德配天”“明德慎罚”“敬德保民”等民本思想,注重“天理”“国法”与“人情”的结合。《论语·雍也》:“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中庸之道,在乎于合理合情。西汉董仲舒提出“天人合一”“天人感应”的哲学理念,并指出“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宋代以朱熹理学为代表的中国哲学家们,皆遵循“三纲五常”的伦理权威,并使之上升为不容置疑的“天理”。由此可以看出在中国特有的情理法观念中,“天人合一”的实现,是“国法”“天理”“人情”的相互贯通和有机融合。“情、理、法”之间所呈现的是伦理道德与社会规范之间的平衡之道,“天理”体现为“国法”,“国法”又上升为“天理”,“天理”需与“人情”相通,“国法”亦须顺应民情,这符合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关于对立面统一的学说”[3],也体现了中国传统社会的礼制精神、中庸哲学和经权能动的思维模式。在这一融合中“国法”的不可抗拒性和伦理性得以彰显。
德育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德育从其现实性来讲,源于现实世界,指向可能世界,在指导人从实然向度过渡到应然向度的过程中,必然无法离开教育客体之“情”和现实世界之“理”。德育不能脱离人们现实生活而存在,背离生活将使德育失去生机与功能,从而消解于与人的疏离之中,道德之“法”也落入虚无。克服这种虚无倾向,需要德育向内求索,向人及人的生活世界的内部发问,在“情理”的协调中,探寻具有融合性的德育之“法”,通过道德法则的完善,实现德育的目标。
何为德育之“法”?“法”是一种具有强制力、确定性的行为规范,制约人的主观意志。康德的墓志铭写道:“有两样东西,我们愈是反复思索,就愈使我们的心灵增长景仰和敬畏:在我之上的星空和居我心中的道德法则。”“道德法则”是实现“人是所应是”的具体途径和方法,即德育之“法”,在德育实践中,体现为实现德育目标的系统化、规范化和强制化的方法和制度体系。然而,“法”的产生实际上源于人们对于“情”“理”的抽象概括,是在交往规律中对于“情”“理”的有意创设,是人们为了更好地实现社会合作,争取社会和谐的努力。因此,“法”作为人类的创制物,绝不是脱离“情”“理”的自在之物,其体现了人类的有限理性。“法”的本性以及所体现的“规律”是公理性与主观性、公益性与意志性的统一。“法”的基础是“情理”,“情理”的实现需要“法”的保证,德育的“情理”是德育之“法”即德育规律优化与进化的基础,而德育之“法”是德育“情理”的固化与强化的条件。
因此,我们前文介绍的德国最高法院在Fullplast Process案中的论证,在理论上是站不住脚的。在方法专利权人将运行该方法的商品投入市场的情况下,他是通过这一商品在市场上投入了他的专利方法所提供的服务。由于他是唯一有机会向市场提供这种服务的人,因此他的利益已经可能实现。至于他是否通过合同或其他方法来实际实现这种利益,则是另外一个层面的问题。
除此之外,以伦理为中心的价值观,试图对人的存在和人的教育探寻一种向内而求的路径,让人摆脱外在的规范性,自由地探求其生存的意义,在此过程中由内而外地产生一种人“是其所应是”的德行。正如孟子所言:“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在这种伦理世界中,“德行伦理”取得了统摄性的地位,虚化了德育之“法”的权威。德育之“法”的固化逐渐让步于自发抽象的“伦理规范”,企望于受教育者自发地产生道德观念,从而实现“至善”的社会,这一美好愿望在现实中必然遭遇个人利益至上的碾压。
定义8 称A(ti+v-1)TA(ti+v)A(ti+v)=A′(ti+v)为变换φi下,关于A(ti+v)的v次传导过程元.
二、德育情理法的困境探析
道德教育,追寻完善的人格,推动人向至善方向前进,不仅是知识的传授与获得,还要着力于全面人格的培养。正如鲁洁在《道德教育的当代论域》中所述,“在道德教育中存在着唯经济主义的扫荡、唯科学主义的僭越、极端个人主义的张狂以及价值断裂的震荡。由此形成了唯知识、唯技术、唯能力的教育,由此产生的‘生理人’、‘心理人’、‘社会人’、‘经济人’、‘知识人’等,使得人越来越不能把握好自身,使人成为自然社会链条中的一个被动环节,放弃了人之为人的人性、德行,堕落为纯粹的物性与自然性”[5]。当代中国社会,随着改革开放的凯歌高奏,人们的物质生活得到前所未有的改善,然而物质主义、功利主义扭曲了现代人的人性,随处可见思想低俗的草根、政治观念淡薄的网友、道德认知混乱的愤青、法纪意识贫瘠的狂妄之徒,更有甚者,屡屡打破道德底线,竟还有活跃于公众视野中的明星大腕。或许,大众对于这些现象已经司空见惯,但是这些现象所蕴含的道德危机冲击着道德文化与道德教育本身,不断滑向德育“情理法”体系的错位与背离。
(一)德育之“法”与“情理”的背离
2.无“情理”的道德理想产生德育的“乌托邦”
情理法观念在生活、法律和道德领域中的运转无处不在,从中华族群特有的“伦理理性”的文化基因看,理想境界是情、理、法的有机融合,既顺应“天理”“人情”又符合“国法”[1]。然而,现实的境况往往无法达到这样一种完美的境界,我们不断地听到各种由于无法实现“合情、合理、合法”而产生的困境甚至悲剧。学生作弊被发现向监考老师求情,由于各种需要向老师索要高分,甚至出现学生因论文答辩没通过而跳楼自杀的极端事件。从“法”的意义上讲,学校为严肃考风考纪对作弊学生进行严格处分,导师为了提升教学质量对成绩和论文水平严格把关;从“情理”角度看,学生在面临强制规范时,希望老师“高抬贵手”“从轻发落”,“情理”总是渴望体谅与变通,“法”则表明无法宽容和放任。当两者冲突时,在实践中往往通过对“法”的变通来满足“情理”的需求,而这种无限的体谅和变通又带来了新的难题,那就是如果“法”不断地为“情理”的需要而变通,是否违背其本身的价值取向,从而造成“情理”对“法”的僭越,或者强制的法理损害教育本质。
唯知识化的德育之“法”与生活的剥离,导致德育丧失生活的意蕴,成为“无人”的教化。鲁洁指出,“道德教育之知本是一种实践之知,当代的道德教育却以普遍化、客体化的知识割断了与生活、实践的联系,走上了唯知识化道路,从而根本上背离了道德和德育的本性,是德育的自我放逐、自我消解”[7]。德育之“法”来源于产生德育“情理”的生活之中,离开人的生活,德育之“法”将成为自在之物,无处安放,成为毫无意义的权威和徒劳的教化。唯知识化的德育之“法”,使德育远离实际生活世界,各种唯知识化的量化方法和具有强制力的“规范伦理”造成了德育对人的精神的束缚,形成对德育伦理和生活的压倒性统摄。唯知识化的德育之“法”与生活的剥离,实际上是与道德“情理”的背离,最终导致个体理性自觉被消解,使德育仅仅停留在知识层面,丧失了德育的生活意义。
何为德育之“理”?“理”的第一个层次指的是“天理”,即“天道”,指向人与社会需遵循的伦理基础和基本规律。在中国传统的情理法观念中,“理”居于“法”“情”之上,在中国封建社会,孔孟儒道倡导“三纲五常”“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要“克己复礼”,以“礼”治国。儒学的“礼”即“理”,成为对人们实行精神、道德教化的正统权威,这种“天理”是高于“人情”和“国法”的道德追寻。除此之外,“天理”也指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一般规律,即事物之间本质的必然的联系,从这个意义上说,“理”本身具备法则意义,属于一种自然法范畴。“理”的第二个层次是指被社会共同认可和遵循的行为规范,即“公理”。在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中形成的共同规则、习惯、传统等内容,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公序良俗”,由此形成了中国传统的道德体系。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明确指出,“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2],统治阶级为了保证自己的思想占统治地位,也要像进行物质的生产分配一样,进行“思想的生产和分配”。因此,“理”的第三个层次指一种代表某一群体利益的公共道德。从社会意识形态角度看,公共道德是社会关系的产物,在阶级社会中带有鲜明的阶级性,即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封建社会的道德遵循孔孟儒道的“三纲五常”,由此教化人心,目的是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的绝对权威。在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下,德育必然要代表人民群众的利益,这一根本准则是调节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利益关系的尺度和规范。在德育的实践中,德育之“理”对于约束人的心理和行为起着上限道德的作用,它的后两层概念与“情”息息相关,故有“情理”之说。
2) 对标《办法》中船长尺度情况,统计至2016年底,在京杭运河航行且船长>45 m的江苏、浙江、山东籍船舶共计18 130艘(见图1,根据各省交通部门提供数据整理),可知各地已全面突破《办法》中三级航段单船总长≤45 m的要求。此外,船舶大型化态势明显,三省船长>65 m的船舶保有量共计2 184艘,也已然难以满足《办法》中二级航段单船总长≤67.6 m的要求。[2]
肉鸡生长过程中常见的病害都是通过病毒、细菌、真菌等病原体进行繁殖和传播,这些病原体大多喜欢温度和湿度较高的环境,若养殖场中保持高温、高湿度、通风不畅,病原体会大量滋生,对肉鸡进行传播,导致肉鸡患病;且肉鸡养殖场内的肉鸡数量多以万计数,每天排泄出的粪便重量上吨,若不能及时清理和消毒,粪便中存在的病菌也容易在温湿度适宜的环境中大面积繁殖,对周围肉鸡进行传染,或污染饲料,导致肉鸡患病。
(二)“情理”对德育之“法”的僭越
古希腊怀疑论学者皮浪指出,“人们行为的善恶、美丑、正邪等都没有确定的区别,绝不可能有任何合理的理由,使人去选择某一种行为而不选另一种”。道德相对主义以这种相对主义哲学认识论、方法论和个性自由等理论为基础[8],否定道德判断的理性原则,使个体的“情”凌驾于“法”“理”之上,强调道德行为是相对的,道德行为具有个别性、特殊性和偶然性。个体之“情”的超越,使得个人如何应付环境,如何“方便”“有用”,成为道德判断的标准。否定客观的、普遍的、统一的价值准则即德育之“法”的规定性,营造出似是而非,使人无所适从的道德规范和道德标准。由此产生的道德信仰缺失、道德权威沦丧,道德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割裂,在个体“情、理”之中把变化的行为状况与不变的道德责任混为一谈,则必然会消解人们对主流价值观的认同感。同样,以自我为中心的道德观标榜个人利益,以个体“情理”的至上性,同样虚化了道德的客观标准。在欲望面前,个人利益成为价值判断的绝对标准,道德底线变成了对我而言是否有用、对我而言是否有利的个人判断。道德一旦走向自我的极端,个人的“情理”超越群体利益,则必然导致德育“情理”的土崩瓦解,最终导致道德滑入虚无的深渊,德育之“法”失效。
除此之外,如何理解理、法、情的轻重关系,如何排列和取舍,这些都渗透到中国传统道德文化对这些看似矛盾的概念的深层理解和融合过程中。从传统的“援法断罪”“执法原情”“人情大于王法”“王法本乎人情”等观念中可知,在中国人看来,第一位的应该是“合理”,顺应“天理”,而“和情”次之,最后是“合法”。在处理交往关系和维持社会秩序中,中国人往往以“理”为根本,以“情”为基础,“法”排在中国人思维的最后。范忠信指出:“中国人的法观念是一个复合的、多元的观念体系。一说到法,中国人很自然地把它看成是‘法上之法’(‘天理’、‘礼’)、‘法中之法’(律条、律例)、‘法外之法’(伦理之情、人之长情)的总和。”[4]“理”作为“法上之法”,“法”作为“法中之法”,“情”则是“法外之法”,这种情理法的逻辑体系根植于中国人的道德文化样态之中。作为一种形而上的探求,“情”“理”是“法”之本源,德育之“法”来源于德育的实践,这促成了德育之“法”的产生,也推动了人们对德育之“法”的掌握。
德育之“法”基于德育之“情理”,然而德育之“情理”不能超越现实成为抽象的概念,“天理”“公理”“人情”“人性”不能超越德育之“法”的规定性。在中国历史上,虽然强调三者的融通,遵循于情、于理、于法的价值判断,但任何情况下却没有个别情节、个人特权可以对“法”进行变通。“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法”的权威性不容置疑。将道德判断主观化、道德选择情感化、道德权威模糊化,皆是对德育之“法”的否定。
阅读对学习语言有很好的促进作用,纵观语言学得比较好的人,基本都是喜欢阅读的人。好的阅读习惯能让阅读者查找到文本中的“蛛丝马迹”,理解其中的细节,从而提升对文章的理解能力,这对高职学生的英语能力提升是显而易见的。阅读根据读者的喜好等可以分为默读、略读、精读等,不管采用何种阅读方式,只要用心积累总会呈现“聚沙成塔”的结局。
(三)德育之“情、理”的缺失
1.德育“情理”的缺失造成道德冷漠
当前,“扶老奶奶反被讹”的道德怪相,演变为“见死不救”“见危不助”的道德落寞,最终使公众丧失公共的道德情怀,引发人性的慌乱,这显然不是德育之“法”可以解决的问题。寄期望于依靠单纯的道德法则的强制性就能使人产生“至善”行为,这种预设在现实中必然遭遇尴尬的局面。
德育之“法”的目的在于使主体能够“知善”“向善”,而能否真正实现主体“行善”,则受制于主体对于道德知识的情感体验和在此基础之上产生的道德需要。德育之“情理”的目的就在于让主体对道德知识产生认同感、责任感,由此衍生出对道德价值的正确判断,实现自我人格的提升。但在德育实践中,由于受教育者对道德知识缺乏情感体验,使得个体对于他人的道德需要毫无反应,心理上产生道德推卸意识,造成一系列道德冷漠问题[9]。道德行为的产生与特定的情境及主体意识有关,这是德育实践中不可忽视的“情理”因素。个体在面临道德考验和判断时,势必会对道德责任和自身的各种利益作权衡,这一权衡过程需要德育的干预和引领,从而使受教育者充分理解自己的社会责任和角色。作为引领和干预的德育之“法”与社会责任和角色的德育之“情理”必须协调共生、同向同行,从而实现受教育者将道德要求和责任内化于心,并外化于行。
教育对于制度化和知识化的追寻,导致科学性的无度张扬。道德教育同样高扬科学主义的旗帜,在客观化与实证化的科学道路上阔步前行,德育因此具备了科学的名分,成为科学化发展大军中的一员。德育之“法”在科学的“犒赏”之下,有了系统的路径和不断细化的方法论体系。然而,“法”的实效性基于思路和理论基础的正确性,如果思路和理论出了偏差,“法”则沦为徒劳的甚至是障眼的附庸物。西方人学理论家恩斯特·卡西尔指出:“要认识人,除了去了解人的生活和行为以外,就没有什么其他途径了。”[6]人的道德生活的丰富性,人的具体性都使德育无法成为一种独立于“情理”而存在的实证主义和客观主义所推崇的“法”。
在中国传统德育体系中,强调对个体的约束,“克己复礼”“存天理灭人欲”等观念类似于禁欲主义的道德价值取向,通过对个体的压制来服从德育之“法”。这种高高在上的先在性道德设计使微小的个体在面对宏大的道德权威时,显得无所适从,无法找到独立于此的个体存在意义,以及个体选择的尊严。传统的德育企图通过“人皆可以为尧舜”“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德假设并强加于个体,目标是塑造不关乎于个性和人性的“圣贤”和“圣人”。这种脱离生活、远离实际的道德理想,使德育背离了“情理”的界限,最终导致了德育的“乌托邦”。知识是具有实践性的,脱离了实践性的知识毫无意义,道德知识同样需要实践,脱离生活实际的德育目标,剥离了德育的“情理”因素,即便通过德育之“法”的强制化灌输,也无法将“德”变为“德行”。
3.德育工具理性的趋向与个体“情理”的缺失造成德育实践的异化
唯工具化的德育之“法”注重工具理性的实效性,在不断系统化、科学化的道德体系中,将人视为待组装的机器,通过程序化的道德知识的装配来启动这一机器,并试图让机器按照预先设定的道德规范运作。这种无视个体情感的德育之“法”,忽视了德育之“情理”,把德育的社会功能无限夸大,造成对人的主观理想化的建构,从而使德育之“法”脱离了德育之“情理”,彻底沦为对个体的压制和约束,甚至使双方形成对立关系,导致德育成为外在化的工具。这种外在化的德育造成了德育实践的异化,使德育之“法”片面地成为一种约束和规范,不仅丧失其教育功能和生活意义,而且造成社会或某些群体,以道德的名义对某些个体行为给予过分的要求和苛责。这就是当前泛滥的“道德绑架”——以自我高尚的道德作为假设,用所谓的道德砝码对个体进行要挟,把道德通过舆论压力强制化到每一个体。道德从个体情感的诉求演变为外在的必须履行的行为规范,由此走向彻底无私的极端。道德教育演变为“道德绑架”,这种德育实践的异化,源于德育之“情理”的缺失。德育崇尚的是人的价值的完善,而不该是对人性的扼杀,德育之“情理”乃德育之根脉所在。
三、对策与思考
中国传统情理法观念历来注重“情”“理”“法”的整体性视角,其三位一体的纵横脉络孕育出了中华文明所特有的气象与格局。正如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批判蒲鲁东的二元对立割裂,以及消灭对立面的观点时指出,辩证法中矛盾双方“对立面互相均衡,互相中和,互相抵消。这两个彼此矛盾的思想的融合,就形成一个新的思想,即他们的合题”[10],可见,马克思认为矛盾的双方重在合,而不在分,矛盾双方在对立和斗争中通过自我扬弃而实现“融合”之道,德育“情理法”冲突的破解之道也基于此。如何克服德育“情理法”的错位与背离?出路不是相互的抵消和博弈,而是需要找到一种能够促成三者有效结合的德育“情理法”观念。以理为本、以法为界、以情为准,回归人的“人性”对现实的人给予完整的关注,对生存之理给予足够的尊重,破除任何形式对道德权威的亵渎,在阐释和理解德育“情理法”的逻辑与意义中为德育提供合理的价值理念,从而实现“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
以理为本。德育通于之“理”要通于“天理”,中国古代社会强调“天人合一”的思想,每个人的生活都离不开整个人类的生存环境,离不开人类社会。从人类的整体性出发,道德具有共享性的社会功能,德育以“理”为本,则必然无法回避个体对所属共同体的归属教育,国家、社会、集体、他人皆是不可回避的因素。通于之理的德育,属于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公共道德情感,超越自我与他人、自我与社会的界限,实现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统一,从而解决人与人之间的信任问题、人与社会的冲突、人与自然环境间的矛盾。
德育通于之“理”,还要通于真实主体的价值预设,消除宏大的伦理价值对个体的束缚。要对真实的具体的人给予足够的关注,德育的出发点不是人们所说的、所设想的目标,而是德育的主体,即人和人的世界。从人的现实生活中去理解人的道德,在人与人的关系中塑造人的德性,避免主观构建的道德预设遮蔽人的情感和理智的决定,让人能够直面生活本身,在理智判断中实现道德自明,提升人对于道德的领悟、体验和践行的能力。从而使个体成为独立、自主、自觉的德行主体,更好地追求现实的有德性的生活,实现“立德”的目标。
以法为界。德育之“法”的树立与实施,目的在于谋求一种具有社会共识的规范和原则,并通过系统化、规范化、强制化的制度体系实现德育目标。尽管道德行为具有个别性、偶然性和特殊性,但道德法则必须有固定的标准,个体道德选择的多样性并不意味着正当普遍的道德原则的缺失。伦理学领域的“金规则”概念、哲学领域的“道德底线主义”都从不同角度阐明了这一标准的有效性和正当性。这种有效性和正当性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人是理性的存在物,在根据自己的需要和情境进行道德判断时,具备一种理性选择的能力,不同的人的道德判断同样存在着共同的理性,这种共同的理性隐含着普遍的道德价值的存在。其次,当个体在接受道德观念时,普遍道德原则对于道德教育具有重要的意义。个体在道德的自我构建中,对道德规范实行主体自身的理解与内化,在这个具有主体性创造的过程中,道德规范具有意志规约的作用,成为个体选择的依据。最后,系统化的德育模式对于德育目标的实现至关重要。就德育的过程而言,德育之“法”,是必不可少的制度化和程序化的过程,是事物性质和状态发生根本性变化的保证。德育需要必要的道德灌输,需要科学完善的制度体系。因此,德育之“法”要尽可能符合和反映社会的一般道德观念和道德认知,并通过“法”的固化和强化作用来矫正社会道德观念中与道德标准不相吻合的内容,使其摆脱社会舆论的影响和绑架,防止相对主义、个人主义通过所谓的“情理”演化为社会舆论,并以社会舆论的形式对德育规范和标准的僭越。
以情为准。在传统德育实践中,德育之“理”为德育提供了具有超越性的价值理念,德育之“法”使这种主观构建对人的理念世界进行逻辑重建,体现“公理”“天理”“社会伦理”的统一道德规范通过系统化、科学化的方式固化个体的道德知识和道德行为,这属于一种从外向内的规训方式,效果往往不尽如人意。其根源是对人作了抽象性的理解,将人从其生活的世界中剥离,忽视了人在德育中的情感体验。然而,道德教育是主体欲望和向善要求得以实现的情感体验过程,这种道德情感能否产生,是德育成功与否的标志。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提倡德育要“以情为准”,德育不能离开现实的人而存在,人的物质需求、人际交往需求、精神层次需求都是具体的人的根本属性,也是德育之“情”的根源所在。
在当代中国社会,生存与发展权利的维护、人生秩序的安排,是当代中国民众所处的社会现实“情境”,“人性”“人的价值取向”“人的利益”等德育主体的自我指向是德育不可回避的重要内容。这就要求德育必须关注人生问题,解决现实困境,实现事实与规则的融合,从而达成“和谐”的“情理法”设计,摒弃传统德育对于人性的无限压制,形成一种具有人性关怀、充满情感活力的德育模式。这种以“情”为准的德育,体现的是对具体的人的完整性的理解,对人的情感及理智的尊重,对人的现实要求的关注,以及对人的精神世界的解放,从而使道德具有内化于心的动力,德育也因此而获得鲜活的生命意蕴。
探究德育的情理法困境,破除德育之“法”与“情理”的背离,避免德育“情理”的缺失或者走向极端,需要从德育“情理法”的融合中建立“知情意行”的整合德育观。以理为本、以法为界、以情为准的德育是一种尊重人、理解人、发展人的德育观,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人本思想的体现。马克思认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1]。因此,德育不能离开人和人的社会关系而独立存在,德育的主体是人,德育“情理法”融合的关键也在于人。破解德育“情理法”困境,必须基于对人的理解和尊重,通过关注人本身及其生活的现实世界,并赋予德育理解、宽容的人性关怀和科学、合理的机制,才能在单个人与他人和社会的分化中,形成独立人格,并使单个人深入地契合他人与社会,从而实现德育“情理”与“法”的同化和统一。“情”“理”“法”的融合生长是德育不断发展和突破的必由之路,大学德育担负着“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协调德育“情”“理”“法”三者的关系任重而道远。
上官星雨小心翼翼地唱,她有着天籁一般的好嗓子,李离听着,不由得上前一步,将她空出来的左手拉起来。这个可怜的姑娘,她的姓氏,会给她带来才华天分,也会带来血光剑影吧,谁知道,她在逃出长安之前,经受过多少孤单与恐惧。她歌声甫歇,余音缠绕在山洞里,久久不散,等最后一丝歌声消失掉的时候,她手中的火把也烧到了尽头,李离赶紧松开她的手,将自己灭掉的火把又重新点燃起来。
【参考文献】
[1]汪习根,王康敏. 论情理法关系的理性定位[J]. 河南社会科学,2012(2): 28-32.
[2]马克思. 德意志意识形态位[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译.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1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178.
[3]列宁.列宁全集(第3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240.
[4]范忠信,郑定,詹学农. 情理法与中国人——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探微[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9.
[5]鲁洁. 道德教育的当代论域[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13.
[6](德)恩斯特·卡西尔. 人论[M]. 甘阳,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17.
[7]鲁洁. 边缘化 外在化 知识化 道德教育的现代综合征[J]. 教育研究,2005(12):11-14.
[8]曲伟杰. 道德相对主义[J]. 伦理学研究,2018(5):98-103.
[9]陈伟宏. 论道德冷漠及其化解路径[J]. 哲学动态,2017(11):75-80.
[10][11]马克思.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译.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1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56.
The Dilemma of Moral Education and Its Solution
Dong Yunchuan, Wei Ling
Abstract: The fusion and growth of "emotion", "reason" and "law" is the only way for moral education to develop and make a breakthrough. "Reason" is always eager for understanding and flexibility, while "law" shows that there is no tolerance and laissez-faire. In theory and practice, moral education in university has been confronted with the problems of lack of rational law, overstepping and conflict. As a result, the practice of moral education is alienated, and the shaping of human beings becomes the suppression of human nature. It becomes difficult for moral education to achieve the goal of the internalization of individual emotional experience, thus making moral education lose its original significance and the moral goal slide into nothingness. In order to overcome the dilemma of moral education, we need to explore the integration of the three methods on the basis of its accurate exposition and orientation, and to establish a view of integrated moral education which is based on reason, limited by law and judged by emotion.
Key words: moral education; rational method;emotion; reason; law
【中图分类号】 G647
【文章编号】 1003-8418(2019)07-0055-07
【文献标识码】 A
【DOI】 10.13236/j.cnki.jshe.2019.07.008
【作者简介】 董云川(1963—),男,云南云龙人,云南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韦玲(1982—),女,云南普洱人,云南师范大学副教授,云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
(责任编辑 曹连观 朱旗)
标签:德育论文; 情论文; 理论文; 法论文; 云南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论文; 云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