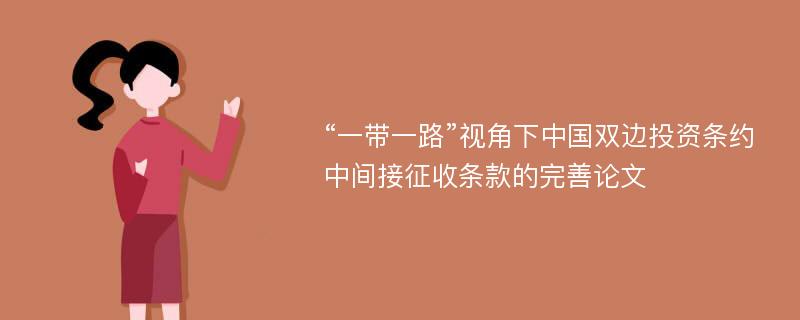
国际经贸
“一带一路 ”视角下中国双边投资 条约中间接征收条款的完善
谷望舒*
摘 要 :中国当前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签订的投资保护条约对于间接征收的概念和标准并没有明确界定,间接征收的补偿标准也并不完善,一些BIT中有关间接征收的仲裁管辖条款与我国加入《华盛顿公约》时做出的通知存在矛盾。上述这些问题一方面导致间接征收的认定存在一定的困难,另一方面一旦发生间接征收,即使申请仲裁,中国海外投资者仍将承担败诉风险。在此背景下,明确间接征收定义及间接征收仲裁管辖范围,并从平衡东道国与投资者利益角度进一步升级中国“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双边投资条约,对于保护中国海外投资者利益,促进海外投资往来具有一定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关 键 词 :一带一路;间接征收;投资仲裁;双边投资条约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历经5年的深入推进,已经成为了中国与沿线国家重要的国际合作平台,尤其是在国际投资领域,依托“一带一路”平台,中国已经实现了对相关国家和地区直接投资连续五年的快速增长,对外投资在世界范围内取得了亮眼成绩。然而随着中国企业不断地“走出去”,中国投资者面临的各种投资风险也在逐步攀升,尤其是来自东道国方面的政治风险。其中,间接征收是中国海外投资面临的最主要的政治风险之一,学理上的间接征收是指“东道国政府从法律上虽未取得外国投资者的所有权,但采取的措施影响或阻碍了外国投资者有效控制、使用或处分其资产,例如,强制转让经营权、强制国有化、不适当地大幅度提高税率、强制股权转让等。此类措施也称为事实上的征收、逐渐征收、间接征收”[注] 曾华群:《国际投资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447页。 实践中,各个国家大多会选择与东道国签订双边、多边投资协议或通过自由贸易协定(FTAs)来为本国海外投资者提供保护,一旦东道国(属于协议缔约方)违反协议项下义务,投资者就有权提起国际仲裁,仲裁庭则主要依据各方签订的投资保护协定等条约进行认定是否构成间接征收,以及解决间接征收的补偿问题。然而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签订的双边投资协定(下文称“BIT”)或自由贸易协定中对于间接征收的认定、例外规定、赔偿标准等问题规定得并不明确,一旦发生间接征收,即使提交到仲裁庭也很难认定存在间接征收并获得补偿,最终将使得海外投资者的经济利益和法律权益都无法得到有效保障。鉴于此,本文将通过梳理中国与沿线国家之间签订的BIT文本以及当前BIT中间接征收条款存在的问题,结合“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发展情况,探索完善中国投资协定中间接征收条款与规则的路径。
《理化检验-化学分册》(ISSN 1001-4020,CODEN编码LJHFE2,CN 31-1337/TB)杂志创刊于1963年,系由上海材料研究所与机械工程学会理化检验分会联合主办的技术类期刊。主要报道化学分析与仪器分析专业领域中的新方法、新技术、新设备以及国内外的研究方向。“面向生产、注重实用、反映动向、兼顾普及”是刊物的编辑方针,旨在最大幅度地满足不同层次读者的需要。涉及的领域为机械、冶金、石油化工、环境科学和生命科学等。主要栏目有“试验与研究”、“工作简报”、“知识与经验”、“综述”、“专题讲座”和“信息与动态”等。
一、“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目前面临的间接征收风险
根据2018年9月发布的《2017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显示,2017年,中国境内投资者共对“一带一路”沿线的57个国家近3000家境外企业进行了直接投资,涉及国民经济17个行业大类,当年累计投资201.7亿美元,同比增长 31.5%,占同期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的12.7%,主要投向新加坡、哈萨克斯坦、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俄罗斯、老挝、泰国、 越南、柬埔寨、巴基斯坦、阿联酋等国家。近五年中国对沿线国家累计直接投资807.3亿美元。[注]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国家外汇管理局:《2017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中国统计出版社2018年版,第15页。实际上统计公报表上一共对“一带一路”沿线的63个主要投资流向国家进行了统计(下文也将针对上述国家与我国签订的BIT文本进行梳理),但其中巴勒斯坦、波黑、黎巴嫩、立陶宛、摩尔多瓦、马其顿6个国家2017年没有投资流量显示,即2017年中国境内投资者共对“一带一路”沿线的57个国家进行了直接投资。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除东欧外,绝大多数国家或地区处于经济转轨的过程中,有些国家内部政局不稳,政治体制矛盾重重,内部公务腐败横行,这些客观环境都增加了海外投资的风险隐患。
马修·阿诺德的一生注定要和整个世界联系在一起。他在世界文学史上的地位独特。一般来说,作家、思想家及哲学家都是去世后才被人们冠以“经典”称号,而他则不同,他是“唯一在世时就成为经典的英国人”[1]。其作品在去世前就引起各界广泛关注,无论学术界还是各类媒体都投以关注的目光——无论是支持还是反对。他的思想体系不仅传承了英国的精华部分,还体现出世界主义的理念:法国的圣伯夫、德国的歌德、俄国的托尔斯泰无一例外地出现在他的文学批评作品中。他两度赴美所作的系列演讲更使他和美国文化有机地联系在一起。这些正是他的思想在日后能够走出英国,迈向世界的重要原因。
(一)“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总体投资环境
东盟十国虽然从整体上来说尚属稳定,但泰国、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等国的政局常常受到国内政治的影响,时局容易动荡。尤其是缅甸内战使得缅甸的政治不稳定因素较多,而且东盟地区还存在着最大的政治风险,也就是南海问题,这无疑也增加了该区域投资的政治风险。南亚八国中阿富汗以及印度和巴基斯坦内部政治欠稳定,不但印巴之间的关系存在着破裂的风险,中印两国之间同样存在边界问题。能源丰富的西亚和北非地区,如伊朗、伊拉克、土耳其、叙利亚、以色列、巴勒斯坦等国,国家与国家之间的领土之争、国家内部的政治权力斗争、经济动荡危机、种族与宗教冲突导致的国内政策不稳定性更是使得中国企业在外投资风险系数大大增加。[注] 商务部投资促进事务局、中国服务外包研究中心:《“一带一路”战略下的投资促进研究》2017年版,第70页。参见https://www.yidaiyilu.gov.cn/wcm.files/upload/CMSydylgw/201706/201706131116055.pdf.
1)煤岩体破裂压力与其自身性质、孔深、孔径及埋深等因素有关,通过对比发现:在没有设控制水压的模型中,第9-1步(压裂孔水压10.5 MPa)进入裂隙萌生阶段,裂隙扩展缓慢、形态发散,第12-3步(压裂孔水压12 MPa)进入失稳破坏阶段;而控制水压为4 MPa模型中,加载至第7-2步(压裂孔水压9.5 MPa)时,裂隙就开始萌生,之后裂隙迅速扩展,第10-1步(压裂孔水压11 MPa)时,就已进入失稳破坏阶段。裂隙起裂水压与控制水压呈反比关系,如图7所示。分析原因有,非对称孔隙压力场提高了控制孔的控制作用,煤体起裂水压降低,迅速进入失稳破坏阶段,压裂周期持续时间越短。
(4)不与其他课程重复原则。课程内容的组织上注意与其他课程,如“生物化学”“茶叶生化”“茶叶审评”等课程的区分,尤其是在实验内容上,通过教学大纲将这些课程(包括实验) 的内容进行规定,节约有限的学时,不重复学习内容。
由于上述很多国家正处于调整、变革、发展的关键时期,因此中国投资者相关国家政治影响相对较大,其中最常见的政治风险之一便是间接征收。国内外政治不稳定的东道国一般会以限制汇款、禁止解雇、不批准原材料的进出口、对外国投资者强加歧视待遇、改变对外资的基本政策、价格管制、强制进行国产化、外国人雇佣限制等,对投资者实施隐蔽的间接征收。而中国对这些国家地区投资涉及的领域多集中在能源资源及交通运输行业,能源、矿产与交通运输等行业具有投资周期较长、股东投资巨大等特性,投资周期较长不但增加了项目在建设、运营期间遭遇间接征收事件的不确定性,而且投资者一旦遭受间接征收,往往遭遇的经济损失巨大。除了上述政治环境相对不稳定的国家之外,随着全球经济的发展,东道国在追求经济利益的同时,环境保护意识也在不断增强,可持续发展、责任投资的理念日益发展,也往往容易在投资领域以公共利益或环境保护等理由对东道国实行间接征收,加大了中国投资者在海外投资中的风险。
(二)“北京城建公司诉也门政府案”与“首钢等公司诉蒙古政府案”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签订的投资保护协定年代较早,其中有关间接征收条款大多比较简单粗略,理论与实践中也一直没有明确统一的定义和认定标准。在“双边投资条约具有不确定性的背景下,国际投资间接征收的判例也具有同样程度的不确定性的特点”。[注] Rudolf Dolzer. THE IMPACT OF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TREATIES ONDOMESTICADMINISTRATIVE LAW[J]. NewYork University: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 Politics, 2005, 37:953-972. 这导致的结果就是即使发生了间接征收,投资者诉诸争端解决机构,也很有可能因仲裁庭对间接征收条款的认定和解释存在差异,而使中国投资者承担败诉风险。
2006年,北京城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城建”)与也门政府民航局(“也门政府”)签署也门新机场航站楼的建筑施工合同,然而开工不久后,双方便发生了摩擦和冲突,多次交涉无果后,也门政府雇佣了本国军队强行阻碍北京城建进入工程现场,最终导致我方员工被迫撤离,无法履行合同义务。2014年,北京城建公司依据《华盛顿公约》以也门政府违反1998年签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也门共和国政府关于鼓励和相互保护投资协定》(以下简称“中也BIT”)为由,将也门政府诉至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ICSID)。随后也门政府对仲裁庭提出了司法管辖权异议,三个管辖权异议之一便是认为依据中也BIT第10条第二款的规定:“缔约任何一方对有关征收补偿款额的争议提交该仲裁程序经审理”,该案并不属于征收补偿款额问题,因此北京城建公司无权单方面向仲裁庭提出仲裁。最终经过审理,仲裁庭于2017年5月31日裁定仲裁庭对本次争议拥有司法管辖权。[注] Beijing Urban Construction Group Co. Ltd. v. Republic of Yemen (ICSID Case No. ARB/14/30).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签订的BIT大部分都采取了赫尔原则作为补偿标准。然而对于进行补偿的价值问题,绝大部分BIT都规定应按照相当于“投资的价值”(或实际价值、真正价值)进行补偿,例如,中国与蒙古1991年BIT中第四条第二款规定:“二、本条第一款所述的补偿,应等于宣布征收时被征收的投资财产的价值,应是可以兑换的和自由转移的。补偿的支付不应无故迟延。”被征收财产的价值如何评估,适用什么样的标准评估,是否应当将投入的资本、折旧、已汇回的资本、更新价值和其它有关因素考虑在内条约中并没有作出进一步的规定。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签订的BIT中只有16份BIT规定的是“征收时的市场价值(公平市场价值)进行补偿”。“公平市场价值(Fair Market Value)”作为评价的标准,即指补偿的价值应当与被征收的财产价值相等,除了支付本金之外,还应当包括利息在内。仅有中国与马来西亚1988年BIT、中国与斯洛文尼亚1993年BIT、中国与阿联酋1993年BIT、中国与阿曼1995年BIT在明确相当于“市场价值”以外,还补充了“若市场价值不易确定,补偿应根据公认的估价原则和公平的原则确定,尤其应把投入的资本、折旧、已汇回的资本、更新价值和其它有关因素考虑在内”。相比之下,此种方式的补偿标准更加合理、适当和实际,从投资者母国的角度来看,更有利于保护中国投资者的利益。
在认定存在征收之后,面临的便是征收补偿问题,目前各国的投资保护协定中,对于征收的补偿问题没有区分直接征收和间接征收,默认间接征收的补偿标准与直接征收相同,且大部分发达国家都认同了“赫尔原则”也就是“充分、及时、有效”的补偿标准。这一原则是以私有财产不可侵犯为基础,以保护既得权益和反对不当得利为法律依据。从赔偿数量、支付方式及支付时间三方面要求东道国政府给予完全的、全部的赔偿。
二、中国投资保护条约中间接征收条款存在的问题
根据2018年9月商务部、国家统计局以及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的《2017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投资情况的统计, 2017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主要集中在了63个国家,[注] 参见《2017年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投资情况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国家统计、国家外汇管理局:《2017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中国统计出版社2018年版,第62页。 下文将对其中的55个与中国签订了投资保护协定的国家进行梳理,[注] 其中中国与阿富汗、巴勒斯坦、黑山、东帝汶、马尔代夫、尼泊尔、伊拉克、约旦8个国家暂无投资保护协定。 试析中国当前与“一带一路”国家签署的BITs中间接征收条款存在的问题。
(一)投资保护条约中有关间接征收的定义
当前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BITs条款中有关间接征收认定的表述分为以下三种:第一种是“征收、国有化或其他类似措施” (similar measures),如中国和沙特阿拉伯王国在1996年签订的BIT第4条规定:“一、缔约国任何一方不应对缔约国另一方投资者在其领土内的投资采取征收、国有化或其他类似措施(以下称“征收”),除非符合下列条件…”中国1991年同匈牙利签订的BIT;中国-阿尔巴尼亚1993年BIT、中国-沙特阿拉伯1996年BIT、中国-埃及1994年BIT、中国-阿塞拜疆1994年BIT、中国-爱沙尼亚1993年BIT等也都采取了这样的表述。第二种是“与国有化或征收效果相同、(effect equivalent)的措施”、“类似国有化、征收效果的其他措施”(similar effect)。如中国-阿联酋1993年签订的BIT:“一、缔约任何一国的投资者在缔约另一国领土内的投资不得被国有化、查封或没收、征收或采取与国有化或征收效果相同的措施。” 中国-白俄罗斯1993年签订的BIT:“缔约一方投资者在缔约另一方领土内的投资不得被实行国有化、强制没收或者对其采取具有类似效果的其他措施。”中国-哈萨克斯坦1992年签订的BIT:“类似国有化、征收效果的其他措施。”[注] 中国-印度2006年BIT中用了“国有化、征收或采取效用等同于国有化或征收的措施”的表述。中国-土耳其1990年签订的BIT、中国-科威特1985年签订的BIT、中国-马来西亚1988年签订的BIT、中国-捷克斯洛伐克1991年签订的BIT、中国-斯里兰卡1986年签订的BIT等采用类似表述。 总的来说,以上两种表述在本质上是没有什么区别的,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签订BIT大多都采取了这样的表述。第三种是明确对间接征收进行了界定,如中国与印度在2006年签订的BIT第一次对间接征收的含义和认定作了明确的规定。在中印BIT签署之际,双方又签署了一份议定书作为该协定的组成部分。在议定书中更加详细地列举了间接征收的情形,还提出了个案审查的方式进行认定,并列举了审查时需要考虑的各项因素。[注] 议定书的第三条中规定:“关于对第五条中征收的解释,缔约双方确认以下共识: (一)除了通过正式移转所有权或直接没收的形式进行的直接征收或国有化外,征收措施包括一方为达到使投资者的投资陷于实质上无法产生收益或不能产生回报之境地,但不涉及正式移转所有权或直接没收,而有意采取的一项或一系列措施。(二)在某一特定情形下确定一方的一项或一系列措施是否构成上述第一款所指的措施,需进行以事实为依据、各案进行的审查,并考虑包括以下在内的各因素: 1.该措施或该一系列措施的经济影响,但仅仅有一方的一项或一系列措施对于投资的经济价值有负面影响这一事实不足以推断已经发生了征收或国有化; 2.该措施在范围或适用上歧视某一方或某一投资者或某一企业的程度;3.该措施或该一系列措施违背明显、合理、以投资为依据的预期之程度;4.该措施或该一系列措施的性质和目的,是否是为了善意的公共利益目标而采取,以及在该等措施和征收目的之间是否存在合理的联系。(三)除非在个别情况下,缔约一方采取的旨在保护公共利益的非歧视的管制措施,包括根据司法机关所作的具有普遍适用效力的裁决而采取的措施,不构成间接征收或国有化。” 除此之外,2011年中国-乌兹别克斯坦签订的BIT中也明确了间接征收的定义即“效果等同于国有化或征收的措施”,规定在某一特定情形下确定缔约一方的一项或一系列措施是否构成第一款所指间接征收时,应当以事实为依据,进行逐案审查,并列举了审查时应当考虑的因素。这种方式的表述在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签订的BIT中所占比例很小,只有个别BIT对间接征收的情形详细的描述和列举。
通过对“一带一路”沿线55个国家的统计,目前采用“征收、国有化或其他类似措施”措辞的BIT共有29个。[注] 如中国-泰国1985年BIT;中国-波兰1988年BIT;中国-巴基斯坦1989年BIT;中国-匈牙利1991年BIT;中国-菲律宾1992年BIT;中国-摩尔多瓦1992年BIT;中国-越南1992年BIT;中国-阿尔巴尼亚1993年BIT;中国-爱沙尼亚1993年BIT;中国-格鲁吉亚1993年BIT;中国-克罗地亚1993年BIT;中国-老挝1993年BIT;中国-立陶宛1993年BIT;中国-斯洛文尼亚1993年BIT;中国-罗马尼亚1994年BIT;中国-埃及1994年BIT;中国-阿塞拜疆1994年BIT;中国-沙特阿拉伯1996年BIT;中国-叙利亚1996年BIT;中国-柬埔寨1996年BIT;中国-黎巴嫩1996年BIT;中国-孟加拉国1996;中国-卡塔尔1999年BIT;中国-巴林1999年BIT;中国-伊朗2000年BIT;中国-缅甸2001年BIT;中国-波黑2002年BIT中国-拉脱维亚2004年BIT;中国-俄罗斯2006年BIT。年份以签订时间为准,下同。 而采取“与国有化或征收效果相同的措施”“类似国有化、征收效果的其他措施” 措辞的BIT共有23个。[注] 如中国-科威特1985年BIT;中国-新加坡1985年BIT;中国-斯里兰卡1986年BIT;中国-马来西亚1988年BIT;中国-土耳其1990年BIT;中国-捷克与斯洛伐克 1991年BIT;中国-斯洛伐克1991年BIT(斯洛伐克承认中国与前捷斯联邦签署的BIT,并在2005年增加附加议定书)中国-蒙古1991年BIT;中国-哈萨克斯坦1992年BIT;中国-吉尔吉斯斯坦1992年BIT;中国-土库曼斯坦1992年BIT;中国-乌克兰1992年BIT;中国-亚美尼亚1992年BIT;中国-阿联酋1993年BIT;中国-白俄罗斯1993年BIT;中国-塔吉克斯坦1993年BIT;中国-印尼1994年BIT;中国-阿曼1995年BIT;中国-以色列1995年BIT;中国-南斯拉夫1995年BIT;中国-马其顿 1997年BIT;中国-也门1998年BIT;中国-文莱2000年BIT;中国-印度2006年BIT;中国-乌兹别克斯坦2011年BIT。其中中乌BIT和中印BIT分别在后面的条文中和议定书中对间接征收的认定进行了进一步阐释。 还有1个BIT在条文中并没有对间接征作出直接表述。[注] 中国-保加利亚1989年BIT第四条规定:“一、缔约国任何一方为了公共利益,可对缔约国另一方投资者在其领土内的投资采取征收或国有化。” 只有两个BIT即中国-印度2006年BIT、中国-乌兹别克斯坦2011年BIT,对间接征收的认定做了较为详细和明确的规定。可见,中国早期的投资保护协定对于间接征收的定义和认定规定绝大部分都较为模糊和简单,中国-印度2006年BIT和中国-乌兹别克斯坦2011年BIT对间接征收的认定规定较为明确,理应作为签订后续BITs的范本,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在这之后签署的数项中外投资保护协定并没有将这样的规定延续下去,如2006年签订的中国-俄罗斯BIT仿佛又回到了20世纪90年代投资保护协定的表述,不但没有明确间接征收的含义,而且继续采用了“征收、国有化或其他类似措施”这样的表述。这样简单粗疏的规定,显然是不利于间接征收的认定,也是造成间接征收认定困难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投资保护条约中有关间接征收的补偿方式
上述两个案子,都是针对中国海外投资保护极具代表性的案件,虽然两个案件的结果截然不同,但两起案件案所反映的是一个共性问题,即中国政府对外签署的投资保护协定中间接征收条款解释问题。间接征收规定的模糊性以及认定的不可预期性,必然会影响投资者对于政治风险的评价与预估,不利于双边或多边投资的推进,更使得我国海外投资者权益很难得到法律的保障。
2010年1月,黑龙江国际经济技术合作有限公司、北京首钢矿业投资有限公司、秦皇岛秦龙国际实业有限公司等三家中国公司,以蒙古国政府没收其持有的矿业许可证的行为,违反1991年签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关于鼓励和相互保护投资协定》(以下简称“中蒙BIT”)为由,请求依照《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仲裁规则》设立临时仲裁庭。2015年末,仲裁庭在荷兰海牙开庭审理了本案。2017年6月底,仲裁庭作出裁决,一致裁定对本案无管辖权。[注] Beijing Shougang Mining Investment Company Ltd, China Heilongjiang International Economic & Technical Cooperative Corp and Qinhuangdaoshi Qinlong International Industrial Co. Ltd. v. Mongolia(PCA Case No. 2010-20). 仲裁庭的理由是,依据中蒙BIT第8条第三款的规定,只有“涉及征收补偿款额的争议”才可应“任何一方的要求提交仲裁”。最终这起久拖未决的仲裁案,以中国企业的失败而告终。
此外,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签订的BIT对于征收的补偿问题,既没有区分直接征收或间接征收,也没有区分合法征收和非法征收。当前中国兼具投资者与东道国的双重身份,如站在投资者的角度来看,在中国签订的投资协定中应当将征收的补偿进行区分,按照中国学者对征收补偿种类的归纳,间接征收的补偿标准方面存在三种情况,而并非“全有”或”全无”,即认定为间接征收的补偿应采取区分制,即合法间接征收的补偿标准不应等同于非法间接征收,即便主张二者在补偿标准上相同,至少在补偿额的计算上前者应低于后者。[注] 参见徐崇利:《利益平衡与对外资间接征收的认定及补偿》,《环球法律评论》2008年第6期,第38页-39页。 同样作为东道国的中国,在实施合法合理的管制措施时,不能一概要求东道国政府对外国投资者承担全部补偿,而是应区分不同的情形给予补偿。正如中国学者所言:“在外国投资财产遭受同等损失的前提下,东道国政府行为的‘适当性’和‘必要性’如何、外国投资者合理期待受损的程度,以及东道国所要实现的社会公共利益有多大等因素,均将影响补偿额的确定”,[注] 参见前引注14,第39页。 在制定和确定征收补偿标准时,应当综合考虑以上各种因素。
如前所述,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签订的投资协定对于间接征收条款的规定十分粗略,文本中也没有相关的解释性表述。尤其像中国与也门、以色列、南斯拉夫、巴林、俄罗斯、卡塔尔、罗马尼亚、伊朗等国签订的双边投资保护协定中,对间接征收的规定更是过于简单。而上述国家的国内局势往往很不稳定,一旦发生间接征收的事实,投资条约存在的缺陷将极易导致仲裁庭对间接征收事实无法认定,中国投资者将承担着巨大经济损失风险。
(三)投资保护条约中有关间接征收的仲裁管辖权
综上,中国在未来签订或升级双边投资协定,可以参照现有的BIT条款如中印BIT议定书,或中国签订的其他投资条约或自贸协定如中加BIT、中国-日本-韩国2012年签订的投资条约议定书等的规定,通过对间接征收的定义和特征给予更加详细的描述列举更多可能引起间接征收的情形,来明确间接征收认定的标准,为仲裁庭在个案中判断是否间接征收提供更坚实的条约基础。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BIT大部分签订于20世纪,而中国早期对外签订的BIT大多对于提交ICSID中心仲裁的争议表现出了谨慎的态度,而将可仲裁的事项范围局限在了“征收补偿款额”的争议上。如前所述在仲裁实践中,对仲裁管辖条款的不同解释,直接关系到仲裁庭的管辖权能否及于间接征收事实认定问题,还是仅仅只能管辖有关间接征收补偿款额问题。因此,有必要在此基础上探讨是否应当将BIT中的仲裁管辖范围进行一定的修正。
丁未(1907年)三月,“徐淮患水,待赈甚迫。南洋学生乃合徐汇学生,假座李公祠,演剧三日,得资助赈。演《冬青树》剧,悉用古代衣冠,实开今日各剧社演历史剧之先河。顾以地处荒僻,不便交通,顾知者鲜而卖座稀”[2]56。
三、中国投资保护条约中间接征收条款的完善
(一)明确双边投资保护协定中的间接征收的规定
这一时期是蒋介石对国民党意识形态建构的重要阶段,其基本的指向是将三民主义儒学化,一定程度上放弃了对三民主义本体的解释,结合自身的观念做了新的发挥。黄道炫的研究表明,蒋介石着力建构的力行哲学是以自己崇奉的王阳明哲学为核心,但又不放弃孙中山学说的外壳,其在调和孙中山的“知难行易”说与王阳明的“致良知”方面做了很多努力,目的就是在不放弃孙中山这一理论旗帜的基础上自我树立。⑱从结果来看,蒋介石所宣扬的力行主义,实际上偏离了意识形态建构的正常逻辑,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意识形态的功能,具体表现就是不主张在党义问题上有任何理论争辩,而只强调实行主义,其中的悖论在于本体论不深究,那所谓力行的依据又从何而来?
随着间接征收行为越来越隐蔽,间接征收的认定问题也越来越复杂。在完善间接征收认定的条款时,在理论上可以参考“目的兼效果标准”。“目的兼效果标准”是指在界定东道国政府行为是否构成间接征收时,一般要考虑行为效果和目的两个方面。简言之,政府行为的效果和目的都会影响认定,通过比例原则为工具和纽带,进行个案的综合判断。可以说“在间接征收方面仲裁庭运用比例原则客观上有助于恰当地实现“效果目的化”与“目的效果化”,即以“比例”为纽带,根据目的判断效果的合理性、根据效果判断目的的正当性。它表明为保护或促进公共利益,特定政府措施并非必然会构成间接征收。在保护私人财产成为各国普遍确认的法律理念背景下这种做法应该说有其合理性可以较好地平衡东道国权力与投资者权益之间的关系。在国际投资实践中,“目的兼效果标准”也得到了越来越多的适用,例如“LG&E v.Argentina”案、“Fredin v.Sweden”案、“Tecmed”案等。[注] 参见蔡从燕、李尊然:《国际投资法上的间接征收问题》,法律出版社2015年版,第36-37页。 因此,在间接征收的条款中,可以对上述标准予以明确或以间接征收的例外情形的方式,将“目的兼效果标准”融入其中,并在仲裁实践中加以运用。
此外,在已经签订的条约中,也有一些值得参考的规定,例如中国与印度、[注] 我国与印度在签订的投资条约议定书中,对征收的解释进行了补充:(一)除了通过正式移转所有权或直接没收的形式进行的直接征收或国有化外,征收措施包括一方为达到使投资者的投资陷于实质上无法产生收益或不能产生回报之境地,但不涉及正式移转所有权或直接没收,而有意采取的一项或一系列措施。(二)在某一特定情形下确定一方的一项或一系列措施是否构成上述第一款所指的措施,需进行以事实为依据、各案进行的审查,并考虑包括以下在内的各因素: 1、该措施或该一系列措施的经济影响,但仅仅有一方的一项或一系列措施对于投资的经济价值有负面影响这一事实不足以推断已经发生了征收或国有化; 2、该措施在范围或适用上歧视某一方或某一投资者或某一企业的程度;3、该措施或该一系列措施违背明显、合理、以投资为依据的预期之程度;4、该措施或该一系列措施的性质和目的,是否是为了善意的公共利益目标而采取,以及在该等措施和征收目的之间是否存在合理的联系。(三)除非在个别情况下,缔约一方采取的旨在保护公共利益的非歧视的管制措施,包括根据司法机关所作的具有普遍适用效力的裁决而采取的措施,不构成间接征收或国有化。 加拿大签订的双边投资协定,与日本、韩国的三边投资协定中有关间接征收的规定。以中国-日本-韩国2012年签订的投资条约议定书为例,该议定书的第二条对间接征收做出了规定,较中印BIT议定书的规定,该条进一步明确了间接征收的罕见情形,相对于其他协定文本已经有很多可借鉴之处,完全可以在新签订的投资保护协定,或是投资补充协定中,参照或直接引入相关内容,完善间接征收的相关制度。正如有学者提出:“议定书2条c款规定的‘除非罕见情形,比如根据其目的,缔约一方采取的一项或一系列措施及其严厉或不成正比,否则缔约一方为正当的公共福利而采取的非歧视性管制措施不构成征收,’虽然这一条规定也没有从法律概念的角度提出识别罕见情形的全面的判断标准,而只是举例式地想了一种情形,但其提出的极其严厉或不成比例标准是有积极意义的。”[注] 蔡从燕、李尊然:《国际投资法上的间接征收问题》,法律出版社2015年版,第226页。 此外,中国与加拿大签订的BIT中的间接征收规定,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中加协定在列举认定间接征收需要考虑的因素时,采取的措辞是“包括但不限于”,[注] 中国-加拿大2012年签订的BIT在文本第二部分第十条的附录中也作了规定:“缔约双方确认如下共同理解:一、间接征收源于缔约方采取的一项或一系列措施,该等措施与直接征收具备同等效力,但没有在形式上体现为转移所有权或直接没收。二、判断缔约方一项或一系列措施是否构成间接征收,需要在事实的基础上针对个案进行调查,需要考虑的因素包括但不限于:(一)该措施或该系列措施的经济影响,虽然缔约一方的一项措施或一系列措施对投资的经济价值有负面影响这个单一事实并不表明间接征收已经发生;(二)该措施或该系列措施在何种程度上干预了作出投资的明显、合理期待;以及(三)该措施或该系列措施的性质。三、除了在极少数的情况下,例如一项措施或一系列措施从目标来看相当严重,以至于这些措施不能认为以善意方式采取和适用,则缔约方为保护公众福祉之合法公共目的,如健康、安全和环境,而设计和适用的一项或一系列非歧视性措施,不构成间接征收。” 相较于中国-印度BIT以及中国-乌兹别克斯坦BIT中列举考虑因素的措辞:“包括以下在内的各种因素”,可以看出中加的措辞更为宽松,为间接征收的认定留下了更大的空间。
目前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签订的投资条约中对于投资争议的解决方式有很多选择,包括提交缔约一方有管辖权的法院,或是设立仲裁庭,或提交国际仲裁如ICSID仲裁、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的专设仲裁庭仲裁或者在双方同意的情况下选择提交其他仲裁机构仲裁。而其中大部分BIT都规定了有关间接征收可以申请ICSID仲裁的条款。然而中国早期签订的BIT不仅对于可以提交国际仲裁管辖的争端事项存在着许多的限制,而且这样的限制还与中国在ICSID中心作出的通知存在矛盾。
(二)明确间接征收提交ICSID国际仲裁管辖的范围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大部分国家都是《华盛顿公约》的缔约国,中国于1993年批准通过了《华盛顿公约》,但这并非意味着只要双方都是《华盛顿公约》缔约国那么所有争端都应当提交ICSID仲裁,ICSID规定了只有在争议双方书面同意的情况下可以对争端进行管辖。而中国在1993 年加入《华盛顿公约》时,依据《华盛顿公约》第 25 条第一款[注] 《华盛顿公约》第 25 条第一款规定:中心的管辖适用于缔约国和另一缔约国国民之间直接因投资而产生并经双方书面同意提交给中心的任何法律争端。可见双方书面表示同意是ICSID管辖的前提条件。同时在本条的第四款又规定:“任何缔约国可以在批准、接受或核准本公约时,或在此后任何时候,把它将考虑或不考虑提交给中心管辖的一类或几类争端通知中心,秘书长应立即将此项通知转送给所有缔约国。此项通知不构成第一款所要求的同意。” 作出了通知:“中国政府仅考虑将由征收和国有化引发的有关赔偿的争议提交中心管辖.”[注] 原文为:“[P]ursuant to Article 25(4) of the Convention, the Chinese Government would only consider submitting to the jurisdic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Centre for Settlement of Investment Disputes disputes over compensation resulting from expropriation and nationalization.” See “NOTIFICATIONS CONCERNING CLASSES OF DISPUTES CONSIDERED SUITABLE OR UNSUITABLE FOR SUBMISSION TO THE CENTRE”, https://icsid.worldbank.org/en/Documents/icsiddocs/ICSID%208-Contracting%20States%20and%20Measures%20Taken%20by%20Them%20for%20the%20Purpose%20of%20the%20Convention.pdf,访问日期:2018年11月16日。 尽管这是一份说明,但此说明是具有法律拘束力的。[注] 参见沈虹:《论ICSID对涉中国投资条约仲裁的管辖权》,《法学杂志》2011年第7期,第129页。 因此,对于征收和国有化引发的有关“赔偿”的争议投资者是可以提交到中心的,这与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签订的大部分BIT中规定的有关“征收补偿款额”的争议才可以提交ICSID仲裁的规定是存在矛盾的。通过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BIT的仲裁管辖条款进行梳理,可以将其分为三类:第一类是规定仅仅有关“征收补偿款额的争议”,当事人(可以是任意一方)才可以提交仲裁庭仲裁,其他争议不可以提交国际仲裁。[注]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大部分都在与中国的BIT中规定了“如涉及征收或国有化产生的补偿款额的争议,可以由当事人将争议提交仲裁庭”或类似表述。如中国-土耳其1990年BIT;中国-克罗地亚1993年BIT;中国-格鲁吉亚1993年BIT;中国-保加利亚1989年BIT;中国-阿曼1995年BIT;中国-阿塞拜疆1994年BIT;中国-老挝1993年BIT;中国-斯洛文尼亚1993年BIT;中国-阿尔巴尼亚1993年BIT;中国-越南1992年BIT;中国-摩尔多瓦1992年BIT;中国-蒙古1991年BIT;中国-匈牙利1992年BIT;中国-爱沙尼亚1993年BIT;中国-卡塔尔1999年BIT;中国-沙特阿拉伯1996年BIT;中国-巴林1999年BIT;中国-马其顿1997年BIT;中国-叙利亚1996年BIT;中国-孟加拉国1996年BIT;中国-黎巴嫩1996年BIT;中国-柬埔寨1996年BIT;中国-以色列1995年BIT;中国-南斯拉夫1995年BIT;中国-印度尼西亚1994年BIT;中国-埃及1994年BIT;中国-白俄罗斯1993年BIT;中国-塔吉克斯坦1993年BIT;中国-亚美尼亚1992年BIT;中国-乌克兰1992年BIT;中国-吉尔吉斯斯坦1992年BIT;中国-哈萨克斯坦1992年BIT;中国-巴基斯坦1989年BIT;中国-波兰1988年BIT;中国-斯里兰卡1986年BIT;中国-新加坡1985年BIT;中国-科威特1985年BIT。 第二类是除了“征收补偿款额”可以提交ICSID,对于其他的投资争议,在当事双方同意的前提下也可以提交仲裁,但“征收补偿额争议”没有双方当事人同意的要求,当事人任意一方就可以提出,其他争议则需要以双方当事人同意作为将争议提交仲裁的前提。[注] 如中国-菲律宾1992年BIT第十条规定:“投资者可以将下列争议提交国际仲裁:(一)有关本协定第四条(即征收)所述的补偿额的争议和其他有关上述补偿的争议;(二)当事双方同意提交国际仲裁的有关本协定其它问题的争议。”中国-也门1998年BIT第十条规定:“缔约任何一方对有关征收补偿款额的争议提交该仲裁程序均给予不可撤销的同意,其他争议提交该程序应征得当事双方同意。”如中国-马来西亚1988年BIT;中国-菲律宾1992年BIT;中国与-捷克和中国与斯洛伐克1991年BIT;中国-菲律宾1992年BIT;中国-立陶宛1993年BIT;中国-阿联酋1993年BIT;中国-也门1998年BIT。 第三类是将ICSID管辖范围扩展到投资者与东道国所有的投资纠纷上,不再只局限于“征收补偿款额”的投资争端。而签订这类BIT的国家数量很少,仅仅只有中国与罗马尼亚1994年签订的BIT、与文莱2000年签订的BIT、与缅甸2001年签订的BIT、与拉脱维亚2004年签订的BIT、与俄罗斯2006年签订的BIT、与印度2006年签订的BIT、与乌兹别克斯坦2011年签订的BIT中开放了ICSID对于投资争议的管辖范围,也就是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签订的大部分BIT仍然将提交国际仲裁管辖的范围局限在了“征收补偿款额”问题上,这实际上并不利于中国投资者的利益保护,因为在间接征收事实发生之后,一旦投资者诉之国际仲裁,那么间接征收的认定问题是否属于仲裁管辖范围之内,便存在着条款解释上的风险,例如间接征收的认定问题是否属于征收款额争议、是否可以提交ICSID,每一个仲裁庭的解读是不一样的,如前文所述的黑龙江国际经济技术合作有限公司、北京首钢矿业投资有限公司、秦皇岛秦龙国际实业有限公司等诉蒙古国政府案,最终仲裁庭仲裁的结果就是依据中蒙BIT第8条第三款的规定,只有“涉及征收补偿款额的争议”才可提交仲裁,而认定对该案无管辖权的。同样,仲裁庭对间接征收认定的管辖权问题也是“北京城建诉也门政府”案争议的焦点之一,幸运的是在本案中,仲裁庭对条约的解释将案件纳入了仲裁庭的管辖范围,但是这样的一份仲裁结果似乎不能成为先例并保证被后续的仲裁庭遵循,因此,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BIT条款仍急需解决上述规定之间的矛盾。
首先,应当解决的是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签订的BIT中有关提交ICSDI中心仲裁的争端事项与中国在ICSID中心作出的通知声明之间的矛盾。如前文所述的北京城建公司诉也门案中,仲裁庭裁决书将中国-也门双边投资保护条约与中国-俄罗斯双边投资保护条约中对于中国投资的保护做了对比,而中国与俄罗斯以及20世纪90年代签订的大部分双边投资保护条约中都采取的是也门政府主张的观点。可以预见,如果中国的投资者在俄罗斯或上述其他国家投资的过程中遭遇了间接征收,在诉诸ICSID时同样容易面临着东道国提出管辖权异议的风险。因此,在未来签订或升级完善投资保护协定时,应当明确中国考虑将“国有化和间接征收问题”提交中心管辖的意思表示,同时可以以补充议定书的方式与中国向ICSID中心提交的通知声明保持一致,避免发生争议后仲裁庭对BIT中管辖权条款作出限缩性解释。
此外,中国与很少一部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签订的BIT采用了“一缔约国投资者与另一缔约国之间的任何争议”或“与投资相关的任何争议”这样的措辞,因此将仲裁范围扩大到任何有关投资的争议(如2005年中国与捷克 BIT第九条、2004年中国与拉脱维亚签订的BIT第九条、2006年中国与俄罗斯签订的BIT第九条、2006年中国与印度签订的BIT第九条等)。对于这样的扩张,中国学者大多持谨慎态度,建议中国在促进海外投资过程中需要兼顾中国作为东道国的利益,不宜完全放开对仲裁管辖权接受范围的限制。[注] 参见魏艳茹:《论中国晚近全盘接受ICSID仲裁管辖权之欠妥》,《国际经济法学刊》2006年第1期,第135页。 一些学者还担心“贸然全面不加限制地接受ICSID仲裁管辖权不仅会极大地限制国家经济主权,束缚东道国对经济调控能力,而且还与中国在批准《1965年华盛顿公约》时接收管辖的投资争端是有限的通知声明相冲突,最惠国待遇条款的适用范围也存在着被扩大化的风险”。[注] 秦红嫚:《中国全面接受ICSID仲裁管辖权的思考》,《商事仲裁》2016年第1期,第68-69页。 一方面是中国投资者在海外的利益,一方面是中国同样作为东道国身份也面临着本国行使国家管制的权利。两者利益如何平衡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笔者认为,“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企业越来越多的走出去,全盘接受仲裁管辖权虽然从一定程度上是有利于保护中国的海外投资者利益但也如其他学者所言的确也存在一定的风险。因此,在现阶段中国应当结合“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具体情况以及投资环境做出综合的评估,对于早期签订的与ICSID仲裁管辖存在矛盾的条款作出适当调整,可以在后续签订的投资条约中或是投资条约议定书中作出规定,使之与中国在批准《1965年华盛顿公约》时作出的通知声明保持一致,将仲裁管辖范围限定在“国有化和有征收的争议”。这样既有利于消除仲裁庭在仲裁管辖权解释上存在的不确定性,保护中国投资者在海外的利益,同时又可以避免全盘接受中心管辖带来的主权风险。
(三)重视外国投资者与东道国利益的平衡
随着经济全球化以及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中国目前已经完成了从纯粹的资本输入国向资本输出国和资本输入国的双重身份转变。因间接征收引发的国际投资争端的增加以及国际投资仲裁实践中漠视公共利益的反思,也凸显了现行国际投资条约法对公共利益保护之不足,以及公益化革新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一方面,中国作为投资者母国,应当高度重视平衡中国投资者利益与东道国社会公共利益的发展趋势,根据“一带一路”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情况,逐步调整立场定位,对现有的双边投资协定中的间接征收规则进行升级完善,突出保护投资者海外利益的需要。另一方面,中国在2017年已成为“外国直接投资流入量”排名仅次于美国位列第二的东道经济体,中国作为投资东道国的身份也不应当忽视。因此,在制定对外投资条约和间接征收相关条款时,应当在投资保护协定中进一步细化构成间接征收的例外规定,增加保护东道国环境、可持续发展等保护公共利益的内容,体现保护东道国的利益和需求。
中国自20世纪八十年代初开始对外商签订BIT,目前与“一带一路”54个沿线国家签署的BIT中大多数是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签订的,这一时期中国主要从资本输入国立场出发,缔结的BIT内容较为保守与谨慎,提供的投资保护程度相对较低。因此,从保护投资者角度看,当前中国在积极与更多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商签BIT的同时,还应注重“升级”已有BIT。当年与这些国家签订水平较低的投资协定毕竟受到了时代条件的限制,如今在新的时代环境下中国应当争取与这些国家重新达成高标准的投资协定。实际上与一些国家也的确存在直接缔结高水平投资协定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完全可以通过重新签订双边投资协定或签订投资议定书的方式实现。有学者提出“一些国家目前暂无直接升级高水平投资协定的路径,如果能够一步到位当然最好,如果不能,那2011年中国与乌兹别克斯坦双边投资协定或许可以作为过渡的模板,该协定整体上与中国此前的投资协定保持了一致,同时也吸收了美式投资协定的要素,具有复合性的特征,中国可以在此模板的基础上寻求增加更多促进投资自由化的内容”。[注] 朱文龙:《论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协定的变革》,《云南大学学报(法学版)》2016年第5期,第121页。 此外,中国与印度2006年签订的BIT其内容更加充分地考虑到了东道国与投资者的实际需求和特点,例如,对间接征收的定义中将“正式转移所有权或直接没收等措施”明确排除,明确将“是否存在歧视”尤其是歧视的程度确立为认定间接征收审查因素之一;还将“旨在保护公共利益的非歧视的管制措施,包括根据司法机关所作的具有普遍适用效力的裁决而采取的措施”也排除在了间接征收的范围之外,不仅使得认定标准更加重视措施的特征和目的,而且对东道国的管理权也予以了充分的肯定。[注] 参见梁咏:《中国投资者海外投资法律保障与风险防范》,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270页。 鉴于中国投资者与东道国的双重身份,在制定和升级BIT时,也应当参考中印BIT的规定,注意东道国与投资者之间的利益平衡。
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于2018年发布的《2018世界投资报告》表明,自2012年以来,已有150多个国家采取步骤,制定新一代以可持续发展为导向的国际投资协定(国际投资协定改革第一阶段)。例如,它们根据贸发会议的国际投资制度改革一揽子方案,审查了各自的条约网络并修订了条约模式。与千年之交缔结的条约形成鲜明反差的是,2017年缔结的所有条约都至少包含六项“改革特征”,而且 2010年前国际投资协定中被视为创新的一些条款现在经常出现,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与文莱在2000年签订的BIT中的关于投资促进和(或)便利化的具体积极规定也被视为是投资协定中的改革导向条款。中国还在对现有的老一代条约进行现代化(国际投资协定改革第二阶段)的过程中,应当借此改革行动之际,从整体上对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BIT文本进行升级,通过间接征收条款的完善,可以为增加中国对制定海外投资规则话语权提供更多机会。 “一带一路”沿线上目前还有尚未与中国签订投资协定的国家,中国应借此时机填补缺失的空白,补充与完善投资协定中的不足之处,尤其有关“一带一路”沿线各个国家之间的条约谈判,应当从整体上划分一定的类别,如按照中国对外投资的领域、投资额、贸易额、未来投资趋势进行有预见性的评估,在评估之后可以制定不同的范本或范本式条款内容,总之,BIT的完善与升级,将会是促进海外投资往来的重要抓手。
如图3所示,θ面上的一个单元和θ+dθ面上所对应的单元构成了一个单元体。上述两个单元上均有应力作用。假设单元节点位移向量有一个虚位移δq(θ,t),那么上述应力所对应的虚功是
四、结语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签订的投资协定中,对间接征收概念界定并不明确,认定标准也缺乏精确性,当前理论界有关“间接征收”规则和学说也处在研究的起步阶段。而目前阶段,投资条约仍然是主权国家间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的基础上达成的国际协议,在东道国对外国投资者所承担的义务方面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进一步升级和完善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的投资协定,是当前保护中国海外投资者利益,以及吸引外国投资者的重要途径。一方面,中国应当牢牢抓住“一带一路”倡议发出的时机,规范和完善中国投资协定的间接征收条款,明确间接征收的定义、征收后补偿标准以及仲裁管辖条款深入对间接征收制度的研究,这样既可以满足现阶段订立BITs实践中保护自身利益之需; 又可以在未来为间接征收国际规则的形成提供有力的国家实践。[注] 章晶:《国际投资法间接征收认定规则之嬗变——间接征收研究意义之于中国》,《上海海关学院学报》2012年第1期,第90页。 另一方面,中国应当更加重视BIT完善和升级,在考虑到中国海外投资者的利益保护的同时,又不能忽视中国作为投资东道国采取管制措施的权利。因此在升级完善投资条约中既要强调对外资的保护,又要保障东道国采取合理措施行使保护环境等公共利益的权利。中国在“一带一路”倡议的引导下,正在全世界范围内扩大投资的影响力 ,中国承担“大国担当”的同时,也应当明确中国的投资协定政策与定位,积极地参与规则的制定,勇于迎接风险的挑战。
The Improvement of the Indirect Expropriations Provisions in China 's Bilateral Investment Treat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Gu Wangshu
Abstract :The investment treaties signed between China and the countrie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do not clearly defin the concepts and standards of indirect expropriation .The compensation standards for indirect expropriation also need to be more explicit .In some BITs ,the arbitration jurisdiction clause on indirect expropriation is in contradiction with the notice made by China when it joined the Washington Convention .On the one hand ,these problems lead to great difficulties in the determination of indirect expropriation .On the other hand ,in the case of indirect expropriation ,Chinese overseas investors will still face the risk of the arbitral tribunal without jurisdic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text of bilateral investment treaties ,it is useful to study the indirect expropriation clauses in China 's bilateral investment treaties ,which is conducive to safeguarding the overseas investment interests of Chinese investors .
Keywords :the Belt and Road ;Indirect Expropriations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Arbitration ;Bilateral Investment Treaties
*作者简介 :谷望舒,华东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国际法专业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 赵世璐)
标签:一带一路论文; 间接征收论文; 投资仲裁论文; 双边投资条约论文; 华东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