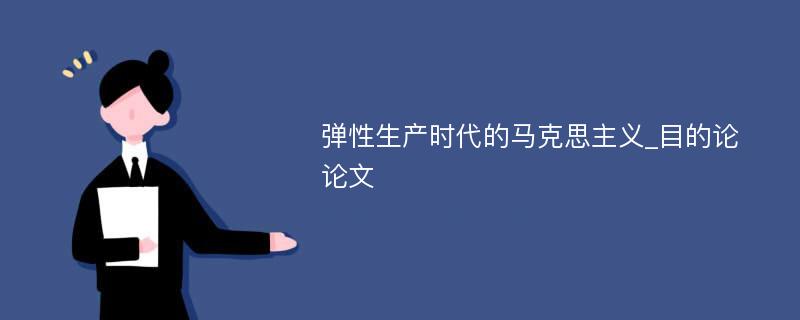
弹性生产时代的马克思主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主义论文,弹性论文,时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关于马克思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历史关系,这里简要重述一下我的几个观点:第一阶段,即19世纪,马克思把整个全球的合并假设为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他认为这既是一个破坏性的进程、也是一个进步的发展过程,因为它使那些沉睡了几个世纪的社会产生了勃勃生机。对马克思而言,所谓“世界空间”(world-space)是由欧洲资本主义经济的扩张而形成,这种经济使其势力所及的所有社会同质化(homogenize)。所谓,世界时间”(world-time)是指欧洲资本主义的时间性(temporality)。而他认为社会主义要通过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来实现,这种观点,已经预设了资本主义的普遍化(universalization)。第二阶段,从19世纪晚期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在这一阶段中,资本主义确实已成为全球化的,但不是马克思所设想的全球同质化,而是产生了新的分化。这种新的分化由两个原因引起,一是资本主义的全球化在加剧了欧洲和北美(还有日本)中心地区的民族竞争的同时,也使民族主义在全球范围内扩散开来,这种扩散引起对资本的同质化力量的抵制,二是资本主义从欧洲中心地区向外的扩张,使这些地区的资本主义的迸一步发展成为可能,但它并没有为外围地区带来普遍的发展,外围地区仍然处于不发达的状况(也就是使外国的经济沦为资本主义中心的附属物)。
第三个阶段,它从70年代起越来越得到人们的认可,这个阶段开始于资本主义的全球化初具形态的时候。这个形态虽然仍保留中心─外围形式(和相应的发达—不发达状况)——当然是以一种新的方式保留着、但它看来的确证实了马克思早在19世纪中期的预言。资本主义确实已经普遍化了,其基础不仅是商品交换和金融交易的全球化,而且最重要的是通过一种“新的国际劳动分工”而实现了生产的跨国化(transnationalization),实际上,就象沃勒斯坦(Wallerstein)等人所论述过的,生产的跨国化现在已经不是什么新东西了,因为“商品链”从一开始就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典型特征。这也许就是一些分析者试图通过类比早期资本主义的历史来理解资本主义的新形态的原因。然而这些类比走得太远,有可能被简单化,实际上资本主义新阶段与早期之间的差别是非常明显的:早期资本主义的发展使得欧洲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中心,而当代资本主义的跨国化却相反,它通过在全球范围内制造资本主义发展的新起点而使资本主义非中心化了(decentered),它结束了欧美在世界上的经济霸权,使资本主义第一次脱离了欧洲中心主义(Eurocentrism):早期资本主义的发展在全球性的同质化过程中导致了以民族为经济发展单位的格局(或者至少是与民族的经济发展相联系),而在新的阶段却相反.资本的全球化过程撕裂了民族国家的边界线,削弱了民族国家的经济主权,并使资本主义从作为发展单位的民族国家中抽离出来,新的全球性经济的最重要单位就是跨国公司(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虽然跨国公司的某些方面容易使人想起早期资本主义发展中那些大型公司(例如西印度公司),但当代跨国公司却以其实实在在的跨国性为荣,他们不带有从中发展起来的那个国家的任何特殊印记。早期公司的商业目的要求与国家和经济实体之间的合作,而新的跨国公司则意味着资本从国家和杜会中获得解脱,因而他们的活动削弱了民族国家的权力,跨国化在世界经济中取得霸权的结果是,一个全球性的专业化管理者阶级(a global professional-managerialclass)的产生,乃至一个全球性文化的产生。
有人把新的世界经济形态描写成一种“全球性的区域主义”(global regionalism)或“全球性的地方主义”(global localism),这种描述捕捉住了世界经济同质化与散裂化(fragmentation)的同时产生。生产和经济活动(从而是经济的“发展”)越来越成为国家范围内的地区性活动,而具管理却越来越需要超国家的监督和调节。换言之,资本发展的新道路穿越国家界线并侵犯国家经济主权,这使得原来那种国家市场或民族经济单位的概念变得名不符实,民族经济的破裂从内部削弱了国家主权。同样地,超国家调节的必要性改变了民族国家的功能,使之在更大的区域或全球性的范围内进行合并。那些正在走资本道路的国家和地区(或正努力使自已走上这些道路的国家和地区),在社会文化和政治上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变得越来越相似;相反,没有走上这资本道路的国家和地区,在越来越紧张的经济、政治和文化边缘化的形势下,不得不尽全力维护自己的独立性。
资本主义的跨国化也排除了将世界划分为三个世界的做法。因为第三世界的某些区域已经变成资本运作的中心,而第一世界中的某些区域已经沦到第三世界的地位上。换言之,原来那种中心---外围关系已经不再是国与国关系的主要特征,而逐渐变成走资本道路的国家和地区与被资本边缘化的国家和地区之间的全球关系:这样就造成了现在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与地方主义(localism)同时并存的悖论。这种新发展,正如它削弱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民族国家一样,也侵蚀了那些曾被预言为具有国家经济主权的社会主义国家。随着社会主义阵营的解体,世界再一次被分为两个部分,一个是实现了资产跨国化的第一世界,另一个是不发达的第三世界。原来属于第二世界的社会主义国家沦落到第三世界的地位,并正想通过资本化道路来改变现状。把世界分为南--北两部分的做法比较清晰地描绘了现阶段的资本主义,它们不仅指地理位置,而且指在世界经济局势中的位置:北方意味着走资本化的道路,南方则在此之外。
我们知道社会主义建立在两个前提上,一是国家自给自足,二是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脱钩,但这两个前提在新的环境下已经不存在了。同祥,马克思主义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甚至作为一种关于全球性现代化的理论,也已经名不符实,马克思主义在理论意义上包含了对欧洲中心资本主义的时空预设,它无法解释资本主义的新形势,因为这种新的形势既具有同质化特征又具有散裂化特征。资本主义本身已力图通过认识这种散裂化超越自身,而使用新的术语来理解世界经济的初步努力产生于非欧美资本,这也并不令人感到惊讶。但是这并不象有人宣称的那样:新的世界形势意味着现代化战胜了马克思主义,或者说在二战后作为与列宁主义相对抗而形成的现代化理论能够比马克思主义更有效地解释世界经济的发展状况,事实上,是否马克思主义在它与现代化理论相重复的地方失败了,以及作为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当社会主义按照它来谋求资本主义的生产目标时,是否就暴露出自身具有尖锐的矛盾.这些问题仍然是可以争论的。
实际上,马克思主义理论比现代化理论更能解释资本主义的空间关系。因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建立在一些对立的社会关系的基础上,这些关系为他的分析引入了一种社会空间的概念,列宁因为认识到国家与地区之间、发达与不发达之间关系的重要性而把握了资本主义的全部空间性。“世界体系”分析(world system analysis) 也明确而完整地把握了空间的重要性,这种分析虽然严格地讲不属于马克思主义范围,然而却是马克思主义分析世界的自然推论。而且,与列宁首要关注的是帝国主义条件下的资本主义关系不同,世界体系分析在沃勒斯坦和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那里已被用来解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部历史(甚至是在这之前的历史)。
由于现阶段资本主义空间关系的重要性,世界系统分析在解释当前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形态时非常恰当。在我看来,为了完成这一任务,马克思的理论必须与另外两种目的论区分开来:关于资本主义时间性的目的论和资本主义自身概念的目的论,换言之,那些分析概念(例如“阶级”)必须在具体的社会存在中加以实现。上述讨论也清楚地表明,民族国家不再是有效的分析单位(在分析资本的动作时),世界系统分析一开始就已经认识到了这一点,但它在贬低经济结构的政治重要性时却显得太偏激了。
沃勒斯坦在他最近的《轻率的社会科学》(Unthinking Social Science) 一书中,不仅否认欧洲中心心的时间性,而且对发展概念本身提出质疑,包括那种已经被单向的马克思主义者的乌托邦主义(unidirectional Marxist utopoanism) 所吸收了的发展概念。这里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主义的概念目的论集中指向阶级的观念。对社会分析而言,阶级概念也许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重要,但是在过去几十年中,阶级分析已经很大程度上被一些社会概念弄得复杂化了。最明显的例子是性别、道德、人种等等。今天,这些概念几乎出现在所有的批判性作品中,并且都因循着既定的陈规老套。从E.P.汤普森(E.P.Thomposon) 《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 到詹姆斯·斯考特(James Scott)的近期著述,阶级都被当作一个僵化的范畴来使用,不是说明了而是掩盖了社会的真实性。阶级已经被当做构成社会存在整体的一个决定性因素,而不是被当作一种社会分析的注释学工具——阶级是描述社会关系网络的诸多范畴中不可省略的一个。在现存的社会主义社会中,阶级这个概念已被先驱领导者抽象化了,用于否定工人阶级自身的社会存在的复杂性。这种目的论不仅被证明是具有政治和社会的危险性,而且在社会存在结构和个人意识已变得异常突出的时候,尤其不能恰当地说明社会阶级关系。
这些观点和我在讨论30年代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革命中的实践时的观点是相似的,但这并不是偶然。我前面已提到过,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时间目的论,因而与其自身的实践产生了一系列矛盾: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社会主义目标与民族主义目标,以及理论概念与社会存在。我并不认为中国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前成熟期的后现代主义,但我想进行这样的一个比较,即由游击战争引起的政治弹性(political flexibility)和当代资本主义的弹性生产(flexible production)之间的比较。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我敢说就是毛的马克思主义)与共产党的目的论没有联系,因而它成为分析当代世界的一个恰当的马克思式的范例。这种马克思主义话语至今仍然通过全球性资本的操作者在世界的概念化过程中继续存在着。所以,一个“游击式营销”(guerilla marketing)策略的倡导者说道:
各位先生们,1984年来到了,怎样面对呢?我们的建议是“游击式营销”。就像游击队员必须依靠熟悉地形而取得战争的胜利一祥,当今的跨园公司同样如此。世界就是我们的地形。随着技术的扩展,我们的目标最终会实现。当今的世界市场,正在被电脑依据残存文化因素(residual cultural factors)(如:习惯用语、当地传统、宗教类别、政治意识形态、民间习俗、传统角色等)、主导文化因素(dominant cultual factors)(如:建立在消费模式基础上的生活方式类型学、电视收视率、音乐品味、时装、动画片和音乐会、家庭影碟出租业、杂志订阅人,家庭电脑软件选择,参与大型超市采购等)和新兴文化因素(emergent cultual factors)(如:提供编导与观众互相交流的影碟片、备有大型图表指南的自动超市、电脑提供多层面交流的消费服务、机器人服务等),浓缩绘制成消费者地形图。我们首先必须关注新兴的市场地形,如果电脑绘制出来的304个消费地带图,不仅能表示出巨型消费单位相当同质的“有意识”需求,而且也能表示出微型消费者花样百出的“无意识”需求,那么,我们就能够占领整个新兴市场。目前,后一种绘制过程已经通过电脑对每个巨型消费单位高达507种类型的微型消费进行了定义和划分。为了扩展和控制市场,必须不断进行这种绘制,这样才能使不管是最自然的还是最不寻常的欲望都可以加以重构。新兴的营销策略是,要使所有营销队伍的思路从商品本身走向商品之意识。这里指的是游击式营销的任务:要像游击队员那样,把我们创造和反对的观念灌输到那些商品意识还没有被系统地建构起来的地方。历史证明,只有发展才有生存。因此,对于跨国公司来说,只有最大限度的追求利润,才能满足公司壮大的需要。我们仍然需要控制和扩展市场,但是现在更重要的是,我们必须控制生产和消费——我们需要推行一整套观念,就像游击队员那样,我们必须赢得民心。要赢得民心,我们就必须采用各种各样的方式,使我们的观念永不停息地得以建构和再建构。
如果除去这段引文中的电脑词汇,它读起来很象30年代在游击战略基础上壮大起来的共产党的一份地方分析报告,而且两者之间的相似还不止于此。游击战争的流动策略需要一种织织上的弹性——既要能适应不同环境下条件变化,又要能始终坚持组织的终极目标不动摇。同祥,游击式营销的强制性要求也使得跨国公司作为一个组织必须具备一定的弹性。“全球性的地方主义”意味着大公司一方面要有组织有系统地顺应地方,融入地方,另一方面又要时刻牢记自己全球性的组织和目标,公司所扮演的这两种不同角色之间的矛盾,自然会引起公司组织上的问题,就像那些忙于游击战中的共产党集权中央所遇的问题一样,CE0(chief executive officer)就是这类公司的代表,他们宁愿把自己的公司称为“跨区域”(multi-do-mestic)公司,而不愿称自己为,跨国”公司,他们对公司面临的组织问题的说法,常象毛泽东描述中国共产党面临的问题时所持的说法,他们说:“ABB(AseaBrowm Boveri)是一个有三种内在矛盾的组织,我们既想成为全球性的,又想成为地方性的;既想大,又想小;还要用集权来推进非集权。如果我们能解决这些矛盾,我们就能创造出真正组织化的优势。”
较早时候的一句激进口号:“全球性地思考,地方化地运作”(“think globally,act locally”)已经被跨国公司成功地吸纳了,营销策略中对地方的关注并不意味着真正承认什么地方自治权,而只是打算用全球的强制性来吞并地方的独特性。让公司在当地社会中“本地化”的做法实际上只是使权力的位置变得更加模糊,因为这些权力并不存在于地方而是集中在公司的全球性总指挥部,是它在调节着公司在各个地方的分支的活动。就象日本的营销分析家Kenichi Ohame曾说过的(听起来又是很像毛泽东的):“全球性的地方主义”是“七分全球,三分地方”(“seventy percent global and thirty percent local”)。当代跨国公司的指南性理想就是使全球同质化。同一个CEO这样说到:“我们真是凌驾于政府之上吗?不是的。我们回答政府的问题。我们遵守公司分支机构所在各国的法律,我们并不制定法律。然而我们的确改变着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我们成为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润滑剂。”
这真是润滑剂,它顺畅地改变了诸种关系!这无疑说明了一个重要的事实:就象激进的游击队员一样,今天的跨国公司,不仅要对环境做出反应,而且为他们自己的成功创造条件。为了达到这一效果,他们首先必须把握社会、政治和文化关系的全部复杂性,而不能仅仅依赖抽象的分析范畴。这些范畴在跨国公司的分析当中只应充当注释学的工具而不是对社会现实的描述,就象在毛泽东的作品中一样。跨国公司进行这种分析,目的不是去满足社会需要,而只是要确切地表达出组织机机构的目的论,当然那个目的论只有用地方性语言来表述才能在各国都获得合法性。
如果全球性资本主义(Global Capitalism)操作者的话听起来很象毛主义者,那并不是因为他们是马克思主义者或毛主义者,而是因为他们面对的是和游击革命者(guerilla revolutionaries)相似的情形,并且也力图通过具体的地方环境表明他们的理论,换言之,全珠性资本主义操作者的任务是,既要在不同的地方使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实现本地化、同时又不能损害资本的全球强制性。他们的分析表明一种想要解释(和 包含)各种矛盾的愿望,而这些矛盾正是资本主义全球化过程本身的产物。这种状况的产生有两个重要的因素。一是来自于地方对资本的抵制,这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第二个阶段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地方对资本的抵制以不同的形式出现:从宣称民族经济自治权,到非常严格意义上的地方——在那里,前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坚决地反抗(或至少是阻碍)那些有助于资本渗透的生产关系和消费习惯。对本土文化和习惯的重新确认(甚至可以说是有意识地宣称)已成为这种反抗的一部分,并且是构成地方语言的不可缺少的要素,不过资本己经对此做出了反应,也就是把这种地方语言看成是和自己的语言一致的。就象游击式营销宣言所表达的那样,他们的目的是要解散(disorganize) 本土文化和习惯以便根据资本主义生产和消费的强制性来加以“重新建构”(reconstructed),同样地,资本的全球化在一些新的地方也导致了前所未有的争夺市场的竞争,即使这种竞争基本上只 是关于谁能最好地“重建”地方消费习惯的竞争,但它的确使人们越来越注意到地方消费习惯的重要性。在过去的垄断状况下,公司可以专注于对生产性质的抽象研究,但是现在,公司必须认真考虑具体的消费习惯和具体的营销环境。汽车工业的例了最能说明这种新的现实,就象日本的制造商一直在说的,美国的制造商就因为忽视消费者状况而丢失了市场。最后,资本的全球性的和地方性的同时成功,意味着既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的资本的推动者的分化,也就意味着资本不得不充分考虑到以前曾经只具有边际利润的那部分人的利益:妇女、道德群体(ethnic groups)、年龄群体(age groups)等等。因此这些群体也必须加以解散以利于“重建”,也就是说必须分析他们所有的复杂性和他们的思想意识,而不再是用一些抽象的范畴来加以认识。
无论如何,资本的目的就是要使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分裂,以便于按照一种全球资本主义的图景全球性重建社会。在当代环境下,散裂化和同质化同样是一种社会存在的条件。用结构语言,我们可以把这种环境描述成“结构连接”(conjuncture of structures) ——全球资本的结构与地方存在的结构之间的连接——的产物:用计算机语言——对资本操作者来说如此熟悉的一种语言、这些环境就是一种“界面”(interface) 状况。这样,空间化范畴就成为一种存在的条件:对时间性的不确定性来说也是如此,因为一种已经过于确定的结构连接.不容许轻易地预设未来。一种全球性的结构连接.不容许轻易地预设未来。一种全球性图景和跨国化的机构也许有助于容纳这些矛盾(例如中共力图使之容纳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党的组织)。但是为了解释矛盾,这种图景和机构必须加以调整,因而现在这些矛盾成为人们关注的首要对象,
作为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已经寿终正寝了,作为理论的马克思主义却远未终结。如果抽掉它的意识形态成分,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分析世界时仍然是有效的,并且在当代众多进行激进批判(radical criticism)的 后现代主义理论那里仍然有生命力。但是,这种马克思主义已经分裂了,它的理论一致性受到破坏,它的概念也遭到解构。不过资本已经吸收了它(其原因却迥异于这种理论的初衷)。与资本通过“现实世界”获得力量相反,激进的批判看来只能够拙劣地模仿它所批判的散裂化状况。资本仍然希望通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目的论来“重构”矛盾,而后现代的批判却不同。它己经直接地将所有目的论都抛弃了,这使得它既缺少一种指南性的理想图示,而且在面临马克思主义已提示过的组织化历史(organizational history)时,也没有任何想要去说明某些组织化活动的意愿。
马克思主义究竟在什么地方仍然是一种关于解放的理论和话语呢?具有反讽意味的是(也许并不完全是反讽地),那些过去曾经是马克思主义者的激进分子这个时候也以怀疑的眼光来看这个问题,认为马克思主义不值得尊重了。但就在这个时候,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同马克思在一个半世纪之前《 产党宣言》中所预言的最相似,资本已经从地域的限制中解放了出来真正成了全球性的:在这个时候,阶级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真实地成为跨国的;而且这个时候,资本主义在全球范围内通过再造/复制相同的社会和文化结构而产生的同质化结果,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明显。今天很少有激进分子会追问:是否社会主义国家的解体意味着马克思主义的不相关性(irrelevance) ,或者它是否为一些人提供了某种借口,这些人的阶级利益——不管是在前资本主义社会还是在前社会主义社会中——要求永远地怀疑和“埋葬”(玛格丽特·撒切尔的报复性术语)作为政治话语的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话语的两个方面确切地说明了马克思主义的相关性:坚持整体性,坚持阶级分析的首要性。后结构主义抛弃整体性,不过是对激进分子抛弃所有的“基本的”历史话语——包括作为资本主义在现代历史的“基本身份”(foundational status) 的那些话语——的一种仿效。这实际上也是对“散裂化”和“差异”的盲目崇拜。他们把诸如此类的概念当成是解决社会不平等和压迫问题的民主化方式由以产生的源泉。同样地,阶级这个概念也遭到批判,因为它“特权化”了一个特定的高于其它阶层的压迫阶级;也因为它坚持社会位置固定化的可能性;以及因为它假设了一个主体,这个主体因阶级分布而被固定化。仔细分析起来,这两个问题实际上是互相缠绕的:作为社会范畴的阶级的首要地位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的基本身分之上,而否定其首要地位又立即引起关于资本主义在社会与历史中的基本身分的问题。
罗伯特·里奇(Robert Reich),是一位重要的全球资本主义分析家,现任克林顿政府的劳动部长,他力图按照全球资本所造成的新的世界形势来调整美国经济。里奇认为,资本的全球化己经改变了劳动的性质。他对劳动进行新的划分,认为劳动分为三种:“符号分析者”(“symbolic-analysts”)、常规产业工人(routine production workers).和普通服务工人(general service workers)。他认为,不论对国家经济来说还是对劳动的国际分工来说,权力都是建立在运用“符号分析”功能的基础上,而这种功能对现阶段的资本主义来说至关重要。里奇并未谈到实际上是人口中的极小部分控制着美国经济50%的资产,但即便如此,他所提出的劳动分类法仍然是建设性的。那些运用自己的头脑进行工作的人(即“符号分折者”)构成本国的和全球经济的统治阶级,而那些运用自己的体力从事劳动的人就成为经济的下层阶级。把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作为决定阶级地位的主要因素而进行划分的做法也许并不新鲜,但它现在却具有了全球性特征。这种分法同样是使世界划分为第一和第三世界的基本依据,因为符号分析功能(进而是研究和发展)要求一种控制全球经济的权力,而常规生产和服务工作则被贬低了第三世界范围内。这样,在全球经济中的阶级分析就对应于第一和第三世界的划分,而这两者都依赖于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分工。
这里的关键不是这种分析对世界的描述是否可以不再受到指责,因为在现在激进改革的时代,现实状况比这种分析所提到的更加复杂和不可预测:关键在于那种全球化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里奇(或《哈佛商业评论》)通过一般公认的激进分子急于加以否定的概念化过程分析了它的运作,他们的分折非常清晰、广泛、并且注意到了种种区域细节。因为他们只有抹平全球性经济的不平等,才能巩固它,并保障它所产生的权力关系。无疑,激进分子排斥整体性问题和全球资产主义抛弃阶级的原因,部分地是由于精神的缺乏和意识形态的无知。
重新恢复马克思的目的论的做法(用杰姆逊的话来说就是“潜伏在资本主义内部的社会主义”)并不能解决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同样,那种把分析范畴同日常生活中过于确定的社会存在相混淆的概念目的论,或者是阶级分析中忽视复杂的社会关系网络的简单主义做法,都无法解决马克思主义的问题,过去的经验清楚地表明,这一类目的论并不能在政治上产生民主化结果,因为——最近的批评直接指出——他们忽略了必须被纳入到任何解放议程中去的一些要素,即差异和同质化。从理论上说、马克思主义者的目的论不再比一种资产阶级现代化主义者的目的论更能有效地解释由全球性资本主义制造的时空散裂化。这种时空散裂化——从它具体的结构的复杂性来看——要求戒除时空简单主义,要求一种对整体性的复杂而矛盾的认可。因此,最终的挑战是,必须用一种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提出整体性(不管已经多么散裂化了的)问题的理论话语,来演生一种关于解放的非整体性话语:也就是用另一方式表明,关于解放的乌托邦式的目标,必须通过理论的科学论述,同未来的殖民主义分离开来、从中解救出来。
任何关于解放的议程,不管它的来源是什么,如果仍想保持对解放目标的真诚,就只能采取为地方着想的整体性计划(或者反过来说是,为整体着想的地方性计划)形式,而不是根据目的论的预设所制定的某种必须遵守的公理——或者是与此正相反的,对地方文化的物化——来制定计划。当资本具有了弹性的时候,对它的激进抵制还能保持刚性和单向吗?在这个总结性小节中,我对这些问题做出了一些回应,不能算是最后答案,只是在思考有关解放的问题时可能值得考虑的一些建议。
标签:目的论论文; 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论文; 资本主义社会论文; 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论文; 世界主义论文; 经济资本论文; 政治论文; 社会阶级论文; 世界经济论文; 经济学论文; 经济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