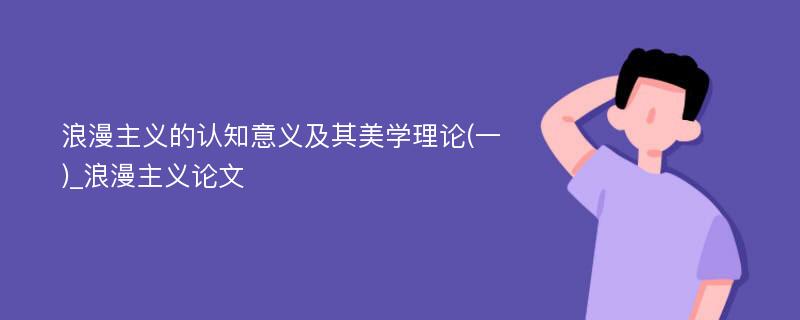
浪漫主义及其美学理论的认知意义(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浪漫主义论文,美学论文,认知论文,意义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 本文论述的浪漫主义只限于十八世纪末至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在欧洲兴起的文化运动。文章首先讨论浪漫主义的内涵和浪漫主义运动前夕欧洲的社会文化背景;论述德国、英国和法国浪漫主义的不同特征、浪漫主义时期的文学创作以及浪漫主义对后世的影响;从西方古代语言起源和修辞学理论以及非理性主义哲学思潮探讨浪漫主义理论的渊源,并从当代心理学、认知理论和哲学阐释学的角度探讨浪漫主义理论的认知意义。文章认为,浪漫主义运动是开创西方现代意识的先躯运动,西方现代主义美学原则是浪漫主义美学理论的发展和延伸。
一、浪漫主义的内涵
本文论述的浪漫主义只限于18世纪末至19世纪30年代在欧洲兴起的文化运动和社会运动,不应与其他地域和历史时期出现的艺术创作方法上的浪漫主义倾向混为一谈。浪漫主义曾于18世纪90年代至19世纪30年代横扫欧洲文明的各个领域,当时欧洲的人文主义、社会主义、民族主义、宗教运动以及哲学、文学、音乐等文化艺术领域都受到浪漫主义运动的巨大冲击或从中获得启示和力量。
什么是浪漫主义,抑或浪漫主义的内涵是什么?许多西方学者对此进行了阐述,但至今“尚未有人能给出他自己和别人都完全满意的界定”。〔1〕美国学者布尔吉姆曾警告说, “谁要试图对‘浪漫主义’予以界定,那么他必然进入一个危险的区域,而且这里已陷入了许多牺牲者。”(《凯尼恩评论》,1941)霍普金斯大学教授亚瑟·洛夫乔伊说,要对浪漫主义的内涵进行探讨,其结果只能导致混乱和错误,“‘浪漫主义’一词所指的东西越来越多,致使它自身已毫无意义。它已不再具有一个文字符号的功能。”(《英国浪漫主义诗人》,1924)美国历史学家巴曾的《古典派、浪漫派和现代派》一书,对洛夫乔伊的论点作了极好的说明,在该书中巴曾列举了关于“浪漫”一词的多达23种解释,其中有些解释意义恰恰相反。伯恩鲍姆在《浪漫主义运动指南》一书中收集了各种各样关于浪漫主义的定义。这里摘要引述,以便从中见出其主要内涵。例如:浪漫主义是病态的,古典主义是健康的。(歌德)/是以一种想象的形式描述情感。(F·施莱格尔)/ 颂扬古典主义拒绝的一切东西。古典主义是明智和规范,是温文尔雅,完美与和谐;浪漫主义则是想象,谬误的狂涛,一种文学自我中心主义的盲目思潮。(布吕内蒂埃)/于大自然之流,而不是脱离自然之流, 去观察无限的一种幻想。(摩尔)/回归自然。(卢梭)/一种事物是浪漫的……在于它违反了因果常规而追求冒险;这一整个运动充满着对无知……蛮荒、乡野、尤其是对童稚状态的赞美。(白壁德)/ 从外界经验的退缩而集中于内在心灵的探索。(阿伯克龙比)/文学中的自由主义, 是悲剧因素或崇高与荒诞的混杂(这是古典主义所弃绝的),是生活的完全真实。(雨果)/生命与中世纪思想的觉醒。(海涅)/对毁灭的膜拜。(杰弗里·斯科特)/古典主义学习往昔,浪漫主义则弃绝于往昔。(谢林)/逃避现实的一种努力。(沃特豪斯)/多愁善感的忧郁。(费尔普斯)/是情感而不是理性,是心灵而不是智力。(乔治·桑德)/ 是对心灵潜意识的解放,一种令人陶醉的梦境。(卢卡斯)/想象力的巨大拓展。 (赫福德)/在想象力的激发或导引下,强调和突出情感生活, 从而促使或引导想象力的进一步发挥。(卡扎米安)/奇异成为美的因素。( 佩特)/在古典主义作品中, 观念是以尽可能确切的形式明确而直接地表现出来;在浪漫主义作品中,思想须由读者借助于作品中的象征与暗示去领悟和补充。(塞恩斯伯里)
尽管有如此多对浪漫主义的解释,新的解释仍在逐年增加。英国哲学家和历史学家艾赛亚·伯林把浪漫主义的本质总结为“艺术对生活的专横。”当代美国音乐史家保罗·朗格认为,“青春的活力、渴望和陶醉”是浪漫主义音乐的三大特点。而文学批评家韦勒克则把浪漫主义看作是关于想象的特殊观点、对大自然的特殊态度和对象征的特殊使用的混合。浪漫主义所复盖的意义如此宽泛,我们不难看出任何一种关于浪漫主义的解释都不是完全和令人满意的,但是纵观这些解释却能使我们对这一文化运动的性质获得一种多层面的理解,从中看出浪漫主义运动的复杂性和多向性。即使在18世纪晚期和19世纪初期,许多被公认的浪漫主义诗人和思想家也对浪漫主义的解释莫衷一是。德国浪漫主义运动的领袖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关于浪漫主义的解释是常被人们引用的那句话:“浪漫主义是以一种想象的形式描述情感。”但是在此之后他在《古代和现代文学史》中,又把浪漫主义同基督教等同起来,他说,“在所有其他戏剧家中,卡尔德隆是富有基督教精神的戏剧家,因而也是最具有浪漫主义气质的戏剧家。”〔2〕19 世纪初期法国展开的美学论战中,浪漫主义被赋予了许多新的意义。史达尔夫人提出,浪漫主义实际上是北欧、中世纪和基督教风格的同义语,与其对立的则是南方、古典和非基督教的风格。在其著作《论文学》和《论德国》中,她又提出了浪漫主义民族主义的问题,这一思想后来成为浪漫主义思潮的一个重要方面。然而对雨果和司汤达及其同时代大多数人来说,浪漫主义主要是区别于古典主义。在《克伦威尔》和《爱尔那尼》的作者雨果那里,浪漫主义等于自由、独特、自然之美和奇异荒诞。然而直到19世纪初期,在英国人们没有使用浪漫主义这一词语,因此也就避免了关于其内涵的争议。华兹华斯在《抒情歌谣集》前言、雪莱在《为诗辩护》和柯勒律治在《文学生涯》中都没有使用浪漫主义这一词语,虽然它们被认为是英国浪漫主义的宣言和重要文献。因此卡莱尔于1831年写的一篇关于席勒的文章中说,“我们(英国人)不必为浪漫主义同古典主义的争论而苦恼。”〔3〕在当时的英国有湖畔派、撒旦派等说法, 但没有浪漫派这一称谓。
关于浪漫主义的界定多得不可计数,几乎可以说有多少论及这一问题的人,就有多少关于浪漫主义的定义,这对该问题的探讨更增加了困难。这使我们想到启蒙主义者的一条“金言”:“懂得了起源,就懂得了本质。”鉴于浪漫主义内涵的复杂性,我们有必要对“浪漫”一词的原本意义作一简要追寻。
中世纪早期,“romance ”一词意指一种同拉丁语文学语言相区别的粗俗语。在古老的法语中,“roman ”是用韵文和通俗故事描写的一种宫廷传奇。这些作品主要描写中世纪骑士的神奇和冒险故事,其中有骑士的爱情和侠义以及神秘莫测、异想天开的传奇故事。romance (传奇故事)这个词首先在英国得到广泛传播,这一点被认为是英国人对欧洲文化的著名贡献之一。在由秩序和绝对真理统治的17世纪欧洲理性时代,这一词语不可避免地名声扫地,它代表着幼稚无知、荒诞无稽和虚妄无实。直到18世纪初期,“浪漫”一词才在人们意识中逐渐获得某些新的意义,由单纯的贬义而获得某些正面意义。大约在此同时,古老的传奇故事也开始恹复它在中世纪、伊丽莎白、哥特和斯宾塞时期所享有的声誉。“浪漫主义”这时还获得了具有“想象的魅力”的意义,想象不再是令人怀疑的异想天开,而是正面意义用于描述古老传奇背景的群山、森林和荒野这些自然风光。大约到18世纪中期,“浪漫”一词已经获得了双重意义:其原本意义即使人们联想到那些古老的传奇以及想象和情感的魅力。就在这时,“浪漫”一词的上述意义开始进入法国。卢梭在《孤步冥思》中写道,“比涅湖畔比日内瓦湖畔更加蛮荒和富有浪漫气息。”1789年出版的《法兰西学院大词典》中对“浪漫”一词的解释是“一般用于诗歌或小说中描述想象中的地方和自然风光。”因此“浪漫”一词开始并不是用于艺术批评的术语,它标示着当时人们从想象和情感的角度去看待事物的一种心理变化。用于文学艺术领域相对而言是一种较晚的用法,一般认为始于施莱格尔于1897年发表的关于浪漫主义的小册子。
由此可见,“浪漫”一词在用于文学艺术领域之前已经获得其自身意义,了解这一点是十分重要的:文学批评和社会生活中出现的浪漫主义这一伟大运动并不是伴随这一词语的出现,而是源于整个18世纪西方出现的根源深远的人们思想观念的变化。正是由于某一社会背景下人们思想观念的变化从而赋予言语以新的意义和内容,“浪漫”一词才逐渐承载了各种不同的新义。因此,浪漫主义同其相关内涵如情感、想象、天才、独创性等意义的相继出现,只能在人们价值取向发生根本变化的情况下才有可能。这种变化不仅改变了文学艺术的创作风格,而且也改变了人们对人和自然的态度。浪漫主义运动是西方社会长期发展变革的结果,如果我们希望把握其根本意义,就必须深入观察其演变过程中的社会历史背景,而不是单纯考查这一词语的意义内涵。
二、浪漫主义运动的社会文化背景
对新古典主义的反动
浪漫主义运动是18世纪欧洲各种社会思潮汇合而成。历史进入17世纪,文艺复兴时期对古典主义的复兴达到了颠峰,以尊重权威、模仿古典、崇尚理性、克制情欲为宗旨的新古典主义统治了整个欧洲,而由天主教会与君主政体联盟所控制的法兰西学院成为在艺术领域贯彻专制思想的先锋。这种贵族艺术是超越个人情感的阶级意识的表现形式,这个阶级的行为准则是基于礼仪和风雅一系列常规之上,一切真挚的个人情感都必须接受理性的规范和约束,这种学院风气不可避免地导致艺术创作陷入规格化和因袭主义。
新古典主义时期的极权主义还来自对心灵和理性力量的一种错误信念。笛卡儿在他著名的“我思故我在”中演绎出人的存在赖于其思想的力量。德国哲学家沃尔夫认为上帝即为“纯粹理性”,而世界则是遵循一系列规律逻辑地运作的机械。17世纪的科学发现,尤其是牛顿的科学发现也助长了人们一切事物都可借助理性而被认识的信念。这种对理性的膜拜就是艾赛亚·伯林所说的已成为欧洲几代人的精神支柱。这一精神支柱为人们提供了一种稳定、和谐的世界观,它来自对宇宙秩序的安全感,因此也为文艺创作提供了一种稳定的参照系。启蒙运动分别在政治上为法国革命和文艺上为浪漫主义运动作了思想准备。浪漫主义是对法国新古典主义的反抗,而这一反抗的旗帜首先是启蒙主义的领袖们竖起的。但是浪漫主义者对启蒙运动反对新古典主义的不彻底性及其宣扬的“理性的胜利”感到失望,因此浪漫主义又是对启蒙精神的怀疑和反动。一种新的居于优势的文艺批评标准和方法的形成是浪漫主义蓬勃发展的主要前提,它虽然是以文艺革命为其主要突破口,实际上却是西欧社会思潮长期酝酿、发展而形成的一种冲击社会各个领域的文化运动和社会运动。
浪漫主义在启蒙运动时期发展的速度和范围与新古典主义传统势力的强弱直接相关。在笛卡儿的故乡法国,直至18世纪后期传统势力依然根深蒂固,浪漫主义发展缓慢。直至1799年,拉阿尔普在其《文学教程》中仍坚持文学创作传统的永恒原则。伏尔泰虽然在政治上观点激进,但在文学上却是保守的,以仰慕的情怀留恋拉辛的时代。他虽然反对过分僵滞的理性主义,但依然强调风雅、节制、得体,即所谓艺术中的“适度”。在《哲学辞典》中,他承认热情和情感在艺术创作中的地位,但强调热情必须合乎情理,即必须置于理智的控制之下。狄德罗曾认为理性有害于诗的创作,但到了晚年,部分地由于统治集团把他作为激进派并对其施以威胁与压力而变得愈加审慎。一方面他对莎士比亚十分赞赏,另一方面对新古典主义的清规戒律遵从不违。狄德罗这种暧昧态度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18世纪法国文化艺术的特征。换言之,18世纪法国的浪漫主义思潮尚未从新古典主义的桎梏中解放出来。
启蒙运动时期的英国文学艺术界出现了摆脱陈旧规范的思潮,但塞缪尔·约翰逊坚持的理性主义仍有很大影响。德莱顿倡导为艺术美而打破清规戒律,这标志着在文学领域出现了新的现象:衡量艺术作品的标准是美而不是陈腐的理性规范。英国人有其王政复辟前的古老传统,即莎士比亚和伊丽莎白时期的传统,这些传统为他们提供了不同于古典传统的文学模式,因此在英国出现了比法国远为自由和宽松的文化艺术环境。风雅、适度和规范依然受到重视,但同时在思想观念和艺术表现形式上都有很大灵活性。至18世纪中期,在英国人中新的思想观念十分活跃,这也是英国启蒙运动的缩影。
兴起浪漫主义运动的另一个主要国家德国,没有英国莎士比亚和伊丽莎白文学繁荣时期,也没有法国高乃依、拉辛、莫里哀等人的“黄金时代”,在启蒙运动初期德国就是一个处于四分五裂、经济落后、且仍在经受30年战争创伤的国家。18世纪上半叶的德国同法国形成一种鲜明的对照:在莱茵河此岸是一个踌躇满志、为其辉煌历史而自豪、不肯忘怀往昔的法国;在莱茵河彼岸却是一个没有值得其自豪的历史而又急于以新的思想实行改革的德国。在某种意义上,德国浪漫主义的出现是对法国控制的反抗,这种反抗首先是对理性时代法国文学艺术风靡欧洲的抵制,后来又是对19世纪初期拿破仑在军事和政治上的胜利的抗衡。正是由于德国的落后而成为欧洲浪漫主义运动的先躯,而强大的古典传统却使法国在历史前进的道路上滞后。
对神秘、奇异的崇尚
浪漫主义者把古典主义所宣扬的理性看作是对文艺的一种束缚,倡导情感和想象在艺术创作中的重要地位。因此新古典主义时期被称为理性时代(Age of Reason), 浪漫主义时期被称为情感时代(Age ofSensibility)。由于浪漫主义诗歌、小说或戏剧的创作都充满浓厚的抒情色彩,所以法国文学批评家有时把浪漫主义称为抒情主义(Lyricism)。英国哲学家休姆在《人性论》中说,“理智是而且仅仅是情感的奴隶。”敏感而富于情感的心灵被认为比善于判断的头脑更为重要。英国戏剧家西伯和斯梯尔充满动人情感和激昂对话的戏剧、法国拉肖塞的所谓“令人伤心的喜剧”和德国克洛卜施托克情深意切的诗歌深受欢迎,正说明当时人们的审美情趣正在发生变化。然而情感在小说中的表现,尤其是在英国小说中的表现,直至18世纪中期才蔚为大观。这些情感小说如塞缪尔·理查森的《帕美勒》(1740)、《克拉丽莎·哈洛》(1747)和《查尔斯·葛兰底森爵士》(1754),哥尔德斯密斯的《威克菲尔德的牧师》(1766), 劳伦斯·斯特恩的《感伤旅行》(1768),亨利·麦肯齐的《多情的人》(1771)和亨利·布鲁克的《朱丽叶·格伦维尔》(或《人类心灵史》)(1774)。在欧洲大陆有普雷沃的《曼侬·莱斯科》(1735),卢梭的《新爱络绮丝》(1761)和歌德的《少年维持之烦恼》(1774)等。《人类心灵史》这个书名可用于所有这些小说,它们都以奔放的激情描述善良、正直的主人公的人生遭遇,去感动和教育人们,激起人们对这些无辜的牺牲者的同情。这些小说中冗长甚至重复的情节和背景本身往往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们为人类情感的宣泄提供了场所和环境。这些小说将当时风靡西欧的浪漫主义时代精神体现的淋漓尽致。
富有浪漫主义色彩的情感小说风靡欧洲标示着人们审美情趣的改变,也为18世纪下半叶出现在文学和建筑领域的哥特风格的复兴创造了适宜的气候。哥特风格是文艺复兴时期首先由意大利艺术家对这种风格提出的一种蔑称,讥笑哥特人对古典准则的无知,因此哥特风格代表一种粗俗、尚未开化和带有情感色彩的风格特征,哥特风格的复兴也成为浪漫主义的一个方面。〔4〕这种哥特风格常常把人们引入一种超自然的恐怖之域,哥特式建筑的兴起主要由于受到英国文学领域出现的哥特小说的刺激。只要回顾一下18世纪在英国出现的一些小说和戏剧的名称,就不难发现其中正在酝酿着的一种审美倾向。这些小说如《闹鬼的修道院》、《恐怖的神秘》、《盗贼》或《迷宫中的爱情》、《流血中的林登堡修女》等。其中霍拉斯·沃波尔的《奥特朗托堡》(1764)、贝克福德的《瓦提克》(1780)、拉德克利夫夫人的《尤道弗神秘事迹》(1794)和马修·刘易斯的《僧人》(1796)在当时极受人们的欢迎,它们标志着浪漫主义一隅的发端。霍拉斯·沃波尔的小说《奥特朗托堡》有一个副标题是《一个哥特时期的传说》,这些故事发生的背景往往是一些神秘的城堡和衰朽凋残的寺院,这些地方有秘密通道、隐蔽的城垛、活动的暗门和从古墓中发出的阴森森的声音。这种环境就是那些被伤害的、天真无邪的、脆弱而无援的女主人公和刚毅、勇敢甚至有些粗莽的男主人公活动的背景。这种传奇故事进一步界定了“哥特式”这一词语的内涵,它令人联想到神秘、奇异和荒诞。伏尔泰曾把它称为粗俗蛮野同精巧的雕饰混合在一起的一种荒诞无稽的东西。哥特小说风靡一时,为司各特小说创作的巨大成功打下了基础,当司各特的小说自1816年始被译成法文之后,又为雨果和大仲马的传奇小说开辟了道路。
这些哥特小说中描写的富有梦幻色彩的城堡首先在英国的一些建筑形式中具体化了,它们是一些富有的怪人异想天开的产物。沃波尔是一位显赫而富有的首相的儿子,他整日沉迷于幻想之中,为他的住宅起了一个名字叫“恐怖的草莓山”。贝克福德把他的哥特式住宅称为“方特希尔修道院”。这些私人住宅建筑为这一建筑风格的内涵增添了一个方面。于是在文学的影响下,哥特风格在英国建筑领域开始复兴,由查尔斯·巴里设计的伦敦议会大厦和厄普约翰设计的纽约三一教堂等至今都是人们熟悉的著名哥特式建筑。以描写阴森恐怖和焦虑悬念情景而充满浪漫主义情调的风格魅力一直持续至19世纪,例如玛丽·雪莱的《弗兰肯施泰因》(1832)以及霍夫曼、爱伦·坡、霍桑的许多短篇小说和所谓颓废派的作品,在传统浪漫主义对美的膜拜的同时,人们的兴趣转向探索生活中神秘而阴暗的一面,成为浪漫主义的另一个方面,这是一种令人奇异的现象。
对悲怆人生的宗教反思
18世纪基督教中的虔信主义运动作为对当时流行世态的一种反动力量不断增长。在德国,虔信主义运动是对在路德派教会中发展起来的贬仰情感和僵滞的教条主义的一种反抗,它同时也反对科学和理性,认为启蒙运动和自然神论都是人类心灵编造的东西,是上帝所不齿的。对虔信派教徒来说,人类理性专横而傲慢,其内容是对宗教的亵渎。因而他们把启蒙运动时期发展起来的科学和艺术成就视为“丑恶与堕落”,是公共生活中“不幸的罪恶的猖獗。”他们认为,真正的宗教是个体道德意识的体现,是感动心灵的内心体验和隐秘情感,是比理性更为合理而可靠的行为指南。被认为是现代基督教新教神学的缔造者施莱尔马赫在《基督教信仰阐述》中指出,基督教教义体现“绝对依存感”,而这种感觉正是知行合一的原始形式。他在《独白》中又从伦理学角度观察宗教,指出宗教是自我个性的直感与行动,每一个人的个性都是无限本身的“代表象征”。施莱尔马赫的宗教思想是对过去的明显决裂,在阿奎那神学的逻辑模式中,五个多世纪以来始终同理性纠缠在一起,对其神学观点都予以论证,甚至论证了上帝的存在。然而施莱尔马赫却坚持,一种理性的形而上学是不可能用于宗教信仰的,信仰是一种心理的和社会学的现象,对信仰对象的证实实际上是无稽之谈。施莱尔马赫认为,虔信是一种情感而不是知识或行动,虔信对一切宗教都是不可或缺的,这种宗教感情完全是主观的,它激发人们的知和行,教会的作用就是激励和升华这种特殊的虔信感情。自施莱尔马赫以降的神学家大都放弃了对上帝存在的论证,而是着重探究宗教体验的特点。由此,施莱尔马赫在《论宗教——致蔑视宗教的知识界人士》中曾明确指出,宗教其实与浪漫主义有密切关系,因为宗教也是“对宇宙的感知和直觉”,是“有限者对无限的感知”,基督教就是这种感知体系之一。所谓无限就是上帝,因而上帝就应理解为这种虔信感的渊源,这就是人类所能知道的有关上帝的信息。
当人们敏感的心灵进入沉思,往往会愈加意识到自身的忧郁和悲怆,而当时的宗教运动更加助长了这种心理倾向。在施莱尔马赫宗教哲学的感召下,18世纪德国路德教的虔信派和英国的卫理公会教徒在他们虔诚的圣咏中常常真情地吐诉其宗教的伤感之情和高扬灵魂的主体意志。虽然他们也有参与社会活动的现实一面,但他们在宗教活动中让人们意识到一种对人生短暂的空寂感,对人类命运感到凄怆和惨淡。这一主题很快出现在如托马斯·格雷的《墓园挽歌》(1742-51)、爱德华·扬的《夜思》(1742)和赫维的《墓地冥思》(1748)这些诗歌中。仅从这些诗歌的标题就可想见它们为什么被称为“黑夜与墓园诗”。在这些哀悼人生命运的诗歌中,伤感的旋律取代了中世纪流行的表现死亡的骷髅舞蹈中粗犷和令人毛骨悚然的氛围。在这些诗歌中,世俗的物质意象隐退了,代之而出现的是表现凄惋的宗教情绪的意象:墓园、废墟、古老的修道院激发人们产生一种悲悼哀怨的人生反思。格雷的《墓园挽歌》在主题和创作技巧上都表现了一种人生悲怆凄恻之情。象征生命短暂的墓地、日暮黄错的蒙影,所有这些细节都用以烘托一种孤寂、肃穆的氛围,通过微妙、朦胧的意象引发一种空灵的诗意和想象,其中回荡着情真意切的情感之流。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些诗歌表面看来似乎是如此颓废、悲观、消极的感叹中,深藏着的恰恰是它的反面,即对人生、生命、命运、生活的强烈的欲求和留恋。上述诗歌这种新的情感模式和表现手法也明显地出现在卢梭的《孤步冥思》(1782)中。这是一部在形式和内容上都体现了一种强烈的主体意识的作品。在以意象和意念之流所连结的冥思中,诗人表达了他们自己的声音、情怀和心境。在沉思冥想中,摆脱了庸俗生活对身心的沉重缠绕,发现了深隐着的自我,认识到生命的本来面目和固有价值,开拓了心灵的广阔空间,寻觅到一块相对自由的精神领地。在忧恐、悲叹之余产生一种强烈的生命冲动,主观意识得到升华,个体价值获得高扬。在虔信主义宗教情绪影响下而产生的上述现象曾深沉地笼罩着18世纪欧洲文学的上空,构成了浪漫主义的又一重要特征。
回归自然
18世纪后半叶出现了各种形式的非理性主义倾向,这种现象的产生是对启蒙运动强调理性的反动。早在1756年,伯克在《论崇高与美》中提出,在文学艺术中,存在一种比美更为重要的东西,这就是崇高。崇高能够超越纯粹之美,而且它甚至允许丑的存在。他说,“任何一种可怕的现象,或者与可怕有关的事物,都是产生崇高观念的源泉。情感的自由宣泄和想象的自由发挥,即使这种宣泄和发挥意味着痛苦、惊恐、可怕,都将是艺术进行探索的不容忽视的领域。”与此同时,人们沉迷于卢梭对阿尔卑斯山风光及雪崩和风暴的描述。之后,卢梭首先吹起回归自然的嘹亮号角,他以高扬壮美的原始蛮荒向人的典雅、文明挑战。费尔巴哈也曾大声疾呼,“只有回到大自然,才是幸福的源泉”,因为大自然是人类的精神家园。人们远离人类社会的喧嚣,投入人迹罕至的大自然怀抱,领略那原始蛮荒的粗犷之美。回归自然的思潮产生了深刻的社会影响,尤其是生活在城市的人们,他们向往着田园牧歌的生活,把法国巴比松山林派和英国风景画家如康斯太布尔等人的作品挂在公寓或市内住宅内。贝多芬的《田园交响曲》和瓦格纳的《山林低语》以及其他许多钢琴曲中都回荡着田园牧歌那令人惬意的旋律。年轻的法兰西王后、路易十六之妻玛丽·安托瓦尼特曾在规整的王宫花园内为自己建造了一所朴素的小屋,旁边有磨房和奶牛场。她还常常离开凡尔赛宫去到她心目中向往的乡村同牧童和牧女们相处,这一情节是回归自然社会思潮的典型例子。
理性盛行的18世纪,卢梭警觉到理性主义对人性的摧残和腐蚀,他提出自然人性的沦丧是从社会文明的产生开始的。卢梭批判理性文明对人的情感的规范和压抑,谴责基督教神学教人们克制情感和欲望以期来世的教义。卢梭提出的回归自然实际上是倡导以自然生命和情感冲击理性文明的一种社会风潮,因此卢梭成为浪漫主义思潮的伟大先躯之一。回归自然的思潮之所以产生了强烈的社会反响,也反映了人们对资本主义的城市文化和工业文明的厌恶。工业文明造成人与自然的分离和对立,人成为孤立的主体,人们以理想的寄托摆脱现实的困扰,从这一意义上讲,浪漫主义思潮的兴起也是近代工业文明社会的必然产物。另外,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激起了知识分子无限而美好的向往,似乎由理性和天才治理的社会即将到来。然而大革命的结局却使他们失望,知识分子在大革命中曾是进步阶级的先导,现在却要对大革命的失误和过火行为负责。接着而来的是政治上的反动而智识却显得黯然失色的时期,他们感到威信扫地和自身的无能而处于被谴责的地位。因此他们企望从现实逃遁,转向潜意识的幻念,转向不可思议的神秘世界,转向梦境和乌托邦,转向原始蛮荒的大自然。一言以蔽之,他们企望从失败的感受中解脱出来。这种回归原始蛮荒和自然状态的浪漫主义思潮也映射出人们在为成功、权力及物质生存竞争中产生的一种焦虑和不安全感的心态。
另一方面,回归自然的思潮是人们对待客观世界的一种全新态度。这一观念的改变可以概括为从机械论向有机论的转变。对于笛卡儿和他同时代的理性主义者,世界是一部由上帝操纵并循从某些规律运作的庞大机械,理智的人类是这一世界上的主宰者。人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把荒野的大自然改造成法国式的规整花园,其中有对称的花坛、整齐的树篱和笔直的花间小径。但是到了18世纪中期,出现并流行自然风光化的英国式园林。这种审美态度的变化是回归自然审美情趣的又一典型例子。自然从作为人类手中的工具开始成为独立的存在;诗人不再使用僵滞的标准语句而是从实描写他们所观察到的客观现象。詹姆斯·汤姆逊的《四季》(1730)、哈勒(瑞士生理学家)的《阿尔卑斯山》(1729)和圣朗贝尔的《四季》(1769)就是这些作品中的代表。人们还往往把客观的自然描绘成充满主观情感的自然,人的情感同自然情状交相辉映,如格雷的《挽歌》、卢梭的《孤步冥思》以及考珀和德利勒的一些诗歌。这些情深意切的作品把我们带进了浪漫主义的门槛。
卢梭还提倡俭朴的生活和所谓“高尚的蛮野”生活情调。这种生活情调在文学中并不是全新的现象。《罗宾逊漂流记》(1719)已是所谓“孤岛小说”的著名例子。但是卢梭把这种冒险故事打上了浪漫主义乌托邦这一观念的印记,这一思想体现在柯勒律治和骚塞的乌托邦式大同世界计划和布莱克“黄金时代”的构想之中。卢梭在《论人间不平等的起源》(1755)中说,腐败源于文明,尤其是源于财产的私有制,它是人间不平等因而是嫉妒和堕落的根源。他提出医治这一社会弊端的方法是回归自然,即回归他所谓的人人平等的“初始社会状态”。在一个贵族拥有大量土地的社会里,这种民主思想对人们的吸引力是显而易见的。尽管这种思想尚属朦胧而渺茫,但确实在当时社会上流行一种“自然状态中稚朴的社会”理想,人们向往着从远方或往昔追寻到那个理想的社会。
这种社会背景下,出现了大量描述大自然神圣奥秘和异国风情的作品,如贝尔纳丹·德·圣皮埃尔的《印度茅舍》(1790)和《保尔与薇吉妮》(1788)。在贝尔纳丹的作品中,颂扬文化原始主义,歌颂田园恋歌式的道德之美,而当欧洲文明侵入之时,就是悲剧到来之日。夏多布里昂的《阿塔拉》(1801)和《勒内》(1805),描写的是美洲原始部落的故事。另外还有描述野蛮人的行为和原始正义思想的作品,如歌德的《铁手骑士葛兹·封·贝利欣根》(1773)和席勒的《强盗》(1781)。人们对过去出版的原始部落的民歌和故事集产生浓厚的兴趣,如托马斯·珀西的《歌谣辑古》(1765)与赫尔德的《民歌》(1778)。在此同时,出现了凯尔特复兴运动和詹姆斯·麦克弗森的《莪相诗集》(1762)。这一诗集的出版在欧洲立即出现了翻译、摹仿热,并在诗歌、戏剧、绘画甚至服饰领域引起强烈的效仿潮。包括年轻的歌德在内的许多文人学者甚至把莪相同莎士比亚并列,可见这些诗歌的巨大影响。这些诗歌的魅力是多方面的:它们是人们崇尚的原始部落的“蒙昧”诗歌,是原始社会图景及哀伤情感的表现;它们激发人们对笼罩在浓雾中的北方风光的向往;是对反古典主义异教凯尔特神话的高扬;是对富有戏剧色彩的古老传奇的追忆;更重要的是,这是一种新的诗歌风格,其中有丰富的形象和比喻,以及由异国情调的盖尔语表现的音乐感和狂热的情感。这些诗歌也证实了浪漫主义者所倡导的新的诗歌理论:诗是诗人充满情感的天赋创造性的自由发挥。从此开创了民谣复兴运动,为浪漫主义诗歌创作提供了灵感和源泉。
对神话的膜拜
启蒙运动时代,神话被看作是一种粗俗的东西,一种奇怪的观念和愚昧的迷信。神话同哲学之间不存在任何可比之处;神话消失之时,才是哲学产生之日,犹如黑暗让位于升起的太阳。在回归自然,回归原始蛮荒思潮冲击下,神话和对神话的研究激起人们的极大兴趣是十分自然的。神话不仅使浪漫主义者发生莫大兴趣,而且成为崇敬的对象。神话被看作是人类文化的主要源泉,艺术、历史、语言、诗歌都源于神话。卡西勒说,“浪漫主义哲学家和诗人们首先从神话的魔杯中饮酒,这使他们感到恹复了青春的活力。从此以后,他们以一种新的不同的态度去观察事物。……对于那些真正的浪漫主义者,神话同现实不再存在任何区别,如同诗与真实之间不存在任何区别。诗与真实、神话与现实相互渗透,相互重合。”〔5〕对神话的这种观点同启蒙运动时代哲学家对神话的观点截然相反,这是对以往价值观念的彻底变革。从这一点出发,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没有明确的区别,宇宙是一个精神的宇宙,人的创造力如同潜在于大自然的创造力。谢林在《艺术哲学》中专门讨论了诗歌同神话的关系,他认为,在神话与艺术的密切关系中实现了人类心智同精神的统一,正是在神话中我们发现了特殊与一般的结合,神话无视两者的区别。谢林建立起一种关于神话功能的全新观念,他是首先把哲学、历史、神话、诗歌视为一个相互关联的综合体的哲学家,成为浪漫主义诗歌的哲学代言人。柯勒律治、罗斯金、尼采等人都对神话有浓厚的兴趣。柯勒律治在《文学生涯》中对原始想象的解释直接受到谢林的影响。尼采是那些探讨关于希腊悲剧中仪式起源的理论家们的一位先躯,弗雷泽、吉尔伯特·默里、简·哈里森以及20世纪的许多神话理论家都从尼采那里得到启发。
浪漫主义者关于神话的研究和讨论中,把神话作为人类文明古老而伟大的成就,神话是相对于理性建构的一种不同思维方式,神话同语言、诗歌、艺术和人类早期思维是分不开的。甚至科学在进入逻辑时代之前也必须经过一个神话的时代:炼金术先于化学,占星术先于天文学,而且神话所表现的内容是不可能以理性的比喻方式进行解释的。后来的荣格、卡西勒及其他一些人都持这种观点。
浪漫主义者与启蒙主义者的不同还在于对历史的新的兴趣,而这种对历史的新的兴趣同对神话的兴趣不无关联。19世纪前期首先在德国出现了现代意义的历史研究和写作方法。浪漫主义者从新的角度看待历史,把新的科学方法引进历史研究。他们不是提出大量历史资料,而是对重要的历史文献进行科学而深入的批判分析,并对不同民族的生活方式从人种学、制度风习以及社会和法律等多角度进行研究,从而开创了历史研究的新纪元。浪漫主义者对历史的兴趣在于历史本身,即为历史而研究历史。对他们来说,历史不仅是一种事实,而且是其最高理想之一,把历史理想化和赋予历史以精神意义是浪漫主义思潮的特征之一。这种心理构架同启蒙主义者完全不同,启蒙主义者研究历史是为了鉴前资后,以历史研究为手段,而浪漫主义者则以历史研究为目的。具有代表性的浪漫主义历史学家是德国的尼布尔和兰克。他们的主要贡献是开创了历史研究中对原始资料进行科学鉴定的新的研究方法。
新的审美情趣
历史进入18世纪,新古典主义体系逐渐被瓦解,一种新的诗歌理论逐渐形成。德莱顿和莱辛对美感的解释,狄德罗提出艺术家不以古人而以自然为师,莱辛提出莎士比亚是富有创造性的天才,所有这些理论的出现都标志着一个伟大的新时代的开端。18世纪前期,在浪漫主义作为一种运动兴起之前,英国首先领导了新的美学方向。由于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成功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情调,从而影响到艺术和美学思想的变革。下面三位英国批评家对浪漫主义诗歌理论的直接贡献值得重视,他们是约翰·邓尼斯、洛斯和爱德华·扬。邓尼斯于18世纪初首先揭示了朗吉努斯以作者的心灵与感情力量作为诗歌效果主要源泉的理论。邓尼斯在《诗歌批评的根据》中提出,“诗歌艺术的主要目的是激发人们的热情”,情感“正是诗歌的本质和特性所在。”另一位批评家洛斯主教也以朗吉努斯为楷模,于18世纪中叶发表了《希伯来圣诗讲演集》(1753)。洛斯在讨论希伯莱诗风的特征时指出,形象的语言是情感自发的、本能的产物,情感能够修改感知的对象。他认为诗歌从“心灵中更为炽热的情感中获得生命”,诗所反映的不是外界事物,而是诗人自身的热情;诗展现了人类自身的形象、冲动、烦扰和隐秘的情感,这种人类自我揭示正是希伯来诗歌的一个显著特征。在这方面,爱德华·扬的思想也是从前人那里继承而来,但他的《浅论独创性作品》仍不失为一部重要的著作。扬系统地总结和阐明了独创性思想的内核,对模仿与独创、学识与天才、规范与自由创造以及古代与现代之间的区别作了明晰的阐述。爱德华·扬说,“可以把具有创造性的作品比作一棵菜蔬,它是从天然的根长出,是生长而不是制作;摹仿则往往是经过某种机械性制作过程,是来自己有材料通过劳作和技巧加工而成。”扬提出的诗歌是“有机生长的意象”说,后来被歌德和柯勒律治所接受,扬所倡导的诗歌创作要有天才的灵感、大胆的开创精神以及对自发性的强调等,都使他成为浪漫主义诗歌理论的直接先驱之一。
爱德华·扬的诗歌理论在国外尤其在德国引起比在英国更大的反响。1760年首次译成德文后立刻引起广泛注意,扬的美学理论几乎可以说是18世纪70年代德国“狂飚运动”的直接思想渊源。年轻的作家如歌德、席勒、赫尔德、克林格、伦茨、伯格等起而向文学、政治、宗教以及世俗社会各个领域的一切清规戒律展开激烈的抨击。在挣脱传统信仰束缚的同时,他们拒绝现状的一切方面,极力倡导自由表达个体意志和个人的天才创造,因此“狂飚突进”运动又被称为“天才的时代”。
前浪漫主义时期,英国的情感小说、伤感诗歌、新的审美情趣以及原始诗歌的发现,越过英吉利海峡迅速风靡欧洲大陆。在英国,开明的言论自由传统有助于新思想的健康发展;另一方面,英国言论自由的社会氛围及其优秀的本土文学基础不需要德国人渴望的那种革命性变革。因此可以说,激烈的“狂飚运动”和德国浪漫主义运动中的极端主义都反映了德国人急切追赶和超越他国的雄心壮志。然而在法国情况与上述两国都不相同:人们既怀有对本土古典主义作家和作品的自豪感,而对异邦观念的好奇心又促使人们渴望出现一种新的局面。于是浪漫主义运动兴起之前的欧洲历史不仅阐释了浪漫主义的整体意义,也规定了不同国家浪漫主义的不同特征。
(待续)
注释:
〔1〕格里尔森:《英国文学的背景》1923年版,第256页。
〔2〕F.施莱格尔:《古代和现代文学史》慕尼黑1961年版,第284页。
〔3〕卡莱尔:《论文汇编》伦敦1890年版,第三卷,第71页。
〔4〕参见彼得·昆内尔:《英国浪漫主义文学与绘画,1717 -1851》。
〔5〕卡西勒:《国家的神话》耶鲁大学出版社,1946年版,第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