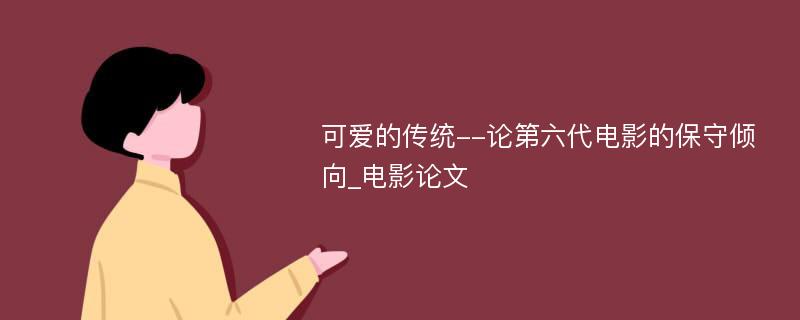
可爱的传统——论“第六代”电影中的保守倾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保守论文,倾向论文,第六代论文,传统论文,可爱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叙事是作者向读者传达知识、情感、价值和信仰的一种独特而有力的工具,实际上 ,认为叙事的目的是传达知识、情感、价值和信仰,就是把叙事看作修辞。”(注:《 作为修辞的叙事》P23,[美]詹姆斯·费伦著 陈永国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5月 。)
电影是以影像为手段的叙事,在传达知识、情感、价值和信仰上具有独特的优势,其 修辞方式具有叙事的共性,也有其特性。本文试图从读者反应和叙事修辞中倚重的价值 体系两者的关联,把握“第六代”电影的文本现象。
冲击当下社会的原始冲动
网上有一篇影片,是关于刘冰鉴的《哭泣的女人》,虽然这部影片在第五十五届戛纳 电影节上受到好评,评审团历史上第一次授予主演廖琴以评委会特别奖,以表彰她精湛 的表演。这篇文章还是认为《哭泣的女人》是一部让人感到恶心的影片,理由是女主角 竟然能够在情人的怀里为丈夫哭泣,而在监狱里又向劳教干部出卖自己的肉体,在丈夫 死后还能继续哭丧职业,收取大把的钞票,总之,作者在这部影片里根本看不到社会和 人性美丽的一丝一毫,便认为影片虚假造作,不符合现实。
无独有偶,网上的另一则评论,关于张元的《回家过年》,认为张元这部影片是招安 之作,文章对两人回家时一路上遇到的好人好事尤其感到不满,比如除夕夜机动车的司 机怎么可能把车费从三元降到二元呢?没这么好的人,更别说有女警官这样的好心人, 放着年饭不吃陪着犯人回家的,“这部影片对于生活的粉饰以及对于人性卖好一面的表 现已经到了不顾现实,不求真实的地步。”(注:《砖之看<回家过年>》银海网。)这种 声音我们听到的也许比前者更多一些,很多“第六代”导演在体制内拍片时都会受到如 此的诘难。
这两个例子虽然是观众观赏影片时当下感受的两个极端,他们一边已经厌倦了高大全 式的好人,一边也不喜欢一无是处的所谓坏人,尤其当这个人是影片的主人公时,但却 说明了电影的叙事修辞都在这一点上遭遇了失败。
导演总是希望观众能认同自己的人物,反过来说,很少有编导会把自己的主人公故意 设置成一个令人恶心的人物,可爱的人物总是容易引起观众的同情,然后进而认同编导 所想要传达的价值观念。于是问题就从这里产生,首先编导想要传达什么样的价值观念 ,其次什么样的人物是可爱的?前一个问题比较明确,编导都想在影片中表达一定的价 值观念,剩下的问题是这个价值观念的表达是明确的还是模糊的。后一个问题需要观众 和编导共同完成,这样问题就更为复杂,观众和编导能达成共识吗?如果能,那么是在 什么基础上?还有,第一个问题和第二个问题之间又存在着什么样的关联呢。实际上, 这正是影片的修辞策略和修辞目的所要研究的。
那么“第六代”导演试图通过影片传达什么样的知识、情感、价值或信仰呢?
“不同于某些后现代论者乐观而武断想像,在笔者看来,现有的‘第六代’作品多少 带有某种现代主义、间或可以称之为“新启蒙”的文化特征。”(注:《雾中风景:初 读第六代》银海网,戴锦华。)
而现代主义在艺术上表现的首要特征就是一种焦虑,否定当下的社会生活,同时也无 法提供新的价值信仰标准,人们在苦苦寻找、彷徨。“第六代”导演的早期作品中的确 明显存在着这样的倾向。在初期的《北京杂种》《头发乱了》《周末情人》《长大成人 》等影片中,“第六代”导演用摇滚这一烦躁的艺术形式表达他们内心的无方向的冲动 。
而且在“第六代”的影片中可以找出这样一些粗俗的段落,这些段落对很多观众的触 动就像《哭泣的女人》对那位观众的触动一样,让人很不舒服。比如,《小山回家》的 前半段,小山和朋友一起喝酒时有一大段对话充满了饭桌上的粗俗言词。在《极度寒冷 》里则有吃肥皂这样“令人恶心”的长长的段落,在《十七岁的单车》里殴打的段落。 这些段落的含义虽然千差万别,但是特点是浓墨重彩,超过了一般叙事的长度,几乎让 人们感到导演是否有嗜痂之癖。粗俗,意味着脱离了原有的、社会公认的道德规范,随 地大小便,说脏话,打架斗殴……都是不文明的表现,正是这些敏感段落必须引起我们 的注意,它们打开了生活的另一扇窗,显示出日常生活的另一种形式,这是导演的一种 姿态,对影片人物的一种修辞,“第六代”的导演正是从这里对当下社会实施他们的现 代主义的艺术策略。“现代艺术触到了普通公民的一个或好几个痛处,而这些痛处是他 们完全没有意识到的。一个普通公民越是对现代艺术感到恼羞成怒,也就越是暴露出现 代艺术涉及到他本人以及他的文明。”(注:《非理性的人》P43,[美]威廉·巴雷特著 ,杨照明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2月。)
以上冲击当下社会的原始冲动的直接表现,让人联想起布努艾尔的《一条安达鲁狗》 。“传统的现代主义试图以审美对生活的证明来代替宗教或道德,不仅创造艺术;还要 真正成为艺术——仅仅这一点即为人超越自我的努力提供了意义。但是回到艺术本身来 看,就像尼采表露的那样,这种寻找自我根源的努力使现代主义的追求脱离了艺术,走 向心理:即不是为了作品而是为了作者,放弃了客体而注重心态。”(注:《资本主义 文化矛盾》P98,[美]丹尼尔·贝尔著,赵一凡译,北京三联书店,1989年。)“第六代 ”电影人在这条路上走多么远,在冲击当下社会的同时,他们试图重建,张元认为,“ 我们这一代不应该是垮掉的一代,这一代应该在寻找中站立起来,真正完善自己”。( 注:《张元访谈录》郑向虹,转引自《雾中风景》,《雾中风景:初读第六代》银海网 ,戴锦华。)在后期作品中,他们试图以不同的姿态冲击同时也重建某些价值标准。与 此同时,他们还希望重建影片的魅力,获取更多的观众。
分析张元的《回家过年》、贾樟柯的《小武》、娄烨的《苏州河》、王小帅的《扁担 姑娘》、《十七岁的单车》、章明的《巫山云雨》、路学长的《非常夏日》等作品,我 们发现他们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放在了涉案题材上。
除了商业性考虑之外,罪犯应该是社会的边缘人物,主流电影通过这样的边缘人物的 毁灭或归顺,重建当下的社会秩序。而“第六代”导演显然是想利用他们去冲击当下的 社会秩序,这样必然导致与主流电影截然相反的叙事修辞策略。
回归传统的修辞策略
好莱坞经典编剧法则之一,主人公是否值得人同情。假如有人像反感《哭泣的女人》 那样反感导演的作品,那导演的一切努力在这个人身上就完全白费了,怎样建立值得人 同情的人物呢?
策略一 用传统美德修饰罪犯。
《巫山云雨》的麦强是个很有意思的人物,在旅馆老板的眼里他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 强奸犯,他和女主人公陈青素不相识,居然听信同伴的玩笑,把她当作妓女和她发生了 关系。这是影片中最强烈的动作,电影试图用这个动作去打破沉闷的小城气氛,让人们 有所期待。而整体故事则是围绕这一动作究竟是否属于犯罪这一悬念而展开。这一动作 本来可以成为一次对整个社会道德层面上对性的压制的挑战,但最终变成了一次浪漫的 一见钟情。在一开始麦强就被塑造为坐怀不乱的柳下惠,他拒绝了真正的妓女的诱惑, 从窗口落荒而逃。普通观众一定会被他遵守传统道德的贞节行为而打动,从心理上认同 这个人物。而影片始终没有展现他和陈青的戏剧性的第一次,避免了去塑造麦强内心渴 望性释放的过程,因为性本身整个社会都羞于谈起。
在《小武》中,如何让一个偷了那么多人,害得那么多家庭落入绝境的小偷让人产生 同情心,以至于观众最后看到他被铐在路边时,不会拍手称快,反而为他扼腕叹息呢? 首先,他是一个重义气的人,仁义礼智信,他不忘兄弟情。其次他是个浪漫的依然相信 爱情的人。第三,他是一个孝顺父母的人。总之,他是集传统美德为一身的人,同时也 在社会上碰得头破血流的人。这样的人观众能不同情吗?观众能不对警察把他铐在路边 展览示众这个行为产生强烈的反思吗?在影片中意识形态始终以冷漠的广播伴随着传统 道德的楷模小武,毫无个性的警察的表现尽量让观众感情的天平向小武倾斜,这样的 叙事策略是非常明显的。
《过年回家》里的女主人公的罪犯也被描述为本质淳朴、只是一时义愤冲动的过失杀 人,而被害者却是内心冷漠,良知泯灭的极端功利主义者。这就为以后主人公被家庭接 受,被观众接受做好了铺垫。
在《苏州河》中,马达本来就不愿意参与绑架行动。
《扁担姑娘》里的高平对同乡扁担东子的关照。
走得最远的《十七岁的单车》里的城里人阿健在殴打阿桂时并不是主谋,而他自己也 受到了其他学生的排挤。
在“第六代”导演的作品里,越出社会规范的主人公的道德品质都向传统看齐,犯罪 不是过失,就是被描述成出于无奈。他们在传统中寻找资源,完成对人物的修辞,以引 起观众的同情。
策略二 用纯洁修饰风尘女子
在《苏州河》里,马达跟随美美回到河边住所,美美对他说“我不是你要找的那种人 。”
在《扁担姑娘》里,阮红因高平给她钱而谴责他“你用钱买我”。陷入了歇斯底里的 状态。
策略三 用浪漫的爱情超越世俗
王全安的《月蚀》讲述了一个小伙子对一位女子的痴心。在这个女子死后,他又碰上 了跟她长得一模一样的女子,这个女子的男友却爱上世俗的和秘书有着暧昧关系的小老 板。
马达对牡丹的执着寻找成为《苏州河》里最主要的动作,结尾也给观众以两人殉情而 死的感觉。
《巫山云雨》中的结尾,陈青不承认麦强是强奸,麦强游过了长江,和陈青拥抱在了 一起,他们的期待终于有了结果。
策略四 用淳朴的农村对抗妖魔般的城市
在王小帅的影片中这一点尤其突出,在《扁担姑娘》里的小东,在《十七岁单车》里 的阿桂,都代表着来自农村的原始的淳朴品性,他们木讷寡言,以此和城市形成鲜明的 反差。
《巫山云雨》中的麦强干脆就住在信号台上,几乎和人间隔绝了来往。
只有在《小武》中,贾樟柯没有给中国的农村以怀旧的光环。
“与‘第五代’那种民俗化、乡土化、历史距离化的策略不同,他们大多是重现当代 城市生活和远离灾变传奇的身边日常经历。”(注:《在夹缝中长大——中国大陆新生 代的电影世界》,尹鸿,银海网。)
这也许是“第六代”之所以成为一代的最显著的标志。农村作为一个缺席的在场出现 在“第六代”电影作品中。而城市本身却都是以一种令人可怖的形象出现,毫无亲和力 。在《小武》里的汾阳,到处是即将被拆毁的房屋。在《苏州河》的片头,城市的河流 被剪辑地支离破碎。从某种意义上说,在“第六代”的电影作品中,城市是被妖魔化了 ,这的确在某种程度上迎合了西方对中国的想像。
这些修辞策略具有明显的回归传统的倾向。但是这并不表明,“第六代”的价值观建 立在怀旧的传统价值观念上。在冲击被金钱所污染的当下社会时,他们在用真诚的心灵 在寻找生活的意义,想重新建立生活的意义。这使他们的影片与以张艺谋为代表的“第 五代”、新主流电影甚至与以张杨、施润玖、霍建起、陆川等为代表的新生代商业电影 相区别,让观众咀嚼生活在悲观苦涩中。也正因为如此,他们的叙事呈现出茫然和断裂 的状态。
叙事的茫然和断裂
对当下社会强烈的否定性感受使“第六代”电影人必须对此作出批判,这是他们的原 始冲动。而在电影观念上他们从现代主义电影大师那取得了一些理论经验和方法。在这 个基础上他们开始了自己的写作行为。
但是毕竟西方的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问题,和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问题有着根本 的不同。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虽然同样是现代化的方案,但西方是宗教信仰和以工具理 性为依托、以科学崇拜为核心的实用主义功利主义之间的矛盾。而全球化趋势中转型期 的中国则以传统文化的逐渐丧失为特征,现代化本身带来了诸多问题。如果说八十年代 的“第五代”导演还能祭起个性自由的大旗向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和当下强大的意识形 态发起攻击的话。九十年代就显得更为复杂。
“八十年代当代中国文化尽管林林总总,但它毕竟整合于“现代化”、对进步、社会 民主、民族富强的共同愿望之上,整合于对阻碍进步的历史惰性与硕大强健的主流意识 形态的抗争之上;而九十年代,不同的社会文化情势来自于从冷战时代变得繁复而暧昧 的意识形态行为,主流意识形态在不断的中心内爆中的裂变,全球资本主义化的进程与 民族主义和本土主义的反抗,跨国资本对本土文化工业的染指、介入,全球与本土文化 市场加剧着文化商品化的过程。”(注:《砖之看<回家过年>》银海网。)
“第六代”电影导演的确在其中迷失了方向,他们要肩负起对当下社会的批判使命, 完成启蒙的文化使命,但手中根本没有武器,没有可供他们发出特别的声音的有力的价 值资源。他们在修辞上倚重传统道德伦理和浪漫主义时代才具有的爱情,是无奈,也是 本能。他们在既不了解传统也不了解当代的情况下开始了他们的叙述。他们陷入了矛盾 之中。他们对传统没有什么真正坚定的信心,对他们来说,传统已成明日黄花,已经负 担不起如此的重任。所以没有办法像张艺谋那样拍摄出《我的父亲母亲》那样的怀旧影 片和张杨的《洗澡》。
而他们所要攻击的目标——城市同样也是抽象的,不被人所认同。在他们向观众诉说 时,没有强有力的价值观念和信仰支撑,显得底气不足,故事的解决不是自我否定,就 是依靠相像。
由于缺乏价值信仰理念的支持,冲突都不能贯彻到底,他们的故事不能够保持足够的 一个半小时的紧张程度,叙事呈离散状态。
《小武》中让小偷梁小武承担起传统化理道德的维纪者的职责,我们看到他的努力是 如何被撞得粉身碎骨。贾樟柯虽然忠实地记录了一切,但就像是意大利新现实主义作品 《偷自行车的人》的续集。在叙事结构上这是三个故事的拼贴。主人公就是在做着与时 代最不符合时宜的事,他想和过去朋友重温旧梦,想和妓女谈恋爱,想在家乡父母那寻 找安慰,简直是异想天开。他每一次动作的发出不到一个回合就败下阵来。冲突根本没 有上升的空间。
在《苏州河》里,娄烨叙事中的不确定性和断裂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对故事的发 展基本上放弃了控制,不再追求表面的合理性。在故事进入时和结束时,他采用了第一 人称作为视点,但在中间又用了马达的视点和全知视点,全面解构了影片的可信度。如 果用常规的叙事状态,这是一个老掉牙的故事,但以这样的叙述方式出现,“我”作为 第一人称叙事者是对马达最后的浪漫的否定,就是对传统的否定。老故事正是这样显出 了不同的意味。在这一点上娄烨好像开始放弃了一种执着的追求,从而使自己的电影开 始挤入后现代的行列。但我们可以发现,这种放弃对娄烨是多么无奈。
自我否定往往走向死亡,这也是“第六代”电影涉及死亡题材那么多的原因。(注:参 见郝建《无法命名的一代》,银海网。“第六代导演的叙事有没有某种深层的共性呢? 在仔细研读了他们的作品之后,我发现至少有一个颇带几分共同性的主题在他们的叙事 文本中占据极其重要地位。这就是被称为文学艺术永恒主题之一的“死亡”。我看到,在最近的一些青年导演的作品中,不约而同地出现了某种“死亡”的主题。像《月蚀》《苏州河》《安阳婴儿》《非常夏日》,都是对于那个人死了没有在叙事上的有模糊解释或堕入梦幻。与第五代的在对父辈的崇敬和逝去的情结中纠缠不能离去不同,第六代电影中主人公与死者都是同辈关系,大多是恋人关系和亲密的关系。”)
二是想像。《巫山云雨》中的结尾带有明显的魔幻色彩,这部电影以一个有力的突转 结束了故事,提高了故事的戏剧强度,没有麦强游过长江和陈青相会,故事必定与生活 一样平淡无奇。
而《花眼》里解决故事的方案干脆就是让红星在他们的额头上出现,这种转变的游戏 性也只能被看作对生活的想像性解决,虽然好玩但毫无力度,在叙事上走上了放任自流 。
当主流意识形态保持着保守姿态,“第五代”导演也趋向保守的时候,“第六代”导 演有没有可能发出真正的新声音呢?回到文章开头所讲的两部影片。
《哭泣的女人》让观众对人物不存在丝毫的幻想,这里没有脉脉含情,只有直截了当 。让我们接触到了人的实在,她让人恶心,就像戏剧大师布莱希特的《大胆妈妈和她的 孩子们》,在这样的基础上我们也许能抛弃幻想,建立起对生存的真实感受。
《回家过年》中同样没有任何理想主义的色彩,张元让我们感到现代社会中宽容的重 要,绝望的困境是我们生活的起点,也许在这样的基础上我们活得会比以前更好。在这 部影片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些许的宗教意味,如果走得更远一点,去除对女主人公道德美 化的修辞策略,回家过年的罪犯原来就是十恶不赦的恶棍,那影片救赎的意味是不是会 更浓呢?
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何处才是立脚的根基?可爱的传统固然能博取观众的同情,但 简单地回到传统显然不能解决任何问题,“第六代”电影怎样才能找到启蒙话语的价值 资源,走出这个矛盾?也许正是因为他们的执着才把自己放在了一个无比尴尬的境地?我 们期待他们走出这样的困境。
标签:电影论文; 第六代导演论文; 哭泣的女人论文; 十七岁的单车论文; 巫山云雨论文; 小武论文; 回家过年论文; 剧情片论文; 中国电影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