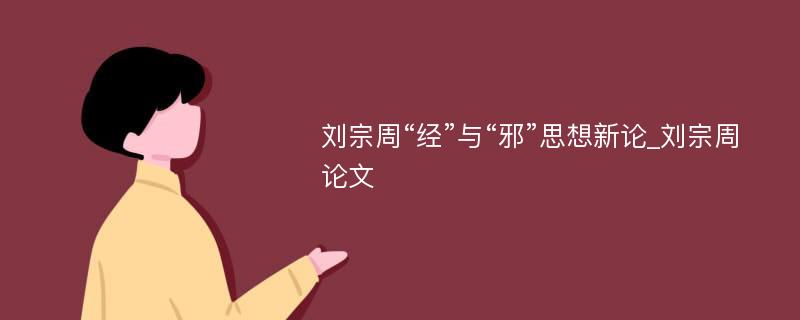
刘宗周《人谱》“过(恶)”思想新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论论文,思想论文,刘宗周论文,人谱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刘宗周(1578-1645),字起东,号念台,浙江省山阴县人,后世学者尊为蕺山夫子,晚年“凡三易稿”①撰著的《人谱》,是其开显哲学思想主旨的最重要文本②。《人谱》分正篇(包括《人极图》和《人极图说》)、续篇(《证人要旨》、《纪过格》、《静坐法》和《改过说》)以及蕺山未竞而由其子刘汋补充完成的《人谱杂记》③。“过(恶)”思想是《人谱》重点关注的问题之一,已有学者展开论述④。《人谱》将人的“过(恶)”划分为“微过”、“隐过”、“显过”、“大过”、“丛过”和“恶”诸形态,并深刻阐发它们的产生缘由及思想实质,本文即对此做详细梳理。从现象言,《人谱》关注人生存世界中具体的“过”与“恶”的形成与危害;而其实质,则是探索意义世界中“本心”的客观性和常在性,是对人性本质的深切把握。
一、“独”与妄心之微过
“心”有“天命之性”,即标示“继善成性”之生生不已之义的“独”。“独知之地”至微至危,稍有不“慎”,离“独”而生“妄”,是谓“微过”⑤。“独知之地”受病即函后来诸过,虽“微”却影响深远,故谓“物先兆”。
“独”内蕴三层意涵。其一,“即心即独”。《证人要旨》“凛闲居以体独”章云:“学以学为人,则必证其所以为人。证其所以为人,证其所以为心而已。自昔孔门相传心法,一则曰慎独,再则曰慎独。夫人心有独体焉,即天命之性。”(《人谱》,第5-6页)“心有独体”表明“独”不离“心”。“心”是“所以然”之理和“所当然”之道:“无善而至善,心之体也。(即周子所谓太极,‘太极本无极也’。统三才而言,谓之极。分人极而言,谓之善。其意一也。)继之者善也。(动而阳也,‘乾知大始’是也。)成之者性也。(静而阴也,‘坤作成物’是也。)”(同上,第3-4页)“心”生生不已而万物成,万物自然有“性”,如《学言》所云:“一元生生之理,亘万古尝存,先天地而无始,后天地而无终。浑沌者,元之复;开辟者,元之通。推之至于一荣一瘁、一往一来、一昼一夜、一呼一吸,莫非此理。天得之以为命,人得之以为性,性率而为道,道修而为教,一而已矣,而实管摄于吾之一心”(《全集》二,第374页)。“心”继善表明生生不已之“动”的过程,“动而阳”;成性表明生生不已之“静”的效果,“静而阴”。而“独”则是对“心之体”动静互蕴、即隐即显、即微即著特性的把握:“独者,静之神、动之机也”(同上,第361页);“莫见乎隐,亦莫隐乎见,莫显乎微,亦莫微乎显,此之谓无隐见、无显微。无隐见、显微之谓独”(同上,第392页)。离“心”说不得“独”,故“即心即独”。在“即~即~”关系中,前者“即~”是后者“即~”的基础,后者“即~”是前者“即~”的落实与开显,二者非“二分独立”,而是“一体圆融”。
其二,“即性即独”。《学言》云:“‘天命之谓性’。以其情状而言,则曰‘鬼神’;以其理而言,则曰‘太极’;以其恍兮惚兮而言,则曰‘几’、曰‘希’;以其位而言,则曰‘独’”(第383页)。蕺山以“独”为“天命之性”。何谓“性”?《原性》曰:“盈天地间一性也,而在人则专以心言,性者,心之性也。心之所同然者,理也。生而有此理之谓性,非性为心之理也。如谓心,但一物而已,得性之理以贮之而后灵,则心之与性,断然不能为一物矣。”(《全集》二,第280页)“性”不能用“具体”之言语概括其内容,但“因心而名”,“性者,心之性”。“心”因生生不已之义而成为事物存在的意义者和主宰者,就“生生不已”言,“心”天然、自然、自在蕴有,故说“心之理”;就事物之意义和价值为“心”所赋予,“心”生生不已之义蕴涵于人事物而言,三者无不含蕴了这样的“理”,无不透过这样的“生生不已”而实现自己的“生生不已”,以此挺立主体性、自觉性和能动性,诚如《学言》所说,“性者,生而有之之理,无处无之。如心能思,心之性也;耳能听,耳之性也;目能视,目之性也;未发谓之中,未发之性也;已发谓之和,已发之性也”(第418页)。同时,“性”是彰明“心”的路径。因多元之“性”的显明,“心”生生不已之义才得以开显。就“性”客观存有讲,“性”非因“心”而“始有”,只是因“心”而“得名”,故“性”为“天命之性”;就“性”在事事物物身上显明讲,“心”作为意义者和主宰者的主体地位是客观存在、自然如此的。“心”有生生运旋之“性”,即“独”;就“独”作为“心”之“性”言,可视其为“天命之性”。故,“即性即独”。
其三,“即独即慎”。“独”动静无端、显微无间,唯“慎独”挺立“心”的自然随性特性。《学言》云:“一理浑然,名言莫措,并其德且归之不显,而百辟已刑之。当此之时,内外两忘而化于道,只是个笃恭而天下平,慎之至也。……独体只是个微字,慎独之功,亦只于微处下一着子。”(第386-387页)“慎独”是对“独”的谨从和随顺,《大学古文参疑》即言,“独之言自也;慎者,敬德也”(《全集》一,第613页)。“慎”之过程以“独”为主宰,“慎”与“独”为“即独即慎”的关系,所“慎”必然为“独”,“独”须有“慎”而彰明。“慎独”之功约束、规范“个体自我”,使人合德符节,实现“本心”的自然而然。
“独”体至微至纯,稍有“不慎”,即生“妄”。《学言》云:“人心一气而已矣,而枢纽至微,才入粗一二,则枢纽之地霍然散矣。散则浮,有浮气,因有浮质;有浮质,因有浮性;有浮性,因有浮想。为此四浮,合成妄根;为此一妄,种成万恶。”(第435页)“四浮”合成“妄”,则“信道不笃”(《遗编学言》,《全集》二,第475页)。且“妄”又“函后来种种诸过”,藏在未起念以前,不可名状,故曰“微”,“最难解,直是无病痛可指”(《人谱》,第10页)。概言之,“妄”有两方面特征:其一,“妄”为“真”之似。《证学杂解》云,“妄”为“真之似”,“依真而立,托真而行”(《全集》二,第262页)。“妄”托“真”而行,则有“妄心”,进而有“妄”形、“妄”解识、“妄”名理、“妄”言说、“妄”事功、“妄”世界。其二,“妄”者“伪”。《证学杂解》还说,人心“妄”根受病则有“欺”,“欺与谦对,言亏欠也”(同上)。“欺”即“亏欠”。因“亏欠”,人不能尽“万物皆备”之道:“万物皆备,而后成其所谓我。若一物不备,我分中便有亏欠,一物有亏欠,并物物皆成渗漏。如人身五官、百骸,有一官一骸之不备,则众官众骸皆不成其位置。故君子一举足而不敢忘敬也,一启口而不敢忘信也”(《学言》,第429页)。“敬”、“信”即是“诚”:“一者,诚也;主一,敬也。主一即慎独之说,诚由敬入。”(同上,第442页)个体之“心”自“欺”而不能“谦”敬“本心”,造成“诚”体亏欠、“独”体走作。“诚”与“伪”对,故“妄”而生“伪”(《人谱》,第10页)人有“伪”,则挟智任术,色取仁而行违,进之则为乡原,“似忠信,似廉洁,欺天罔人,无所不至,犹宴然自以为是,全不识人间有廉耻事”(《证学杂解》,第263页)。
二、“念”与七情之隐过
“独”是对“心之体”动静无端、显微无间状态的描述,但若个体之“心”不能专注于此,必动而生“念”,势必成“过”。《证人要旨》“卜动念以知几”章曰:“独体本无动静,而动念其端倪也。动而生阳,七情著焉。念如其初,则情返乎性。动无不善,动亦静也。转一念而不善随之,动而动矣。”(第6页)“动而无静”则有“念”,因“念”而“情”离乎“性”,造成“隐过”之“七情”:溢喜、迁怒、伤哀、多惧、溺爱、作恶、纵欲。
“心”本无善恶,只是“至善”:“无善而至善,心之体”。“至善”就是“善”,著不得人为:“有善,非善也,有意为善,亦过也”(《书》,《全集》三,第319页)。“善”具有自然性和自在性特征,及知善而行、见善而迁、省过而改的能动性和自觉性特征。“善”非有意而为,故说“无善”;“善”又无时不行、无时不显,生生不已,故说“至善”。“至善”之“善”非与“恶”对待之具有道德意义的“善”,而与“极”相当,具“本体”义,如《大学古记约义》言:“盖云善本不与恶对耳。然无对之善,即是至善,有善可止,便非无善。其所云心体,是‘人生而静’以上之体,此处不容说,说有说无皆不得”(《全集》一,第646-647页)。“心”是“人生而静”之“体”,“说有说无皆不得”。若有意为善,则“动而无静”而生“念”,如《学言》云,“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欲动情炽而念结焉……念之为心祟也,如苗有莠”(第417-418页)。有意为之“善”破坏了“心”体的自然自在性,从而“起念”,是谓“心祟”。
何以起“念”?“心”是“天地之仁”的代名词,落脚点在“人”,《证学杂解》即言:“仁者,人也,天地之心也。人得天地之心以为心,生生不息,乃成为人,故人与天地同体,而万物在宥”(第261页)。但是,整体之“人”由多元个体之“人”张显,而个体之“人”之个体之“心”面对复杂的社会环境、物质利益、事件冲突、道德抉择而具有不同的感悟方式与体察视域,彰显出“个体性”和“差异性”,造成“有善有恶”之多元“个性”并存。“念”正是对个体之“心”变幻不测性的揭示。《治念说》言:“欲为善则为之而已矣,不必举念以为之也;欲去恶则去之而已矣,不必举念以去之也。举念以为善,念已焉,如善何?举念以不为恶,念已焉,如恶何?又举一念焉,可乎?曰:念念以为善,穷于善矣,如念何?念念以不为恶,穷于恶矣,又如念何?”(《全集》二,第316页)“念”即是“有意”为善、“有意”去恶,其开显的“好”、“善”流变为“伪”:“为善而取辨于动念之间,则已入于伪”(同上)。个体之“心”本来至善、好善恶恶,但多此起“念”,便遮蔽其“真性”。
“心”有仁义礼智“四端”,且自然彰显为喜怒哀乐“四德”。仁义礼智“四端”一似好家当,使人“无由入禽兽一途”(《学言》,第469页)有此“性”则必有其“情”,《学言》即云:“恻隐,心动貌,即性之生机,故属喜,非哀伤也。辞让,心秩貌,即性之长机,故属乐,非严肃也。羞恶,心克貌,即性之收机,故属怒,非奋发也。是非,心湛貌,即性之藏机,故属哀,非分辨也。又四德相为表里,生中有克,克中有生,发中有藏,藏中有发。”(第421页)仁义礼智“四端”与喜怒哀乐“四德”圆融一体:其一,“即性言情”。作为天然、自在如此的“性”之四端,必有四德之自然如此、自在如此之显发,不杂“人伪”,诚如《商疑十则·答史子复》言:“天无一刻无春夏秋冬之时,人无一刻无喜怒哀乐之时。……夫喜怒哀乐,即仁义礼智之别名;春夏秋冬,即元亨利贞之别名”(《全集》二,第345页)。离“性”则无“情”,故即“性”言“情”。其二,“指情言性”。喜怒哀乐之“情”本来自在如此,与“心”本真“诚通诚复”。“心”自觉运旋而显露于外,“情”中自有其“性”,如《学言》所论:“言语既到快意时,自当继以忍默;意气既到发扬时,自当继以收敛;愤怒嗜欲既到沸腾时,自当继以消化。此正一气之自通自复,分明喜怒哀乐相为循环之妙,有不待品节限制而然”(第414页)。因此,喜怒哀乐之“四德”为仁义礼智之“性”的彰显,其“发用”是至善之“心”体之自然流行,“喜怒哀乐,性之发也;因感而动,天之为也”(《学言》,第381页)。
个体之“心”因“念”起“欲”,“四德”演变为“七情”之过。“心”无内外,“浑然不见内外处,即天理”,但个体之“心”有所向,“向内向外皆欲”(《学言》,第370页)。“欲”表现多样:重之为货利,轻之为衣食;浓之为声色,澹之为花草;俗之为田宅舆马,雅之为诗琴书画;大之为功名,小之为技艺(同上,第400-401页)“欲”是“心病”,“出手展足不免时时掣肘,当大利害,便全身放倒”(同上,第434页)。因“欲”,自然纯粹的“四德”之“情”纷然错出为“喜怒哀惧爱恶欲”之“七情”,“离乎天而出乎人”(《学言》,第399页)。
“七情”之“过”是个体之“心”因物感动而造成的“性情之变”,“人事之感召使然”(《学言》,第396页),“藏而未露”,故为“隐”过(《人谱》,第11页)。不过,“隐过”建基于“微过”之“妄”,“妄”不改,因“妄”而生之“念”便转生为“七情”,“(隐过)仍坐前微过来,一过积二过”(同上)。“过”从“微”至“隐”,一步步遮蔽“本心”之澄明。
三、“诚”与九容之显过
《证人要旨》“谨威仪以定命”章曰:“慎独之学,既于动念上卜贞邪,已足端本澄源。而诚于中者形于外,容貌辞气之间有为之符者矣,所谓‘静而生阴’也。”(第7页)内有澄明之“本心”,外必有自觉之“践行”,所谓“诚于中形于外”。但个体之“心”会因“放心”而生“九容”之“显过”(《人谱》,第11页)。
人禀有“本心”,容貌辞气自有“当然之则”,即“命”定。《易衍》说:“顺人而人,故曰‘道’;道本然,故曰‘性’;性自然,故曰‘命’。”(《全集》二,第135页)“心”内蕴的“天命之性”必由对应的“动作礼义威仪之则”(《人谱杂记》,第31页)张显。张显“过程”即“诚”。“诚”有三层内涵:其一,“诚”体本天。“诚”为至善,本“无为”。《学言》云:“意根最微,诚体本天;本天者,至善者也。以其至善,还之至微,乃见真止,定、静、安、虑,次第俱到,以归之得,得无所得,乃为真得。”(第453页)“诚”为“心”之“天命之性”,惟其“无为”,方由“至善”而彰显“至微”,落脚于“无所得”之“自得”。诚敬遵行“本心”,自能保持“本心”之澄明;“自得”之“得”方能使内无外无“亏欠”。内有“圆满”,其外显自然“无处不圆满”(同上,第453-454页)。其二,“诚”蕴工夫。“诚”自身实现本体与工夫的圆融统合。《答史子复二》信指出:“夫‘真切笃实’非徒‘行’字之合体,实即‘诚’字之别名,固知‘知行’是一,‘诚明’亦是一。”(《全集》三,第385页)一方面,“真切笃实”为“诚”。“真切笃实”既描述事实,反映“心”之诚实无欺性和真实无妄性;又描述过程,反映“心”真实无妄地、诚实无欺地体知自我、体认万物的能动性和自觉性。另一方面,“诚明合一”为“诚”。“诚”既是“心”上做工夫的状态,是“道心”的体露;又是“心”上做工夫的过程,是人去“探求”自我的纯真。体露“道心”,是“明”心,使心“澄明”;“探求”纯真,则是心“诚实无欺”性的自在显明。故蕺山论曰:“本体只是这些子,工夫只是这些子,并这些子仍不得分此为本体,彼为工夫。”(《刘宗周年谱》,第398页)其三,“诚”则必形。作为“天命之性”,“诚”是“心体”的自然要求和必然步骤;作为工夫,“诚”实现本体与工夫、自在“本心”与自觉礼义威仪的融贯。因此,“诚”于中必“形”于外,《学言》即云:“诚则必形。有诚者,天道之形。有诚之者,人道之形。天道之形,见乎蓍龟,动乎四体是也。人道之形,啐面盎背,施于四体是也”(第402页);《人谱》亦言:“天命之性不可见,而见于容貌辞气之间,莫不各有当然之则,是即所谓性也。故曰威仪所以定命”(第7页)。因此,蕺山将施于“容貌辞气”的“人道之形”细化为“九容”之“当然之则”,即:足容当重,无以轻佻心失之;手容当恭,无以弛慢心失之;目容当端,无以淫僻心失之;口容当止,无以烦易心失之;声容当静,无以暴厉心失之;头容当直,无以邪曲心失之;气容当肃,无以浮荡心失之;立容当德,无以徙倚心失之;色容当庄,无以表暴心失之。(同上)
“心”之“诚”可通过“九容”将“天命之性”彰明无遗,但个体之“心”会因“放心”而生“九容”之“显过”。所谓“放心”,《求放心说》言:“仔细检点,或以思维放,或以卜度放,或以安排放,或以知故放,或以虚空放,只此心动一下,便是放。所放甚微,而人欲从此而横流,其究甚大”(《全集》二,第304页)。“放心”是有所欲念的“心”。看个体之“心”是否为“放心”,即是看其是否与人们所共同挺立的规范和原则——“九容”之当然之则——相呼应。个体之“放心”必通过容貌辞气显明,即足容上箕踞、交股、大交、小交、趋、蹶;手容上擎拳、攘臂、高卑任意;目容上偷视、邪视、视非礼;口容上貌言、易言、烦言;声容上高声、谑、笑、詈骂;头容上岸冠、脱帻、摇首、侧耳;气容上好刚使气、怠懈;立容上跛倚、当门、履阈;色容上令色、遽色、作色,等等。(《人谱》,第11-12页)
不过,“九容”之过与“七情”之过相交融。《纪过格》言:“九容之地,即七情穿插其中”(第12页)。“九容”之每一容都有“七情”内蕴其中,且每一容之下的“每一过”都会因“七情”而引起。如蕺山举例,“喜”会带来“足容”之过之箕踞、交股、趋、蹶,那么,怒、哀、惧、爱、恶、欲亦会如此。据此类推,“九容”与“七情”交叉引起的“过”将达二百零三种。此时之“过”,已非“藏而不露”,而是“大显其道”。
四、“五达道”与五伦之大过
人在成熟自然生命的同时,必然要成熟意义生命,而意义生命即是由系列“关系”铺就,诚如《处人说》所言:有生以后,人身属之父母;及其稍长,有兄弟与之比肩;长而有室,有妻子与之室家;至于食毛践土,君臣之义,则无所不在;朋友联合,虽属疏阔,而人生实赖以有觉。此五者,“合之称五伦,人道之经纶管于此”(《全集》二,第307页)。《证人要旨》以“五伦”为“五达道”:“父子有亲属少阳之木,喜之性也。君臣有义属少阴之金,怒之性也。长幼有序属太阳之火,乐之性也。夫妇有别属太阴之水,哀之性也。朋友有信属阴阳会合之土,中之性也。此五者,天下之达道也,率性之谓道是也。”(第7-8页)但是,五伦之道须时时践行敦笃,“畅于四肢,发于事业”,若不能力尽其分,便不能体悟其中自然之韵味、应然之规模,从而流变为“五伦主之”之“大过”(《人谱》,第12页)。
“五伦”为“天下之达道”,为“心”之“诚”。《人谱杂记》曰:“右记五伦,学问随人,大做大是,小做小是,总之,不远于一诚者皆是。”(第51页)“五伦”是“诚”达于事业的必然反映。但是,因前有微过、隐过和显过,过过相积,个体之人不能时时于“心”之“诚”处实现内外、显微间的融贯通畅,便会造成“五伦”之“过”。如,(1)父子类大过:非道事亲、亲过不谏、责善、轻违教令、先意失欢、定省失节、唯诺不谨,等;(2)君臣类大过:非道事君、长君、逢君、始进欺君(考校、筮仕钻刺之类)、迁转欺君(夤缘、速化)、宦成欺君(贪位、固宠)、不谨,等;(3)夫妇类大过:交警不时、听妇言、反目、帷薄不谨(如纵妇女入庙烧香之类)、私宠婢妾、无故娶妾、妇言逾阈,等;(4)长幼类大过:非道事兄、疾行先长、衣食凌竞、语次先举、出入不禀命、忧患不恤、侍疾不谨,等;(5)朋友类大过:势交、利交、滥交、狎比匪人、延誉、耻下问、嫉视诤友,等。(《人谱》,第12-13页)
蕺山对“大过”的分梳,意蕴有二:其一,“过”与“善”相对,知如何是“过”,便知如何为“善”。五伦作为人之本性,畅于四肢、发于事业,自然有合道德、合规范的具体表现。而这些表现,正是“过”之对立面。即是说,由“过”逆推便是“真”、“诚”,从“过”中能看到正当的、自然的、必然的五伦之则。因此,(1)“父子有亲”:以道事亲、亲过有谏、称善、无违教令、无意有欢、定省谨节、唯诺严谨,等;(2)“君臣有义”:以道事君、勿助长君、勿逢迎君、勿始进欺君、勿迁转欺君、谨言、干练,等;(3)“夫妇有别”:时时警告、勿听妇言、举案齐眉、帷薄谨严、无私宠婢妾、娶妾有合礼、妇言不逾阈,等;(4)“长幼有序”:以道事兄、勿疾行先长、衣食勿凌竞、勿语次先举、出入禀命、忧患体恤、侍疾有谨,等;(5)“朋友有信”:勿势交、勿利交、勿滥交、勿狎比匪人、勿延誉、不耻下问、尊重诤友,等。“繁琐”的道德规范之上是客观的人伦之“当然之则”和“应然之理”。人是特定文化语境下的人,当遵守特定的规范和伦常。以此,人方明晰何谓“人”、“人”当如何。
其二,“规范伦理”与“德性伦理”的圆融。蕺山详细罗列和分疏诸种形态的“过”,一层递进一层,一种比一种完备,实现“规范伦理”与“德性伦理”的融贯。所谓“规范伦理”,是依凭规范的伦理,以原则、准则、制度等规范形式为行为向导并视其为道德价值之根源的伦理。规范具有原初的价值意义,而德性则因其不确定性处于相对不重要甚至可疑的价值地位。而所谓“德性伦理”,是指出自个体德性的伦理,即以个体的德性为自因,德性伦理的实现过程是道德、伦理的主体化、个性化过程,是将外在的伦理要求内化为个体自身的道德品性、道德素质的过程⑥。蕺山对“过”的阐释,是以“本心”之诚明为逻辑起点,既把握了人之为人的内在规定性,又强调主体自我的道德践履,德性与规范圆融统合。
五、“物”与百行之丛过
“心”通过“知”与“能”而成为“物”的意义和价值的主宰。《人极图说》云:“无善之真,分为二五,散为万善。上际为乾,下蟠为坤。乾知大始,吾易知也;坤作成物,吾简能也。其俯仰于乾坤之内者,皆其与吾之知能者也。”(第3-4页)“心之体”具造化生生之理,事物之意义的存在、价值的彰明实是“心”的“对象化”,诚如《读书要义说》所言,“盈天地间,只是个生生之理,人得之以为心,则曰‘仁’,亦万物之所同得者也。惟其为万物之所同得,故生生一脉,互融于物我而无间,人之所以合天地万物而成其为己者”(《全集》二,第312页)。作为构成人生存世界的“物”,则是由“五伦”推演所成,《证人要旨》即言:“只繇五大伦推之,盈天地间,皆吾父子兄弟、夫妇君臣朋友也。其间知之明,处之当,无不一一责备于君子之身”(第8页)。生存世界诸“物”往往表现为与色食财气相照应的“百行”。于此,个体之人不能把持人“心”之纯真,必造成“百行”主之之“丛过”(《人谱》,第12页)。
“心”为“物”之本,“即心即物”。《学言》有云:“有万物而后有万形,有万形而后有万化,有万化而后有万心。以一心纳万心,退藏于密,是名金锁钥;以一恕推万恕,偏置人腹,是名玉钥匙。持匙启锁,强恕而行,但见邦家无怨,终身可行,止此一心,是名大统会。”(第431页)“心纳万心”之“纳”指“心”收摄“万心”,“心”为“万心”之“体”,“万心”是“心”之显露。“心”为“一”,但又落实于万物,故说“心有万分”,《大学古记约义》有言:“盈天地间皆物也,自其分者而观之,天地万物各一物也。自其合者而观之,天地万物一物也。一物本无物也。无物者,理之不物于物,为至善之体,而统于吾心者也。虽不物于物,而不能不显于物。耳得之而成声,目寓之而成色,莫非物也,则莫非心也”(《全集》一,第647-648页)。从“本根”之“意义存在”看,“心”外无道,“心”通由个体之人、万物而彰明;从“流行”之“多元存在”看,所有人、物皆为“心”之呈露,“心外无物”。
人是世间最难以把握的“东西”,“有一种说不出的道理,又有一种形容不得的头面,一齐和合在这里,吾强而名之曰‘人’”(《学言》,第433页)。“说不出的道理”构成“人”之为人的那个“所以然”,“形容不得的头面”构成“人”之为人的那些“容貌辞气”。人生活于自己所创构的文化环境之中,“随俗习非,因而行有不慊”(同上)。本来,人“心”“廓然而大公,物来而顺应,终身不动些子”(同上,第434页),却为“俗习”之“私”、“欲”遮蔽,“为习所转,一切捱排是非计较凡圣,恐都是习心”(同上,第476页);“每日间只是一团私意憧憧往来,全不见有坦然释然处,此害道之甚者”(同上,第382页)。其最终结果,个体人之所作所为,“非本心使然,已然走进‘伪’、‘欲’”(同上,第378页)。故“物”虽本是规范与德性的融贯,是“本心”的显露,但生存世界中的个体人的言行举止、百行诸业非皆能成其就为“物”,而流变为“丛过”。这主要有六类:(1)“谨独”关之过,如游梦、戏动、谩语、嫌疑、造次、乘危、繇径等;(2)“色”关之过,如床笫私言、蚤眠晏起、昼处内室、狎使婢女、挟妓、俊仆等;(3)“食”关之过,如饕食、憎食、纵饮、深夜饮、市饮等;(4)“财”关之过,如轻诺、轻假(我假人)、轻施、与人期爽约、多取、滥受、居间为利、献媚当途、躁进等;(5)“气”关之过,如谋风水、有恩不报、拒人乞贷、遇事不行方便(如排难解纷、劝善阻恶之类。)、横逆相报、宿怨等;(6)“学”关之过,如弃毁文字、雌黄经传、读书无序、主创庵院、拜僧尼、假道学等。(《人谱》,第13-14页)只是,“丛过”乃从“五伦”之过演变而来,诚如《人谱》所言:“百过所举,先之以谨独一关,而纲纪之以色、食、财、气,终之以学而畔道者,大抵者皆从五伦不叙生来”(《人谱》,第14页)。
“过”使人“心”受蔽。“微过”积而成七情之“隐过”,“隐过”积而成九容之“显过”,“显过”积而成五伦之“大过”,“大过”积而成百行之“丛过”,后过从前过而来,前过不改则积累为后过,过过相积,人离当然之“人”、应然之“人”越来越远。
六、“迷复”与成过之“恶”
有过不可怕,只要善于迁善改过,“便做成圣人”:“自古无现成的圣人,即尧、舜不废兢业”(《人谱》,第9页)。但是,人若遇过不改,便成“恶”;即便是迁善改过,若不能自“心”而“克念终始”,依然是“恶”。《纪过格》曰:“成过,为众恶门,以克念终焉。”(第13页)
迁善改过可“复”其“本心”,是谓“迷复”。《复卦》卦辞说:“复,亨。出入无疾,朋来无咎;反复其道,七日来复。利有攸往。”《复卦》“上六”爻辞曰:“上六,迷复,凶,有灾眚。用行师,终有大败;以其国,君凶。至于十年不克征。”《周易古文钞》释曰:“复至于上,又更端而示诫曰迷。未尝不复也,而不胜其迷。乃重云叠雾,暂露日光,随复随蔽,于是谬戾百出,大灾小眚,无所不备,何凶如之!虽然,尚可图也。用困勉之力,如行师然,决胜于往,无益反害,动为心痗,迷转得复,不之恤也。……近而复,故可喜也;而远复之复,尤大可幸也。”(《全集》一,第104页)《说文》解“迷”曰:“惑也。从辵,米聱。”《广雅·释诂》:“迷,误也。”《周易集解》引卢氏曰:“坤,臣道也,妻道也。后而不先,先则迷失道矣,故曰先迷。”卢氏以“迷”有“失”义。《韩非子·解老篇》曰:“凡失其欲往之路而忘行者之谓迷。”⑦“迷”是迷失“道”,蕺山以之为“更端”。而“复”,《杂卦传》曰:“复,返也。”《周易集解》引何妥曰:“复者,归本之名。”《释文》曰:“音复,反也,还也。”朱熹《周易本义》曰:“反复之复。”⑧“复”即“回来”、“返回”。蕺山以“复”为回“心”之义,“迷转得复,不之恤”。当然,“迷复”过程“重云叠雾,暂露日光,随复随蔽”,但“尚可图”,其要在“学”,《学言》即曰:“有剥即复,间不容发,此一点元阳,在天地间无一息间断。……今人皆所谓频复者,甚之迷复,迷复亦是学”(第495页)。个体之人须时时“借他人眼孔照自己肺肝”(同上,第367页),时时反观“心体”,“君子无日而非至日也,无时而非至时也”(《周易古文钞》,第105页)。由是而“复”心,则能“不贰过”(同上)。
“迷复”是以“本心”尝明为前提,“圣人言复,又遡姤,见姤、复通为一体,是人心至妙处”(同上,第103页)。无论个体之心有怎样的“过”,其“本心”始终诚明净洁,不会因生存世界“习染”之遮蔽而消失,诚如《问答》所说:“真性中岂有习染?后来世故交接,遂有习染。习之既深,口之所言,身之所行,即至衾影梦寐,无非是习。然此点良心却又完完全全,是以为小人者,虽习染深厚,至于呼之即应,叩之即觉,又不因习染深浅,遂分利钝”(《全集》二,第353页)。故《人谱》言:“人虽犯极恶大罪,其良心仍是不泯,依然与圣人一样。只为习染所引坏了事。若才提起此心,耿耿小明,火然泉达,满盘已是圣人”(第15页)。个体之“心”有“过”是谓“迷”,有“迷”则可改,改过即是“迷复”。
“本心”之明被遮蔽,若个体之人不做迁改工夫,“过”最终演变为“恶”。“恶”是对“过而不改”状态的描述,如《纪过格》所言:“微过成过曰微恶”、“隐过成过曰隐恶”、“显过成过曰显恶”、“大过成过曰大恶”、“丛过成过曰丛恶”(第15页)。《纪过格》还将“恶”之端始视为不同的“门”,即微恶之祟门、隐恶之妖门、显恶之戾门、大恶之兽门、丛恶之贼门。由此入“门”用工夫,迁善改过,即可实现“迷复”:“诸过成过,还以成过得改地,一一进以讼法,立登圣域”(同上)。
不过,改过工夫无穷尽。《证人要旨》言:“学者未历过上五条公案,通身都是罪过。即已历过上五条公案,通身仍是罪过。才举一公案,如此是善,不如此便是过。即如此是善,而善无穷,以善进善亦无穷。不如此是过,而过无穷,因过改过亦无穷。”(第9页)因此,《人谱》设计了紧密的“证心”工夫步骤,即:针对妄惑微过,则“静坐读书”,明人禽之别、敬肆之分,以悟“本心”之“明”;针对七情隐过,则“知几葆任”,惩欲窒忿,当下廓清;针对九容显过,则“变化气质”,以气质定威仪,由知礼而显性;针对五伦大过,则“随事体当”,践履敦笃,以黾黾战兢之心尽伦常天道;针对百行丛过,则“反身而诚”,万物皆备于我,由尽“我”之心而尽人尽物;针对成过之恶,则“克念始终”,时时自讼反省,善于从习染昏蔽中提撕“本心”。终究而言,“一迁一改,时迁时改,忽不觉其入于圣人之域。此证人之极则”(同上)。
总之,人虽有自在诚明之“本心”,但非皆常葆此“心”显明,故有“过(恶)”。《人谱》深刻、细微地分析了“过(恶)”的产生根源及其类别,几将人世间可能的“过(恶)”囊括殆尽。从本质言,蕺山眼孔里面看到的不是“过(恶)”的具体形态,而是人“本心”的客观存在和时时存在。人一旦明悟了何谓“过(恶)”,也就体勘了何谓“善”。无论有怎样的“过(恶)”,“心”常明常止,“迷复”即达圣域。
注释:
①蕺山子刘汋(1613-1664,字伯绳)指出:“《人谱》作于甲戌,重订于丁丑,而是谱则乙酉五月之绝笔也。一句一字,皆经再三参订而成。”(姚名达:《刘宗周年谱》,吴光主编:《刘宗周全集》第六册,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477页。)即,《人谱》初撰于崇祯甲戌(1634年),再订于崇祯丁丑(1637年),定稿于弘光元年即乙酉(1645年)闰六月。
②拙文《刘宗周〈人谱〉研究回顾与展望》(《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版),待刊。)有详细论说。
③刘汋说:“先生绝食中,谓汋曰:‘……《人谱杂记》属垂绝之笔,尚多残缺,宜辑补完之。’”(《蕺山刘子年谱》,《刘宗周全集》第六册,第192页)
④如:何俊《刘宗周〈人谱〉析论》(《中国哲学史》1998年第1期)、李明辉《刘蕺山论恶之根源》(载钟彩钧主编:《刘蕺山学术思想论集》,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筹备处,1998年,第93-126页)、李振纲《解读〈人谱〉:圣贤人格的证成》(《哲学研究》2009年第9期)等。
⑤《人谱》,《刘宗周全集》第二册,第10页。下相似引文皆随文简注。
⑥吕耀怀:《规范伦理、德性伦理及其关联》,《哲学动态》,2009年第5期。
⑦张立文:《帛书周易注译》,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236页。
⑧张立文:《帛书周易注译》,第27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