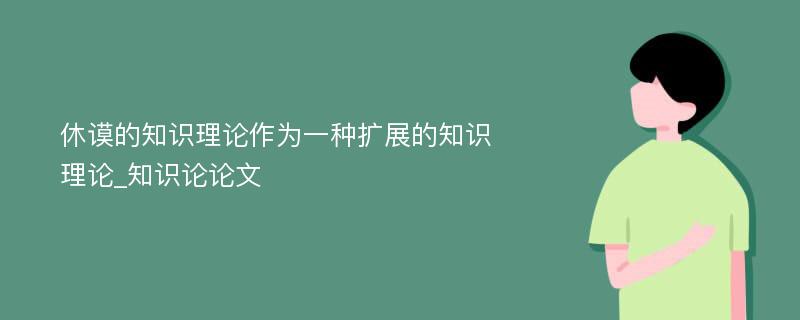
作为一种延留知识理论的休谟知识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知识论文,理论论文,休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842.1 文献标识码:A 休谟对经验知识的态度,目前有两种解释。描述主义解释认为休谟的自然主义资源只能说明信念形成的机制,却不足以建立规范性知识论。①规范主义解释则认为休谟通过对信念形成机制的自然主义处理形成了某种规范性的认知论,尽管规范主义解释的支持者们对其中规范性特征并没有形成统一的理解。②本文的目的是为规范主义解释提出一个正面的论据。我将论证我们完全可以从休谟的自然主义资源中形成一个令人满意的对经验知识的知识论地位的刻画。J.麦克道尔(John McDowell)的延留知识理论(the theory of retained knowledge)为完成这个刻画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技术支持。建立在延留知识理论之上的休谟知识论具有清晰的认知规范的要求,而且这一要求能够同时照顾到休谟哲学中的自然主义和怀疑主义两个层面,使得规范主义解释形成统一的对休谟知识论中规范性特征的理解成为可能。麦克道尔与休谟自有许多不同之处,颇受康德影响的前者也许会认为后者的哲学陈旧落后。但我想指出的是,两者从不同的学术背景不约而同地对经验知识中自然与理性的辩证关系形成了十分类似的观察,即对于有限认知能力的人类认知主体来说,经验知识必然是可错的,因此,对其知识论地位的规范性刻画只能同时是自然主义的。本文第一节梳理麦克道尔延留知识理论的论证结构,第二、三节指出该论证结构同样存在于休谟的《人性论》第一卷最关键的讨论中,形成了休谟的规范性自然主义最基本的论证。 一、麦克道尔的延留知识 知识论地位(ES,epistemic standing)可以被定义为这样一种条件:认知主体s持有信念p,当加入这个条件ES时,p就能够成为知识: (1)S相信p,ES→S知道p。就是说一个信念p在具有知识论地位之后,便可在知识论意义上成为知识。麦克道尔的延留知识理论提供了一种规范性的和自然主义的对知识论地位的理解。这个理论通过一个否定性的步骤和一个建设性的步骤建立起来。否定性步骤否认可以通过论据为媒介来获取知识论地位。这个看法来自于塞拉斯。③他认为给出信念p的知识论地位过程不是描述过程,而是辩护过程。在给出p的知识论地位时,我们把p放置在一个逻辑的理由空间(SR,space of reasons)中。问题在于如何理解这个理由空间。一个常见的错误看法认为这个理由空间以论据为媒介[SR(Ar),the space of reason mediated by argument],也就是说,Ar为p提供一个论据,在其中p是论据的结论。把知识论地位看成以论据为媒介的理由空间运作的结果,就意味着知识论地位的规范性完全来自于论据的说服力,并以此来刻画知识论地位中的理性成分。 这种看待知识论地位的方式有两个困难。第一个困难是,如果论据Ar是演绎推理,那么,以论据为媒介的理由空间SR(Ar)虽然可以给认知论地位ES以最强有力的支持,却无法对经验知识给予任何帮助。这是因为经验知识建立在经验证据之上,在论据Ar中经验证据由前提表达,而经验知识由结论表达,结论中的经验知识的内容要多于前提中的证据的内容。这个事实无法用演绎推理来刻画。而第二个困难是,如果论据Ar是归纳推理,那么,无论前提中的证据给结论多高的概率,仍然无法给知识论地位ES以足够的支持。 我们不妨通过一个例子来看这第二个困难。让我们想象一个人在轮盘赌时已知轮盘上99个格子为红字,只有1个格子为白色。如果他是理性的认知主体,就会预测下一次转动会停在红格子上。我们是否能把这个建立在高概率(99%)之上的预测看成是知识?麦克道尔认为不能,因为总是存在着下一次转动停在白格子上的可能,而这个可能无法被高概率消除。用麦克道尔话说,“一个人通过论据对一个预测结果建立起高概率,他当然对预测拥有再好不过的理由,但这个事实仍然改变不了(他对结果并不拥有知识的状况)。我们可以换其它例子让概率更高,但我无法看出概率值的变化能导致任何原则上的不同。如果白格子的比例是千分之一甚至百万分之一,那个人仍然无法知道下一次轮盘转动的结果不是白格子”。④ 麦克道尔接着在建设性步骤中给出延留知识的定义,并说明其知识论地位如何不建立在以论据为媒介的理由空间中。麦克道尔对经验知识的本质做出如下观察:经验知识是关于可合理地延续却非永存的(reasonably durable but impermanent)事态的知识,而对这样的事态我们在知识论层面上只能给出间断地检查。事态可合理地延续,因而具有稳定性,这使得经验知识成为可能;而事态的非永存性使得经验知识从本质上来说是可错的。麦克道尔把具有这种性质的经验知识称为“延留知识”(retained knowledge)。⑤它持续于一段时间内:在该时间段的前一个时间点上,之前的证据支持事态的延续性,在后一个时间点到来时,新的确证经验会对事态是否延留给出新的信息,而在两个点中间的时间段中,我们没有在知识论层面上对事态进行检查,因而关于其延续性的信念是可错的。我们看个例子: 假设一个常年对天下大事予以关注的人,假如他每天早晨六点都从一个可靠的新闻广播台中听取当日新闻。在温斯顿·丘吉尔生命中的某一天下午三点钟,我们能否把这个关注天下大事的人心中所具有的“丘吉尔仍然在世”的信念当作知识?在直觉上,答案应该是能的。⑥在这个例子中,作为世界知名的年迈政治家丘吉尔,如果偶遇不幸或健康出了问题,都会作为重要消息发布在每日新闻中。而那位关心天下大事者从当日早晨六点中的新闻中没有听到有关丘吉尔的消息,且最近一段时间里也没有丘吉尔健康出现问题的消息。因此,如果有人在当日下午三点问他“你认为丘吉尔是否在世”,而他真诚地回答说,是。我们会在直觉上认为他所说的信念是知识。这个知识的言称(knowledge claim)是可错的。即使可能性极小,却仍然有如下可能,即此时丘吉尔在两个小时前已去世,讣告还没有来得及见诸新闻,而这位信念持有者只有在晚上六点再听到新闻时才会知道他在下午三点时持有的信念是错的。尽管有可错的可能,我们仍然把他在三点钟拥有的丘吉尔仍然在世的信念看作知识,即延留知识,除非我们有理由怀疑信念持有者之前证据的可靠性。比如,信念持有者如果因为外出旅行,造成有一段时间未能按时收听新闻,那么,我们就可以怀疑也许他漏听了有关丘吉尔的最新信息,从而不再把他的信念当成知识。这种延留知识的辩护并不依赖于以论据为媒介的理由空间,而是具有以下特征: 如果某人在某时刻对事态拥有正确的认知把握(cognitive grasp),比如,他看到事情是如此这般的,我们就会允许他接触的已知事实的原始状态所具有的知识论地位可以继续延留。我们可以将对其知识论地位的信任,保留到他不再直接注视事态之后的某个时间,我们会说他延留了最初通过知觉获得的那部分知识。当然,在事态发生变化后我们就不能这样做了。但当事态还未发生变化,起码在一段时间内,我们可以认为他对事态仍持有正确的认知把握。⑦ 在麦克道尔看来,一个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常用的知识言称策略(knowledge-claiming policy)就是在没有反面证据出现的情况下,延留拥有之前证据所支持的信念的知识论地位。也就是说,在没有理由去怀疑事态的延续性时,我们可以合理地对关于非永存的事态的信念的知识论地位采取延留的态度。这个知识言称策略可以用以下缺省条件来表达: (DC,default condition):如果认知主体S对信念p拥有正确的认知把握,即p被之前的证据所支持,那么,在没有反对理由出现时,p可以被看成为知识。值得注意的是,尽管DC是经验知识的必要条件,却不能单独地刻画经验知识的知识论地位。外在主义知识论会立刻意识到DC可以用来刻画信念形成的可靠机制在运作时所遵从的规则。这个规则允许认知主体采用以下策略,即“在未发现任何事情有所变化的迹象时,他仍可宣称事情仍像之前所知道的那样”。⑧然而,这个规则只是延留知识的必要却非充分条件。因为独断论者或轻信他人的人都可以拥有可靠的信念形成机制。他们都是在知识论层面上不负责任的人,他们在运用DC规则时不过是碰巧获得了真信念,因此,我们无法把他们的信念看成为知识。避免独断论和轻信他人的要求,麦克道尔称之为“对信念负责”: (DR,doxastic responsibility):一个认知主体S对其信念负责(DR),是指他对信念中所涉及的事态发生改变的可能性具有敏感力和洞察力。 再用关于“丘吉尔仍然在世”的信念为例。信念持有者如果有一段时间未能密切关注新闻,或者他已经知道丘吉尔的健康状况不佳,那么,作为一个对信念负责的认知主体,他就应该悬置“丘吉尔仍然在世”的信念。麦克道尔认为,理由空间不应该以论据为媒介SR(Ar),而应以对信念的责任为媒介SR(DR)。也就是说,理由性空间的合理性并不仅来自于论据的说服力,也来自于认知主体对事态变化的可能性的敏感与洞察。在麦克道尔看来,正是这份敏感与洞察加上对缺省条件的运用形成了延留知识或经验知识的知识论地位: (2)S相信p,ES(DC,SR(DR))→S知道p。也就是说,S的被之前证据支持的信念p是延留知识,当S对p中的事态拥有正确的认知把握,并且对事态的可能变化具有敏感力和洞察力。麦克道尔把(2)称为延留知识的知识理论(epistemology of retained knowledge)。⑨它有两个后果值得一提。首先,该理论中“知道”一词与20世纪西方知识论所理解的“被辩护的真信念”有所不同,因为,无论是DC还是SR(DR),都无法保证p一定为真。其次,建立在DC和SR(DR)之上的知识论地位超越了外在主义和内在主义知识论之争。敏感的读者可以察觉到DC是个外在主义的运作规则,而SR(DR)是个内在主义的要求。上述延留知识理论的论据提醒我们DC和SR(DR)尽管不可或缺,却都无法独自建立知识论地位。⑩ 本文要论证休谟的规范性自然主义知识论就是一种延留知识理论。我们已经看到,麦克道尔论证延留知识的知识论地位(2)用了两个步骤:第一是否定性的,破除知识论地位可被以论据为媒介的理由空间SR(Ar)来刻画的观点;第二是建设性的,即用DC和SR(DR)来刻画延留知识的知识论地位。下面两节论证休谟的知识论分别建立在这两个步骤之上。第二节指出休谟对经验知识中理性地位的处理类似于麦克道尔的否定性步骤。第三节论证休谟的自然主义知识论相应于麦克道尔建立(2)时所用的建设性步骤,其中DC和SR(DR)分别说明了休谟知识论中的自然主义和怀疑论的来源。 二、理性的局限性 用麦克道尔的理论来理解休谟时要说明的第一个问题是休谟哲学中的经验知识是否就是延留知识。在休谟哲学中,经验知识是从感觉直接形成的或依靠因果推理间接形成的信念。(11)对休谟的自然主义解释展示休谟如何通过探讨人类的认知局限来说明这些信念形成的机制,这当然与麦克道尔对知识论地位的直接分析的做法不同。我们在直觉上可以说,休谟哲学中通过因果推理从感觉中间接形成的具有可靠性的信念可被看成为延留知识。但这个判断需要更严密的论证。严格地说,延留知识由下面四个因素组成: a.对一个信念p的经验辩护要求其知识论地位ES必须在经验中寻找知识论支持。 b.经验对p的支持是间断的。 c.在两个连续经验支持点之间,p所表征的事态有可能变化。 d.鉴于b和c,如果p所表征的事态不具有合理的延续性的话,就无法被看作知识。不难看出,a刻画了经验在延留知识中的作用;b和c分别强调了经验证据支持的间断性和由此引起的可错性;d则指出延留知识的必要条件之一是事态的合理的延续性。而这四个因素同样构成了休谟哲学中的经验知识。 首先,a体现在休谟的第一原则中,因此,所有的简单观念都因果地由简单印象所引起,而且是简单印象的精确复现。由于信念由观念组成,而经验知识又是正确地复制了简单观念及其组合的可靠的信念,因此,它也必须满足a。其次,休谟在讨论人类认知能力的局限性时同样认识到了b。在《人性论》第一卷第三章第二节的第二自然段(T1.3.2.2)中论证感觉对象的同一性不能只来自于感觉时,休谟指出这是因为我们常常无法拥有“一个不变的和不间断的知觉”来判断对象的“个体继续是同一不变的”。(12)我们不能永远地注视或触摸一个对象以保证其同一性。当我们眨眼或短暂地停止触摸时,对象就有可能改变,就像c所说的那样。这直接导致了对齐一性原则(principle of uniformity)的否定(T1.3.6.4),引发了著名的休谟问题,以及对感觉对象、人格同一性等问题的怀疑论立场(T1.4.2; T1.4.6)。休谟论证,对感觉对象或人格同一性的因果推理最终建立在想象之上。想象的成功运用不仅依靠认知主体自身的能力,还需要一点运气来获得外在世界的合作,就像d所意味的那样。正是因为我们可以暂停哲学思考,把自己交给这点运气,才能够从怀疑论的绝望中恢复过来(T1.4.7)。我们在下一节还要讨论这个问题。总之,延留知识的基本特征都可在休谟知识论体系最关键处找到其表达,因此,把休谟的经验知识看作延留知识是有根据的。但对这个判断更重要的论据是麦克道尔对(2)的论证也同样存在于休谟对经验知识的刻画中。 对应于麦克道尔对以论据为媒介的理由空间SR(Ar)的批评,休谟论证理性不足以决定因果关系,因而也不足以完成知识论的任务。在这里,休谟所说的“理性”可以被理解为SR(Ar)。如同罗斯所说:“(在休谟哲学中)如果理性或知性可以决定(因果)推理,那么,必须有一些论据来支撑推理的运作”。(13)然而,这个论据不能是演绎推理,原因同麦克道尔所说的一样,是因为因果关系中的结论的内容超过前提中的内容。对于归纳推理,休谟的否定过程初看起来与麦克道尔的处理颇不相同。休谟的讨论导致了著名的归纳问题,而麦克道尔并不关心是否存在对归纳的辩护,他所关心的是,归纳推理无论具有多高的概率,都无法完成刻画知识论地位的任务。然而,也会发现两者在深层次上有着至关重要的联系。 我们不妨从休谟的论据着手。休谟学者迪克尔对休谟的论据做出如下重构: (T1)事实的知识如果不建立在当下的知觉或记忆之上,就需要建立在因果关系之上。 (T2)因果关系无法先验地获得,只能从过去的经验中推得。 (T3)从过去经验中推得的归纳推理无法被合理地辩护。(14)休谟又对(T3)做出如下论证:想要辩护从过去经验推得的归纳推理需要预设自然的齐一性,否则该辩护只能是循环论证。但由于自然界的事态是非永久的,自然的齐一性无法建立,因此,(T3)与(T1)和(T2)一起推出因果关系无法被合理地辩护。然而,20世纪后期,一些贝叶斯主义者开始质疑休谟为(T3)所作的论证。(15)他们认为对归纳推理的辩护无需预设自然的齐一性,只要能够刻画出认知主体在面对新证据时对信念相信程度的变化就足够了,而贝叶斯概率为这个刻画提供了所需的工具。对(T3)的否定导致了我们无法从(T1)和(T2)推出休谟对因果关系做合理辩护的否定,从而一举解决休谟问题。 我们无法苛责休谟未能预见200年后的反对意见。但如果我们回想起麦克道尔批判以论据为媒介的理由空间SR(Ar)时的论据,就能看出即使归纳推理可以用贝叶斯的方式予以辩护,但仍不足以为因果关系提供知识论层面上的合理辩护。为了看清这点,我们不妨以麦克道尔的方式重构(T3): (T3’)来自于过去经验的关于事实的知识是关于非永久性事态的知识,从过去经验推得的归纳推理无论具有多高的概率,都不足以刻画该知识的知识论地位。建立(T3’)的论据来自于麦克道尔对SR(Ar)的批判,而与归纳推理本身是否能够被辩护无关。(T3’)与(T1)和(T2)一起仍能得出休谟想要的理性无法决定因果关系的结论。也就是说,休谟的论据必须依赖于麦克道尔对SR(Ar)的批判才能经受住当代哲学的拷问。这是因为麦克道尔对SR(Ar)的分析让我们看到休谟问题中关键的一步并非像休谟最初想的那样依赖于对归纳推理的辩护,而是直接依赖于无法用以论据为媒介的理由空间所把握的自然的齐一性。 三、重构休谟知识论 我们再来看延留知识的知识论地位ES中两个重要部分即缺省条件DC和以信念的责任为媒介的理由空间SR(DR)在休谟哲学中的作用。对于DC,我们可以说它是对休谟哲学中规范性自然主义部分的一个准确的刻画。这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休谟的自然主义所要说的正是一组信念形成机制加上缺省条件。这些信念形成机制包括知觉、记忆、直觉、因果推理等。它们属于心理运作过程,其产生的原因需要心理学家而非哲学家来解释,因为哲学家们找不到任何理由来充分地说明它们。我们对于事实的判断是心理机制的习惯性想象的结果,如果没有相反的证据让我们质疑它,我们不会使用逻辑推理来反思它。我们对于外在对象的信念无法用哲学论据建立起来,而是自然通过信念形成的心理机制的习惯性想象引导我们这样相信。当想象发动起来之后,“会继续下去,正如一艘船在被浆推动以后,不必重新推动,仍然继续前进一样”(T1.4.2.22,SBN198)。 DC对休谟的自然主义的刻画的第二个方面在于它成功地把握住在相反的证据出现之前,信念形成机制运作时的非反思性、前理论性的特征,即这个运作是直接的和自动的。反思性的推理过程只有在相反的证据影响到信念形成机制时才会出现。休谟在许多地方讨论过非反思性信念形成机制过程,最为详细的是在讨论因果关系的时候。原因和结果的观念被想象习惯性地联结在一起,而我们自己并没有意识到这种联结是如何发生的(T1.3.6.2,SBN87; T1.3.6.12,SBN92; T1.3.6.14-15,SBN93)。 DC对休谟的自然主义刻画的第三个方面是它表示出了信念的动力性特征(motivational characters of doxastic status)的关键转变点。这些动力性特征包括信念的不可抗拒性(irresistibility)、可靠性(reliability)、稳定性(stability)和坚固性(steadiness)。一些对休谟的规范性自然主义的解释正是用这些动力性特征来说明休谟的自然主义中规范性的来源。(16)而DC给出了这些动力性特征的变化中最重要的转变点。当相反的证据未出现时,认知主体跟随着自然的指引,对由非反思性过程产生的信念不产生任何抗拒感,感觉它是可靠的、稳定的和坚固的。但当相反的证据出现之后,不可抗拒感动摇了,可靠性、稳定性和坚固性降低了。而动摇和降低的程度如果不断增加,就会引发认知主体最终放弃该信念。DC正是对这个转变点的把握,它给出了休谟哲学中自然主义资源具有认知规范性的界限,即什么时候自然主义资源在知识论地位ES运作时是决定性的,而什么时候又是不充分的。因此,总结这三个方面的表现,我们可说DC在休谟的规范性自然主义中有着重要的地位。 如果相反的证据出现之前的信念形成机制的规范性可由DC来刻画,那么,相反证据出现之后的反思性认知过程就需要SR(DR)来引出。休谟意识到,当只有DC运作时,“我们只是顺从于心灵的习惯性倾向,我们就不经反省而由一个对象推移到另一个对象,其间并无片刻停顿。这个习惯既然不依靠于任何审查,所以它是立刻发生作用,不容有任何反省的时间”。但是,人类很多认知过程都是反思性的。“……我们平常总是有意识地考虑过去结果的相反情况,我们比较折中相反情况的两个方面,并仔细衡量我们在每一方面所有的那些实验:由此,我们就可以断言,我们的这一类推理并非直接发生于习惯,而是由间接方式发生的……”(T1.3.12.7,SBN133)需要有反思性认知过程的是个知识论要求。正如休谟学者罗斯所说,反思性资源如“仔细、有应变能力和持续性”,“一般来说,都是辨别证据、理性或辩护所要求的,而这些证据、理性和辩护正是认识主体正当地获取其结论所必需的”。(17)拥有这些反思性资源的人,如果用延留知识理论的术语来说,就是一个对信念负责的人。这种人对经验知识中事态发生变化的可能性具有敏感力和洞察力,而只有这种人有能力以对信念的责任为媒介建立经验知识的理由空间SR(DR)。对信念负责的人在运作这个理由空间时,通过新的证据来反思和校正通过非反思过程获得的信念。用休谟的话来说,“我们应当永远把从知性本性得来的另一个判断,来校正那个从对象本性得来的最初判断”(T1.4.1.5,SBN115)。 对信念负责的人首先应该明白通过经验获得的信念都是可错的。人的感官是有限的和可错的(T1.4.7.1,SBN264; T1.4.7.3,SBN265),记忆会减弱会欺骗我们(T1.3.5.5,SBN85-86),即使在逻辑和数学论证中,也会因我们认知过程的疏忽减弱论证的可靠性(T1.4.1.1,SBN180)。当我们进行因果推理时,一系列的因素会影响推理的可靠性。 我们是借着习惯由原因推移到结果的;我们是由某种现前印象借取活泼性,并将此活泼性传播于相关观念上。但是当我们不曾观察到可以产生强烈习惯的足够多的例子时,或者当这些例子相互反对时,或者当类似关系不精确时,或者当现前印象微弱而模糊时,或者当经验有几分消失于记忆之外时,或者当联系依靠于一长串的对象时,或者当推论虽然由通则得来、可是并不符合于通则时:在所有这些情况下,随着观念的强力和强度的减低,证信程度也就减低了。(T1.3.13.19,SBN154) 因此,在休谟看来,所有的经验信念都是概然判断。对信念负责的人对造成信念可错性的因素敏感,当他们洞察到这样的因素出现时,就会进入到理由空间SR(DR)中,用对这些因素的反思和运作所形成的新的证据来核对和校正通过非反思性的自然机制形成的信念。他们会感觉到原始信念所涉及的事态有可能并不是原先所相信的那样,因而,原始信念的不可抗拒性、可靠性、稳定性和坚固性就受到了动摇。如果在之后反思性的探求中不断地发现新的相反证据,那么,原始信念的证信程度就会越来越低,直到最终被放弃。而那些对信念不负责的人则无法进入理由空间。他们很容易轻信感官直接带来的信念和他人的言说(T1.3.9.12,SBN113),并习惯对自己的信念采用独断论的态度(T1.3.9.19,SBN117)。对信念负责的要求也正是休谟知识论的要求,它的作用就在于避免轻信和独断。SR(DR)精确地刻画了这个作用。 然而,如同DC一样,SR(DR)在休谟的知识论中也无法单独地完成刻画知识论地位的任务。这是因为在休谟看来,对信念负责的认知主体如果不断通过反思来考察可能引起信念出错的地方,就会不断地降低信念的可信度,并最终使之降到零(T1.4.16,SBN183)。这最终会导致皮浪式的怀疑论,使得对信念负责的认知主体不得不悬置所拥有的信念。SR(DR)所意味的怀疑主义是对轻信和独断的预防,但当SR(DR)没有节制地涉及所有经验信念上时,就会产生极端的怀疑主义,使得所有的经验信念都被悬置。T1.4.7上半段所表达的著名的休谟式的绝望就是这种怀疑论的极致状态。所以,以对信念的责任为媒介的理由空间SR(DR)的运作必须要有限制。这个限制在休谟的哲学中最终来自于经验本身。 但是经验会使乐于尝试的任何人充分相信,他在前面[怀疑论]的论证中虽然不能发现错误,可是他仍然在照常继续相信、思维和推理。既是这样,他就可以坦然地断言,他的推理和信念是一种感觉或特殊的想像方式,单纯的观念和反省不可能把它消灭。(T1.4.1.8,SBN184)在这里,经验作为自然主义资源又回到知识论的运作中。经验之所以有这种运作能力,用延留理论的术语来表达,正是因为事态有着合理的延续性。这种合理的延续性使得休谟在没有任何论据反驳怀疑论的时候,能够从绝望中恢复过来,重新跟随自然的倾向以愉快的心情来生活和从事哲学研究。 休谟通过这种自然和理性的辩证关系来揭示经验信念形成机制的做法,可以很好地用延留知识的知识论地位(2)来刻画。一方面,如果我们没有理由去怀疑自然主义的信念形成机制所产生的信念,我们就应该相信它,尽管这个机制是可错的;另一方面,对信念负责的认知主体需要对信念的可错性拥有敏感力和洞察力,一旦发现相反的证据就应进入理由空间去校正原始信念。这种反思过程不应该导致极端的怀疑主义,只要自然与我们合作,使得信念所涉及的事态拥有合理的可延续性。因此,我们可以说休谟哲学中对经验信念的讨论可被看作一个延留知识理论,它不仅仅是一种自然主义的描述,也是一种规范性的自然主义知识论。通过延留知识理论,我们可以很好地安置休谟知识论中的自然主义和怀疑主义这两个成分。 (初稿曾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举办的“经验与概念——麦克道尔与塞拉斯哲学研讨会”上宣读,会议组织者唐热风及其他与会者们的批评对定稿的形成至为关键,特此感谢。) 注释: ①其代表研究有Don Garret,Cognition and Commitment in Hume's Philosophy,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7; Don Garret,"Hume's Theory of Ideas",in A Companion to Hume,Elizabeth S.Radcliffe ed.,Blackwell Publishing,2008,pp.41-57; David Owen,Hume's Reas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 David Owen,"Hume and the Mechanics of Mind:Impressions,Ideas,and Association",in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Hume,2[nd] edition,David Fate Norton and Jacqueline Taylor ed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9,pp.70-104. ②比如,K.史密斯(Kemp Smith,The Philosophy of David Hume:A Critical Study of Its Origins and Central Doctrines,Macmillan,1941)认为休谟知识论中的规范性来自于经验信念的不可抗拒性(irresistibility)和不可避免性(inevitability);F.施密特(Frederick Schmitt,Knowledge and Belief,Routledge Press,1992)认为该规范性来自于经验信念的可靠性(reliability);A.贝尔(Annette Baier,A Progress of Sentiments:Reflections on Hume's "Treatis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1)和C.M.科斯佳德(Christine M.Korsgaard,The Sources of Normativity,Onora O'Neill ed.,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6)认为来自于认知主体的自我细查(self-scrutiny)的能力;而L.E.罗布(Louis E.Loeb,Stability and Justification in Hume's Treatise,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2)认为来自于信念的稳定性(stability)。 ③Wilfrid Sellars,"Empiricism and the Philosophy of Mind",in Minnesota Studies in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Herbert Feigl and Michael Scriven eds.,vol.1,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56. ④John McDowell,"Knowledge by Hearsay",in Meaning,Knowledge,and Reality,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8,p.422. ⑤Ibid.,p.423. ⑥Ibid.,p.422. ⑦John McDowell,"Knowlede by Hearsay",p.426. ⑧Ibid.,p.423. ⑨John McDowell,"Knowledge by Hearsay",p.423. ⑩麦克道尔对超越内在主义和外在主义知识论的讨论,可参看John McDowell,"Knowledge and the Internal",in Meaning,Knowledge,and Reality,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8,pp.395-413。 (11)众所周知,休谟并没有使用“经验知识”一词,而是把“知识”一词留给具有绝对确定性的信念,如逻辑和算术。这使得“知识”一词的使用范围戏剧性地缩小,连几何学也无法成为知识。目前,一些休谟学者为了讨论的方便,开始使用当代知识论中的“经验知识”一词来指称休谟哲学中建立在经验之上的、虽不具绝对确定性却具可靠性的信念。本文也采用这种用法。 (12)David Hume,A Treatise of Human Nature,L.A.Selby-Bigge e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8,p.74.下文再引按休谟研究惯例于文中简称SBN,不再注出。译文采用休谟《人性论》关文运译,商务印书馆,引文页码为SBN页码,亦见于关译本页边码。另下文指称《人性论》某部分内容时,按休谟研究惯例使用类似“T1.3.2.2”的表达法,不再注出。 (13)Abraham Sesshu Roth,"Causation",in Blackwell Guide to Hume's Treatise,Saul Traiger ed.,Blackwell Publishing Ltd.,2006,p.108. (14)Georges Dicker,Hume's Epistemology and Metaphysics-An Introduction,Routledge Press,1998,p.61. (15)最清楚的表达见Samir Okasha,"What Did Hume Really Show about Induction",in The Philosophical Quarterly,2001,vol.51,pp.307-327;另可参看Colin Howson,Hume's Problem-Induction and the Justification of Belief,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3。 (16)关于这一点,参见注②。 (17)Abraham Sesshu Roth,"Causation",p.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