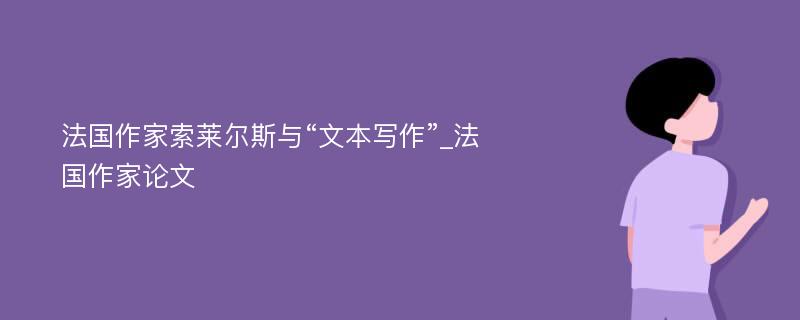
法国作家索莱尔斯与“文本写作”,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法国论文,莱尔论文,文本论文,作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菲利普·索莱尔斯(Philippe Sollers,1936-)是当代法国文坛最活跃、最具影响、最有发展前途的作家之一。作为法国“原样派”(又译“如是派”)的杰出领袖,他为当代西方文学观念和人文思想的革命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他所提出的“文本写作”的概念,具有浓厚的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的色彩,是一种对传统文学认识的反驳和更新。这种概念运用苏联形式主义文学研究成就,成功地走出了超现实主义的死胡同,后来竟发展成为“原样派”的最主要理论之一。20世纪下半叶,这种理论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索莱尔斯不仅是一位著名的文学理论家,而且是一位出色的小说家,主要作品有《挑衅》、《奇怪的孤独》、《公园》、《中介人》、《弗朗西斯·蓬热》、《戏剧》、《数字》、《女人》、《法国女人的爱情》、《游戏者的肖像》和《绝对的心》等。索莱尔斯曾直接从传统文学一下子过渡到“反文学”,后来又一下子从“反文学”回归的传统文学,其风格上的“波动”,在法国文学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文本写作”最基本的概念,简单地说,就是自从有了人、有了写作的人以来,世界上只有一本书。这本书是一部冗长的、唯一的、不间断的、未完成的、无法完成的、无名称的文本,换句话说,世上从来就没有一本一成不变的“神作”,任何文本都处在好几个文本的结合部,它既是复读,也是强调、浓缩、位移和深化。任何文本都是由另一些文本写出来的,而不是出自一些句子和词汇,不管作者是否参照先前的作者没有,他所写的与其它文本都是相互关联的。任何文本既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产物,同时也是所有时代的产物,它的真正价值,就在于对其它文本进行积分式的、破坏性的行动。文本与文本之间的相互渗透,不仅能够使一连串的作品复活,能够使它们相互交叉,而且能够使它们在一个普及本里走到极限意义的边缘。索莱尔斯对引号意义的论述见解独特:“引号里可读的部分并不是引言,而是从不同的文章材料里提取出来的东西,其目的是为了表明整篇文章的构造与引用的那篇不同”。索莱尔斯推崇“可写性”的文本,力贬“可读性”的作品,主张读者应该通过自己的想象去阅读,这与罗兰·巴特对“可写的”文本的论述一脉相承。在索莱尔斯眼里,文学世界变得越来越大,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文本的不断增多,任何文本最终都会走向无名的状态,走向所谓的“反文学”。
《数字》和《戏剧》成了索莱尔斯“文本写作”概念的试验“基地”。在《数字》里,索莱尔斯通过实际的创作揭示了文本间的相互关联性(intertextualité,简称互文性或文本间性),为我们彻底地更新了对文本意义的传统认识。所谓“互文性”,就是每一个文本都不是一个孤立封闭的作品,它处在一个巨大的网络系统之中,它在引证参照的同时,也为自己构成了一个复杂的网络系统。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数字》里无任何内容,也没有作者,但它是一部破译机器,能够破译那个被视为我们唯一财富的、少得可怜的现实。这部作品共分四段,第一段、第二段和第三段为未完成过去时,占作品篇幅的四分之三,只有第四段是现在时,只占作品的四分之一。其开放式框架,断断续续的场景和虚幻的现实,就像《戏剧》作品的无形棋盘或代表时间的黑白相间的格子。这种手法如同一个表现写作力量的暗室,能够让我们在里面冲洗出一些图像,但这些图像里的“我们”永远只是个负片而已。达·芬奇曾经说过:绘画是一个增加的过程,而雕塑是一个减少的过程。索莱尔斯把观众当作演员,实际上是为了说明,文本的解读也是一个增加的过程,这种增加不但反映在解读者对文本添加了新的意义,而且更重要的是揭示了各种潜在意义的可能。换言之,对文本的多义性的强调,也是对古典文本那种专断的意义中心化和一元化的抗拒。索莱尔斯不仅更新了文本的传统意义,而且对作为传统哲学里主体的“我”的认识也进行了全新思考。他认为,没有确切意义的,不仅仅是指现在的“我”和“我”现在的生活,还包括“我”过去的一切,甚至包括“我”将来的一切,因为今后的“我”根本不会知道现在的“我”究竟是谁,正如现在的“我”就连“我”究竟在什么地方都不知道一样。在《戏剧》里,关于这个似存非存的“我”、这种值得怀疑的、具有意义不确定性的生活,索莱尔斯写道:“变得跟你一样;不知道我是谁。但保留着能够让我说‘我’的东西。”这里,索莱尔斯对主体“我”的意义的怀疑,实际上是对传统的作者主体性的根本否定。在《数字》里,从未完成过去时(第一、第二和第三段)到现在时(第四段)之间有这样一段耐人寻味的过渡:一个没有场景、没有剧院的戏剧,那里所使用的词语变成了一个新游戏团体的演员和观众,传统意义上的作者、叙述者、人物和读者都消失了。显然,索莱尔斯把作者和读者的传统地位彻底地改变了。1968年,在克卢尼召开的一次学术研讨会上,他发表了一篇题为《一个现代文本的新语义》,他把这种导演、这种戏剧的存在方式解释为自己的戏剧、自己的文本和自己的演员,这里的观众不可能是通常意义上的观众,他们首先是被动的演员,因为这出戏是一出“没有演员的戏剧”。①索莱尔斯的观点渗透着后结构主义的色彩,写作类似于一个持续否定的过程,它不断地消解作者,这与罗兰·巴特的“作者之死”的观点十分接近。
《数字》和《戏剧》是“互文性”的最好明证。《数字》里的某些段落是用汉字结尾的,索莱尔斯把非拼音文字的汉语写进了法语文本,这种别出心裁的写作方法令许多不懂中文的读者十分费解。《戏剧》采取了《易经》的结构,共分六十四章,相当于六十四卦,单数与偶数以及第三人称和第一人称分别对应于阳爻和阴爻;而《数字》则使用了大量的汉字和《道德经》的引言。②索莱尔斯的小说十分注意对词的研究,总是带有浓厚的学术气息。罗马尼亚评论家奇奥朗说过:“作者为曾经所写的东西而写的东西有时比他们的作品更有价值。”在《写作与革命》里,索莱尔斯为我们深刻地论述了文本写作的概念和这两本与中国文化有关的小说。在他看来,中国文化的实质就是“没有上帝,没有法律”,汉语是革命性的语言,汉字既不是概念,也不是空洞抽象的符号,它可以摆脱表达机制的限制,体现行动的活力。这种别出心裁在法语作品里插入汉字的做法,与异国情调毫不沾边,索莱尔斯之所以留下中国的痕迹,其目的并不是希望产生一种引人入胜的效果,而是为了表明“抑制本能的回归”,一种从内外触及西方的语言系统,并开始对它进行深刻的反思或超越,在这里,索莱尔斯强调的是一种无声和沉默,这种无声和沉默能够让读者理解更多的东西。《写作与革命》一文,后来与福柯、巴特、德里达、克丽丝特娃等人在《原样》杂志上发表的文章一道,被收集在“原样派”的纲领性文集《全体理论》里。
在进行“反文学”创作风格的时候,索莱尔斯曾一度摒弃冗长的描写,尤其是强调元音的发音方式。他从根本上摆脱了文学创作的理性束缚,通过这种“无法卒读”的方式,使读者的注意力全部集中到听觉上去。他对所有东西都很感兴趣,十分留心身边的所有事物和所有细节,就像纳波科夫所说的,他对怎么起床,怎么渡过上午和下午,以及晚上的安排等平凡的琐事都感兴趣。在他的笔下,语言的反刍带来了一种神奇的现象,为了抓住一天,抓住每一个时辰的每一个细节,为了把个人原因引起的内心剧烈震动全部细腻地表现出来,索莱尔斯在《天堂》里开始了简直可与音速相比的“自动创作”。这部作品的篇幅很长,但没有一个标点,也没有一个段落。在这“胡子连到眉毛”的语言里,在这“一泻千里”的节奏里,索莱尔斯体验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快感和乐趣。他的这种创作方法是从1972年开始的,也就是从写《法律》开始的,那时,他反复阅读了乔易斯的小说,反复阅读了但丁的作品、圣经和其他一些先知先觉的文章,《天堂》一书,就是他在阅读了这些文学技巧特别高超的作品之后“一气呵成”的。从第三部作品《戏剧》开始,索莱尔斯的小说结构一下子就变得晦涩难懂,读者几乎无法把握“这组史诗”,故事的情节是片段的、不连贯的,《戏剧》的匠心很大程度上旨在它的结构,①在这部作品的背面,细心的读者会发现这样一句解释:“这部书是由六十四首瑕瑜互见歌曲组成的——尽管如此,人们仍把它比做国际象棋里六十四个黑白相间的方格。用这种写作方式来串联一个个片段,目的是想用包容性很强的语言来揭示一种快速出现的思想。”索莱尔斯的语言跟“醉汉诗人”阿尔托的一样,是多元的、多声部的、不确定的和流动的。在评论阿尔托无序和无定向性的语言时,德里达曾说过:“阿尔托的呐喊给我们所预示的,是用‘存在’、‘肉体’、‘生命’、‘戏剧’和‘残酷’的名词依次连接在一起的,在发疯和写作之前,那是一种艺术的意义,但它还没有产生其他作品;那是一个艺术家的存在,但它还没有通向其自身以外的道路或经历;这是一种作为躯体言语的存在,一个作为戏剧本身的存在,一个作为文本戏剧的存在,因为它不再受以前的作品、某个构造性文本或构造性话语的控制。”
索莱尔斯提出的“文本写作”的理论,实际上是“原样派”集体智慧的思想和理论结晶。索莱尔斯反传统的作品刚发表的时候,能够读懂它们的人并不多,要不是福柯、巴特、德里达、克里斯特瓦等人不厌其烦的评述,要不是《全体理论》的发表,他的许多作品恐怕至今仍然是读者难以企及的“天书”。1960年,他与其他一些年轻人创办的《原样》(Tel quel)杂志,是20岁至40岁之间的年轻人的所谓“原样派”进行战斗的一个重要的理论阵地,“原样派”竭力主张一种新的写作理论和写作技巧,即通过研究文学性文本产生的方式,为我们彻底地破除了传统文学概念的神秘性,而且为我阐释了一种全新的阅读方式。如,罗兰·巴特曾断言,只有“不可卒读”的文本才能够体现文学的终极目的,因为它向读者的期待心理进行了挑战,罗兰·巴特通过“写作零度”和“作者之死”等概念,彻底地消解了作者在文本中所起的主体作用。①“原样派”所竭力主张的这种阅读方式,是文学走向主观主义和印象主义的第一个重要尝试。带着强烈的革新愿望和强烈的深入研究的历史使命,索莱尔斯在他的文学理论里不仅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的文艺观,而且借鉴了当代语言学和经济学观点。1967年,《原样》打出了“科学/文学”的招牌,这本杂志虽然于1983年更名为《无限》(L'infini),但只是办刊的单位由原来的瑟伊出版社变成了现在的伽利玛出版社,其根本宗旨并没有根本改变,观点也没有太大的变化,它不仅是一部文学杂志,里面还刊登了大量的科学、艺术、政治、哲学等方面的文章,而且许多文章都是文学、哲学、政治和艺术的结合体。当然,文学所占的比重最大,因为在索莱尔斯的眼里,文学的产生先于哲学和政治,人们可以用文学去观照一切,认识一切,可以从中寻求主观的深层的真理。哪怕有千百万政治、经济、社会方方面面的争论,但相较而言,人们偏爱从文学和艺术中去寻求事实的真相。几十年来,无论是《原样》,还是《无限》,都十分注重创新,注重具有现代意义的思想,积极培养出了一批非常杰出的作家,尤其是享有国际声誉的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文艺理论家。
索莱尔斯是个不断追求创新的作家,其风格也在不断发生巨大变化,他曾赢得了“创新者”的称号。他的第一部作品《挑衅》,是一则简短的故事,但是真正让他在法国文坛崭露头角的,是他的另一部长篇小说《奇怪的孤独》。在这部作品里,作者为我们描述了一个土里土气的乡巴佬初到巴黎的情形,尤其是那种孤独、生活没有保障、披星戴月、日夜奔忙的痛苦经历。其完美的古典风格一下子赢得了法国文学界的高度重视,尤其是得到了弗朗索瓦·莫里亚克和路易·阿拉贡的称颂。本来,《奇怪的孤独》的作者可以凭这种风格无限地创作下去,但是他没有这么做,而是走了一条别人没有走过的艰难而曲折的道路,不过,他当时没有告诉任何人。只有认真阅读了《原样》杂志之后,读者才能够明白其风格“波动”的真正动因。对于把创作当作模仿而不是当作使命的索莱尔斯来说,文本的基本模型是存在的,写作只不过是一种填充练习而已,但是,他是个典型的不安现状的文学革新者,他反对故步自封,他不愿成为某某流派,不愿成为“新小说派”,也不愿成为“新新小说派”。记得《女人》里有这样一句话:“我们反对传统文学,我们反对现代派,我们创作的目的是为了文学”,这话实际上就是索莱尔斯本人的艺术追求。
索莱尔斯在风格上的“波动”或“自我否定”耐人寻味。他曾从传统突然过渡到反传统,后来又从反传统一下子回到传统,他以一种近乎神秘的方式惩戒了文学。结构主义大师罗兰·巴特似乎对他很了解,曾为他写过一个小册子《作家索莱尔斯》,他在纪德式的“摇摆”和索莱尔斯的“变化无常、出尔反尔”之间划了一条界线,称索莱尔斯是无法辩护的。所谓“无法辩护的”可以这样来理解:即不应该去为文学辩护,因为它的特点决定它是“有罪的”,记得巴塔耶也说过同样的话:“文学是罪恶的帮凶,它是不可能用道德的形式来进行辩护的”。在文学创作上,索莱尔斯极力反对学院派,常常使用一些不规范的语言来表示他在语言上的革命。他反对改革世界、人生和人类本身,要求一切原封不动,希望通过文学来获得世界,即获得“原样”世界。他播下了先锋主义的梦,希望把文学和革命有机地集合起来,主张任何复杂或细致的判断都不能使用这种一成不变的陈词滥调的语言,文学创作必须符合现代实际,必须表现世界的本来面目。索莱尔斯深受普鲁斯特和乔易斯的影响,极富创新精神,想法也十分特别,他甚至还希望用他以前使用过的形象来拼凑一个索莱尔斯,用他的语言来创造一种社会学。《公园》(1961)是一篇小说体的诗,其思想性和连贯性都不受拘束,读者已无法找到他的成名作《奇怪的孤独》里的那种古典气息,《戏剧》是一部小说式日记,却不是小说,诗和小说被作者紧密地联系在一起。1972年,索莱尔斯曾来过中国,中国的古典文化和古典思想,尤其是中国古典文字,对他的文学创造和理论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但是出人意料的是,自1983年起,他连续出版了一系列具有传统风格的小说。《法国女人的爱情》讲的是一个法国人和一个美国女人之间的爱情,是一本十分纯洁的书。这对恋人生了一个女儿,名叫法兰西,然而法兰西长大后并不认识他的亲身父亲,他们生活在一起,后来竟发生了两性关系。新出版的《女人》有了标点,有了大写字母,也有了段落,再也不是那种无法下读的文章了,此后,他出版的《游戏者的肖像》、《绝对的心》等作品可读性十分强。
索莱尔斯在法国文坛是个有争议的作家,甚至不受欢迎或被孤立,人们无法接受的尤其是他风格上的“波动”。1970年,他由让普及出版社出版了《奇怪的孤独》普及本,而且还加了个说明,说什么当时他之所以署了假名,是因为他在创作那本书的过程中遵循了腐朽的传统写作风格,做了一件违心的事,这也是他为什么长期站在其对立的立场上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有人曾用“在一些人面前显得才智过人,在另一些人面前像是十足的大傻瓜”概括他,然而,索莱尔斯对这些走极端的“新闻语言”和当今的文学评论嗤之以鼻,也有人曾用“夹在指缝里的肥皂”来形容他,索莱尔斯对这种比喻似乎倒也乐意接受,他觉得这个比喻很形象,因为它像鳗鱼一样难以捕捉。不过,指责索莱尔斯的最主要原因,相较而言,倒不是他创作风格上的“波动”,而是他的为人,尤其是“出卖”他的老师和朋友的卑劣行为。在他所写的文章里,有很多情节涉及到罗兰·巴特和他原来的那个团体里的拉冈和阿尔图斯,把他们的私生活竟然公布于众。索莱尔斯把阿尔图斯视为神秘主义者和修道士,把罗兰·巴特说成是同性恋者,把拉冈看作老年痴呆者,在他的眼里,法国的知识分子的命运太惨了,把他们的不幸的命运公布于众完全是出于善意,完全是他应尽的义务,而不是一种背叛行为,因为小说家的任务就是把想做的事变为现实,因为读者总是希望从文学和艺术里,特别是从作家的身上找到深层的主观真理。索莱尔斯对自己的“欺骗行为”感到心安理得,他认为那些隐瞒事实真相的伪君子才是最可恶的,早在《奇怪的孤独》里,他就写过这样一句话:“欺骗,是我长期以来的座右铭”。在索莱尔斯看来,欺骗是他的一种正常的权利,因为整个社会本身就是一种巨大的监视体系,全人类都在犯罪,犯罪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主要化学物质。在《法国女人的爱情》里也有类似的一段话:“每个人都在监视每个人,每句话都在被传播,任何一点细微的变化都会被记录下来,这对于一个作家来说,就更糟糕了。”索莱尔斯把“欺骗”视为一种使自己销声匿迹的权宜之计,视为为自己建立自我保护体系的一个重要手段。
索莱尔斯的“文本写作”观,彻底地否定了文本的终极意义。在他的眼里,任何文本只不过是一个铺天盖地巨大意义网络上的一个纽节,它与四周的牵连千丝万缕,无一定向。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一种没有中心意义的、快节奏的、狂热的语言冲动,以及一种纯净的、超脱的语言境界,成了索莱尔斯竭力主张的艺术追求。通过对文本之间的相互关联性,通过对作者和读者概念的更新,以及通过否定语言的终极意义,索莱尔斯彻底地否定神、权威和理性。而他所神往的摆脱一切传统的束缚和放纵个性的写作方式以及自由阅读的方式,又不可避免地使他陷入到另一种强调“个人性”的泥沼。这种文本理论带来的悖论格局,无庸置疑,迫使他从“反文学”又回到了传统风格的创作。
①Claude Mauriac:l'alittérature contemporaine,Albin Michel,Paris,1969,pp.334-345.
②方生:“法国的‘如是派’对中国的理想化误读”,《法国研究》第二期,1999年,第53页。
①廖星桥:《法国现当代文学论》,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333页。
①周宪:《20世纪西方美学》,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380页。
